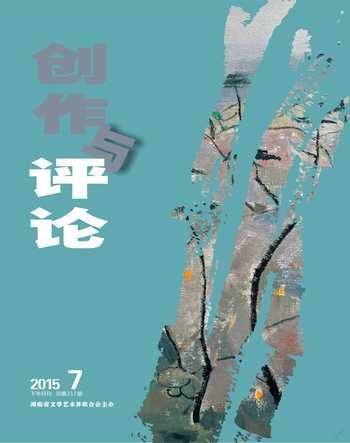是控诉,还是忏悔?
2015-05-30魏春吉刘进才
魏春吉 刘进才
乔叶的小说《认罪书》一经发表,迅即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和一致好评。有人认为《认罪书》是她本人也是整个“70后”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文本而言,有评论家指出《认罪书》内在的幽深和旁及的宽阔形成互动互映;还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隐藏了一位女作家向历史迂回进军的雄心。作家李佩甫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心理扫荡意义的小说,是乔叶在个人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小说的确不负众望,于2013年度获得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在我看来,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反响和热议,这部小说的魅力不仅在于以上所述的诸种要素,还在于一个“70后”作家以关注当下的方式回溯历史——尤其是那段在共和国历史上乃至在世界历史上也堪称独异的不堪回首的文革历史,作者采取了富有意味的叙述策略进入历史记忆,使家庭伦理题材与文革历史记忆以及当下的社会事项交互汇聚,小说文本回荡着历史拷问、现实批判和道德救赎的多重声音,由此行成了它的广袤和幽深。
一、小说的叙述策略:历史记忆如何可能?
对于作家而言,或许越是非常辽远的历史则越能提供一个想象和驰骋的空间。作为一个“70后”作家,叙述文革历史似乎隔了一层。对于乔叶而言,进入文革历史则需寻找一条恰切的小心谨慎的途径。乔叶说《认罪书》是她“写得最辛苦的作品”。我想这辛苦不仅仅是一个长于散文写作的作家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所面对的文体转变——诸如对于小说情节的构思、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锤炼、结构的经营等,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文革后的作者如何有效地进入文革历史书写。在这方面,乔叶精心营构的小说叙述提供了一条进入文革历史书写的便捷而有效的途径 。
历史能够被后人得以记忆或留存,一是靠口头讲述,一是靠文字书写。《认罪书》在叙述机制上刻意经营,不但达到对文革历史的书写意图,也严厉拷问了在极端历史情境中庸常人的卑琐人生和丑陋人性,小说的批判锋芒直逼当下那种阴魂不散仍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国民心态。
小说开头的叙述以“编者按”的形式交代了这部书稿的来历,可谓是作者以假乱真、煞费苦心的叙事。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叙述方式中并不鲜见。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开端“小引”,鲁迅就首先交代了日记得来的途径,正文中展示的十三则日记,通过狂人之口由此展开了对中国封建家族制度振聋发聩的猛烈批判。茅盾的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开篇也是采用了类似的叙述:
这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整抄既毕,将付手民,因题“腐蚀”二字,聊以概括日记主人之遭遇云尔。①
这种有意向读者交代文本来历的叙事方法,是对于古典小说上帝式全知叙述的一种挑战,因为叙述者是一个有限的个体,他/她知道只是有限于自身的生命经历,同时,这种得来的文稿或听来的故事也造成了一种似真的假定历史情境,以便引领读者顺利进入文本。
《认罪书》开篇“编者按”以一个编辑收到一位已经死去的作者的文稿,开始了故事讲述。这位作为叙述者的编辑从文稿的定名《认罪书》,到书中陌生词语的注释都做了参与写作工作。尤为可注意的是:这位编辑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和感受:“虽然把它当成了小说来出版,但在读的时候,我是按照自传来读的。这里面所写的一切,我都不得不相信是真的。……总而言之,这部作品超出了我的阅读常规。我只能说:如果这是个自传的话,那就是个很特别的自传。如果这是个小说的话,那就是个很特别的小说。”作为读者,我们非常清楚:这是作者在自己谈论对自己这部小说的阅读感受,这种类似于元小说的叙事观念事实上是作者与读者未读之前事先达成的一个阅读契约,一种把虚构的小说作为真实的自传来读的“似真”契约。借此,我们才会在打破阅读常规中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阅读契约,读者才会跟随作为70年代的作家所操纵的叙述者进入历史书写,从而获取历史记忆的可能。
《认罪书》的文本可以从文字的书写和表述中划分三个组成部分,主体宋体字部分是金金的自传,编者注手写体字迹是编者听从金金的要求对陌生词语的注释,另外是金金原稿中与主线部分相对游离的文字,文本中以“碎片化”手写体字标明。就小说文本中的注释而言,中国现当代小说早已有之。周立波反映东北解放区土改斗争的小说《暴风骤雨》因运用了许多生僻的东北方言,在小说正文中每每以页下注释的方式详细解释方言土语的内涵,以免造成其他地域读者的阅读障碍。韩少功的《马桥辞典》则是以词条的形式结构文本,政治及地域词语的注释本身即是小说的主体内容。阎连科的《受活》也以“絮言”的形式主要对小说中地域方言以及对历史专有名词进行了必要的注释。但《认罪书》却别具深意,与前此判然有别,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究耐人寻味的划分。如果历史可以分层的话,中国历来就有正史与野史的划分,当下所谓宏大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历史的划分庶几近之。照此分层,《认罪书》的主体部分金金的自传是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书写,而“编者注”部分则是关乎历史、政治、语言(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等近乎正史的历史宏大叙事,“碎片化”的文字则是金金以个体独特化的心理视角对历史、社会、人生等反思性的省察,三者共同构成了对历史整体性的把握和叙述。“编者注”和金金的主体叙述之间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相互阐释的互文本关系,二者共同推进了向历史深处开掘的多种可能性。金金和梁知第一次正式在咖啡厅见面,梁知为金金找到了在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工作,金金对于梁知的好意心存疑虑,二人就“天上会不会掉馅饼”展开了富有意味的对话,日常生活场景的对话中却聊出了1975年驻马店大洪水特大历史灾难,直升机给灾区空头食物——可谓是天上掉馅饼。小说叙述至此,“编者注”对75·8洪水进行了详尽注释:
【编者注: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在一次猝然降临的特大暴雨中,包括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在内的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数十座小型水库、两个滞洪区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1015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超过8.5万,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有专家认为,酿成惨剧的主要原因是:一、设计失误;二、预报失误;三、忽视忠告。】
这段镶嵌在小说主体故事中的叙述,像一把锋利的刃子直逼历史深处,发掘出造成历史惨剧既是天灾更是人祸的深层缘由,在看似客观冷静的历史叙事中回荡着严厉而激越的审判声音,诸如此类的编者注构成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同时也是对历史记忆的打捞,通过在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中引入注释,使小说叙述如行云流水,了无雕琢之印痕。不要小觑这种近乎碎片化的注释,它在小说文本中不是可有可无的叙述点缀,如果把这些“编者注”集中排列阅读,简直可以称之为一部凝练的共和国小史,其中关乎合作社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批判黑五类、黑帮分子剃阴阳头、现行反革命、学制缩短教育革命、三忠于四无限、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新世纪文革忏悔事件、瘦肉精事件等已经发生过的宏大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些在当时引起社会极大动荡、引发人们心灵极大震荡的历史事件逐渐地被遗忘、涂抹乃至改写,如果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么,《认罪书》对历史的书写则意味着作者打捞历史记忆的忠诚!当然,作者打捞的不只是那些枯燥乏味、压抑人性的宏大历史事件,也有对民间日常生活场景书写,比如对1960-1980年代女孩子们最喜欢的翻花绳和抓子儿游戏注释,在怀旧情调的书写中隐现出诗意的温馨。
正如小说开端所言,如果说《认罪书》的“编者注”对历史的书写可以直接借助“中华解词网”从而避免了作者文革历史经验不足的弊端,那么小说主体部分关涉文革的日常生活书写,作者通过叙述人称的不断转换采取了有效的文革历史的叙述策略。
《认罪书》以一个看似俗套的“始乱终弃”的叙述模式起步,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跟着金金复仇的脚步,这个在中外文学中已经习见、几乎烂熟的叙述模式逐渐转换成一个带有侦探和悬疑色彩的小说类型。这种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的叙事方式增强了长篇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使小说回归到讲故事的原初状态,与那种故弄玄虚、玩弄技巧的所谓“先锋性”叙述相比,这种最朴素的写实主义的叙述仍显现出其持久的魅力。当然,《认罪书》与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并不相同,乔叶非常机智也富有创造性地采取了复调式的多声部叙事,在一个故事的多种讲法中实现了对历史多面性、丰富性、深邃性的开掘和揭示。
梅梅的故事在不同叙事者的口中各有侧重,一个故事却呈现出不同的叙述。
在梁新的叙述中妹妹和哥哥梁知是一般的兄妹关系,梅梅民办教师清退以后就去外地打工。梁知的叙述则是超越了一般的兄妹之情,梅梅清退民师后到南方打工去了。两个兄弟的叙述都有意省略了梅梅在钟潮家做保姆被侮辱被损害的经历。在老姑的叙述中,梅梅和梁知开始情投意合,后来梁知考上大学,梅梅未能考上,顿觉在梁知面前矮了一截,孕育了后来的悲惨结局。作为文革亲历者,老姑的对文革的叙事显然具体详实。当事人钟潮的叙述又是另一番面貌,梅梅并非是民师清退,而是张小英为了儿子梁知晋升科级特意为钟潮送的一份软礼,在钟潮的软硬兼施下,梅梅的妥协也是出于对梁知的爱。作为文革的造反派,钟潮第一人称叙述了梅好为救父亲所经受的非人折磨,不但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疯狂,也弥补了作者对文革生活经验的匮乏。婆婆张小英的叙述则更是另一种说法,梅梅和梁知的关系是梅梅主动勾搭的结果,把梅梅送到钟潮家做保姆也是为了以后给梅梅找个好工作,对于梅梅被损害的结局,张小英则认为梅梅太精明,一心想当上市长太太。小说中即便是对梅梅死亡方式的叙述也有病死和跳楼的不同说法。
一个故事却有着面貌各异的多种叙述,每个亲历者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要么回避、要么辩解,要么修饰,要么强调。如果说曾经发生的原生态的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话,那么,对于历史的叙述则呈现出众说纷纭的主观性。历史难道真如后现代史学所声称的那样——一切历史都不过是叙事而已?在我看来,《认罪书》在多声部众声喧哗的叙事中则是一步步逼近历史的真相。每一个叙述各异的片段相互拼接共同完成了历史的叙事。小说中不时回荡着作者关于历史哲学的深入思考:“据说人都是在为历史服务,可历史的主体到底是什么?不还是无数的人么?人是在为历史服务,历史不也是在为人服务么?”这是主人公金金的沉思,也隐含了作者自己对历史的考量。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也关乎历史实在与历史书写的历史哲学命题,同样关涉到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体的如何面对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间绵延性问题。小说中金金与申明的对话透露出作者对历史书写如何可能的资格性探寻,金金质疑没有文革经历的申明主办“我们”专栏、谈论文革历史的合理性问题,申明则反唇相讥:亲身经历固然是认识历史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是劣势,需要付出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努力。申明对追问历史意义的强调进一步凸显了历史进程与个体生命成长类似的同构性关系:“历史其实也是当下和未来。历史虽然死了,但是也一直活着,而且活得比什么都长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是由一段一段的历史累积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事实上,金金的追问可能是隐含读者的质疑,申明长篇大论的申述正是作者乔叶谈论文革、追寻历史的合法性申辩,这种带有元小说的叙事机制使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乃至作者、文本、人物及读者相互之间构成了饱满充盈的张力。
我们前文已经论及,凭借着靠口头传承或文字书写使历史记忆得以留存。但历史还可能以另外一种反仿的滑稽样式出现,这构成了历史的反讽。旅游新景点拾梦庄的开发就具有这种历史的戏谑性。原本是惨烈的文革历史,如今却成为人们开发利用、嬉笑谈资的生活作料,人们谈论起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不但没有丝毫的忧伤悲戚,眉梢和眼角还闪烁着自豪的微笑,这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历史,也颠覆了历史,实质上是对历史记忆的涂抹和遮蔽。
从小说的情节主线来看,金金寻求真相的过程也是作者直逼历史、恢复历史记忆的过程,小说通过以上所述的一些叙事机制实现了对文革历史记忆如何可能的独到性思考。
二、历史中的人性:道德救赎何以实现?
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念总是把历史看成是人类的作品,看成是人类意志和心智的产物。如果我们遵循并信奉这样的历史哲学,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独特生命体验和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个体如何在社会历史境遇中进行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既然历史是人类的作品,而每一个个体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也是每一个生命个体必须思考并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否则,人们在这个普遍沉沦日益浮华的尘世中就会屡屡犯错而不自知。
以此作为参照,《认罪书》中塑造的这些庸常的小人物尽管没有犯下滔天的大恶,但也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也犯下了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我们先看看作为小说主人公的金金,自从遭到周围人嘲弄她为“野种”,便狠毒地大骂自己的亲生母亲“怎么那不要脸么”。小小年纪开始说谎话,欺负女生,甚至要把自己的生父“哑巴”推入井中。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以自己的身体为资本主动与不爱的男子上床,诱惑梁知并偷偷怀孕逼梁知在这个并不道德的婚外情上乖乖就范。一个个精心算计和谋划失败之后,又和梁知的弟弟梁新结成不伦之婚姻,想以此折磨梁知逼使他走向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当梁新得知真相之后,羞怒之下出车祸而死,梁知也割腕自尽。金金诱惑梁知这一小小的举动,就像那最先倒掉的一张多米诺骨牌,引起了此后所有的倾覆。以此看来,金金每个毛孔都似乎充满阴戾之气、流淌着复仇的欲望。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同样犯下了庸常人的恶。梁知和梁新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和罪恶制造者,他们兄弟俩不是用绝情的方式同样把自己的妹妹梅梅推向了死亡的窗口么?梁文道和张小英也是眼睁睁看着梅好走进群英河,不去阻拦,不去施救,这冷漠无情的灵魂麻痹症同样折射出人性深处的恶。钟潮在文革中参与侮辱梅好,后来又诱奸霸占梅好的女儿梅梅,可谓是孽债累累,罪恶深重。即便金金的四个哥哥,也为了抢占母亲临终托付给金金的房产采取了处心积虑的策划。
金金进入梁家的过程是自身复仇的开始,既是探秘的过程,也是发现罪恶的过程,当然,作者的用意不在于一味地揭开伤疤、展览罪恶。罪恶已经产生,面对每一个庸人所犯下的罪恶,我们是沉浸在无休无止的谴责、控诉、声讨、以牙还牙上,还是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开始反躬自省,回归良知、自我归罪并走向忏悔救赎之路?答案当然是后者,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忏悔和救赎的可能,没有罪恶,也就根本谈不上忏悔和救赎。
与基督社会中所说的原罪不同,《认罪书》中人物的罪过是庸常人在社会生活自己主动犯下的罪恶,有许多罪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人虽然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自我选择的能力。张小英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让梅梅到钟潮家做保姆。她之所以要这样,完全处于个人的私欲的考虑——拆散梅梅和梁知的恋情,通过讨好钟潮使梁知获得晋升。梁知梁新兄弟得知孤苦无告的梅梅在钟潮家饱受欺凌侮辱,不但不为妹妹伸张道义,反而以绝情的方式扭送梅梅到南方打工了事。这是因为梁知在源城要保住自己的局长位置,梁家要保住外表华丽的面子。金金即使和梁知恩段情绝,也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属于自己的人生,没有必要非得嫁给梁知的弟弟梁新,但由于是复仇欲望的驱使,她点燃的仇恨的烈焰烧死了梁知和梁新,最终也埋葬了自己。
罪恶并不可怕,关键是施恶者对待罪恶的态度。金金坠入自己亲手制造的罪恶深渊,在窥见自己及他人所犯的一系列罪孽中幡然醒悟:“要认罪,先知罪。”梁新的死打开了金金和梁知忏悔和救赎的大门:“我,和梁知,我们就是杀死梁新的凶手。那辆别克就是我和梁知所开。我和他都是驾驶员,都是发动机,都是滚滚向前的轮胎。”“我们隐形,让他以最迅疾最决断的方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别克。”当梁知双膝久久地跪在弟弟梁新的坟前直到夜幕四合,他暧昧不明的良知已经发现,开始已踏上道德救赎的自新之路。梁知卸下人生的伪装和人格面具,在和金金、安安享受“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本真生活中获得了生命的片刻宽慰,他割腕自尽最终以死亡偿还了人生的债务,在肉体的涅槃中得到灵魂的进化与提升。
并不是所有的犯罪者都会自我归罪,走向忏悔自新的救赎之途。这才是最让人担忧和可怕的事情。没有悔过,不但罪恶难以避免和消除,而且历史的罪恶的幽灵还会以同样变本加厉的面目在人间徘徊游荡。《认罪书》中金金是一个彻底地审视自己的罪恶,并向世人公开自己罪恶的悔罪者。也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她还去看望寂寞的梁远、孤独的老姑、梅梅的遗孤未未,并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为自己的哑巴父亲立碑献花和祭奠。金金以自己的行动展演了“忏悔—赎罪”的逻辑历程:由犯罪施恶到人性发现、归罪忏悔,再到赎罪拯救最终得以人性升华。小说中其他人物对待自身的恶,不但没有如金金那样走向自新和救赎,而且对自己造成的恶或辩解,或隐瞒,或推脱责任,或依然故我。那个叫王爱国的阴鸷女性,以满身的暴戾和凶残虐待梅好,是造成梅好发疯致死的罪魁祸首。但,多年以后的王爱国们,有的避谈及文革,有的忙于赚钱,那个下岗之后打扫厕所的王爱国无疑是文革时期王爱国幽灵的复活——霸道蛮横、欺软怕硬、尖酸刻薄。与王爱国一道,在文革时期参与折磨虐待梅好的甲乙丙丁们,死去的已经死去,活着的要么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过把自己也打扮成一个受害者,要么以集体的名义推卸历史责任,得过且过,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生。钟潮亲眼目睹了王爱国们失去人性的暴行,在事后的追忆中不但没有丝毫的忏悔,而且在自己所谓“没有对错”、本能驱使的借口中轻轻打发掉本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也许正因为没有历史的担当和反省,没有对罪的自觉认知,才使他在多年以后以近乎命运循环的形式使梅好的女儿梅梅又沦落到他亲手制造的罪恶渊薮。这种对罪的推脱、辩解、遗忘乃至否认,正是小说作者严厉拷问的道德主题。乔叶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指出:“《认罪书》的本质和道歉有关,和忏悔有关,和反思有关。”“我最想让小说里的人和小说外的人认的‘罪,也许就是他们面对自己身上的罪时所表现出来的否认、忘掉和推脱。”作为沉沦在世的庸常之人,完全杜绝对他人的伤害似乎难以达到,但是如何直面罪过,否认、忘掉、推脱则是另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正是因为人类是一个具有灵肉二元的合体,动物的兽行欲望本能与人的向善的神性总是在发生永无休止的交战。为此,中外文化史上对人身上充溢着的恶都有具体的规训和警醒。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像学界有人声称的那样缺乏忏悔因子,从孔子的“过则勿惮改”到曾子的“一日三省吾身”,从儒家的“返身而诚”到佛教的“忏悔”“自陈过”,无不蕴含着忏悔的萌芽。尽管和基督教世界中的忏悔观念不尽一致,但忏悔都是以坦白公开的形式,以认罪和悔罪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主动性行为,无论其遵循的价值尺度的终极根据是指向神圣的宗教世界——佛祖或耶稣,还是日常生活的世俗社会,忏悔的精神一直灌注在古今中外的文明之中。
忏悔是达到道德救赎的必要途径,灵魂的忏悔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主动性行为,不是旁人呼吁胁迫的结果,也不是因惧怕报应轮回的个体性救赎,真正的忏悔应该是超越了末日审判的恐惧,对生命本体有了深刻领悟。真正的忏悔者不是审判他人,而是严厉地坦露解剖自己,是直面灵魂深处的责任担当,是悲天悯人身怀大爱的彻悟和洞明。照此观念,则金金的忏悔是一种主动性的认罪,可谓达到了基督教神学所说的“完全性忏悔”,而梁知的忏悔最多知不是一种“不完全性忏悔”。梅梅的故事是一个被杨家乃至社会其他人共同遮蔽的故事,金金这个梁家局外的闯入者逐步揭秘被发现了这个故事。随着历史记忆的逐步发掘,梁知才被迫承认自己把梅梅推上了绝路,这种认罪显然有迫不得已的成分。既便是梁知初识金金,涌动起从与梅梅长相相近的金金身上找回赎罪的冲动,但这虚伪肤浅的赎罪行为反而滋生起新的更大的罪恶,旧罪未认,又添新罪。“解铃还须系铃人”,可见,主动性的忏悔和个体担当才是抵达灵魂提升和道德救赎的必备之途,正如《认罪书》作者的题词:“要认罪,先知罪。”“要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认”就是主动承认,主动领受,主动受罚。因为这主动不但关系到历史,也同样关乎我们当下的时代,有人呼唤“这个时代,我们要自己解毒”,诚哉斯言!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究《认罪书》中人物作恶的性质,每一个人的为恶并非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而是一种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人的恶”,它有别于“极端的恶”或“根本的恶”,“平庸人的恶”可以用自私、贪婪、渴望、权利欲望、怯懦等个人的罪恶动机来解释,面对邪恶的沉默与不抵抗也是一种恶。因而,“平庸人的恶”不是从政治体制的社会结构功能来追究历史罪责,而是从人性层面来拷问政治领域的道德集体和个人的责任。作家乔叶似乎非常认同“平庸人的恶”这一概念,她手持人性的解剖刀冷静而锐利地解剖着人性的软弱和丑陋,自私与卑劣。倘若我们以历史的“了解之同情”去观照并追溯《认罪书》中人物的恶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金金的恶与她早年身份认同的焦虑不无关联,作为世人眼中的一个“野种”,她的内心也许早已斩断了与父亲连接的纽带,这种带有原罪的“弑父情结”的恶的种子已经深深植入了幼小的心灵中。就此而论,她在杨庄的被嘲弄、被侮辱并非是她自己的罪过,那么,为何要让一个无辜的孩子内心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创伤性噩梦,这,才是金金此后“平庸的恶”的根源。照此推断,自身的恶并不必然地有自身所导致,他人的恶也会导致另外一些人的恶。在此,我并非刻意为庸常人的恶进行道义上的辩护,我试图强调的是:在一个良知毁灭、伦理颠覆的时代乱相中,每一个人都有意或无意间可能成为自身的或他人“平庸的恶”的制造者。就此而论,我们对于他人的恶的拷问和历史的反思必须从自我开始,这也是小说中人物金金的发现:“我发现了他们的罪。但是,现在,我居然也发现了自己的罪。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与他们为敌”,其实“我是在与自己为敌,在与自己的内心为敌”。如果每一个人都与自己的内心为敌,忏悔和救赎就不会只是仅仅停留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被社会认可的时代风潮。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个体才有可能抵达救赎的彼岸,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想,这正是《认罪书》带给我们的反省和思考。
注释:
①茅盾:《茅盾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言土语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4BZW1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