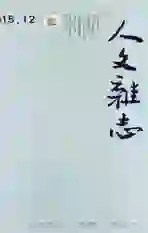汉代初期祀“太一”制度成因考论
2015-04-29朱喆琳
朱喆琳
内容提要 汉武帝时期对“太一”的祭祀高度空前绝后,完成了对国家信仰的初步整合,其制度设计的动因涉及社会信仰、文化传统、政治变迁等多方面因素。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巫术信仰、汉代朝廷的政治理性共同完成了对“太一”至高神格的塑造,反映出制度构建与文化形成的互动。
关键词 汉代 郊祀 太一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2-0126-03
一、汉初郊祀制度形成略述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国家祭祀是引导民众信仰,申明统治权合法,构建国家政治礼制的重要环节。中国三代国家宗教的特点是从自然崇拜中发展出了天神崇拜。①商人将祖先抽象为天神,赋予其管理人间秩序的社会属性。周时,由于道德化的“天”意象过于宏大抽象,“上帝”被保留下来执行天命,天神的神秘性、祖先的宗法性共同统辖国家秩序。
据《史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郊社最初仅奉祀上帝,其他为配食。秦时以雍四畤和陈宝之祀最尊,并“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汉初继承秦制外,刘邦自封黑帝,立黑帝祠,统称雍五畤,郊祀五天帝。又对七国故地神明进行整合奉祀。②武帝对“太一”的祭祀来自齐地方士的建议,出土刻画疑似“太一”神的画像石也以山东为多。③初在琅琊郡设太一祠,后谬忌进奏:“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于是改祠太一坛于长安东南郊。历年后,奉“太一”为至上神祀于甘泉宫,五帝坛环祀周围。而随着后土也被纳入郊祀,郊祀最终演变为共祭天地的“大祀”。国家祭祀体系完成了初步构建,形成以天神、地祇、人鬼为核心的三大祭祀系统,成为后世范本。④
二、先秦至汉初“太一”神格的整合
“太一”一词的出现时间及其神格演变,基于哲学、神话、天文等诸多方面,皆有讨论。珠玉在先,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以证“太一”神格演变。
1.哲学本体论方面
通说“太一”一词约出现于春秋末期。⑤楚简《太一生水》篇,言“太一”生藏于水,不可琢磨,乃万物之母,先于天地,神明只是天地相辅之产物,为“太一”思想之开篇。⑥在道家宇宙观中,太一即“一之又一”,是其先于天地神明的根据。⑦同时,道家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法系重构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0JZD0028)
①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② 李炳海:《汉初异地群巫参与朝廷祭祀的政治文化意蕴——〈史记〉相关篇目的对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③ 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④ 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4年,第11页。
⑤ 谭宝刚:《“太一 ”考论 》,《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
⑥ 韩东育:《〈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与〈老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⑦ 钱宝琮:《太一考》,《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9卷,辽宁教育出版集团,1998年,第202页。
也将“三皇之前”的混一视为 “淳风未散”的理想状态,是上古圣君及封禅之君之时,是将“太一”与上古圣王等同的依据。陈忠信:《〈太一生水〉之混沌神话》,简帛研究:[EB/OL]http://www.bamboosilk.org/Wssf/2002/chenzhongxing01.htm,2013年12月5日。汉代黄老学说将“道”归纳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的状态,并具有君王所需的“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的功用。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8~389页。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楚儒生陆贾关于道与术的论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的说法也与黄老术士的看法颇为相近。《淮南子》中有“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及“帝者体太一”,“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德泽施于四方,名声传于四方”的论述,亦使之兼具了圣王的形象。
2.神话方面
钱宝琮认为西汉初期“太一”方演变为总理阴阳的天神。B12钱宝琮:《太一考》,《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9卷,辽宁教育出版集团,1998年,第209、208页。但“太一”作为神名,早已有见,如《鹖冠子》将“太一”置于“百神仰制”的地位,又如《高唐赋》言:“醮诸神,礼太一”,将其作为至上神与诸神分祀。也有学者据《九歌》的祭颂序列与《周礼》对比,进而证明“东皇太一”的神格。赵晓斌:《〈九歌〉“东皇太一”祭祀渊源考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但是,自古对“东皇太一”的定性即诸论不一,古时神名混同、一神兼有多种神职也是常见的现象。另有学者认为“东皇太一”为东方光明之神,暗指太阳,太阳神崇拜在战国确实相当普及。但《史记·封禅书》记:“晋巫,祠五帝、东君。”《史记索隐》引《广雅》曰:“东君,日也。”即东君与五帝一起祭祀。古时也有木神句芒的传说,为汉时“太一”下佐之五方神,主东为青帝,对应春天。在帛画中,“太一”四周绘有四季神,春神画作青面,上标“事司”。⑧王煜:《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可见汉初,日月神为郊祀陪祀,雍和齐也另有祭祀,与“太一”有明确区分。此外,楚辞神名与出土楚简也存在区别。如包山简所录敚词的神祇序列往往以“太”或“蚀太”最前,第二为后土,即社,为地祇。五祀诸神在中,大水、二天子、峗山在后。祷辞有“举祷太一[羊肤],后土、司命各一牂”,对“太一”的供奉独一无二,且与祷楚先分别进行。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170页。楚人以炎帝和祝融为祖,祝融为颛顼后,据《尚书》载,颛顼整顿巫政,命重黎“绝地天通”,为统一国家信仰活动的开端。也有学者认为高阳即郊社的音变,高阳即为颛顼。涂又光:《楚国哲学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页。通天地之建木生于昆仑,汉代“太一”崇拜也与昆仑登仙传说存在关联。⑧汉代,设五行官神配祀五帝,“火正祝融”对应南方。回看《东皇太一》篇将所祀对象敬称为“上皇”,但全篇对该神形象并未描写,与后续篇章不同。或可推断在战国末年,“东皇太一”的人格化形象与“太一”混沌缥缈的哲学概念是共存的。既然时人认为“太一”神蒸腾无象,则也无法以兴像手法描写。至两汉,“道”彻底神格化为“太一”,民间修仙升道之说也与之衍伸联系。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3.天文方面
作为星名的“太一”也存在争论。甘石《星经》云:“太一星在天一南半度,天帝神。”日本学者证实《星经》关于“招摇”“选戈”的记录与战国之事相符合,但有关“太一”的记录应存疑。[日]桥本敬造:《先秦时代的星座和天文观测》,《东方学报》,1981年,第189~232页。谭宝刚推测“太一”指值岁星。谭宝刚:《“太一”考论 》,《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钱宝琮认为汉代初期还无“太一,星名”的解释。B12李零先生将出土的战国“兵避太岁”戈所饰神人图像认定是《封禅书》所记之的“太一锋”,并将包山2号墓出土的占卜类简文位列首位的神释为“太一”,认为“太岁即太一”,在先秦即兼有星、神、终极物三重含义。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以笔者所见,以星名的“太一”始见于《韩非子·饰邪》:“此非丰隆、五行、太一……岁星非数年在西也。”此处太一作为岁星,未论及与天帝的关系,与《星经》记载不同。且楚简中“太一锋”被视作疾疫之神,“太”既可指星神,也可指鬼神。晏其昌:《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页。可知先秦时“太一”确已作为独立的星名出现,《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天极星即“北辰”,是“政德”的象征,“太一”成为至高神后,相应被比附为该星。天文学界认为“太一”确实措辞不当北极星,但因为岁差,汉时已经离开了北天极。赵永恒:《“太一”星象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张政烺也指出北辰不在紫宫,汉代文学对“紫薇垣”与秦公簋所记“帝之环”的比附于古无证。张政烺:《张政烺文集: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第276页。但足以说明此时“太一”已取得天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其被附会为太昊、泰皇,也应是同一思路。汉帛画对“太一”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人神有序,四时有行的盛景,正是其神格最终上升的表现。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三、汉代“太一”神格整合的制度意义
综上,“太一”的三重属性在先秦时代都已出现,诸家学说共同推动了“太一”神格的演变。汉代将政治信仰整合到一个知识体系之中,唯一最高天神的塑造正是重要的一步,⑨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利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6、114页。具有深刻的制度意义:
首先,汉以“孝”治天下,祀奉五帝无法表明“天子”祭天具有孝道仪式的属性,且五帝祭祀的制度易带来“政出多门”的不利后果。武帝时,政治上对儒家的推崇和对黄老之术的摒弃,必然影响到精神领域的信仰倾向。董仲舒提天人三策,要求国家制度层面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等理念的具体落实加以配合。道家也有将三皇与道家三一相互联系的论述。钱宝琮:《太一考》,《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9卷,辽宁教育出版集团,1998年,第220页。三统说即由董仲舒提出。儒家学说对“道”和“太一”特性的吸收,汉武帝自身对方术的喜好,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中间选择。“太一”神格上升的顶点发生于太初改历之后,信仰和历法的更新都以天文星象为知识基础,秦汉历次易服色、改正朔意在将年始、服色、数度、政治、刑罚等统一。杨英:《秦汉诸家正朔说考》,《秦汉史论丛》第10辑,《中国秦汉史学会第十届年会会议论文集》。奉“太一”为至高神的活动服务于汉家受天命得天下的证明,也符合当时儒家的正统思想和政治需求。
其次,“太一”“后土”的对祭奠定了后世天地祭祀的基础。汉成帝“罢诸淫祀”以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方式,取代了甘泉太一祠和汾阴后土祠,仍基于利用神权统一巩固思想统治的目的。“天”的内涵融入了“太一”囊括的“道”与权威性,其后所称皇天、昊天等,俱是代表“天道”的最高统治名位的变形。西汉中期“太一”的神格逐渐下降,至东汉跌出国家祀典。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51页。随着道教的发展,其多元神格也被重新打散。王煜:《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但是,后世天地对应的祭祀方式依旧带有“太一”“后土”的两相对立的影子,民间“皇天后土”对称的习俗,可看出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帝”“太一”与天;“社神”“后土”与地的关联与变迁,是社会关系从巫到礼、从礼到儒变迁的缩影。
最后,信仰统一是思想统治的前提,对普遍社会尊崇的“神”的认同赋予了政权应然的合法性,本质为一种政治价值的认同。⑨奉祀共同神灵的仪式,具有加强群体认同,促进社会秩序一体化,强化社会政治伦理的作用。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6页。汉承秦制,实行一君万民的垂直统治秩序,其国家祭祀必然贯彻这种模式。国家祭祀制度在汉代初年的变化,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交融影响下,统治者基于政治伦理和情感偏好对国家宗法制度构建的过程。巫术的国家典制化之下,统治者通过血缘和道德标榜其权威来自于神,也受制于神的内涵。至上神或许基于王权的选择,诸神则自于普遍创造,庇护众生的社会需求与国家法权相遇时,其超验性反作用于法律的演变,为政治划定了道德限度。篇幅所限,诸因素对汉代郊祀礼制度确立作用的可能性,尚需进一步补证。但可明确,“太一”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传统为时人所熟知和利用,服务于将共同国家意志与皇帝政治制度由上自下一以贯之的重要目的,是大一统国家形成必然要求的社会情感基础,也是集权政策高效推行的思想认同保障,统一的国家性祭祀的制度化则为之提供了国家法律层面的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