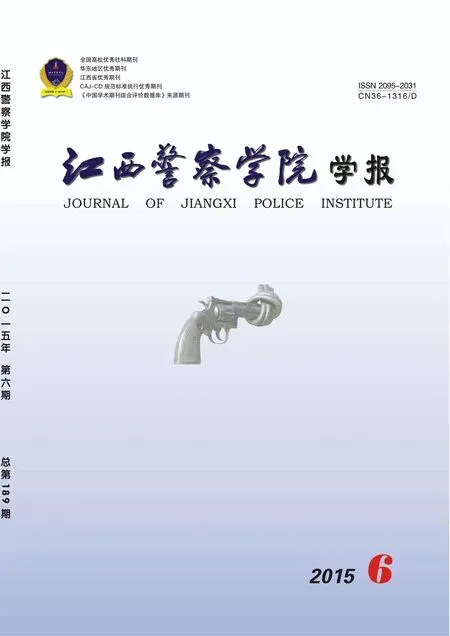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组织行为的认定
2015-04-18岳黎春
岳黎春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任何科技的进步都具有两面性,器官移植在给人类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因活体器官供需的不平衡引起了一些新型犯罪,例如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器官供需的不平衡是现阶段器官移植医疗的现状。器官供需不平衡也是导致人体器官买卖的原因,而人体器官买卖的猖獗又加剧了器官供需的不平衡。为了维护医疗移植秩序,平衡器官供需关系,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但是关于本罪所保护的法益、组织行为的方式和对象,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本文将就这几个问题阐明笔者的观点。
一、健康权抑或医疗移植秩序的法益之辨
学界对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人的身体健康还是医疗移植秩序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所侵犯的客体是人的身体健康和医疗移植秩序双重客体,但主要侵犯的客体还是医疗移植秩序。[1]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系人体器官商业化的行为,导致人体器官成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另外,不符合医疗程序、医疗卫生地摘取人体器官,致使传染病流行,加大器官移植的风险,造成器官移植医疗秩序的混乱。[2]也有学者认为,从我国刑法典的体系来看,本罪规定在第四章故意伤害罪之后,足以见得本罪所侵害的法益与故意伤害无异,应当是人身权利。虽然本罪与组织卖血罪有相似之处,但是本罪对人身的侵害更大,组织卖血行为并未给人身带来明显的侵害。因此,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故意伤害罪的特殊表现形式。[3]上述学者对本罪法益的推导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如王春丽和陈家林所述,从行为的实质推导本罪所侵犯的法益,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是医疗移植秩序;另一种是从本罪在刑法中的既定位置,反向推导本罪所侵犯的法益为人身权利,即张明楷和邓毅丞教授所持的观点。讨论本罪的法益理应从本罪的实质出发,从本罪所造成的危险角度考虑由此推导。罪名的既定位置只是所侵犯法益的参考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因此本罪所侵害的法益应从罪行的实质判断。
本罪从行为来看,既伤害个人的身体健康,也扰乱医疗移植秩序。但是主要侵犯的是医疗移植秩序这一法益。首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了器官捐献供体和受体的权利义务。器官一旦进入市场进行买卖成为换取金钱的手段,违反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基本法理。使国家对器官移植的医疗活动失去管控,致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受到停滞,进而衍生其他严重犯罪。[4]其次,本罪和组织卖血罪非常相近,器官也是只能捐献而禁止买卖的,刑法不惩罚单纯的买卖器官和血液的行为。卖器官和血液是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因此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和组织卖血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惩罚这两类犯罪的原因在于组织者破坏了医疗移植秩序。被害人只有在轻伤结果以下的承诺才有效力,组织者应当对被害人重伤以上的结果承担故意伤害罪的责任。被害人对危及生命安全的器官,例如心脏,的承诺是无效的。因此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医疗移植秩序。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组织行为的体系性考察
组织行为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核心行为模式,也是法律规制的重点。在刑法典中,“组织”的定义因罪名的不同而不同,即使在相同的罪名中,学界对“组织”的定义也有不同见解。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组织’是指行为人实施领导、策划、控制他人进行其所指定的行为活动。组织的手段可以是招募、拉拢、利诱等,但是本罪中不包括强迫、欺骗。”[5]根据本罪第二款的规定,若行为人采取强迫、欺骗手段获取被害人器官,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不再属于本罪的规制范围,因此本罪“组织行为”不包含强迫、欺骗行为。
(一)我国刑法典中的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是指组织者采用招募、雇佣、教唆、引诱、欺骗、强迫等手段将多人聚集起来,领导、策划、指挥被组织者有目的地从事某种犯罪活动并对团伙成员或者被组织者产生控制和约束作用。[6]在组织犯罪中,有些犯罪依我国刑法要求具有多人次的特点,例如非法组织卖血罪的立案标准为组织卖血3人次以上的;[7]但是也有的犯罪并不要求多人次,例如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8]在组织卖淫罪中,不要求组织者是多人,但是要求被组织者必须是多人,至少两人以上。因此组织者是否为多人并非组织犯罪的判断标准。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是指以领导、编制、管理、介绍、安排等方式教唆他人出卖自己的人体器官,或者招募、雇佣他人帮助自己出卖他人的人体器官。换言之,“组织”是指从事唆使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活动。[9]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组织行为”排除引诱和欺骗手段。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在刑法学“组织”理论中的定位
我国只有一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都有关于“组织”的定义。一部法典中,关于同一词语的应用应当保持意思一致,但不同位置、不同罪名中的“组织”又有其特性,很难在一部刑法典中保持完全一致。
刑法总则中对“组织”的定义系对“组织犯”的定义。“组织犯”是与“帮助犯”、“教唆犯”并列的概念,是在共同犯罪中按照在犯罪行为中的分工不同来划分。“组织犯”一般情况下不是实行行为人,而是在幕后进行统筹、分工或者在事前进行领导、策划的人。若要排除组织犯是共同正犯,组织犯必须以非实行行为的组织行为来参与共同犯罪。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不成立共同正犯关系。正如前文所述,本罪中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被组织者,即实行行为人是自愿出卖自己活体器官的人。被组织者出卖活体器官是被组织者作为被害人的自我承诺行为,不构成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组织者在刑法总论“组织犯”的概念中,是出卖人体器官的帮助犯。犯罪行为具有从属性,若作为被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实行行为人不构成犯罪,帮助者自然在法律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不应构成犯罪。因此惩治本罪中的组织者,需要借助刑法典分则中有关“组织”的理论。
刑法分则中对组织犯罪的规定均要求行为人具有实行行为,据此可以将“组织”犯罪分为有组织犯罪和组织型犯罪。有组织犯罪是必要共同犯罪,系指由三人或多人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确立的犯罪,[10]一般表现为集团犯罪。组织型犯罪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必要共同犯罪中的组织型犯罪是指在必要共同犯罪中实施组织、领导、策划、指挥他人犯罪的行为人,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对首要分子定罪处罚,属于广义的组织犯的概念。例如我国刑法典中的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任意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组织行为的,成立具体犯罪的共同正犯。例如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非法组织卖血罪、组织卖淫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组织会道门邪教、组织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等。必要共同犯罪中,被组织的行为往往单独构成犯罪,在任意共同犯罪中,被组织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被组织的行为是出卖人体器官,该行为单独不构成犯罪,只有被组织者组织进行出卖人体器官才构成犯罪,属于任意共同犯罪。同时,在总则中,本罪中的组织者属于“组织犯”的范畴。虽然组织者并非最后导致被害人身体受损的行为人,也不是直接扰乱医疗移植秩序的行为人,但是组织者在该行为中起到了事前的领导、策划、编制、管理和控制作用,例如为供体寻找合适的受体、为受体联系做手术的医生,甚至供养供体直至找到配型成功的受体、组织受体到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在分则中,本罪不符合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我国刑法典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因此本罪属于组织型犯罪。前文中所述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中,“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应当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范畴。将分则所规定的单独犯的既遂类型的处罚范围,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加以扩张的,称为任意的共犯;反之,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类型中,有些犯罪的参与形态本身便预定由多处人参与,对此予以类型化的,就是必要的共犯。[11]必要共同犯罪要求被组织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组织者组织行为人实施该行为也构成犯罪。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被组织的行为是出卖人体器官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本罪不属于必要共同犯罪,而是任意共同犯罪。在必要共同犯罪中,刑法只惩罚组织中的首要分子和起主要作用的人;在任意共同犯罪中,只要是参与了组织的犯罪行为,均是分则中组织型犯罪的惩治对象。
刑法分则中,带有“组织”的罪名有十三个,其中有的是组织犯、有的是组织型犯罪还有有组织犯罪。组织犯实施的是组织犯罪行为,但组织犯罪的人并不都是组织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组织行为才是组织犯的组织行为。
本文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划分到已有的 “组织”犯罪理论体系中,旨在用已有的成熟的“组织”理论解决本罪存在的不明确的问题。组织型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是我国刑法学中“组织”犯罪理论的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组织型犯罪包含有组织犯罪。[12]有组织犯罪属于必要共同犯罪,组织者和被组织者均构成犯罪,两者都要求人数众多,至少达到三人以上。本罪属于组织型犯罪中的任意共同犯罪,被组织者不构成犯罪,组织者构成犯罪,这也是组织行为实行行为化的一种表现。本罪中组织者的行为多种多样,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组织出卖他人的器官;第二种是组织他人进行器官出卖;第三种是中介,不直接买卖器官。这三种行为都是组织行为的表现方式,都是本罪的规制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本罪所规制的组织行为已具有了规模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特点,我国刑法典将实质上是将帮助行为的 “组织犯”做了实行行为化的处理,旨在从源头上打击出卖人体器官犯罪。因此,本文从理论上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划分在了任意共同犯罪的理论之中,加大了对本罪的惩治力度,明确了本罪的惩治对象。
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行为方式
(一)组织的人数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被组织人数的多少,学者们意见不一。高翼飞等学者在文章中认为,“本罪属于有组织犯罪,一般要求被组织者达到三人以上,至少应当是复数,才能构成本罪。”[13]张明楷等学者则认为,“本罪中的‘组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本罪是共同犯罪中组织犯实行行为化的表现。另外,单人、单次也足以造成他人身体的伤害,所以本罪的认定应如认定故意伤害罪一样不要求人数与次数。”[14]
法益保护是刑法的核心,贯穿于整个刑法条文和刑法解释。本罪的组织的人次是否是多人,要从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出发进行分析。支持本罪侵犯的是医疗移植秩序的学者大多主张该“组织”行为应当限于三人以上,[15]多人次才能影响秩序的正常运作。主张本罪侵犯个人法益的学者则认为“组织”一人也可以构成本罪。[16]
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医疗移植秩序,“组织”多人才能构成本罪。首先,本罪和组织卖淫罪和非法组织卖血罪一样,惩治的是“组织”行为。也就是说,单一的卖淫、卖血、卖器官行为并不是刑法惩罚的对象。因此,如果组织一个人卖器官,就是非法出售器官的帮助犯,既然出售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帮助犯自然也不构成犯罪。其次,本罪侵犯的是医疗移植秩序,一个人出售器官的行为并不足以扰乱该秩序,只有组织多人进行非法买卖器官的行为才会对医疗移植秩序造成混乱。一般情况下,组织一个人出卖器官不构成本罪。但是,若组织并教唆一个本来不具有出卖器官意思的人出卖器官,或者招募一个人对其进行“精心照料”,然后出卖其器官的,行为人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二)组织的行为模式
组织行为的内容多种多样,前提是必须有被害人对伤害的承诺,并且组织行为针对的对象是活体器官,不包括尸体器官。本罪的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组织他人出卖自己的器官;第二,组织出卖他人的器官;第三,作为中介,撮合双方进行器官买卖。对于前两种行为,可以总结为以出卖为目的,供养“供体”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活体器官的行为构成本罪。对该种行为模式构成本罪,学者们并无异议。针对第三种中介行为是否构成本罪,学者们争议较大。“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主要是指招募、供养器官提供者,撮合人体器官供需双方,并从出卖他人人体器官行为中获利的人。[17]因此只要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提供过一次“中介服务”的或者说进行过一人次的组织行为,即可认为构成本罪。[18]也有学者认为组织行为应当限于拉拢、策划、联络等积极的组织行为,而不应当包括普通的中介行为。
中介行为在器官买卖市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最暴利。因此,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行为模式必然应当包括中介行为。根据本罪的罪状,本罪的行为人有两类,一类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组织者;一类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被组织者。成立本罪并不要求有牟利的目的,也不要求有经营意图。因此,只有在组织者与被组织者均无出卖意思的情况下,才不构成本罪。中介行为也构成本罪,原因是从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现状看,我国尚未建立一个全面的、及时的器官捐献服务平台。面对器官捐献者少、器官需求量大、活体器官捐献信息不透明、活体器官供需不对称的阻碍。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全面及时的器官供需平台。该平台的作用在于公开器官的供需信息,使供体能够及时了解自己器官的需求,甚至可以追踪自己器官的去向,从而督促医疗机构规范自己的移植行为。这样的平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都应当由医疗机构或者政府机构主导进行,不能由个人私自进行。否则会导致一些犯罪从简单的买卖器官行为升级到非法摘取活体器官,进而导致买卖器官行为的团伙化、集团化、国际化。若要全面深入打击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中介行为应成为本罪的规制对象。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行为模式除了领导、编制、管理、招募、介绍、安排等行为,还应当包括运输行为。如前文所述,组织出卖人体器官不仅包括组织他人出卖自己的活体器官,而且包括组织出卖他人的活体器官。犯罪嫌疑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对活体器官进行运输应当依本罪处罚。运输在本罪中是出卖人体器官的帮助行为,本罪的立法本意就是将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进而打击出卖人体器官犯罪。若不将运输纳入本罪的行为模式之中,本罪会迅速发展为跨国犯罪、国际化犯罪,给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打击出卖人体器官犯罪带来阻碍。因此将知情的运输行为纳入本罪的规制范围是阻止本罪走向国际化的有效手段和必要手段。
(三)组织行为的完成形态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形态主要是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保护的是人的身体健康权,但是本罪并不要求对被害人造成实质的损害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保护的是医疗移植秩序,以组织行为完成为即遂标准,即“只要组织者无需为出卖器官再进行下一环节活动,就表明组织出卖器官的行为环节已经完成,就应认定为即遂,牟利与否或者器官是否成功摘取不影响本罪的即遂。”[19]因此,本罪的犯罪形态是行为犯。
笔者也认为本罪是行为犯。首先,从本罪的罪状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即构成本罪。“由于‘……的,’表示罪状的表述完结,而罪状是对犯罪具体状况的描述,所以,‘……的,’所描述的不只是形式,而是实质内容。”[20]在本罪的罪状中没有关于犯罪结果的规定,根据本罪的罪状,本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已实施或已充分实施本罪规定的组织行为,则构成本罪。另外,本罪保护的法益为器官移植秩序。行为人有计划地组织供体出售器官行为本身已经扰乱了正常的器官移植医疗秩序,而后续结果是否严重不是本罪成立与否的考量因素。
因此就本罪而言,应当准确界定组织行为的着手、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以免在实践中扩大本罪的打击范围或放纵本罪相关的行为人。
四、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行为对象
组织出卖器官罪,显而易见,本罪中组织的对象是“器官”。在医事刑法的范畴,认定器官的范围离不开医学上对器官的认定,但医学上的器官并不等同于法律规定上的器官。本部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器官的规定范围不同。“日本是将角膜等人体组织纳入器官移植法的调整范围。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人体器官既包括主要脏器,也包括肠、肢体和视网膜,但不包括骨髓;韩国的器官移植法所规制的对象既包括主要的脏器,也包括骨髓、角膜等人体组织;瑞典将生殖细胞、生殖腺以外的人体器官与组织都纳入器官移植法的对象范围之中。”[21]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确将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排除出器官移植的范围。”正是该《条例》的存在,使得学者们对本罪中“器官”范围的认定存在分歧。
确定器官的范围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应当遵循《条例》的规定,即认为本罪中的“器官”应与《条例》中的“器官”范围一致。第二种是将器官做扩大解释,包括细胞、角膜、骨髓等。虽然在《条例》中明确例举了器官的范畴,但刑法与行政法并非同一法律系统,而且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不是行政犯,《条例》对本罪不具有基础性的规定,因此本罪对器官的界定无需参照《条例》。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对“器官”的定义也不宜过于扩大。反对将角膜纳入本罪“器官”的范围的学者认为,角膜构造简单,现代医学已经突破了用动物角膜代替人类角膜的技术,若强行摘取角膜,会造成受害人失明的后果,完全可以通过故意伤害罪来规制。{22}
广义来讲,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都可以通过故意伤害罪来规制,但如此规制不利于刑法典的精细化和准确化。也不能因为期待医学的发展而放弃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角膜对人的视力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失去了角膜,也就失去了光明。根据本文观点,对人具有重要功能或者丧失该器官会对人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器官或组织都应当纳入本罪器官的概念。
要确定器官的具体范围,首先应当考虑本法所保护的法益。本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复杂法益,既侵害了被害人的身体健康,也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移植秩序。从侵害被害人身体健康角度看,无论是摘取身体器官还是组织,都是对被害人身体的伤害。从医疗移植秩序的管理角度看,虽然《条例》排除了对组织的适用,但行政法不调整不意味着刑法就不规制。正是因为行政法在此方面有缺陷和不足,刑法才应当对“器官”做扩大解释,弥补行政法的缺漏。其次,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通过外国对该行为客体的界定,将“组织”纳入器官的范围是可行的。但血液和骨髓不可以作为本罪的对象。因为非法组织卖血罪中对相应的行为已有规制,在此不必重复规定。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虽然是新罪名,但是组织出卖器官的行为存在已久。从已发生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件可以看出,本罪已经出现了集团化、跨国化的特点。因此明确本罪的打击对象,把握本罪的打击力度,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扼杀在萌芽期,阻止该犯罪行为发展成枝繁叶茂的集团犯罪和根深蒂固的恶性犯罪。
[1] 王春丽.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适用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2011(4):111.
[2] 陈家林.《刑法修正案(八)》器官犯罪规定之解析[J].法学论坛,2011(3):22.
[3] 邓毅丞.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基本问题研讨[J].清华法律评论,第六卷第二辑:135-136.
[4] 张明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基本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1卷第5期:86.
[5]莫洪宪,杨文博.刑法中的人体器官犯罪——对《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的理解[J].人民检察,2011(9):26-27.
[6] 秋山.新《刑法修正案(八)》诠释器官移植中的伦理与法律困惑[J].中国卫生法制,2011(4):5.
[7] 刘静坤,陈晖.组织出卖、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犯罪的刑法规制[J].法治论丛,2011(3):30.
[8] 郑飞云.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初探[J].犯罪研究,2011(5):110.
[9] 高翼飞,高爽.买卖人体器官犯罪的司法认定[J].人民检察官,2012(1):11.
[10]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EB/OL].(2008-06-25)[2015-08-25].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_9l2ksLJTlEoEM9De2O3X8Y-JAczI5QZI hrwop6cISLD5JCB9s2t5DLUpmq37SCQ5i6jeC8FwN2SM ReNS-Ze_.
[11]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EB/OL].(1991-09-04)[2015-08-25].http://baike.baidu.com/view/2016164.htm.
[12]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EB/OL].(2000-11-15)[2015-08-25]http://baike.baidu.com/view/94281.htm
[13]西田典之著,王绍武,刘明祥译.日本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37.
[14]傅翔宇.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探析[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20-21.
[15]马宁.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刑事侦查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3(366):29.
[16]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J].人民检察,2011(8):52.
[17]熊永明.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理解与适用[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5):8.
[18]王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之解读——解析《刑法修正案(八)》第 37条[J].政治与法律,2011(8):34.
[1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75.
[20]江苏高院公报案例:王海涛等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犯罪案例 [EB/OL].(2015-02-11)[2015-9-12].http://www.zwjkey.com/onews.asp?ID=13217
[21]赵秉志.略论我国《刑法》新增设的人体器官犯罪[J].法学杂志,2011(9):34.
[22]金轶,李刚.出卖、摘取人体器官犯罪司法实务分析——《刑法》第234条之一的司法适用问题刍议[J].法学杂志,2011(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