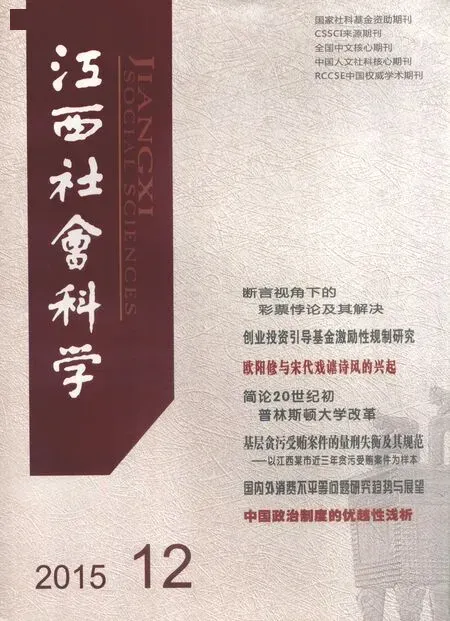别样的“山寨”与“恶搞”:李蔚然电影的创意模式
2015-04-15黄洁茹
■王 涛 黄洁茹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社会观念转变为山寨文化的生存提供了现实土壤。山寨来源于民间,具有平民化、草根化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反对权威和中心的后现代特性。但与此同时,“山寨电影”一词也为社会各方所诟病,被认为内涵空虚、品位低下,但我们不能仅看到“山寨”的弊端,更应该正确对待其为中国喜剧电影所起到的作用。“首先,山寨电影大大拓展了中国喜剧电影的想象力。其二,在电影创作观念乃至电影观众的接受意识中,山寨电影强化了电影意识和电影是一个虚构世界的概念。其三,山寨电影在电影固有的低端增强了国产电影与观众的亲和力。”[1]
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型之后,大众的世俗趣味渐渐占据文化主导地位,而山寨电影以精神娱乐和商业盈利为目的的特性,非常贴近大众的审美情趣,这也就是部分山寨电影之所以能获得高票房的原因。山寨电影具有通俗性,它是建立在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富含市民文化的娱乐想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山寨电影无论好坏,它的出现都是必然的,山寨只是多种电影形式中的一种奇特形态,丰富了电影艺术的多形性。
《决战刹马镇》这部影片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山寨”喜剧电影,但“山寨喜剧”电影丰富了其创作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拓展了喜剧的类型,将虚构与现实相结合,虚构的幻想世界中并未脱离对现实的把握。
一、创意与“山寨”、“恶搞”
当我们看到李蔚然这部影片名字的时候,肯定会把这部影片与《决战犹马镇》联系起来,也会误将此片等同于盛行的“山寨文化”产物。时下,国内“山寨文化”的盛行,导致涌现出一批质量参差不齐的所谓喜剧电影,这也正是山寨与商业元素杂合的产物。国外的山寨电影多是对经典影片的“翻版”,或是对知名导演惯用艺术手法的“模仿”,而国内的山寨电影则多了一层搞怪的含义。从“模仿”到“冒牌”,到对原片及现实的戏谑讽刺,国产喜剧电影也是不断在自我发展。李欧梵认为,电影中的戏仿是“一种在风格和形式上对早期作品进行有意识地模仿的类属上的衍生和模仿……也可能包含一种电影类型上的混合”[2]。“山寨电影”承袭的是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基本特征,是对电影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发展,在电影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文化的多元性也给“山寨电影”提供了无数种可选择的表现手段,并且,“山寨电影”把后现代的一些特点诸如戏仿、拼贴、解构等手段发挥到了极致,这些手段也成为诸多电影创作者的倾向与选择。
在《决战刹马镇》中,被模糊了地域的偏远小镇中,一群“傻”得掉渣的村民与外来“精明”的骗子之间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这样一个常见的故事,在导演的创意与夸张的人物塑造之下,电影透露出独特的喜剧气息。其中看不到以往国产山寨电影的那种 “拿来主义”,电影情节中的“恶搞”却又有着生活的依据,看似“恶搞”却在情理之中。影片在开头刻意“山寨”了好莱坞西部片之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另一个“山寨”的西部乡村,戈壁山沟的刹马镇像是一个山寨版的嘉年华,在这座偏远的乡村上演的是发展旅游经济之后的破落,在“山寨”的背后突显的是导演对于“本土化”的追求。开场段落对全民收藏风潮下应运而生的鉴宝类节目的戏仿,无论是从节目样式还是节目的构成,都“复制”了鉴宝类节目。但是,从鉴宝专家风仁义、马知庸、牛杜澎的姓名上,我们又能看到导演对现实的嘲讽,与其说“风马牛”的“恶搞”不如换成善意的批评。
低层次的山寨喜剧往往是为了搞笑而搞笑,而《决战刹马镇》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刻意“山寨”背后的内容,李蔚然的影像世界中,人物的语言、性格以及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中,充满了对时下中国社会的影射,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背景支撑,在观众的笑声背后更多的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喻。而正是这种把对现实的嘲弄巧妙地融入商业电影中,是对商业电影与艺术追求的结合,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趋势。
当“恶搞”成为网络视频的主角时,当草根们用“恶搞”的手段狂欢宣泄时,华语电影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恶搞”混搭着各种手法成为时下电影的一种叙事方式。“恶搞”依赖已有的社会生活素材,这些素材包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历史人物、事件,时事新闻热点,流行语汇,名人轶事,电影场景等。通过对其中一些广为人知的原始素材进行再度创作,讽喻、调侃、戏弄原始素材的主题,加之观众对原始素材相对熟悉,这也使得“恶搞”可以以高效的方式获得颠覆原始素材的效果。“大众对既定模式的模仿的时尚追求中,它既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异性、个性化的要求。因而,这种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拥有高度灵活的分化的吸引力。”[3](P85)陈林侠认为“社会的一致性”满足大众急于逃离孤单的心理需要,更以快速多变、翻新出奇的先锋面貌迎合追求差异性、个性化的大众心理。[4]前面提到的后现代的多种特点,也正因为这些特点更加“通俗”、“大众化”,更利于大众的接受,这也就成为“恶搞”手段可以与观众产生共鸣的原因。“恶搞”利用电影独特的技术、艺术手段,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恶搞电影”暴露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在强调娱乐至上的大环境下,电影价值与意义的缺失。
近年来,众多的新锐导演纷纷脱离毫无营养的疯狂“恶搞”系列,转向关注贴近现实的社会题材,把广为人知的社会新闻或流行事件等作为影片讽刺嘲弄的对象,以期使观众在娱乐之余能对社会深层次问题能有所思考。《决战刹马镇》在这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影片时时处处都体现着李蔚然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对社会现实弊端的冷静思考。当票房成为电影人夺取市场、受认可的衡量标准时,电影在喜剧元素上却被融入了“为搞笑而搞笑”的所谓娱乐元素,脱离了现实的基础,丧失了生活的本质意义。
“恶搞”手法在《决战刹马镇》里数不胜数,片中多处关于“张导”的“印象刹马镇”,片尾在刹马镇旅游业开展得风生水起时,村长唐高鹏接到国际知名导演“张导”的电话,对方透露要执导一出《印象刹马镇》的情节,孙红雷的那句“你娘个腿的张导,真的是张导啊”,是更为直接地拿张艺谋调侃。影片中,镇主任让全镇种西红柿,最终换来的却是投资商中途撤资,西红柿销不出去的局面。而后又因唐高鹏收购西红柿,在感谢唐高鹏的酒会上喝得昏天黑地,其出门撒尿,以为裤子解开了就直接尿在裤裆里,极尽嘲弄之事。在这些“恶搞”中,无能镇主任的所作所为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同的模板,是对当下某些地方不顾实际情况而盲目发展的写照,也是对部分不称职公务人员的讽刺。片中村委会与村计生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同一个办公地点,除去这两块牌子别无他物,这看似不起眼的一个道具安排,却肩负着“恶搞”的使命,狠狠地嘲弄了某些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导演对现实的关注与挖掘在其中体现无遗,细细品味起来有丝丝冷峻的态度涵盖其中。另外一个让人记忆犹新的情节,村里英语说得最好的村姑,在回答骗子英语问候的时候,不自觉地带上了“and you”,这是典型中国应试教育模式培养下的中国式英语的用法,这段情节的设置,既符合了人物的性格,同时又不忘对中国教育模式进行了一番讽刺。在最后骗子们全副武装夺宝时,导演更是出人意料地对美国大片中的英雄大兵形象进行了无厘头式的“恶搞”,在片中的“地道战”中,两个装备精良的“美国大兵”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里,土办法解决了洋玩意,被偷鸡和摸狗两个村民用来做电击亮灯的导体。
演员在创作上也是极尽所能,其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 “偷鸡摸狗”两个奇葩人物。包贝尔饰演的摸狗的造型,身着绿裤,露股沟,让人联想到周星驰《功夫》中的“酱爆”,据说摸狗的绿毛裤原本得体,但遭遇水洗之后就缩成了最后出现在影片中的样子。这件土得掉渣的绿毛裤被包贝尔用到了极致,片中只要看到他就能看到他白花花的屁股,甚至把香蕉藏进了露着股沟的绿毛裤里。偷鸡作为摸狗的难兄难弟,无论是演死人被勒住,还是袜子里藏糖果的情节一定会被观众所记住。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刹马镇里,从村长到偷鸡摸狗两兄弟,再到进城打工的大炮三兄弟,几乎所有的人物看似都有些癫狂,甚至说都有些不正常,而恰恰是这种村民的“不正常”,用着“不正常”的“恶搞”手段,可以在与外来高智商骗子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剧中所有演员们的表演都非常夸张,虽然所有人物的表演看起来有些脱离实际,但在这样一个高度风格化的电影里面,我们又发现这些人物都有他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设置也给影片增添了更多的荒诞元素。
有创意的“恶搞”对于“山寨”电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决战刹马镇》中的各种恶搞没有落入俗套,相反,里面的种种情节都会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如同看李蔚然所拍摄的耐克广告一样,而这种“恶搞”的背后,又有着如同《别人的孩子》一样的深度内涵,给人思索、回味的空间。影片深层次的价值与意义,在“恶搞”同时把它传达给观众。
二、主流喜剧片的新尝试
李蔚然在接受南都娱乐采访时曾说,《决战刹马镇》是一次中国喜剧的新尝试,李蔚然将《决战刹马镇》的风格,定位为“另类的现实主义喜剧”。这部让我们从头笑到尾的影片,犹如当年《疯狂的石头》一般,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影片毫无严肃感,始终贯穿喜感,观众在混杂各种流行元素的电影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欢乐的电影时光。“喜剧似乎格外适合杂交,其主要原因是引人发笑的各种局部形式可以在某些点上插入其他大部分的普通语境,同时又不打乱他们原有的规范。”[5](P5)《决战刹马镇》似乎也遵循着这一规律,影片故事发生在一个被虚构架空的世界中,但又平添几分现实感,黄土岭,黄土屋以及土坡上的村民总给人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
《决战刹马镇》开头很有西部CULT片的意味,胡栓子死了似乎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茫茫黄土上,胡栓子的腰牌显得如此神秘。这也会让人联想到各种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漠英雄故事,然而《决战刹马镇》却有意地跟观众开了个玩笑,随着富有卡通戏谑味道的音乐变化,再加上卡通字体的影片字幕出现时,影片的风格发生了180度的转折,随即上演了一出荒诞喜剧。影片中的地点应是在西北,而村民们却操着一口保定话,这无疑是一个模糊了地域的世界。在这个荒凉贫瘠的地方,村民不种地,而村长却总希望能带着村民致富奔小康。影片中在唐村开展的刹马镇旅游行业不景气,孙红雷饰演的村长整天想着不着边际的旅游业,想利用旅游业干出一番事业。刹马镇旅游的文艺演出总是那一出有关土匪胡栓子的传说,村长老唐一句“请的是县里的这个话剧班的大腕儿排的”充满了黑色幽默。李立群、黄海波饰演的骗子们携一干手下以发展旅游业为名到刹马镇。于是,各种充满创意又令人大跌眼镜的笑点随故事而展开。一群透着傻劲的村民用无厘头的方式战胜了一群奸诈的骗子,在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村民的傻与“鸡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间中还带有强烈的对现实的讽刺感。导演李蔚然声称此片将一个美式故事复制到中国西部,在影片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李蔚然不仅是复制了美式故事,他还深入挖掘了乡土片的温情气息,更是把香港喜剧无厘头的方式加入其中,大大增强了影片的喜剧色彩。影片的总体风格同《三枪拍案惊奇》有着相似的地方,而《决战刹马镇》本身也没有刻意回避,而是在片中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片中多处出现与《三枪》有关的“张导”、“印象刹马镇”等,在这种戏谑的背后增添了另一种“山寨”喜剧的味道。
在这部充满创意笑点的电影里,我们能感受到导演对于每个细节的追求,不胜枚举的创意笑点让观众目不暇接,但这也是对导演整体掌控影片能力的考验。毕竟李蔚然是第一次做长故事片,比起以往的广告片来讲,难度就在于如何把短小的故事情节贯穿起来,同时又不会让整体失控。但遗憾的是李蔚然的对长故事片的掌控能力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在这些喜剧笑点背后,给人一种情节堆砌的感觉。剧情远没有想象中的跌宕起伏,相反只是极平淡地围绕简单的剧情结构展开,“鉴宝—探宝—挖宝—夺宝—护宝”。其中若干的细节也有刻意为营造喜剧效果而设置的,情节上缺乏连贯性,内在的逻辑又有些不合情理,经不起观众的推敲。不过由于电影本身具有荒诞喜剧的色彩,这也掩盖了导演整体掌控能力稍弱的硬伤,但作为一个类型老套的影片,被李蔚然演绎出了新的色彩,赋予了新的喜剧类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希望。
西部、黄土、土匪、宝藏,这一系列关键词会让我们联想到同一类型的电影,当 《双旗镇刀客》为我们交上国产西部片的出色答卷后,中国电影人也加快了对西部类型片的探索脚步。国产西部片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西部电影的准备阶段,再到20世纪90年代《双旗镇刀客》所开创的具有鲜明的美学追求的类型片,西部片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对于成熟的美国西部类型片,“中国西部片虽未如美国西部片那样具有比较定型的形态,确已大体形成其特定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6]。例如:厚重的黄土文化、粗犷的人文气息、朴实的风格特色、广袤的自然风光等一定的类型化特征。
近些年的 《盲井》《可可西里》《刺陵》《西风烈》《无人区》描绘的都是西部的风情,也似乎都在努力打造具有中国西部风格的新类型片。而在《决战刹马镇》这样一个充满多种类型元素的电影,让我们领略到的不仅仅是一部西部片那么简单。各种元素的错位,现实与历史的错位,地域间的错位,人物身份的错位,为这个喜剧电影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决战刹马镇》虽说是发生在中国西部一个小镇,影片中展现的也是富有西部民族特色的地域特征:漫天飞舞的黄沙与土墙高砌的西部瓮城,但电影实质上却混合了不同的地域与时空色彩。西部荒原上的现代嘉年华、民国的军阀与土匪、17世纪的加勒比海盗,加上人物语言的错位,种种这些错位将影片与现实脱离,但又将夺宝与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用的是各种混搭和山寨的喜剧表现手法,开创的不仅是西部片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三、结语
也正如李蔚然所说,在他的《决战刹马镇》里,西部类型片、喜剧片被他赋予了独特的艺术样式,似有要颠覆传统的冲劲。《决战刹马镇》是一部从各方面都显得过火的电影,无论是导演还是表演,比起“山寨电影”又多了个性追求的内容。在自由张扬自己文化性格的风格下,还在不停地实现对传统权威话语权的挑战和反讽;在追求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之时,还不忘针砭时弊,大张旗鼓地“恶搞”现实生活。如同“山寨电影”一样,这是一种彰显草根文化生命力的商业类型电影,但李蔚然的《决战刹马镇》却披着大众审美的外衣,倾诉着小众的精神内涵。导演自己曾说过:“《决战刹马镇》探讨的主题其实是草根小英雄拼搏到最后能够达到和得到什么。我希望大家通过这部电影能够看到自己为了生活、生存和理想不惜以命相搏的状态。《决战刹马镇》表面上看是一部热闹的喜剧电影,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带有黑色幽默的都市寓言。”
李蔚然的大银幕处女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融入的不仅是作为广告导演那种自发的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思想,还有他对现实生活冷峻的表现。更多的是他开创的新的喜剧风格,在怪诞夸张中突显社会与人的本质,就如同观赏卓别林大师的影片一样,欢笑过后留给我们的思考内容远比笑声厚重。《决战刹马镇》在这种抽空的现实中,多方位错乱的时空里,用充满创意与趣味的“恶搞”,把这个疯狂的夺宝喜剧演绎得淋漓尽致。《决战刹马镇》将商业、创意、“山寨”、“恶搞”结合,用“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游戏风格样式,冲击了主流国产喜剧电影的模式。
[1]李迅.后山寨电影向何处去——评《决战刹马镇》[J].电影艺术,2010,(5).
[2]李欧梵.两部香港电影——戏仿与寓言[J].世界电影,1998,(4).
[3]肖伟胜.现代性困境中的极端体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陈林侠.类型电影的叙事智慧、难度与知识结构[J].社会科学,2005,(5).
[5](美)史蒂夫·尼尔,弗兰克·克鲁特尼克.娱乐电影和电视喜剧[J].徐建生,译.北京电影学院教学编译参考,1993,(1).
[6]罗艺军.盘点第四代——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研究[J].文艺研究,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