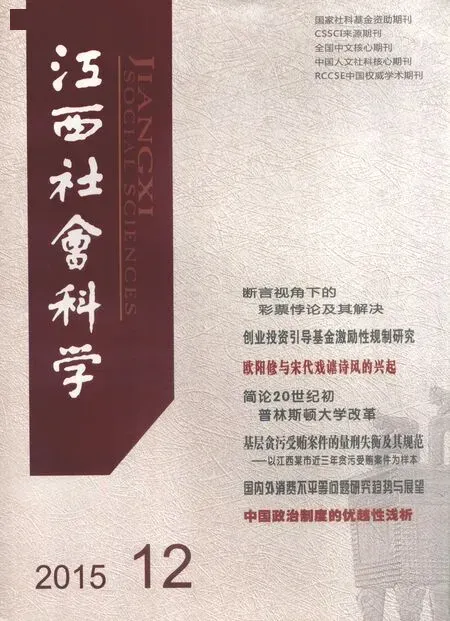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2015-04-15郭朝辉
■郭朝辉
黄河中下游交接地带的河南,古代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湖泊众多,水草丰茂,是动植物生长的乐园,人类发展的宝地。基于此丰富的水土资源,便利的农耕、灌溉、航运条件,古代河南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然而,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加之人为因素,携带大量泥沙,古代起就以善淤、善决与善徙著称。在“自周定王五年(前602)至一九三八年花园口扒口的2540年中”,黄河 “决溢次数多达1590余次”。[1](P51)正所谓“中国之水非一,而黄河为大,其源远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质浑而浊,其为患于中国也,视诸水为甚焉”[2](卷17,P252)。在黄河26次较大的改道中,至少20次发生在河南。宋元以前,人类文明的进程发展缓慢,黄河相对安流,水患带来的危害相对较小。宋元以降,黄河在今颍河以东、大运河以西、淮河以北的黄淮海平原上,以开封、商丘、徐州为主线,频繁地漫溢、决口与改道,使黄河中下游地区饱受水患之痛。
据统计,有明一代(1368—1644)276年中,发生黄河决口的年份达112年(不论一年决口多少处,均以一年计算,决后未堵的泛滥年份不计,下同)[3](P34):洪武至宣德(1368—1431)63年中27年[3](P257-260);正统至弘治(1436—1505)69年中32年[3](P264-268);正德至隆庆(1508—1571)63年中21年[3](P276-277);万历至崇祯(1573—1642)69年中32年[3](P283-286)。这些黄河水患,许多发生在河南,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月,“河决河南开封府之阳武县,浸淫及于陈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兰阳、陈留、通许、太康、扶沟、杞十一州县”[4](卷215,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庚寅,P3170)。永乐八年(1410)“秋,河决开封,坏城二百余丈。民被患者万四千余户,没田七千五百余顷”[5](卷83《河渠一》,P2014)。正统十年(1445)十月“辛亥,河南睢州、磁州、祥符、杞县、阳武、原武、封丘、陈留、安阳、临漳、武安、汤阴、林县、涉县皆以今夏久雨河决”[6](卷134,正统十年十月辛亥,P2666)。正统十三年六月,“河南陈留县奏,今年五月间河水泛涨,冲决金村堤及黑潭南岸”[6](卷167,正统十三年六月癸酉,P3233),七月“己酉,河决河南八柳树口”[6](卷168,正统十三年七月己酉,P3253);黄河当年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八柳树决,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开封、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康等处,没田数十万顷,而开封为患特甚”[6](卷230,景泰四年六月己丑,P5021)。万历二十九年(1601)“秋九月壬寅,河决开封、归德”[5](卷21《神宗纪二》,P282)。真乃“黄河之害,惟豫省为甚”[7](卷76《艺文五》之《条陈民困疏》,P539)。由于文献缺失,许多黄患未被统计在内,实际水患年份应远多于此。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自然环境变迁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频繁发生,河水不断夺淮入海与冲击运河,改变了黄患区的水陆生态环境,使这一区域的河流、湖泊水系发生巨大变化,造成大片土地沙化与盐碱化。
(一)河流水系重组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使泛区河流水系发生改变。黄河侵泛的较大河流,经人工挑浚后尚有流水能力,侵泛的小型河流常被淤成平地。泥沙淤积还使河流常常发生汇合与分离。
河南黄河南决夺颍、涡、濉等入淮,使这些河流泥沙淤积严重,河床明显升高,常漫溢成灾,造成更大危害。有的河流因此发生较大改变,甚至消失。如濉河,源于今开封县南,经杞县、睢县、宁陵县、商丘县,最后由宿迁县入泗河[8](P92);至明代,由于黄河泥沙淤积,不知源头所在;至清代,源头与河道均发生极大变化,注入洪泽湖。如古蔡河,原为颍河支流,永乐时还是重要航道,至明末,已难觅故迹。黄河在河南北决,改变了黄河以北河流流量与流向,常冲击张秋运河。为保证张秋运河安全,必然要对黄河及其以北河流朝着利于漕运的目标进行引导与利用,却破坏了原有河流水系。明代经过徐、吕二洪的运河,为借黄济运航道,而河南黄河水患特别是决口,无论是北决还是南决,多造成此段水流微弱,给漕运带来不便。为了保证此段运河安全,所进行的河工也改变了此处的河流水系,特别是明后期泇河的开凿成功,虽保障了漕运,但使汶、泗、白马、漷、薛、沭、沂等河的水系发生改变。
黄河水患还促成了地上河的形成。黄河水患的影响,迫使人们在黄河中下游两岸筑起长堤,随着泥沙淤积河床,长堤年复一年加高,造就了地上河。直至今日,黄河中下游地上河的形象仍未改变。地上河成了淮河与海河、汶泗沂沭水系的分水岭,成了要防范的对象,对所经地域的水系影响甚大。
(二)湖泊水系变迁
河南黄河水患,使黄患区的湖泊水系变迁。一些湖泊缩小或干涸,一些则扩大或形成。
黄河泥沙沉积使湖底变浅或析出,湖泊缩小或消失。如圃田泽,战国时形成,位于今郑州与中牟县城间,虽经泥沙淤积,北魏时仍“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9](卷22,P347-348)。可知,当时该泽十分宏大。以后,不断受黄河泥沙影响,其中沙滩渐被开垦。至明代,更为频繁的黄河水患,特别是黄河夺颍河、贾鲁河等入淮,加剧了湖底升高,水患时,汪洋一片,水退,则仅剩少许积水。至清代,终被垦为农田。如山东大野泽 (又名巨野泽),由于黄河多次决入,在梁山周围低洼地形成了著名的梁山泊。明前期,梁山泊还是一大片浅水洼地。景泰四年(1453),徐有贞治河策中还建议把梁山泊作为黄河北决的泄洪区。[10](卷37《言河湾治河三策疏》,P284)弘治时刘大夏在北岸筑长堤后,黄河多南决入淮,梁山泊缺少水源,湖面面积锐减。清康熙时,梁山周围全成平陆,“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居人以桔槔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11](卷八《艺文》之《过梁山记》)。其他如河南开封附近的逢泽、好草陂、雾泽陂、西贾陂,商丘东北的孟诸泽、蒙泽,山东定陶东北的菏泽,鄄城南的雷夏泽,江苏丰县的丰西泽,也由于黄河南泛而先后消失。
黄河河水流经湖泊与洼地时水量潴积,使原有湖泊扩大或形成新湖。明后期黄河全河夺泗、淮以来,泗、淮河床不断抬高。原有水系被破坏,水排泄受阻,使原有湖泊扩大,许多洼地积水成湖。如南直隶洪泽湖,由于“束水冲沙”与“蓄清刷黄”方针下的大修东岸洪泽湖大堤(前身为高家堰),明中后期湖不断扩大。至清,形成今天完整的湖身,明代泗州城沉入湖底。以昭阳、南阳、独山、微山为名的南四湖也是黄河夺泗与运河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再如受黄河入淮影响,淮河沿岸形成城东湖、城西湖、花园湖、天井湖等。
(三)土地沙化与盐碱化
华北平原是由黄、淮、海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其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黄河每次决溢改道,都把大量泥沙带到河外,改变了水到之处的土壤,是淤肥还是淤沙,无法把握。有时漫淤过后,土地有质物增加,土地趋于肥沃。如新乡县,由于黄河改道不再过境,县内黄河“退滩甚饶,居民利焉”[12](卷1,P9)。但更多的是,泥沙淤积使土地严重沙化与盐碱化。
河流改道后,留下的枯河床和河堤上的沙质沉积物,形成许多断续的沙丘。如嘉靖年间,刘天和奉命治理兰考至鱼台间黄河故道,亲见“自赵皮寨东流故道,凡百二十余里,而至梁靖,河底视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东流故道,凡二百七十余里,而始至谷亭,已悉为平陆”[13](卷2《治河始末》,P266),其间多为沙岗。如仪封县,嘉靖时有黄河、圈头店河、黄陵冈河、贾鲁河等黄河徙道,“地之高者尽是沙薄”[14](P116),“每狂风一动,四野飞沙,如黄冈迤东直抵石家楼一带,四十余里,尽为斥卤,犁锄罔施”[14](P80)。
“黄河水含盐碱量较大,若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方,经日光照射蒸发,土壤中的各种盐质经日晒后集聚于地表,即成为盐碱地。”[15](P15)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灌溉研究所编 《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16](P9-12)与周志远主编《农田水利学》[17](P229-230)都认为洪、涝、旱是促成土壤盐碱化的主要根源。黄河频繁的决溢,使沿岸地区成了洪、涝、旱的集中区域,“豫冀鲁交界一带平原,若濮县、鄄城、菏泽、东明、长垣……尤多”[15](P15)。崇祯十五年(1642),开封黄河决口后,“浊流汹涌,由杞东下,幅员百里,一望浩渺,其后水涸沙淤,昔之饶腴,咸成磏卤,尽杞之地皆为石田”[19](卷7《田赋志》,P476)。盐碱地亦能治理,其法是根治水环境,注重排水,适时深翻窝盐、绿肥治碱、植树造林等,但在水患频仍、动乱不断的明代,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
二、社会经济发展受制约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使河南为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给黄河沿岸城市带来巨大影响。
(一)破坏农业生产
黄河水患造成大量的农田、村庄被淹,使常泛区人口锐减且增长缓慢,制约农业生产发展。如洪武八年九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开封府祥符、杞、陈留、封丘、睢州、商水、西华、兰阳等八州县,以六月积雨,黄河水溢伤麦禾。淮安府盐城县,自四月至五月雨潦,浸没下田,诏并免今年田租凡一万四千六百余石”[4](卷101,P1710)。可见黄患破坏农业生产之严重。永乐元年九月“壬午,工部言河南陈州、西华县沙河水溢冲决堤堰,以通黄河,伤民禾稼”[20](卷23,P419)。宣德元年(1426)七月“己未,河南布政司奏,六月至七月连雨不止,黄、汝二河溢,开封府之郑州及阳武、中牟、祥符、兰阳、荥泽、陈留、封丘、鄢陵、原武九县,南阳府之汝州,河南府之嵩县,多漂流庐舍,渰没田稼”[21](卷19,P514)。崇祯五年六月“壬申,河决孟津口,横浸数百里”[5](卷28《五行一》之《水潦》,P454)。水患造成当地人口增长缓慢,如河阴县,洪武二十四年户为2492、口16 126,成化十八年(1482)户1522、口16 311,八九十年间,未增200口;原武县,洪武二十四年户3333、口29 892,成化十八年户3533、口29 894,八九十年间,只增2人。[22](卷3《开封府上》之《户口》,P387-389)这在多子多福的古代是不可想象的,黄患影响于此可见。农耕时代的两种重要因素——耕地与人口的减少,对农业经济来说是致命伤害。黄患所至之处,“崩我土地,决我城郭,溺我人畜,倾圯我墙屋,淹没我禾稼,为患有不可胜言者矣”[23](卷1《河渎》)。
(二)减缓城镇发展
黄患引起地理环境恶化,农业生产破坏,交通条件改变等,滨河水患城镇发展环境受损,许多城镇不得不迁址。“今郑州市西北邙山,古称广武山,山北有大片滩地,唐时置河阴县……元迁县治于广武山北一里……到明代,不得不再迁治于广武山南的今荥阳东北广武镇。”[24](P346)如仪封县圮于河,洪武二十二年,知县于敬祖南迁县治于通安乡“白楼村”[4](卷195,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癸亥,P2933)。景泰四年,“河南水患方甚,原武、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5](卷83《河渠一》,P2017)。成化十五年正月,“迁荥泽县治以避水”[5](卷83《河渠一》,P2021)。归德州(今商丘)被水,正德六年(1511),治所“迁徙城北高地”[25](卷2《建置志·城池》,P55)。有的县如考城,洪武二十三年和正统二年两次迁城。
黄河水患导致了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城市由盛转衰。北宋以前,黄河从河南卫辉、浚县经河北大名等,在天津入海,开封离黄河较远,发展达到鼎盛。金至明清,黄河由东北转向东南入海,开封水患不断,走向衰落。河南汜水县城,在隋唐以前是虎牢关城,明清时期,每逢夏秋暴雨之时,黄汜齐涨,汜水县城便危若累卵,终使汜水县地位不断下降,由县变镇。开封、祥符、兰阳、单县、曹县、泗州、宿迁等城镇本是依据黄河冲积平原产生与发展,宋元以降,黄河频繁的决溢与改道,使得这些地区原先优越的自然环境发生改变,失去了便利的水运交通及发达的周边农业生产,在明清时期走向衰落。
三、社会秩序变动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多发,也对明代社会秩序产生了一些影响。
(一)官场生态变化
1.总河成为常职,治河官职具化
治河之官,古已有之,至明,更为复杂。《历代职官表》言:“汉以后所置都水、河堤等官,皆在京师……并非专事河防,今其职已并入工部都水司,与河道总督之职较殊,但自宋以前,防河并无专官,而宋、金、元之都水外监、都水行监,实今日总河之职掌。”[26](卷59《河道各官》,P332-333)元末,“命(贾)鲁以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27](卷187《贾鲁传》,P4291),专职治河,虽未形成定制,但为明代设置总河提供雏形。明初中央无专职治河官员,一般以工部尚书、侍郎,都督等在治理运河时兼治黄河,中期,河患愈烈,明朝不得不重视河道。宪宗时,召王恕为刑部侍郎,总理河道,命其“严督各官并一带军卫有司人等……凡有便宜方略可举行者,悉听尔勘酌施行,一应官员人等敢有违误者,或量情惩罚,或俱奏拿问”[28](卷97,成化七年十月乙亥,P1845)。“自恕以后,总理不复设,间值河有他故,遣大臣行视,图方略治之,事竟还朝。正德十一年始专设总理,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或左右副都御史兼侍郎兼军务,其沿河分理河务则有工部郎中三人。”[29](卷下《河官考》,P61)总理河道(即总河)为定制后,多不再由他官兼理河道。①总河职权,也由权微向权重发展,嘉靖五年(1526),盛应期治河时,敕“命总提督河道事务,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三司官员俱听节制”,督沿河“府、卫、州、县管河官员趁时设法多方处置”[30](卷3,P222)。嘉靖十七年,总河更是“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闸郎中、主事及各该三司军卫有司掌印管河兵备等官”[31](卷165,P564), 原来由总漕管理的管洪、管泉、管闸等官现俱由总河来管,可见其权力之大。总河的设置不但适应了河患形势的需要,也对明朝的治河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中央派出的总河,管理河道、洪、泉的主事以及巡河御史等外,地方也曾设置各级治河官员 (明以前的朝代也有兼职或专职的地方治河官员,但明代更为具体与强化)。省设治河按察司副使;县则知县兼管,下设主簿或县丞专门负责治河;重要的闸坝处也设闸坝官等。如成化、弘治间,“河南、山东……二省各设按察司副使一员,专理河道”,“凡府、州、县添设通判、判官、主薄、闸坝官,专理河务,不许别委”[32](卷10《理河职官考》,P82)。正德八年设“东明、长垣、武城、曹县主薄各一员,专管河道”[33](卷198《河渠三·黄河钱粮》,P998)。地方治河官员也常随黄河迁徙而增删,如嘉靖十四年二月戊申“裁革南直隶丰县、河南阳武县管河主薄各一员,复设……河南原武、封丘、兰阳、仪封、夏邑等县管河主薄各一员,添设河南睢州、归德州管河判官及南直隶萧县主薄各一员”[34](卷172,P3741)。 与文官相对应, 也有武官治河官员出现,只不过多是本职外的一种兼职。如隆庆元年(1567),黄河沿岸各府、州、县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判、主薄等官专领其事,卫亦有巡河指挥,诸闸坝有闸官、坝官”[29](卷下《河官考》,P61)。地方治河官员在履行职责时,既受地方最高官员指挥,也受中央所派治河官员调遣。
总之,明代总的河渠管理职责属于工部,即便中央派出的总河具有提督下属诸多治河官员的权力,但也多受工部掣肘。延及清代,治河由工部专责过渡到总河专责。[35](P166-172)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罢置总河,长达四百年的总河退出历史舞台。
2.治河及河、漕官员出现矛盾
总河设立后,治河效率提高不假,但其权力过高,职掌地域较广,与其他官员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在所难免。如嘉靖七年,总河盛应期开昭阳湖东之新河以避黄河冲决,工程过半,遭管河郎中柯维熊(开始时柯氏支持开凿新河)等反对而被迫停工,盛氏也被召回。嘉靖四十四年潘季驯以都察院佥都御史,佐工部尚书朱衡治河,督理河道时,主张复黄河故道,与衡主张开昭阳湖以东之新河意见相左。隆庆四年,潘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次总理河道兼提督军务时,遭到首辅高拱重用的工部尚书朱衡和勘视河工的礼科给事中雒遵的责难;以朱衡言“河道通塞,专以粮运迟速为验,非谓筑口导流,便可塞责”[36](卷60,隆庆五年八月甲寅,P1470),命潘戴罪管事;五年十二月,免去潘总河之职。张居正为首辅,颇重潘,再次起用之。后居正事发,潘也受牵连。地方治河官员也因意见、利益不同而出现相互排挤、推诿等现象。
另外,明中后期贪污之风肆虐,总河及地方治河官员不乏营私舞弊、贪污钱粮之辈,进一步恶化了官场风气,加重了百姓负担。明廷曾颁布治河律令,从中央到地方的治河官员,都有其惩处与奖励的具体规定。总河有犯,要 “奏闻请旨”,由皇帝定夺。弘治三年规定“令各府、州、县管河官带领家人专在该管去处住坐管理河道,不许私回衙门营干他事”[37](卷1《律令》,P20)。对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行为,规定“若该管地方军卫,有司官员人等,敢有徇私作弊,卖放夫役,侵欺椿草、钱粮及轻忽河务,不服调度,并闸溜浅铺等夫工食,不与征给,致误漕运者,轻则量情责罚,重则拿问如律”[38](卷5《河臣纪》,P655)。
治河与治漕官员间也有矛盾。总河定制前,治河的地方官与治漕官员之间由于不相统属或各顾其利益,存在矛盾。如正统十二年,漕运右参将都指挥同知汤节因河决亲视要修筑河工时,河南三司及各府州县因其无敕而不允兴工,汤节请敕提督南京至通州沿河官司及管河官员,英宗不从其请。[6](卷155,正统十二年六月壬戌,P3023)总河成定制后,职权与总漕部分职权交叉,引起两者相互推诿与冲突,给河道管理带来负面影响。如嘉靖二十年,“二洪浅阻,粮运不通,总漕乃具疏尽推河道。奉旨切责,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料理,自此总河、总漕分为二,竟以漕为米,不知为河矣,而且彼此水火,漕法始乱”[31](卷165,P564-565)。万历五年,河决崔镇,因总河傅希挚与总漕吴桂芳治河分歧很大,而“并河于漕”,后因“责分而官无专督,故修浚之功,怠于无事,急于临渴,河患日深”[39](卷197,万历十六年四月甲寅,P3705-3706)等,重设总河一职。此后虽间有河漕兼任者,但多数为总河与总漕分任,并且这一制度沿用至清朝。
明代治河官职的设置,完善了河患治理机制,有利于提高河患治理效率,减轻朝廷与百姓负担,但是治河官员的任用及派遣,与河工修筑、护漕保陵、派系党争等问题相纠结,更兼许多治河官员本身以治河为发财手段,促使官场生态发生变化,加速了明朝的吏治腐败与衰亡。
(二)社会矛盾尖锐化
1.土地兼并加剧
河患严重地区,多是土地兼并激烈之地。由于黄患,农民不断逃亡,土地买卖频繁,当地藩王、卫所等趁机兼并流徙农民田地。明代河南,封藩繁多,约占明王朝分封宗藩总数的1/5。明中后期,河南藩王多方设法兼并滩地和民田。如成化年间秀王见澍就藩汝宁府,曾讨得归德、陈、睢、寿、颍等州以及霍邱、商水、鹿邑等县黄河退水滩地。[28](卷125,成化十年二月壬申,P2390)弘治十三年,崇王见泽奏求归德州等黄河退滩地二十余里。[40](卷159,弘治十三年二月乙酉,P2850)弘治初,军人张允因妒忌鹿邑、亳州农民垦种河堧地6190余顷,亩多税少,便以之为荒献于徽府。[41](卷47,正德四年二月甲戌,P1066)由于河滩争地原因,河南奸民王良等将“黄粮民地七十八顷四十一亩五分混作佃户子粒投献徐府”[14](P61)。 归德卫军屯地与农户田地杂处一起,多出现军占民地的情况。地方权贵与邻县居民也抢占黄河滩地,经常引发争夺纠纷。如“洪武永乐间,诏河南开垦荒田,永不起科,考境黄河屡迁,豪黠吞并滩地,杞县人因入垦田,得八百余顷。宣德时,朝廷收其地,起科征解。景泰中,刘鹏恐为考之害,奏归之杞。于是种地在考,纳粮于杞,考之空粮为累甚巨”[42](卷13《人物列传》)。如仪封县,因黄河退滩地多,陈留、兰阳与山东曹、单,直隶东明等县人民来县开垦住种,造成县际赋税纠纷不断。这些兼并或抢占田地,都使赋役征派混乱,民间诉讼增多,对里甲制度构成冲击,使地方社会矛盾尖锐化。
2.人民负担加重
明代黄河频繁的水患,特别是大面积的灾荒,倾圮城镇,吞没农舍村庄,冲毁农田,阻断交通,淹死民众,更使众多受灾者无家可归,成为流民,经常处于死亡边缘。为了防止水患以及保漕护陵,明朝修建与修复许多水利工程,征用大批民夫,使民众负担雪上加霜。如仪封县,“滨于黄河, 常苦差繁赋重”[14](P18),“人民仅有千五百户,应当各处军伍、匠作、厨役、力士,并王府校尉、卫源等冲要驿递,牛驴重差,兼之修理河道……堡季夫役,卷埽筑堤,挖浅塞口,岁无宁日,人无息肩”[14](P82)。弘治三年,白昂役夫25万,筑阳武民堤,治河以防张秋;万历二十四年,杨一魁分黄导淮,役夫20万;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曹时聘挑朱旺口,用夫50万。统治者及治河者首要目标是保漕护陵,无力顾及或根本不虑民众疾苦,加剧了社会动乱与农民起义。如万历二十七年,“浙江民赵占元至徐州谋作乱,徐州及丰沛人多有从者”[43](卷5《纪事表》,P93),其中黄患即为一个重要原因。
四、治河思想发展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发,使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治河思想主要体现在刘天和《问水集》、万恭《治水筌蹄》与潘季驯《河防一览》等著作,以及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王恕《王端毅公奏议》、李若星《总河奏议》等奏疏中。治河思想由分流而治、北堵南疏,发展为束水冲沙与蓄清刷黄,给后世治河者以深刻影响,在中国治河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一)分流而治、北堵南疏
洪武时,百废待举,经济实力未允大规模治理黄河,加之,南京为都,虽军事上有漕运需求,但无关国家安危。明初,宋濂虽主张对黄河分流治理,但政府多以免租、赈灾、护堤来处理黄河水患。永乐时迁都北京,疏浚开通运河,漕粮北上,黄河水患威胁漕运,亟须治理。至此,治河与治漕交织,出现分流而治、北堵南疏治河思想,代表人物有徐有贞、白昂、刘大夏与刘天和等。
正统十三年黄河于新乡八柳树决口,洪水直抵张秋,沙湾一带运道冲毁。朝廷派王永和治理,效果不显,后虽几次派人治理,又被冲决。景泰四年,佥都御史徐有贞提出置水闸门、开分水河、挑深运河三策。第二策言:“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黄河之势大,故恒冲决;运河之势小,故恒干浅。必分黄河水合运河,则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请相黄河地形水势,于可分之处开成广济河一道。”[10](卷37《言河湾治河三策疏》,P284)此即分流而治,以黄济运。由于黄河积淤效应,其分黄济运,不久即给黄河大堤与运河带来危害。弘治二年,河南境内河大决,再次冲决张秋运河,命白昂为户部侍郎治理。白昂在河南考察后,基于北决口已淤,南流合颍、涡的支流水脉颇微,建议在南岸“宜疏浚以杀河势”,“于北流所经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5](卷83《河渠一》,P2021),即北堵南疏思想。实践中,白昂“乃役夫二十五万,筑阳武长堤,以防张秋。引中牟决河出荥泽阳桥以达淮,浚宿州古汴河以入泗,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至宿迁以会漕河,上筑长堤,下修减水闸。又疏月河十余以泄水,塞决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5](卷83《河渠一》,P2021-2022)。二年后,河又决冲张秋,弘治六年,以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张秋运河。刘氏疏其南下入淮,浚黄陵岗南贾鲁旧河、孙家渡等,使黄河由颍、涡以及归德、徐州入淮,同时北岸修数百里长堤,阻其北流,保护运河,是分流而治、北堵南疏思想的全面体现。于是,大河“复归兰阳、考城,分流迳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5](卷83《河渠一》,P2024)。其后刘天和在这一治河思想的基础又有所发展,提出“植柳六法”,著《问水集》,但总体仍是分流而治、北堵南疏。
(二)束水冲沙、蓄清刷黄
北岸筑起长堤后,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黄河对张秋运段的危害,但归德以下地区,仍多次夺运,且威胁凤阳皇陵、寿春王陵、泗州祖陵安全,更令统治者不能容忍。在治河争论中,束水冲沙、蓄清刷黄治河思想发展起来,并被付诸实践。
束水冲沙观点,早已有之,王變时大司马史张戎治理黄河策略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而成空而稍深”,针对民引水灌溉情况,提出“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44](卷29《沟恤志》,P1697)明代,万恭《治水筌蹄》详细记述了束水冲沙之策:“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则可浅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则南北堤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45](P50)河入河南后,“水汇土疏,大穿,则全河由渠而旧河淤,小穿,则水性不趋,水过即平陆耳。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缓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吾从而顺其势——堤防之,约束之,范我驰驱,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水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趋其高,河乃不决。故曰黄河合流,国家之福也”[45](P27)。万氏束水冲沙思想,潘季驯深有体会并发展之,于治河所用。
自嘉靖四十四年至万历二十年,潘氏先后四次主持治河。潘氏言:“黄流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非极汛溜,必致停滞”;又言“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46](卷2《河议辩惑》,P170、P171)束水冲沙思想在潘氏治河过程中得到实践,且一定时期内收到成效。他又认为:“清口乃黄淮交会之所,运道必经之处,稍有浅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须令全淮之水尽由此出,则力能敌黄,不为沙垫。偶遇黄水先发,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浅阻。然黄退淮行,深复如故,不为害也。”[46](卷3《河防险要》,P189)这即蓄清刷黄思想,潘氏大筑高家堰,逼全淮之水出清口,与黄合流,冲沙入海。
潘氏践行束水冲沙、蓄清刷黄思想,不仅在明代得到统治者认可并有显绩,也被清廷奉为圭臬。潘氏在治河实践中把几千年来单纯治水的主导思想转为强调治沙,水沙并治,这是治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得到今人认可。如李仪祉认为“潘氏之治堤,不但以之防决,兼以之束水刷沙,是深明乎治导原理者也”[47](P19),故治河之法,潘氏得其要诀,“盖自王景以后,贾鲁虽智术胜人,而遭逢乱世,未能扩展,乃至潘氏,而再收治河之功者也”[47](P20)。张含英说:“潘季驯氏倡‘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之议,一改疏、濬、塞并行之说,开明、清治河之新途径。潘氏对于治河,研究之精深,为历代最。”[48](P22)郑肇经评价:“宋明以来,司河者惟知分河杀势,如庸医之因病治病,而不寻其本源,季驯天才卓越,推究阃奥,发前人所未发,成一代之殊勋,神禹以来,一人而已。”[49](P59)
潘氏治河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河道畅通,但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而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在下游,下游河床不断抬升,长此以往溃堤也在所难免,如万历十五年“河流散漫,自开封封丘、偃师等处,及直隶东明、长垣地方多有冲决”[39](卷191,万历十五年冬十月乙亥,P3595)。这给漕运和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威胁,因此遭到了张企程、杨一魁、王士性等人的反对。因而,与束水冲沙、蓄清刷黄相对的“分黄导淮”思想产生,主张在黄淮交汇的黄河下游河段处开分水河以杀水势,导淮水入长江或者其他河流入海,以减轻淮河流域的水患。但是,由于主张分黄导淮者内部分歧颇多,言多行少,又受“分黄之工遂成,则黄淮不交,有伤王气”[39](卷295,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丙申,P5497)思想影响,人工分黄导淮未能较多践行。直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决口,东北流入渤海,黄、淮最终分流。
五、结语
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黄河水患至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研究中国黄河水患,透彻了明代就把握了整个问题的关键。河南黄河水患与明王朝相始终,前期最为严重,后期则是最为严重的水患区域之一,在明代黄河水患研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恶化。黄患所及之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许多滨河城镇走向衰落。黄河水患给整个官场生态也带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黄河水患影响下的治河思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束水攻沙,蓄清刷黄。这些又与保漕护陵交织,使得黄河水患对明朝影响超过对历史上任何其他王朝的影响。
基于黄河水患给明王朝带来的巨大影响,清朝在利用明王朝治理黄河水患成效的基础上,进行着更为主动的黄河治理,如继承并发展束水冲沙思想,在防范与处理河患时集历代之大成,更好地将设官、仓储、河工、调粟、通商、蠲免、抚辑流民等措施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发展与秩序稳定。但终清一代,也未能使黄河真正安澜,这足以令后人深思。
时至今日,如何在黄河安全时期就做好水患防治,如何在水患来时,保证人民生活、社会安定与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减轻危害,依然是值得思考的课题。毕竟,黄河不能永作地上河,这是人们不忍也不愿一直看到的。
注释:
①定设总河官职时间,史料记载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正德四年(《明神宗实录》卷197,万历十六年四月甲寅,页3705;张廷玉《明史》卷73,页1775);二是正德十年 (《明世宗实录》卷144,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庚戌,页3350;《明武宗实录》卷126,正德十年六月己未,页2516);三是正德十一年(傅洪泽《行水金鉴》卷165,页566;朱国盛《南河全考》卷下《河官考》,页61)。实际上,后两种说法都是以赵璜总理河道为标志的。
[1]黄河的治理与开发[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2](明)丘濬.大学衍义补[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3]黄河水利史述要[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
[4]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7](清)田文镜,王士俊.(雍正)河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8]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陈桥驿,注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10](明)徐有贞.言河湾治河三策疏[A].陈子龙.明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清)滕永祯.(康熙)寿张县志[Z].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12](明)储珊.(正德)新乡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9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
[13](明)刘天和.问水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14]佚名.(嘉靖)仪封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选刊续编:第5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
[15]陈洪友.近代山东土盐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
[16]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M].北京:农业出版社,1977.
[17]周志远.农田水利学[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
[18]张含英.黄河志:第3篇[M].上海:编译馆,1936.
[19](清)周玑.(乾隆)杞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8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20]明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21]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22](明)胡谧.(成化)河南总志[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4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23](明)社 绪 宦.(嘉靖)兰阳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52册.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
[24]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25](明)李嵩.(嘉靖)归德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
[26](清)纪昀.历代职官表[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7](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8]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29](明)朱国盛.南河全考[M].续修四库全书:第7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0](明)车玺.治河总考[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31](清)傅泽洪.行水金鉴[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32](明)刘隅.治河通考[M].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3](明)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4]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35]江晓成.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J].求是学刊,2015,(5).
[36]明穆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37](明)朱国盛.南河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2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38](明)谢肇淛.北河纪[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39]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40]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41]明武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42]张之清.(民国十三年)考城县志[Z].铅印本.
[43](清)吴世熊,朱怡.(同治)徐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5](明)万恭.治水筌蹄[M].朱更翎.整编.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46](明)潘季驯.河防一览[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47]李仪祉.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A].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C].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
[48]张含英.治河策略之历史观[A].治河论丛[C].上海:编译馆,1936.
[49]郑肇经.中国水利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