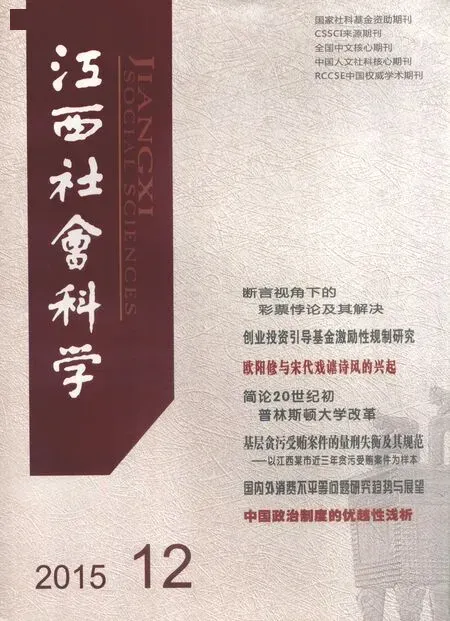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2015-04-15■冯芸桂立
■冯 芸 桂 立
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冯 芸 桂 立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宋代;商人;社会慈善救济
冯 芸,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桂 立,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云南昆明 650000)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同时其社会救济事业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整个两宋时期,其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是前代社会无法企及的。而宋代社会救济事业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不仅源于国家权力层面的重视,形成了制度化的政策措施,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民间社会力量对社会救济的积极参与,而商人作为宋代平民社会兴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商人参与社会慈善救济的主要形式
(一)通过赠物施药、收恤孤独、安置病老、济婚助丧等方式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救助
这是宋代商人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最基本的形式。如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记载长期寄住于杭州凤凰山的“江商海贾”、“数中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暖其体。如此赈于饥寒得饥, 合家感戴无穷矣”。[1](卷一八,P173)检索宋代方志、文人散记、笔记小说、谱牒等,似此等乐善好施、救助贫弱危病的义举于宋代商人而言可谓比比皆是,兹举数例如下:
绍兴诸暨商人张绪,“平居固救邻曲,多趋人急,或窭且病,遗之珍药,不以贵靳”,“尝大雨雪,寒泫积日,府君登楼凭眺,有至脯西无炊烟者,然发困分赡,所全活甚众”。[2](卷二二,《张府君墓志铭》)
成都以商致富的刘革,“好施惠出天性,凡以冠昏贫病死徙叩门丐贷,无戚疏高人,皆实而归”[3](卷七六,《刘府君墓志》)。
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友人以贫不能葬其亲者……即为买田,出钱以办丧事,而友人之亲得葬者五丧”。“至于字亲族之孤,急交游之难,赖其施者甚众。”[4](卷三六,P1174)
北宋中期“徙家京师(开封),卖药自给”的陈靖,“或遗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尝有所蓄”[5](卷一,《陈靖》P10)。
因靖康之难而流落南方的太原人张勰,后航海交趾、勃泥诸国而致富,其“同宗有漂泊江浙者,往来必周其乏,女无归者,或为资谴,故人以穷归君,欣然发囊无纤啬态。北人多称之”[6](卷七,《太原张君墓志铭》)。
河南洛阳胡和叔“殖货至于巨万”,不仅自己抚育孤女,且“其子娶张氏,张巨产而无后,欲以产遗婿,和叔谓其子曰:‘丈夫无因人,矧于义可乎?不若请賙彼亲族。’遂竞不使受”[7](第42册,P77)。
江西饶州兼营农商的张潜,“贫病无归者,饮食医药之;亡则给具棺给地以葬。游官之士以患难告者,无不得其所欲”[8](第二编《北宋墓志》,《通直郎张潜行状》,P85)。
江西修水以商致富的谈资“賙亲戚之急,嫁孤遗之女,掩弃胔,举贫梓,施衾于寒,设食于囚。义当为者君必为之”[8](第三编《南宋墓志》,《吉州助教谈资墓志铭》,P184)。
临川商人吴伯俞,“岁饥低谷价以惠贫民,疾病不能谒医者,为发药治之,赖而活者颇众”[9](卷十,P121)。
邛州经营茶场的张子履,“家故饶财而好施,岁具布褐百称以给老贫,行之不倦,施而不报”。甚而“邛州大饥,君恤穷民,以数万茶场典”[10](卷二三,《张子履墓志铭》)。
(二)于灾荒之时,用所积米谷减价出粜或无偿赈济以惠贫乏
在灾荒之际,不乏商人本着向善乐施、积财能散的好义精神以粮食减价出粜或无偿赈济,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如丰城人管迪“尝载粟抵他郡,岁适大饥,谷价翔踊,众商皆意得,公独低价以粜,仅不至折阅。比辛卯岁大旱,有司劝督富室移粟赈济,人多贿吏求免,公独发廪辇运,不惮劳费,粜溢其数”[8](第三编《南宋墓志》,《管迪府君墓志铭》,P154)。黄岩人黄原泰,“性乐施予,岁歉,贸粟于闽浙,损半直以济邑人”[11](卷六,《人物下)。 前述江西饶州人张潜,“春夏之交,大发仓廪,率减市价十之一,小歉则散之,如是者三十年,环旋数百里闻,谷价不踊,细民赖之,虽甚饥无流徙者”。江西修水人谈资也曾因“往岁民艰食,君置廪诸乡,贵籴贱粜,率以为常”。庐陵吉水人王公权善于经营,“闾里资产至数万计。熙宁中岁大旱,民间谷皆前此费去,而君家廪庾相望所至,皆完实……于是,悉发所藏谷为平其直,不当价之十七八,远近赖以活者数万人”[12](卷三二,《王公权墓志铭》)。
(三)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
整个两宋时期,民间借贷非常普遍。于借贷者而言,到期偿本付息无论是就经济伦理还是社会道义而言,皆被世人视为理所应当之事,袁采就说:“假贷钱谷,责令还息,贫富相资不可阙者。”[13](卷二,《小人难责以忠信》)因而一些商人对借贷者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甚或对力不能还本者焚券免债的举动,也是商人慈施贫乏、恤穷赈施义举的一种延伸。这类事例,在宋代史籍中也多有记载。以“煮盐为富人”的井研人青阳简,“内外族姻待之以炊者数十家。或以伪券取其金,君与金而焚其券。或为君行钱而负之,君折其券,终善遇之”[14](卷十,P1670)。前述诸暨人张绪,“有所称贷,率薄其赢;里中子钱家因相视为率,不得多责息”[2](卷二二,《张府君墓志铭》)。以商致富的金华人吴圭,“鄙世俗嗜利子,汨贪无艺,以子贷豪取”,“或负约,将剔田屋以偿,则笑谢曰:‘以逋负利人田庐,岂吾心哉?’卒弃责弗取”[2](卷二二,《吴子琳墓志铭》)。 前述江西修水人谈资,“人有逋负,欲鬻业捐产以偿者,君闻之折券毁约”[8](第三编 《南宋墓志》,《吉州助教谈资墓志铭》,P184)。“服贾力穑,卓然遂成富室”的玉溪人赵师孟,“时有贫不能自给者,公贷而与之,或久假不归,一无所问”。[8](第三编《南宋墓志》,《赵师孟府君墓志铭》,P119-120)
(四)捐资道路桥梁、筑陂建堤等公共设施建设
宋代商人资助或参与地方上的公共交通和水利设施建设虽不似明清时期那么突出,但是此等社会公益事业,由于它没有特定的捐助对象,是惠及大众、造福一方的义举,因此更能体现出商人们致富后报效桑梓、回报社会的尚义精神。如北宋时期由民间出资兴建的著名水利工程——福建木兰陂,其兴建就有商人的身影活跃于其间。木兰陂的建成经历了数代人的艰辛和努力,在英宗治平年间,长乐女子钱四娘和其同乡林从世先后捐资筑陂,但皆因陂址选择不当和水流过急而失败,钱四娘并因此投水,以身殉陂。神宗熙宁八年(1075),侯官人李宏“富而能仁”,人称李长者,再次捐资筑陂,他在拥有丰富水利工程技术知识的僧人冯智日的协助下,认真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至元丰六年(1083),终于建陂成功。该陂建成后“凡溉田万顷,使邦无旱暵饥馑之虞,百年于兹。故长者得以庙食焉”。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李宏以何治生之法而致富,但是从僧人冯智日“日贳酒于其家,三年不索酬”[15](卷二,《重修木兰陂记),因而授以李宏筑陂之术的记载来看,李宏可能开设酒店并从事酒店生意,应该是具有商人身份的。类似的例子还有:浙江义乌余彦诚“用家钱百万修废堰潴源水,遇见旱岁,无高下彼我均浸之,邻里沾足”,“其余津梁断坏,病涉之地,靡不修举”。[16](卷十五,《余彦诚墓志》)镇江金坛人陈亢,“殖资治产,家用饶衍而勇于义,不啬施予。家居邑南,地多沮泽,古速渎久淤,壅水为灾,率众筑堤,延袤十许里,以便行者。而浚渎以通洮湖,水患遂息”[17](卷六,《陈亢》)。前述江西饶州人张潜,“桥梁道路艰于往来者,葺之不计费”[8](第二编《北宋墓志》,《通直郎张潜行状》,P85)。
除了出资兴建公共设施外,还有商人捐资教育,如前述庐陵吉水人王公权,“县有学舍,湫隘弗缉,至栋宇败挠,至十数岁,无省视者。君为白官,出私钱十万,与里之仕进者同首其劝学”[12](卷三二,《王公权墓志铭》)。
由于史料的缺乏,笔者只能主要从现存的一些宋代墓志铭中管窥当时商人的一些足迹。特别是虽然宋代商业的繁盛吸引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纷纷投入商海,但是在大部分官僚士大夫和士人的观念中对与商贾争利还是有所保留,因而在他们所撰写的墓志铭中对于墓主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仍持相对隐晦的态度,几乎略而不提。因此,宋代商人投资社会公益事业当远不只上述所提及的这些事例。
(五)以业缘为纽带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
商人以业缘为纽带所建立的同行业者之间的互助救济,是与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建立的保障体系不同的另一个保障系统。如南宋临安的商人“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1](卷十八,P173)。显然,这种行业内的互助救济体系是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业社会成分在宋代社会经济结构中不断增长而逐步形成的。宋代从商人数迅猛增加,商业虽易致富,但是从商所伴随的行业风险,诸如破产、失业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困、疾病、无家可归、死亡等风险显然比士、农、工行业要大。宋时,在工商业者众多的城市中普遍设立了行会,此种商业行会除对外与官府交涉、代表本行承接生意、对内制定种种行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结成行业内部的相互保障,应对商业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并对行内贫困者或疾病者施以救助,以增加本行的凝聚力。刘宰就曾说:“向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其地与资,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忌心,此等风俗可爱。”[18](独卷)这种以业缘为纽带的行业互助救济虽在宋代史料记载中并不多见,但却正是明清时期商人们以商会、会馆为组织而建立的较为完善的行业保障体系的前奏。
二、宋代商人参与社会慈善救济的特征及其行为解析
(一)宋代商人参与社会慈善救济的特征
从上述商人参与社会慈善救济的状况及形式来看,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
1.宋代商人所从事的慈善救济活动涉及社会救济的各个方面,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内容上的广泛性
从形式上看,商人的慈善活动包括了救贫济穷、扶弱解困、赈济灾荒、社会公益事业等不同的社会救济形式。从内容上看,商人慈善救济活动不仅包括发生灾荒人祸时的急难救助,如赈粜施粥、赠衣施药、宽免逋欠等临时性救助,而且他们广泛参与到经常性的社会慈善活动中,如扶弱助困、济婚助丧、养老慈幼、助学济士、筑陂建堤等方方面面,内容十分广泛。从此可以看出宋代商人的慈善救济行为并非偶一为之的偶然性行为,其参与的范围和参与的规模均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从而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2.商人施善行为的慈善客体呈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
中国传统民间慈善救济的慈善客体往往与施善主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而言,这种慈善救助都是依托于亲缘、族缘、乡缘关系所进行的以族内、乡内救助为主体的慈善救济,惠及范围主要囿于家族、宗族、乡里内部的族人、乡党,即受助对象与施善主体都是宗族乡里的熟人,具有明显的“熟人社会”的封闭性特征。而宋代商人慈善所及的范围已有突破过往亲缘、族缘、乡缘等人际亲情关系的模式,商人慈施周济的对象并不像传统民间慈善救济往往限于宗亲、邻里、朋友、故旧之间。特别是在城市中,商人们赈济的对象往往延伸至受灾饥民、城市贫民、乞丐流民、同业贫乏者等原本与自己并无密切联系的不确定群体,甚至是陌生人,在此类救济行为中,施善主体其慈善行为的实施并不以受助对象与己之间是否具有亲近的关系为行动的依据,而主要根据慈善客体的实际需要实施救助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3.实施慈善救济的商人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南多于北,主要以南方商业较为兴盛地区为主的特征
从上述所引史料来看,实施各类慈善救济的商人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区。考之究竟,笔者以为就整个两宋时期而言,南方地区是宋代商业发展最为繁盛、突出的地区,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更是远胜北方,相应地,这些地域的商人财富力量的增强乃至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处于明显的优势。按照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类似于脚本规定了演员的行为,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规定了人的社会行为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19](P311)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前代社会极大的提高,而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必然要通过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社会角色这样一种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财鬻货、以通有无不再是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唯一角色,他们作为一个力量不断壮大的社会群体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公共参与意识,积极地投身各项社会管理事业。因此,在商业较为繁盛,商人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较北方为高的南方地区,商人从事的社会慈善救济也较为突出。
(二)商人投资社会慈善救济的行为解析
无商不言利,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商人之所以为商的重大驱动力,然而社会慈善救济的基本形式是付出而非收益,这显然有悖于商人商业行为利益最大化的抉择原则。在社会舆论层面上,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为富不仁”的思想。宋时,真德秀也说:“仁之与富不相为谋,有富者之力而无仁者之心,不暇以济物;有仁者之心而无富者之力,不能以济物。”[20](卷二五,《上饶县善济桥记》)但是,事实上,我们却看到自宋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富而能仁”、“富而好仁”,对社会需要救助的群体慷慨解囊,以自己的财力奉献社会、报效桑梓,成为民间社会救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历来以富为业、以逐利为目标的商人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对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种行为背后潜藏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
首先,中国民间社会诸如“行善积福”、“积德裕后”等传统伦理意识,是宋代商人投身社会慈善救济的心理基础。
王卫平将古代民间富裕人士从事慈善活动的原因归纳为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仁义学说、佛家的慈悲观念与因果报应思想、民间善书所宣扬的道教思想等四个方面。[21]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部分代表了民间社会施善的心理基础,特别是对于古代商人来说,他们不事生产,以贱买贵卖获取高额利润的职业特征,使商人在世俗眼光中被贴上了“无商不奸”、“阴险狡诈”的标签。特别是经商风险系数极大,稍有不慎就有折阅失本乃至倾家荡产的可能,而在笃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古代社会中,施善就成了商人们寻求心灵救赎和精神慰藉的一条有效途径,他们希望通过施善来缓解因为世人对于他们所从事职业的责难而带来的精神压力,也希望以施善的方式获得神灵的眷顾,保佑他们商途坦荡、财运亨通。这些固然是商人们经营获利后将经商赢余还之于父老、家乡、社会的思想基础和伦理动机,但仅以此为原因,还是难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自宋以来,商人阶层会在社会救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乃至成为民间社会救济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赢取社区生活中的话语权,是宋代商人投资社会慈善救济更为重要的目标诉求。
宋代商品经济的跃进式发展使得商人成为宋代最活跃的一个阶层,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财富、正在兴旺成长中的群体,商人参与社会救济不再仅仅出于“行善积福”、“因果报应”之类的伦理意识。随着财富力量的增长,富人商贾们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有了更高的目标诉求: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声誉的提高和厚德形象的树立创造条件。
按照社会学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财产、权力、声望来看,宋代商人阶层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实力仍处于相互分离状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呼应的地步。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活动能力,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商人以财富为支撑,通过科举入仕、捐纳买官、与贵者联姻等路径获取政治权力,而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则成为商人通过财物的付出来换取提高自身社会声望的有效通道和途径。
通常人们认为:在慈善活动中,捐助者不向受助者索取任何的回报,完全是为了帮助别人,因而这种施善行为理所当然是一种纯粹无私的利他行径。而按照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每一个人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都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在投入与产出中都倾向于尽力缩小自身所付出的代价,扩大自身的收益。在此,似乎慈善行为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相悖的。但是,实质上慈善行为并不像其表面上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利益的纯粹付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捐助者的确付出了实实在在的财物和时间成本,但是他也在付出的同时有所收益,具体而言,其收益一是通过对他人提供帮助,获得一种自身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二是通过他人对其施善行为的积极评价,获得自身声誉的提高。对于宋代商人而言,当他们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之后,经济上的强势必然会促使他们要尽力取得与本阶层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通过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一方面改变在世人眼中商人 “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固有印象,提高自身的声誉;另一方面提升自身和家族的社会地位,进而争取在地方事务中的话语权。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得自宋以来商人阶层在社会救济的公共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乃至在明清时期成为民间社会救济中的核心力量。对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宋代一些轻财好义、热衷公益事业的商人在地方事务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来加以佐证。
如浙江义乌的余彦诚,“乡人无不称其长者,故纷争斗怒者,得其一言,则释然以平”[16](卷十五,《余彦诚墓志铭》)。成都的刘革“好施惠出天性”,民众“至有争阋,不到官府惟府君曲直,则俯首听命”[3](卷七六,《刘府君墓志》)。很显然,这些商人正是由于他们轻财乐施、对乡里社会有贡献,才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敬,从而成为地方上的意见领袖。
这些地方富商不仅平日仗义疏财、扶贫济困,在地方积累了极高的威望,而且一旦遇到盗匪战乱,他们更成为族人、百姓仰仗之势力,甚至成为地方秩序的维护者。如义乌余彦诚,当“宣和庚子,青溪盗起,浙东西诸郡往往失守,彦诚纠率里豪捍蔽乡曲,有奇功”[16](卷十五,《余彦诚墓志铭》)。同样是在方腊之乱时,金华吴圭“徙家聚族,壁险自固”,其他百姓也纷纷投靠于他,且由于他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盗过者亦相诫无窥吴氏,每望屋引去”。[2](卷二二,《吴子琳墓志铭》)诸暨张绪“纠族属聚落,合力保壁,众悉附服,贫丁轻猾,无敢去为椎窃,乡境赖安”[2](卷二二,《张府君墓志铭》)。还有玉溪商人赵师孟,“建炎间,干戈四起,公携族属拉里人,逃伏远遁,屝屦资粮,公悉共焉。林林之众,咸脱虎口之患者,实公之力也。由是远人慕义求聚而居焉”。不仅如此,“公宅之北,邻于鄱阳大湖。爰自兵兴后,群凶之聚,商贾无辜而死者,不知其几千人矣。公以咸誉闻于所司,乃以土 (缺)委焉,公授命之日,治舡、整器械,剿绝奸雄,扬旗舞戈,则寇攘敛袂。迨今江湖肃静,往来之人,谕及公之德者,无不以手加额”。[8](第三编《南宋墓志》,《赵师孟府君墓志铭》,P120)
很显然,这些地方富商之所以成为一方之势力,与他们平日轻财向善、取而散之的尚义精神是截然不可分的。在参与慈善公益活动的过程中,他们固然付出了大量的财物和时间成本,但是也为自身带来了社会效用的提高,不仅赢得了好的社会声誉,也带来了潜在的物质收益增加的可能性。如前述金华吴圭乃以“信实得人和”,越四十年而“储义甚富,而日积月累,资亦高矣”。[2](卷二二,《吴子琳墓志铭》)
三、宋代商人投资社会慈善救济的影响及评价
宋代商人无论是在社会灾荒救济体系,抑或是民间慈善救助体系中均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成为宋代社会保障参与主体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商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能力和财富力量的增加,商人们的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通过扶孤恤寡、乐善振贫、修路筑桥等方式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社会生活中,成为宋代民间社会控制中的重要力量,这是宋代商人阶层力量发展壮大后,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集体发力的结果。而反之,商人们乐输善资、贡献社会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又进一步地扩大了其影响力,为商人阶层社会中坚形象的塑造打下了基础。这种影响力的扩大不仅仅体现在“富商大贾为国懋迁”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前期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对社会秩序具有极大危害性的商人阶层,自宋以来却成为国家维持社会稳定不得不倚重的力量,北宋时苏辙在奏疏中就曾言:“坊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22](卷三五,P762-763)魏了翁在《鹤山集》中也记载,南宋时,“金人大入,东取上津,西断梁洋”,危急之际,全州通判郭公“面谕豪民、富商,倾财募士,寇遂遁去”[23](卷八二,《故太府寺丞兼知兴元府利州路安抚郭公墓志铭》)。
以往有论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们致富之后把大量的商业利润投资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此举消耗了商业资本,影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从而成为阻碍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世资本主义转化的重要因素。在此,我们姑且不论此类观点是否正确,首先,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言,“为富而仁”、“慈心善行”不仅是中国人内在于心的价值伦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同情也是全人类普遍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商人以富为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商人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商人阶层作为社会中的富裕群体,为了保持社会和自身财富的稳定,必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自宋以来,商人们以财富为支撑积极参与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商人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这对于商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人而言,政府处于绝对控制的地位,商人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那么其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社会资源,更有可能连商业上的利益也难以保全。
另外,从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角度而言,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社会资源 (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必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对应关系,而社会慈善公益的实质就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当商人从商业领域赚取巨额财富后,他们将一部分财富投入诸如扶贫济困、修路筑桥、助学兴教等公益活动中,不管他们出于何种伦理动机或现实考虑,从客观效果上看,原本属于他们名下的一部分社会财富,却通过慈善捐助悄然地转移到往往在社会资源(财富)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被捐助者手中,从而使社会资源(财富)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整个两宋时期,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呈现出的是贫富两级的严重分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财产制度,富于分化特征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无不把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推向截然相反的两极,一极是财富高度集中于社会特权阶层和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手中,另一极则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数目庞大的贫民阶层。对此,梁其姿曾言:“大体而言,在宋以前,虽然贫富的差别在中国社会一直是明显的经济现象,但 ‘贫穷’并不构成一个需要解决的特殊经济社会问题。”[24]显然,宋代所出现的这样一个亟须解决的“特殊经济社会问题”,对于始终处于战乱之中、财力困乏的宋政府而言,是没有能力完全予以承担的。而商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为他们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并且随着经济地位提高而不断增强的提升自身和家族社会地位的强烈意识,自然使商人阶层成为弥补政府社会保障不足的重要力量。不唯如此,从社会安全控制的角度考量,商人作为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各种慈善公益事业的慷慨解囊,也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而对有可能走向失序的社会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恰如袁采所言:“如富家平时不刻剥,又能乐施,又能种种方便,当兵火扰攘之际,犹得保全,至不忍焚掠污辱者多,盗所快意于劫杀之家,多是积恶之人。富家各宜自省。”[13](卷三,“刻剥招盗之由”条)因此,宋代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把一定的财富投资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不仅是宋代较汉唐为高的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体现,它也是在宋代贫富日益加剧的情势下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继而对社会贫富分化进行控制并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不论这种方式的实施效果如何,其在社会意义、价值伦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1]吴自牧.梦粱录[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40.
[2]范浚.香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洪适.盘州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秦观.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5]张师正.括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吕祖谦.吕东莱文集[M].丛书集成本.
[8]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9]谢迈.谢幼盘文集[A].宋集珍本丛刊(第33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4.
[10]黄庭坚.山谷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万历黄岩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12]刘弇.龙云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袁采.袁氏世范[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5]郑樵.夹漈遗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郑刚中.北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佚名.京口耆旧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车若水.脚气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20]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M].四部丛刊本.
[21]王卫平.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J].江苏社会科学,1999,(2).
[22]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魏了翁.鹤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立霞】
K24
A
1004-518X(2015)12-01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