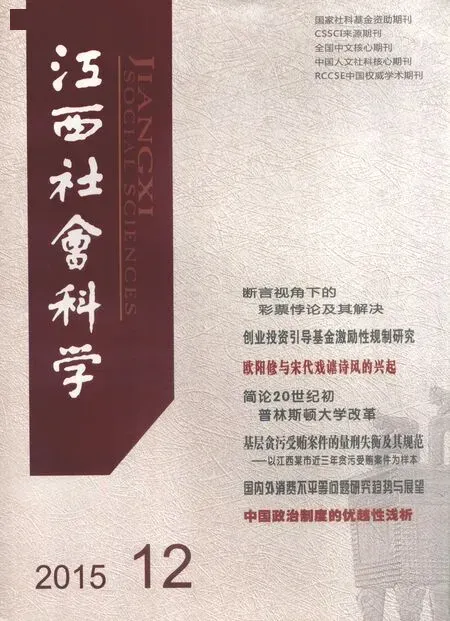简论20世纪初普林斯顿大学改革
2015-04-15■张澜徐禹
■张 澜 徐 禹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除了极少数保守的宗教气氛浓厚的高等教育机构仍然固守传统,美国多数综合性大学开始积极做出调整,对社会需求做出回应。当时,美国综合性大学至少存在四种相互竞争的办学理念与功能定位。最早的一派直接承续中世纪大学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学术保守派,因为与世俗生活不产生直接关联,学术保守派于19世纪60年代末受到以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为首的职业导向派的挑战。他们提倡大学应以实学和职业为导向,推崇自由选课制度,让学生自己选择任何对他们未来职业有用的课程。职业导向派主导的大学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奠基于培养社会需求的职业人才。但是,这种合法性是一种弱合法性,因为它使综合性大学有演变成高等专科院校的危险。19世纪80年代,受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美国教育界为大学增添了科学研究的使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但是,科学研究派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旨仍然与社会现实的需求存在距离。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念:融精神提升和学术训练于一体的教育。持这一观念的教育家反对大学的职业导向和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强调大学为国家服务的功能。这四种教育观念既前后相继,也一同并存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高等教育界,形成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1](P93-94)。
威尔逊的教育观念显然属于最后一个类型。他认为,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是培养和储备国家高级人才之地。高级人才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标准:明了国际国内的时代精神和具备精深的专业修养。[2](P134)而当时哈佛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等机构的办学定位有将综合性大学办成职业技术大学的倾向,难以培养出能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才。1896年,威尔逊发表题为“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提出是服务精神,而不是学术,在国家层面为大学赢得了一席之地。[3](P30)也就是说,威尔逊认为,学术研究无法为综合性大学提供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处在20世纪初的美国综合性大学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有能力服务于国家的需要。1902年,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的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选择了年轻的威尔逊出任校长。锐意改革的威尔逊发表了“为国家服务的普林斯顿大学”就职演说,明确提出:“学术机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服务公众存在的。随着国家事务日益复杂,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国家的需要是非常明确的。国家需要高效而智慧的人才。”[4](P170)明确了1896年演说中“服务精神”的内涵,即普林斯顿大学之为国服务,就是为国家培养高效而智慧的人才。亦即,能否为国家培养高效而智慧的人才决定普林斯顿大学的兴衰存亡。威尔逊显然也认为,所有综合性大学都要承担起培养高效而智慧的人才的责任,以此证明自己有资格在国家层面享有一席之地。威尔逊没有否认教育和研究是大学的两大功能,他想要强调的是,如果大学脱离国家的需要,它的教学和研究两大功能本身就失去了目标,无法为大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基础,这就好比中世纪大学如果培养不出合格的神职人员就没有存在的资格一样。
威尔逊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教育,将教育视为具体而微的政治,把教育看成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全局的政治观念来办教育。他说:“我的责任几乎完全是政治的,我自己总是将大学视为一个政治机构,我不是将大学看作一个直接处理政治问题的机构,而是指大学是一个促进国家权力和整个智慧的机构。”[2](P481)威尔逊为普林斯顿大学,也是为美国所有综合性大学提出了存在合法性的现代转型问题,并提供了自己的答案:为国家服务。这反映了普林斯顿大学为满足社会现实需要而积极入世的心态,也反映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大学教育观念;这也是当时美国大学对日益复杂的国内问题和20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做出的回应,说明美国大学的办学功能定位开始出现新变化,国家的需要开始成为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二、重塑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为国家服务”这一办学定位,普林斯顿大学重建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能否落实“为国家服务”的办学宗旨,取决于能否确立适合时代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出“高效而智慧的人才”是普林斯顿大学改革所要达成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所谓高效而智慧的人才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前面提及,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念:融精神提升和学术训练于一体的教育。此处之精神与神学无关,指的是时代精神。威尔逊希望看到美国大学生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变成一个“世界人”,具备世界的眼光和精神;同时,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成为真正的专家。前者需要综合教育,以获得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后者需要单科的体系性教育,以达到知识的精专:“如果没有专业训练前的综合教育,他的知识是扁平的,浅陋的。专业人员应该接受综合教育,哪怕是使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不致闯入明显自己无知的领域。”[5](P285)可见,威尔逊领导下的普林斯顿大学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通专结合的高端人才,是为美国社会培养领导精英。这与他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的观念完全相符。普林斯顿大学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显然针对的是当时美国名校,尤其是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职业导向派力主的职业人才培养目标。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综合性大学被职业导向派主导,力主围绕学生未来职业取向开设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职业化课程。为了满足学生需要,这些大学实施自由选课制度。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主张学术自由,尊重学生自我选择的权利,认为只有选修课才能满足学生的兴趣。在艾略特的领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全面实行选修制。到1895年,除英语和现代外语为必修课外,其他课程均为选修课。自由选修制保证了学生自由选课的权利,但又造成学生培养质量低下。自由选修制对学生的课程选择没有任何要求,学生的选课缺乏系统性;学生往往选择容易取得学分的课程,无法获得任何学科的系统知识。
时任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就激烈反对艾略特的改革,并公开表示不接受自由选课制度。他认为,大学生还不够成熟,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门课程。因此他反对给学生自由选课的权利。[6](P6)
威尔逊在1903年的一次关于教育的演讲中,这样评论当时盛行的自由选课制度:“目前的自由选课制度是给学生一系列使其困惑的课程,无论这个学生有多勤奋,他也不可能在四年内完成这些课程。老师们对学生不提供任何建议。”[7](P80)在当时流行的自由选课制度之下,老师们让学生自己做选择,选出自己感兴趣的科目。既不告诉学生,学习的殿堂应该从哪里入门,也不告诉学生应该从哪里出门,这必然导致学生学无所专,难有所成。因此,自由选课制度遭到质疑在所难免。
威尔逊批评把大学办成培养社会劳动力的机构,抨击当时美国大学存在的严重的技术主义办学倾向。他指出,大学教育是很高层次的教育,大学教育“是为了那些能看到更广阔舞台的少数人”[4](P176)。
威尔逊认为,唯一可取代自由选课制度的做法是在数门课程中进行选择,数门课程围绕一个主导的课程。在任何一个科学的学科中,文学和哲学可以作为其补充,如古典学科,就必须配以科学和哲学使其丰富。这样,学生在学习每一门课程的时候,都会有学科占主导位置,并由那些经验丰富的人设置课程,从而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7](P82)基于此目的,1903年开始普林斯顿大学推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课程改革运动,以实现培养高层次的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
三、重组行政管理机构
普林斯顿大学要实现自己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抛弃威廉·佩顿时代的自由选课制度,按照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要实现课程体系改革,就需要对普林斯顿教学行政管理体系进行重组,为课程体系改革提供组织保障。课程体系改革与行政管理体系重组是一体两面的,课程体系改革方向决定行政管理机构重组的走向,成功的行政管理机构重组为课程体系改革保驾护航,为实现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提供组织保证。
在威廉·佩顿担任校长的30余年里,普林斯顿大学的管理体系杂乱无章。当时管理体系由学院部和科学院组成。学院部包括哲学系、语言文学系和数学与自然科学系。从学科属性来看,哲学系和语言文学系属于人文学科,数学和自然科学系是理学学科,将两个不同属性的学科大类整合在一个学院里,显得不伦不类。哲学系包括伦理与精神哲学(包括心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艺术史学和建筑学;语言与文学系包括各类语言和文学(不论是古代的语言和文学,还是现代的语言和文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系则包括所有科学,既有物理学又有生物学。这些系包含的专业相互之间虽然不无关联,但是区别明显,整合在一个系内,表明普林斯顿大学管理层对这些专业属性的认知仍然不是很明确,这与当时各个专业仍处于分化和定形过程中密切相关。
属性不同的专业混杂在一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大的问题是科学院与学院部的课程设置上有很大的重复。科学院设科学系、市政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科学院内设置的科学系与学院部内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系显然重叠,必然导致管理组织重叠和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这些科系或专业没有正规组织,教授和教授之间没有行政管理关系,每一位教授只向校长负责。校长通过一个一个的教授来管理学校,而不是通过一个二级教学管理组织来进行。尽管校长常常亲临管理一线,但是精力有限,仍然无法面面俱到,导致当时学校管理比较混乱,普林斯顿大学在常春藤联盟中学术地位不高,学生培养质量较差,学校声誉一直不太好。因此,普林斯顿大学要想达到人才培养目标,有必要依据学科属性对学科进行重新组合,在此基础上改革教学行政组织,在校长与教授之间设立中间管理层。
1903年11月3日,威尔逊向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提交一份报告,提出校系重置方案。根据方案,全校所有专业将纳入到11个系,包括哲学系,历史和政治学系,艺术与考古系,古典学系,数学系,英语系,现代语言系,自然科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和天文系。除了艺术与考古系之外,其他每个系都设置一名教授作为系主任负责各系的日常管理,并明确了系主任的职能,所有教授对系主任负责,系主任对校长负责。这一方案获得了董事会的支持并于1904年4月26日正式生效。[8](P252)相比威廉·佩顿时代,普林斯顿大学在校长与教授中间设置了一个管理机构——系,通过系来管理各个系的教师及其教学活动,大大减轻了校长的工作压力,校长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学校发展的要务上。
1905年6月12日,在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的研究课程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Course of Study)上,系的设置被认为是一项重大创新。[8](P128)校系两级管理体系,层次分明,权力集中,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效率。行政管理机构重置为课程改革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四、重组课程体系
1903年11月3日,在给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的报告上,威尔逊还描述了课程改革计划。“一年级之后的课程,我们准备开放不少于10种研究课程,学生从中选择一种。这样的目的是使这些研究课程都能够围绕某一个核心研究展开。尽管每一组研究课程都有某一主体研究作为核心,但它会因为其他研究课程的辅助安排而具有完整的通才学科的性质。例如,每一组科学课程,会配以文学与哲学研究使之丰富,每一组文学或者哲学研究将配以科学研究课程。这样,每一组课程本身似乎都成了深思熟虑的通识课程计划。”[7](P72)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系的课程设置都将具备文理兼修的特点,这样,不论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能够有比较广阔的视野,也学有所专。
1904年4月25日,普林斯顿校董事会“研究课程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Course of Study)通过了威尔逊提交的课程改革计划,开始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彻底的课程改革进程。按照威尔逊的计划,对本科生的课程设置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与当时流行的自由选课制不同,普林斯顿大学将课程的选择限定在有限的选项当中。
大一的新生必须接受学校安排的必修课程的学习,如拉丁语、英语和数学等。“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这些人来到这里为以后的事业做准备,必须使他们经过磨炼,才能完成以后的工作。”[7](P381)
根据新的课程设置,学生在大二的时候必须修读一学期的逻辑学和心理学;此外,学校将为学生开放选修课,但这些选修课也是有限定的,必须在基础课程中选择。另外,大二课程的一个创新,便是给那些精通哲学、政治、文学和其他人文课程,但不精通希腊语的学生提供一个文学学士学位;理学学士的入门也不需要学习希腊语。这个新的文学学士学位被贴上了 “为进行人文训练而不学习希腊语”的标签。威尔逊和其他一些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都迫切希望取消希腊语和传统的学士学位,他们认为作为一门死语言的希腊语,早应该退出本科生的必修课行列。其结果就是两个文学学士学位的妥协,一个需要希腊语,另一个不需要希腊语。这个妥协一直延续到1919年3月17日,普林斯顿在下一次本科生课程重大改革中,表决放弃希腊语作为文学学士的必要课程,并取消了新的文学学士学位。总之,大二课程的学习是为了高年级的学习做准备。在大二学年结束的时候,学生需要在11个系中选择自己专业所属的系,以便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进行专业学习。[7](P387)
大三的时候,学生学习的课程数目由原来的七门课程,缩减到五门课程,但每门课程的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两小时扩展到每周三小时。五门课程中,有两门课程是在所选择的系中做出选择;第三门课程是推荐给学生关于他专业的相关支撑性课程;第四门课程是在所选的院系之外选择一门课程;第五门课程便是按学生的意愿去选择科目。直到学生大三结束,学生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重新选择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在重新选择的系中修完两门课来证明他有进入这个系的资格。也就是说,在一名学生升入大四之前,他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系,并在选择之后在该系中学习。[7](P382)
大四的时候,文学学士生和理学学士生每学期可以在开放给大四学生的课程当中自由选择七门课程。当然,一些高级课程需要基础课程作为先决条件。[7](P282)这样既限定了学生的选择范围,保证了学生知识学习的系统性,又尊重了学生选择课程的自由权利。文科生的学科知识体系中有基础性理科课程,而理科生的学科知识体系中有基础性文科课程,既通识也专业。
从普林斯顿大学四年课程安排来看,前两年的课程是不分专业的通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为三年级确定专业学习打基础,体现了人才培养目标中的通,三年级和四年级课程以专业课程为主,体现了人才培养目标中的专,实现了通专结合的课程设置。这一设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课程改革实施的第一年,只有12名大四学生要求改变院系。[8](P128)对于1904年开始实施的课程改革,整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8](P129)
五、塑造平等的校园文化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要育人。威尔逊认为,美国大学生应该成为符合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的合格公民,为此需要培养学生的平等意识,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聚居在一起是一个必要措施;而导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则会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塑造他们的平等意识,同时提高学生的学术修养。
1905年6月15日,45人以助理教授的名义被任命为导师。[8](P131)1906年开始,普林斯顿大学全面推行导师制度。该制度的目的是向本科生提供只有小学院的学生才能享有的教师与学生亲密接触的机会,使教师成为学生的顾问、引路人,甚至是朋友。老师和学生在很多场合经常联系,这些联系使得师生彼此了解加深,形成良好的平等关系。
为了配合导师制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展,便于学校的管理及教育,威尔逊提出了“住宿学院计划”(quadrangle plan)。该计划预备将学生组合到四个年级混居的数个生活区,并将教师安排其中,促进导师制度的贯彻,同时也培养学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意识。
普林斯顿大学起初没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只给学生提供寄宿服务。意气相投的学生通常就自愿组合在一起吃饭,而且在没有找到足够多的适宜寄宿房子的时候,他们就租住在一起或者自建生活区。[2](P180)这样,高年级的学生就自愿组成了俱乐部,当然,低年级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俱乐部将各个年级分成了碎片。它们的组织完全脱离了校方的监管,与学业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更糟的是,这些俱乐部不利于学生养成平等观念,与正在走向大众民主时代的美国社会需要背道而驰。威尔逊计划废除这些所谓的“吃喝玩乐”俱乐部,但这一计划遭到了许多富家子弟及其父母的反对。
“住宿学院计划”原本是为了消除富家子弟与平民子弟之间在思想和生活上的隔阂,在校园中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然而由于受到资金条件的限制,“住宿学院计划”的争论一直到威尔逊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也未结束,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最后否决了这一计划。当然,“住宿学院计划”并没有被遗忘,于1978年被重新提出来,学校决定建立两年制住宿学院,为一二年级学生服务。1983年,巴特勒住宿学院正式启用。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决定建设包含四个年级学生的住宿学院,2009年秋季正式启用。威尔逊100余年前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严格意义上,“住宿学院计划”是违背民主精神的,因为其剥夺了学生长期享有的住宿选择权。毕竟,寄宿制一直是美国大学的传统之一,它背后隐含的是一种自由选择权。威尔逊为了在学生中养成平等关系,促进民主,力主实施“住宿学院计划”,实际上是要以平等价值平抑自由价值,这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仍是不合时宜的事情,是一项超前的计划,招致失败在所难免。
六、普林斯顿大学改革对美国大学的影响
这场改革对美国大学最重要的影响是,明确提出大学为国服务的办学宗旨,重建了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1902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综合性大学和高等专科学院两大部分,高等专科学院本身就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成立,不存在合法性重建问题;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为代表的职业导向派靠拢社会需求,力图使自己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但是模糊了高等专科学院与大学的办学功能差异,贬低了自身的价值,并没有真正为大学建立起新的存在的合法性。普林斯顿大学的“为国服务”宗旨既响应了时代需要,又明显与专科学院区别开来,从而确立了大学在新时代的合法性基础。
大学合法性基础的重建带来的重大影响是它改变了大学与国家的关系。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教育虽然不再局限于教学与科研两项功能,但是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若即若离,大学教育与国家需求脱节。威尔逊的普林斯顿大学为国家服务演讲,明确提出大学的办学宗旨和功能不仅在于教学和科研,更在于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国家的需要开始成为大学办学的重要动力,大量的国家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大学,大学的独立自主地位开始面临挑战。
普林斯顿大学最早实施校系两级管理体制,第一个在本科生中施行导师制,一跃成为美国大学学习的楷模。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采用了同样的制度,此后,校系两级管理体制、导师制度逐步被全美各大学采纳,形成美国教育的一项管理制度,至今仍然行之有效。普林斯顿大学课程改革引发了哈佛大学等一系列大学类似的改革。1902—1903年,哈佛教职工委员会调查了哈佛大学课程模式,找到了自由选课制度中存在的不少缺陷。调查报告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1908年哈佛大学决定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相结合制度。1909年,劳伦斯·洛厄尔当选哈佛大学校长,接替艾略特并开始实施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制度。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要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保证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9]在此期间,洛厄尔将威尔逊和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学习的范例。洛厄尔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后不久,便邀请威尔逊来哈佛大学做了题为 “学习的精神”的演讲,该演讲在一定程度上攻击了自由选课制度。洛厄尔大力赞扬了威尔逊的研究,并在公共场合支持他的观点。所以,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实施的课程改革成为当时美国其他高校课程改革的模板。
当然,这场改革的后续效果未必都是积极的。威尔逊在“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的号角声中展开的这场改革,主动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结果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地位让位于国家的需要,短时间内没有明显功利效果的科学研究很可能被淘汰,大学办学开始进入功利时代。大学办学的国家利益取向开始在综合性大学扎根。提倡“为国家服务”的大学教育功能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因为威尔逊把大学为国家服务的功能拔得太高,明显高于教学和科研的功能,导致教学与科研两大功能等而下之,大学有可能成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而美国国家利益常常被利益集团绑架,这会进一步强化大学的功利倾向。如今,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功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利益集团的渗透无处不在,这种倾向与普林斯顿大学为国家服务的宗旨之间的内在关联,值得深思。
[1]Ronald J.Pestritto.Woodrow Wilson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Liberalism.Lanham,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5.
[2]Arthur S.Link 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17,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3]Arthur S.Link 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10,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4]Arthur S.Link 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14,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5]Arthur S.Link 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8,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6]柴晋芳.哈佛大学第五次通识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08.
[7]Arthur S.Link 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15,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8]Arthur S.Link 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16,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9]李志峰,周璇.哈佛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及其影响[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