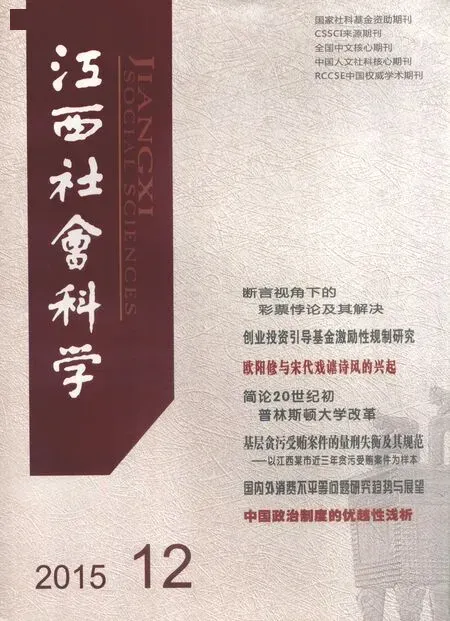从“现代”到“后现代”:林耀德与台湾都市文学的经验书写
2015-04-15林秀琴
■林秀琴
从“现代”到“后现代”:林耀德与台湾都市文学的经验书写
■林秀琴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视域下的都市经验书写与文化论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至90年代“新世代”作家群有显著的发展,其主要线索是从早期较为普泛的存在主义论述转入资讯文明、后工业时代消费文化语境下个体的异化与分裂,都市这一承载、演绎、生产现代商业文明与资讯交互的地理空间,正是促进现代性在“后现代”时期质变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它更加彰显了现代性的迷离与眩晕带来的异化体验。对此,台湾“新世代”作家林耀德以其对自我与存在的拷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经验,他不仅捕捉到晚期资本主义混乱失序的时代自我的悲剧性,更说明了分裂的个体与畸变的社会空间如何形成了相互生产的关系。
城市;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集体无意识;自我
林秀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福建福州 350001)
都市文学的兴起、发展是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历史建构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次文类”,都市文学中的“都市”从原始的意义上讲,是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和文学地理空间的设定,因此并非所有的都市文学都可以归入现代主义文学的脉络,对都市生活日常琐碎的忠实记录所呈现的都市经验或文化论述,从美学形式的诸种质素到主题结构的演绎轨迹来看,很可能是和现代主义文学大异其趣的。但无可否认的是,都市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促成和维持着这种内在的文化粘连的源头,即是18、19世纪西方世界在新兴资本主义推动下的“现代性”这一历史经验的生产,城市的崛起被视作 “现代”社会的到来在社会空间上的转型与表征。这一论述最早也最富于代表性的是本雅明对巴黎、伦敦等发达欧洲城市的观察。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本雅明甚至奠定了一种至今仍然深刻发挥着作用的现代性论述,即现代性对传统的断裂和现代性对短暂的、倏忽即过的、碎片化的时间意识及感觉经验的强调。其中有关都市文学的经验书写,恰恰是附属在这种现代性论述之下,或者说是承载着这种现代性论述的特殊的文化形式。
基于这一视角,将都市文学的经验书写置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脉络和现代性的视域,就是自然而然的。以林耀德小说为代表的台湾都市文学经验的书写,是探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借由城市经验视角从“现代”进入“后现代”轨迹的重要线索。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里“现代”与“后现代”并不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分野或者如利奥塔所言的 “后现代”乃是对“现代”的断裂、终结,相反,笔者更属意于将“后现代”视作“现代”的一种延续或者“创新”。所谓创新,是强调它所因应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是 “晚期资本主义”的表述或者“后工业时代”的表述——所呈现的文化结构的变迁和美学传统的更新。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从20世纪50、60年代发端,到20世纪70、80年代,在城市经验书写上已然表现出新的线索与方向,其中最为突出的转折和变化当属以黄凡、林耀德、张大春等为代表的“新世代”作家群。
一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萌芽,彼时留学日本的台湾知识分子将日本现代文学的风貌带入并由此植入现代主义文学的种子。现代主义文学在“光复”之后的台湾地区重新崛起,史学界更多地将其追溯到纪弦1953年创办的《现代诗》、1954年成立的 “创世纪”诗社和1960年由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这些文学现象(事件)借由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渠道,共同表达了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纪弦所宣扬的“新诗乃横的移植, 而非纵的继承”[1](P308),“现代诗与传统诗是两种极端相反完全不同的文学”[1](P314),或如《现代文学》在其发刊词中所言明的“旧有的艺术形式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2],这些说法都建基于“现代意识”的觉醒之上,并以对“现代”的标举来与“传统”相隔断、决裂,从而为引进、移植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在本土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提供合法性。
我们可以借由布鲁姆“影响的焦虑”这一视角,来定位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重新崛起与现代知识精英试图重新架构“文学史”的冲动,但更值得强调的是文学话语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独特表征所能够呈现的社会学的视角和意义。台湾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兴起事实上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这一现实语境在文学层面的映射,简单地说,“光复”之后的台湾经济社会的复苏和工业化时代的浩荡前行,文化领域则由于对“西化”文化思潮的接纳而导致更为深刻的结构性的变更,其表面的征象即是以“现代”来否弃“传统”,而其内在则是呼应社会结构转型的文化质变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上的 “失所”。朱立立在《知识人的精神私史》一书中说:“现代派小说是战后台湾文化危机的产物,这种危机源于一种被迫从传统社会抽离所造成的精神的流离失所,也源于一种文化价值的迷失和自我身份的认同焦虑。”[3](P1)
很显然,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移植进东方的重要典范,并经与本土现代性经验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形态与艺术样式。美籍华人学者张诵圣认为:“台湾的现代主义运动在某些方面强烈地反映出西方现代主义的另一特色:精英式的美学观念。这种精英式的美学观念主要体现为对抗现代中产社会的庸俗功利倾向。”[4](P4)显然,这种论述有意结合雷蒙德·威廉斯将西方现代主义描述为 “资本主义异议文化”的观念,这种论述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现代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其所置身的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的质询与反思——这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反思现代性”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了对工业革命背景下僵硬、异化的理性秩序的反抗,对文化工业背景下膨胀的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线索最终又归结到对都市文明的知识重构与文化再造,都市不仅是现代性的产物,也不只是现代性赖以寄寓的场所、空间,都市更是现代性的生产者,那么,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都市经验的叙写和都市精神的折射就毫不奇怪了。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虽然起于20世纪50、60年代,但现代主义的都市文学书写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真正形成一定的景观,这与台湾地区都市化的历史是相呼应的。诚如张诵圣所指出的,王文兴《家变》所呈现的20世纪50、60年代的台北生活中,关于都市的书写基本阙如,相反,贫困的生活境遇和彼时台北的“前都市”风貌则多有呈现。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为代表的一批乡土文学作家所呈现的城市书写,如《华盛顿大楼》《唐倩的喜剧》《莎扬娜拉,再见》《小林来台北》等,则是在城乡对峙、阶级分野的政治论述里呈现都市文明的“剥削”内核。基于这一原因,张诵圣并没有将上述“左翼”立场下的城市书写纳入现代城市经验书写的脉络。但必须指出的是,乡土文学作家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城市肌理的揭露及批判,事实上也是“资本主义异议文化”的重要构成,它所呈现的都市论述是台湾地区本土城市化经验不可剥离的部分,将其与现代派的城市书写进行隔断将可能破坏台湾都市文学论述的有机性。
在张诵圣看来,对都市文学景观和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有意识的呈现,尤其要以“战后婴儿潮”的女性作家为代表,如袁琼琼的《春水船》《自己的天空》、朱天文的 《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等。张诵圣指出这些女性作家提供的都市景观与经验书写中不乏对现代都市文明之物质丰裕的慨叹和“自足”心态,她将其称为 “中产趣味”“中产性格”。[4](P50)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些文本的确触及了现代社会个体心灵上的扭曲与精神上的畸变,尤其是朱天文的都市叙述中,都市已经被赋予恶魔化的象征,都市犹如啃嗫现代社会个体灵魂的怪兽。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重新接续上了西方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思现代性的传统。但是,与《世纪末的华丽》中主角沉浸于“物”的包围、迷恋于“物”的感觉以及作家在这一命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相比,黄凡、林耀德、张大春所代表的“新世代”作家群对都市文明的揭露与批判,则表现得更为坚决、彻底和淋漓尽致。
从作家年龄代际来说,“新世代”作家群与“战后婴儿潮”作家活跃于中国台湾文坛的时距大约是十年,对这一差别的强调乃是因为,信息社会、资讯文明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已然促使现代性的时空压缩的特征更加显著并对既有的现代性经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颠覆,换言之,信息社会、资讯文明在新近20年来的发展促使现代性加快其自我更新、重构的步伐,即在信息社会、资讯文明主导下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嬗变。黄凡、林耀德、张大春所代表的“新世代”作家即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文化重构和都市文明质变的背景下展开其都市经验书写与文化论述,信息社会、资讯文明的发达超越了传统的伴随着 “物”的丰裕而导致的异化,时空的高度压缩加剧了现代性的迷离或眩晕并创造了崭新的异化体验:一种更刻骨的更具有摧毁力的异化。
在这个角度上解读“新世代”作家的城市小说文本,才能够比较清晰地发现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视域下都市论述的结构性变迁,林耀德的小说文本则提供了透视这一变迁的重要例证。
二
林耀德是台湾地区“新世代”作家的重要代表,所谓“新世代”,即“战后第三代”以降的小说作者群。[5]林耀德身处台湾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物质生活的丰裕、城市化的快速扩张、资讯时代的巨大冲击、社会文化的悄然质变,皆在社会个体的精神结构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以《大东区》《恶地形》为代表的都市小说是最能表现林耀德对资讯文明、后工业时代的思考的作品,也是最能体现其在现代主义叙事上的追求与风格的作品。这些小说呈现了一个敏感的城市观察者 (犹如波德莱尔式的城市漫游者)的经验与思考,他检视着资本主义的各种文化仪式在台北城市上演,他的敏感赋予其锐利的目光并得以穿透城市的浮华,看到欣欣向荣的城市生活表面下掩饰着的空虚与浮泛,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混乱失序的时代所必然的悲剧性,清醒地批判了各种病象与邪恶所滋生的社会温床,在这种观察与批判中跳动着的哀伤与悲恸,则又是一个敏感、不安的青年作家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质疑、困惑与沉淀的冷静的思考。
在繁华热络的城市生活中,什么最能引起一个城市漫游者的关注?壅塞的马路与肮脏的空气,稠密的市井与迷宫般的巷道,高楼上阴森的玻璃幕墙,虚伪的办公室政治,挤满红色圣诞老人的百货公司……作家的目光穿越漫漫的城市丛林,他将抵达在哪个终点?“人是万物的尺度”[6],在《恶地形》和《大东区》两个小说集中,作家记录下了不同社会群落的集体影像,其中,有无聊的问题少年、堕落的少女、颓废的艺术家、冷漠的警察、厌世的保险业务员……这是一群被渗透进城市的结构又游离于城市空间的边缘人,他们就像现代生活的一个个零碎的断片,被城市这个巨大的磁盘牢牢吸入现代生活的漩涡。小说《大东区》讲述了一群无聊少年躁动、不安的一夜:飙驰的机车、电子游戏、酒精、毒品、性、街头斗殴,一群无所事事的少年男女,在膨胀的欲望和迷茫的追逐中纠结,在肉身的喧闹与精神的苍白中挣扎。《大东区》关注的问题还是一群无知少年青春期肤浅的激情与年少轻狂的虚荣,《喷罐男孩》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个体心灵深处的残暴与恶毒。《喷罐男孩》可以看作是《大东区》的续编,人物与故事皆有交集:从迪斯科舞厅回到居所的少年小克,在性臆想与恶作剧中消遣无边的寂寞与释放空虚的情绪,在午夜街头主演一出血腥的屠狗游戏。在这个曾经痴迷于追逐彗星的少年眼中,训练有素的屠杀行为并非残酷的暴行,而是一种艺术灵感的行为实践——这些心灵上的扭曲与变态折射的正是现代社会个体肉身的沉沦与精神的异化。《我的兔子们》《氢氧化铝》继续将这种心灵的黑暗推向另一个峰极,在其中可以看见现代人精神的荒芜与触目惊心的罪恶。《我的兔子们》的杀伤力正在于它细腻展示了自我的残暴与冷酷:“我”在工作室里饲养了众多的兔子,细心地照料它们的饮食与排泄并为它们一一编号,但在兔年除夕夜零落的爆竹声中,先前温馨的场景倒转为血腥的屠戮,生命屠戮带来的刺激感成全了主角新年庆典的最后仪式。《氢氧化铝》讲述的是现代人的心灵冒险,充满诡异的色彩。身为保险业务员的“我”自觉地配合别有用心的摄影师D完成了一次秘密的杀人与自杀游戏,小说最奇特的地方在于“我”对D的阴谋了如指掌,却自觉配合并参与导演了这一场以自身生命为代价的荒诞剧。“我”是死于他杀,抑或自杀?是D迷惑了“我”,还是“我”迷惑了D?是D拯救了我的灵魂,还是我拯救了D的艺术?这是小说富有意味的命题,它映现了社会个体在失却自我之后荒诞、悲凉的生命经验,即生命的无意义感:“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7](P9)正是这种生发于内心的无意义感,自我的分裂感,导致了社会个体自我毁灭的命运——“自我毁灭是现代派小说人物的必然结局”[3](P152)。
从对他者的毁灭到对自我的毁灭,林耀德的小说不乏关于生命终结的叙事。社会个体如何觉知自身在社会空间与文化结构中的处境,如何体察自我的异化与分裂?这是现代主义文学所要处理的重要命题。现代主义显然更着重于从个体内在的精神困境出发,发现外部现实与个体内在的冲突、矛盾,从个体的视角来认知与诠释外部社会并从而返观自身是现代主义的美学逻辑,因而,将自我对象化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惯用的手法。小说《一束光投掷在被遗忘的矶岩上》和《一线二星》的主角身份都是警察——在一个扭曲的社会,警察显然是最能体现社会体制悖谬的身份,两个小说虽然对警察这一特殊阶层的身份境遇仅作寥寥几语的描绘,但已然呈现其社会生态的腐败,不过作家更关注的乃是这种社会生态如何“绑架”作为个体的自我。《一束光投掷在被遗忘的矶岩上》中的一个事件耐人寻味:“我”对一个年轻的盗窃犯不懈追捕,并最终将他逼上高楼的天台,被惊骇的男孩无奈纵身跃下,以生命的终结作为对追捕的逃避,这个意外的结局使“我”意识到,追捕罪犯的“我”犯下了比年轻盗窃犯更大的罪——对他人生命的冷漠,“我”得以照见自我的黑暗面。《一线二星》对自我的揭示与鞭挞较前作更加尖锐,通过漫不经心的叙述,小说暗示了作为警员的“我”事实上正是自身所调查的两宗杀人犯的凶手,“我”杀害女线民和同事的根源在于两个被害人事实上正是“我”的对象化,或可以称其为见证人:他们见证了“我”的堕落与阴暗。因此,当“我”无法直面那个腐败的自我,杀死女线民和同事就成了逃避自我、割断自我的方式,“我”通过杀死别人来杀死自我,因厌憎自己而厌憎同类,是因为同类就像一面镜子时时反射他自身。
在这些文本中,作家有意从扭曲、夸张、荒谬的行为中突显现代社会生活的荒诞与社会个体自我的破碎和分裂,或者说,诡异、荒谬的情节使社会个体真实而荒诞的自我世界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林耀德擅长在作品中制造一种富于反讽的情境,反讽正是其投射、映现社会个体生命经验和暴露自我之荒谬的通道。作家在《喷罐男孩》中不吝以华丽的语言描述城市的华丽景观,但是,恰恰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光鲜华丽与男孩心灵内部无边的黑暗构成了巨大的讽刺。在 《圣诞节真正的由来》中作家以身穿红制服满街发传单的圣诞老人为意象,来说明包围着城市的虚假的、迷惑的节庆气息只不过更加尖锐地映射出现代社会生活的“幻觉”性质罢了。小说所批判的正是过度“消费”的商业社会以及它对现代社会个体意识的麻醉,圣诞老人发放传单显然是消费社会的一种商业行为,它不断提醒世人要享受消费沉迷享乐,另一面,世人却已无法舍弃圣诞节所制造的现代幻觉,他们需要一个圣诞节来矫饰真实的生活,需要一个不必戳破的传说、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一个黑色的幽默来维系虚幻的欢乐与繁荣,必须强调的是,这种需要是“真实的”——一种被异化、被生产出来的“真实”。作家清楚地认识到:在地处东亚的台北,圣诞节是一种被阉割了历史的文化仪式,是一场自觉的文化合谋,大众或者说一个个“无名”的个体参与进了圣诞节所隐喻的现代狂欢。
林耀德的小说文本所描述的现代城市光彩亮丽:二十四小时超级市场的灯光不眠不休,百货商场里红彤彤的圣诞老人,街头飙驰的锃亮机车,喧腾的舞厅,嘈杂的游戏机房,青春的肉体与暧昧的性……这些景象拼贴出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繁荣与浮夸。但另一面,这个世界又飞腾着腐败、死寂的气息,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作家钟爱的意象是坟墓、废墟、荒漠、迷宫,诸如此类的文化象征反复出现在作品中——《我的兔子们》中“我”放逐生灵的那一段“断壁残垣”,《恶地形》中那一片荒凉、诡异、绝望的“被诅咒的土地”,《巨蛋商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中像“一整排特大号的墓碑”的玻璃帷幕,《氢氧化铝》中的城市如同被各种光影切割的“人工的荒漠”,《大东区》中的“迪斯科舞厅”是城市“迷宫”的形象化。这些恐怖、狰狞的意象彰显了作家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内心经验,以及这种内心经验的真实与外在现实的疏离。
林耀德努力从“迷宫”的城市地理学中抽象出了城市欲望沉浮、迷离失所的哲学。在作家看来,声光电化的现代城市,不过是一片喧闹的废墟,现代生活的嘈杂与混乱、荒芜与悖谬,现代社会个体的迷失与苦闷、焦虑与分裂,正是社会空间失序的产物,分裂的个体与他们所置身的畸变的空间是一种相互生产的关系。作家毫不介意地大声宣扬:“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不同招牌的精神病院。”在城市中,充斥着警察、医生、艺术家等各种身份与形式的精神分裂者,他们是无聊的周末抑郁症患者,是骂骂咧咧的躁郁狂,是颓废主义的实践者,是险恶的阴谋家,是无耻的偷情者,是游荡在街头的影子,是潜伏在暗夜里的幽灵,是卑污灵魂的无声啜泣。在或光鲜或猥琐的装束下,在或平静或不安的神容下,他们纵容内心的欲望与黑暗,与仅存的微薄的自我搏斗撕扯。他们是现代生活的幽灵,潜伏在城市阴暗的角落,目睹自身的异化与沦陷并从中追索存在的快感。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或是沉默的认同,或是无谓的挣扎,或是惨烈的毁灭,任何一种形式的救赎最后都变成了新的罪恶与沦陷。喧嚣浮夸的现代生活,何处才有真正代表了希望的“春神”?林耀德以反讽的叙述形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主体精神的破产。
对自我的分裂与异化的焦虑,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美学议题。林耀德对创作有一份成熟的觉知:“八○年代末期到九○年代初期是我对文学的态度更为清晰的一个阶段。……我的心灵视野开始开展,知道如何在现实中找到无数通往梦幻和恶魔的通道,如何在世人的想象力中看到现实和历史被扭曲的倒影,如何进入他者的内在或者穿越集体的幻象,如何表达卑鄙与崇高并存的自我。”[8]这段语义丰富的表述印证了我们在林耀德叙事作品中所体验到的那种现代的“无名”的痛苦,它呈现了现代社会生活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情境对个体自我的碾压与异化,并且表现为极其复杂的形态和样貌,作家的使命即是从似是而非、纷繁多变的现代社会的生活表象中,探掘与直面那个扭曲、破碎与分裂的自我。作家不断通过小说文本来说明,社会个体自我的异化源于其所置身的现代社会生活空间的破碎感,城市则是现代社会生活空间的物质载体与文化形式。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尤其是台北这种日益“国际化”的都市,成为西方现代资讯文明的飞地——但是,作家却透过社会生活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表象,看到了现代城市生活在快速发展和过度膨胀之后的虚脱与空心化。
三
“自我”的拷问,存在的荒谬与荒诞,异化的经验与焦虑,反讽、寓言式的文本结构与叙述形式,这些征象都表明,林耀德承续的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火种。台湾地区社会文化空间的巨大更迭,迫切地召唤、寻求一种新的哲学与方法给予认知,从罗门、林彧、白先勇、陈永平、王文兴,再到黄凡、张大春、林耀德等,台湾现代主义作家,孜孜于建立一种“当代都市文明的现象探索”和“一种精神荒原的追索”的文化思考。林耀德曾经带着批判性意味地表达对台湾地区早期现代主义的看法。他指出,台湾地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文明”产生的是一种“既拥抱又批判的矛盾”,其“拥挤而孤寂”的现代主义主题呈现的是现代文明的幻灭性。[9](P197)所谓“拥挤而孤寂”,即是“人群中的孤独”,它描述了变化的、多样的现代社会世象中的现代性幻觉与自我的疏离感、孤绝感,它揭示了现代性的社会空间对个体的压抑与分裂——“把孤寂视为普遍的人类处境,是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独具的”[10](P136),卢卡契对现代主义的鄙薄倒是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主义独特的文化品格。
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现代派的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新世代”作家群的城市书写的蔚为风潮,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总体而言是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对“自我”的艰苦追索,也表现出了现代性之“孤寂”的普遍性的情绪,但因应于文学生产所架设的不同的文化空间,对“孤寂”的阐释与表现也派生出不同的线索与立意,或可说,中国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不同时代演绎出了关于自我与存在的不同变奏。在白先勇、王文兴、李永平等一批现代主义作家那里,表现命运的荒谬、人生的孤绝境遇以及反抗荒谬、重建自我的生命激情,是与中国台湾文学中放逐、失根的主题遥相呼应的,自我的追索乃是奠基于家国乡愁与“失根”的焦虑,知识分子对自我的省思与重构因而显得华丽而沉重。随着林耀德与他的同辈黄凡、张大春、东年、王幼华等“新世代”作家群的跃起,自我的追索中则楔入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空间与结构。林耀德清晰地指出,“新世代”作家群与前行代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符号体系:“他们成长的过程正是台湾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完整地诞生在资本主义的下层结构中;出生于1960年代以后的‘新世代’更被全岛都市化的信息系统所包容。”[5]换言之,架构“新世代”作家群的经验世界与心灵结构的是一种后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与文化语境,这一现实也必然催生“新世代”作家群建构出台湾地区文化思想的新面向和文学创作的新美学。林耀德对 “新世代”作家群的这番文化与美学的指认,也可以视作他对自身文学创作美学追求的一种定位。
城市作为现代生活最重要的物理场所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表征,为现代主义这把利刃提供了最佳的战场,也为台湾地区“新世代”作家经营新的文化美学提供重要舞台。如果说,“前行代”的现代主义作家更多聚焦于知识分子境遇与经验的“自况”,这种精英关怀在“新世代”作家这里逐渐走向了终结,在一个以碎片化、多元化、异质化为新质的现代社会形态中,在既有价值体系与文化秩序已然解构的时代,对精英情结的否弃说明了现代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中产阶级自我批判的文化的深入和自我纠正。与此同时,与城市一同成长的市民社会 (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落),也为这些作家提供了更丰富的聚焦与更广阔的思考,作家们通过文学书写面向的延伸与拓展,说明了“孤寂”已经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落的“专利”,相反,它是一种弥散在城市现代文明中的普遍性的情绪,是一种笼罩在大多数社会个体(而非仅仅中产阶级)身上的“文明的牢笼”,而以城市为空间的现代生活提供了这种情绪的肥沃土壤。林耀德小说的意义在于,作家在那些日常的、偶然的、意外的事件中把握到一种普遍性的现代生活的底色,在那些零落的、碎片化的、卑微的自我中把握到了一种深刻的疼痛与悸动。它来源于无所不在、无法回避的现代生活,这种生活加诸所有的社会个体,现代生活不再是外部于自我的力量,而是自我的结构,是自我潜意识层面的巨大洪流。
因而,林耀德所表现的就不是某种孤立的情绪,他的自我并非单一的自我,而是现代社会个体的“集体无意识”。这正是林耀德城市书写所强调的方面,即资讯文明时代现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的建构如何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进行结合。他指出:“‘新世代’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发明,是处理了集体潜意识的问题。从个别人格主体意识内省式的心理写实飞跃入集体潜意识的洪流,不仅是叙述模式与章法技巧的改装,更涉及‘新世代’作家的心灵结构与精神底蕴的质变;能够从容地刺探当代光怪陆离的都市文化,势必先要能从容地进入集体潜意识的幽晦中寻找创造性的光源。”[5]在这里,集体潜意识显然指向被现代生活表象所掩饰的社会个体的精神内在世界,现代性对传统生活的断裂是导引自我存在主义焦虑的重要根源,社会文化空间的质变必然在社会个体的意识领域留下深刻的痕迹,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精神的荒漠同步,新贵阶层的兴起与底层百姓的挣扎并存,现代城市生活流光溢彩的表象掩饰了自我的挣扎与沦陷——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察与文化思考,使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地区本土生产出了其所独有的、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内涵。
[1]白少帆.现代台湾文学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2]发刊词[J].现代文学,1960,(1).
[3]朱立立.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M].上海:三联书店,2004.
[4](美)张诵圣.当代台湾文学场域[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
[5]林耀德.新世代小说大系·总序[M].台北:希代书版公司,1989.
[6]林耀德.恶地形[M].台北:希代书版公司,1988.
[7](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8]林耀德.大东区[M].台北:联合文学,1995.
[9]林耀德.重组的星空:林耀德论评选[C].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
[10]袁可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彭民权】
I206.7
A
1004-518X(2015)12-00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