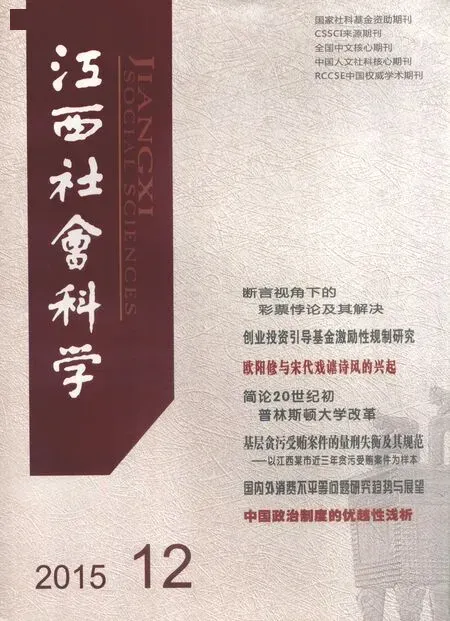宋代笔记中的人物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为中心
2015-04-15赵惠俊
■赵惠俊
诗人写诗,或感于哀乐,或缘事而发,因为言志抒怀是诗歌最重要的发生机制与写作传统。而笔记作家记笔记则是因为某些人事勾起了他的兴趣,或欲记下备忘,或欲为此评论,或欲辨析疑义,或欲以供谈资……勾起兴趣的人事就是每一则条目的话题。如果我们将以同一人物为话题的条目汇总起来,则可以看出是他们的哪些性格特点或个人经历成为勾起笔记作者的话题。同时,我们又可以发现人物在成为某种笔记的话题之后,便不再是其本身,而成为被该笔记作者塑造的形象,这种形象往往又会成为后代笔记作者的话题,如此循环下去,形成一个属于笔记文本空间里的特定形象。本文拟以宋初文士杨亿、晏殊与石曼卿为例,探讨本朝人物形象如何勾起了笔记作者的话题,笔记作者如何在话题中选择谈论点,又如何在话题的谈论中塑造出笔记形象。
一、杨亿:“神童”与翰林学士
人是社会属性的动物,每一个人都带有若干种社会身份。无论他人还是自我,都需要通过身份来认识自己,定义自己,随之又通过身份来寻找同类与归宿,从而形成社会群体。对于这样形成的群体来说,一个拥有他人皆不具备的特殊身份的人物,往往会成为其间的焦点,成为引起群体兴趣的话题。杨亿,一个由“神童”成长起来的士大夫,是士大夫及其周边文人经常谈论的人物,“神童”便是最先入话柄的特殊身份。与士大夫关系密切的僧人文莹就写下了这样一则笔记条目:
杨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阙下,太宗亲试一赋一诗,顷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书,俾宰臣再试。时参政李至状:“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王仁睿传圣旨,押送建州十一岁习进士杨亿到中书。其人来自江湖,对扬轩陛,殊无震慑,便有老成,盖圣祚承平,神童间出也。”[1](P12-13)
文莹选择的话题谈论点是杨亿应 “神童”试之事。绝大多数士大夫的科举经历在程序和现场两方面基本大同小异,没有谈论的必要。但杨亿所应之“神童”试则不然,这对于宋人来说是陌生的,会引起他们的好奇。然而引起文莹兴趣的不是杨亿应“神童”试的程序,而是杨亿何以成为“神童”。因此记叙中穿插进“顷刻而就”、“顷刻而成”的两处重复,强调着杨亿敏捷的才思,又通过援引试诗中的句子证明年少的杨亿确有非凡的文才,告诉读者杨亿的“神童”并非浪得虚名。文莹节引的李至状表中“盖圣祚承平,神童间出也”一句似乎不能轻易放过,他将此句保留在有限的篇幅中正意味着对其的重视,因为它道出了“神童”存在的意义——太平盛世的标志与点缀。
“神童”有过于常人的文才,杨亿因此获得了“神童”身份,又必须时时展现此能力以维护他的身份。正如朱刚指出的那样:“如果进士们可以把写作诗赋的能力当作敲门砖,通过考试后便不妨丢弃,那么‘神童’就必须追求终生具备写作方面的特长,否则就显得名不副实。”[2](P125)杨亿在“神童”试之后屡屡进献谀颂之文,将自己卓越的文才投放在对升平时代的称颂中,以此捍卫着自己的身份。这种行为不断强化着“神童”身份,为士大夫提供了许多此类话题谈论点,但他们多还是以摘引句子的方式进行谈论,如徐度 《却扫编》、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曾敏行《独醒杂志》等均有对杨亿的记载。
上述笔记摘引之句并不局限于所进赋颂中,还包括平日的应答妙语。但各条目关注的话题点却和文莹一样,都感兴趣于杨亿非凡的文才与敏捷的才思。二者是杨亿得以拥有“神童”身份的前提,他也因此受到帝王与大臣的赏识。当然,并非所有笔记作者都对此抱以赞赏,《儒林公议》中就有一则条目叙述了时人对于杨亿及其西昆体诗风的贬斥[3](P87),这也是当时的一股重要潮流,但依旧属于上述话题下的论说,只不过以不同的立场,与上述诸条一起,构成了话题中的正反两面。
“神童”不可能一直在秘阁读书,当其长成之后,就需要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官职。这时,“神童”的身份又一次提醒人们注意其文采斐然与才思敏捷的特征。这正是负责草拟文诰诏令的翰林学士必备素质,授予其这个官职是人尽其才了。那么再反过来说,当人们看到一位具有翰林学士身份的人时,会想当然地认为他肯定具备这两点特征。
翰林学士本身就是宋代笔记中的常见话题,笔记作者在这个话题下除了讨论翰林学士的文才之外,还往往会将他们当作笑料谈说,似乎觉得他们的人品并不怎么样,带上了一些轻视与偏见。杨亿之前,最能引起笔记作者话题的翰林学士莫过于陶谷,而话题的谈论点多集中在著名的“依样画葫芦”事上。此事被许多笔记作者记下,以魏泰《东轩笔记》卷一记载得最为详细[4](P8)。但不同作者的叙述情感却是相同的,都认为陶谷除了舞文弄墨之外便别无长处,对他抱以轻蔑与讽刺的态度,展现出一个没有自知之明又略带酸腐猥琐色彩的陶谷形象。但是笔记作者并非仅仅这样认识翰林学士陶谷,往往也会将其迁移到所有翰林学士身上,特别是那些以文才捷思著称于世的学士。在以翰林学士为话题的笔记条目中,杨亿也成为一个与陶谷相似的穷酸文人,如高晦叟《珍席放谈》卷上云:
杨文公在翰林,母处外被疾,请告,不待报即去。上遣中使赐御封药洎金帛以赐,谓辅臣曰:“亿侍从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对曰:“亿本寒士,先帝赏其词学,寘在馆殿,陛下矜容,不然颠踬久矣。然近职不当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轻肆,而圣君优假,大臣又善为之地,真幸遇矣。[5](P189)
王素《文正王公遗事》也有相关记载。这两则条目谈论的都是杨亿因为母亲病重,未报请朝廷而擅自归阳翟事。这件事有两个焦点,一个是杨亿自作主张回家探母;另一个则是真宗对此的反应,他并没有处罚杨亿,反而赐予医药,以示安抚。这个事件颇具可谈性,故而我们会看到重复谈论此事的条目。二者谈论的焦点不在杨亿拒绝草制,而是真宗没有惩罚杨亿。王素在叙述中拉入了先祖王旦,其间王旦“杨亿文人,幼荷国恩,若谐谑过当,臣恐有之”之语暗示王素认为杨亿的行为就是其本身性格所致。所谓谐谑就是开玩笑、发牢骚,玩笑与牢骚之间也透露着其恃才放旷,对礼法与帝王并不是那么尊重。这种性格是杨亿本身确实具有,还是旁人根据其文人、翰林学士的身份做出的推断我们不得而知,但王素一定认可这种性格与翰林学士的身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到了高晦叟那里,这种性格被坐实在杨亿身上,“夫近侍轻肆”一语便是直接给杨亿形象增添了一笔灰色。高晦叟认为杨亿擅自离京没有别的深层原因,就是缘于他轻肆的行为习惯。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二者都是不加考辨地叙述,他们都相信自己说的就是对的,认为翰林学士杨亿就应该会做出这样的行为。那为何杨亿就应该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许就是因为翰林学士的身份给人们带来的先入之见,无论是柔弱还是轻肆,都是这个身份的典型形象特征。笔记作者没有史传作者统筹全局、考辨事实的义务,他们在撰写笔记条目的时候只要抓吸引谈论的重点就可以了。
综上可见,“神童”与翰林学士的身份让杨亿成了士大夫间的话题,而士大夫在谈论此话题时又根据这两种身份来建构杨亿的形象,通过不同笔记的记载,杨亿在笔记中出现了一种文采斐然又才思敏捷的翰林学士形象,但这里的翰林学士是陶谷式的翰林学士,与后世苏轼式的翰林学士迥然不同。
二、晏殊:“神童”与富贵宰相
拥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会成为群体中其他人的话题,但话题的谈论点却并非人尽相同,因为某些原因,拥有同样身份的人物很可能会被谈论成迥异的面貌。晏殊与杨亿都是“神童”,都会因“神童”的身份而成为人们谈论间的话题,但笔记作者在同样的“神童”话题下却谈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6](P80)
沈括以晏殊应“神童”试为谈论点,却没有像文莹以此点谈论杨亿时那样引用应制赋颂中的句子。看来他的兴趣点并非晏殊的非凡文才,而是他超于常人的道德水准。不仅是沈括,其他笔记作者也很少引用晏殊赋颂的文句。但是晏殊毕竟是“神童”,他一定和杨亿一样有着斐然的文才与捷思,也同样会写大量的赋颂文字以履行“神童”的身份与职责。他在真宗东封西祀之时就写过大量的应制文字,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文章一定工整华丽,受到时人的称颂与帝王的青睐,毕竟晏殊是和杨亿齐名的四六大家,但是笔记作者对这个谈论点集体失声。
不过“神童”身份总归会吸引人们去谈论他的文学才华,但是笔记作者悄悄地从点缀升平的赋颂转移到了诗:
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7](P254)
善评诗,善作诗当然需要非凡的文才与深厚的学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神童”身份也可以做到。但诗尊贵的文体地位远非赋颂能及,它是属于士大夫的必备技能,是士大夫的身份象征,而当时的诗歌评价标准更是充满着科举士大夫的立场。这样来看,“神童”的才华是写好诗的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还需具备极高的道德修养才能胜任。杨亿写的诗就广受士大夫的斥责,因为他于“神童”之外的身份只是以文字立命的翰林学士,他写的诗也是与其身份相符的应制赋颂之作,并不能写出科举士大夫立场下的好诗,反而是在道德标准下不被士大夫认可的诗,于是他也就没有资格对士大夫诗指手画脚。但同为“神童”的晏殊却拥有着杨亿所无的宰相身份,而他又积极提携了大量著名科举士大夫,备受这一群体的尊重。于是乎笔记作者似乎不会简单以翰林学士来定义晏殊,而将视线落在相国身份上。在宋祁的笔下,晏殊俨然成为士大夫间的诗坛宗主,与其宰相身份十分相配。不过笔记作者选择宰相身份作为话题,也因为宰相晏殊身上有一般士大夫没有的富贵气质。这对于宋代科举士大夫来说非常罕见,因为这是贵族士大夫的特点,需要诸如四世三公的世家才能沉潜涵养得出。在贵族消亡的宋代,士大夫必须经过科举才能走上仕途,因此他们少年的读书都带上了很强的目的性与实用性,唯有如此,他们才能顺利通过科举。当他们步入仕途之后,也还必须努力获取功业或被帝王赏识,否则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但晏殊与之不同,“神童”出身的他获得了在秘阁读书的机会,自由地增强学养,涵育风神。这与贵族子弟的读书心态非常近似。此外,仁宗伴读的身份让他在仁宗亲政后顺利进入宰辅系统,既获得了避免潦落词臣一生的幸运,又有着近似贵族的稳定,因此才能拥有富贵生活与富贵气质。
笔记作者不仅谈论着晏殊诗歌中体现的富贵气象,还乐于从宴饮中表现其富贵气质里的风流与从容:
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幸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8](P267)
贵族喜好宴饮并以此为乐不会招致太多的非议,因为宴饮行为是其身份的一种象征,他可以这样做,他也需要这样做,故而叶梦得在叙述完这一谈论点后发出了“前辈风流,未之能比”的感叹,既是羡慕晏殊的富贵气质,也是表明晏殊这样的人物在北宋已经十分罕见。但是没有贵族身份也没有类贵族经历的科举士大夫却不能像晏殊这样生活,他们如果沉迷宴饮会被批评为游手好闲、不思进取,也会招致诸如骄奢淫逸的道德指责。于是宰相晏殊就与普通科举士大夫群体在富贵气质上产生了矛盾,这是一个绝佳的话题,高晦叟在《珍席放谈》卷下就记载了晏殊以不同生活方式对待富弼与杨察两位科举士大夫女婿的故事[5](P187)。尽管晏殊能如此区分自己与普通科举士大夫的不同生活方式,但还是会与一些执拗的士大夫发生纠纷: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者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4](P86)
欧阳修将军国之事引入到晏殊的私人生活空间,于是招致晏殊的不满,这是二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观念差异。下层士人魏泰用这一条目记载了这个故事,又在同书其他的条目中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4](P120),认为这是二人在以各自的身份去审视对方,当然会导致互相看不顺眼。欧阳修不应该对富贵宰相晏殊的私人生活空间指手画脚,晏殊也不必对欧阳修强调政治空间太过斤斤计较。
晏殊话题被谈论到这个地步,也出现了一种被固定在某个侧面上的现象,但其与杨亿的不同很大程度是缘于最终不同的身份。晏殊的形象告诉我们,“神童”出身的翰林学士杨亿也是科举士大夫,他完全具备一个士大夫应该拥有的素质。而杨亿的形象告诉我们,“神童”出身的富贵宰相晏殊也有着辞章立命的时候,也有着翰林学士的文才和捷思。只不过,笔记作者在谈论与二人相关的话题时总是记挂着二人最终的身份,因而在此先入之见下每每选择与身份相适应的谈论点,而且其后的谈论者都沿袭着那些话题,于是不断强化着原初选择的形象侧面,从而造就了二人在笔记中的形象。
三、石曼卿:未中举的豪士
上文对比了杨亿与晏殊的笔记形象,可以看出笔记作者在谈论人物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复杂人物形象之一端。同样未经正常科举渠道入仕的石曼卿更加典型地体现着笔记作者在谈论人物时的此种特色。石曼卿终其一生也没有做到学士以上的大官,流传至今的生平事迹并不丰富,因此可以很清晰地考察出笔记作者面对着的是一个怎样的石曼卿,他们在谈论他的时候选择了什么,丢弃了什么。
石曼卿幸运地结交到欧阳修这么一位朋友,欧公为其撰写了一篇墓表与一篇祭文,今日我们所了解的石曼卿生平基本来源于欧阳修的《石曼卿墓表》。在这篇墓表中,欧阳修主要记载了石曼卿生平四事:一是在张知白的劝说下接受三班奉职的恩赐;二是拒绝阿谀之臣范讽的援引;三是敏锐指出西夏之患,并在西夏犯边时成功募集数十万乡兵;四是平生意气雄豪,颇好剧饮。[9](P665)从墓表的记载来看,石曼卿是一位有气节、有才华的士大夫,同时具备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当然还有落落不羁的一面。这四个方面就是今日我们可知的完整石曼卿形象,四者都是很好的谈论话题,但笔记作者却偏偏只对其中的一点感兴趣。有意思的是,正是欧阳修首次撰写了以石曼卿为话题的笔记条目: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有刘潜者,亦志义之士也,常与曼卿为酒敌。闻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不交一言。……二人饮啖自若,慠然不顾,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久之乃知刘、石也。[7](P267)
正因为欧阳修写就了《石曼卿墓表》,因而我们可以断定他以剧饮为谈论点是他有意识的选择。笔记中的轶事没有被写入墓表,可见欧阳修不是认为此事虚妄,就是认为这件事显得石曼卿太过狂放,有损墓主之形象,但这些完全不是笔记的顾虑。既然是闲谈,那么这样一个曲折离奇的事情才非常合适,而且条目中的石曼卿狂饮一日不醉又符合其本人喜剧饮的性格,完全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不管欧阳修到底相不相信事件的真实,他将此事记入笔记正说明笔记就是需要这种话题。
欧阳修在笔记中谈论石曼卿得到了后世充分的回应,但无一不是接续着欧阳修的话头,只是醉酒故事变得更为虚诞,同时也会融入纵豪不羁的特点:
石曼卿与刘潜、李冠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将别,语潜曰:“到官可即来相见,寻约痛饮也。”……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谈,徐曰:“何来?”又久之曰:“何处安下?有阙示及。”一典客从旁赞曰:“通判尊重,不请久坐。”潜大怒索去。云:“献汤。”汤毕,又唱:“请临廊。”潜益愤,趋出。曼卿曳其腰带后曰:“刘十,我做得通判过否?扯了衣裳,吃酒去来!”遂仍旧狂饮,数日而罢。[10](P162)
王铚的谈论在意石曼卿跟老朋友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表现出他谐谑的一面。但是从这个玩笑中可以看出,当石曼卿摆出通判的架子时,狂饮不能发生,而放下通判的身份之后,狂饮才能够如期而行。这似乎表明石曼卿的狂饮习气与士大夫的身份有所矛盾,狂饮代表着轻狂不羁的个性,通判则代表着士大夫身份,当石曼卿说“我做得通判过否”时,是在主动消解士大夫身份,可见要做士大夫则不能有轻狂不羁,要想轻狂不羁,那就不能厕身于士大夫群体。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笔记中看到一些类似的围绕着酒与谐肆的条目,如:
世传仁祖一日行从大庆殿,望见有醉人卧于殿陛间者,左右亟将呵遣,询之曰:“石学士也。”乃石曼卿。仁庙遽止之,避从旁过。[11](P160)
在这条笔记中,石曼卿的身份是馆阁学士,关于学士的先入偏见也再次出现。既然如此,他的嗜酒、轻肆也就都变得合情合理。目无礼制地醉卧宫中会让我们想到醉卧沉香亭下的李白,而这个形象也来自于笔记,身份也是翰林学士,可见以文字立命的侍从之臣一直都是笔记作者乐道的话题,叙述中也多带着几分轻薄。石曼卿的传闻比杨亿曲折离奇得多,甚至还会出现关于他死后成仙的传说[12](P15),但无论哪则条目,他都是以醉客的形象出现,以至于被固化在嗜酒豪士之上。士大夫对于“神童”出身,并得谥“文”的杨亿还是给予了几分尊重,并没有过分铺衍,笔记中也能见到称赞杨亿的条目。但对于石曼卿就不用顾虑太多,可以在此话题下肆无忌惮地说开去,越说越离奇、浮夸。或许,石曼卿要想摆脱学士身份带来的偏见,唯一的途径就是拥有晏殊的身份。但是晏殊是罕出的,绝大多数未由正常科举渠道晋身的文才之士都停留在学士身份上,他们身上与科举士大夫相异的性格行为一直都是笔记作者的话柄。
四、余论:形象聚群与作者立场
笔记种类多样,内容芜杂,本身的文体属性非常模糊,故而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分类或定义。刘叶秋在结合前人尝试的基础上将笔记大致分成“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辩证考据类”三类[13](P1-5),较为公允合理,可以作为参考。不过,笔记内部条目与条目之间大多各自独立,无甚关联,故而我们在为每一种笔记归类时每每有难以统摄全篇之感。多数笔记先有一则则条目,再有汇编而成之书,而非先有一个类别大构想,再往里面填入一则则相关条目。
如此说来,每一则笔记条目都有一个话题,笔记作者抓住话题之后,再通过选择谈论点来完成条目的撰写,每一则条目都可以被归入通过话题分出的类属中,于是就构成了一组组条目聚群。就人物形象而言,每一则条目只能反映人物的一个故事、一个侧面,而由不同条目构成的形象聚群才能呈现这个人物在笔记中的整体形象。人物的某种身份为笔记作者提供了话头,成为每一则条目文本中的身份,而文本身份的集合又构成了一种形象主体,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重建这个人物形象。在笔记构成的形象聚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形象聚群,笔记形象聚群只是笔记作者从更大的形象聚群中选择的结果。比如欧阳修的《石曼卿墓表》叙述了石曼卿的四种形象特征,这是从现存文献中能看到的最大的石曼卿形象聚群。所有关于石曼卿的笔记条目构成了石曼卿笔记形象聚群,只不过聚群中的每一则条目都是选择嗜酒狂豪作为话题,围绕这个话题讲出的每一个独立故事就成了不同作者撰写的每一则笔记条目。除了人物自身的形象聚群之外,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构成着一个个类属聚群。杨亿、晏殊、石曼卿三人就构成了一类人物形象类属聚群,他们由未经正常科举渠道而入仕的身份聚合在一起,又分别代表了这一类人物中的一方面。杨亿以词臣终老,晏殊顺利晋身高位,石曼卿潦倒于下层,可以说囊括尽了此类人物可能会有的人生道路。
笔记形象聚群是出于笔记作者的选择,而每一则条目的撰写也是笔记作者将事实混杂在想象中的产物。根据《石曼卿墓表》,我们可以大致相信好剧饮是真实的人物性格。然而从上引材料可知,以之谈论开来的醉酒故事则有很大程度的虚幻与失真,可以大致确认是经过虚构处理的。但是虚构处理的故事和真实的性格却有着内在的联系,故事是作者根据人物性格想象出的一种潜在发生可能。于是乎勾起笔记作者谈论兴趣的并不全是话题带出的故事本身,而是这个话题能让人们想象出的潜在可能,这些可能往往是现实中不太常见的,甚至是完全不会发生的。挖掘事物的潜在可能需要笔记作者的想象力和思辨力,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笔记文体的最大魅力。笔记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形象,之后便将这一世界捣毁,通过笔记条目撰写重建了一个新的笔记世界,而这一新世界既非描述的人物对象本身,也不是纯出作者之想象,而是现实与想象的融合。笔记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区别也正在这里。笔记作者在文本里追求带有自我思辨色彩的可能性,而笔记读者也期待着从中看到多样化的可能;而历史文本的作者和读者都在追求一种趋同的可能性,于是必须按照一套标准的想象模式展开论述。文本就是这样以作者与读者之间达成的某种共识为基础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才会觉得笔记文本夹杂了太多的虚构,其性质更多偏向于文学文本。
那么笔记作者根据什么进行选择?他们又是如何展开想象的呢?想象总是根据现实的经验展开,是作者意志的显现,标明着自我的本质、对现存世界的某种态度。宋代笔记作者大多数是科举士大夫,偶然出现的非士大夫作者也都可以被定性为士大夫周边文人。因此,笔记文本更多呈现的是科举士大夫的立场,表明的是科举士大夫对于自我人格的追求与强调。这种态度主宰着笔记话题的选择与形象的建构,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杨亿、晏殊、石曼卿三者的形象聚群多是单调的,因为科举士大夫想借他们三人引出的话题谈论他们不认可的东西,以之强调他们眼中的应有之义。对于这三个人物形象来说,其背后正蕴含着北宋真宗、仁宗朝特定的士风变局。
变革士风是当时的主流话题,是一场以“庆历士大夫”为代表的科举士大夫改变士风的行动。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呼吁着士大夫应该有的品质与人格,诸如石曼卿这种无视礼法、放肆清狂的行为是与士大夫自律稳重的人格完全格格不入的,要予以坚决地打击与斗争。而杨亿作为翰林学士,不应该只满足于唯帝王之命是从,一味点缀升平,而应该利用自己草诏的身份,在军国大事上给出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庆历士大夫最为看重的品质。而发生在晏殊与欧阳修之间的矛盾故事,同样也蕴含着庆历士大夫对富贵生活方式的不满。在这种立场下,三人都不是科举士大夫认为的完美自我形象,从而需要不断强调他们与应有形象的差异,并对此展开批判,于是笔记形象聚群中不断出现相关元素。而当话题人物变成科举士大夫理想中的完美人物时,我们就能从形象聚群中找到各不相同的风姿,这些面貌交代着士大夫应该具备的品性,苏轼形象便是此类最好的代表。
而当笔记作者身份疏离于科举士大夫的时候,他们所持的立场决定着科举士大夫追求的消失,因而会出现一些特别的笔记条目,稍微丰满着笔记形象聚群的样态。比如恩荫得官的章炳文在《搜神秘览》中就讲述了一位以相术大师身份出场的杨亿[14](P111),这是科举士大夫笔下绝不可能出现的内容。章氏在重建世界时运用的想象与科举士大夫完全不同,从而也就想象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笔记形象,展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笔记世界。
[1](宋)文莹.湘山野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2]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宋)田况.儒林公议[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4](宋)魏泰.东轩笔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5](宋)高晦叟.珍席放谈[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6](宋)沈括.梦溪笔谈[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7](宋)欧阳修.归田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8](宋)叶梦得.避暑录话[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9](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宋)王铚.默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1](宋)蔡絛.铁围山丛谈[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2](宋)欧阳修.六一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3]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14](宋)章炳文.搜神秘览[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