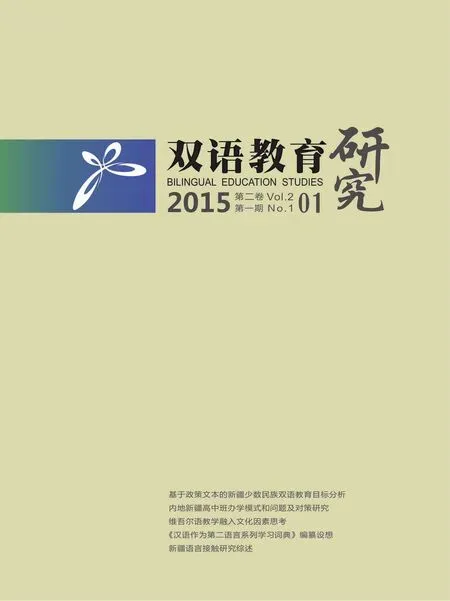《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的语用学分析
2015-04-10李少平
李少平
(喀什师范学院中语系,新疆喀什 844006)
《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的语用学分析
李少平
(喀什师范学院中语系,新疆喀什 844006)
语用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的学科,与翻译有着一样的研究对象,同为语言的使用和理解。近年来,语用学理论已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翻译研究之中,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方法。文章从语用学视角,通过对《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中的称谓语、委婉语和熟语的分析,浅析了语用学理论在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跨文化翻译中的应用,阐述了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汉语-维吾尔语文化负载现象的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同时还讨论了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不仅应追求形式和语义的等值,更应根据语境寻求语用意图的等同。
红楼梦;语用学;语境;文化;翻译
运用语用学理论进行翻译问题研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探讨。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其研究范围得以扩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这为翻译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方法,如运用语用学理论探讨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实践,解释翻译现象。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语用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和实践,解决了诸如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语用类问题,同时也论证了它对翻译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跨文化翻译上更具等值效果,但现有的成果中关于运用语用学理论研究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间的翻译问题的较少。本文拟从语用学的角度,通过对《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的分析,浅析语用学理论在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跨文化翻译中的应用,讨论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解释力。
一、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视角
语用学对普遍的语言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这是毋庸置疑的。语用学对翻译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也已被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所证实。最早用语用学来研究翻译的见诸于哈特姆(Hatim)和梅森(Mason)的《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以及格特(Gutt)的两本著作《Tra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和《Relevance Theory:A Guide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Translation》。之后,国内外学者相继运用语用学的语言行为理论、礼貌原则、合作原则、关联理论、篇章组织、语篇标记等理论开展了大量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将语用学理论介入到翻译研究之中,在不断的探索中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认识,具体表现如下。
翻译是一种信息交流活动,应该对语言交流中的语用意义给予重视,尽可能地使译语获得和原语同等的语用效果。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关注语言的表面意义,更要关注语言的语用意义,选取合乎语用功能的表达方式,向译文读者成功地传达句法意义、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达到最大限度的意义转换对等。
翻译是动态的信息交流活动。虽然翻译的基本任务是意义的等值转换,但是翻译除了意义之外,还有形式和功能,而功能是语言中最富动态性的因素。意义的表达形式常常受功能的支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将文本看作不是静止的语言成品,而是译者和原文本创作者、译者和目的文本读者群的“言语”,重视语言交际的功能性,既考虑语言结构本身的意义和翻译,也考虑在语言交际活动中因语境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意义及其翻译。
翻译是译者关联顺应翻译语境的选择活动。由于语言所表示的意义常常会受到语境的影响,且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是确定的,所以翻译时语境也必然影响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根据原文的具体语境推断出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正确理解原文的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同时作出译文语境假设,准确判断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阅读期待,寻找关联链和最佳关联,然后作出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符合他们的文化背景的具有最佳语境效果的翻译,将原文作者的预设和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
二、《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的语用学透析
《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是一部成功的汉语-维吾尔语翻译作品,也是汉语-维吾尔语翻译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它不仅丰富了汉语-维吾尔语翻译理论,也指导了翻译实践。译文中既能体现出重视语言形式和意义等值的翻译观念,也能够发现关注信息和语用等效的翻译思想。下面是我们对《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中的称谓语、委婉语和熟语进行的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透析。
(一)称谓语
称谓语是人们在社会交际、家庭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关系标记,能反映出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亲疏程度和社会地位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态度和感情。它的使用与语境密切相关,因此,正确把握语境是理解称谓语真实含义的前提和条件。《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的译者在翻译称谓语时,根据原文的具体语境,充分考虑了交际的对象、场合和社会文化等因素,推理出原文作者的用意,并动态地使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的表达式传达原语的语用意义。例如:
1.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第四回)
—ejtqɑnliribεrhεqrɑst,—dedii∫ikbɑqɑr mijiqidɑkylyp,—εmmɑ,siliniŋbuejtqɑnliri hɑzirqi zɑmɑnʁɑ munɑsip kεlmεjdu.……
2.探春因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第二十七回)
—nεʧʧεkyndinbujɑnbεɡɑtɑmsizni qiʧqɑrtmiʁɑndu?—dεp soridi tεnʧyn.
这两个句子中的“老爷”,译者不是根据词汇意义简单地译成χoʤɑ或bεɡ,而是根据不同的语境,进行了符合语用需要的处理。例句1中的“老爷”是下人对新任应天府知府贾雨村的称呼,相当于“您”,所以译者在译文中使用了表示敬称的后缀silεr来表达,这应该说是对等、贴切的,既表达出了原文信息中仆人对主人的尊敬之意,又符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例句2是探春跟宝玉姐弟之间的谈话,用“老爷”称呼自己的父亲。译者译成了bεɡ ɑtɑ,这与原文的语用要求是一致的,一方面让译文读者了解到了封建社会的尊卑思想和权贵思想,即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也较好地明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
3.(周瑞家的)便笑着说:“……如今太太不理事,都是琏二奶奶当家。你道这琏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当日大舅爷的女儿,小名凤哥的。”(第六回)
……hɑzirɑʁiʧɑχenimi∫lɑrbilεnkɑri bolmɑjdiʁɑnbolupqɑldi,hεmminiʤɑlijεn beɡimniŋɑʁiʧisi sorɑwɑtidu.ʤɑlijεn beɡimniŋ ɑʁiʧisi kim ikεnlikini bilεmsiz?u wɑŋɑʁiʧɑχenimniŋ ʤijεn qizi bolidu,uniŋbowɑq wɑqtidiki isimi feŋɡe.
4.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第六回)
ɑŋʁiʧεʤurujniŋɑjɑlimu qɑjtip kεldi wε:
—ʧoŋɑʁiʧɑχenim:“byɡyn meniŋ ʧolɑm tεɡmεjdu,kelin ɑʁiʧɑ bilεn køry∫simu,mεn bilεn køry∫kεnɡεoχ∫ɑ∫,bizni seʁinip kεlɡεnliki yʧyn køp rεhmεt.birεr zøryrijεt bilεn kεlmεj,tɑmɑ∫ɑ yʧynlɑ kεlɡεn bolsɑ,uniŋjoli bɑ∫qɑ.dεjdiʁɑn ɡεp-søzliri bolsɑ,kelin ɑʁiʧiʁɑ dεwεsimu boliweridu”didi,—dεp feŋʤjeɡεmεlum qildi.
5.(贾母)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第三十三回)
mεnɑʁiʧɑŋbilεnbɑwjynieliphɑzirlɑ nεnʤiŋɡεketimεn!
例句3至5中的“太太”虽然都指王夫人,但是译者却根据语用需要,将它们译成了不同的称呼。例句3是周瑞家的和刘姥姥两个没有身份的人谈话时,对王夫人的称呼,联系下文,译为ɑʁiʧɑχenim是妥当的;例句4是下人周瑞家的回凤姐话时,对王夫人的称呼,译为ʧoŋ ɑʁiʧɑχenim是贴切的。在封建时代,士大夫官僚的妻子被称为太太,这包含有身份高贵之义。译者对这两句的处理不仅符合当事说话人的身份,而且也将说话者对王夫人的尊敬之意表达了出来,让译文读者在译语的环境中能解读出说话人和被称呼人的身份和地位;例句5是贾母在生贾政气的情况下,称其妻子王夫人为“太太”,译者将其翻译为ɑʁiʧɑ,是十分贴切的,既符合贾母的身份,又表达了贾母当时气愤的情感。
6.王夫人哭道:“……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第三十三回)
—dedi wɑŋɑʁiʧɑχenim jiʁlɑp turup,—jεnε kelip mu∫undɑq tomuz issiqtɑ,uluʁɑnimizniŋtεn sɑlɑmεtlikimuɑnʧεjɑχ∫iεmεs.bɑwjyniurup øltyrywεtsilεbuniŋkɑriʧɑʁliq,mubɑdɑ uluʁɑnimizʁɑ birεr i∫bulup qɑlsɑ i∫ʧoŋijip kεtmεmdu?
7.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第三十三回)
—uluʁɑʁiʧɑχenim keliwɑtidu!—dεpχεwεr qildi.
例句6中的“老太太”是贾政的妻子王夫人劝贾政不要再打宝玉时对贾母的称呼,实指“母亲”。译者将其翻译为uluʁɑnɑ,既表达了血缘关系,又反映了晚辈对长者的尊敬;例句7是仆人对贾母的称呼,译者从语境出发,忠实原文地将其翻译为uluʁɑʁiʧɑχenim,既符合原文的本义,也体现了贾母在荣国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委婉语
委婉语是文化承载厚重的修辞格。委婉语的使用与本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汉族与维吾尔族的文化因心理意识、地域风貌、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特征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因此《红楼梦》中委婉语的使用给维吾尔语翻译增添了障碍。但是,《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的译者对委婉语的翻译处理得较好,除了理解指称意义外,还结合语境和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领会说话人的真实意图,理解言外之意,在译文中同样选择了符合读者认知语境的委婉语来表达文化内涵丰富的汉语委婉语,达到了译文与原文信息传递上的功能对等。例如:
1.王熙凤(对贾母)说:“……举眼看看,谁不是您老人家的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您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第二十二回)
byzrykwɑr ɑnimiz qɑrɑp bɑqsilɑ bolidu,qɑjsi birimizøzliriniŋbɑlisiεmεs?øzliri u ɑlεmɡεsεpεr qilʁɑndɑ,øzlirini udullɑʤεnnεtkεuzitip qojidiʁɑn birlɑ bɑwjy ukimizεmεstu?
原文中,“上五台山”是“死后登仙成佛”的死亡委婉语。在人们的思想中,对于自己的亲人或爱戴、尊敬的人去世是不能用“死”字的。这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感情和态度。译者理解到了原文中的这一语用功能,没有将其翻译为øly∫,而是在译语中同样使用了与原语语义和感情色彩相对应的委婉表达u ɑlεmɡεsεpεr qili∫,在译语中很好地体现原文的语用功能。
2.尤氏道:“我也叫人暗暗地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暂且慢慢地办罢。”(第十一回)
—mεnmuχeli burundinlɑ tujʁuzmɑj tεjjɑrɡεrlik qilip qoju∫ni bujruʁɑnidim,—didi ju∫i,—rɑsttinlɑ heliqi nεrsεyʧyn jɑχ∫i jɑʁɑʧtɑpɑlmiduq,kejinʧε tepilipmu qɑlɑr.
尤氏由于不便直说“棺材”,故委婉地说成了“那件东西”。译者将其翻译为heliqi nεrsε,是出于语用效果的需要,同样使译文也起到了说话人顾念对方情感,避免引起不快的交际效果。译文读者根据上下文语境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其含蓄婉转的语用意义的。
3.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姣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第六回)
bɑwjyɑdεttimu∫irenniŋkili∫kεnɡyzεl ʧirɑjiʁɑ køjyp jyrεtti.uʧy∫ini søzlεp bolʁɑndin kejin,ʁɑjipɑlεmdεpεrizɑtʤiŋχuεnøɡεtkεn heliqi i∫ni∫iren bilεnmuøtkyzmεk bolup uni tutup zorlidi.
“云雨”在这里是指男女性事的委婉语。译者在原语语境中解读出了文化含义,正确判断译语读者通过上下文语境是可以理解其言外之意的情况下,选择了顺应译语的表达,将其翻译为heliqi i∫,是能够委婉地传达出原语信息的。
4.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第二十一回)
ʤɑlijεn feŋʤjedin ɑjrildimu,ʧɑtɑqʧiqɑrmɑj turmɑjti.……
贾琏生性好色,他女儿得了天花,必须搬出去住,他却抓住这个机会寻花问柳。“寻事”为委婉语,暗含义为挑逗女性。译者通过自己的认知语境理解原语的真实含义后,在译文中同样使用了委婉表达,将其译为ʧɑtɑqʧiqiri∫,准确地传达了语用意义。
5.凤姐冷笑道:“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好的丢下的东西:戒指、汗巾、香袋儿,再至于头发、指甲,都是东西。”(第二十一回)
—on nεʧʧεkyndin beri bu ki∫ini sɑq jyrdi deɡilimu bolmɑjdu,—didi feŋʤje jεnεkylyp turup,—kim bilidu,ɑ∫nisiniŋyzyk-pyzyki,jɑʁliq-pɑʁliqi untulup qɑldimu teχi?
译者将“难保干净”译为sɑq jyrdi deɡilimu bolmɑq,是根据具体语境的需要对原文的委婉义的忠实。王熙凤对贾琏与外面的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但是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另外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不允许妇女不尊重自己的丈夫,所以她只能委婉地表达这层言外之意。
6.他生性轻浮,最喜拈花惹草,……(第二十一回)
uniŋystiɡεjεŋɡiltεk,ki∫ilεrniŋojʁɑnmiʁɑn bεzlirini ojʁiti∫qɑ bεk ɑmrɑq birʧokɑn idi.……
“拈花惹草”泛指好色多情之意。色情、淫乱是封建礼法所不允许的,属于避讳的事物,不能在一般的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出现。因此,汉语习惯上用一些听起来文雅的词语,如“花”“草”“月”“柳”等替代。译者将其译为ki∫ilεrniŋojʁɑnmiʁɑn bεzlirini ojʁiti∫qɑ bεk ɑmrɑq,与原文作者想表达出本性轻浮相一致,获得了与原文一致的委婉、含蓄的语用效果。
(三)熟语
《红楼梦》维吾尔语译本译者在处理汉语熟语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是:在自己的认知语境和原语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推理出原作的文化信息,并对译语读者的认识语境作出正确的假设,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选择适当的译文,尽可能地使原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待相吻合。这种翻译实践是与语用学的关联理论相一致的。例如:
1.(宝玉)因又自叹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第三十四回)
—bumu rɑsttinlɑ ɡyl bεrɡilirini kommεkʧi bolʁɑnbolsɑ,buχuddi∫i∫iniŋqe∫inituru∫ini qo∫nɑ qizniŋdoriʁɑnidεk jeŋi qiliqʧiqirimεn dεp teχimu sεtli∫ip kεtkinidεklɑ bir i∫boptu—dε.
“东施效颦”说的是越国的美女西施因有心脏病,病发时会捂住心口,紧蹙娥眉。同村的一个丑女,后人称“东施”,见到西施发病时的神态认为很美,此后也在村里学她的样子,却丑得可怕。比喻胡乱模仿,效果适得其反。译者将其译为∫i∫iniŋqe∫ini turu∫ini qo∫nɑ qizniŋ dori∫i,并对“东施效颦”的故事及含义通过注释做了文化背景补偿,这样不仅较好地保留了原语的形象,而且读者也能领会其语用隐含。
2.香菱笑道:“好姑娘,你趁着这个工夫,教给我作诗罢。”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第四十八回)
—obdɑnχenim,—didi kylyp∫jɑŋliŋ,—mu∫u pursεttinpɑjdilinip,mɑŋɑ∫eirjezi∫niøɡitip qojsiŋizʧu!
—sεn-zε,ørdεkniŋɡø∫ini jimεj turuplɑʁɑzniŋ pejiɡεʧy∫ypsεn-dε,—dεp kyldi bɑqʧεj,……
“得陇望蜀”是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成语,原义指已经得到了陇(古地名,今甘肃东部),还想占领蜀(古地名,今四川中西部),比喻贪得无厌。原文语境指的是一个好学的丫鬟香菱在得到与宝钗做伴的机会后,又要求宝钗教她做诗。宝钗说她得陇望蜀,并无责备之意,只是嗔怪她求学心切。译者将其译为ørdεkniŋɡø∫ini jimεj turuplɑʁɑzniŋpejiɡεʧy∫y∫,将词汇信息的形象与语用含义没有关系的原文形象省去,换之以译语读者熟悉的形象,并把原来的贬义译成中性感情色彩的意义。其语义、语用都符合原文,而且使译语语篇表达流畅。
3.(王夫人)说道:“……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第八十一回)
χεqlεrniŋqiz bɑlɑ“itqɑ tεɡsεitniŋqoli,pitqɑ tεɡsεpitniŋ”diɡεn ɡepini ɑŋlimiʁɑnmidiŋ?hεmmε qizlɑrʁɑʧoŋɑʧɑŋdεkχɑni∫bulu∫ʧy∫yp qɑptumu?……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意思是指旧时女子没有婚姻自由,只能听凭父母安排,无论嫁给什么样的人都必须跟着这个人。这是古代女子“三从四德”的文化折射。译者在原语和译语之间寻求了一种相似的文化表达,把它译为译语谚语itqɑ tεɡsεitniŋqoli,pitqɑ tεɡsεpitniŋ。
4.王夫人道:“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俗语说的,‘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叫我能怎么样呢。”(第八十一回)
buniŋʁɑʧɑrεjoq,—didi wɑŋɑʁiʧɑχenim,—konilɑrdɑ:“jɑtliq qilinʁɑn qiz jεrɡεsepilɡεn su”deɡεn ɡεp bɑr.meniŋqolumdin nemεkelεtti?
“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这句俗语的文本语境为原语读者和原语读者能够共享的语境,译语读者凭借自己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因此,译者把它译为jɑtliq qilinʁɑn qiz jεrɡεsepilɡεn su。这样达到了既忠实原文传达语言意义,又很好地传达了文化信息,使译文形神兼备。
5.(芳官):“……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呢!……”(第六十回)
siliniŋkelip meni tillɑjdiʁɑnʁɑ hεqqiliri joq, meni sili setiwɑlmiʁɑn.ʧørilεr bir-biriɡεqol berip tuʁqɑn bolu∫simu hεmmisi bir qul!mɑŋɑ nemε kørɡylyk bu!
“梅香”代指婢女、丫鬟。“拜把子”是指异性结为兄弟、姐妹。这条歇后语的意思是大家一样都是奴才。译者在判断出译语读者缺乏相应背景理解这条歇后语后,将其译为ʧørilεr bir-biriɡεqol berip tuʁqɑn bolu∫simu hεmmisi bir qul,虽然损失了原语的形象,没有传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但是成功地传递了原语的语用意义。
三、结语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汉语-维吾尔语文化负载现象的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可以填补汉语-维吾尔语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语言空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文读者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近似等值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实现语用等值;有利于译者充分理解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语用意图,并准确地选取恰当的译语表达出来;能够较好地解释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取问题。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原文和译文之间在形式和语义的尽可能等值,更应该是争取在语用意义上的功能等效,使得翻译“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作的内容’,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以求等效。”①因此,我们认为语用学翻译理论在汉语-维吾尔语的跨文化翻译中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随着语用学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语用学将不断发挥其在翻译领域的作用,逐步拓宽翻译研究的途径和视野,使翻译研究更为深入,为跨语言跨文化间的交际提供更加宽阔的平台。
注释:
①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1]曾文雄.语用学翻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钱多秀.翻译的语用学研究与翻译中的道德——评介三本翻译学书籍[J].中国翻译,2003,(2).
[4]肖维青.翻译研究的语用学新视角——评陈科芳博士的《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1.
[5]马志刚.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视角——评介《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8,(2).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Application of The Uyghur Translation of A Dram of Red Mansions
LI Shao-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Kashi Normal College,Kashi Xinjiang 844006)
Language application is a science of studying the language of language users;it has the same research audience of translation,and is about the applic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languages.In recent years,Language application theory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 translation research,and created a new perspective and way of thinking.The paper analyses the titles,euphemisms and idioms of Uyghur translation of'A Dream of Red Mansions'from the language application perspective.It analyses the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theory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mong the Chinese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It explains the significant guiding functions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theory in translation research,and the enormous explanation ability to Chinese-Uyghur language carrying culture translation.The paper discusses that translation not only searches for equivalence in meaning and form from language application perspective,but also seeks fidelity in the intention of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contex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Language application;Language context;Culture;Translation
H215
A
2095-6967(2015)01-065-06
[责任编辑:贺飙]
2014-10-11
本文系新疆民汉语文翻译研究中心一般项目“汉维词语的文化附加义对比研究”(XJEDU010813C03)的阶段性成果。
李少平,喀什师范学院中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