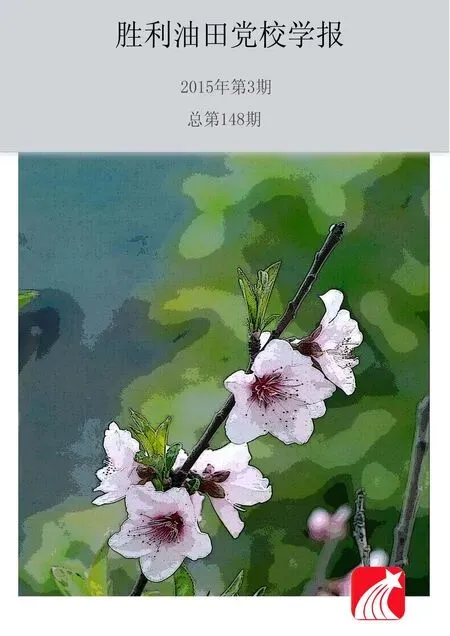旧制度的毁灭与重塑
——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开去
2015-04-09纪光欣张静静
纪光欣,张静静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580)
旧制度的毁灭与重塑
——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开去
纪光欣,张静静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580)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不仅催生了大革命,而且塑造了大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使大革命后的法国无法摆脱旧制度阴影。这场伟大变革的背后蕴含着旧制度的毁灭与重塑,也启示人们不断反思并探寻抗衡行政集权、保障自由的民主建设之路。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央集权;社会变革
1789年爆发的“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1]40法国大革命,无疑是给统治欧洲和法国若干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强烈冲击。然而,这场革命并没有缔造一个新的法兰西,却使法国陷入专制与革命的循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通过回望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阐明“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1]75这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关系的批判性分析为后人留下深深的思考空间。
一、法国的旧制度及其中央集权制
为了厘清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托克维尔“阅读并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1]5,能够“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1]5,使法国的旧制度得以复原。
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是中世纪封建制度残余与中央集权体制的复合体。随着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日渐衰落,中央集权制自路易十四以来却不断强化。在大革命前,法国就已经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集权制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1]75
托克维尔用详实的资料和较大篇幅再现了法国在大革命前就已形成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场景,旧制度下中央集权已经无处不在,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和国民的日常生活,“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1]30-31可见,中央集权下的法国政府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监护人”。
二、中央集权的“旧制度”催生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产生了众多恶果,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对民主和自由的严重践踏,强化了众多社会恶果,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催生了大革命。托克维尔称之为大革命从旧制度中自动产生。
1.阶级的分化孤立以及各阶级矛盾的激化。大革命前的法国自上向下主要由王权、贵族、领主、教士、资产者、城市平民及农民等社会阶层构成,各阶层之间彼此孤立、敌视,阶级矛盾不断恶化。
首先,以国王为代表的王权摒弃城市自治和教区管理,以“蛮横”的中央政府表面上控制着一切,以至于“在旧制度下,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1]93但另一方面,政府该管的却又不管或管不好,激起其他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
其次,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制度名存实亡。中央集权制下,“组成御前会议的并不是大领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有资历的前总督以及其他有实际经验的人,所有成员均可撤换。”[1]77国王任用没有贵族身份的平民出任行政官员,贵族统治被官吏等级制取代。在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法国贵族却保留并新增了众多令人民反感的专有特权(以免税特权最为明显),再加上贵族将居住地迁徙到城市,彻底摆脱了对农民的领导,同农民的关系从领导者蜕变为收取地租的债权者,也使整个农村共同体直接暴露于中央政权之下。本来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但是当“因为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1]73再者,由于贵族享受一定的免税特权,资产者通过购买官职也能享受该特权,政府就只能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尤其是农民背负沉重且不平等的捐税和徭役,生活困苦不堪,势必会引起强烈不满。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力并使它骤然死亡。”[1]140
2.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的泯灭。18世纪的法国,“大臣已经萌发出一种愿望,要洞察所有事物,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府的完善,这种愿望日益强烈。”[1]103以王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逐步侵吞地方自主与独立,并控制了地方一切事务。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有意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管理,着手制定并实行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规,御前会议(国王领导)主持整个中央政府的工作并通过总监派出的总督和总督任命的总督代理实现对地方的层层管理。“城市一切工程都得依照御前会议裁决的方案和预算进行。”“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总督的意见,他对每件事都有坚定意见;他一直管到了节日庆祝问题。”[1]88正如托克维尔所感叹的,“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之深远胜于这项规定所示范围;它的权力远远大于它的权利。”[1]88
路易十四以后,国家行政机构对司法独立性的侵蚀越来越严重。君主制最后一个世纪里国王所颁布的敕令和宣言以及御前会议的命令显示,在这一时期,“政府在采取一项措施之后,往往要指出:该措施所引起的争议和可能由此产生的诉讼,应一律提交总督和御前会议处理。”[1]95此外,御前会议还以“调案”的方式对司法不断进行干预,“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释政府法令引起的争讼,均不属普通法庭管辖”[1]95,而归总督或御前会议审理,这是大革命前法国政治生活的惯例。在当时,凡是涉及政府的所有讼案只有行政法院才能真正理清。1770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撤销,更是使司法独立在名义上不复存在。而在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指出,“它的思想属于旧制度。”[1]95
3.原子化社会的形成以及人民政治参与机会的丧失。中世纪的法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和团体主义特征,以行会或其它团体的形式进行活动,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但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制摧毁了这些具有堡垒作用的社会中间团体,使中央政权直接面对公民个人。一方面,这使所有法国人相似且趋同,人们完全摒弃公益品德并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1]35。另一方面,“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1]116,各阶级之间相互疏离并难以合作,而当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权力时,由于缺乏中间团体的保护,他们只能任由国家侵害。
此外,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政治自由的丧失、政治生活的紊乱。由于那些没有任何政治实践经验的法国文人控制了舆论的领导权,“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1]177。贵族和资产阶级却长期被集权政府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缺乏政治参与和经验。这种“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1]178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民众政治参与、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的丧失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过分依赖,“政府取代了上帝”[1]109,“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1]107
从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的描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旧制度下的中央政权以所有可能的手段强化中央集权,分散和消解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被分散的社会力量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状态,这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革命都显得必要且迫切。
三、旧制度的重塑:大革命后的旧制度阴影
“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1]31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要小”[1]29,因为大革命之后所创建的国家政体在本质上仍然是旧制度及其内涵的延续甚至加强。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在很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这些岂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央集权制吗?……这是同一事物。”[1]99于是,托克维尔断言,革命后的集权体制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他分析,旧制度的核心即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后得以延续和重塑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1.大革命进一步摧毁了法国社会中保障自由的中间团体。表面上,大革命攻击和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但“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1]49。大革命打碎了法国社会中保障自由的中间团体,试图“在每个法国人身旁设立政府”[3]239,使革命后的新社会依旧由不足以胜任公共行动的孤立的个体组成,这便使中央集权成为构建国家的唯一依靠。
2.旧制度塑造了法国具有集权倾向的民情。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塑造了法国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1]29追求平等与自由本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目标,然而鉴于法国人民尤其是法国农民在大革命前遭遇的种种压迫和不平等待遇,法国人民对平等的渴望可以说更加激烈且紧迫,相比之下,“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3]496所以当自由遭遇平等时,往往人们优先选择实现平等。但托克维尔担心的是,平等往往会“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2]838。事实上,由于法国人民对平等的极度渴望和追求,为了实现他们所憧憬的平等状态,他们对中央政府过度信赖、对权力过分依附与服从,“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1]107这种深藏于旧制度中的集权倾向在19世纪始终是法国人民的一种思维方式,也为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后的延续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3.大革命后的新法国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泛滥。在民主时代和商业社会背景下的新法国,由于大革命摧毁了保障自由的社会中间团体,社会原子化趋势强化。一方面,与具有团体主义特征的贵族社会相比,弱小的个体因缺乏依靠只能仰仗集权政府安身立命,他们倾向于远离公共领域,退避回私人世界,个人主义成为社会的普遍信念;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醉心于物质福利,更不愿献出精力参与公共事务,使强大政府的存在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1]35这些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被日渐强大的集权政府所控制而不能自主,专制在个体退居私人生活时乘虚而入且日趋稳固。
四、寻求抗衡行政集权、保障自由的民主之路
旧制度下的法国平等和自由尽毁,这一切都使大革命不可避免,但不可否认,大革命后的法国仍旧笼罩在旧制度阴影之下,始终尴尬地徘徊于革命与集权的循环之中。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法国抗衡行政集权、保障自由之路呢?
托克维尔不赞同将英国视为法国政治楷模的论断,尽管两国政治机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越来越不同。它们就像两条线,从邻近点出发,但沿着略有不同的倾斜度伸展,结果两条线越延长,相隔越远。”[1]139他选择踏进不曾有过旧制度困扰的美国,并从美国自由和繁荣的原因中为法国寻找药方。
1.积极培育社会中间团体,保障结社自由。强大的国家和个人之间有必要存在各种形式的中间体来避免国家对个人施加压力,而“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制止滥用职权的天然社团。”[2]217但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贵族这一可以与专制抗衡的社会中间力量,使分散而脆弱的公民个人因直接暴露于中央政权之下,任由国家宰割侵害。要想使法国走出旧制度的阴影,真正抗衡中央集权,有赖于在既有的中央集权与原子式个体之间建设起具有凝聚力量、使个体具有归属感的社会中间组织。“在民主社会,社团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贵族社会中贵族的社会、政治角色。”[2]639通过结社形成的自由团体:一方面,可以作为中央政权与公民个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帮助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克服个人主义的人情冷漠,增强公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缓和社会分化和矛盾——它们无疑成为保障自由的社会中坚力量。
2.自觉推进公民投身政治实践,构建公民社会。托克维尔强调政治实践在培养公民民主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作用,“在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实践中,公民养成了参与政治的习惯和能力。”[2]638个体只有真正摆脱狭隘的私人空间,与其他公民一起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其自私性和软弱性,培养公共意识。当充满公共精神的公民以自由意志联合起来行动时,专制便绝无立足之地。托克维尔非常推崇美国的“乡镇自治”。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2]67乡镇自治孕育了美国人民共同的自由精神,成为美国人民抵御专制的重要力量。
多元民主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更多地强调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它强调创造一个具有实质独立性、自主性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空间。美国强大的公民社会与相对收缩的政府之间的对抗模式显然成为保障其民主与自由的无法撼动的根基,而这也更加符合人们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诉求。
3.有选择地“扬弃”,正确处理社会进程中革命与传统的关系。托克维尔在书中这样分析革命者的心态:“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1]29革命者将旧制度视为一切恶的根源,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旧有的社会制度及结构,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至于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也只是被革命者理解为颠覆旧有秩序、重建自由民主的新秩序的必经阶段。但是,尽管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承接1789年革命的依旧是法国社会的动荡以及革命与集权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革命绝非抛弃历史,而是对历史的重建。正如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所言:“法国革命家们在横扫罪孽深重的旧秩序时,却没想到旧秩序也是对人性阴暗面的制约,秩序的坍塌只会导致人欲的肆虐无忌,造成道德的丧失和无法无天的行为。”[3]113他们专注传统的缺陷,却忽视了其潜在的必要性,所以大革命后出现社会的混乱与失序不可避免。社会变革是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传统的结果,必须正确处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对传统进行有选择的“扬弃”或“转化”。
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既有渊源流长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处于集权体制之下。传统社会的专制集权统治及其文化心理,依然是走向现代社会的沉重包袱,托克维尔对旧制度在法国毁灭与重建过程中的理性反思无疑为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埃德蒙·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Regime——Based 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Alexis de Tocqueville
JI Guangxin,ZHANG Ji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Qingdao 266580,China)
I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lexis de Tocqueville recognized that the centralized system in old regime not only spawned the French Revolution,but also shaped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 structure after the revolution,resulted that France after the revolution could not get rid of shadow of the old regime.The great revolution implied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regime and inspired us to rethink and explore constantly the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road of resisting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as well as guaranteeing freedom.
Alexis de 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social revolution
D07
A
1009-4326(2015)03-0022-04
(责任编辑 王先霞)
2015-04-20
基于经典著作研读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SDYC13044)的阶段性成果
纪光欣(1966-),男,山东临沂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行政哲学与行政思想史。
10.13600/j.cnki.jpsslof.issn.1009-4326.2015.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