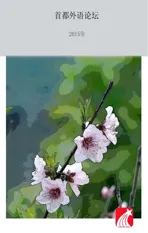一个唯美主义者的“中国梦”
——评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
2015-04-08首都师范大学英文系
首都师范大学英文系 杨 波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中国梦”
——评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
首都师范大学英文系杨波
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哈罗德·阿克顿痴迷中国文化,他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再现了他关于东方中国的跨文化体验。“唯美者”阿克顿怀着对西方世界的失望和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旅居中国,并在中国北京找到了理想的美和心灵的寄托。然而,作为一个“唯美者”,阿克顿的中国观是建立在纯粹的艺术追求上的中国印象,他所爱的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经过他的艺术眼光过滤的、梦里的中国。
哈罗德·阿克顿东方主义“唯美者”“中国梦”
引言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也是20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与独到的理解。他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再现了他关于东方中国的跨文化体验。《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中的中国观呈现出与萨义德《东方学》中以欧洲中心论和殖民叙事为特点的异文化观迥然不同的面目。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形象隐藏了文化帝国主义阴谋:精心构筑原始、野蛮、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从而为西方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奠定基础。然而,一种激进的理论往往在有所揭示的同时,也会有所遮蔽。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在揭露和批判文化殖民主义的同时,也有将东方主义同质化、单一化的缺憾。周宁在《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一文中指出:“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在建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道德权力,使其在西方扩张事业中相互渗透协调运作;另一种却在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表现出西方文化传统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①周宁:《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5—6页。应该说,《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中的中国观正是属于后一种“东方主义”,它以仰慕东方、憧憬东方为其特点,是一种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唯美者”阿克顿经历了欧洲的战乱,心灵的创伤使他向往古老宁谧的东方文化。他怀着对西方世界的失望和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旅居中国,并在中国北京找到了理想的美和心灵的寄托。
一 哈罗德·阿克顿的中国情结
《回忆录》中的阿克顿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痴迷。早在来中国之前,阿克顿就通过亚瑟·韦利译的中国诗歌、翟理斯译的《庄子》、理雅各译的儒家经典了解了中国文化,因此来到中国以后,他发现对中国的一切都很熟悉。尽管如此,他刚踏上这片土地时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深情地说:“我刚进入北京时的心情就好像是吉本进入永恒之城时的心情一样,‘一连几天沉浸在如痴如醉的感觉之中,只有等自己慢慢缓过神来之后,才能开始冷静而细致的考察。’”②Acton,Harold.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Hamish Hamilton Ltd,1984.p.276.缓过神来之后,阿克顿对紫禁城及北京周边的建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并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赞叹。在阿克顿看来,欧洲的宫殿无一能和紫禁城媲美,紫禁城开放式的院落使其与周围的亭阁和自然环境融合得天衣无缝,“连天空也成了建筑设计的一部分;那些带着弧度的金顶就好像是镶嵌着珠宝的高脚杯一样盛托着蓝色的天空”,使得整个建筑群显得既宏伟,“又不失灵动与优雅”,有一种“仿佛向上飞升的空灵的质感”。①Acton,Harold.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Hamish Hamilton Ltd,1984.p.276.
令阿克顿心醉的不仅是中国的建筑,还有中国的古典文化和艺术。阿克顿热爱中国戏剧,尤其是京剧。他说,虽然中国戏剧声音吵闹,但是“吃了几年中国饭以后,响锣紧鼓对他的精神是一种甜蜜的安慰”,而与中国戏剧相比,“西洋音乐好像哀乐一样了无生气”。②阿克顿对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师从溥杰亲王学习中国绘画,并拜访了当时与溥杰齐名的平民画家齐白石。阿克顿认为,中国画完美地体现了人品与画品的合一;中国画看重的不是外在的技巧和形式,而是内在的精神,因此中国画不是某种技巧的展示,而是“人的整个精神的结晶”,“在欧洲只有在近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对于自然的精确模仿并非绘画的第一要旨,而只要我们看一看宋朝的山水画,我们就会发现欧洲人还在摸索的那些问题在中国早已有了答案。”③Acton,Harold.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Hamish Hamilton Ltd,1984.p.374.
1937年,阿克顿曾回了一趟佛罗伦萨的老家,那里一切都未曾改变,景物依旧迷人,亲情和友情也依旧浓郁。阿克顿称佛罗伦萨是自己的“出生地”(my birthplace),而北京则是自己的“收养地”(my place of adoption),在究竟该选择“出生地的活力而世俗的美”,还是“收养地的更加空灵的美”之间,他感到难以取舍。④Acton,Harold.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Hamish Hamilton Ltd,1984.p.384.阿克顿最终选择了回到北京,希望能在北京安度此生。然而,1939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展开,阿克顿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精神之乡。离京之前,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为阿克顿画了一幅罗汉打坐图,并题其像赞:“学贯西东,世号诗翁。亦耶亦佛,妙能汇通。是相非相,即心自通。五百添一,以待于公。”①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离开中国之后,阿克顿还连续多年支付着他在北京寓所的房租,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北京与中国文化再续前缘,可惜此生未能如愿。
二 西方人的“中国梦”及阿克顿“中国梦”的特点
阿克顿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仰慕并非特例。西方人的“中国梦”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代。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以一种描述人间乐园的语言描述了“大汗的大陆”,那里有广阔的土地、无尽的财富、繁华的城市和幸福的人民。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中国崇拜开始波及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织品,中国的园林艺术,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并在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同早期的西方人相比,启蒙哲学家更关注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赞美中国的开明君主,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他们看来,中国之伟大,不在器物,而在于思想观念。伏尔泰说,欧洲王公贵族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是知识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②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19世纪初,西方的“中国热”开始告退。这部分由于欧洲的“中国式风格”热潮已经走到了自然规律的尽头,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欧洲势力的增长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及海外领土的扩张而产生的优越感。欧洲人觉得自己不仅在自然科学,就是在伦理学方面也是最优异的,而与之相反,中国则成了停滞不前的、东方专制的中华帝国,成了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于是,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逐渐被蔑视所取代。对中国的批评指责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甚至一度酿成了“黄祸论”,而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阴险狡诈、无所不能的“傅满楚”博士更是成为坏蛋中国佬的典型。
然而,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们造成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极大地打击了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西方人开始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并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中找寻欧洲文明危机的出路。一时间,西方文化中的“中国热”再次达到高潮,这一轮的“中国热”在继承早期有关东方异国情调式的想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用东方文明批判西方社会文化的反思精神。自20年代起,一些西方哲学家、文学家怀着对自身文化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怀着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吸引和亲近感来到中国,试图从这个古老的国度中找到新的希望。英国思想家罗素1920年来华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在中国停留了近一年。罗素对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以及老庄的思想境界都很感兴趣。他认为,中国人有着宽容友好、谦恭有礼的品格,和西方人的尚武好斗形成鲜明对比;罗素非常珍视中国文化蕴含的全人类价值,认为中国文化对于构建未来的人类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有可能成为拯救危在旦夕的人类文明的妙方。剑桥人文学者洛斯·迪金森一直梦想着以希腊和中国模式建立现代价值,而来到中国之后他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认为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场所。新批评家瑞恰慈一生到中国六次,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崇尚中国古代哲学,试图用中国哲学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来平衡西方哲学的精确性。剑桥诗人燕卜荪也是一个执着的中国迷,他在中国一待数年,感到中国每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并著有《南岳之秋》、《中国谣曲》等诗歌来纪念中国。
与其他同时期来华的西方有识之士一样,阿克顿同样是在目睹了一战后西方人的信仰迷失和精神危机 (即所谓“精神的现代病”)之后,出于心灵救赎的需要,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寻求答案。在小说《牡丹与马驹》中,阿克顿借主人公菲利浦之口道出了心声:“是中国治好我的病,战争让我的生活变成沙漠,而北京让我的沙漠重现生机,就像那牡丹盛开。”①Acton,Harold.Peonies and Ponies.Oxford:Oxford UP,1941.p.121.然而,阿克顿看待中国的心态又与其他来华的西方学者有所不同。像罗素、狄金森、瑞恰慈、燕卜荪等人来到中国都是为了从东方汲取传统文化拯救丧失信仰的西方世界,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只能是在西方,并非真想安心做一名中国人,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而阿克顿则一心想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在《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中,阿克顿不仅像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一样住在四合院中,而且努力学中国话,练中国字,画中国画,试图尽快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他这样描述四合院生活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受:“我以一种甜蜜而愉悦的心情细细地品味着四合院生活的和谐安宁,我头顶的星空,以及巷子里小贩独特的叫卖声。……这里我的生活过得如此的丰富,以至于我之前在欧洲的存在显得那样无足轻重,似乎这些年来的努力都只是在追逐鬼火。”①Acton,Harold.Memoirs of an Aesthete.London:Hamish Hamilton Ltd,1984.p.351.在北京的四合院中,阿克顿不仅获得了心灵的安宁,并且对自己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完成了自我的精神蜕变。他希望和自己的过去“说再见”,并在北京度过余生。因此,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寻求良药以拯救西方文明的危机,他们来自西方,并带着中国的精神回到西方;而唯美者阿克顿的目标则是在东方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阿克顿就像是“西方文明的逆子,又仿佛是中国文明流落在欧陆的弃儿,怀着一份倦游归乡的挚诚,把北京当作安身立命的归宿、栖息灵魂的家园。”②葛桂录:《论哈罗德阿克顿小说里的中国题材》,《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5页。
三 阿克顿“中国梦”的思想根源
阿克顿不仅热爱中国,并且以身在中国过着中国人的生活而快乐,这在西方人中无疑是罕见的。然而,阿克顿对中国的热爱是建立在他是一位“唯美者”这样一个前提下的。作为一个“唯美者”,阿克顿的人生观是艺术的,他的中国观也是建立在纯粹的艺术追求上的,所以他的“中国梦”充满了浓郁的历史和艺术气息,而非建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在《回忆录》中,阿克顿曾短暂离开北京,赴上海、南京、广东等地旅游,然而,这次南行的经历令阿克顿倍感怅惘,因为这些地方离他对中国的理想太远了。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也是中国的时尚之都、工业之都、娱乐之都,但是在阿克顿看来,上海跟许多西方工业城市一样是缺乏人道的城市,资本家靠剥削和压榨劳工完成资本积累,而工人阶级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广东曾经是南方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并且如阿克顿所说“是各种先进事物的总部”,但也同样没能给阿克顿留下好印象,因为这里已没有多少历史遗存。阿克顿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他心目中的理想国,那个充满着浓郁艺术气息的东方国度,像上海、广东这样的地方有悖于他的主旨,自然会令他感到失望了。只有当他结束南部的旅行回到北京之后,他才重新找到家的感觉。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很容易将中国误解为像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是一个文物博物馆。”①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将中国博物馆化,是西方人(尤其是20世纪西方人)的典型心态,这一点阿克顿也不例外。而且阿克顿作为一个“唯美者”,纯粹是从艺术追求的角度去看待中国,所以他的“博物馆”心态和一般人相比显得更深刻彻底,这在他对中国京剧与古典艺术的嗜好上得到突出体现。对阿克顿而言,中国是一个古典的中国,一方吟诗作画尚美多礼的文化;正是古老中国的灿烂文化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唯美者,为他提供了心灵的安宁和慰藉。至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和现实需要,则既不是他所能顾及到的,也不是他所感兴趣的。事实上,当他意识到中国的现实并非他所想的那般美好时,他选择了逃避和对现实视而不见,选择退回到北京城的四合院当中,安守着自己的梦想家园。所以,“唯美者”阿克顿对中国的爱是盲目的,他所爱的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经过他的艺术眼光过滤的、梦里的中国。
J.J.克拉克在《东方启蒙》一书中指出:“对西方持久的东方迷恋,最基本的解释就是一个词:浪漫主义。根据这一观点,西方人对东方的兴趣大部分取决于一种要逃遁到某个遥远的、美幻的‘他乡’,在那里找到一种幻觉般的超越,实现复归失去的智慧与黄金时代的梦想。……简言之,东方迷恋是欧洲的一种集体梦幻,表现着西方文化中不断出现的厌倦感。”②Clarke,J.J.1997.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 and Western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19.西方人不满于工业社会的现状,却又苦于在西方文化自身的范围内找不到出路,于是便借助于对异域文化的想象,来表达他们的思乡恋旧与不满情绪。这种关于异域文化的构想物,福柯称之为“异托邦”。按照福柯的解释,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点的地方,而异托邦是既超然于现实之外、又在现实中有确定方位的“真实之地”,“它在现实中可以落实到某个位置,却又表现得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它是一个完全另类的地方。”①Foucault,Michel.Of Other Places,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edited by Nicholas Mirzoeff,Rougledge,1998.p.239.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正是这样的“异托邦”,它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现实的、确定的国家,而是一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异度空间”。它是西方文化精心构筑出来的“他者”,是西方社会集体梦幻的投射。作为“异托邦”出现的中国形象,价值不在于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现实,而是作为一种具有审美逃避与超越意义的梦幻故乡。它表明了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逃避和超越异化现实的途径。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特别是北京,对唯美者阿克顿而言是“别处,是梦想之地,在那里可以摆脱自我的负担,是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场所,是可以畅游的地方,是家园”。②Bris,Michel Le.Romantics and Romanticism.Geneva:Skira,1981.p.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