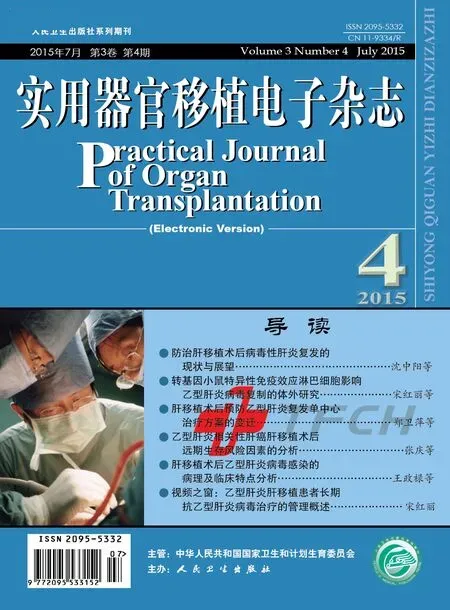肾移植术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治疗
2015-04-02涂金鹏郑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天津300192
涂金鹏,郑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天津 300192)
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引起肾移植术后肝功能损害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肾移植术后移植物失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患者的长期存活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1]。目前,肾移植患者HCV感染率为10%~40%[2]。肾移植术后HCV感染与蛋白尿、排斥反应、移植肾小球肾炎、移植后糖尿病等密切相关[1-3]。
肾移植术后HCV感染的治疗方案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目前抗HCV药物种类仍相对有限,除经典的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外,新式药物如蛋白酶抑制剂多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尚无针对肾移植患者的临床研究。目前认为,对于HCV感染的尿毒症患者,移植术前抗病毒治疗是十分必要及有效的[4]。由于患者移植术后须长期使用的免疫抑制药物可加重抗病毒药物的不良反应,移植后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及治疗方案尚存在争议。本文对肾移植术后HCV感染者的预后、并发症及治疗方案进行概述。
1 肾移植术后HCV感染的预后
多数文献认为,HCV并不影响术后短期生存率,但对比10年生存率,肾移植术后HCV感染患者生存率较未感染者低。Pereira等[5]的报道显示,肾移植患者HCV感染后的死亡风险要比HCV阴性患者高出1.41倍,HCV是影响患者10年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而Maluf等[6]报道的包含43例肾移植患者的前瞻性研究表明,HCV感染的患者术后1年及3年生存率显著低于无HCV感染组(HCV感染组为81.4%及68.5%,无HCV感染组为97.1%及92.9%,P=0.01)。降低术后生存率的因素为肝病、心血管疾病、脓毒症、蛋白尿、移植器官衰竭等。
2 并发症
2.1 移植后肝病:移植后肝病是肾移植术后HCV感染的首要死亡原因。HCV引起肝细胞损伤机制主要是细胞介异的免疫性损伤,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使机体对病毒抗原的识别、清除能力下降,致使HCV病毒复制增加。但此时肝脏依靠自身的代偿能力维持着在病毒损伤和自身代偿之间的平衡,因此移植术后早期的患者/肾存活率与正常人群无明显差异。一旦超过机体的代偿极限,在诱发因素(如感染、药物中毒)出现时,肝脏细胞大量坏死,迅速进入肝功能衰竭状态。Seth等[7]报道了6例肾移植术后因HCV感染而出现快速进行性肝衰竭并导致死亡的病例。这些患者从肾移植术后到出现肝衰竭的平均时间为11.8个月,而从移植术后到死亡的平均时间为27个月。
2.2 排斥反应:HCV感染与移植肾排异的关系目前尚无统一认识,Forman等[8]研究发现,肾移植术后HCV感染患者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为19%,而未感染患者发生率为6%。陈旭春等[9]对54例肾移植受者进行随访,其中HCV抗体阳性受者27例,结果HCV阳性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9.14%比6.38%,P<0.01),HCV阳性组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23.40%比12.76%,P<0.01)。
3 肾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
肾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NODAT),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猝死及器官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主要机制为HCV直接或间接诱导了胰岛β细胞的免疫损伤[10]。此外,免疫抑制剂也是NODAT的重要致病原因,而免疫抑制剂是否通过促进HCV的复制而引起NODAT尚无相关研究。因此,对于肾移植术后HCV感染患者,术后免疫抑制方案应尽量避免应用他克莫司,并适当减少激素用量[11]。
4 丙肝相关性肾炎
丙肝相关性肾炎(HCV-GN),多数表现为镜下血尿,可伴有肾功能受损,部分患者可出现蛋白尿、水肿、高血压等症状,约5%患者可进展为急性肾功能衰竭,其发病机制与HCV所致的免疫复合物在肾小球沉积有关。通过肾活检能在肾小球中发现HCV抗原存在。常见的HCV-GN的病理类型有膜增生性肾炎(MPGN)、膜性肾病(MGN)、冷球蛋白血症肾炎等[12]。Hammoud等[13]在 399例肾移植受者中发现,12例为MGN,9例为MPGN;而HCV阳性患者MPGN比例最高(占78%,9例中有7例)。此外,在所有HCV阳性的患者中GN占到6%(7/117),而HCV阴性的患者中GN仅为0.7%(2/282)。
5 肾移植后的抗病毒治疗
对于肾移植患者HCV感染的治疗一直存在争议。由于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HCV病毒复制一般偏高,而对抗病毒治疗的持续病毒学应答(SVR)较低,且不良反应大,同时抗病毒药物也可增加排斥反应及移植物失功的风险。因此,对于移植后是否常规进行抗HCV治疗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在患者已明确有移植后并发症的情况下,才考虑进行抗HCV治疗[14]。
5.1 干扰素:干扰素是一种广谱抗病毒剂,并不直接杀伤或抑制病毒,而主要是通过细胞表面受体作用使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从而抑制病毒的复制,同时可降低肝脏的损害及肝硬化的发生率。20世纪90年代早期,肾移植术后一般采用单用标准剂量干扰素α,即3万~10万单位,3次/周。50%患者出现转氨酶下降,25%患者病毒学转阴,但急性排斥反应和移植物丢失的风险大大增加[15]。有研究报道,肾移植术后继发HCV感染患者应用干扰素治疗后,移植物排斥反应发生率为17%~73%,且一旦发生排斥反应,移植肾的功能将不会再恢复[16]。因此,多数研究认为肾移植术后只有继发重症肝炎才可应用干扰。
Fabrizi等[17]进行的荟萃分析共收录了12个临床试验(102例病例),评估肾移植术后应用干扰素α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干扰素α单独或联合利巴韦林),结果SVR为18.0%〔95%可信区间(95%CI)=7.0~29.0〕,流失率35.0%(95%CI=20~50),终止治疗最常见原因为移植物功能障碍(n=28,71.7%)。最终结论,肾移植术后以干扰素α为基础的治疗方法缺乏安全性和耐受性。
5.2 利巴韦林:利巴韦林是人工合成的鸟嘌呤核苷类似物,可通过抑制病毒RNA聚合酶抑制病毒复制,单用利巴韦林治疗可减少肝脏的免疫性损伤。2003年Kamar等[18]首次对单用利巴韦林治疗肾移植术后HCV感染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了研究。16例患者给予利巴韦林治疗,初始剂量1 000 mg/d,以后根据患者血红蛋白(Hb)水平调整剂量,32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未经治疗。研究发现,单用利巴韦林降低转氨酶及肌酐水平,并可改善蛋白尿水平,但对病毒复制无显著影响,3例患者因严重贫血中途停止治疗。Sharma等[19]报道8例单用利巴韦林治疗肾移植术后HCV感染的研究,经过6~24个月的治疗,转氨酶显著降低(U/L:198.4±147.6比 104.8±66.5,P < 0.05),仅一例HCV-RNA转阴。由此可见,单用利巴韦林可改善生化指标,但对病毒血症无显著作用。
6 干扰素联用利巴韦林
临床试验表明,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是最有效的抗HCV治疗方案,干扰素α联合利巴韦林治疗慢性丙型肝炎总的SVR为61%[20]。Pageaux等[21]报道8例应用干扰素α联合利巴韦林治疗肾移植术后丙肝,其中4例病毒学持续应答,1例因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导致移植肾失功。而Shu等[22]报道11例患者应用小剂量干扰素α联合利巴韦林治疗肾移植术后丙肝,疗程48周,其中3例患者中途终止治疗,1例因急性移植物失功,2例因进展性闹脓毒症,仅3例患者持续病毒学应答。综上所述,目前干扰素联用利巴韦林治疗肾移植术后丙肝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但在治疗过程中常因移植物功能障碍、肾功能损害、贫血等不良反应而不能耐受,尚需大规模、多中心的对照性临床研究论证。
7 蛋白酶抑制剂
2011年2种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蛋白酶抑制剂Telaprevir和Boceprevir上市。近几年源源不断的DAAs新药临床研究结果的公布并陆续上市,为丙肝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23]。总体而言,DAAs适应更广,疗效更佳,不良反应更少,丙肝治疗前景充满希望。DAAs与干扰素/利巴韦林的三联疗法改写了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格局,2014年全球就发布的4个HCV诊疗指南,其中3个指南中都有涉及DAA的治疗方案[24-27]。Boceprevir联合干扰素、利巴韦林治疗,可使基因1型初治患者的SVR从40%提高至70%,经治复发患者的SVR可提高至75%,无应答患者的SVR可从40%提高至52%[28]。但目前还缺少这类药物应用于肾移植后患者的数据,其可能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尚需更深入的研究。
8 小 结
肾移植术后HCV感染的治疗一直是临床上的棘手问题。一般认为,患者手术后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标准的抗HCV方法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因此移植后的抗病毒治疗存在争议。无论单用干扰素、利巴韦林,还是干扰素/利巴韦林联合治疗,其疗效及安全性均不理想。随着新型抗病毒药物的使用,肾移植术后HCV感染的治疗前景充满希望。但新的抗病毒方案、治疗时机还需多中心、大规模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也需要临床医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