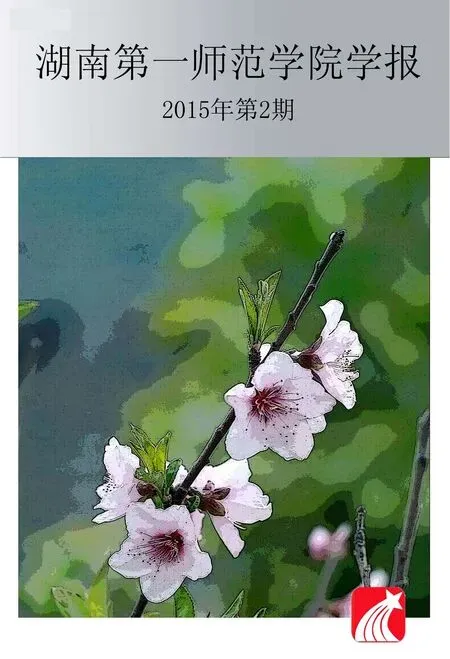土地与语言:生态文学双重本体论
2015-03-27陈彩林
陈彩林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土地与语言:生态文学双重本体论
陈彩林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生态”与“文学”的遇合,凸显出人的生态本质与语言本质,旨在构建以生命意识为主导的社会公共性话语。中国三十多年生态文学创作还存在着深层生态伦理矛盾、价值观混沌与审美性缺陷。这种情状尤需要立足中国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复杂性,对生态文学作出本体论的澄明,使之在人类生存与文学创作上担负起引领性,成为真正的生命艺术。
生态文学;生态本质;语言本质;生命艺术
文学是时代的表征,面对新时期以来纷呈的中国文学现象,如果要问哪一种文学潮流以极强的批判精神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以建构生命意识贯注的话语场的启蒙方式试图唤醒现在与将来的人共同关注与营造生命韵律更为和谐的生态整体系统,最终使“诗意栖居”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就会以自我救赎的心态将目光聚焦于生态文学。这一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兴起于欧美的文学潮流,迟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中国出现。生态文学在欧美兴起、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本身不仅表明二者现代化进程的先后,而且还显示出人类总体性现代转型与发展中所遭遇的共同性问题——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引发生态焦虑,生态焦虑催生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深度反思着高速现代化之中的人类生存,从而“为中西交流、在全球化语境下建立真正的社会公共性话语开辟了渠道”[1]。整体审视中国三十多年的生态文学创作历程,中国作家凸显出了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与生态忧患意识,以文学的方式将现代性发展所加剧的生态危机表现得触目惊心,助推了国人环保意识、绿色生活意识等生态主义生存理念的孕育与提升,但是创作中的深层生态伦理矛盾、价值观混沌与美学建构缺陷也显露出其思想穿透力与艺术感染力的局限。生态文学能否产生经得住历史与时代检验的经典性作品,我以为还需要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对生态文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再思考。其实,生态文学这一逐渐获得世界认同的历史性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双重本体论:一,从生态文学表现的对象——“生态”这一角度讲,生态文学显示出人类生存由“万物的尺度”向生态系统整体观转向的宇宙人生本体论;二,从生态文学表现的方式——“文学”这一角度讲,生态文学显示出“意识形态充盈物”(ideological impletion)的语言本体论。“生态”与“文学”的遇合,既显示出人的生态本质与语言本质,也显示出文学的生命关怀本质与审美艺术本质。因此,生态文学所示现的乃是人类生存与文学创作的双重本体自觉,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在更高发展阶段为人类开辟崭新的生存之路。那么,生态文学能否在人类生存与文学创作上担负起这种引领性呢?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本体论的审视与澄明,使之成为真正的生命艺术。
一、从顺承到动态的宇宙人生本体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三十多年的生态文学创作显示出两个方面的总体性内容:一是生态自然环境极度恶化的忧患,比如徐刚的《沉沦的国土》、麦天枢的《问苍茫大地》、乔迈的《中国:水危机》、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沙青的《皇皇都城》、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王治安的《悲壮的森林》、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等。二是自然生命世界的美妙与神性,比如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银狐》、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张炜的《刺猬歌》、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周晓枫的《鸟群》等。当然,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很多作品是二者的并行与交织,比如哲夫的《天猎》、陈应松的《猎人峰》、李存葆的《大河遗梦》、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等。这两个方面的总体性内容都归向于从生态系统整体主义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欧美生态文学》的作者王诺“在对古往今来生态思想作较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在对诸多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作细致分析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生态学者的观点”[2]所界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那样,“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3]。从文学具体内容层面对生态文学做出较为明确的界定是必要的,因为概念的泛化对于文学目标的实现并无助益。但是,仅仅从形而下的层面对于具体内容做出界定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观照才可能使生态文学创作获得坚实的文化支撑。事实上,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与永恒性是以丰厚的文化含量为洪炉大冶铸就的。更何况,不管是触目惊心地展示生态危机的可怖,还是美妙奇特地展示自然生命世界的和谐共生,其终极目的乃是为了以文学形象可感的方式促使人类自身重建崭新的生命本体,构筑起人类现代生存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总体审视中国生态文学,以上两个层面的创作在人类生存意识上试图确立的实质是宇宙人生本体论。
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净空大师的答案是:“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与诸多生命个体生存于天地之间这是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在中华文明的源头之处,我们的先人在《易经·彖传》中就对天与地之于生命的孕育满怀圣意与激情的礼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简言之,生命万物是借助天与地而产生的,正如冰心在《繁星》中的温情表达:“我们都是自然地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因此,在我们的母体文化之中就一直延续着祭拜天地的传统。宇宙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最切己的基本事实莫过于“顶天立地”。如果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让我们对宇宙充满敬畏的话,那么“无地难成家”、“土,食之本也”更让我们对宇宙充满了感激。对于中华民族个体而言,安土重迁是生之传统,叶落归根是死之夙愿,故土是一个饱含着家国情怀的词语。因此,在中国这个包含着两千余年封建史的农业国度里,土地意识是极为强烈的。土地意识实质是我们从切己的生存之本出发满怀敬畏与感激的宇宙意识、生命意识。“土地,社神也。村巷处处奉之”,这绵延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的风俗绝不能仅仅以封建迷信蔑视,它所再现的乃是我们的先人与天地宇宙之间的顺承关系,效法天地正是中华民族培育本体精神最本源的方式,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此,天地宇宙充满神性的时代绝不能与封建迷信时代划等号,前者实质是从生命本源、生存根本的基点对于宇宙的敬畏与感激,后者实质是统治者借助神权牧民的帝王之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从文化本源上讲实则是中华民族最原初的宇宙人生意识与生存实践。人顺承天地,敬畏与感激宇宙孕育生命万物的神性,取向于同天地自然之间的和谐,正是神性时代宇宙人生最基本的特质。事实上,在几千年的传统时代里,这种顺承天地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本体论在现实生存之中是具有极强自律性的。面对灾难的降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会检讨自身违背天意的失德之处。因此,这种宇宙人生本体论所取向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4]。这种“四合”的个体便是传统神性时代的生存典范,是曰“大人”、“君子”。事实上,中国生态文学从文化底蕴上来讲依然显露出这种“四合”宇宙人生本体论的理想取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为了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之下解放出来,五四新文学以历史主义的姿态以西方人文主义为精神资源以图实现人的解放,极力突显个体存在的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主体社会意识形态使然,中国进入一个人定胜天的激情高涨的无神论时代。人同自然之间的传统“四合”顺承关系也转变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极端状态无过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人的主观意志被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人的经济意识被全面激活。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与物质需求的高度期待与满足,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呈几何级递增。江河枯竭,鱼虾鸟兽被过度捕杀,水土空气污染严重,森林被过度砍伐,草原沙化严重,农药化肥激素过度催生农业,土地资源被高速城镇化吞噬,沙尘暴、雾霾肆虐,等等。诸如此类的严重生态危机迫使国人重新思考发展模式与生存理念。生态文明、和谐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突出主题。国人不仅关注自然生态,而且还关注精神生态,生态整体主义时代正显示出一种历史性归向。
虽然生态文明时代展露出了历史的曙光,但是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取向于生态整体主义并不是要退回顺承自然的原始农耕时代,退回到前工业技术时代,毕竟现代性发展势不可挡也是一种客观事实。由于中国发展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有很多地方至今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还是关照人类自身的人道主义问题,生态主义对于他们而言还是一种奢望。而且,从民族复兴大业来讲,继续推进中国现代性发展依然是百年来乃至二十一世纪社会进程的主线。这本身也是中国生态文学作家难以化解的生态伦理矛盾,一方面他们满怀忧患高扬生态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负效应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边远偏寂但生态又相对保存完好区域人的艰难生存满怀着人道主义的悲悯;一方面现代性发展还需强力推进,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又成为时代必然。这种生态伦理矛盾并存于胡发云《老海失踪》等生态文学作品之中。胡发云在《老海失踪》中一方面借老海之口对现代科技与人类贪婪批判到极端,甚至宣称“路是人类向大自然吸血的管道”,另一方面又借地委书记老朝之口提出在山地农民温饱无着的贫困状态之下乌猴保护的意义又在哪里的疑问。如果生态文学作家回避了现实生存矛盾,为了凸显生态主义,一味将目光投向深山、密林、雪域、高原等天然生态之地,甚至不惜过度使用神秘叙事策略极力渲染自然生命世界美妙奇特的神性,而内在心理中实际已经对现代工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关闭了大门,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边地生存体验的现代人与城市人来说,这种文学书写无异于猎奇,而猎奇性质的文学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因此,生态文学作家必须首先确证出更为科学合理、更为成熟的生存本体论。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的创作实绩在很大程度上所确证的依然是传统神性时代顺承的宇宙人生本体论。的确,这种顺承的宇宙人生本体论包含着现代人可资借鉴的宝贵的生态主义思想,体现了独特的东方文明智慧与诗性生存理念,但是其间也存留着绝对理想化的成分。或者说,在现代性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情形之下,我们面对生存矛盾更需探究的乃是如何将传统顺承的宇宙人生本体论与现代性发展相融合,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构建出适合历史发展大势的动态的宇宙人生本体论。所谓更高的发展阶段突出体现在现代科技与生态在更高层面结合,现代城市文明在更高层面实现生态和谐。因此,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生态文学所要承担的实质是民族生存本体论重建的文化任务,一方面要撷取出传统顺承的宇宙人生本体论中具有永恒性的部分,以文学形象可感的方式促使国人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系统整体主义转化,将宇宙人生本体论树立为鲜明的主体生存意识;另一方面又要以更为包容的心态、更为实际的眼光、更为前瞻的意识将宇宙人生本体论构建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足以让现代人与城市人接纳的更具时代科学意识的动态的宇宙人生本体论,而非生态文学前文本中存在的那种近乎退回蒙昧与神秘幽玄的自说自话。
二、生命意识充盈的语言本体论
王诺等学者从以卡森为代表的欧美生态文学创作中得出的启示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存在的主要价值是应对生态危机,是批判反生态的思想文化和生存发展方式,是介入生态危机和生态保护现实,唤起民众的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5]事实上,从中国三十多年的生态文学创作来看,其主要价值也大致如此,原因是“其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既不是作家、批评家的求新冲动,也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的推动,而是生态危机的现实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灾难的巨大压力”。[6]生态文学存在的主要价值与兴起、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了其自身是一种现实性、介入性极强的文学形态。2009年8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干脆亮明会议的主旨就是“酝酿一场新启蒙运动”,启蒙的核心便是生态主义。既然是启蒙,自然包含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这样看来生态文学又是一种对话性极强的文学形态,而对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启生态主义之蒙。当我们从生态文学的鲜明针对对话性这一层面来审视的时候,生态文学是极为契合话语理论的。
话语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巴赫金、福柯等为代表的话语理论之前,语言学理论是以索绪尔为主导的。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重心在于语言的共时性静态情境,忽略的是语言的历时性动态因素(语言的社会、历史、交往等因素)。他将语言的结构形式置于决定性支配地位,而非话语内容。虽然索绪尔对语言结构形式的研究为人类语言现象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但是他对语言内容的忽略则为话语理论留下了巨大研究空间。话语理论的形成首先归功于巴赫金。他从文学切入来研究交往和对话并建构他的话语理论。他的话语研究揭示的是人类生存、历史发展、社会运转的一种普遍存在方式,揭示出语言的交往与对话本质,而且他还深入到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突出了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支配作用,即语言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充盈物”的存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开启了西方话语研究的思维闸门后,后继者络绎不绝,福柯堪称大师。福柯从话语视角切入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建构了话语权力理论。在福柯看来,掌握了话语也就掌握了权力,也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去规划真理面目,去决定历史的取舍,去破坏生态或灭绝物种,话语实质构成的是层层叠叠的权力网。因此,不管是巴赫金还是福柯,其话语理论都极为重视历史、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制约和影响,重视话语对历史、社会的反制约和反影响。这样,话语既然是由历史决定的,且它又能“表述”历史、铺陈历史和制约历史,它就必然成为“意识形态充盈物”[7]。
生态文学不仅显示出了其由伴生于现代性发展的生态危机催生的历史本来面目,也显示出了作家以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表述这一历史本来面目与反影响、反制约这一历史危机的启蒙意图,还显示出了其作为“意识形态充盈物”的本来面目。具体地说,中国生态文学试图借助话语场力实现由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高扬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变,由人的文学向生命的文学转变。从这一角度来说,生态文学所凸显的乃是其作为生命意识充盈物的语言本体论的本来面目。或者说,生态文学立足语言本体论试图以生命意识的充盈来建构社会公共性话语。中国三十多年的生态文学创作显然有效助推了环保意识、绿色意识、人与自然和谐意识等生命意识充盈的社会公共性话语的建立。
从人与宇宙的“四合”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再到生态整体主义意识,从神性时代到无神论中心时代再到生态文明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最深刻的话语变革,这也是最伟大的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而生态文学试图走在这场话语变革、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前沿。虽然中国生态文学在三十多年创作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实绩,但是前文本中所包含的生命意识充盈的语言本体论则是可贵的,因为以此指引有助于在全球化语境下真正建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社会公共性话语。
三、生态文学怎样成为真正的生命艺术?
生态文学的宇宙人生本体论标示出人的生态本质,即人在本性上作为自然物的存在,而非技术构建物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回归自然是本性的需要。既然人类离不开自然,宇宙人生在人的本性上实则是一种天然的存在,而自然宇宙又是一个生态整体系统,即人绝不是唯一具有内在生命价值的存在物。因此,将宇宙人生本体论确立为生态文学的核心意识显示出人性宇宙的真正拓展与深邃,使“悯人”与“悲天”获得双重体现,一种善待众生、更为博大的自利利他的生命意识。生态文学的语言本体论标示出人的语言本质,即彰显语言之于人类存在的本体意义,以生态主义与生命意识的贯注重构消解生态危机、更新人类生存与发展模式的社会公共性话语。生态文学的双重本体论表明这一文学潮流既是一场人类生存意识的变革,也同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公共性话语变革,即生态文学作为生命意识充盈物的本来面目。但是,生态文学的最终归属是文学,文学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我们既要考虑它的“意味”也要考虑它的“形式”。具体地说,文学的内容是具有形式感的内容,文学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黑格尔语),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因此,生态文学要成为真正的生命艺术就必须对其独特的生命意识与审美特性做出澄明。
从中国三十多年生态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生态文学的思想性还必须进一步辨明,因为前文本还存在着价值观的混沌。一方面生态文学作家满怀生态焦虑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高速现代性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对于人类生存古典诗意的吞噬,对于自然生命世界和谐状态的摧毁,试图还原自然生命世界的自在性,激活人们原初的自然神性感,但是对于神性的理解存在着盲点。自然神性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上可追溯至远古先民无物不神的泛神意识,近可追溯至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对于人的异化的自我救赎。也就是说,生态文学重新呼唤自然神性的立足点是高度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我们必须关注从传统神性时代经由现代性发展时代而至重新呼唤自然神性的生态文明时代这一历史性。如果为了纠正现代性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而不加区分的将神秘文化作为自我救赎的法宝,那么就会消解人类自身可贵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事实上,生态文学前文本就存在过度神秘叙事的问题,对于狼、蛇、狐、异人等的书写“神气”弥漫而非“神性”彰显。神性的本质是为了凸显人类生存的诗意,即个体身与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然之间更为和谐的自在性,而不是退回到先民原始思维的桎梏。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并不是排斥百年中国现代化所崇尚的科学与理性,而是为了消除现代化进程中因为人欲的膨胀与不节制的物质追求造成的生态危机,以更为科学理性的精神善待自然、善待生命,在生态文明这一更高发展阶段享受科学理性的福祉,担承科学理性的生态伦理责任,实现自利利他的宇宙人生。另一方面生态文学作家面对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生态整体主义,但是对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盲点。生态文学前文本存在着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绝对化的倾向,素不知彻底泯灭了人对自然改造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否定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也就否定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事实上,生态文学取向的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发展更高阶段的标志。这一更高发展阶段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而非退守到前工业文明时代。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不仅代表了一个高度科学理性的发展时代,而且还代表了一个人性善良因素不断拓展的时代。自然伦理的立论不是以绝对的自然万物平等观消解人文精神,而是人将道德关怀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对于自然予以良知的尊重。[8]也就说,自然伦理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升华,人格的进一步完善。比如姜戎《狼图腾》中所极力推崇的“丛林道德”就显示出自身对于自然伦理的混沌。作品将狼维护草原平衡的生态作用推向极端,最终作品价值观走向了人类社会对于弱肉强食的狼性哲学的运用,拜狼为祖,将嗜血的动物拜为中华图腾,以至于只见“生态”而不见“文明”,模糊了文明这一划分人与动物的底线。显然,生态文学绝不是将人折向动物的大回转,丛林哲学绝不是人类生存的福音,更不是令人敬畏的自然神性,自然神性本质是人性诗意与灵光的折射,没有人性善良因素的拓展、人格的不断完善、人的日趋解放,自然道德、生态伦理就无所依傍。为此,生态文学惟有去除价值观的混沌才能成为为人类开辟崭新生存之路的真正的生命艺术。
从中国三十多年生态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生态文学的艺术性也必须进一步提升,因为前文本还存在着现实干预性有余而审美性匮乏的问题,中国生态文学作家还缺乏较强的将客观的生态美提升为艺术美的审美转换能力。生态文学的落脚点是文学,要成为真正的生命艺术当然要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文学源于生活,而生活对于作家不是浮泛的,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进入文学,它必须是深入到作家灵魂深处与意识边际的生命体验,这对于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尤为切要,否则,就会流于失去鲜活生命感的干瘪与枯燥,而这正是文学的致命伤。换句话说,只有深入到灵魂深处与意识边际的生命体验才能根柢性地切入宇宙本源、世界本质与生命本真,才能作出独特的生命观照,因为文学将这种真切的生命感直笼其中,最本质地还原了这种精神性的氛围,使之弥漫周遭,与人生即会。因此,仅仅在生态文学作品中展示生态危机,传播生态思想,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至今还缺乏生动记录渺小生物的《昆虫记》、《瓦尔登湖》式的大型生态作品。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家对于这样的生命世界与自然世界缺乏深切的生命体验。只有创作主体的心灵与审美对象的生命价值融合无间,自身生命世界与审美对象生命世界和谐交融,超越了自身的生命局限,超越了万物为我所用的狭隘与自私,从而获得了真切的宇宙人生体验,才能在具体创作中将客观的生态世界转换成审美的艺术世界。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先平的《黑麂的呼唤》、周晓枫的《斑纹——兽皮上的地图》等作品于此展示了可贵的探索。这也是很多生态文学作家本身就是野地探险家、科研人员、博物学家等多重身份的原因。对于生态文学作家而言,不仅要对人性宇宙有深邃的探索,而且还要对另外一个“他者”的生命世界有身体力行的体验,要真正理解自然。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的文学魅力更为深层、更具本质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带给读者以绵绵无尽的、极致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哲学体味,即波兰美学家英伽登所说的伟大作品需要具有的“形而上质”,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状态”。也就说,对于自身(人类世界)与他者(自然世界)真切的生命体验与丰厚的生命积淀是客观生态美转换为艺术美的关键,这也同时是艺术美动人生命力量的源泉。
在生态危机依然充斥的情势下,生态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被赋予鲜明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复杂现实背景下,这种现实意义要真正得以实现,从本体论视域澄明生态文学的文学本原、存在方式与文学本质就更为必要,因为这种澄明有助于生态文学在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上穿越混沌走向真正的生命艺术。正如生态文学的创作主体与研究主体是人一样,生态文明的构建主体也只能是人,只是此“人”更需要以清醒自觉的宇宙情怀、大地意识守住包含自己在内的自然生命世界的诗意与灵光,而作为语言艺术的生态文学正是为了建构这样一个具有本体意味的人类诗意栖居的“存在之家”。
[1]姜桂华.生态文学大有可为[N].人民日报,2004-06-29.
[2]姜桂华.《欧美生态文学》读后[N].光明日报,2004-06 -23.
[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金永.周易译解[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8.
[5]王诺,封惠子.从表现到介入[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6]田中阳.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7]雷鸣,李晓彩.中国生态文学亟须走出价值观的混沌[N].河北日报,2010-03-12.
[8]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Land and Language:The Dual Ontology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CHEN Cai-l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Arts,Yulin Normal University,Yulin,Guangxi 537000)
The fusion of ecology and literature shows the ecological essence of people and the language essence of human being.This is to build the social public discourse that is dominat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There have been still the deep contradic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the values of chaos and the aesthetic defects in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s creation in the past more than 30 years,so we must clarify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ntology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soci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complexity to make it become the art of life to lead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the ecological essence;the language essence;the art of life
I206.7
A
1674-831X(2015)02-0083-06
[责任编辑:胡伟]
2014-11-20
陈彩林(1973-),男,湖北襄阳人,文学博士,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