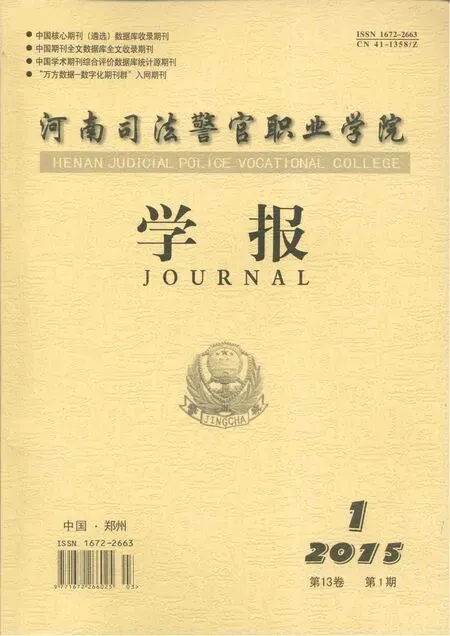论“亲亲相隐”的法律性质
2015-03-26罗强
罗 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450046)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近年来,学术界就此制度的现代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澄清了一些认知,揭示了一些价值,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亲亲相隐”是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假如它是一项权利,那么它是隐私权还是豁免权,是拒证权还是亲属权,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以抛砖引玉。
一、权利还是义务
“亲亲相隐”究竟是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这涉及我们对这一法律制度在性质上的基本定位。遍览诸家学说,大多数人倾向于将这一制度理解为一项“授权性”规范或原则。依据这一原则,相应的法律主体拥有容隐特定对象犯罪行为的权利。故而,很多学者将“亲亲相隐”简化等同于所谓的“容隐权”。即使置于程序法的语境中来讨论“亲亲相隐”制度,很多人也都倾向于将其归纳为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拒证权”。无论如何,这种权利说的确有很大的合理性。从“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源头以及随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制度也的确是以赋予尊亲属以某种特殊权利资格为初始目的的。然而,权利和义务实在是一体之两面,有时候,我们对于某种法律现象的定位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视角。
中国式“亲亲相隐”制度的根基和背景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宗法家庭制度,这一宏大背景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差序格局”,而整个国家的礼法制度就是服务于这种格局、为维持这一格局而存在的。因此,所谓的容隐行为,以这种“差序格局”为背景来看,就具有两个最基本的指向:一个是由上到下,另一个是由下到上。前者是尊亲属容隐卑亲属,后者是卑亲属容隐尊亲属。那么,既然这样一整套制度都是服务于这个差序格局的,“上隐下”就是名正言顺的权利,而“下隐上”则是理所应当的义务了。
“上隐下”的权利性,表现得十分明显,也不存在本质性的争议,那么,作为义务如何呢?
事实上,“下隐上”的义务性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随着时间推移才慢慢明显起来的。早期的“亲亲相隐”制度局限在近亲属之间,随着历史的发展,才开始慢慢产生亲属之外的主体间容隐,比如《宋刑统》即规定了雇佣工人和奴婢对主人的容隐义务。作为定位于差序格局底层的佣人和奴婢来讲,容隐显然就不是一项可以放弃的权利,反而成了一项必须做到的义务了。
“亲亲相隐”的义务属性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判断。正如有时我们判定某项权利之为权利,可以从它是否能够放弃来看一样,判定一项义务是否为一项义务,也可以从它被违反是否能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来分析。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记载,早在秦代,法律中即已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1〕这一规定中非常明白地讲到,“下”违反了容隐义务,反而告“上”,必定会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即被追究刑事责任。除了秦律,有学者研究认为:“自唐至清的刑律均规定:告越亲近的尊亲属罪越重、告越亲近的卑亲属罪越轻。这种规定表明,从卑对尊来说,为近亲属容隐的义务重于为远亲属容隐的义务,从尊对卑来说,为远亲属容隐的义务重于为近亲属容隐的义务。”〔2〕这一研究结果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亲亲相隐”作为义务性的强弱与法律主体在亲属等级结构中的地位有着直接关系,而同时,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性又决定了,义务性的强弱一定伴随着对应主体权利性强弱的变化。
由此可见,容隐行为究竟是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端赖我们分析的角度和方向。仅就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而言,对于在上的尊亲属而言,容隐是一项权利,而对于身处差序格局对应下位的卑亲属或者其余社会底层的人而言,容隐尊长则是一项法律义务。
二、隐私权还是豁免权
在我国学者对“亲亲相隐”这一制度的讨论中,学者刘水静和邓晓芒之间的论争颇为引人瞩目。先是邓晓芒教授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提出,“亲亲相隐”的法律本质是一种隐私权。针对这一观点,刘水静博士提出“亲亲相隐”实质上应当是一种豁免权,而非隐私权。〔3〕
对于隐私权说,笔者认为此说过于狭隘。诚然,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的确规定了夫妻之间在作证时,有权拒绝提供仅限于夫妻间了解的个人信息。例如美国的《1999年统一证据规则》第五条规定:配偶之间的秘密交谈和婚内交谈可以不批露。这一特殊证据规则的上位原则是英美证据法上的特权规则。“在普通法上,享有特权的交往又称为法律上特许不予泄露的内情,共有7种基本的类型,即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不作对配偶不利的证言的特权;维护夫妻关系信任的特权;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特权;心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特权;牧师与信徒之间的特权;为提供情报者身份保密的特权。”〔4〕然而,作为证据法上拒绝作证或拒绝披露相关信息的特殊证据规则,仅仅是“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或部分内容而已,以此来概括整个“亲亲相隐”的法律属性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相比之下,此论争的另外一方观点,即豁免权说则更为可取。具体来说,“亲亲相隐”的核心是当事人的容隐行为,而容隐的对象则是违反了国家刑事法律的犯罪行为。这种容隐行为常常以容留、包庇、协助或不与司法机关合作为表现。依据刑法的一般性规定,这样的行为本身也是违反法律甚至构成犯罪的。但是,出于人性化司法等更高位阶法律原则的考量,我们免除这一行为本身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甚至完全不将其视为犯罪行为。这样的做法是法律制度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刑法学界通常称其为“去罪化”,有的学者称其为豁免权,而无论称谓如何,这一特殊制度规定的本质其实就是“合法化”(justification)。这里笔者所谓的“合法化”就是指某一行为本身单纯地看不符合法律规定,甚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可是参考该行为做出的背景和原因等因素,我们会依据一些高位原则(往往是“自然法”)来“去除”该行为的违法性质,进而使其“变为”合法。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和这里所讨论的“亲亲相隐”制度无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因此,将“亲亲相隐”归结为一种豁免权,也是相较隐私权说来讲更为贴切和合适的。
三、拒证权还是亲属权
2012年我国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可以视为学界多年来研究、呼吁的结果。同时,围绕这一规定,大多数学者将“亲亲相隐”归结为程序法上的“拒证权”。
任何法律规定只有通过司法化进而落到实处才有意义和价值。“亲亲相隐”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容隐行为最终都会呈现出在国家机关追诉犯罪行为时的某种态度和立场。这种态度和立场,具体观察,又往往是在举证环节中才出现。因而,各国立法也常常将“亲亲相隐”具体化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证明问题来加以规定。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2条第1款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5〕类似的规定在不少国家的诉讼法中都能见到,前述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也采纳了这一规则。
无疑,从程序法的角度将“亲亲相隐”定位为所谓的“拒证权”是合理的。但笔者认为,跳出程序法的局限,从实体法的视角来审视“亲亲相隐”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观点。例如俞荣根教授就撰文指出,从亲属权的视角来看“亲亲相隐”也许才更有助于我们领会这一古老制度的精神本质。〔6〕
民法上的亲属权是以家庭关系为背景的一种民事权利,其内容往往包含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大方面。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较,亲属权更偏重于人身权性质,强调主体的身份属性。同时,亲属权自身虽然名义上为权利,但义务性也很突出,是法律上权利与义务合体的典型之一。这些特点恰好都与“亲亲相隐”相契合。“亲亲相隐”顾名思义,强调的是亲属之间基于家庭身份关系而享有的某项权利或义务,虽然后来在主体方面有所扩展,并不绝对局限在法定亲属范围内,但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像这一制度最初产生的时候一样,建立在亲属或如同亲属一般的某种身份、感情基础之上的。这种法律之外的伦理情感因素在这一制度的运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如前所述,“亲亲相隐”本身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这一点也完全与亲属权的特点相吻合。因此,从亲属权的角度来理解“亲亲相隐”也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亲亲相隐”并不是一项单一的、简单的制度,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多面体。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看似不同的结论实质上又并不矛盾,它们都可以统一在“亲亲相隐”这一制度标题之下。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某一法律现象的定位或归类,往往是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和语境;从司法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又告诉我们,“亲亲相隐”是贯穿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我们对它的理解倘若失于片面,就难免会导致偏差。
〔1〕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95-196.
〔2〕路保钧.“亲亲相隐”孰之权利〔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2).
〔3〕刘水静.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J〕.学海,2012(2).
〔4〕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M〕.卞建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2.
〔5〕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李昌珂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10.
〔6〕俞荣根,蒋海松.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J〕.现代法学,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