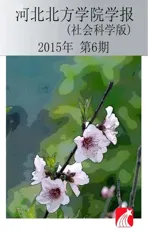浅论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兼评王玉雷案
2015-03-26刘矾
刘 译 矾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2)
浅论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
——兼评王玉雷案
刘 译 矾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从王玉雷案中可见,在检察环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检察官落实客观义务、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以及公诉权引导侦查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制度下,基于检察机关冲突的角色定位、公检之间错位的关系、检察机关“权责不一致”以及检察官缺乏客观义务的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尚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落实。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促进非法证据排除在检察环节得到更好的落实。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检察环节;王玉雷案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130.1123.044.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30 11:23
继最高法出台《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两个规定”)后,2013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正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在中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明确指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于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和审判这一整个程序之中,它的贯彻落实将对于消解侵犯人权违法取证,减少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保障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此次刑诉法修改中,检察功能得到全面强化的检察机关拥有侦查监督权、公诉权以及广泛的法律监督权,且作为唯一一个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参与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对该规则的落实无疑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4年2月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的王玉雷案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该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引导公安机关抓获真凶,使得险些成为翻版的呼格吉勒图案(下称“呼格案”)的王玉雷案得到了纠正。此案发生之后,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方面,王玉雷案得到了最高检以及社会的高度评价,认为其充分地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中依法履职,严格把关,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坚守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1];但另一方面,从该案办案人员反映出来的信息也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基于立法等多方面的原因,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还存在相当多的障碍与困难,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得到充分的落实。基于此,笔者以王玉雷案为例,在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检察环节落实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之上,结合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贯彻落实的障碍以及成因,并为解决上述障碍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得到更加彻底的落实,使其更好地发挥“保障人权,防范冤错案件”的重要使命。
一、翻版的“呼格案”
实证研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笔者以案例入手,首先对不久前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的王玉雷案件作简要的介绍,并将其与“呼格案”进行比较,从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作用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一)王玉雷案简介
2014年2月18日晚上近22时,王玉雷和李强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躺在地上,身旁有血迹,似乎已经死亡,便拨打“110”报案。后保定市顺平县公安局经侦查认定,受害人是王玉雷同村村民王伟,疑被他人用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公安机关经过侦查认为,报案人王玉雷有作案时间,并在侦查过程中存在撒谎行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2014年3月8日,公安机关对王玉雷作出刑事拘留。2014年3月15日,因被怀疑杀害同村村民王伟,王玉雷被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顺平县检察院在审查案卷材料,并经2014年3月18日和2014年3月19日两次提讯后发现,王玉雷疑似被冤,原因是王玉雷案的口供和物证均存有疑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显示,对王玉雷的询问和讯问笔录共有9次,前5次均为无罪供述,后4次为有罪供述。同时在有罪供述中,王玉雷对作案工具有斧子、锤子和刨锛3种不同供述,但其供述的3种工具均不能与尸体照片上显示的致命伤口呈‘U’形相吻合。同时,检察机关在讯问王玉雷时发现,王玉雷右臂打着石膏缠着绷带,起初王对其伤口的成因支支吾吾,后在检察人员开导之下,王玉雷嚎啕大哭直言“被打了”。2014年3月21日,保定市两级检察院就王玉雷案进行专题研究,认为应当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2014年3月22日,顺平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对王玉雷案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不捕理由说明书》《补充侦查提纲》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随即对王玉雷变更强制措施。2014年7月1日,王玉雷被无罪释放。2014年7月7日,公安机关将杀害王伟的犯罪嫌疑人王斌提请逮捕。2015年1月17日,保定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王玉雷案与“呼格案”之对比
社会舆论将王玉雷案视为翻版的“呼格案”,是因为王玉雷案与“呼格案”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第一,从案情来看,凶杀案都发生在晚上,向警方报案的人都是两个人,被警方怀疑的犯罪嫌疑人也都是最初的报案人之一;第二,从案件现有的证据来看,案发现场都没有遗留太多的物证或其他证据,在查获真凶之前,警方都没有对其中某些关键性的物证做必要的调查与鉴定,例如,在“呼格案”中,警方在被害人体内提取了凶手的精斑,但却没有将其与呼格吉勒图的精液进行对比;在王玉雷案中,警方在现场收集到了疑似凶手留下的手套,但没有对手套中可能存在的有价值的微量物质进行鉴定,更没有将其与王玉雷比对;第三,从案件的非法程序来看,在两个案件中,警方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且都获得了有罪供述,最终警方也都将该口供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虽然王玉雷案与“呼格案”在客观条件上存在上述的相似之处,但最终王玉雷案还是幸运地没有成为翻版的“呼格案”,王玉雷本人也没有成为冤屈的“替死鬼”,他的正义并没有来得那么迟。是什么使得两个案情相似的案子最后呈现出如此不同的结局,又是什么让原本走偏了的诉讼程序重新回到正轨上来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王玉雷案与“呼格案”的本质区别所在:第一,在定罪证据方面,检察机关遵守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没有忽视口供所述的作案工具与伤口形状不吻合的矛盾;第二,在非法程序方面,检察机关根据现有的线索没有忽视刑讯逼供存在的可能性,在犯罪嫌疑人没有主动向其告知的情况下,通过循循善诱,证实了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行为的存在,并果断地排除了由刑讯所获得的“有罪”供述,切实地贯彻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在对侦查行为的引导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纠正警方非法程序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同时,在侦查方向上向警方提出了“对案发现场遗留的手套进行鉴定”的补充侦查的建议,引导警方顺利地查找案件的真凶,使“真凶者入罪,无辜者出罪”。
二、非法证据排除在检察环节落实的意义
如上文所述,王玉雷案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机关得到良好落实的典范,从这个个案中可见,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对于防范冤假错案有着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其对于落实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实施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实现公诉权引导侦查权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检察官落实客观义务的必然要求
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源于对检察官法律守护人角色的定位。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指出,“检察官应当担当法律守护人之光荣使命,追诉犯法者,保护受压迫者,并援助一切受国家照料之人民”[2]22-23。到目前为止,尽管国内外法学界对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涵与外延尚未有十分准确的界定,但是陈卫东基于中国检察官客观义务产生根源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认为中国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容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对客观真实与法律公正的全方面追求”[3],这也就意味着检察官虽然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控诉权,但其在刑事诉讼中并不能完全以实现成功定罪与胜诉为主要的目标。检察官在行使控诉权的同时,要履行“证据客观”等实体上的和“逮捕审查”、“法律救济”与“正当程序维护”等程序上的多种义务。而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检察官在落实实体上和程序上客观义务的必然要求。
第一,从实体上来看,通过违法侦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诸如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辞证据以及通过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在证据属性方面,其客观性与真实性都存在很大的缺陷,运用这些证据所证明的案件本身也就存在极大的虚假性,这显然与检察官客观义务所追求的实体上的“证据客观”存在冲突,若将其流入法庭,将严重影响案件真实的发现,损害司法正义。同时,相比于法官的被动裁判,检察机关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能够更早更直接地接触到可能存在的非法证据,也能够更主动地纠正违法的侦查行为,排除非法证据,更好地实现实体上的客观义务。
第二,从程序上看,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利的保护是检察官客观义务之“诉讼关照义务”的应有之义,而当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受到损害之时,对其进行救济也是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必然要求。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在手段上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救济,对其进行物质上的补偿是一方面,为了从源头上或者根本上杜绝或者预防刑讯逼供这一已成惯性的违法侦查行为,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就应当排除该违法侦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使其实现不了法律上的价值,这也许更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从而实现检察官正当法律程序这一客观义务的要求。
(二)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必然结果
中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权以及审判权的监督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基础。
第一,从对侦查权的监督来看,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任务是通过行使侦查权,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在案件由侦查阶段进入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在审查这些证据材料是否合法、是否具有可采性以及是否为非法证据需要排除在事实认定的范围之外时,就必然会考虑获取证据材料的侦查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换句话说,检察机关对于证据材料进行判断,认定其证据能力或证明力的过程,就是对侦查行为本身进行监督的过程。
第二,从对审判权的监督来看,检察机关在庭审之前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外,有助于从客观上解决中国因庭审模式的设置而造成的法官易受非法证据不当影响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庭审模式是由案件审理者同时对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决的一元法庭庭审模式,且不存在类似国外的预审法官或者中间程序,如果将非法证据流入法庭,即使其最后被成功排除,也难以避免法官会受到该非法证据的不良导向或者干扰。因此,如果检察机关能够在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就将非法证据尽早地排除,就会减少非法证据进入法庭的机会,从而更好地避免法庭受到非法证据的干扰。
(三)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公诉权引导侦查权的必然路径
公诉权与侦查权在本质上都属于刑事追诉权,在中国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所享有,两者在功能指向以及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有效的控诉。但两者在具体的分工上存在不同,检察官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原告”出庭公诉,履行指控犯罪的职责;公安机关则是在庭前通过行使侦查权为检察官出庭公诉准备必要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侦查是为公诉服务,是为有效的公诉做准备”[4]。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关系先互相独立,再相互配合,这也就意味着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并非天然地能够满足检察机关的控诉需要[5]。侦查中的违法行为所产生的非法证据不仅无法帮助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占据诉讼优势的地位,实现有效的控诉,还在无形中增加了检察机关“要证明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巨大压力,如若无法完成证明责任,就很有可能陷入诉讼不利的地位,难以实现有效的刑事追诉。而在审前阶段,检察机关使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参与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是要“过滤”掉这些在法庭上可能会起到相反作用的证据,纠正公安机关错误的侦查方向或者手段,引导其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朝着成功起诉的方向收集证据,最终通过合法的证据构建确实充分的证明体系,实现刑事追诉的目标。
三、检察环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
自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法律条文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在2014年10月29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作《关于人民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从2013年初至报告日,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证据决定不批捕750人、不起诉257人。”[6]由此可见,检察机关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确实是将一部分不符合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排除在刑事程序的范围之外。但是在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并非“畅通无阻”和“一帆风顺”,与检察机关2013年-2014年决定批捕与起诉的案件数量相比,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决定不批捕和不起诉的案件数量简直是九牛一毛,这并非得益于中国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规范的侦查行为和高质量的证据链条,而是因为已经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得到有效充分的落实。在很多案件中,检察官对于需要立即排除的非法证据并没有直接排除,而是简单权衡案件的追诉可能性和警察违法的严重程度,在功利主义的计算中,只有当警方的违法程度十分严重且无法补正时,才会排除该非法证据;“大量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都是通过补正或者要求公安机关开具说明的方式,及时地将非法证据合法化。”[7]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检察机关想排除非法证据,他们也会因为来自被害人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而不敢排除。王玉雷案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检察日报对此有相关的描述——“3月21日,是王玉雷案进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期限的倒数第二天。是否做出逮捕决定,保定市、顺平县两级检察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为此,保定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彭少勇召集保定市、顺平县检察院业务骨干,就王玉雷案进行专题研究……有人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该不批捕;有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王玉雷作案嫌疑,应该批捕,否则将面临被害人家属上访等……”[7]从这一段描述中不难发现,即使检察机关在有证据证明有非法证据存在的情况下,也还是不敢理直气壮地适用规则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他们要专门为此进行专题研究,进行一系列的利益衡量和风险评估,承担巨大的压力。值得欣喜的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顺平县检察院最后还是作出了不批捕的决定。与其说是排除非法证据“拯救”了王玉雷,还不如说是检察机关的魄力与担当“拯救”了王玉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已经被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不能得到有效充分落实呢?
(一)检察官缺乏客观义务理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落实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检察官在执行司法活动中缺乏人文关怀和责任伦理意识,缺乏客观义务理念。一方面,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刑事诉讼理念的大背景下,以程序上的瑕疵获得实体上的胜利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到现在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有罪推定”的理念在检察官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仍然根深蒂固,“无罪推定”的理念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或者移交起诉的案件,在检察机关看来,批准逮捕或者提起公诉往往是正常的作法,就像是在王玉雷案件中,即使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刑讯逼供获取非法证据的违法侦查行为,即使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物证存在重大的矛盾,仍然有人持批捕意见,原因在于“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王玉雷作案嫌疑”。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批准逮捕只需要该犯罪嫌疑人有嫌疑即可,而不批准逮捕却要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罪,这显然是将“入罪”与“出罪”的证明标准颠倒了过来,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想。
(二)检察机关的角色冲突
根据《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国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多种角色,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在中国的宪法体系下,检察机关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行使进行无部门利益的法律监督;同时,检察机关在中国又享有检察权,依法履行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的职责;在自侦案件中,检察机关还享有侦查权。基于这些不同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身兼数职”,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第一,当检察机关自身在行使侦查权时,检察机关既是办案机关又是监督机关,而众所周知,用违法的不规范的手段常常是更有利于办案。在追求侦查效益的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侦查行为的时候,就会出现检察机关内部互相监督的情况,“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正义难以实现。第二,检察机关本身是控诉机关,需要依靠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来支持指控,打击犯罪。在当下仍以有效的控诉率作为检察机关绩效考核的标准,以成功的支持公诉作为衡量检察官能力的重要指标的制度背景下,由检察机关去监督违法侦查取证行为,排除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可能会敷衍了事。综上,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角色的冲突主要是由这些角色所追求的不同的司法价值所导致的,而在行使侦查监督权与追诉权时,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大的理念环境下,也会毫无疑问地偏重对后者的落实与强调。
(三)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错位关系
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起检警一体化的体制模式,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行使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引导作用,而这种引导也多为一种事后的建议,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在中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实践中,“相互配合”多于“相互制约”,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侦查监督部门发现了公安机关有侵犯人权和违法取证的行为,但受机关利益的考虑,也不会或者很难启动非法证据排除来对该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因为在目前的绩效考核以及错案追究机制之下,一旦案件进入刑事程序轨道,执法司法人员就有利益的考虑,如果退出程序,则意味着否定前期或前一机关的行为及其成果,轻者影响了前期或前一机关的业绩考核,重者甚至有关主体可能就会承担错案责任。因而,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手段的纠错机制很难启动。另外在中国公检法3机关中,公安机关虽为侦查机关,但其有十分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检察机关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排除公安机关收集的非法证据更是难上加难。
(四)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手段缺乏明确授权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就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纠正方式与手段予以了规定,其指出,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由此可见,首先,在内容上,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应当调查核实,但是对如何进行调查核实,即调查核实的具体手段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与授权;检察机关从发现可能存在非法证据的线索到具体将其确定为非法证据,这个过程也并不是随意的,也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检察机关在对非法证据调查方面缺乏执行力,由此所导致的权责不统一也会进一步使检察机关缺乏积极主动调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意愿[8];其次,在形式上,法律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但这一“意见”在法律属性上也仅为建设性的,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效果。所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当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遭到违法侦查行为的侵犯时,如若其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而检察机关却无法对公安机关施以有法律影响力的处理行为,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的权利难以实现!
四、完善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措施
如上文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落实中存在的障碍源于检察机关自身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错位关系以及检察机关权责不统一等原因,而这些原因又与中国现存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模式紧密结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要想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建立或者修改某一项或某几项制度就能完成,而必须要对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公检法3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分配等深层次的问题予以考虑与设计,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关键问题,避免“治标不治本”的尴尬局面。基于此,下文简要提出以下几点改革建议,以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得到更好落实有所裨益。
(一)建立客观义务之理念,落实程序正义价值
检察官应尽早建立履行客观义务的理念,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在思想上摆脱“大控方”的角色意识,淡化自身的追诉色彩,“以司法官的立场而非控方立场来看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并以客观公正义务来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9]。同时,在绩效考核方面,应当取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单纯的以“实体正义——逮捕率和成功追诉率”为标准的考核指标体系,积极关注通过刑事公诉而展现的程序正义的价值,并将之落实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不以实现实体上的正义为最终目标。
(二)理顺检察机关的职能,优化职权配置
第一,在检察机关的内部职能配置方面:一方面,应在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调查违法侦查行为的手段和权力,真正做到“权责相一致”,同时,也应当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部门的独立性,使其尽可能少的受自身侦查权以及控诉权行使的影响;另一方面,提高检察机关内部的公诉部门与侦查监督部门的对接机制,在非法证据的线索发现方面加强沟通,提高非法证据排除的准确性和效率,不断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第二,在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关系方面,应尽快建立“检警一体化”的诉讼模式,改变检察机关滞后的监督方式,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在侦查权行使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取证领域的指挥作用,提高公安机关的取证质量与办案水平。
第三,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尽早在中国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检察机关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控辩双方的充分质证与认证才可以作为最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解决中国目前虚化的庭审,给检察机关在审前积极调查违法侦查行为并排除非法证据施加压力。
(三)赋予辩方有效的排除申请权,加强外部监督
刑事诉讼立法应赋予辩方有效的申诉救济权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权,这也就意味着检察机关不仅可依职权排除非法证据,也可依辩方的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当辩方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申请时,检察机关必须对该申请作出回应。如果检察机关未对辩方的申请作出回应,一方面,辩方可以向检察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诉,要求救济;另一方面,当案件由检察机关移交法院时,辩方也有权要求法院在庭前首先就该非法证据是否应当排除作出程序性的裁决。
近些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因非法证据而被错误认定的冤假错案接连发生,这些冤错案件在一次次考验公众心理承受能力极限的同时,也在严重地挑战法律与正义的底线,当很多公众开始对中国的刑事司法产生质疑甚至有所失望的时候,被社会高度关注的河北王玉雷案无疑又点燃了社会公众对中国刑事司法的希望。王玉雷案一方面反映了在检察环节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尽早预防冤错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现阶段基于各种原因,在中国检察环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一些障碍。在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中国应当尽早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理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多重角色,加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转变检察官“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促进其尽快建立客观义务的理念。
参考文献:
[1]周宵鹏.保定检察机关排除案情疑点预防错案[N].人民日报,2015-01-20(8).
[2]林钰雄.检察官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陈卫东.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立法评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3):33-34.
[4]林钰雄.检察官在诉讼法上之任务与义务[J].法令月刊,1998,(10):8-10.
[5]刘计划.检警一体化模式再解读[J].法学研究,2013,(6):150-151.
[6]徐盈雁.纠正王玉雷冤错案:排除非法证据引导抓获真凶[N].检察日报,2015-02-13(2).
[7]林喜芳.论我国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基于刑诉法修改与实践语境的分析[J].当代法学,2013,(6):86-95.
[8]王志勇.论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2):190-144.
[9]张健升,万毅,易延友,等.检察机关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职责要求与机制建设[J].人民检察,2014,(7):41-48.
(责任编辑治丹丹)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Procuratorial Proceeding
—Comment on the Case of WANG Yu-lei
LIU Yi-fan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Analyzing the case of WangYu-lei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the procuratorial proceed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prosecutors’ objective obligation,implement the legal supervision and guide the investigation.But in China’s current judicial system,because of the prosecutors’ conflicting rol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urator and the police,procurators’“inconsistent responsibilities”and their lack of the concept about objective obligations,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has not yet been implemented fully and effectively in the procuratorical proceeding.Aiming at the problem,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Key words: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procuratorical proceeding;case of WANG Yu-lei
中图分类号:D 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5)06-0029-06
作者简介:刘译矾(1991-),女,湖北襄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收稿日期:2015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