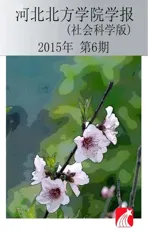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以江苏“4·22”特大交通事故案为例
2015-03-26唐治
唐 治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
——以江苏“4·22”特大交通事故案为例
唐治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化确有必要,但由于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多元化的,为充分保护法益又兼顾罪刑法定原则,有必要将吸毒驾驶规定为危险驾驶罪的第三种行为方式,以起到两个效果:一方面,使得危险驾驶罪的法益得到最全面的保护;另一方面,使得吸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入罪明文化,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可对中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危险驾驶罪作以下修正:“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吸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立法完善;吸毒驾驶;罪刑法定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130.1123.050.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30 11:23
自四川省成都市发生的孙伟铭醉酒驾驶案尘埃落定以后,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两种社会危险性极大的行为定为犯罪。然而,法条对于危险驾驶的类型存在描述上的缺陷,这意味着有必要全面研究危险驾驶的类型,对于法条提出修正意见并予论证,以更有效地指导司法实践,在危险驾驶罪的刑事领域实现司法公正。
一、完善危险驾驶罪立法的思考与建议
在全面研究危险驾驶的类型之前,应先回到对该罪的立法探讨上来。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入罪提供了法律上依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上规定了危险驾驶罪,这是从罪刑法定的角度,明确危险驾驶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使得“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担忧不复出现。
罪刑法定原则最初由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予以规定,目的是为了限制英国国王的权力,以犯罪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角度,将保障人权和防止犯罪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而起到“没有法律就没有处罚,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1]29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现使刑法领域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化与规范化,也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得以彻底保证。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有: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明文化、法不溯及既往、禁止绝对刑和不定期刑等。当然,日本有学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还包括禁止不公正的刑罚等,但罪刑法定原则中对于保证公民自由不受非法追究的机能是其核心与关键所在。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如果《刑法》不保护法益,就丧失了基本正当性。其实,中国《刑法》与德、日《刑法》具备共同性,都以保护法益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技术构建[2]。中国《刑法》分则的章节也都是根据法益的种类不同而作不同划分,在根本意义上都起到保护法益的积极作用。当然,中国刑法学通说将“社会关系”作为法益的另一种提法。笔者认为,这一点可以商榷。社会关系是一种模糊的弹性极大的提法,可以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适用,但不应在法学上适用。法学的目的是研究和解释法律及其背后的自然法,并不在于追求单纯的出入人罪。如果将单纯的出入人罪作为其价值构造,法学就不成其为科学,而完全成为惩罚人的工具。法学必须反映公平正义的效果。因此,在严谨的法学研究中,不适宜采用“社会关系”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必须回到法学的本质——自由的保障上来适用法益的概念。法益是德国学者毕伦巴姆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给犯罪的本质寻找一个确定和科学的概念。虽然法益的概念从被提出就经历了各种争论,但百年来由于德国及日本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法益的概念大抵可以确定为“刑法所保护的法律利益”。中国刑法学通说承袭前苏联,在理念与技术上都比较偏向于政治导向,不具备德国与日本刑法学所具备的保障人权和保证自由的倾向。因此,以法益的概念取代社会关系概念,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转变的必然。罪刑法定原则旨在限定刑罚的发动,而法益似乎是为了启动刑罚,表面上看两者存在冲突,但从实质上看两者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法益也是为了限定刑罚。如果没有法益概念,仅以抽象的概念则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比如,将领导人的个人喜好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这会不可逆转地造成公民人权被肆意侵害而不受制约。可见,从法益角度来界定危险驾驶行为非常有必要性,也可以使危险驾驶罪建立在罪刑法定的坚实基础上,为良法之治取得较大的可能性。
(一)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法益根据
危险驾驶罪的保护法益是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和重要财产安全。这是一种很重大的法益。
首先,人的生命是异常宝贵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可逆转,值得成为最重大的法益,由刑法予以保护。中国《刑法》对于人的生命权的保护不遗余力,更是开门见山地将人的生命权作为其保护法益。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中国《刑法》的专利和特色。但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对象并不是行为人自己,此处存在一个自然法原理:任何人只要不侵害他人利益,都有自由行动的自由。因此,行为人自杀的,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然,自杀的定义需要明确界定。中国学者王钢在其论文中提出了自杀的明确定义,在论述中排除了过失自杀这一概念,认为自杀必须是出于故意。当然,就危险驾驶罪而言,也呈现出一种对于人的生命权保护的立法态度。同时,生命权法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人。一般而言,无论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还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都会危及道路上人的生命权法益[3]。醉酒驾驶机动车法益侵害性和社会危险性很大,值得动用刑罚予以处罚。法益主体的不特定化往往是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理由之一。刑法理论中,犯罪可以分为实害犯与危险犯、行为犯与结果犯两对范畴。实害犯是指行为对法益造成确实的侵害犯罪,比如故意杀人罪;危险犯是指行为对法益具备危险即应处罚的犯罪,比如放火罪;行为犯是指行为本身侵害法益,无须结果发生即构成犯罪的犯罪,比如非法拘禁罪;结果犯是指行为本身无法直接侵害法益,结果发生才昭示法益被侵害,犯罪才得以成立的犯罪,比如诈骗罪。危险驾驶罪从定性而言,属于行为犯和危险犯;具体而言,属于抽象危险犯,这更决定了应将其在《刑法》中入罪。
其次,人的身体权同样属于重大法益。人的身体是生命的载体,一旦受到侵害,不仅受害人痛苦万分,其亲属和朋友也会受到精神上的伤害。因此,刑法不可不对其加以保护。中国《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便是以身体权作为保护法益的典型犯罪。危险驾驶行为中,追逐竞驶行为对道路上交通参与者的危害极大,如果行为人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车祸,使得交通参与者的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汽车越来越成为居家必备之物,不再固守其奢侈品的地位,这造成道路上的机动车越来越密集。行为人在道路上追逐竞驶,一旦对不特定人的身体权造成伤害,还容易进一步导致其身体伤害演变为死亡,被侵害的法益从身体权演变为生命权。醉酒驾驶机动车更是“马路杀手”的行为,根据有关统计,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的车祸比一般行为造成的车祸更多。所以,中国立法者依据当前形势,将“醉驾”设立为犯罪,可以说是针对现实在立法上作出的无奈反映。
最后,重要财产安全也是一种很重大的法益类型。财产是公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本。中国《刑法》将重要财产安全作为保护对象,表达了立法者的态度:财产的保护不容小觑。刑法分则也设立了不少保护重要财产的犯罪。比如,盗窃罪、抢劫罪和侵占罪,都旨在保护财产法益。那么,危险驾驶罪同样可以危及道路上不特定人的财产法益。例如,行为人在朋友家喝酒之后,驾车出门,在道路上将被害人停在马路边上的进口汽车撞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无疑,但其行为给被害人的重要财产造成损失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重要财产”,必须加一个设定:数额为1 000元以上。中国盗窃罪规定了“数额较大”,这说明,数额可以作为客观处罚条件来限定刑罚权的行使。数额较大也可以借鉴性地作为危险驾驶罪中对重要财产的限定。这种限定表明了立法者将最后手段性原则作为刑法解释的原则之一,最后手段性原则又称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法益保护原则的一个重要限制。对重要财产作数额较大的限定,可谓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得以运用的一个必要规制。
(二)危险驾驶行为的主要类型
中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分为“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然而,从法益角度而言,上述两种类型并不完整合理。
首先,危险驾驶罪的保护法益是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和重要财产安全,其被侵害的方式是多样化的[4]。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是常见的典型的危险驾驶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吸毒驾驶、疲劳驾驶和超速驾驶等各种行为。吸毒的人驾驶机动车,极可能因无法良好操控机动车而发生交通事故,从而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及重要财产安全。疲劳驾驶与吸毒驾驶一样可以导致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及重要财产安全被侵害。超速驾驶也是一种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容易导致车祸的行为。行为人一旦超速驾驶,其车速得不到迅速控制,遇有紧急情况时会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也具备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危险驾驶罪的保护法益——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及重要财产安全被侵害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仅为《刑法》规定的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方式。
其次,危险驾驶罪的保护法益决定了多样化行为方式必须体现在立法中。立法上一旦确定了某种犯罪就不可轻易更改,否则会造成人民群众在法律面前因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然而,某种犯罪如果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缺漏,就无法充分全面保护法益[5]。法益保护是一种重大的立场,绝对不能被颠覆。因此,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必须因法益被侵害方式的多样化而变得多元,不能保持单一而不改变。那么,有必要讨论的是,由于法条必须具备简略性,不可能将所有的行为方式事无巨细地规定在法条上——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是否可以用“等”的方式,来概括法条所无法完全描述与覆盖的行为方式呢?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其下有一条子原则:明确性原则。这是指法律条文在用语上必须明确具体,不能抽象模糊,否则,“法将不法”,罪刑法定原则将被违背与架空。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是法治在刑法领域的表现[6]。因此,即便《刑法》对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规定有遗漏,也不能为了追求填补法律漏洞,而使用“等”来起到兜底条款的作用。
最后,吸毒驾驶应该成为危险驾驶罪的第三种行为方式。虽然前文论述了危险驾驶的行为方式不仅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还有吸毒驾驶、疲劳驾驶及超速驾驶[7]。然而,这3种行为方式的危险性是存在区别的。其中,吸毒驾驶的危险性最大。详言之,疲劳驾驶和超速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概率并不一定很大。事实上,经常出现一种情况:行为人疲劳驾驶和超速驾驶也没有导致交通事故,不会侵害危险驾驶罪的保护法益——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及重要财产安全。因此,忽略危险性较小的疲劳驾驶和超速驾驶行为,转由《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其他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来制裁,是比较妥当和合理的处理方式。根据相关统计,吸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的概率非常大,这是将其明文入罪化的最大的根据,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刑法修正案(八)》在中国《刑法》分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确立危险驾驶罪是有必要的,但由于危险驾驶罪的法益——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和重要财产安全被侵害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吸毒驾驶也是一种常见且极其容易引发法益受到侵害的行为方式,从充分保护法益又兼顾罪刑法定原则之子原则——法律的明确性原则的立场,有必要将吸毒驾驶规定为危险驾驶罪的第三种行为方式,以起到两个效果:一方面,使得危险驾驶罪的法益得到最全面的保护;另一方面,使得吸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明文化,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由于立法是法得以形成的尤其重要的途径[8]79,故笔者特提出修正中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建议:“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吸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二、江苏“4·22”特大交通事故案再解析
提出修正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建议之后,有必要重归司法实践,以个案检验的角度,来验证笔者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否具备充分的理论价值与实务意义。
(一)案情与判决
2012年4月22日,江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案情如下:
被告人王某于2012年4月22日上午,在吸食毒品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情况下,驾驶沪BL1290大客车(车上乘客32人)从上海市人民广场出发前往常熟市尚湖风景区。上午9时许,车辆行至常合高速公路(S38)1 km+180 m(常熟境内原沿江高速段)附近时,因操作失当致车辆偏驶撞击中央隔离栏后进入对向车道,与在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刘亚东驾驶的苏ED1655中型厢式货车相撞,致刘亚东、吕加明及徐良栋等14人死亡,刘伟良、严洪强及周开清等19人不同程度受伤,后被民警查获。
被告人王某于2012年4月23日0时50分,经胶体金法检测甲基苯丙胺,结果呈阳性。经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高速五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王某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全部死者近亲属及部分伤者已得到经济赔偿。
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某在案发时患有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但该精神异常系因吸食毒品引发,故对王某在本案中的刑事责任能力不予评定。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14人死亡和19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情节特别恶劣,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正确,予以采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一百和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9]。
(二)分析
法院对该案行为人王某吸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定性,笔者大致是赞同的。王某的行为确实构成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从而发生重大的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中国《刑法》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比较粗略,这是由法条的精简性决定的。然而,司法解释实质上起到细化法律甚至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虽然学界对于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必须适用司法解释。这意味着司法解释事实上起着法律的作用。那么,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就必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王某吸毒后驾驶机动车,明显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造成了14人死亡和19人受伤的后果,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完全具备了司法解释中对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从此意义上来看,上述行为人的毒驾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是无疑的。
然而,法院对于王某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予评定,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刑法学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刑事责任能力作为主体要件,在定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10]78。在德国与日本3阶层犯罪论体系中,刑事责任能力是有责性(又称罪责)阶层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讨论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不能忽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探讨。这里涉及3个问题:第一,王某是否具备刑事能力?这应由法官结合司法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分析王某是否具备辨认和控制其行为的能力。司法鉴定中心已经给出结论,王某具备精神障碍,但法官并不据此分析王某是否由于精神障碍而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和控制其行为的能力,即刑事责任能力,这是一个极大的漏洞甚至错误。第二,如果王某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是否应根据原因自由行为进行讨论。原因自由行为是为了解决当行为人的罪责与行为不同在时,是否应该处罚其行为?一般认为,必须坚持罪责与行为同在原则。所以,必须提出一个学说来论证行为人在实行行为时具备罪责。根据工具理论,由于行为人在原因行为时,将失去罪责的状态作为利用的工具,相当于间接正犯的构造,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11]236。那么,即便王某丧失刑事责任能力,但因其在吸毒时应预料到可能导致精神障碍的后果,以及应预料到精神障碍后可能导致车祸,但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预见后轻信能避免,是过失性原因自由行为,视为在交通肇事时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据此,根据罪责与行为同在的原则[11]313,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三,如果王某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也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应减轻刑罚。根据刑法学理论中的基本原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罪责大为降低,应该减轻刑罚,方为公平。当然,用前述原因自由行为的论证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由于行为人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是由其先前的过失型原因自由行为导致的,视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不应减轻处罚。无论如何,法院不对王某的精神状态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更不从原因自由行为的角度进行说理,在笔者看来,是一种遗憾与漏洞,也导致了对王某的行为没有科学公正的评价。
三、对于讨论意见的回应
在该案的讨论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王某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7]。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是错误的。王某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中国《刑法》中一个较有特色的罪名。为了充分保护公共安全——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及重要财产安全,立法者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罚不能以其他犯罪论处但危害了公共安全的行为[9]。根据《刑法》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方式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可说明以下几点:
首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属于兜底条款,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并未具体明确地规定危险方法究竟有哪些类型,这与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发生冲突[12]435。事实上,中国《刑法》在1997年修改之前,有不少模糊的罪名受到学界的诟病与质疑,比如流氓罪。诸如此类模糊的罪名在《刑法》修改之后依旧存在,体现了中国立法者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视不够,试图以模糊抽象的立法用语涵盖所有的社会危害性行为。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将行为人的方法认定为危险方法存在难度。危险方法既然在法条中无从展现,司法实践工作者就不能直观与直接地找到认定依据,转而依靠各自的审判经验与生活经验,甚至根据学者的观点来认定行为人是否采用了危险方法。其弊端为:一方面,无法发挥立法对于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造成定性时各方观点各自为阵甚至观点“打架”局面,混乱法律秩序的统一性。
再次,危险方法必须同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危险性相当。虽然立法者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是危险方法,但从法条的规定来看,危险方法位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说明立法者认为危险方法的危险性必须类似于前述方法,否则,将危险性不如前述方法的行为认定为危险方法,将造成不证入罪,会扩大刑罚范围,也架空了立法者在危险方法之前列举各种典型的危险方法的初衷[13]211。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能是故意犯,亦即行为人在使用危险方法时,明知其行为可能导致侵害法益的结果,但希望或者放任这一结果发生。过失则不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中,王某造成重大事故的原因是操作不当,这说明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据此,王某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王某的行为固然构成交通肇事罪,但问题是,假设王某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比如,只造成一个人重伤,就会面临一个尴尬情况:对王某的行为无法定罪。因为王某没有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而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这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将吸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增设为危险驾驶罪的第三种类型,极其具备现实针对性、紧迫性与必要性。司法实践中千奇百怪的行为造成了抽象的刑法条文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显得捉襟见肘。然而,保护法益的立场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明确性原则决定了法律漏洞必须得到填补。认识到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存在缺漏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将是对于法律修改启动的呼唤。承认立法漏洞、倡导法律修正、坚决保护法益及明确法律用语,是此文对危险驾驶罪进行考察与论证后,作出的一个结论兼呼吁。
参考文献:
[1]周光权.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
[2]李瑞生.论危险驾驶罪的价值及其完善[J].河北法学,2012,(12):145.
[3]赵秉志,赵远.危险驾驶罪研析与思考[J].政治与法律,2011,(8):15.
[4]王志祥,敦宁.危险驾驶罪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7):49-56.
[5]李波.当前我国危险驾驶罪考察与批判[J].犯罪研究,2012,(1):25.
[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钟君.危险驾驶罪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5):34-35.
[8]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9]北大法学信息网.王某某交通肇事案——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定罪与处罚[EB/OL].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displaycontent.asp?gid=121004466.2013-12-12/2015-01-22.
[10]柏浪涛.刑法攻略(讲义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11]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3]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治丹丹)
Legislative Perfec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Taking the Extraordinarily Serious Traffic Accident of Jiangsu 4.22 as an Example
TANG Zhi
(Law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207,China)
Abstract: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onduct of dangerous driving to be a crime.But its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are diversified.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he principl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and the full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law,it is necessary to classify the driving behavior after taking drug into the third act of the dangerous driving,which can bring about two effects.On one hand,it can giv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to the law interests of dangerous driving;on the other hand,it determines the drug driving and sticks to the baselin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principle.The 133rd article of China’s Criminal Law can be modified as“Those on the roads who conduct the chase driving with wicked acts,or the drunk driving or the drug driving are given criminal detention and fined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dangerous driving;perfection of legislation;drug driving;legality
中图分类号:D 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5)06-0035-06
作者简介:唐治(1990-),女,四川富顺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刑法学。 张凯强(1990-),男,河北张家口人,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FX067)
收稿日期:20150509 2015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