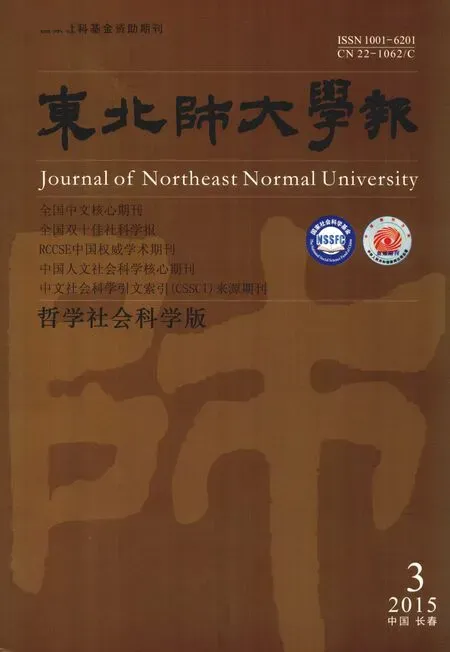父母法定继承顺位的立法论证
2015-03-22房绍坤
郑 倩,房绍坤,2
(1.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烟台大学 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父母法定继承顺位的立法论证
郑倩1,房绍坤1,2
(1.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烟台大学 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关于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我国《继承法》采取的是将其与配偶、子女均设置于第一顺位的立法模式。然而,世界普遍立法趋势是将父母设置于第二顺位。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不仅符合被继承人将遗产转移给自己的直系晚辈血亲、保留在家庭内部的主观意愿,且与作为规制法定继承顺序经济基础的当前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法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对民间继承习惯与社会伦理规则的顺应。
法定继承顺序;父母;被继承人意志;立法建议
在法定继承制度中,法定继承人的顺位因其不仅对继承人的利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更牵涉被继承人权益的维护和个人意志的尊重而成为最为重要的制度内容。自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颁布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时事的变迁为完善《继承法》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命题,并催促立法机关将修改《继承法》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事实上,目前我国学界对于修改法定继承顺序的争论已然颇多,且焦点之一即为父母的法定继承顺序。关于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我国《继承法》采取的是将其与配偶、子女均设置于第一顺位的立法模式。然而,世界普遍立法趋势是将父母设置于第二顺位。笔者认为,将父母与子女并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一定的弊端和滞后性,势必会降低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运行效率。本文就父母的法定继承顺位问题略述己见,以期为《继承法》的修改完善尽绵薄之力。
一、父母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的反思
对于我国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立法现状,理论界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我国法定继承顺序的修改,应集中在顺位的数量方面。考虑到继承制度应用的社会惯性,不宜对法定继承顺序做过于激烈的改动,除增加法定继承顺位的数量外,原立法规定包括父母的法定继承顺序可以保持不变*参见王利明(项目主持人):《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页;梁慧星(课题组主持人):《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徐国栋(项目主持人):《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杨立新、杨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21页;郭明瑞、房绍坤、关涛:《继承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将父母与子女同时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立法模式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应当参照各国相关立法通例,维持子女的法定继承顺序,将父母设置在第二顺位继承人*参见陈苇、冉启玉:《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2期,第55、56页;陈苇(项目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案建议稿》,载易继明主编:《私法》2013年第2卷,第12页;张玉敏:《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确定》,载《法学》2012年第8期,第16页。。
笔者认为,除法定继承顺序的层级数量外,法定继承人在各顺位中的排序对于法定继承制度的有效实施,甚至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权益的维护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忽视子女与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不合理性,以及重新部署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必要性,很有可能导致法定继承制度在实践应用的比拼中成为民间继承习惯的手下败将,削弱其应有的实践价值和法律的权威。
(一)父母法定继承第一顺位有违被继承人的主观意愿
从古至今,人们的普遍观念和意愿是将身后财产保留在家庭内部,造福子孙后代。将父母设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不仅降低了配偶与子女获得遗产的比例,而且父母从被继承人处继承的遗产还将成为父母遗产的一部分,待父母去世后被父母的其他子女、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即原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姑叔姨舅等旁系血亲继承,导致原被继承人的财产被稀释、流落到家庭外部,这显然彻底违背了被继承人的主观意愿。
事实上,除了遗嘱继承外,法定继承也应当强调对被继承人意志的尊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继承法律制度具有财产与身份双重属性。财产属性决定了继承法要确认并维护被继承人的财产所有权,肯定被继承人处置其身后财产的自由;身份属性则要求继承法承担一定的家庭职责,对被继承人自由意志加以限制。在萨维尼看来,无遗嘱继承(即法定继承)“主要建立于死者推定的、因而是默示的意图之上”[1]。换言之,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都旨在尊重与维护被继承人处分自己遗产的意志,区别仅在于遗嘱继承是以清晰明了的方式体现被继承人的意志,而法定继承采取的是推定默认的方式。身为财产所有权人的被继承人,虽然不能自行决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但仍然享有捍卫自己处分意志的权利。父母不是被继承人不情愿给予的人,只是被继承人不情愿自己的财产通过父母遗留给旁系血亲,最情愿给予的人是自己晚辈血亲*直系血亲是指与自己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即生育自己或由自己生育的上下各代亲属。旁系血亲是指与自己同出一源、具有非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父母从被继承人处继承的遗产还将成为父母遗产的一部分,待父母去世后被父母的其他子女、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即原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姑叔姨舅等旁系血亲继承,导致原被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能够继承的遗产比例被稀释,原被继承人的财产流落到家庭外部,这显然彻底违背了被继承人的主观意愿。。如果法定继承制度适用的结果是被继承人的财产被遗留给旁系血亲,而不是直系晚辈血亲,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被继承人的意志。试想,一个人一生拼搏努力积攒的财富根据法律规定遗留给了自己极不情愿给予的人,而自己情愿给予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财富流到别人手中,那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二)父母法定继承第一顺位过分强化了继承的赡养功能
我国《继承法》关于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一直带有“死后赡养”的色彩,即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带有延续被继承人赡养义务的遗产*鉴于《继承法》制定期间,我国正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会财富较为贫瘠、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的社会大背景中,致使我国的继承制度除了具有捍卫公民合法权益、延续家庭功能的意义,还有“为了保证未成年的子女和需要赡养的老人以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者获得生活资料,从而减轻社会的负担”的功能。可见,在提供生活保障方面,继承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重合与一致性。学界对于继承发生的根据提出多种学说,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即为死后赡养说。该说认为,从家庭职能出发,被继承人生前对家庭负有扶助赡养义务,死后其留下的遗产仍应当用于扶助赡养家庭成员,以保障他们的生活。我国相关著述亦将死后赡养表述为养老育幼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参见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1页,第43页;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1-653页;张玉敏:《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确定》,载《法学》2012年第8期,第15-20页。。然而,继承与赡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父母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过度侧重于分担社会养老职责、履行赡养义务,这不仅混淆了赡养与继承的功能,更忽略与牺牲了被继承人对自己财产的主观意志和掌控权。虽然保障父母生活与权益的出发点具有正当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修改继承制度的属性与职能。况且,通过在《继承法》中规定子女与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来解决养老问题,原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因此,我们应当厘正继承与赡养之间的辩证关系,转变以分担社会养老压力决定父母法定继承顺序、过分强化赡养职能的错误观念。
二、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的正当性证成
综上可知,将父母规定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实际上是加重了继承的赡养功能,而忽视了被继承人的主观意志。为了实现尊重被继承人意志与保障父母权益的兼顾,笔者认为,较为合理且正当的解决方案是使父母的继承地位退居子女之后,成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
(一)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适应社会发展水平
马克思曾指出:“继承法最清楚地说明了法对于生产关系的依存性。”[2]继承制度的建设不仅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且这种决定性和依存性更加直接、密切。这既反映了现行《继承法》对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是受法律制定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产物,也意味着该规定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进行适当的改进。
首先,《继承法》孕育时期,社会物质财富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令人堪忧。当时人们的个人财产仍以供给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的生存资料为主,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比例较小,私人财富十分单一、匮乏,死后可供分配的遗产甚少。在子女死亡时,父母继承子女的遗产,充其量能够解决赡养问题,没有发生赡养之后的剩余财富于父母死亡时转由父母的其他子女,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的可能性,更不会发生本应由自己晚辈直系血亲继承的财富转由兄弟姐妹的晚辈直系血亲继承的问题。如此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立法者在规制继承问题尤其是法定继承顺序方面的问题时,没有将遗产分配顺序的合理性与归属价值最大化列入重点研究范围。
其次,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制度建设略显粗劣与生涩。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国家和国有企业为唯一的资金来源,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府与企业的财政收入并不丰腴,难以完全负担如此沉重的经济依赖。因此,极易导致社会保障制度陷入资金危机,无法实现正常运转。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很难妥善完成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任务,立法者在设计法定继承顺序时,将父母与子女均规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使父母的法定继承带有死后经济赡养的性质和社会保障的功能,以充分发挥家庭老有所养的社会职能,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功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上,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私人财富价值最大化。个人财产数量和结构的丰富,致使被继承人与继承人对待遗产分配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被继承人对自己身后财产去向的重视,以及继承人对遗产分配合理性的要求都更加强烈。
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也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自90年代中期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改革,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入了稳步上升的阶段。尤其是养老保险方面,不仅覆盖范围逐步扩大,而且保障力度也不断增强。在政策推动下不断改善的养老体制,意味着我国《继承法》分担社会保障养老职责的分量可以有所减轻。
总之,作为父母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的经济基础,如今已实现了跨越式的飞跃,加之被继承人财产和意志的保护与尊重逐渐成为当前主流的价值取向,只有将父母法定继承顺序合理调整至第二顺位,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水平,符合法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二)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符合民间继承习惯
萨维尼认为:“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形成的。”[3]法人类学家鲍哈那也提出“法是习惯的再制度化”、“法律不能改变习俗”的观点[4]。诚然,习惯,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获得公认的行为准则,并能被人们自觉遵守。因此,习惯可以被界定为“不仅最古老而且是最普遍的法律渊源”[5]。继承制度所具有的身份属性,使其与其他财产法相比承担了更厚重的家庭伦理责任,相应的受社会风俗伦理规则的影响也更为强烈。“法律的约束力来源于人们的同意。”[6]继承法律制度只有真实准确地反映民间的继承习惯与观念,才能妥善调整财产继承法律关系,满足公民维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的需求。然而,我国对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却与社会风俗伦理规则相悖。家产自上而下、在家族中代代相传一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遗产流转规律和传统,我国民间也始终延续着将遗产留给晚辈直系血亲的继承习惯。只有在晚辈直系血亲缺位的情况下,才由父母继承遗产。而我国《继承法》规定子女与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显然不符合民间继承习惯。因此,对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设计,有必要尊重和参考民间继承习惯。与之相违背,很容易导致该立法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瓶颈,难以实现既定的立法目的和司法效果。
(三)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顺应了世界立法趋势
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承接政治、文化、环境等多方位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在此背景下,法律全球化自然是在法律方面对这一世界性发展潮流的必然回应。法律全球化的典型表现之一,即世界各国和地域间的法律规范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趋同发展。各国国内法的构建和完善,逐渐超脱国界的局限,增添了国际间的互动与交流。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发展形态显然与法律全球化的氛围格格不入,更不符合现代法治建设的要求。中国作为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该主动投身于法律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尤其对于立法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法律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要涉及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关先进立法经验的参照与借鉴。
放眼当下,我国关于父母法定继承顺位的规定同样应该与世界接轨。现今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俄罗斯[7]、越南[8]等极少数国家规定父母与子女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9]、德国[10]、瑞士[11]、意大利[12]、葡萄牙[13]、奥地利[14]、日本[15]、韩国[16],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17],都普遍遵循子女第一顺序继承,父母位列第二顺序继承的立法模式。我国香港*参见《香港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3155/167858.shtml,2014年9月9日访问。、澳门、台湾地区*参见《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973条,http://www.law110.com/law/macao/law110200415002.html,2014年9月9日访问;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38条,高点法学研究中心主编:《民事法规》,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01页。亦不例外。可见,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已成为国际普遍认可的法定继承规则。将父母设置在法定继承第二顺位,不仅顺应了世界立法趋势,更体现了我们积极推进法律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态度和决心。
三、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的制度衔接
任何一个法律规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边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制度无不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废除旧有制度而建立顺应时代需求的新制度时,不对周边法律规则或制度进行配套梳理与和谐构建,那么新的制度将孤掌难鸣,难以奏效。这就要求我们在废除父母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确立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的同时,必须予以相关的制度衔接与梳理。
(一)父母养老制度的衔接
作为全球老年人口绝对值最大的国家,我国当前正面临着规模与程度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鉴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势必会有学者质疑,将父母设定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是否会不利于缓和极其严峻的养老形势,难以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针对这一质疑,笔者认为,将父母的法定继承顺位调整至第二顺位,绝对不等同于被继承人拒绝承担赡养义务或违背孝道,或者说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绝非以规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为目的,如果修正现行父母第一继承顺位的结果是摈弃了千年文明古国的传统美德,排出了被继承人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那么,这种修正就是失败的。为了确保父母老有所养,在确定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的同时,必须确立和明确相关的制度。
1.强化被继承人子女对被继承人父母的赡养义务
既然被继承人先于其父母死亡,其子女享有代位继承权,那么,被继承人死亡,其子女在有负担能力的情况下,应当向被继承人的父母尽赡养义务。即便被继承人的父母还有其他的子女承担赡养义务,也不能排除被继承人有负担能力的子女的赡养义务。我国《婚姻法》第28条对被继承人子女的此种赡养义务进行了规定*我国《婚姻法》第28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因此,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在被继承人子女有负担能力的情况下丝毫不会影响父母养老问题。
2.确立父母对被继承人房屋的居住权
居住权是否能实现法定化在我国理论界始终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赞成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王利明教授与徐国栋教授均在其著述的民法典草案中表示了对居住权的肯定,并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与阐述。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378页。而梁慧星先生则反对设立居住权,理由是《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规定居住权,是因为法国民法未实现男女平等,不承认夫妻之间相互的继承权;而我国已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实行了住宅商品化政策,废止了公房制度,这些条件瓦解了居住权存在的基础。参见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1245,2014年6月24日访问。。尤其是在我国《物权法》制定期间,居住权的法定化问题更是成为草案审议中颇受瞩目的焦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四审议稿第十五章专章对居住权进行了规定,但却在第五次审议后被删除了,最后《物权法》正式颁布的版本并没有包含对居住权的规定。。虽然,居住权以无现实适用的必要性为由没有在物权法中落实*立法者认为,居住权的适用面很窄,基于家庭关系的居住问题适用婚姻法有关抚养、赡养等规定,基于租赁关系的居住问题适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情形都不适用草案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而且,居住权大多发生在亲属朋友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可以通过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救济渠道加以解决。,但在父母法定继承第二顺位的情境之下,居住权却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事实上,居住权的产生与继承制度具备的养老育幼的职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古罗马进入共和时代,宗法社会日益蜕变为商业社会,古罗马身份继承原有的绝对地位也逐渐被财产继承取代。家父为了实现非必然继承人“生有所靠、老有所养”,即通过设立遗嘱的方式,将自己特定遗产的用益权或房屋的居住权赋予该继承人,于是,居住权便应运而生。
可见,针对父母法定继承的问题,利用居住权制度增强赡养职能的发挥并不是无稽之谈。于被继承人死亡之时,父母没有自己房屋用于居住的,对被继承人的房屋享有居住权,直至其死亡。居住权不同于所有权,以父母的生存为存在的条件,父母死亡,居住权消灭,不具有可继承性,不会像所有权一样由继承人继承。这种性质的不动产权利,一方面解决了父母老有所居问题,另一方面又使其子女顺利继承遗产,即在不影响被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权行使的情况下,确保了父母的赡养问题,从而避免了父母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房产之后,于父母死亡时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遗产的不利后果。在满足继承制度尊重被继承人意志的需求方面,这样的制度设计一定是被继承人内心意志最真实的表达。
3.确立遗产信托制度
为了解决父母对不动产的需求,可以设计居住权制度;而对于父母日常生活必要费用的需求,可以通过遗产信托制度予以实现。被继承人于其生前作为委托人,或者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作为委托人将被继承人财富一部分以赡养为目的交付给信托机构,与信托机构形成财产信托关系,父母为信托受益权人,信托机构作为信托人依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履行信托义务,将经营所得收益逐月向父母支付,以供赡养父母的必要开支。父母作为受益权人于信托人不履行义务时有向其主张支付费用的请求权,就行使受益权所得利益,父母享有所有权,可依其意志自由支配。父母死亡,其受益权消灭,信托关系终止,信托人将剩余款项交付给委托人或委托人的继承人。
[1]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与时间范围[M].李双元,张茂,吕国民,郑远民,程卫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20.
[3]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耿谈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39.
[4] [美]鲍哈那.法和战争[M].北京:自然历史出版社,1987:197.
[5] [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高鸿钧,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84.
[6]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9.
[7] 黄道秀.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全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5.
[8] 吴远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04.
[9] 罗结珍.法国民法典:上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71.
[10] 郑冲,贾红梅.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47.
[11] 殷生根,王燕.瑞士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7.
[12] 费安玲,等.意大利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45.
[13] 唐晓晴.葡萄牙民法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88.
[14] 周友军,杨垠红.奥地利普通民法典[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15.
[15] 陈国柱.日本民法典[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179.
[16] 金玉珍.韩国民法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7.
[17] 陈苇.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90-393.
The Legislative Demonstration of Parents’ Legal Inheritance Order
ZHENG Qian1,FANG Shao-kun1,2
(1.School of Law,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2.College of Law,Yantai University,Shandong Yantai 264005,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country’s law of succession,parents belong to the first inheritance order along with descendants and spouse,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wide trend,in which parents belong to the second order. Actually,in accordance with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al productivity,as well as the decedent’s will and the custom of inheritance,parents should indeed be the second order heir.
Legal Inheritance Order;Parents;the Decedent’s Will;Legislative Suggestion
2014-11-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FX080)。
郑倩(1987-),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房绍坤(1962-),男,辽宁康平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D923.5
A
1001-6201(2015)03-0031-05
[责任编辑:秦卫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