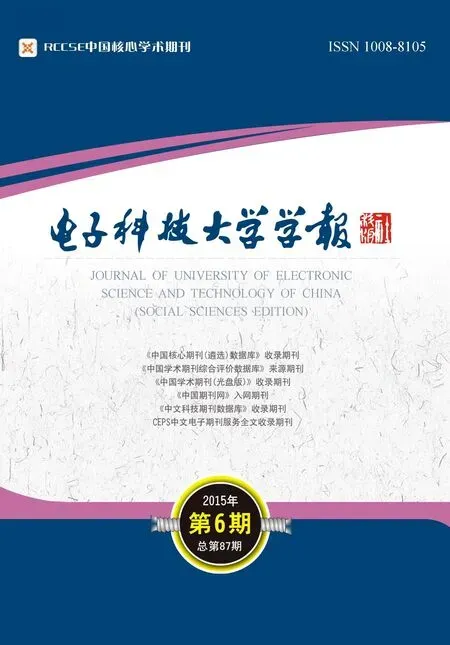纳兰容若与清代词体嬗变
2015-03-22郑亚芳
□郑亚芳
[泉州师范学院 泉州 362000]
纳兰容若与清代词体嬗变
□郑亚芳
[泉州师范学院 泉州 362000]
清词独特的成长环境使得词体呈现出蜕变的状态,表现为向婉约词风的本真回归,自我情感倾诉与婉丽词体的完美结合,哀感顽艳的审美追求,词体与诗体在内质上的吸收融合,在地位上的并驾齐驱,词派的纷繁与包容等。这一过程中,纳兰容若担负里程碑的使命,以他的创作诠释清词嬗变的过程与发展特质,成为这一时期的词体代言。
清词;词体嬗变;纳兰容若
一
词体发展到清代,摆脱了元明两代的沉寂,奋然勃兴,追步宋词,开始新一轮的成长与嬗变,出现众多创作活跃成就斐然的词人,进入中兴时期。
其间,纳兰容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直为同时代人和词学家们所鼎力推崇,况周颐说他是“国初第一词人”[1],王国维说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梁启超也认为“清代大词家固然很多,但头两把交椅,却被前后两位旗人——成容若、郑叔问占去也。”[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清代词人当从纳兰性德为始,词最有名,为清代词人之冠。”[3]作为词人,他是不可复制的,而作为清代词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身上凝结着一代词人的共性和追求,所以我们就以纳兰容若为例,探讨清词发展特性,以图达到以一斑窥全豹的目的。
关于纳兰容若,《清史稿·文苑(一)》中记载:“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4]
他的经历与词风的不协调,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探讨其词风成因的文章非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要做的是在词史中对他和他的词进行定位定性,勾勒出清词词体嬗变的时代特征。
清词的成长环境迥异于前代,不像宋词,契合统治者“多买歌儿舞女,旦夕饮酒相欢……”的号召,以一种娱乐自娱的状态存在。明清交接之际,汉族士人的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破国的彻骨之痛,亡家的泣血之感,交杂在士人的情感世界里,颤栗、惊悸、彷徨,百感丛生,身处新贵立国的狂喜,他们即使血泪交迸,也只能低头轻吟。在这样的环境里,清词肩负汉族士人痛苦吟唱的任务,词体需要以它的温柔婉媚安抚他们的魂灵。正如叶嘉莹先生在《清词丛论》中指出:
汉族士人在清初无可选择地接受了江山易代、满族入主中原的残酷事实。他们怀着故国之思与个人前途的考虑,带着耻辱、悔疚与惶恐的心理入仕于清王朝;这种复杂而辛酸的情感在词作中以极隐微的方式表达出来[5]。
就是因为明清易代,经过这样破国亡家的挫折和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适合于写入词;他们的词写得好,也就正是这种破国亡家的悲哀挫辱,才使得清词复兴的。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深层的美感,不能只从外表说[5]。
叶嘉莹先生充分认识到清词特殊的成长环境对清词复兴的影响。这样的环境促进词体某些特质的转变,词体功能由娱乐言情彻底转向抒情言志,负载词人心声志意的表达,衍生为“言志体”之词,进而成为众多文人士子首选的抒情托意的工具。至情至性的表达,往往会引起社会共鸣,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生性敏感多愁的纳兰容若虽不是汉族士人,但与汉族士人交往密切,同情他们的遭遇,深受他们情绪感染,他亦选择词体作为表达工具,倾注对人生,对情感的切身感受,表述的虽不是李煜的亡国之痛与李清照家破人亡之悲,但父子、君臣、家人、仕宦中难言之恩怨,一种貌似无来由的伤感和悲苦还是令他的词作颇具感染力。他的词中常常出现“飘零”一词,“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浣溪沙》)”“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临江仙·寄严荪友》)”,表现灵魂的漂泊无依,“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和迷茫,一种压抑的、轻声的、极尽委婉曲折的呐喊。而“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浣溪沙》)”,更是怅然哀婉、抑郁凄凉,这样的情调微妙地契合那个风云迥变的时代,契合很多汉族士子的情感体验,进而跟“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之时代气质相通。正如李泽厚所云:
这种由于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生空幻的时代感伤,甚至也可以出现在纳兰词里……其作品却是极其哀怨沉痛的……尽管富贵荣华,也难逃沉重的厌倦和空幻。这反映的不正是由于处在一个没有斗争、没有激情、没有前景的时代和社会里,处在一个表面繁荣平静实际开始颓唐没落的社会阶级命运中的哀伤么[6]?
同时代的其他词人的作品中也出现类似的情绪,如朱彝尊“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解佩令·自题词集》)”,王士禛“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浣溪沙·红桥》)”都表现出难以解释的悲观与感伤。
所以说,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社会悲剧意识,封建社会末世的大环境、大氛围影响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为清词的嬗变提供了迥异前代的土壤。纳兰词中的愁苦之音,就是时代情绪的折射,他的自我情感的抒发,契合时代期待与词体阅读追求,突显清代词体嬗变的时代性选择与表达趋势,激发人们的共鸣。这就是他能得到同时代人认可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二
清代词人对词本性的认知,倾向于向婉约的本色本体回归,倾向于对情性的体认和同情。如谢章铤评价王士祯的词说:“阮亭……半在《花间》,……且平日著作,体骨俱秀,故入词即常语浅语,亦自娓娓动听[7]。”严绳孙说彭孙遹的小词“啼香怨粉,怯月凄花,不减南唐风格[8]”。从观念到创作都将词视为一种婉曲之语表现内在情致的文体。可见,词发展到清代,作为清代众多文人士子表情达意的工具,被认可的是婉约艳丽善于言情之本色,“非情之近于词,乃词之善言情也。”[9]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依旧是“诗庄词媚”“要眇宜修”“诗言志,词言情”,以温柔精致的姿态,潜入人的内心,表达精微细腻柔婉之感受。
陈子龙《三子诗余序》云:
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嫷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10]。
在陈子龙看来,“纤刻之辞”“婉娈之趣”“妍绮之境”“流畅之调”是词体创作特有的本色表现,婉畅秾逸,超越温厚含蓄的规范,直接出于内心的不加矫饰之至情,他肯定的是南唐二主和北宋周、李的风格。
纳兰容若选择的亦是从花间、李煜而下,一直到北宋,一脉相承的婉约本色。同时代的词人清晰地指出之间的传承关系,并给以肯定的评价:
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11]。
陈词天才艳发,辞锋横溢,盖出入北宋欧苏诸大家。朱词高秀超诣,绮密精严,则又与南宋白石诸家为近。而先生之词,则真《花间》也[4]。
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调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乎[4]。
尤喜为词,自唐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本。……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4]。
从这些评价,我们可解读出评论者对此种词风的推崇与肯定,也可以看出时风所向。
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纳兰容若做出自己的评价:“《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4]词人追求的是“烟水迷离之致”的韵味,他对李后主的肯定,对南渡诸家的排斥,表现的亦是对婉约词风的认可,并在创作实践加以证明。他的词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词调选用上受花间词后主词和小山词的影响,有些词句甚至直接或间接化用花间词、后主词或小山词句的。如:“多少滴残红蜡泪”明显化用了温庭筠的“玉烛香,红蜡泪(《更漏子》)”;“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岂人为(《南歌子》)?”跟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词意很相近;而那句“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就很明显是从晏几道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来的,其他的如“百感消除无计(《金缕曲》)”,“换取红襟翠袖,莫教泪洒英雄(《清平乐》)”很明显是来自人们很熟悉的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和辛弃疾的“倩何人,换取红襟翠袖,搵英雄泪”。纳兰容若的才气使得他在化用前人词句词意时,表现出如盐入水的无痕之感,恰当地抒发他的个人情愫。
况周颐称道纳兰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1]。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由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王国维以“自然”“真切”评价纳兰词,把它提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况周颐以“性灵”标举纳兰词,誉其为 “国初第一词手”,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样说道:“我们试着看纳兰性德对于其爱妻的悲悼与对于朋友的信义以及对于一花一草的歌咏……没有做作,没有虚伪,只是实实在在地吐露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真实的诗、美丽的歌,纳兰性德词的价值全部在这地方。”[3]都表现出对纳兰容若向词的“本真之美”即具自然形态深情真率回归的肯定和赞赏。真切自然婉约倚情是词发展之初的主要特质,表明清词在对前代词体成就的全方位学习的基础上,选择词体的本色表现的自觉。而当代研究也指出:纳兰容若“表现南唐花间久已失去的光芒,这对清初词坛自有一番强烈的震撼力”[12]。可见,纳兰词在词体风格的选择上巧妙契合词体的时代选择,凸显独特的贡献。
而清词向婉约本色回归的同时,内在特质与传统婉约词存在根本的不同,表现为通过有意蕴的表达,突破前代积淀的情感诉求。词人们借助的是词体的形式,表现的是自我的心志,《花间集序》中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的炫丽的景象到清代词人笔下,成为负载纷繁情绪的外衣,寄托幽微情感的工具,词人们胸中郁结的情绪,在政治环境中纠缠的复杂与辛酸,在词中以比兴寄托的方式隐微地释放出来,词人的本心被美丽地隐藏了,词体的情感内蕴更加丰富和沉重。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写道:“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13]清词表现儿女之情,与《离骚》变《雅》之义相通,以婉约之态发抒诗情,呈现诗化趋向。
况周颐亦云:“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1]。”况氏认为填词要讲求寄托,要融入个人的身世之感,个人的灵性,纳兰容若亦契合这样的词体发展变化,认为“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鞋心事杜陵知”[4],持词承诗缘情而发,接《风》《骚》之精神,讲究比兴寄托的观点,在创作中,他把难以言说的心绪寄托于词中,释放难以言说难以解释的诸如人生难测、前途无望、理想幻灭、幸福不永的苦闷,倾诉对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追寻,以个人的性灵感受自然万物,再运以才学笔力,出以自己的言语,形成具有个人情性和时代特质的表述风格,以他的才情与敏感,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引领着词体回归的时代选择,从而缔造了自己在清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成就。
所以说词体发展到清代以比兴寄托、词继风骚的观念呈现出蜕变式的回归,饱含新的情感内涵的柔媚与婉丽,生命意识更加充盈的舒泄与传达,越发显出它本真的可贵。这是清词嬗变的重要表现,从而推尊词体,带动这一文体成为时代的选择,受到广泛的尊重和注意。
三
词体和词情的结合是评价词作高下的一个标识,结合完美的词作往往能获得广泛的认可。在词史上,真正把词体与词情甚或生命结合起来,前代比较突出是李煜、李清照,到清代就是纳兰容若。
纳兰容若在词中表达的情感有爱情、友情、亲情,都是人们易于感知的情感,那种对美好情感的描述和追忆,有前代词人的积淀,又有自己的情怀与寄托,形成独具特色的纳兰式的表白,往往激荡起读者类似的情感体验,特别是爱情词中凄婉的哀泣,近乎绝望的倾诉,切中人性情感的极致,人们容易被这种断肠之情所感动,达到理解之同情,甚至感同身受,纳兰容若的平生至交顾贞观评价其词“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4]。
纳兰容若把自我情感的倾诉与婉丽词体的表现融合在一起,聂晋人认为,读纳兰词,“香艳中更觉清新,婉丽处又极俊逸,所谓笔花四照,一字动摇不得者也。”[4]
在创作的过程中,纳兰有继承也有发展,表现为扩大词的表述空间,将词的情感指向从延续已久的青楼歌姬、婚外恋情拉回到正统的空间里,指向妻子指向家庭指向自我的真情,完成词体情感向正统伦理方向的转变,提高词体的情感规格①,从而为清词开辟迥异于前代的另一个表述空间,这个空间因此吸引女性文人堂而皇之地介入,成就一大批女性词人,也成就清词坛与前代不同的创作群体。
具体表现上,纳兰接纳花间的意象,挖掘其中新的意蕴,做到“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回廊、画阁、美女、心香、灯影、玉阶、玉壶红泪等等精美的意象,附丽着幽微的情绪: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虞美人》)
不如前事不思量,且振红蕤欹侧看斜阳。(《虞美人》)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欲诉幽怀,转过回廊叩玉钗。(《减字木兰花》)
熟识的意象被赋予新的涵义,意象与情感形象叠加,让人耳目一新。叶嘉莹先生就说他“鞭影落春堤,绿锦障泥卷。脉脉逗菱丝,嫰水吴姬眼”数句,“以写情的‘脉脉’二字形容菱丝,以写人的‘吴姬眼’三字形容‘嫰水’,真是写得生动异常”。而“落红片片浑如雾,不教更觅桃源路。香径晚风寒,月在花飞处”数句,写月夜中朦胧之光影下的落花,便也能在古今所有写落花的诗词中,更写出一种未经人道的境界[14]。
而纳兰词的边塞意象,亦给清代词坛带来清新之风。边塞意象在过去的边塞词中比较单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盛唐边塞诗,盛唐边塞诗出现的意象常常是征衣、明月、玉门关、黄昏、羌笛、浊酒、鸿雁等等,表现建功立业的壮志或将士思乡的情怀,格调大多昂扬高亢。清代是一个疆域辽阔的朝代,但唐代张扬的神采在清代文人身上似乎无迹可寻,古戍荒垒、连天衰草、寒月悲笳、塞马长嘶、西风夜哭、黄昏青冢等景物在清词中结构着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气韵,表现出清词词体的独特意蕴。相比较唐代边塞诗,清代边塞词更多表现的是寻找的状态,寻找历史,寻找表达,进而寻找倾诉,寻找异域风情,寻找苍凉之感。在外在的寻找中,寄托个人的幽思。纳兰的边塞词就是把寻找的历程带给时人,并带来独特的异域风光,带来他作为贵族子弟扈从巡边的独特感受,冲击着词坛,也刺激时人的心灵。
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菩萨蛮》)
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 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忆秦娥》)
这里传达的不是前人守边的思绪,而是后人面对苍凉历史的兴亡之感,以一种逆时性的表述,呈现对历史的回望式的理解和感怀,成为时代的代言,他代这个时代言说边塞情怀。他独特的经历成就他独特的词篇,他独特的词篇记录独特的时代。所以,他被这个时代所记录。
陈维崧评价纳兰容若的词“哀感顽艳”[4],在词评中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清初宋征璧对柳永的评价中:“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后来又延伸到宋代秦观身上,认为秦观“把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作,也就是有顽艳之感,而柳永、秦观在词史上被定位为婉约词人,是宋代词史上重要的词人。用一个相同的词语评价纳兰和柳永、秦观之词,可以说是前代风格在清词上的积淀的表现。“艳”触及词的核心特征,从词进入花间的范畴,“艳”就是词的一个标志,一个符号,所谓“词为艳科”,“艳词”是也。所谓“顽”字,用钱钟书的解释是“‘顽’,心性之愚也”;“‘艳’,体貌之丽也”;“‘顽、艳’自指人物,非状声音;乃谓听者无论愚智美恶,均为哀声所感,犹云雅俗共赏耳”[15]。
况周颐评明代屈大均《道援堂词》:“词中哀感顽艳,哀艳者往往有之,独顽以感人,则绝罕觏。道援斯作,沉痛之至,一出以繁艳之音,读之使人涕泗涟洳而不忍释手,此盖真能感人者矣[16]。”可见写艳词易,写顽艳之词难,写哀感顽艳之词更难。哀感顽艳是力度强烈的情感抒发与婉丽凄艳的词体表现的结合,二者所释放出来的感人力量摄人心魄。这也是词体创作达到的较高境界。
“哀感顽艳”在纳兰容若的词作中得到充分展现。顽艳意象,顽艳情愫,结构成一张顽艳之网,很好地抒写他的哀感,对爱情的期盼和绝望,对扈护生涯的厌倦和隔离,对边塞风情的亲近和感怀,他在传达个人的真挚情怀时,带出人们普适性的情感经验和感受,引起“雅俗”共鸣,得到时人认可与推崇。“哀感顽艳”也成为清词创作追求与审美趋向之一,成为评价清词的一个特点,一个特定的词语。朱彝尊在诗话里评价当时诗人黄任(字莘田)道:“其艳体尤擅长,细腻温柔,均顽艳感。”[17]
纳兰容若和同时代众多词人一起,在与前代词人的精神相通中逐步完成词体的抒写与嬗变,在与前代词体形式的沟通中,获得创作灵感因子。他们愉快地选择性地用调,适时地创调,而无需像宋代词人,为创调而努力,大量前代的储存可供他们利用,他们把词牌词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他们不是在抒写配乐的歌词,而是在填写歌词,音乐的旋律消失了,他们玩味的是文字的美感,在文字的美感中沉淀心灵的寄托,安抚躁动的情感,直到这样的状态出现,词才真正成为时代的文体,真正发挥它歌咏言声依永的魅力。“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18]“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
纳兰填词常常使用一些传统的词牌,如小令《菩萨蛮》《临江仙》《虞美人》《蝶恋花》《清平乐》《采桑子》等,慢词《沁园春》《金缕曲》《水调歌头》等,但他自创调也非常突出,有自度曲分别为:《潇湘雨》《青衫湿》《湘灵鼓瑟》《玉连环影》《落花时》《秋千索》《秋水》《添字采桑子》。成就比较高的是小令,他把小令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代表清词小令的最高成就。他常常通过一个个情感片段的倾诉,触动人类内心中最隐微的所在,打动读者,引起情感共鸣和审美感悟,这是奠定他清初第一词人地位的重要依据。“纳兰的个性与作品都和李后主相伯仲,他的小词在清代是无足与抗衡的。”[19]有论者云:“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词坛。陈天才艳发,辞风横溢。朱严密精审,造诣高秀。容若《饮水》一卷,《侧帽》数章,为词家正声。”[4]
纳兰容若笔下,很多词牌与原本情感限定的距离越来越远,脱离原先的内容限制,如《蝶恋花》本不宜填慷慨激昂的内容,《念奴娇》也不会出现肝肠寸断的作品。而纳兰却把“今古河山无定数。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这样慷慨的句子用在《蝶恋花》中,这在清以前是比较罕见的。纳兰填词时,还常常出现同一个词牌填写不同题材的现象,他的《采桑子》18首,内容就涉及爱情、咏物、悼亡等多个题材。因此,需要解说,有的在词牌后加一个标题如《忆秦娥·龙潭口》《卜算子·咏柳》《卜算子·塞梦》《一络索·长城》等,有的附以小序,《沁园春·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装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标明主旨,便于阅读。
虽然宋代张先开词中运用题序的先河,但广而用之形成风气,是到清代。这个时期,词牌对内容的限定作用逐渐减弱,只成为一种文字格律和字数的说明,清代词人需要用题解对词牌和内容进行阐释,但这并不影响词情的抒发,反而成为清词的一大特色。
温婉的情感、婉丽的表述和自由的体式和谐统一,词情与词体完美结合,使得纳兰容若的词作走在清代词坛的前列,指引清代词人创作追求的方向。词的娱乐功用在清代逐渐消失殆尽,词与音乐最初的亲密关系在不自觉中逐渐剥离。人们依据词谱填词,词体在自觉不自觉中扩大表达的范围,成为时人叙事抒情的工具,完美地完成从娱乐和实用中脱离,进入词人生命书写的价值范畴的历程,词体因此嬗变,逐渐从类诗状态凝定成长短句抒情格律诗的形式,更具表现力与功能性:
词的与生俱来的长短句式,……比近体诗就显得更多些自由和弹性。这种自由和弹性恰恰能使抒情性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样,词不仅获得了自《诗》《骚》乐府以至五七言古近体同样的抒情功能,而且还奇妙地构成了它独具的或旖旎绵密、缱绻回环,或激越飞扬、奔泻跳宕的更适宜于歌哭悲欢之情绪波段的特性[20]。
从词体的嬗变过程来看,这也是纳兰容若与同时代词人对前代词人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依谱填词,依律填词,从声律的角度,走向与诗的合流,却又能展现自己绰约的风采,“词的抒情功能愈益增强,抒情主体的特性也逐益显明,作为广义的抒情诗的一体的独立性完全确定了。”[20]当清词有了自我,有了独特,发展的前景就不同一般。
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写道:
词在清代,已用其实在的,充分发达的抒情功能表征着这一文体早就不再是“倚声”之小道,不只是浅酌低唱、雕红刻翠徒供清娱的“艳科”了。所以,清人之词,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任何“诗庄词媚”一类“别体”说均被实践所辩证。词的可庄可媚、亦庄亦媚,恰好表现出了其卓特多样的抒情功能[20]。
形式给内容提供空间,内容使得形式更加有表现力,于是,体式从容、抒怀言志之词体,因不局限于前代形式的窠臼,可以自由地寻找更恰当更准确的抒情方式而成为清代许多文人的选择,造就了清代词坛的繁盛与独特。
四
清代词坛还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词人众多,词派纷繁。清代词人词作数量,超过鼎盛时期的宋代,词人同声相和,呼朋引伴,在前代可资借鉴的丰富创作经验基础上,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理论的自觉应时而生,词人们有意识地创建各种词派,提出自己鲜明的词论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互辉映。身处鼎盛时期的宋代,词的开宗立派没有形成一种风气,有些学者提出“宋词无流派”之说②,倒是在诗歌的范围内出现众多流派。同样,在被认为是诗的伟大时期的唐代,人们的注意力也没放在诗派的构建上。流派的出现是一种文体进入总结时期的标志,也是人们对这一文体的认可和尊重的表现,当词派和诗派一样,能大量堂而皇之走进文学史,也就是一直被戴着诗余帽子的词扬眉吐气的时候,这是清词的一大壮举。
清词在中兴之初就以流派的形式出现,成为清词中兴的外在表现,是清词进入总结时期的一个标志。明清交接时期的云间词派,吹响了清词中兴的号角,随后的柳州词派、广陵词人群、毗陵词人群,形成了词学名流云集,倚声填词异常活跃的局面。清初影响较大的词派就是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了。他们自觉地开宗立派,编选词集,尊崇词体,掀起了清词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他们的理论主张影响着清初词体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纳兰容若没有归属哪一个词派,没有组建自己的词派,没有公开发表词学声明,但是在那样的时风中,他交游的词人群体,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的词派特色,他们的特点是风格相近,志趣相投,诗酒唱和,情谊绵远,于是就“被词派”了,有人称之为“渌水亭词派”,这是以他们唱和之地为名的,或是“饮水词派”,这是以纳兰的《饮水词》得名的,或是“日下词派”,这是以纳兰的职位得名的,无论取什么名谓,都是以纳兰为中心,而纳兰散见于作品中的词学主张,俨然成为后人为他立派的纲领。这在清代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北宋没有类似的词派,人们所谓的婉约和豪放,只是对众多词作风格的归纳总结,就是在苏轼身边集结的众多的文人,他们的创作也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趋同成派的状态。只是到了南宋,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之下,人们在辛弃疾的词作里找到情感的寄托和宣泄的渠道,才有辛派词人的出现,但作为词派的组成还显得很不成熟。更不用说出现众多同气相和的派别(观点佐见于谢桃坊《词学辨·宋词的流派问题》)[21]。纳兰容若这种“被词派”的现象,表现时人对他和他的词作风格的推崇和认可,是时风所致。有的研究者认为“日下词人集团”的形成和存在是清词所以能“中兴”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清词中兴”最有力的证据,是有一定道理的[22]。
清代众多的词派以前代为皈依进行选择,不互相排斥,显示出豁达的包容,派别之间和平共存,共同缔造清代词坛的繁荣,造就中国词坛又一片绚丽多姿的景象,展现的是词体嬗变的丰硕成果。
结语
清词清晰地延续前代词体的发展脉络,为词体嬗变提供合适的土壤。这土壤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即词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清初的时代特性、清代文人的自觉等,引领词体发展进入总结期,引发词体的中兴。
词体是时代选择的结果,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人们没办法发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吼,只能借助词体的婉约缠绵,怯怯倾诉,无言低泣,表达难以言说的情怀。从这个层面上看,这就为词体嬗变提供情感支撑与表现基础,词体得以进入抒情主体生命书写的价值范畴,促进词体与诗体地位上的并驾齐驱,使得清词最终以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的完美形式存在于文学史中,具体表现为向词体本真之美的回归,情感性灵与婉丽词体的完美融合,体式自由,表达从容,词派兴迭,独立突出。
在这个过程中,纳兰容若充当的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天生纤柔善感,天才地发挥了词体所具有的要眇宜修、婉转纤柔的特质,表达心中柔婉精微的感受,生命中所经历的悲苦与无奈,在自然真切中呈现凄婉而耐人寻味的情感体验,其真情极情的抒写顺应当时词坛对“情”的呼唤,契合清代词人以赤子之心抒写时代悲吟与哀婉心境的需要。他以他的博学多才和与词体特性相契合的气质性格,以他对时代情绪的自然感应,以他对前代创作成就的充分掌握,充分学习,以一种集大成的词性存在以及诠释,完成了清词嬗变的使命,成为清词的标帜人物,使得清词得以在词史上与宋词相媲美。
注释
①此类作品首创于苏轼,但大量创作应始于纳兰容若。
②谢桃坊在《词学辨·宋词的流派问题》一文中是这样界定文学流派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作家,他们因有共同的文学思想和相同的艺术风格而结为一个群体,表现出基本思想与艺术特征的统一,体现了某种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或联盟,提出了新的理论纲领,于是形成文学流派,因此,他认同胡云翼先生在《宋词研究》一文提出宋词无流派之说:“宋词人作词是很随意的,……没有一定的派别。我们绝不能拿一种规范的派别来限制他们。”认为这是词的体性与娱乐功能决定的,并进而提出“宋词无流派,也许真正玉成其为时代文学”的观点。
[1] 唐圭璋. 词话丛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 梁启超. 梁启超文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M]. 台湾:中正书局, 1980.
[4] 张秉戍. 纳兰词笺注[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5] 叶嘉莹. 清词丛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6]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7] 谢章铤, 刘荣平.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8] 徐珂. 清代词学概论[M]. 上海: 大东书局,1926.
[9] 沈丰垣. 兰思词钞[Z]. 康熙吴山草堂刻本.
[10] 陈子龙. 三子诗余序[M]//安雅堂稿(卷三). 台北:伟文图书出版公司, 1977.
[11] 纳兰性德. 纳兰词笺注[M]. 张草纫, 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2] 李惠霞. 纳兰荣若及其词研究[M].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
[13] 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四十)[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4] 缪钺, 叶嘉莹. 词学古今谈[M].长沙: 岳麓书社, 1993.
[15]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6] 梅向东. 论况周颐对明词的重新评价——兼及况氏之词心史观[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9(11): 73.
[17] 郑方坤. 全闽诗话[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8] 查礼. 铜鼓书堂词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9] 胡云翼. 新著中国文学史[M]. 北京: 北新书局, 1937.
[20]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21] 谢桃坊. 词学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2] 宋培效. 略论以纳兰性德为首的“日下词人集团”及其创作[J]. 承德师专学报, 1987(4): 76.
Nalan Rongru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Qing Ci-poetry
ZHENG Ya-fang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The unique developing environment of Qing Ci-poetry put it on the verge of evolution,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its return to truthfulness from gracefulness and restraint,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expressing self emotion with elegant Ci, aesthetic pursuit of making Ci so pathetic as to move both wise and the dull, inherent absorption and fusion of Ci and poetry while being kept pace with each other in status, the complex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Ci schools, etc. During this process, Nalan Rongruo was shouldered with the landmark mission of explaining with his works the evolving process and traits of Qing Ci-poetry, and eventually becoming the spokesperson of the Ci-poetry of this time.
Qing Ci-poetry; the evolution of Ci; Nalan Rongruo
I222.8
A
10.14071/j.1008-8105(2015)06-0064-07
编辑 邓 婧
2014 − 12 − 10
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科项目“清代词体形态研究及清词中兴探因”成果(JA11231S).
郑亚芳(1973− )女,福建省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