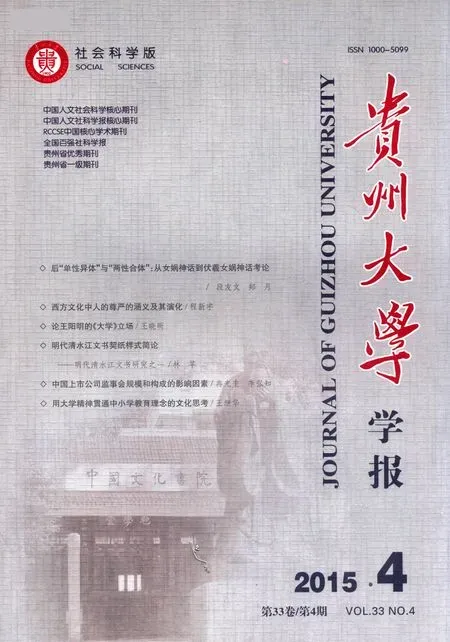“大团圆”叙事模式的早期表现及伦理基础——以《列女传》为例*
2015-03-21史常力
史常力
(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大团圆”结局类型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叙事类作品惯用的一种结局方式,王国维先生、鲁迅先生都精辟地分析过“大团圆”式结局对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巨大影响,在这之后多有学者对中国人为何钟爱“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种带有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结局方式自有其形成的文化土壤及成长过程,本文尝试以一部早期叙事性作品为例,具体地分析早期作家如何将本来以悲剧结尾的故事改变为“大团圆”结局的,借以探讨这种结局方式的早期形态及最初的伦理来源。
《列女传》由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编纂,是我国第一部女性传记集,文体性质介于传统的史书和虚构的小说之间,是征实的史传向虚构的小说演化过程中的实例,正符合考察对象的要求。《列女传》虽然多采前代史书、子书中已有故事改编成书,但经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刘向在改编时,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追求善的圆满实现与恶的崩溃毁灭这样一种“圆满化”的叙事格局,这种“圆满化”的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启了后世“大团圆”结局的先河。刘向构建的圆满化叙事格局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情节本身相对完满;另一种在情节上则属于悲剧,相对来说更能体现出作者自觉的叙事追求。
一
在《列女传》中那些结局相对完满,或者以和缓的方式解决了矛盾冲突的传记中,圆满化叙事的倾向很明显。这种类型中,刘向基本上遵循着“善有善报”这样一种朴素实用的道德观念来设计传记结局。
《列女传》中大部分传记的圆满结局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态:儿子或者丈夫听从了母亲或者妻子的教导和劝告,有所成就或避免了危险的发生;另一种结局则相反,故事中的男性不听从女性主人公的劝告,一意孤行,结果导致失败,但这正证明了女性判断的准确,符合对女性赞美的意图;还有一种结局是作为母亲或妻子的女性,依靠单纯但深厚的感情成功地拯救了处于危险中的丈夫或儿子。以上传记中结尾的圆满化基本呈现为“善有善报”,女性在这些传记中都是正面人物,这种圆满的结尾,都是对她们在故事中表现出来的善良、守礼、全心相夫教子、聪明睿智等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的回报。
《列女传》中还有一种结局类型与此正好相反,表现为在故事结尾处对女性恶行的惩罚。这一类型集中在卷七《孽嬖传》。这一卷中的女性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她们的行为都违背了礼法的规定,在道德上都呈现出恶的形态,都给所在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动荡。因为这些女性的行为明确表现为过分的嫉妒,对正直人物的排挤和迫害,对国家权力不该有的欲望等,所以为了清晰地表达对她们的批判,在结尾处都会明确写清楚她们给国家造成的伤害,并且明确将她们自身悲惨的结局与曾有过的恶行联系起来。但也应该看到,刘向在对她们批判的同时,却缺乏对恶行原因的深层思考,只将一部分原因归于女性的美貌这一外在形态,对造成这些灾难背后的根本原因——宠爱、放纵这些女性的男性则缺乏批判[1]68-72。
在这一类型中,是与非,善与恶,结局的好与坏能够清晰对应在整体叙事中,结局中善的圆满化和恶的毁灭一般都可以很顺畅地实现。刘向构建这种结局的基础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衡量的标准,是道德评价简单且直接的实现。
在很多故事中,代表正义与邪恶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下的正、反双方,因为有激烈的斗争,很多时候正面人物会受到伤害甚至死亡,而这些故事又多来自明文记载的史书,刘向不可能更改其中人物的悲剧结局,但却会使用其它叙事方式增加一个“圆满化”的结局,这种与原有记载中不同的结局方式也就更能体现作者的主观追求。
卷四《楚平伯嬴》和《梁寡高行》这两篇传记就是此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其中的伯嬴是战争中战败一方的夫人,面对战胜一方的占有企图,伯嬴毫无所恃,只能听人摆布,任人宰割。伯嬴面对吴王阖闾以一种战胜者的身份“尽妻其后宫”的威胁,为了自保,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反抗方式:持刀相要挟。伯嬴通过这种方式赢得了劝说吴王的机会,并成功说服了吴王,不仅使吴王惭愧而退,并且派兵保护伯嬴的安全。《梁寡高行》中的高行是梁国的一个普通寡妇,立志不嫁,已经拒绝了梁国众多贵族的求婚,当她面对梁王的请求时,自知很难顺利地拒绝国君的请求,因为梁王并没有强占的举动,又是派大臣正式迎聘,可她又一心想要守住贞节,就只能在口头拒绝的同时,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乃援镜持刀以割其鼻”[2]160。高行通过毁容不仅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又使得梁王不再因为她的美貌对其有所觊觎。被她的道德感动也好,被她的行为震慑也好,结果梁王不但打消了强占的念头,更赐给她“高行”的尊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高行保住了名节。最重要的是,起初站在女性对立面的反面人物,以对她们让步、赏赐的行为表现了对她们崇高道德的认可,最终实现了和解。
另外一些故事则更惨烈,女主人公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类型的悲剧色彩无疑更浓,但如果透过表面这种充满痛苦和血泪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结局,仍旧可以发现作者注重的并不仅仅是对故事中个体人格刚烈、坚贞等方面的弘扬,这种类型的悲剧故事仍然是以情节本身的自我完善,或者通过作者启发读者而达到道德理性的觉醒,化解了悲剧冲突。
卷三《息君夫人》,这个故事本于《左传》,但这里的息君夫人刚烈的个性并不十分显著,她在亡国被楚王掳走后,为楚王生了三个孩子,只是以“不共楚王言”这样的方式进行默默的反抗。刘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造,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感情基调:息君和息君夫人在亡国后双双被掳到楚国,息君为楚国守门,而楚王一心想占有息君夫人,却始终遭到拒绝。最终息君夫人借楚王出游之机面见息君,互诉衷肠后双双自杀。这本来是一个典型的为了追求理想婚姻而殉情的悲剧,如果按照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悲剧观点来分析,这正是美好的愿望与不能实现的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最终导致美好人格的毁灭。但刘向所写的故事并不仅仅到此为止,他又增添了一个情节:楚王被息君夫人所感动,以诸侯礼节合葬了息君夫妇。这一情节安排并不只是表现反面人物的觉醒和悔过,也不只是单单是要通过楚王的举动来反衬息君夫人行为的崇高。有了这个附加的结尾,这篇传记就不仅仅是对息君夫人坚贞行为的表彰,也不再停留在对一人一事的记录上,而是趋同于更加广泛的道德理性。激烈斗争的双方在一种惨烈的结局过后,原来企图占有息君夫人的楚王显然已经被强大的道德力量所感染,他做出的补救措施可以看成其道德理性的反省和觉悟。此外,在以“君子谓”和引《诗》评论这两种常规形式对息君夫人赞美的基础上,刘向又以作者的身份插入了一句议论:“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2]144这样处理的结果就将原本充满悲伤情绪的故事情节引向了对道德完善的追求上。
类似的安排在《列女传》的悲剧故事中还有很多。卷四《宋恭伯姬》中的伯姬,因为守礼不肯在傅母未到场的情况下离开火场而被烧死,在结尾处又有这样的情节:“当此之时,诸侯闻之,莫不悼痛,以为死者不可以生,财物犹可复,故相与聚会于澶渊,偿宋之所丧。”[2]133卷四《楚昭贞姜》中的贞姜同样因为不肯违背礼法规范而被大水淹死,结尾处又有她的丈夫楚昭王对贞姜的赞美:“王曰:‘嗟夫!守义死节,不为苟生,处约持信,以成其贞。’乃号之曰贞姜。”[2]151卷五《楚昭越姬》中的越姬起初不肯因为只是为了共同享乐的原因而答应与楚王同死,但25年后,当楚王表现出充满仁爱之心且身患重病时,越姬则以自杀而死的方式表达了对楚王崇高道德的肯定和追随。故事的结尾,楚国大臣相信“母信者,其子必仁”[2]173,共同拥立了越姬之子为楚王。卷五《盖将之妻》中的盖将之妻不忍心在亡国后看见自己的丈夫身为亡国之将还独自苟活,自杀而死。结果:“戎君贤之,祠以太牢,而以将礼葬之,赐其弟金百镒,以为卿,而使别治盖。”[2]176卷五《魏节乳母》中魏国公子的乳母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独自保护魏公子,双双被秦军射死,但“秦王闻之,贵其守忠死义,乃以卿礼葬之,祠以太牢,宠其兄为五大夫,赐金百镒。”[2]191
在以上故事中,这些女性自杀后所增添的情节,都体现着作者一种将整个传记圆满化,将悲剧人物所蕴含的道德精神普泛化的意图。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篇末那些起初意图行凶恶人的退却、悔悟,这些女性的抗争和牺牲就毫无意义。这些故事如果没有这样的“尾巴”,只是单纯的悲剧,只有正面人物白白毁灭这样无法挽回的遗憾存在,只会让读者为之心痛惋惜。那么刘向为何要孜孜追求这样一种圆满化的结局呢?这取决于《列女传》一书的性质。
二
《列女传》全书共有一百多个故事,可以明显发现其内在叙事模式具有一种非常类似的同构性,所有故事类型都按照同一种叙述模式搭建起来。这个叙事模式就是,以绝对化的、高度理性化的道德准则作为整部作品的最高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物会达到成功,而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物则会失败。
这种绝对化的叙述模式,又是由《列女传》这部书的性质决定的。从《列女传》的成书原因上可以看出,刘向并不只是记载女性的事迹,而是借记载这些故事来对汉成帝及其后妃们进行劝诫。《汉书·楚元王传》中清楚地记载了刘向编纂此书的目的:“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3]1957刘向编纂《列女传》时汉王朝在汉成帝统治下危机四伏,而外戚专权则是造成这种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外戚专权又源于皇帝对后妃的专宠以及后妃自身的僭越擅权。可见,刘向编纂《列女传》带有极其明确的目的性,他要借助对女性美好品德的表彰和对恶劣品性的批判,来达到劝谏皇帝和教育后妃的目的。
整部《列女传》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带着鲜明劝诫性质的谏书。通常意义上的劝诫,除了口头形式以外,又能够以书面的形式来完成。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对诉诸书面的劝诫就有过如下阐述:“夫说贵抚会,驰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4]329这种诉诸文字的劝诫虽然能够突破特定场所的限制,但与面对面的语言劝诫相比较,又有其特殊的要求。因为不是直接面对被劝诫人,而且被劝诫人汉成帝及其后妃们的高贵地位也不准许刘向没有遮拦地直接告诉被劝诫人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要完成劝诫目的,故事中就必须对是非、善恶有非常明确的区分,并且要在人物结局中鲜明表现出这种区分给人物造成的影响。这样,在故事中设置一条绝对的标准就是达到以上目的所必须的。整部书中的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受到预先设置的这一标准的控制,无一例外。任何人,无论是什么身份,出身高贵也好,出身卑微也好;做任何事,无论大小,治理国家也好,处理日常琐事也好,只要人物的行为符合作者预设的标准,就会成功,反之则都会失败。只要这样,才能清晰明确地传达是非、善恶观念。这种叙述模式,虽然稍显简单,而且有些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成分,但确实能够有效地实现对是非、善恶的区分,更好地实现预期目的。
如果以上这些故事的结局一如原本记载:好人没好报,恶人可以随便做恶,尽管可能符合历史真实,但却根本无法有效传达出对善的褒奖和对恶的批判,这样的作品又怎么能够给汉成帝那些已经十分骄淫的后妃们树立行为规范呢?所以,刘向一定要扭转这些故事的结局。他不可能让这些女子死而复生,就只能在她们死后做文章,在她们死后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声。既然正面人物已经毁灭了,而刘向他能做的其实也就只能是让反面人物受到感化,以对正面人物表彰为主要方式表达他们的忏悔。这可能是刘向无奈的选择,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整个传记中善的圆满化,矛盾双方在这样的圆满化中实现了和解。《列女传》虽然并不是每篇传记都以“大团圆”的方式作为结局,但还是可以体察到整体上具有一种期待和解、追求圆满的叙事倾向。从以上分析即可看出,只要故事出现“不圆满”的结尾,刘向都会采取某种人为的操作方式,将本来不那么和谐,甚至是充满血腥对立的故事在结尾处引向和解,使整个故事变得圆满。
而且应该看到的是,虽然矛盾双方趋向于和解,但这种和解并不是道德批判上的模糊化,不能将上述这种和解看成是善恶不分或者是一种简单的调和主义,刘向也绝不是在“和稀泥”,这是作者主动追求的叙事效果。和解的基础是邪恶一方被正义一方强大的道德力量所感化,或者表现为悔过,或者表现为羞愧,都停止了对正义一方的侵害行为。可以说,和解的实现是以正义对邪恶道德上的征服为基础的。
三
学界在讨论中国叙事文学偏爱“大团圆”结尾时,主要将答案集中在国人缺乏成熟的悲剧观,儒家讲求“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审美心理,早期形成的循环式宇宙观、人生观,以及伦理道德决定论等方面。这些分析都有其合理性,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叙事性文学“大团圆”结局盛行的原因。吴士余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根源在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准悲剧”的思维形态,中国古代小说这种缺乏深刻悲剧意识的原因即在于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儒家“中和”的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思维机制一直在小说写作中发挥作用[5]37-56。这种“中和文化精神”实质上是结合了民间朴素因果报应观念以及儒家伦理道德体系而来。
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刘向通过将道德观念凌驾于具体行为之上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叙事目的。先秦儒家就已经建立起以“仁”作为核心、以“礼”作为规范的道德体系,而且认为道德修养对于个人来说极为重要,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正如孟子所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6]259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的整合强化,儒家道德观开始变得严厉并带有强制性,“三纲”“五常”等观念与天地阴阳相联系,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从《列女传》中多次强调“三纲”“三从”等观念的情况来看,刘向对于这种绝对化的儒家道德观是很认同的。刘向灌注在《列女传》写作中的正是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意识,以伦理道德来抹平现实事件中不可改变的缺憾,并将这种缺憾转变成值得人们感动、颂扬的道德标杆。从以上具体篇章中可以看出,刘向会给原来正面人物被毁灭这样的故事加上一个反面人物被感动,双方实现和解的尾声。在对待受批判的反面人物时也是如此,只要不违背历史真实,刘向就会明确写出她们遭受的惩罚,并指出这些惩罚正是她们先前的恶行结出的恶果。但这几个在《列女传》中遭受惩罚被杀的女性,像末喜、妲己、骊姬等,都是死在政治斗争中获胜一方的手中。实际上,即使她们先前贤良淑德,作为失败一方,在乱兵之中也很有可能被杀。也就是说,将她们最终被杀写成对她们的惩罚,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结尾,来源于刘向的理解和阐释,他做出这种阐释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结局符合儒家道德体系对人格恶的惩罚。
除了儒家伦理道德以外,这些故事中普遍存在的还有朴素的报应观念,这种观念主要来自民间。虽然中国的“业报”观念是在佛教传入后才最终明确起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但在古老的中国,类似的观念早已开始萌生并为人们所信奉。刘向本人的其它作品中对这种观念也有反映,在《说苑》一书中还专门设有《复恩》一卷,大部分都是这种做了善事日后得到回报的故事。善恶有报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美好的向往,通过对行善事的褒奖以及对恶行的惩戒来实现。尽管在这种观念中,当事人的行为与结果其实并无必然联系,但因为这种观念表达了对维护社会正常道德秩序的期望,也能够为儒家道德思想体系所容纳,从某些方面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善恶有报的故事作为实证,这个道德评价体系才能被确认为是正确的、有效的。善恶有报观念因而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得以显现。刘向正是在《列女传》中融入了善恶有报的观念,借以实现结局中善的圆满化和恶的毁灭。
善恶有报的观念在中国史书中早有普遍的记载,著名的“结草相报”故事就来自《左传·宣公十五年》,这个故事甚至很早就成为了善恶有报观念的代名词。《左传》中另一个著名的故事:赵盾在晋灵公要加害他的危急时刻,得到“桑下饿人”的拼死相救也正是因为赵盾曾经救助过这个人。赵盾的得救表达的也是善有善报的观念。王靖宇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中就指出:“(《左传》)这个模式是这样的:正如恶人、蠢人和高傲的人通常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一样,善人、智者和谦虚者终将得到应得的报偿。”[7]35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对善恶有报这种观念产生了质疑——从《伯夷叔齐列传》中对伯夷、叔齐二人为仁义而饿死有何善报这种尖锐的诘问中可以明确看出司马迁的质疑,但这种怀疑正好证明这种观念在社会上很流行,传记中就记载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8]2124这种当时社会普遍的说法。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中国古老的史书文化中,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叙事模式:以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作为衡量人物和事件的最高准则。史书叙事在很早的时期就取得了一种超越其它文类的意义地位,作为史书的《春秋》及《左传》最早被纳入“经”的体系就是明证。这种意义地位使得史书的叙事模式具有了一定的支配意义,其它文类也以仿效史书叙事模式的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文类地位。“大团圆”结尾的形成过程是可以看出史书叙事影响的。
重视伦理道德的儒家思想和朴素的报应观念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列女传》实现结局中善的圆满化和恶的毁灭的伦理基础。这其实也是贯穿在日后绝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伦理基础。不能说刘向开风气之先,但这种结尾方式为过去叙事文学所罕见,《列女传》在这一点上正体现了以纪实为主的叙事文学向虚构的小说过渡的特点。
[1]史常力.“美女破国”理念的产生与确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2(3):68-71.
[2]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