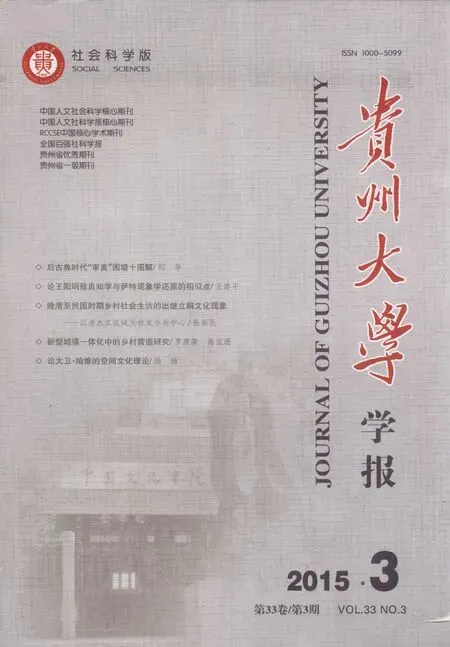阳明后学思想家罗汝芳研究综述
2015-03-20鹿博
鹿 博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8)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作为中晚明重要思想家,以往研究多将其纳入阳明心学泰州学脉,探讨思想家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建构。从阳明心学的视域出发,结合思想家早年对阳明学的研习和推崇,以私淑弟子身份将罗汝芳划归阳明后学,实至名归。但以泰州学派界定近溪哲学,无论是就地域层面考虑,抑或从师承角度、思想面向来说,都存在质疑。地域层面无需赘言,就师承来讲,罗汝芳一生“善无常主”,且其自道所遇“真师”唯胡子宗正,据此,仅以罗汝芳与颜山农的师徒因缘,将其划归泰州学脉不免牵强。而就思想上的继承和开拓而言,泰州并非可以阳明真脉称名,与此同时,近溪立学也早已跳脱泰州思想涵盖范畴,比如成熟阶段的近溪思想已然呈现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双向汲取。在此前提下,思想家在本体论层面偏向于“归宗性地”,在工夫论层面则主张“默识”,无论就哪一个层面考察,罗汝芳哲学创制与王艮、颜钧等人的学术宗旨愈行愈远。正是立足于文献辑考的最新结果和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罗汝芳的思想史地位有待给以新判。
一、研究成果综述及方法理路分析
目前,罗汝芳研究大体上呈现两方面特色:一者文献辑考独立于思想研究;二者,研究者多循阳明后学泰州学脉,在划分派系的前提下,概论近溪学术特色。就前者来看,文献领域的罗汝芳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诗文的搜辑与整理;其二,关于近溪生平活动资料的文献辑考。在诗、文整理方面,2007年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阳明后学丛书之一《罗汝芳集》的出版实为一大学术贡献。该书所收罗汝芳著作版本,除《明儒学案》外,其他皆为明版本,另对近溪门人整理辑出的《尊贤録》作了筛选采纳,保证了后人引用的准确性。关于近溪生平活动的梳理方面,1995年程玉瑛先生撰写了《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近溪)诗文事迹编年》,2003年吴震先生的著作《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2006年历史学者吕妙芬论著《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等书的出版为学界对近溪生平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2011年刘聪先生在《阳明学刊》上发表《罗汝芳与佛教的因缘》一文,为罗汝芳宗教文献的搜辑开启了新路。遗憾的是,以上文献整理工作对罗汝芳生平史料的考述并非系统化的展开。
罗汝芳文献史料研究的相对匮乏,反映了一则事实,即学界对罗汝芳的关注仍集中在其哲学及思想层面,该领域研究成果相对丰赡。早在20世纪,牟宗三先生曾以“清新俊逸,通透圆熟”[1]评介罗汝芳思想特色,且用“破除光景”一说解析近溪子哲学建树。牟先生上述观点对后代学界影响深远,后来学者的探索路径多以此为准的。大陆学者张学智先生对罗近溪学术思想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其专著《明代哲学史》第十七章中,题目为罗汝芳的“赤子良心”之学。张学智先生认为,罗汝芳学术宗旨在于“赤子之心,有无合一”[2],其功夫论取径在于顺适当下。张学智先生对近溪子思想宗旨及其功夫路径的把握,可谓精辟,然按此路数,罗近溪对阳明学的发展,便体现在思想家对“祖师禅”的借鉴。吴震先生在《罗汝芳评传》一书中将罗汝芳的思想风格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求仁”为宗旨、以“孝弟慈”为核心内容,以万物一体为最终归趋的儒家伦理思想;二是以“天心”观为基础,以敬畏天命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伦理学说;三是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以宣讲“圣谕六言”、制定“乡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思想。
此外,吴震先生又在《泰州学派研究》一书中,将罗汝芳定义为“泰州学的终结”,且认为,“相对于阳明的那一套心学话语而言,近溪思想的特异之处同时也是其思想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仁孝学说、身心理论、天心观念、宗教关怀、政治意识以及参与社会的担当精神”[3]。
总体来看,吴震教授对罗汝芳思想的阐释与唐君毅先生的观点有承继和推展的关系。事实上,试图在罗汝芳思想研究领域寻求突破的学者,向来不乏其人。龚鹏程先生曾撰写专文《罗近溪与晚明王学的发展》,试图跳出牟宗三先生对阳明学的分系理路,从更客观的角度评述近溪思想之得失。认为近溪之学“非以无工夫为工夫”,乃是“以在日用常行间做工夫”[4]。依据这一认知前提,龚先生认为,罗汝芳于泰州之功,实是发展出了一套“克己复礼”的新体系,“以致阳明的良知学逐渐由‘体仁’走向‘立礼’、由‘自证本心’走向‘明明德于天下’”[4]38。周群先生在论文《从阳明到卓吾的中介——论罗近溪思想的定位》中,以近溪之学为李卓吾重“私”理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的铺垫之故,实现对罗汝芳思想史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往研究的丰赡成果和创新思路启发我们关于罗汝芳研究,或可从更宏观的视角,依据更翔实的文献考据,大胆开拓,系统分析。
二、史、论并重:研究方法论的再探讨
针对当前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的疏离,我们试图以史、论并重为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展开关于罗汝芳生平思想的探讨。这一方法论原则规定了一则基本事实,即思想研究的推进必然以文献辑考为前提。比如学界多以王学“左”派定位泰州宗旨,在惯性思维导引下,即以“任侠”“狂禅”看待近溪生平及思想特征。此番评介涉及两方面重要事项:其一,罗汝芳的师承问题;其二,罗汝芳与佛道二氏关系之争。
1.文献考述证罗汝芳学术派系划分不确
罗汝芳一生拜师求学向有“善无常主”之说。笼统地以“泰州学传人”概述近溪学术归属,单纯从史实考据层面而言,就存在三方面疑问:第一,若以“门人”定义“传人”,罗汝芳实出自徐存斋之门。第二,如按执弟子礼与否界定,罗汝芳不仅曾拜颜钧为师,且曾执弟子礼于胡宗正,并称后者为“真师”。第三,从思想传承上讲,罗汝芳哲学思想创制早已跳脱泰州学术宗旨。关于罗汝芳的徐阶门人身份,由徐氏弟子郭斗《刻近溪罗先生会语叙》中记其与近溪同“为相国存斋先生门人”可知。又据文献,罗汝芳确曾拜颜钧为师,但也有执弟子礼于胡宗正的史实记录[5]938。曹胤儒《罗近溪师行实》记:
戊申,师遣人以厚幣聘楚中胡子宗正。宗正旧常以举业束脯师。师知其于《易》有得也,兹欲受之。比至,则讬疾杜门,寝食不相临。及有所扣,漫不为应。师曰:“我知之矣。”遂执贄愿为弟子。[5]835
按曹胤儒记,罗汝芳嘉靖戊申(1548年)学《易》胡子宗正之时,即执弟子礼。且按如近溪自己所说:
予早年未遇真师,亦儘是把这工夫去做,亦喜其说为得《易经》之蕴。后弱冠遇人教以讲《易》须先乾坤,乾坤须先复,乾坤二卦,虽不相离,而不可相并,六十卦皆是此意。[5]279
据罗汝芳此说,其早年所从非“真师”,直至学《易》于他人,方才遇得。嘉靖戊申年(1548),罗汝芳三十四岁,该时间段之前,罗汝芳嘉靖庚子(1540年)拜师颜钧,按此分析,近溪认可的“真师”便是胡子宗正,颜山农原不在其列。
排除形式方面的考虑,从思想传承上讲,近溪立学其高度融合的思想特色早已超脱泰州“大成”宗旨。即便是思想家关于“现成良知”、“当下直承”的强调,和王艮、颜钧等人对“平常日用之道”的侧重虽有相通处,但其理论基点也各自有别。更为关键的是,在对罗汝芳研究文献的辑考过程中,可以发掘,步入成熟阶段的近溪思想并没有局限在阳明学范畴内,而是最终完成了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融会贯通。近溪弟子杨起元曾作《白沙先生全集序》,云:
某自四十以前未足以窥先生藩篱,不知是集所系之重如此,四十以后从近溪罗先生学,转读兹集,乃稍窥一斑。
结合杨起元生卒年限,其四十岁正是万历丙戌(1586年)前后,杨氏既云此时从学近溪,开始读陈白沙文集,究其缘由,应是受罗汝芳影响和指引。而杨起元理解的白沙学风和罗汝芳正有相近处,因其评白沙其学:
以自然为宗,乃其静中妙悟,不由师傅云,其言曰:“天自信,天地自信也,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牛自为牛,马自为马,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呜呼,尽之矣。至于进退辞受之际,截然不苟纲常伦理之间,蔼然太和。形与性合,人与天侔……甲申乙酉之间,议先生从祀……中丞赵麟阳先生①扬起元:《重刻杨复所家藏文集》卷二,第577-578页。携先生遗书,在署速梓,而出之观者始心服,而议遂定。嗟夫,道之兴废存亡岂不以人哉!②赵麟阳,即赵锦(1516—1591),字元朴,号麟阳,浙江余姚人。与罗汝芳同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万历癸 酉(1573年)罗汝芳得补东昌,赵氏曾为其打抱不平,云:“奈何促贤者出,仅以郡劳之!”详见罗怀智《罗明德公本传》《罗汝芳集》第830页。
杨起元对白沙学的领悟,某种程度上和近溪对“信性任命”、随顺自然之道的宣扬,正有相通处。再者,杨起元又有致管东溟一书,信中道:
我朝学问,自白沙、阳明二先生而来,至于先师,始会合要旨,取法孔颜,而以明德亲民为至善。今曰此不可学,则又将何学哉?③《重刻杨复所家藏文集》第二卷,第689页。
杨起元作为罗汝芳高足弟子,向来以续衍宗脉为己任,此处竟有关于明德夫子融汇白沙、阳明之学的主张,可以推知,在杨氏看来,近溪晚年思想成熟时期正是得二位先圣学术之精粹。除从杨起元可得线索之外,罗汝芳另一重要弟子的詹事讲曾与罗汝芳明确讨教过学术真脉的问题,详见詹事讲《叙罗近师集后》,在得近溪说明后,至其督学南畿即“上封事,首列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圣庙”[6]。就明代思想史的整体发展脉络而言,阳明学与白沙学得以趋同一致的根本理论基点,实在对“性”体的共同关注,对“自然之学”的分殊践行。罗汝芳正是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宗“性”主张,“归宗性地”的前提下践履“明德亲民”之道,同时侧重順适自然的“默识”工夫,最终实现了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融会贯通。
2.“公珍”与“自用”:罗汝芳与儒释道关系新探
作为中晚明江右思想家,罗汝芳一生的佛道因缘尤其深厚。以往研究中,有学者曾作专文详述罗汝芳自幼时至耄耋之年于佛学的涉猎,其中提及罗汝芳幼时诵读《法华》,居官宁国修缮佛塔诸例。综合前人整理成果,我们认为相关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一者,脱离社会环境、地域风俗的考虑,强项立案;二者,缺乏对罗汝芳与僧道交游的详实考证;三者,关于罗汝芳二氏之交,尚缺深层探索和特色分析。从第一方面讲,我们之所以认为对罗汝芳的“杂禅”甚至“狂禅”之称有言过其辞之嫌,原因在于中晚明阶段的理学家与佛道二氏向来不乏交游经历,进一步说,宋明理学的发展和推进原本摆脱不了对佛道之学的汲取。比如阳明心学的开创者王守仁本身于二氏之学,也始终未得“尽去枝叶”。该情形下,罗汝芳之近禅,并非仅是个人特征,乃是整个社会风气、学术思潮的风向使然。尽管如此,明余继登《淡然轩集》卷二《覆杨止菴疏》中又曾详录罗汝芳涉佛之举,言近溪子治民有讼者“则令其趺枷公庭,敛目观心学佛自慈悲为善,一时士悦之,僧道徒归之。”①参见余继登:《淡然轩集》卷二,《四库全书》集部二三零,总1291册,第796-800页。但考宁国风俗,该地据《宁国府志》记:“丧葬用佛事,至感于风水。”[7]据此,罗汝芳的行政举措及其修缮佛塔等等举动,某种程度上皆是安民、便民之举。
对罗汝芳与佛道因缘的考述,其根本问题并非是于普遍社会现象的揭示,乃是要落实到更为重要的事项上,比如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罗汝芳与婵界人士具体往来情况如何,又是如何将好佛推进新的层次?近溪具体来往的高僧中有笑岩禅师。袁中道《珂雪斋集》中载:
有学子至,商及学问事,曰今日惟郑中丞讳如壁号崑岩者,参求最切,今不幸死矣。崑岩旧与龙溪、近溪相商確,曾言及与近溪同参笑岩事,云:“某初与近溪在京师,同参笑岩。时会中多人,笑岩云:‘此会中诸人,皆可与论学,惟近溪不可与论学,以其载满也。’近溪向前礼拜,称谢教。笑岩又云:‘诸人皆不可闻此语,惟近溪可闻此语。’因留近溪宿其寺。予出寺后,思此夜决有激扬,乃潜取襆被宿于寺中,命寺僧密之,夜往临房窃听。凡两夜,所语皆凡俗事,心甚疑之。惟与近溪分手曰:‘近溪说不得的便是。’某于时若有省焉。”崑岩之言若此,一僧又言:“某初不知用工,卓师教以参话头,提父母未生前,那个是本来面目。予问卓师曰:‘未见和尚提话头,何也。’师曰:‘我提要汝知耶?’”又问予近日学问,予曰:“我生死心甚不切,学问全不得力,逐境迁流惟有愧怖而已。”[7]
关于袁中道所记罗汝芳与笑岩之交善,明人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四《规箴》也曾记曰:“罗近溪偕郑昆岩诸同志,访悦心长老。悦心遍叩之曰:诸公皆可进此道,独不敢许近溪公。愕然问故,曰:载满了。近溪大服。已谓昆岩诸公曰:此语惟近溪公能当对,诸公却不敢道。诸公皆大服。”②(明)李绍文撰《皇明世说新语》卷四,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22册,第271页。材料中提及的郑昆岩即郑汝璧,《明分省人物考》记:“郑汝璧,字良玉,号崑岩,缙云人隆庆戊辰(1568年)进士,初受刑部主事,累转郎中。”③过庭训纂:《明分省人物考》卷五十六,《明代传记丛刊》第135册,第140页。罗近溪与郑崑岩二人共同拜访的法师笑岩德宝,原名月心(悦心),法名德宝,号笑岩。罗汝芳不仅与笑岩有过交游经历,又曾为与笑岩等人有关的佛塔撰写铭文。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八记:“柳巷在西城,今西直门草厂地有此名。笑岩德宝禅师生都下,受法于玉泉明聪,万历初居西城柳巷,人罕至者。一日有梵僧来参,亚身翘袖作种种相,师以柱杖画字,随方答之,僧作礼腾空而去,弟子问:‘适来僧问何?’法师曰:‘此阿罗汉西天秘密语也。’云棲株宏曰:‘予尝遊京师,参笑岩于柳巷,败屋数椽,僧数辈而已。’其高致可想。见此塔在小西门,万历十二年立塔,铭云南布政司参政罗汝芳撰。①”作为明代禅宗临济宗高僧,笑岩法师历来与阳明学士群体多有接触,然与近溪子交善夜谈实乃罕见。
进一步讲,罗汝芳涉佛不乏自身特色。其一,与其他信从者不尽相同,近溪子不仅好佛并且拥有谈佛相契的固定群体。《云南唐中丞墓志铭》一篇中,罗汝芳自言其一生论佛相契者又有五台陆公、秋溟殷公、平泉陆公、大洲赵公、望湖吴公、济轩唐公等人。这其中每位人士与佛教之学皆有深入涉猎。比如秋溟殷公,即殷迈,其从《楞严》发悟,向有居官位然身修头陀之行之嫌。《明清进士録》载其乃“嘉靖二十年(1541)二甲六十四名进士。江苏溧阳人,字时训,号白野。由户部主事,改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隆庆时,迁江西按察使,擢四川布政使。万历时,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性恬淡寡交,非相投者,不与交往。”[9]钱谦益《列朝诗集》记:
迈字时训,南京人。嘉靖辛丑(1541年)进士,除户部主事,改南吏部。出为佥事副使,请致仕。又起原官,历布政南太仆卿,复致仕。万历初,即家起南太常卿,升礼部右侍郎,管南祭酒事。后再疏致仕。性尚玄泊,淡默寡交。少求格致之义,不得其说,参正内典,诚思静照,久之忽有省,自此皈心佛学,栖息天界寺,灰心缚禅,精持戒律,虽老禅和不能及也。华亭陆文定公(陆平泉)称其坐镇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钱宣靖,洞明宗要则杨次公、晃太傅。至其通道之笃,不言而默成,视理学诸儒不知何如也。二公外修儒行,内閟禅宗,皆为法门龙象,故文定之称殷公,其信而有征如此。[10]
由引文可证近溪友人涉佛之深,此外,钱谦益《列朝诗集》又载殷迈《牛首山阅楞严夜坐》一首,诗中即呈现了殷迈研习佛经的具体情形。
其二,罗汝芳对佛学修养有融合禅、净两派的倾向。关于罗汝芳佛教思想的归属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其基本依据集中在两则事实上:一是罗汝芳与禅界人士多有来往,二是罗汝芳与李卓吾之间关于“净土”的讨论。从前者来讲,罗汝芳对“觉悟”的强调,确与禅宗学说极相契合,据此,罗汝芳有“杂禅”之嫌。但这不意味思想家于其他佛学宗派不具关联。比如后者关系到的“净土”之争。罗汝芳对李贽大力宣讲的“西方净土”的否认,与前文言及的思想家关于“唯识”思想的汲取具有相通性,在此前提下,从净土宗的思想体系上讲,罗汝芳否定“西方净土”的必然实存,某种意义上正揭示其对“心净土”的认可,对“佛净土”的不置可否。
其三,罗汝芳对待儒释道的真实态度,实是以佛道自用,以儒学为公珍。根据上述文献整理、考辨,罗汝芳近佛涉道已是不争事实,并且这一事实贯穿近溪一生。或有人问,罗汝芳行为上对宗教事宜的涉猎,是否有违思想家晚年“复归圣学”的定断?有一种理解,或以近溪实质上是以儒学为教,以佛道自用。管东溟《续答杨少宗伯理会大事书·丁酉》即曾评近溪实乃“犹程伯子之藏身于禅宗,而发窍于圣学也。”[11]管东溟此处答复杨起元的书牍中,已经明确对罗汝芳生平论学提出重判,认为近溪子乃是践行程明道“藏身于禅宗,而发窍于圣学”的路径。某种程度上,管东溟所说启发后人,或可重新看待阳明学人士与佛道、与儒教圣学之间的切实关联。从个人修养途径的选择上来说,佛道二氏于士人并非全无益处,宋明理学的发展从二氏之学汲取的养分,毋庸置疑。然作为一位有自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发挥儒学之用,施展淑世情怀,则需要以“孝弟”之道为“公珍”。更严格的说,无论是王阳明,还是罗汝芳,其晚年都曾坦承自身于佛道二氏的沉溺,但其一生宣教布道的思想中心,仍是儒教学说。也正是就宋明理学家的切身体会和实践精神考虑,“自用”与“公珍”在得以区别对待的前提下,并无必然冲突的结局,世人的质疑和批判,往往是站在自身的政治、学术立场,以私心之见,臆度通家之志。
三、“归宗性地”:关于罗汝芳思想史地位的重判
罗汝芳宗“性”主张,或可从颜钧的评介得见一二。《明儒学案》记山农“尝曰:‘吾门人中,与罗汝芳言从性,与陈一泉言从心,余子所言,只从情耳’”[12]。此外,罗汝芳“归宗性地”观点又得证于门人邓潜谷的一则质疑。潜古云:“宋时晦菴先生意似向外,乃于无极、太极再四称是;象山先生意似向里,乃于无极、太极再四相非。近如我师归宗性地,却又以至善为圣训格言,门下独不为然,则又留心经解之最笃者也。岂非古今一异事也哉?”[9]308此处,邓潜谷以“归宗性地”一概其师之学,得到罗汝芳默认,且近溪教诲潜谷曰:“此处关键颇重,故不敢苟从,但我潜古蓄疑不放,久当沛决江河也。”[9]308罗汝芳此说实是教潜谷克服“分别”之学的偏执,从“性”体根本处融贯旁通。
1.罗汝芳“性”本位理念的确证
从罗汝芳对“归宗性地”的默认来看,其“宗性”主张尤其鲜明。事实上,阳明学对“性”体向来极为重视,但其理论起点多是建立在“心”本位之上,相应地,王阳明关于“性”的主张实为强调“心”的浑然天成。有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阳明答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13]在阳明看来,“性”之名相多样,可谓“天”、可谓“帝”、可谓“命”、可谓“心”,诠释角度不同,“性”之界定自然也有别。从“心”之发用层面来讲“性”,不仅仁、义、礼、智可作为其“表德”,即便“孝”、“忠”之类也是“性”之显露。
与阳明观点颇为不同,罗汝芳对“性”体的侧重并非落在“心”本位上。更明确地讲,罗汝芳“归宗性地”宗旨标新立异处,即在于他不仅将“性”视作“心”、“理”概念得以区分的媒介看待,却以其作为自身哲学构建的第一性存在。罗汝芳曰:“盖性之为性,乃乾坤神里,无善亦无不善,亦不善而亦无善,所谓:上天之载,声臭俱泯,而为善之至焉者也。”[9]314罗汝芳这里说到的“性之为性”,“无善亦无不善,亦不善而亦无善”,是从本体论层面将对“性”体的探讨超越伦理德性的评判,使其成为“是其所是”的自在存在。且在罗汝芳看来,“性”体具备“常在”与“浮用”二种特性。其云:“孔孟性宗,同归于善。今子悟性固常在矣,独不思善则性在时为之,而不善则亦性在时为之也。吾子以常在而主张性宗,是又安得为全善也耶?”[9]267又曰:“盖常在者,性之真体而为善;为不善者,性之浮用。体则足以运用,而用不能以运体也。试思耳之于声、目之于色,其千变万化于前者,能保其无善恶哉?是则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听之,均视之,一一更均明晓而辨别之,是则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终日终身更非物感之可变迁者也。”[9]267罗汝芳这里所说“盖常在者,性之真体而为善;为不善者,性之浮用。体则足以运用,而用不能以运体也”是谓“性”具有“体”的特征,其用或有不善,然而并不能代替其真体的至善性。近溪又认为因“物感”产生的“善”与“不善”之念,皆受控于“心思之能事”,“心思之能事”效力的发挥又全在人秉“性”而生,原本具备理智思维的能力。据此,我们认为近溪哲学体系中,“性”的“体”“用”兼具特征或可以作为近溪思想的开拓创新处给予关注。
在确立“性”本体定位的同时,罗汝芳曾多番强调“性”体的普遍有效性。有云:“尧舜止言心,而性则自汤言也。明于‘性’之一字,则‘降’之义,自明矣。尽性从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万世之民,天下万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固其生之为性,即帝之性。只此一‘降’字,汤乃为下民警之。其实,下民即上帝,如子之于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也。”[9]326这里,“性”的普遍有效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因“降”之义,“性”承“命”而生,流行不息;其二,以“性”为媒介,上帝与下民,父与子,众生平等。事实上,罗汝芳更为大胆之处,乃是在“性”本位前提下更进一步取消了“人”与“物”之间的差等关系。当门生问,人、物何以区别?近溪答曰:“世言物类莫贱于蛇,然蛇知潜修,多成蛟龙,其变化飞升,又万夫莫及矣。此无他,其性天本灵,而与人同贵也。故知悟觉在人,极为至要,能觉则蛇而可龙;不觉则人将化物,甚哉!”[9]45罗汝芳此处讲“性天本灵,而与人同贵”,强调的正是人、物皆秉“性”而生,二者差别只在能觉否。近溪又道:
人之所以独贵者,则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虽得天性生机,然只成得个山水;禽兽虽得天性生机,然只成得个禽兽;草木虽得天性生机,然只成得个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这个人来,却便心虚意妙,头圆足方,耳聪目明,手恭口止。生性虽亦同山水、禽兽、草木,而能铺张显设,平成乎山川,调用乎禽兽,裁制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为君臣之道;联合恩爱,以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为长幼之道;辨别嫌疑,以为夫妇之道;笃投信义,以为朋友之道。此则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贵之人身;以有觉之心,而弘夫无为之道体。使普天普地,俱变做条条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9]178
罗汝芳以能“觉”与否和“率性成道”作为评判“人”、“物”之别的准则,正是将理论重点落实在对理性精神和责任意志的强调上。在近溪看来,“人”与“物”皆秉性而生,然唯“大人”能以理性的态度,意志的效力,以及责任的驱使,积极对待这个世界。因此,近溪讲“觉”则为人,不“觉”则“人将化物”,是以功夫的践行结果评判人、物之分。至于他又讲“人之所以独贵者,则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是将“率性成道”作为评判“人”之尊贵的终极准则。罗汝芳用践履的标准取代概念的区分,其核心价值正在于对“责任”的侧重,而出于“责任”的担当正是道德意志的体现。就该层面来说,罗汝芳将“率性为道”界定为评判“人”之尊贵的至高条件,与康德在实践理性方面的相关主张具有一致性。康德讲:“在自然界中,每一件东西都依照规律而动,唯独理性的存在者有能力依照规律的概念,即依照原则而行动。这个能力就是意志。因为理性为出自于规律的行动所必需,所以意志就不是别的,而正是实践的理性。如果理性对意志的规定一贯正确,那么,这样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行为,正如其在客观上被视为必然的一样,在主观上也同样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意志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只选择那种,在不受偏好影响的情况下,理性认为在实践上是必然的东西,即善的东西[14]。
在康德看来,唯理性的存在者方能自觉履行“至善”的意志,于罗汝芳认为,“人”之所以为贵也正因他是世间唯一的理性存在者。据此,罗汝芳提倡“率性成道”,正是出于对道德意志践履原则的奉行,在这一思想前提下,实践成为检验人之人的核心准则,而“性”同时被揭示为万物共同具备的要素。
2.解“心”建“性”的完成
依据前文分析,罗汝芳“宗性”主张在其理论建构中具有鲜明体现。接下来需要继续追问的是,罗汝芳如何在“心”学思潮中确立“性”学根基。事实上,罗汝芳在“归宗性地”前提下从本体论、工夫论两个层面进一步实现了解“心”建“性”的过程。
(1)近溪思想对“心”本体论的消解。严格意义上讲,这一重建的过程首先需要解构“心”的本体论定位。罗汝芳解“心”建“性”主张从其“破除光景”一论即可见得。牟宗三先生曾认为罗汝芳“光景”一说实是“顺泰州派家风作真实工夫以拆穿良知本身之光景使之真流行于日用之间,而言平常、自然、洒脱与乐”[1]183。与此同时,从罗汝芳该番言论之间,更可识其本体论观点。其云:
即汉儒以来,千有余年,未有不是如此会心以误却平生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团灵物,万感万应而莫究根源,浑浑沦沦而初无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后人不省,缘此起个念头,就会生个识见,因识露个光景,便谓吾心实有如是本体,本体实有如是朗照,实有如是自在宽舒。不知此段光景原从妄起,必随妄灭。及来应事接物,还是用著天生灵妙浑沦的心,此尽在为他作主干事,他却嫌其不见光景形色,回头只去想念前段心体,甚至欲把捉终身,以为纯亦不已,望显发灵通,以为宇太天光,用力愈劳,违心愈远。兴言及此,情甚为之哀恻,奚忍明公而复蹈此弊也哉?[5]270
罗汝芳所说的“光景”近似王阳明“影响”论。阳明曾道:“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13]5阳明提及的“影响”便是指世人脱离践履的前提下的虚空念头。与阳明观点相近,罗汝芳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揭示的正是世间之事确有其本,然非一“心”可括的道理。据此,众人所识“光景”原从“妄”生,却非本然,一味捕捉“光景”之人实际是要将未被触及和不可把握的本体从可触知的东西中抽离出来。然在罗汝芳看来,本体始终是不可强行独立于经验世界之外,作为一个被观详和考察的对象呈现在现实的对立面。世人无论是通过“静观”还是借由“反省”的原则,始终无法得识本体。因静观原无力把捉,何得“光景”,而反省本身就是一个对经验世界质料进行重组和加工的过程,这一进程的最终所得仍旧是夹杂着主观认识的认知现象,依然并非事物的自在本体。在上述认知观念下,罗汝芳讲到“及来应事接物,还是用著天生灵妙浑沦的心,此尽在为他作主干事,他却嫌其不见光景形色,回头只去想念前段心体,甚至欲把捉终身,以为纯亦不已,望显发灵通,以为宇太天光,用力愈劳,违心愈远”,揭示的主题实则是“心”的“应感”效力和认知机能。
基于此,罗汝芳对“心”的感知机能的强调正是就其“用”而论。程朱理学认为“心”之“用”在于反省。在程朱看来,“心”向“理”尽可能地靠拢以至工夫纯熟,方可与“理”统一,该“心即理”的工夫路径正是延续“反省”的思考模式。该模式下,人作为认知主体,“格物”的过程即是认知的推进。从认识论出发,这一思维逻辑偏向于物理世界的探索途径。然在王阳明等思想家看来,质料的不断涌现,人的认知无非是在“逐物”,据此,陆王心学一反程朱思路,将“心”之功能理解为本体论层面的优先存在、包容万物,实则是站在主体受用的角度,宣告人对自然物的所有权。他们极力宣扬主观心灵,并且宣称“心”无所不包、无所不明,便是将客观存在的普遍之物推向为我所用的次要地位。与前人主张皆有区别,罗汝芳在“心”学思潮中,虽以“心”为“用”,但又有别于程朱。结合前文所说,近溪认为“心”的根本机能体现在意识本身的应感和认知方面,却不在于“反省”。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将罗汝芳学术宗旨命名为“心学”正基于近溪建立“宗性”主张的过程始终和解构陆王“心学”心本体论保持同步。
(2)“宗性”前提下,罗汝芳“默识”工夫理念解析。提及“默识”,要从孔子“默而识之”一语说起。朱熹注孔子“默而识之”一语时,即云:“识,记也。默识,谓不言而存诸心也。”[15]93王夫之《四书训义》注云:“盖必默,而后其识者切于己也。”[16]479典籍训诂之外,《世说新语·识鉴》曾载一例,提及善识人者为众赞叹曰“精于默识”,[17]366注者便解“默识”为“用思深秘,暗中识人的能力”[17]367。就语素构成分析,作为词汇的“默识”,“默”作为“识”的修饰成分,本质指向于“识”的一种静态模式。这种静态模式从认识论层面讲,可以“暗中领会”概之,这一训解即将“默识”一语,延伸至认识论乃至工夫论的范畴,尤其在宋明阶段。从语词的注解到工夫论的演进,宋明理学家对“默识”的强调,侧重的则是静处体认的工夫理念。宋代杨时云:
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①参见杨时:《寄翁好德其一》,龟山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25册,第277页。
杨时以上言论实则揭示了“默识”的核心特色:首先,“身体之”、“心验之”,意味“默识”的过程乃是一种内向度的体认模式;其次,“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暗示“默识”的进展需要依托静处用功;再者,“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揭示“默识”有别“口耳诵数之学”之处,即在于“默识”的过程便是“自明”、“自得”的推进,且其不借笔舌刻意而为,又是以“自然”途径,实现对“至道”的领会和体认。相较前人,罗汝芳“默识”理念其内涵又有延伸,延伸的基点正在思想家将“默识”与“性”体广大之用相接。例云:
罗近溪先生偕白下诸同志遊大中桥,睹诸往来者,无虑千百万计。近溪因指示诸同志曰:“试观此千百万人者,同此步趋,同此来往,细细观之,人人一步一趋,无少差失,个个分分明明未见確撞,性体如此广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识矣。”一友咈曰:“否否,此情识也。如此论性,相隔远矣。”友述以问耿先生,先生曰:“否否,谓此指示者非性,别求性体,此为楞严转,非能转楞严者。内典亦云:‘离识归寂,譬忘己之首,而别求首领矣。’曰‘识’,至此已乎,曰‘实识’,到此便自欲罢不能,安肯歇手。虽然,亡者东走,追者亦东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则异也,即兹来往桥上者,或访友亲师,或贸迁交易,或傍花随柳,或至淫荡邪僻者,亦谩谓一切皆是混然无别,此则默识之未真也。学先辨乎此而后可与论孔孟血脉、孔孟路径也。若以近溪此示为情识,而别求所谓无上妙理,是舍时行物生以言天,外视听言动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贯之指矣。[18]102-104
在罗汝芳理解,人人趋步同行,未曾跌撞,乃是得以“性体广大”之用,其友则不以为然,认为人的行走皆在“情识”的范畴,尚未达到“默识”的境界。质言之,后者并不认为“性”在“当下”“这等”,故人亦不能随时随刻任“性”体流行而随顺作为。之后近溪挚友耿定向以“楞严转”一语,评后者“别求性体”原已与孔孟路径愈行愈远。进一步讲,对该篇中提及的“默识”一说的理解,需要结合“情识”概念整体分析。关于“情识”,熊十力先生曾以心官之“思”言之,其云:“思者思辨,或思索、思考,皆谓之思,此理智之妙也。极万事万物之繁赜幽奥,而运之以思,无不可析其条贯,观其变化。思之功用大矣哉!心之官则思,系于日常实际生活者,情识也,非心也。情识之役于境,是系缚也,不能思也。离系而后能见心。心不为情识所障,而后思无不睿也。”[19]92熊十力先生所云启发学人,或可以“思”的不同介质,看待“识”的不同形态。比如“默识”与“情识”的区分处,即在于“境”之间的关系,前者不在“境”中,后者则系于“境”。以罗汝芳与友人之间的“默识”与“情识”之辩,从“境”的介入考虑,罗氏理解的“默识”即是暂时忽略了具体环境、及周遭客体的存在,其意识有且只是集中在行走的进行中,后者则认为人与“行走”本身都是心中有明确所想、所思,当然时时刻刻与环境相系。某种程度上讲,熊十力先生的诠释为问题的诠释,提供了一条切实有效的方法,但也同时存在缺漏。因罗汝芳以“默识”为“性体广大之用”,一者具有任“性”作为的要素,二者也喻示行动中的人,其意识的指向问题。具体来说,近溪子之所以认为“默识”乃是“性”体之用,本质上即是认定,路人在行走时刻并没有运用心思之智,那么这时人的主体意识就有两种存在可能:与“良知”合一;暂处别处。就前者而言,乃是与陈白沙、湛若水等人的体认工夫,与王阳明“良知良能”等说并无异处,然就后者来看,其中涉及的意识指向论题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意识的指向论题,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在《社会、经济和哲学》一书中,也提及“默识”一说,或可为我们关于罗汝芳关于“默识”的理解,具有一定启发之用。波兰尼“默识”(tacit knowing)理论的界定前提,是对“辅助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与“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的发掘。为说明两种意识类别,波兰尼以手指指向画面为例,讲到“我们附带地意识到指着的手指和集中的意识到手指指向的对象”[20]352,据此,前者即称作“辅助意识”,后者相应地便是“集中意识”,从“辅助意识”过度至“集中意识”是一个连贯的整合的过程,这一整合的过程即是在默识推论中进行,而非借助引证立据或确立三段论演绎。依据波兰尼默识理论,如艺术赏析过程中,外观的改变,是默识整合的通常伴随物,日常行为中,经验的自觉生效则可看作默识整合的随顺机能。这一随顺机能往往被中国哲学诠释为性体的自然流行。罗汝芳对“行走”的默识定义便是由此而来。
继续我们的追问,罗汝芳以“默识”界定“行走”本身,以“性体的自然流行”诠释这种默识行为,那么在思想家看来,这种具备整合性质的默识行为便不可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下意识”。原因在于,默识的发生是在辅助意识转向集中意识的过度中。质言之,罗汝芳认为千千万万之人在行走的当时,虽是双脚在移动,但浑然不觉,此次此刻,人们的心灵寓居在目标事项上,至于移动的双脚暂时处于被搁置的状态,一旦当人们将视线转移至双脚,辅助意识被有意关注,它的意义即消解。这便是波兰尼所说的,“当我们将注意中心从默识整合的有意义结果中移开,并对准辅助物的时候,他们的整合就消失了”[20]354。就这一层面讲,条件反射式的“下意识”其发生机能则不然,只要条件生成,无关乎人的意志和关注度,“下意识”一样可以发生。
从宋明理学的整体视域考虑,罗汝芳“默识”理论的提出,即是从性体的自然流行展开。在此基础上,关于“赤子之心”关于“当下直承”,本质上皆是在默识整合前提下延伸而来。具体来讲,罗汝芳“默识”主张强调两方面内容。其一便是默识模式的整合意义。这一整合因素侧重的正是一种不勉而中、勿忘勿助的工夫路径。这一路径和白沙“自然”之学具有相通处。关于该理念的认知,或可借助对比研究的方法予以揭示。程朱理学力图将“仁”的信仰清晰地根植于人心之中,并且以“礼”的演绎,明确其意义。根据这一理路,程朱“存天理,灭人欲”观点,虽并非主张格除所有正当的、本能的欲念,但仍有克制自然人性的嫌疑。其中原因就在此一“存”字,已经是对倚赖默识模式的整合原则的拒斥。至于王阳明重提“良知”,则是在以“良知”取代“天理”。费纬《圣宗集要》卷六《王守仁》载:
诛逆濠,后居南昌,始揭致良知之学,曰:“圣人之学,心学也。宋儒以知识为知,故须博闻强记以为知;既知矣,乃行亦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圣贤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于是举《孟子》所谓“良知”者,合之《大学》“致知”,曰“致良知”,以真知即是行,以心悟为格物,以天理为良知。[21]943-944
费纬所记阳明始揭“致良知”之学时,既以“真知即是行,以心悟为格物,以天理为良知”作根蒂,再结合阳明又曾曰:“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三《新建侯文成先生世家》)[21]969王阳明从本体论、知识论两个层面将“良知”以“天理”相对待,“致良知”便不仅具备心力反省的指向,并且同时意味“穷理”的可能。
比较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对“天理”、对“良知”的强调和展开,罗汝芳向有“破除光景”的观点,且曾言“天地生人原是一团灵物,万感万应而莫究根源,浑浑沦沦而初无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5]27。按罗汝芳对阳明学心本体论的上述认知,不以“头脑”立学,原则上便揭示了他所理解的本体并非仅仅是先验的、超越的,并且内隐于具体的、生动的生活实践之中。这一“体”“用”兼顾的特征,正如牟宗三先生认为,“天理”抑或“良知”,并非“孤悬在那里的先验性和超越性,而是混融于真实生命中的内在的先验性,具体的超越性。若说它是体,它是‘全体在用’的体;若说它是用,它是‘全用在体’的用”[22]100。本体既非独体,相对应的,罗汝芳在工夫论层面以随顺自然为宗旨,原则上与其“默识”主张正相契合。除此之外,建立在“默识”主张基础之上,罗汝芳“捧茶童子”一说也得借此得以诠释。无论是“行走”还是“捧茶”,相关行动之所以浑然天成,之所以不费人力,都因人们借助于一种整体的关注,其意识并不在某个单项的动作之上。童子是在捧茶,他的心灵寓居在这一事件中,但不在移动的脚步上,不在抬起的双手上,更不在载水的茶杯上,他的目光,他的关注,全全因集中意识兼顾整体,脚、手、茶杯是他辅助意识的介质,而茶杯也因此成为他身体的一种延续。此刻的童子,人在行动中,其浑然不觉,正因他“身”与“心”构成了“辅助意识”与“集中意识”的默契关系。于此,依托默识整合理论,童子捧茶时刻,“身”“心”得以合一,行动成为意识的延续。
(3)罗汝芳宗“性”主张的时代意义。罗汝芳宗“性”主张某种程度上启迪世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一追求从根本上讲,即是人本意识的觉醒。关于“平等”一说,儒释道三教之中,佛教于万物皆空的基础上论“众生平等”,道家在取消物、我相对的前提下,提出“一齐”主张,罗汝芳站在儒家道德主义立场,以道德理性的先天综合特性和实践可能,消解了人与物之间的根本区分,某种程度上也抹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之别。比如近溪有“下民即上帝”一说:
尧舜止言心,而性则自汤言也。明于“性”之一字,则降之义,自明矣。盖性从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万世之民,天下万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固其生之为性,即帝之性。只此一“降”字,汤乃为下民警之。其实,下民即上帝,如子之于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也。[5]326
当然,此处近溪论“下民即上帝”是就人之“性”原就统率于天性,换言之,“上帝”之心即圣人之心即生民之心,从这一视角出发,不仅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并且“下民”与“上帝”在诞生之处,性体一致、平等。由此可见,如果说近溪言“贵下贱”乃是沿袭孟子民本主张,那么其“下民即上帝”一说则是从心性本体论上为孟子之论寻到了理论根基。与近溪“贵下贱”主张相近,同时期的王龙溪则曰“厚其下”,但就两人理论出发点切入,“二溪”各有侧重。王龙溪《剥·大象》一篇云:“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句下注曰:“山高而反附于地,圮,剥之象也。观剥之象,以厚其下而安其居也。民犹地也,君犹山也。地惟厚,故载华岳而不重;民惟厚,故奠邦国而无危。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23]660据此,近溪讲“贵下贱”其认知前提,乃是“上”与“下”之间在“性”体方面原本一致,在“成圣”理论上原本共同,因此“贵下贱”即是以平等待之;然龙溪言“民犹地也,君犹山也”,又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实是在严格等级制度前提下,在强调“君统”的同时侧重“君”、“民”辅车相依之关系定位。也正因如此,王龙溪又有曰:“上天下泽,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为典礼,使各安其分,以定民之志。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则上下相逐于崇高侈肆,天下不可得而治也。”[23]656此外又道:
君子节天下有道,曰:“制数度,议德行”。“制数度”,以政事而言谓尊卑礼命之轻重;“议德行”,以人才而言,谓大小名位之优劣。凡舆服宫室,立为科条以制之,莫不有多寡隆杀之等,使贱者不得以踰贵,卑者不得以踰尊,所以防其僭拟凌逼之渐。凡名器禄秩设为品级以议之,莫不有黜陟迁调之典,使德之大者居上,德之小者处下,所以防其玷混滥冑之弊。泽上有水,不有以防之,将浸淫渀荡无所不至。节也者,人才政事之大防也。先儒以商度求中节为议德行,似非本旨。[23]673
王龙溪这里引证的“制数度,议德行”几乎全全以政事“尊卑礼命之轻重”展开,因此龙溪说“使贱者不得以踰贵,卑者不得以踰尊,所以防其僭拟凌逼之渐”尤其可见其以《易经》论治世的出发点实在于严格分层的等级意识和正统观念。
通过以上比较研究,我们对罗汝芳宗“性”观念或有更深层面的理解。一直以来,学界多以罗汝芳继承颜钧“制欲非体仁”路径,探讨近溪立学于当时乃至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但由其宗“性”主张考虑,思想家真正启迪他人的乃在于其道德主义立场及自由平等之意识。就前者来说,“率性成道”乃是推崇德性得最佳表达;从后者展开,汤显祖作为罗汝芳门人,其戏曲创作代表作《牡丹亭》塑造的人物无一不与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相关,排除原有故事情节的因素,即便是红娘,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力。因此,从晚明文学的整体视域考察,与其说是由“情”到“欲”的解放,不如说是世人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已然突破了传统伦理的枷锁。
四、结语
在史、论并重方法论的导引下,我们对罗汝芳生平思想的研究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就其“善习古道”的立学初衷来说,罗汝芳对先秦儒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都有继承、扬弃的具体理据。
第二,从思想根基层面展开,罗汝芳立学宗旨实在发挥心体之用,强调“率性”之能,以近溪宗“性”主张作为探讨中心,罗汝芳于明代心学,尤其是阳明学术确有开拓,但其真正精神,则侧重在道德理性的践履方面,正由思想家的道德主义立场出发,罗汝芳关于“性”与“命”、与“情”之间关系界定,都有新说,且在该前提下,罗汝芳进一步消解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等级区分,同时默认了儒家“仁爱”和墨氏“兼爱”的异曲同工之处。这一突破,严格来说,已经逾越传统儒学理路,反与佛氏推崇众生平等具有相通之处。且罗汝芳此论再结合其“能己”之说,某种程度上讲,正为当时知识界人士以及普通民众关于自我解脱和平等意识的追求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时人乃至清初人士对其展开的质疑和批判留下话柄。于此来说,当时诸儒以及清初朱彝尊等人以近佛好道之嫌,否定罗汝芳学术建树,事实上也仅是表象,真正原因实是罗汝芳之“勇猛”已逾越儒学正统的根基。
第三,罗汝芳在学术主张上的突破创新,就他本人的哲学努力方向而言,即为成就浑融一贯之学。从这一逻辑起点考虑,罗汝芳在《易》学领域,对宋明以来先天《易》学的推崇,对以“身”言《易》、以“己”论《易》、以“心”解《易》的融会贯通,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近溪子的思想融合意识。与之相应地,罗汝芳一生与佛道羽仙之间的频繁往来,及其对佛、道学术的汲取、对二氏教规的践行,也验证了管东溟给以近溪子“以身所践之孝弟慈为与人之公珍,而以心所注之净土为自用之家珍”的评介。严格来说,管氏所评不无依据,但罗汝芳引二氏“自用”,证儒学“公珍”又有何过失?一者,不足以“狂禅”评判,二者,尊重自身受用的同时,亦不违“仁”道。
第四,关于罗汝芳研究以往诸家之说的重新考察,亟须我们提供研究结论。通过系统分析,笔者认为,罗汝芳论学真正精神及其思想践行宗旨,可用“信己”“安常”定断。“信己”与“能己”相承,宣扬一种关于抽象的、精神自我的追求;“安常”与“随顺”契合,侧重的则是不勉而中的工夫路径和洒脱自然的心性态度。应该说,罗汝芳“信己”、“安常”主张对当今社会关于塑造君子人格的提倡,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设想,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第五,综合以上文献发掘和理论分析,近溪治学多由自得,且其思想的复杂融合性质,非简单范畴能够涵盖,正因如此,近溪一脉的衰落也与之相关。从学术传承的角度讲,罗汝芳弟子中,得其真传者屈指可数,且不论邓潜谷、焦澹园等人关于近溪“能己”一论的质疑,翟秋潭等人在二氏之学层面的偏执一端,即便是杨起元,罗汝芳去逝后,扬起元先后拜师周柳塘、私淑李卓吾,又经管东溟多番规劝,最终偏离罗汝芳学术宗旨,至此,近溪一脉几绝矣。
参照以上五点内容,罗汝芳研究尚有待持续推进。而推进的途径,一者需要借助史、论并重的方法论原则;二者需要突破惯性的思维路径,从更开阔的哲学视域,追问罗汝芳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以及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所面临的生存困惑,以及他试图给出解答的哲学论题。唯有以上问题得解之后,一名思想家方能够以生动翔实的面貌得以再现。
[1]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183.
[2]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52.
[3]吴震.泰州学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19.
[4]龚鹏程.晚明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8.
[5](明)罗汝芳.罗汝芳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938.
[6](清)张謇.中国方志丛书[M].王豫熙修.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888:735.
[7]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888:337.
[8](明)袁中道.遊居柿録(卷三)[M].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54.
[9]潘荣胜.明清进士録[M].北京:中华书局,2006:422.
[10](清)钱谦益.列朝诗集(第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6382-6383.
[11]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378
[12](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8:703.
[1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7-18.
[14](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23-24.
[1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93.
[16](清)王夫之.四书训义:上(〈船山全书〉第七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0:479.
[17]刘义庆.世说新语译注·识鉴(第七)[M].张万起,刘尚慈,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366.
[18]刘元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70册)[M].谢秉谦补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102-104.
[19]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一)[M].上海:上海书店,2007:92.
[20](英)迈克尔·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M].彭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52.
[21]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43-944.
[2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0.
[23]王畿.王畿集(附录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660.
猜你喜欢
--(第一夜 新婚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