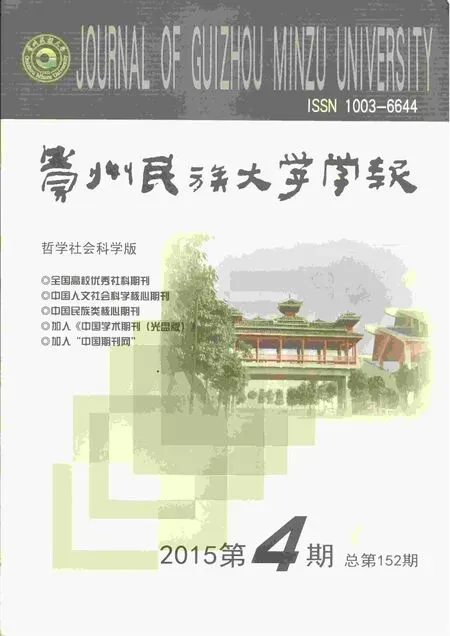《弹歌》考论①
2015-03-20杨德春
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断竹,续竹”考
《吴越春秋》云:
于是,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1]P152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五〇云: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云:“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质,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断竹,属木,飞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鸟狐之残也。”[2]P1612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五五云: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曰:“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断竹,属木,飞土,逐肉。’”[3]P3352
首先,陈音,楚人也。陈音所言之弩生于弓而弓生于弹之历史,就是强调弹是弓、弩产生的基础,而弹又是楚人创造的,既然弹是最早的弹射武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造弹之时必然选择具有天然弹性之材料,竹之天然弹性明显优于木之天然弹性,故最早之造弹之地必是南方产竹之地,故古者之弹歌必是断竹续竹。
其次,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这是由于神农、皇帝活动之区域以产木为主,木易得,故以木制弓矢。以木制弓矢显然是模仿以竹制弓矢,故主要活动于北方的神农、皇帝不可能是竹制弓矢的发明者,即主要活动于北方的神农、皇帝不可能是弓矢的发明者。
再次,《弹歌》开篇已言断竹,这是用竹制弓矢,其下所言必与竹有关,而不可能言木,若其下言属木,则与断竹前后失去关联。另外,竹之改为木,实为后世之妄人为避免二竹字之重出,而妄改为木字,古诗不避重出,而近诗力避之,重出之字,以近义之字置换之。古今诗歌演变之势可证后世之妄人力避二竹字之重出,近义之字,多不押韵,而妄改为木字,以求即近义又押韵,竟不知竹木前后失去关联,以至于最终露出马脚。
“逐害”考
《吴越春秋》云:
于是,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4]P152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五〇云: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云:“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质,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断竹,属木,飞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鸟狐之残也。”[5]P1612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五五云: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曰:“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断竹,属木,飞土,逐肉。’”[6]P3352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五〇所引《吴越春秋》与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五五所引《吴越春秋》文字略有出入,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五〇所引《吴越春秋》和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五五所引《吴越春秋》与今本《吴越春秋》颇有出入,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五〇和卷七五五所引《吴越春秋》显系摘要,而非原文引用。摘要既经《太平御览》编者修改,则其所录之《弹歌》不可信。
陈音所谓遂令死者不犯鸟狐之残也,残者,害也。陈音所言皆为禽兽残害父母之尸体或曰肉身,故其后所引之诗必为逐害。此其一也。
陈音明言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守之即守父母之尸体或曰肉身,若古人歌之曰逐肉,则必然擅离职守,追逐已被射伤之野兽,如此则父母之尸体或曰肉身必遭其它禽兽之残害,不仅失去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而作弹以守之之宗旨,而且也使陈音之所言前后矛盾,故所逐必为害而绝非肉。此其二也。
陈音明言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守之即守父母之尸体或曰肉身,食父母之尸体或曰肉身者,不仅有走兽,尚有飞禽。若古人歌之曰逐肉,已被射伤之走兽,犹可追逐之,已被射伤之飞禽,焉可追逐之?可证逐肉不通,必为逐害之误。既然逐害正确,则逐字必不训追逐,而当训驱逐、驱赶,如此训诂方可与“作弹以守之”相一致。此其三也。
古诗不求必押韵,而近诗力求之,不押韵之字,以近义之字置换之。古今诗歌演变之势可证后世之妄人力求押韵,而以押韵之肉字置换不押韵之害字,肉害字形相差甚远,擅改原文,难售其奸,遂书以字形相近之宍字,冒充古字,竟不知此宍字非为古字,实乃晚出之俗字,明方以智《通雅》卷十八身体云:“《古乐苑》载《吴越春秋》古孝子《弹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但从宀从六,或古籀之形讹耶?诸书不收,惟孙愐收之,以为俗作宍。颜元孙亦曰:‘宍,俗肉字。’”[7]P857-394古人断不会有此宍字,自然也就无从用之。后世之妄人亦竟不知此举致使前后矛盾、漏洞频出,以至于最终露出马脚。此其四也。
从写作诗歌之思维来看,当作害,写作诗歌之思维以形象思维为基本特点,害指害虫,即残害父母之尸体或曰肉身之禽兽,害是具体名词而非抽象名词。若为肉字,肉之抽象性明显高于害字,禽兽是肉,父母之尸体或曰肉身也是肉,自己也是肉,如此抽象之肉如何逐?具体逐哪一种肉?故从写作诗歌之思维来看绝不可能是肉字。此其五也。
在古代汉语中以肉释禽兽没有其他例证,即以肉释禽兽没有训诂学上的依据,故不可以肉释禽兽。此其六也。
冯惟讷、梅鼎祚之时代的《吴越春秋》版本就作“逐害”,明冯惟讷《古诗纪卷一·古逸第一·歌上》:“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注曰)宍古肉字。今《吴越春秋》作害,非。”四库全书本《吴越春秋》亦作“逐害”。明梅鼎祚《古乐苑·古歌辞》:“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注曰)续一作属;宍古肉字。今《吴越春秋》作害,非。”此其七也。
“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之“故”表明叙事已经完结,在“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的过程中没有唱歌,“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断句有误,应该作“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意为所以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说的就是此事,显然,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是后人所歌,所表现的必然是“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则必然是作“害”不作“肉”。此其八也。
《弹歌》非为黄世歌考
《文心雕龙·通变》:“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8]P198
《文心雕龙·章句》:“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9]P219
《文心雕龙·通变》和《文心雕龙·章句》均以《弹歌》为黄世之歌,其说没有任何依据,不可信。
《吴越春秋》云:
于是,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10]P152
《吴越春秋》明确记载,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并未记载古者即黄世。
《吴越春秋》明确记载,先有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于是后有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可见,《弹歌》非为黄世之歌,《弹歌》的产生不仅在黄世之前,而且在神农之前,故以《弹歌》为黄世之歌之说法不能成立。
《吴越春秋》明确记载,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是中国很早的原始社会的人,实际上,炎帝、黄帝之时代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是处在原始社会之晚期,已越过血缘群婚制阶段而发展到族外婚制阶段。传说中的炎、黄事迹,更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已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并明显地向对偶婚及一夫一妻制发展。但中华民族的前身的历史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之久,其中原始社会很长很长,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仅仅反映了原始社会最短最近的一个阶段。
传说中的神农要早于炎帝、黄帝之时代,而《弹歌》的产生不仅在黄世之前,而且在神农之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弹歌》的产生如此之早以至于《弹歌》的语言文字形式和艺术形式与《弹歌》的产生年代是否相符合的问题。
北京房山的山顶洞人文化遗址明显分为下室和上室两部分,下室发现青年女性、中年女性和老年男性之头骨各一个,在一骨盆和股骨周围发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还有介壳等装饰品,基本上可以认定山顶洞的下室当是墓地,并且是我国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墓地。山顶洞人活动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将死者埋葬,并且以赤铁矿粉末和矿石及少量装饰品饰终。
《弹歌》的内容反映的情况是尚未将死者埋葬,其反映的年代只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即在山顶洞人之前。山顶洞人活动时间一般认为约在距今五万年前,《弹歌》的内容所反映的情况则在距今五万年前之前。这样就产生了《弹歌》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时间矛盾。
《弹歌》的语言文字形式是整齐的四个动宾结构,这是语言文字发展的高级形式之一,一般认为在语言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没有词类之分的,也不可能达到语言文字形式的整齐划一。《弹歌》的语言文字形式与《弹歌》可能产生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推测不相符合。
《弹歌》的语言文字形式是整齐的四个动宾结构,而且《弹歌》的整齐的四个动宾结构还可以组成两个整齐的四言句式,《弹歌》的所谓二言极为整齐划一,与《诗经》中的二言句有本质的区别,《诗经》中的二言句不可能组成整齐的四言句式,这说明《弹歌》所具有的既是整齐的四个动宾结构又是整齐的两个四言句式只能是借鉴了《诗经》的语言文字形式,即《弹歌》的语言文字形式产生于《诗经》之后。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从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就创造了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根据绝大多数史学家的意见,我国大约在夏代进入阶级社会,所以汉字形成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11]P25-26
所谓的甲骨文中已有老、考二字,老字见于铁76·3,考字见于前7·35·2,老、考二字皆可以通孝,但有了孝的通假字,不能说明孝的观念已经产生。关于孝产生的时间问题不当以孝的通假字之出现为准,而当以孝字之出现为准。现在所谓的甲骨文未见孝字,而所谓的金文始见孝字,《弹歌》所反映的主要是孝的观念,《弹歌》的产生不会早于周代。
《吴越春秋》所谓“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之“故”表明叙事已经完结,在“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的过程中没有唱歌,“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断句有误,应该作“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意为所以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说的就是此事,显然,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是后人所歌,而且《弹歌》的产生不会早于周代。
由此可见,野外裸葬之年代当早于北京房山山顶洞人于下洞墓地埋葬死者并以赤铁矿粉末和不少装饰品饰终之年代,即野外裸葬之年代当早于距今五万年前之旧石器时代晚期。而《弹歌》的语言形式和所反映的孝的观念却又不可能早于周代,即不可能早于《诗经》的语言形式之前。如此则《弹歌》只能是后世追记或臆测古代之情况而形成之作品,而且《弹歌》的产生不会早于周代。
褚斌杰关于《弹歌》的高论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
如汉代人赵晔所著《吴越春秋》载有一首《弹歌》,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它采用二字一句的形式,内容是写用弹(土丸)逐击野兽,是记述远古人狩猎活动的。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
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反映了渔猎时代人民的劳动生活,描写了他们砍竹、接竹,制造出狩猎工具,然后用弹丸去追捕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短歌中流露着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诗,很简短,但浑朴、自然,有很强的概括力,是一支原始型的优秀民谣。[12]P37-38
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
但就其内容和形式看,无疑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人民的劳动生活,描写了他们砍竹、接竹,制造出狩猎工具,然后用弹丸去追捕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短歌中流露着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13]P19
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
从其内容和形式看,无疑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人民的劳动生活,描写了他们砍竹、接竹,制造出狩猎工具,然后用弹丸去追捕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这首短歌无疑流露着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14]P24
优秀与否只有比较方能知晓,褚斌杰说《弹歌》是一支原始型的优秀民谣,那么,原始型的不优秀的民谣是什么样子的,恐怕难以考证。
原始人的生活条件远不如今人,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今人有冰箱,可以储存食物,原始人只能是现打现吃,打猎物多了放不住,只能吃腐肉,其一不好吃,其二容易得病。由此可见,原始人绝没有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够吃即可。褚斌杰以自己的无限欲望度原始人的淳朴之心,表现出褚斌杰思维的非缜密性。如此则褚斌杰是怎么从《弹歌》中看出原始人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的?笔者细玩细按《弹歌》,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弹歌》中有原始人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因此,褚斌杰的上述结论难以成立。
褚斌杰说《弹歌》中流露着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褚斌杰是怎么看出《弹歌》中流露着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的,《吴越春秋》以《弹歌》为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而作弹以守之,这是悲歌,何来自豪感和喜悦?退一万步讲,就算《弹歌》是所谓的猎歌,从字面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弹歌》中有自豪感和喜悦,可见,《弹歌》中有自豪感和喜悦的结论存在疑问。
另外,褚斌杰说渔猎时代的人民用弹丸去追捕猎物,用狗可以去追捕猎物,用弹丸如何去追捕猎物呢?
褚斌杰关于《弹歌》的高论特别值得学术界反思。
几部中国文学史所谓的《弹歌》主题
林庚《中国文学史》:
“诗经为生活中最古的一声歌唱”,林庚《中国文学史》:“诗经这部书一向被人奉为经典;它彷彿是这民族最古的一声歌唱,便从此唤醒了人们的爱好。诗经有一个序,乃是东汉卫宏所作,……”[15]P21
林庚《中国文学史》于中华民国由国立厦门大学出版,书中未提及《弹歌》,以《诗经》为生活中最古的一声歌唱,这个生活是人类生活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林庚未明言,就当是中国人的生活中最古的一声歌唱,如此则《弹歌》就不是中国人的生活中最古的一声歌唱。林庚《中国文学史》接下来又说《诗经》彷彿是这民族最古的一声歌唱,林庚自己都迷迷糊糊,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林庚《中国文学史》说《诗经》有一个序,一个序是何意思?又是如何而来?今本《毛诗》每一篇前有一小序,第一篇小序之后有一篇大序,林庚《中国文学史》说《诗经》有一个序,到底是哪个序?林庚就写这样的东西!林庚说诗经这部书一向被人奉为经典,林庚说一向就是不正确的,一般认为《诗经》在汉代被尊为经,我认为《诗经》是在战国后期被尊为经。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
《吴越春秋》又载有相传为黄帝时弹歌的歌辞: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
这歌辞很古朴,虽然记录下来较晚,当正是古代打野兽的歌。[16]P1-2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
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指禽兽)。
从前有人认为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的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回忆了几乎全部的狩猎过程,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17]P16-17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一:
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指禽兽)。
从前有人认为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的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回忆了几乎全部的狩猎过程,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18]P19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卷:“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19]P25
《弹歌》的主题不是猎歌,飞土之土不可能杀伤禽兽,飞石方能杀伤禽兽。飞土的目的不是杀伤禽兽,而是驱赶禽兽,飞土本身就证明《弹歌》的主题不是猎歌,而是孝子驱赶禽兽的悲歌。
林庚在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没有提到《弹歌》,解放后,林庚修改《中国文学史》,其《中国文学简史》以《弹歌》为打野兽的歌,即猎歌。游国恩、褚斌杰、袁行霈也以《弹歌》为猎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认为文学起源于劳动,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劳动者的作品很难流传下来。要编写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只要把劳动者的作品很难流传下来这个问题讲清楚,是完全能够得到理解的,根本不需要指鹿为马地硬要伪造出来一首劳动者的作品。可见,林庚、游国恩、褚斌杰、袁行霈等人的观点值得质疑。
林庚、游国恩、褚斌杰、袁行霈竟不知宍非为古肉字,实乃晚出之俗字,明方以智《通雅》卷十八身体云:“《古乐苑》载《吴越春秋》古孝子《弹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但从宀从六,或古籀之形讹耶?诸书不收,惟孙愐收之,以为俗作宍。颜元孙亦曰:‘宍,俗肉字。’”[20]P857-394林庚、游国恩、褚斌杰、袁行霈等的观点难以成立。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关于《弹歌》主题的错误论述值得学术界反思。
[1][4][10]周生春. 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3][5][6]李昉等.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7][20]方以智. 通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9]王利器. 文心雕龙校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2]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3]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4]褚斌杰,谭家健. 先秦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5]林庚. 中国文学史[M]. 厦门:国立厦门大学,1947.
[16]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7]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8]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