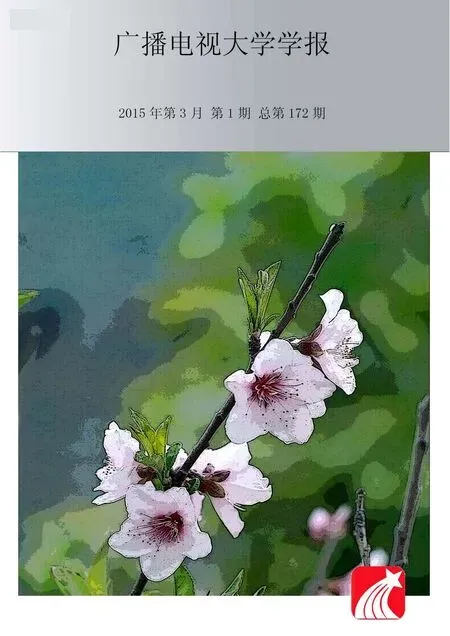匈奴的宗教与信仰体系
2015-03-20郭大地
郭大地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匈奴的宗教与信仰体系
郭大地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秦汉时期,匈奴形成了完整有序的宗教与信仰体系:以信“天”为核心的自然崇拜体系,相信灵魂不灭与祖先崇拜,迷信鬼神、偶像崇拜并崇尚勇武,习惯盟誓,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多行使巫术,巫履行宗教行为外兼及医之职能。该体系对匈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有利于其统治者维护统治,增强本族凝聚力,是匈奴游牧政权的精神支柱和匈奴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匈奴;宗教与信仰体系;游牧政权;政治和经济意义;精神支柱;民族文化构成
匈奴是秦汉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广泛影响。学界关于匈奴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习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是就其信仰体系和宗教的研究,仍然属于薄弱环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使得匈奴人形成独特的生活与风俗习惯,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信仰体系与宗教。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的一种社会意识,并随之而产生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2]P37宗教与信仰体系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匈奴史作为中国古代史组成部分,其信仰体系与宗教也需要进一步探究。本文以史料与考古资料为依据,对匈奴的信仰体系与宗教做初步探讨。
一、以信“天”为核心的自然崇拜体系
秦汉时期,匈奴人生活在以今内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广大地域。内蒙古高原、蒙古高原是内陆高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降水较少,植被以草地为主,在这一区域活动的古代民族也就形成了“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3]P2879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畜群是主要财富,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4]P105因此,其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流动性、分散性与不稳定性。[5]P105-107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的依赖性非常强,改造自然的能力却十分有限,从而形成了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内容,以信“天”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1.匈奴的宗教信仰体系为多神崇拜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廷,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3]P2892由此可见,匈奴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与仪式。其祭拜的对象包括祖先,天地,鬼神。在《史记索引》中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3]P2892可见匈奴人还崇拜有“龙神”等神仙。这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是有区别的,如犹太教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说:“(耶和华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外再没有真神”。[2]P215一神教信仰的神具有独一性,排他性,而多神信仰则不然。这足以证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是多神的,而非一神信仰,并与一神信仰有着明显而本质的区别。
2.匈奴的宗教信仰核心为“天”
前文所述,匈奴的信仰是多神的,但匈奴信仰的众多神灵中,核心神灵是“天”。“天”在匈奴的信仰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最明显的是:“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5]P3751可见单于是以天之子自称的,如此自称也象征着其对天的尊崇。又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匈奴俗,岁有三月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6]P2944可见“天”或“天神”是匈奴祭祀的主要神灵。在匈奴单于给汉文帝的信中说:“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3]P2896可见匈奴单于自称自己为“天所立”。其对天神的崇拜与君权神授思想,也从侧面证明了天神在匈奴信仰体系中的崇高地位。而在狐鹿姑单于给汉武帝的信中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5〕P3780匈奴人以“天之骄子”自居。匈奴军臣单于在武帝元光二年马邑之战中,由于汉朝的一名尉史告密,因此脱险。脱险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5〕P2905可见单于将告密的尉史视做天派来的使者,尉史告密助他脱险完全是“天赐”的。对于攻打月氏人取得的胜利,单于也称为是“以天之福”〔3〕P2896。由此可见,“天”是匈奴人信仰体系的核心。
3.匈奴的宗教信仰体系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内容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3〕P2879。“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3〕 P2879“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3〕 P2915可见,匈奴人的衣食住行皆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正是对大自然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匈奴产生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信仰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7〕 P354除了对“天”的崇拜外,匈奴人还崇拜日、月、地等自然物。“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3〕 P2892可见匈奴人是崇拜日、月的。文献记载说匈奴人还“拜天地”,可知匈奴人是将地与天同拜,地也是匈奴人崇拜的神明。单于就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3〕 P2899更证明了虽然地、日、月列为天之后,但是也是匈奴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国考古学者道尔吉苏荣发现在蒙古国呼尼河第12号匈奴墓北面墙壁上钉着饰有日、月的金片,认为这是匈奴崇拜日、月的物证。〔8〕 P271自然景观的变化,往往影响着匈奴人的军事行动。所谓“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3〕 P2892可见匈奴人将月亮盛亏作为凶吉的标志,并伴有对星星的崇拜。而日、月、天、地、星都是大自然中的物质,可见匈奴人的宗教与信仰体系的偶像,是以自然物为主要内容的。
二、相信灵魂不灭与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普遍存在于各民族的信仰之中,其基础是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并相信死者的灵魂继续与活在世上的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人们既祈望祖先神灵能帮助活着的亲属,又害怕他们得不到抚慰而加害于后人,因此人们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祭祀仪式。〔3〕 P171-172匈奴人也不例外。匈奴人的祖先崇拜,具体表现在具有厚葬之俗,对祖坟的重视与定期聚会祭祖仪式。且对于祖先的信仰与崇拜已然成为其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匈奴人十分重视对死者的安葬,兴厚葬之俗。“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3〕 P2892可见匈奴人对死者的陪葬品十分贵重丰厚,甚至还有活人殉葬现象。而据考古资料显示,匈奴人的随葬品甚为丰富。〔3〕 P259-290对其祖坟,在匈奴人看来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3〕 P2891从中可见,作为匈奴属部的乌桓,随着实力有所恢复,以挖掘匈奴祖坟的方式来报冒顿之怨。而匈奴人对祖坟高度重视,对祖先十分崇拜,为祖坟被掘之事可以发动一场战争。可见,祖先崇拜是匈奴人信仰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迷信鬼神、偶像崇拜并崇尚勇武
1.迷信鬼神
匈奴人五月龙城大会,对于鬼神的祭祀是与天地、祖先同祭的。虽鬼神列与祖先、天地之后,但亦可知匈奴人同时也是迷信鬼神的。而究竟是哪些鬼神,从文献记载来看并非独一或者几个,应当是很多的。匈奴人的信仰是多神信仰,其崇拜的鬼神也有很多。如在“白登之围”中,匈奴单于的阏氏接受了汉朝方面的“厚遗”后,为汉高祖向冒顿单于求情,其重要理由就有“汉主有神(护佑)”。〔3〕P3753尽管汉主的所谓的“护佑神”并不是匈奴人信仰的神灵,但匈奴人仍然畏惧三分。又如《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王号昆莫……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3〕 P3168可见,匈奴对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认为是有神相助,而敬神三分。
2.偶像崇拜
匈奴具有偶像崇拜。在霍去病出征陇西时,曾经“得休屠王祭天金人”。〔5〕P3768对“金人”的解释,注汉书的颜师古如是说:“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5〕P3769可见匈奴人具有偶像崇拜这一宗教行为,做金人是用金人代表天神以祭拜的。金人偶像崇拜,是崇天信仰的延伸。除了有祭拜天而设的偶像,还有其他一些偶像,比如,南匈奴归汉后,“兼祠汉帝”〔6〕P2891。既以汉朝皇帝为偶像崇拜之。
3.崇尚勇武
据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6〕P2879“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3〕P2879“壮着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3〕P2879可见匈奴人的生产生活处处与战争息息相关,且带有浓重的尚武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匈奴真正的贱老弱,前文所述的祖先崇拜就可以否定其含义,这大抵是匈奴人尚武的一种写照。这段史料的重点是“贵壮健”而非“贱老弱”。这一点在中行说与汉使的对话中已经有了明确解答,“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5〕P3760同时,匈奴人甚至可以通过其勇武提升社会地位,侧面可见其尚武精神。如头曼单于欲废太子冒顿,并将其送往月氏为人质,而头曼单于迅速攻打月氏,可见其目的是为了借月氏人之手除掉冒顿。〔3〕P2888而冒顿在危难之时,“盗其(月氏人)善马,骑之亡归”。因此,头曼单于认为其“为壮”,“令将万骑。”〔3〕P2888可见头曼对冒顿态度之改变,冒顿社会地位之提升,源自其“壮”即勇武,侧面可见匈奴人对勇者的崇拜与尚武精神。因此,尚武精神作为匈奴人的重要社会意识而存在,甚至成为了游牧社会公认的信条。
四、匈奴人的盟誓
盟誓,在现代虽然是一种政治条约的缔结,是一种法律行为,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盟誓因其特殊的仪式,而属于一种宗教行为。《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了一次匈奴与汉朝的盟誓:“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5〕P3801可见匈奴人具有盟誓的习惯,并且在盟誓中有刑白马、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并和结盟对方饮血而盟的习惯。
五、匈奴人的巫与医
作为有着形成体系信仰的匈奴人来说,必定要有联系人与“神“的中间人——宗教人士的存在。在匈奴社会,宗教人士以“巫”的形式存在。巫的职能主要是占卜、祈福等宗教行为,甚至还有救人治病的医的功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5〕P3913“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5〕P3913由此可见,匈奴人巫术的行使方式很多,既运用于日常生产生活中,也用于军事生活。同时,匈奴的“巫”也具有医者的职能。苏武在匈奴因认为自己无颜归汉,曾经挥刀自杀,而后“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毉。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5〕P2461可见匈奴的巫医具有治病救人的能力,具有一些医术。
六、匈奴人的宗教与信仰体系对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1.政治意义
首先,匈奴统治阶级以其信仰核心的“天”来神化最高统治权,自称“撑犁孤涂单于”,加强其统治地位。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所谓“撑犁孤涂单于”为天子单于,意为君权神授。单于也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可见其将整个自然崇拜的宗教信仰体系,充分地运用到了政治生活之中。
其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5]P2888宗教集会每次可能也让“诸长”聚集在单于庭,便于统治阶级内部交流,也便于单于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后汉书·南匈奴传》说的更明白:“会诸部,议国事。”[6]P2891其宗教性集会同时也具有了政治集会的意义,也是匈奴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
再次,一同祭祀祖先的宗教行为,可以增加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即传递一个信号: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人。
对于偶像崇拜方面,在南匈奴归汉后,匈奴人同时“兼祠汉帝”〔6〕P2891,表示了政治上对中央王朝的附属,也极大增强了匈奴人的大一统国家意识。
2.经济意义
《汉书·匈奴传上》载:“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5〕P3752匈奴人的宗教集会也具有经济活动的职能。宗教集会成为统治阶级组织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趁着马肥之际的集会可能随之带来一些商品交换与物资流通,丰富了匈奴地区的物质经济交流。
秦汉时期,与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匈奴的宗教与信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一有序的宗教信仰体系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对整个匈奴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匈奴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已经成为匈奴游牧政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匈奴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赵家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形成过程及系统论证[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1).
[2]吕大吉.宗教学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林 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5]班 固.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6.
[6]范 晔.后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8]林 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9][日]泽田勋.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王庆宪、丛晓明译)[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12.
[责任编辑:降小宁]
Hun’s Religion and Belief System
GUO Da-di
(InnerMongoliaUniversity,HuhhotInnerMongoliaChina010070)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Hun formed a complete and organized religion and belief system composed of a naturism stvcture with the core of “Tengri”, belief in ghosts, spirits and immortal soul, worshipping ancestors and idol, advocating valor, habituating to oath and alliance, exercising frequently sorcery in routine and military, and the koradji’s performing religious pillar and doctor function mutually. Being the Hun regime’s spiritual pillar and nation cultural component, this system contained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for the hierarchy to assert its authority and enhance the tribe’s cohesion.
Hun nation; Religion and belief System; Nomadic regim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Spiritual pillar; Nation cultural component
2015-02-16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北方游牧民族视角下的匈奴战争研究”项目号:LYSZ08
郭大地 ,男,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在读硕士研究生。
10.16116/J.ISSN.1008-0597.018
K232
A
1008-0597(2015)01-009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