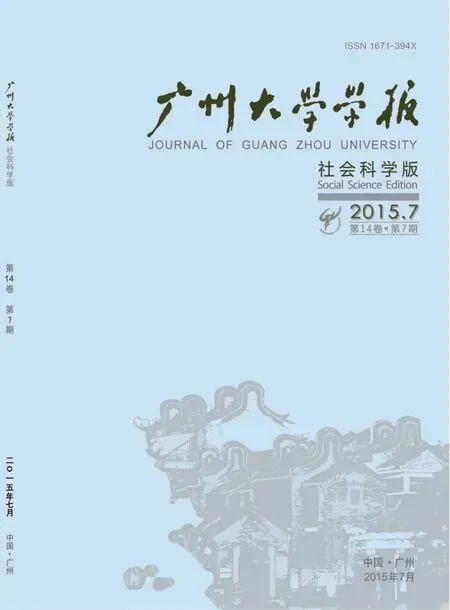《伊豆的舞女》:非电影化小说电影改编的困局与突破
2015-03-20杨世真
杨世真
(广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和其他经典小说一样,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1899~1972)的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也曾被改编成电影文本,并且电影本身产生的国际性影响,反过来助推作家作品的进一步传播。毋庸讳言,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伊豆的舞女》的跨媒介转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来之不易。因为按照传统电影改编的观点,电影倾向于表现一种“物质的连续”,而小说侧重表现一种“精神的连续”,常常含有某些非电影所能掌握的元素,这种情况在现代派小说中表现尤为明显[1]3。《伊豆的舞女》作为日本“新感觉派”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正是这类侧重“精神的连续”的小说。川端康成在《新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说明:“新感觉派”是“西方多种现代流派的混合……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感觉,新感觉派是通过这种感觉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2]19从电影改编的角度来看,现代派小说总体上偏重人物主观感觉,而电影则侧重一种“实体的美学”,其基本表现手段是“物质现实的复原”[1]3,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的确会给电影改编带来非同一般的困局。但如果因为某些意识流小说电影改编的失败案例,就断定“把《尤利西斯》拍成电影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乔伊斯的作品是不能拍成电影的”[3]140、146,则显然走入另一个极端。在电影越来越多地涉足现代派小说(特别是意识流小说)改编的背景下,从成功的改编案例中总结经验,而非一味拒斥改编,也许是更为理性的思路。
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的跨媒介改编能否成功,既取决于编导的艺术功力,也来自于小说文本自身的状况。本文将集中讨论后一种情况。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把“凡是在内容上不越出电影的表现范围”[1]305、更有利于实现成功电影改编的小说称为“电影化小说”,反之则称为“非电影化小说”。探讨《伊豆的舞女》这部“非电影化小说”的成功改编,既能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小说的特点,也可以为其他现代派小说的电影改编提供借鉴。
一、媒介转译概述及评价的前提
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自1926年诞生以来,就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广播剧、舞台剧等多种媒介文本,显示了小说巨大的文化衍生能量。在各类改编文本中,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主要是电影文本。早在1933年,就出现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此后又分别拍摄了5个版本(1954,1960,1963,1967,1974)的电影作品。在6个版本的电影改编中,1963年版与1974年版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最大,男女主角分别是高桥英树、吉永小百合以及三浦友和、山口百惠,而导演都是西河克己(1918~2010)。在中国,广为观众熟知的也是这两个版本。其中1963年吉永小百合版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1974年山口百惠版由中央电视台配音。除非特别说明,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1974年版。
要评价小说《伊豆的舞女》的电影改编是否成功,需要明确三个大前提。
第一,是基于“自由的改编”,还是“忠实的改编”?
“自由的改编”很少注意原著的精神。乔治·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指出:“在根据小说拍摄的影片中,许多'小说化'的元素不可避免地被抛弃掉了。这种抛弃的严重程度,使得新的作品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已经和原作很少相似之处。……影片摄制者只不过是将小说当作素材,最后创作出自己独特的结构。”[4]2-3对这一类改编作品进行评价,须涉及更广泛的方面,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改编成功与否跟小说自身的特点几乎没有多大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过不少根据二、三流小说改编的出色影片。
“忠实的改编”则不同。它虽然不等于逐字照搬,而会出于银幕表现的特定需要,对原作有所改动,但是仍然表现了“一种保全原著的基本内容和重点的努力,至于成功与否,姑且不论”[1]304。相比而言,“忠实的改编”往往更多地涉及经典小说,因而较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议也较大。由于经典小说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改编者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改编时,究竟是采用“自由的改编”,还是“忠实的改编”?这取决于改编者。对于一部已经完成的改编作品来说,要识别其属于哪一种改编,这并非难事。从总体上看,人们总是可以很方便地将其归类。两种改编方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评价改编成功与否不在于改编偏向前者还是后者,改编一旦被归为其中某一类,人们很自然地有理由按照该类改编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伊豆的舞女》的改编显然属于“忠实的改编”。小说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场景、对话、行动和道具都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电影中。因此,它的改编是在“忠实的改编”这一前提下进行的。
第二,是基于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
在这里,我们无意卷入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孰优孰劣的历史纠葛,而只想按照人们公认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叙事特征,先将其大致归类,为我们评价《伊豆的舞女》的改编确立一个基本框架。如果用艺术电影的标准去衡量商业电影,或者相反,就很难对一部改编影片做出合理的评价,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在少数。
通常所说的“艺术电影”(essai cinématographique,art film)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变体,如诗性电影、纯电影、散文电影、先锋电影、实验电影、欧洲电影、文艺片或现代派电影等许多变体。这些变体既互相叠印,又互相区别,涵盖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影片,很难取得准确的一致性。但是,在有意识地拒斥商业电影(以好莱坞电影为典型代表)这一点上,这些变体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曾对二者做过具体的比较:
古典好莱坞电影中,通常有心理背景明确的人物,试图解决某个明显的难题,或者达到某些目标。在这过程中,人物与他人或外在环境产生冲突。故事以一个关键性的胜败收场,或是问题解决,或是目标达成或失败。……在古典的故事框架中,因果关系是最主要的整合原则。[5]335-336
“艺术电影”与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相比,主要有四点差异,其一,用较为松散的事件取代好莱坞影片紧密的因果关系;其二,重视人物塑造以取代好莱坞重情节的刻画;其三,多表现时间的扭曲,这种扭曲的时间受到柏格森所说的心理时间的游戏,而非牛顿时间定律的影响;其四,较为突出的风格化技巧的运用——如不常见的摄影机角度、醒目的剪辑痕迹、大幅度的运动摄影、布景或者灯光非写实的转换或是以主体状态来打破客观写实主义,乃至用直接的画外音进行评论等。[5]431-438
对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规则,人们并无多大分歧。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并运用这些叙事规则。假如仅从上述对比的情况来看,小说《伊豆的舞女》虽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被视为川端康成的一部典型的“新感觉派”小说,但是改编影片《伊豆的舞女》却在总体上更接近传统商业电影。尽管它的人物动机不够明确,与他人或周围环境的冲突也并不激烈,各场次之间的因果链条也不甚紧密,但它距离艺术电影的距离则更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将其归入商业电影的名下,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它与小说文本的跨媒介转译。
第三,是基于小说的客观因素,还是改编者的主观因素?
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否成功,不但取决于小说自身的特点是否适合于电影的手段,而且更取决于改编者与导演的创作能力。就“忠实的改编”而言,小说自身的特点对改编成功与否的制约作用相对来说更突出一些。让我们暂且撇开千变万化的个人因素,只专注于小说文本的客观因素对改编造成的影响,就像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那样,“只检查一个方面: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电影手段的要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先假定改编者和导演都是技巧完美、感觉敏锐的专门家”[1]304-305。
也就是说,有两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将小说《伊豆的舞女》改编成一部商业电影,会面临哪些客观的阻碍?改编者与导演又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下文将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二、“非电影化小说”改编的困局
《伊豆的舞女》电影改编遇到的困局不仅仅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跨媒介转译,而且来自小说自身的“非电影化”元素,因而比一般小说的改编难度更大。这些“非电影化”的元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主观现实为核心内容的“新感觉”;其二,与主流电影相悖的“小情节”模式;其三,比喻手法。
首先,以主观现实为核心内容的“新感觉”。
1924年10月,“新感觉派”文学的主阵地《文艺时代》创刊,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等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1925年,川端康成发表了《新近作家的新倾向解说》,可以说它是“新感觉派”理论的指导性文章。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他认为日本的“新感觉”表现在认识论上与欧洲表现主义的理论相同,二者都主张艺术家应当完全从自我出发,从主观出发,表现自我的主观现实;而小说《伊豆的舞女》正发表于1926年1月和2月的《文艺时代》上,因而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出“新感觉派”文学的特色,其实有引领潮流的意思。[6]100-115
小说突出表现的“主观现实”给电影改编带来了困难,因为“主观现实”超出了电影摄影机所能再现的领域。比如茶馆躲雨那一幕,小说里写道:
“今天晚上那些艺人住在什么地方呢?”
“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少爷。什么今天晚上,哪有固定住处的哟。哪儿有客人,就住哪儿呗。”
老太婆的话,含有过于轻蔑的意思,甚至闪起了我的邪念(——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既然如此,今天晚上就让那位舞女到我房间里来吧。
雨点变小了,山岭明亮起来。……[7]77
这个“邪念”不论对小说还是改编影片都很重要,如果没有此处的“邪念”,就没有后面“我”看到舞女裸身跑出浴场时的感觉,即“仿佛有一股清泉荡涤着我的心……脑子清晰得好像被冲刷过一样”的感觉,也就无法凸显女主角的纯真与美好。然而,“邪念”却是很难用摄影机直接再现的主观现实,很难找到它的客观对应物。1963年版和1974年版的《伊豆的舞女》对此的处理方式引人关注。它们都出自同一位导演西河克己之手,但是对这一重要的“邪念”却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在1963年版的影片中,“邪念”被外化为一场梦境——“我”在深夜潜入舞女的房间,被舞女的哥哥发现,接着被扔下万丈深渊。电影叙事只有一个时态,那就是现在进行时;而在当下的叙事进程中插入一场梦境,打断了主叙事进程,显然是生硬的。这种手法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语言成熟之后就渐遭淘汰。1963年版的影片之所以还这么做,想必编导既感到了“邪念”的重要性,却又很难找到符合摄影机拍摄需要的方法。
面对同样的难题,1974年版则不但放弃了梦境,而且连“邪念”内容本身也删除了。虽然放弃了陈旧的手法,却又造成了重要内容元素的流失,真可谓旧憾刚除,新憾又生。
对于小说中男主人公其他多处心理活动,影片改编者干脆用画外音的方式来呈现。比如,当“我”回想舞女裸身跑出温泉冲我挥手的情景时,影片用了如下画外音:
她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也许是看到我们了,所以她高兴得光着身子跑了出来。看着她高兴的样子,我的心突然像被清水洗涤过一样,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
克拉考尔曾以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不适合改编成电影为例,指出:“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常常会伸展到某些绝非电影所能再现的领域……电影绝无可能暗示出这些对比和随之而来的沉思默想,除非他求助于某些不正当的手法和人工的设计;而电影一旦乞灵于它们,它当然就立刻不成其为电影了。”[1]302画外音造成电影声音与画面两种手段的分割,形成以声压画的弊端,正是典型的不适合电影表现的“不正当手法”之一。旁白、内心独白的多处运用,正是《伊豆的舞女》这类非电影化小说改编困境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个不得已的解决办法,时至今日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除了直接描写主观现实外,小说《伊豆的舞女》中的外部事件,也大都渗透了强烈的主观色彩,表现的是一种克拉考尔所说的“精神的连续”,含有某些非电影所能吸收的元素。它不像有些文学作品,描绘的是一种可以通过物质现象的连续来加以再现和模拟的精神现实。因此,即便就外部事件而论,小说《伊豆的舞女》跟电影也相去较远,不像其他一些小说那样跟电影较为接近。[1]304-305
其次,与主流电影相悖的“小情节”模式。
美国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在《从小说到电影》(Novels into Film,1957)中提及,情节奇特的事件,尤其是19 世纪的通俗历史画、戏剧或流行的蜡像中常见的那种血淋淋的事件,是早期活动电影最合乎观众口味的三种题材之一[4]7。匈牙利的电影美学理论家巴拉兹·贝拉(Balázs Béla)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确有可能把一部小说的题材、故事和情节改编成一部完美的电影剧本。[8]276然而,小说《伊豆的舞女》在情节上可谓先天不足,它讲述的是一个尚未开始就已结束的故事,没有电影经常从小说借用的完整情节,有的顶多只是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所说的“小情节”。所谓“小情节”(Miniplot),是指介于大情节(Archplot)和反情节(Antiplot)[9]44之间的一种情节模式。大情节是指一种经典设计,具有突出的因果关系、闭合式结局、线性时间、外在冲突、连贯现实、主动主人公等特征,是“世界电影的主菜,过去一百多年来,它滋养着绝大多数备受世界观众欢迎的影片”。反情节是指一种现代设计,类似于文学领域的反小说或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以偶然性、非线性时间、非连贯现实等为特征。而小情节则是指对大情节的突出特征进行提炼、浓缩、削减或删剪,但又没有滑向彻底的反情节、反线性叙事的程度,它以开放式结局、内在冲突、被动主人公为特征。[10]53-54罗伯特·麦基更倾向于将小情节归结到反情节,从而与大情节形成对峙。
上述对比分析表明,小说《伊豆的舞女》几乎缺乏主流电影情节所需要的全部特征。男主人公“我”虽然对小舞女萌生爱意,但自始至终都是欲言又止,欲行又止。这份爱意是如此模糊不清,一直被“闷”在心里,形成不了明确的人物动机,当然也就没有外化为语言,更谈不上采取行动,因而也就难以形成一个贯穿全片的真正的冲突,结尾只能是无果而终的开放式结尾。基于忠实原著的要求,改编影片不可能再造或夸大人物的欲望和行动,从而导致改编影片因果链条极为松散、薄弱。虽然改编影片保留了小说的线性时间链条,男女主人公结伴同行的五天四夜,清晰可辨,但也只是自然时间的变化,缺少戏剧性内涵,最终只能沦为可有可无的时间空壳。
再次,比喻手法。
比喻是小说借以突出事物的相似之处的特殊方法。小说《伊豆的舞女》中有多处这样的比喻,如温泉浴场里一段:
洁白的裸体,修长的双腿,站在那里宛如一株小梧桐。我看到这幅景象,仿佛有一股清泉荡涤着我的心。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噗嗤一声笑了。……我更是快活、兴奋,又嘻嘻地笑了起来。脑子清晰得好像被冲刷过一样。脸上始终漾出微笑的影子。[7]84]
与这一段中的比喻手法相似的还有许多,仅再举一例:当舞女一行因故推迟行程,不能按约定与“我”一起动身去下田时,“我顿时觉得被人推开了似的”[7]86。以上两例都不是一两句简单的描绘,而是直接涉及人物内心体验,事关人物行动。如小说所述,“我”性格中有扭曲的孤儿气质,正是因为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我”才去伊豆旅行。“我”在与舞女一行结伴旅行途中,开始真正变得开朗,时常不经意间留下喜悦的泪水。而当舞女一行不能与“我”继续同行时,“我”的失落感无疑是巨大的。这份由悲转喜、又由喜转悲的混合情感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现在的问题是,小说中这两处重要比喻的内涵如何用电影化手段来表现?或者说,这几处比喻给电影化改编带来了哪些难以克服的障碍?
用比喻的目的不在于让读者在想象中“看见”洁白的裸体、修长的双腿,而在于通过小梧桐的形象作比较,将肉体的层面跃升至精神的层面,突出舞女给“我”带来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因此裸体不仅仅是裸体。这一点,小说用读者熟知的事物(“小梧桐”“清泉”)和动作(“荡涤”“冲刷”“推开”)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而对于电影来说就很成问题了。除非运用内心独白这一陈旧的手法,电影似乎只能停留在肉体展示的层面。虽然电影用了全景急推近、切换成上半身近景的镜头语言,以强化视觉冲击带来的心理变化,但观众看到的裸体终究还是裸体!
小说中的“看见”与电影中的“看见”有着很大的不同。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曾说:“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文字的力量,让你们看见。”[11]336而16年后,美国电影导演格里菲斯(D·W·Griffith)总结自己的主要意图时也曾表示:“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首先是要让你们看见。”[12]126虽然小说家与电影导演的意图相同,但是布鲁斯东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说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4]1-2
电影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比喻方式,最为常见的手法是在剪辑时,通过两个镜头的对列在彼此之间建立新的含义。苏联蒙太奇学派常常运用这一方法,如导演普多夫金在《母亲》一片中将工人游行示威的镜头与春天河水解冻的镜头组接在一起,用以比喻革命力量势不可挡。爱森斯坦也曾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切入来自不同地方、与剧情毫无关系的三只石头狮子的形象,用它们卧倒、抬头、跃起的三个镜头衔接来比喻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然而,上述手法很快就被电影创作者所抛弃,因为它们代表了电影语法形成期的积极探索,但是结果并不算成功。电影运用比喻所受的限制要大得多,正如布鲁斯东所言:“可以有一种特殊的电影借喻,只是它必须服从电影的语言:它必须是自然而然从背景中产生的。……将不同的事物比较时,电影借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彻底消除它们的现实感。”[4]23
《伊豆的舞女》中的借喻要么无法用影像传达,要么是无法消除其现实感,而依旧保持自身的存在,导致喻体与本体“抢夺眼球”。如电影改编中增加舞女阿君之死这条线,就是简单而铺张的借喻。在小说文本中是没有阿君这一人物线索的。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版与1974年版都增加了阿君形象,其用意非常明显,即用阿君从卖艺沦落到卖身、最后得病而亡的悲惨经历来暗示女主人公熏子的命运。但问题在于,由于影像自身复制物质现实的特性,阿君故事的现实感很难彻底消除,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阿君的故事作为喻体必须为本体熏子的故事服务,另一方面却又具有自身的完整性,难免与熏子的故事分庭抗礼,游离于主人公熏子的故事之外。电影无法像小说那样借用语言手段,用A 来说明B,而需要向观众直接展示A。因此,虽然编导明显在阿君这个比喻性质的人物身上下了很大功夫(同一位导演的两个改编版本都保留了阿君的完整故事线),但是仍然面临着跨越媒介的巨大障碍,最终与上述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等人的比喻一样,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忠告也许能给人以更多的启示:“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也能在我们心中唤起:晶莹欲滴、温润凝滑、鲜艳的殷红、柔软的花瓣等多种多样而又浑然一体的印象;而把这些印象串连在一起的那种节奏自身,既是热恋的呼声,又含有爱情的羞怯。所有这一切都是语言能够——也只有语言才能够达到的;电影则必须避免。”[4]23
以上几点足以说明,从“忠实改编”的角度看,小说《伊豆的舞女》绝非电影的近亲,顶多只能算是电影的远亲。不过,《伊豆的舞女》的导演对此并非束手无策。因为这部小说毕竟不像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那样的纯意识流小说,并不仅仅表达一种“精神的连续”;若果真那样,就会把电影改编逼上“非电影化”的绝路。就《伊豆的舞女》而言,只要编导善于找到与本体相对应的形象化喻体,将小说文本固有的内在性用具体的形象或戏剧动作加以外化,小说文本中的比喻依然可以转译到影片文本中。正因为如此,《伊豆的舞女》为改编者朝着“电影化”方向前进留下了一丝希望。
三、电影化改编的突破
蒙太奇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苏联导演C·M·爱森斯坦(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1898~1948)在《狄更斯、格里菲斯和今日电影》一文中提到,他从狄更斯作品中获得了重大启示,因为狄更斯的有些小说是很电影化的。[4]2狄更斯是现实主义作家,爱森斯坦从其小说中发现电影化元素是不足为怪的。不过,如果认为“只有现实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小说才能改编成令人满意的影片,那就是完全出于误解了。事情并非如此。实际上,一部小说的改编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它是否专门描写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看它的内容是否具有心理—物理的对应。一部显然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对外部世界的描绘,可能是出于根本不适合于电影表现的题材和主题的需要。反之,一部小说以内心生活过程为内容,并不一定就因而成为一部不可改编的叙事作品。”[1]37
从电影改编的一般情况来看,《伊豆的舞女》作为一部具有“新感觉派”风格与手法的小说,的确存在上述诸多改编困局。但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编导面对一部非电影化小说,仍然实现了电影化的改编。其主要的手法有三:一是突出运动性场景,二是突出民俗的可视性,三是强化线性叙事。
先看运动性场景。
希区柯克曾表示“追赶是电影手段的最高表现”[1]52,弗拉哈迪认为西部片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在原野上策马奔驰的景象是叫人百看不厌的”[1]53。克拉考尔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多种多样的运动是最上乘的电影题材,是真正“电影的”,因为“只有电影摄影机才能记录它们”。[1]52小说《伊豆的舞女》中当然没有西部片中那种“策马奔驰”的追赶场面,有的只是男主人公的一趟旅行经历。然而,旅行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带来空间的不断变化,从而大大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
小说主体部分写到了途中茶馆、汤野客店以及下田小客店三处主要的固定场景,期间穿插的正好是三段山间赶路的场景,这三个场景都在电影改编中得以完整保留。这是一种很电影化的选择。
第一个场景出现在影片序幕阶段,“我”与一群流浪艺人在山路上穿行,忽遇雷雨,到一家茶馆避雨。第二个场景是雨停后,一行人继续赶路去汤野。第三个场景是离开汤野去下田的山路。几位流浪艺人与一位旅行的学生在山路上结伴行走,其紧张激烈当然比不上西部片中你死我活的追赶场面,但影片《伊豆的舞女》的赶路场景绝不可视同一般的旅游风光片,因为这三次场景的时值越来越长,戏份越来越重,对人物关系走向及主题基调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第一个赶路场景中两拨人各走各的,没有交集,雷雨设计顶多也是并不高明的“巧合”,那么第二个场景中男女主人公有了初次的正面交谈、交流,预示着电影已经从运动带来视觉上的可看性升华为人物内在的吸引力。在第三个赶路场景中,通过熏子挑竹竿给“我”当拐杖,以及熏子和“我”单独在山巅相处这两个分场景,赶路已经从通常的过场戏转化为主场戏。
运动性场景除了增加可看性之外,还对叙事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运动为特征的山路为外景,与固定场景交替出现,影片的整体结构从视觉上富于变化,产生了视觉的愉悦。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文本中还提到“我”初见舞女也是在途中,当然也是充满运动性的素材,但是电影文本弃之不用。这也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做法,因为初次见面时只是“我不时地回头看看她们”,没有她们与“我”的互动性,[7]75缺乏后面几次同行时越来越强的戏剧性,毕竟最吸引观众的不是一次竞走比赛,也不是沿途的自然风光,而是行走中的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
总之,将运动性场景与戏剧性融合在一起,是《伊豆的舞女》实现电影化改编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看民俗的可视性。
小说《伊豆的舞女》虽然汲取了欧美现代派小说的某些观念与技巧,但是这些观念与技巧仍是为了表现一种东方情调。电影文本承继了小说中的东方元素,但是尽力将这些东方元素视觉化,以适合电影的表现手段。
电影文本中作为视觉符号的民俗元素处处可见。比较突出的有温泉、日式小木屋、服饰、三弦琴和日式传统舞蹈等。果戈理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13]374《伊豆的舞女》中充满这些民俗元素,但它们不仅仅是符号,不是为了展示而展示,而是与人物关系、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等结合在一起。
比如,日式温泉不但是故事发生的主场景,而且也很自然地向观众展示了一幅民间风俗画。大大小小、档次不一的温泉旅馆,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阿君们在这里卖身丧命;温泉既是舞女们赚钱谋生的舞台,也是“我”接触市井、排遣孤独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温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视化的场景,其本身也成为“有充分资格的演员。从无声喜剧片里的自动楼梯、倔强的隐壁床和疯狂的汽车……它们以主人公的姿态出现”。[1]57可以说,没有修善寺温泉、汤岛温泉、汤野温泉,就没有“我”和舞女的故事。反之,如果仅仅作为孤立存在的故事背景,那众多温泉就是可有可无的,温泉的设置也是非电影化的。
舞女的发式在改编成电影时也得以充分表现。在小说中,第一人称的视角用“丰厚”“非常浓密”“秀美”等词语多次赞美熏子头发之美。电影文本没有忽略这个重要的视觉元素,许多涉及头部的镜头都运用近景或特写,使得发式必然成为视觉注意中心。同时,电影文本还保留了小说中与熏子头发有关的一个重要的细节,即熏子和“我”下棋时,她的头发几乎碰触到我的胸脯(电影中碰到的是“额头”),引起两人的羞涩与局促不安。不止于此,电影文本还另外增设了两处关于梳子的情节:在去下田的山顶上,当两人独处之时,熏子的梳子掉落在地,“我”帮熏子捡起,并亲自给她别在发髻上;最后离别时,熏子赠送梳子给“我”。小说文本中对头发属性的名词和形容词描述具有一种静态和抽象的特征,这就给电影化改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下棋时头发碰到男主角,这改变了小说中的静态特征,而梳子的设计也较好地克服了抽象化文字的不足。
最后看线性叙事的强化。
如上所述,布鲁斯东和巴拉兹·贝拉都认为,奇特的情节对于成功改编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小说《伊豆的舞女》讲述的是一个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初恋故事,人物没有明确的主导动机,没有果断的行动,因而难以形成直接的戏剧冲突,没有一波三折的传统戏剧套路,男女主角不但欲言又止,而且欲行又止,属于淡化情节的类型,故事线索比较松散。针对这一情况,电影改编者努力强化了线性叙事,整部影片也由此而更加电影化。
在小说文本中,缺乏行动的男主人公不时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结构上显得零散。而电影却提取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相对完整的事件,努力构建一条贯穿全影片的线性叙事链条,大致形成了主流故事片采用的“线性结构”,即全片分为开端(beginning)、中端(middle)、结尾(end)三幕,三部分对应的戏剧功能分别是建置(setup)、对抗(confrontation)、结局(resolution)。[14]2这种叙事主线的设计与小说有了很大的区别。小说主要以第一人称“我”的视点叙述故事,按照旅行的自然时序来展开,而且叙事重点一直在男主人公的内在情绪上,外界的一切包括女主人公都不过是“我”的感觉的外化与投射,难以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因为双方并不享有平等的叙事权利。电影则赋予男主人公一个很强烈的动机——“一个希望”,希望和舞女们一道旅行,和舞女下棋,甚至和舞女亲热。有了这个希望,才导致男女主人公采取行动试图接近对方,彼此一步步由陌生变得熟悉,由熟悉到互相爱慕,也才有了最后无奈分手的哀伤。
另外,新增的舞女阿君也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1974年版的电影中阿君这条线索完整性更加突出。就连男女主人公之间作为信物的一把梳子,在电影文本中也有始有终,梳子多次出现,而且牵扯的情感纠葛也越来越复杂。
综上所述,虽然《伊豆的舞女》的小说文本具有一些“非电影化小说”的特点,给这部小说的电影化改编增添了额外的难度,但是电影编导在现有小说文本的基础上,依据电影语言的表现规律,通过突出运动性场景、突出民俗的可视性、强化线性叙事等处理手段,使得《伊豆的舞女》的电影改编成为“非电影化小说”改编的一个成功典范,对许多现代派小说的电影改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1]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2]何乃英.论日本新感觉派[J].现代日本经济,1989(05).
[3]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4]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5]波德威尔.电影叙事:剧情片中的叙述活动[M].李显立,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
[6]何乃英.川端康成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M]∥川端康成文集.叶渭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8]贝拉.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9]MCKEE R.Story:Substance,Structure,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M].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7.
[10]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11]王春元,钱中文.英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5.
[12]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3]梁仲华,童庆炳.文学理论基础读本[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
[14]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M].鲍玉珩,钟大丰,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