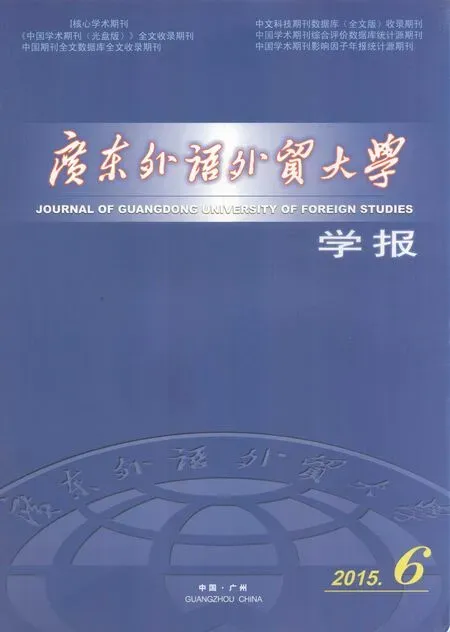宗白华《流云小诗》对宇宙生命本体幽深体悟与传达
2015-03-20杨胜刚
杨胜刚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州 510521)
一、对宇宙生命本体的幽深体悟
宗白华经常谈论他对宇宙生命本体的幽深体悟。在宗白华的体认里,在宇宙万象、无穷的自然人生的运动背后,存在一种“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他还用其他的词,如“宇宙灵气”、 “宇宙的造化”、 “宇宙的意识生命情调”、“宇宙的深境”来指认这个在他看来是宇宙生命本体的东西。宗白华还认为,人可以从体察丰富的宇宙动象入手,以一颗活泼空灵的心灵深入到宇宙的内部,领悟到宇宙的“幽意”,用宁静和澄澈的心灵来涵映世界的广大和精微,“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可以用心灵去触碰这宇宙最深的本体生命,最终与这最深的宇宙生命相生相感、融合无间,从而回归到宇宙的本体生命之中。
那么,人又能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直探生命的本原,并与这飞跃的宇宙生命一起搏动,与这幽深的宇宙生命融合而回归生命的本真呢?在宗白华看来,必须要在忘我中“静照”,才能追蹑宇宙之心。如何才可以做到“静照”呢?宗白华认为,首先注重平素精神的涵养和天机的培植,经常地“热情地深入宇宙的动象”,养成活泼泼的心灵。而“静照”的发生又是在突然间成就的,它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时刻。人只有在能完全放弃人世人事的挂碍,放弃人世习得的“识”和人世现实的考量与算计,以一颗纯朴之心直接与宇宙相接触,才有可能进入“静照”。这就是宗白华所说的:“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在人平素所养成的活泼泼的心灵“能舍”而变“空”了的时刻,人的心灵才能够像一面纤尘不染的明镜,“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也就是在这一刻,“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人的性灵”,人融化于宇宙,与宇宙的迁流大化冥合,从而获得精神的极致自由和发自深心的惺惺喜悦 (宗白华,1994:348-349)。
在宗白华生命中自小开始形成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静美情调的品味,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一直未变。长期徜徉于自然之中并对自然体验和沉思,让宗白华生命中“结成一个长期的微渺的音奏”,养成了一颗既活泼飞跃、又能静观寂照的心灵。在留学德国期间,即宗白华的生命“转到生活的飞跃”的那个时期,对宇宙体合时刻就经常不期然地降临在他的心灵。“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听到永恒的深秘节奏,静寂的神明体会到宇宙静寂的和声” (宗白华,1989:192)。
一、《流云小诗》对人与生命本体体悟的状写
宗白华对人与宇宙生命本体相互体合的幽深体悟,保留在他早期所写作的诗集《流云小诗》 (以下简称《流云》)中。他的诗句传达了他经常所说的以心灵映照万象,映射天地诗心,聆听“永恒的深秘节奏”,体合“宇宙静寂的和声”的高妙体验。例如:
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星里/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得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夜》)
月的幽凉/心的幽凉/同化入宇宙的幽凉了!(《解脱》)
心中的宇宙/明月镜中山河影。(《断句》)
月天如镜/照着海平如镜。/四面天海的镜光/映着寸心如镜。(《月夜海上》)
以上这些诗句,抛开过程的描写,直抵心灵体验的高峰状态,直接状写诗人将自我弥散、化归于宇宙中,让自己的一颗“觉心”脱去现实存在的实体形骸,变成一面晶莹剔透的明镜,来烛照宇宙之精微的心灵境界。
日前,记者从云南电网丽江供电局了解到,今年国庆旅游高峰期,为确保向丽江游客提供优质、可靠的电力保障,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中秋”“国庆” 节期间,丽江供电局累计出动保供电人员2316人次,出动保供电车辆297辆次,应急发电车(500kW) 1辆次,应急发电机(5kW) 2台次进行保供电,切实做好保供电期间的应急物资准备,充分发挥党员服务队的示范、带头作用,圆满完成国庆保供电任务。
在《流云》里,宗白华这一高峰时刻有时是破空而来,不期然降临;有时又是需要触媒的引动或环境的诱发。《流云》最经常写到的触媒是音乐。音乐可以洗涤诗人的心灵,让心灵变得宁静,把人的神明远引至无尽的时空。《流云》中也多次描述音乐如何把他的心魂招引至对宇宙诗心的悠远体会。例如:
我低了头/听着琴海的音波。/无限的世界/无限的人生/从我心头流过了,/我只是悠然听着。/忽然一曲清歌/惊堕我手中的花,/我的心杳然去了/泪下如雨。(《听琴》)
水上的微波/渡过了隔岸的歌声。/歌声荡漾/荡着我的寸心/化成音乐的情海。/情海的音波充满了世界。/世界摇摇/摇荡在我的心里。(《音波》)
音乐让诗人出神,把诗人的心灵引向“无限的宇宙,无限的人生”,让诗人彻底消去了他的形骸,彻底向本体生命敞开,随宇宙的创化和生命的节律一起搏动。
当然,《流云》所表现的诗人体合宇宙的时刻更经常地发生在夜里。诗集的《序》中,宗白华虽宣称“我愿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灵魂,起来颂扬初生的太阳”,但在《晨》这首诗中,他又说,在晓色初露的时刻,“现实展开了。/空间展开了。/森罗的世界/又笼罩了脆弱的孤心。”似乎他害怕白昼世界喧嚣、动荡不宁的模样,因为白昼的扰攘会侵凌他那颗“脆弱的孤心”,所以宗白华的《流云》更经常描述的是诗人在夜晚的内心歌唱。《流云》不啻是一曲“夜的歌”,在那里星光闪烁、碧月如镜、夜色如水、晚风送幽,诗人也是在这无边的夜空里,让一颗寸心与“冷月齐颤”、“星光合奏”,进入“深宏无尽”的宇宙。例如:
“黑夜深,/万籁息,/远寺的钟声俱寂。/寂静——寂 静——/微 眇 的 寸 心/流 入 时 间 的 无 尽。”(《夜》)
这是《流云》中第二首以“夜”命名的诗,这首诗同第一首《夜》一样,都是表达在夜晚诗人的心无遮地与自然相接触,而与自然发生最深的亲切交会,与宇宙“同齐流”的幽深体验。
诗人体合宇宙、追蹑天地之心的时刻为什么总是发生在夜里?“伟大的夜/我起来颂扬你:/你消灭了世间的一切界限,/你点灼了人间无数心灯。”(《夜》)。这是《流云》中第三首以“夜”命名的诗歌,这首诗清楚地解释了夜对于领受宇宙内部造化的重要。只有黑暗来临,动荡的白昼才止息了下来,才让一切都笼罩在黑暗里,让宇宙万物在姿容色相上的差异一起被黑夜隐藏起来,也抹去了广大人类身份地位的差别,喧嚣朗朗乾坤的在这时回归于原出一体的本质,浑然一体;夜晚诗意的安宁,也可止息人的欲望,让一颗颗在世俗中奔波浮荡的心安宁下来,让那些被世尘所蒙蔽的真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只有在心灵的尘滓都从心头被夜的宁静和深远荡涤而去,在心灵变得晶莹的时刻,才能让自己的本心与世界的本相直接相接触,与世界的“真”通明对视。就像宗白华自己所描述的“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在这一刻,“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在这一刻,“微眇的寸心/流入时间的无尽”。《流云》中的这类诗歌,精微地描述了夜晚让诗人的心归于宁静,点灼诗人的心灯,诗人在夜色带来的无边安宁和心的静寂中领悟天地之心,感知到冥冥之道,乃至充分融入到宇宙生命的本体,回归生命本源的精神过程。
宗白华在《流云》里,反复状写了夜晚和音乐让诗人收摄心神,在静观寂照中以一颗晶莹剔透的本心映照和体合宇宙生命本体,自我在深静中领会宇宙整体的精神经验。《流云》既诗意地写出了个人体合宇宙内部生命本体的心灵条件和通道,也描述了人进入宇宙的过程和自我深心体合宇宙生命时的高峰体验,还对人在高峰体验时心灵的状态做了表述。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满自足的精神经验发生的全过程,表明宗白华已经通过《流云》对自己那种直感式、体验式的生命领悟进行了比较形象、比较完整的表达。
二、东方式体验与西方式哲思相结合
宗白华认为“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 (宗白华,1981:132),而《流云》描述宗白华常常在夜里,在无边的夜晚让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刻,他的那颗被滚滚人世的洪涛所激荡的心归于安宁,一颗晶莹的心灯被夜晚点亮而“一真孤露”。这样的心灵过程与庄子所说“心斋”的过程一样,都是要关闭耳目视听,终止世尘的纷扰,而把心灵打开,敞开心灵,放出性灵,以一颗“真”心与世界相接。另外《流云》所描述的“心的幽凉/同化入宇宙的幽凉了”、 “微眇的寸心/流入时间的无限”与庄子所表达的在坐忘中化归大道,也都是在讲取消自我和无限宇宙的界限的“天人合一”之境,都在表达收摄心神,在静观寂照中以一颗晶莹剔透的本心映照和体合宇宙本体生命的精神经验。从这一角度而言,说宗白华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哲学是“中国式的生命哲学” (彭锋,2000:87)也不为错,因为他通过《流云》表达的在夜色带来的无边安宁和心的静寂中领悟到天地之心的精神过程和精神经验,与老庄在虚无中体悟冥冥之道的精神经验都是在说“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中国古人体合大道的经验也在宗白华的心灵中再次发生。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宗白华就完全回归到庄子或者回归到中国古典哲学里。无论是庄子还是老子,他们的心斋、坐忘或至虚极、守静笃,最终不是要把捉住“道”,而是追求一种“忘我”(忘掉自我的现实处境、现实的存在),化归到根本,达到与道冥同的境界。正是在这一点上,宗白华与传统不同。比如:
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里星/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得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里/在里面灿着。(《夜》)
这首诗同样是在讲觉心对世界的映照和对宇宙的化归,但从诗歌的表述我们也能看到,“表里俱澄澈”和化归并不是诗歌的终点。诗人的一丝意念在化归之后,又从物我两忘的状态中跳脱出来,不断地去分辨“我”、“我的心”的位置和状况。
所以说,宗白华不是像陶渊明那样,在“忘言”之后放弃“辨”,他还是要去“辨”。而他“辨”的是什么呢?是自我意识,是自我在这极为沉浸的状态下自我心灵状况。宗白华在极为深邃的体验中让自己的意念从自己的思想中分离出来,把自我的意念高高地置于自我的心境之上,俯视自我,静观自我,从而把捉自我。他要把自我在高峰体验的时刻自我的精神状态分辨出来,要品味出自我化归宇宙深处时心灵的情形,捕捉自我在心灵澄澈一片时其意识和心境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实况之中,是在追踪自我在追蹑天地之心时自我意识所划过的印迹,实录自我精神在天地遨游时气韵生动的精神经验。
宗白华在化归宇宙深处时揽镜自照,反观自我,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进向就不完全是中国式的,而是比较西方化的。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精神无疑是把自我尽量向宇宙弥散,消融自我,而宗白华所表现的运思指向却是在融化自我时指认自我,反身自照,始终保持对自我的清明意识和观照,这显示出的无疑是把自我当做客体来打量、来思辨的西方式的理性思维路向,有一种追求“天人合一”,又穿透和超越“天人合一”的意味。
从中西思想文化史的整体来看,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精神方式有两种样式或结构,一是“主体—客体”结构。这种结构把人和世界的关系看做是相互分离、彼此外在的,人作为主体可以凭借认识来理解和征服客体。二是“人—世界”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内在的、非“主—客”关系中的对象性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融。西方哲学史经历了古希腊早期、原始的早期“人—世界”合一和长期的“主—客”式思想发展后,到海德格尔等人形成了包摄了“主—客”式的一种更高级的“人—世界”合一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人—世界”结构的一种形式,不过老庄的“天人合一”境界和哲学是缺乏“主—客”式思想和认识论,是未经“主—客”式思想洗礼的一种原始的“天人合一”,未达到欧洲“主客二分”式思想长期发展之后的高一级“人—世界”合一水平的 (张世英,2004:32)。由此看来,在《流云小诗》中,宗白华所表达的生命经验,是他经过西方“主体—客体”思想洗礼,在有了“主—客”式思想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式“天人合一”哲学的重新表述。
李泽厚曾说宗白华的思维方式是抒情的、古典的、中国的、直观的、偏于艺术的 (李泽厚,1981:2)。不过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流云》宗白华所表达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哲学固然有浓郁的中国情调,但其文字表述所表现出的思维进向或思维方式却又体现宗白华接受过西方思辨哲学训练的思维素养。正是经历过了西方现代“主—客”式思维的洗礼,宗白华在《流云》中所表达的生命哲学才既具有东方式深邃的沉冥,又有了西方式理性的清明。那么,宗白华为什么在极接近直观世界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地方,又与中国式的神秘和混沌划清了界限的呢?主要原因在于宗白华在开始写作小诗之前,就已经经历过比较系统而深刻的西方哲学思维的训练。1914年夏天,17岁的宗白华入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工学堂中学部就读,深受德籍教师迪斯莱兹的赏识。1917年该校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此时的宗白华无心学医,而是花大量精力来研读德国文学和哲学,尤其对叔本华、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和歌德、荷尔德林和席勒等人的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年,他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萧彭浩哲学大意》,表现出对叔本华哲学的深入领悟,也表现出宗白华良好的哲学思辨才能。
此后几年,宗白华没有停止过对德国哲学和文学的研读,也不断推出自己研读哲学的心得,发表多篇有自我独到理解的哲学论文,如《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哲学杂述》、《欧洲哲学的派别》、《“实验主义”与“科学的生活”》等。这些文章都显示出宗白华良好的西方哲学思辨功底。1920年,宗白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主要以修习美学和历史哲学为主。从宗白华所受的教育和自我研读的兴趣都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塑造了宗白华的世界观,而且对宗白华的思维方式也是一个良好的训练和培植,让他在思维方式上更加理性。西方哲学的思辨,特别是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一个重要的起点就是把自我和世界分开 (宗白华把这个理解为心物之辨),并把自我当做客体做精细的分析和研究,对自我意识、自我精神做深刻的挖掘和精细的分辨。西方哲学这种把自我意识、自我存在当做客体对象进行精细而深入打量的思维方式,在宗白华长期的阅读和训练中变成他自身的一部分,变成他的一种思维素养,也对宗白华的研究和写作自然会发生巨大影响。
《流云》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对自我进行观照的视角,跟宗白华这方面的哲学训练和哲学素养是不能分开的。中国古典哲学、古典诗歌对人如何化归于宇宙的迁流大化中的精神修习途径多有表达,但都像陶渊明那样不去分辨人在进入这一状态时精神的状况是怎样的。宗白华具备西方哲学的素养,能从西方哲学训练出的反观自我、认识自我的思辨理路出发,把个人精神深入沉浸在宇宙中的体验和精神状态进行捕捉、分辨,并在《流云》中用诗歌的形式传达和凝定下来,在“吾丧我”的时刻,去追蹑自我意念和自我的一线灵思,把自我在高峰体验的心灵状态进行状写,把那种深远幽眇的心思和沉冥到“无尽的深”而领悟到“最生动的‘生’”的惺惺喜悦进行思性的表述。
所以说,宗白华与中国古人在以深心的自我领受宇宙之真方面是完全想通的,但中国古人对“与道冥同”的表达止于自我消弭,宗白华由于所受西方自我分析的思辨哲学训练,使他能在这一时刻把自我超拔出来,对高峰时刻的自我进行辨析和表达,把一种飘忽不定、微渺不可言传的精神经验用明白的语言形式固定下来,化解了中国人对“道”、“天地之心”的体悟过程中的混沌和神秘主义因素,赋予其理性的清明。所以说,宗白华把中国古人这方面的描述向前推进了一步,将其现代化了。这也使他的诗就不完全是东方的或中国式的,不完全是传统的,而表现出东方和西方交融、古典和现代结合的特色。
李泽厚.1981.序[M]∥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彭锋.2002.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87.
张世英.2004.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宗白华.1981.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M]∥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宗白华.1989.我和诗[M]∥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宗白华.1994.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M]∥宗白华全集(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