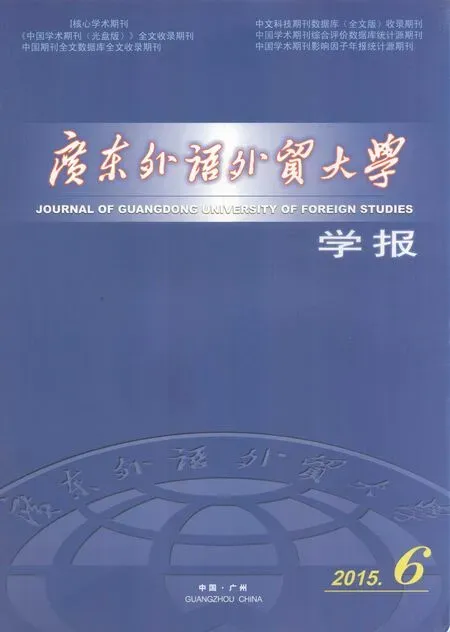返回自然的乌托邦——论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的空间叙事
2015-03-20沈永英
沈永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420)
勒·克莱齐奥被誉为是“世界主义”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描绘主人公漂泊流浪于世界各地,空间叙事成为其小说重要特征之一。在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叙事中,情节的展开与人物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叙事,后者往往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超越了前者。空间的场景不仅是小说叙事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成为作家写作特点的表征。不同空间的建构以及个体对于空间的体验成为小说的叙事线索。勒·克莱齐奥代表作《沙漠》发表于1980年,小说主题秉承作家一贯的写作风格,以非洲某个部族的小人物的遭际命运来突显非洲大陆的文明受到资本主义的挤压和冲击的过程。《沙漠》有两条空间叙事线索:一是以努尔为代表的沙漠蓝面人后代在非洲大陆上反抗侵略者的反殖民战争;一条是女主角拉拉从沙漠空间被迫进入现代都市空间,辗转流浪后返回沙漠故乡的经历。这一过程也是漂泊者拉拉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追寻之旅。
勒·克莱齐奥小说中人物在不同的空间迁徙流转,自然空间与都市空间的强烈对比成为文本鲜明的叙事特点,这与人物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方 (2013:122)认为:“勒克莱齐奥小说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自然空间逐渐从隐性走向显性,成为都市空间相对等的存在,甚至成为超越都市空间之上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沙漠》所展现的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都市空间,同时也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都市空间,人在都市中逐渐失去自我,走向异化之路。而自然空间则是人的精神栖息之地,它让人的灵魂得到提升与净化,心灵变得纯粹而宁静。回归到自然,返回沙漠故乡成为了《沙漠》的空间叙事主旨。我们认为,勒克莱齐奥所指的返回自然空间,目的是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亲密对话的理想状态。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实际上给人类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孤独,而都市存在的环境污染、物质至上、人的异化等一切现代疾病让勒克莱齐奥不得不去寻找另外一条反思现代性的出路。事实上,西方许多作家已经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后果与不可低估的缺憾。回到自然空间,回到人原初的纯粹的境界,恢复心灵的平静与安宁,实现“诗意栖居”(海德格尔),恰恰就是勒·克莱齐奥在空间叙事中所建构的理想境界。但是这种空间叙事建构呈现出来了一种“乌托邦”叙事特点,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说叙事理想。如果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的空间叙事是关于非洲原始部落的赞歌,无法解决非洲黑人现代性剧烈的冲突与种族之间的割裂等问题。
一、自然空间叙事:家园意识和身体记忆
在小说《沙漠》中,勒·克莱齐奥以拉拉和努尔两个主人公的视角来展开叙事。这种叙事视角的特点在于叙述者随着空间的转换,展示不同的身体体验,从而凸显了自然空间与都市空间二元对立的差异。《沙漠》女主人公拉拉父母早亡,被姑姑阿玛养大,在部落中得到亲人的关爱,她与自然空间亲密贴近,不受约束、自由自在地成长。由于战争的原因,拉拉离开沙漠流落到法国马赛,生活在底层的巴尼街,成为白圣人旅店的清洁工,目睹了许多黑人在马赛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后来拉拉被摄影师发现,成为当红的模特,但是拉拉放弃了豪华的生活,回到了沙漠故乡。而小说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努尔追随蓝面人领袖阿兹尼亚与异族的侵略者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没有枪炮,只有大刀和木棍,甚至是徒手的作战。面对枪支和大炮,血肉之躯的沙漠战士纷纷倒下,队伍的幸存者们紧跟领袖。然而风烛残年的阿兹尼亚也结束了生命,努尔目睹了这一切,在黑暗中依然等待光明,依然守护着沙漠这片土地。
在拉拉的叙事视角里,沙漠自然空间是幸福的存在,拉拉身体的记忆感觉在空间中凝聚,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家园意识。因此,勒·克莱齐奥的家园意识,是建立在原住民朴素的原初的空间感上的价值理念。加斯东·巴什拉(2013:9)认为:“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时间而凝结下来的延绵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巴什拉关于空间的鸿篇巨著告诉我们,空间是人的情感的依托之所在,也是人本体的存在。而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空间叙事元素包括沙漠的沙土、风、火、水、海等构成了一副异域生活的图景,建构了沙漠人的家园意识和身体记忆。海德格尔也认为“空间包含着被压缩的时间”,对记忆来说,最重要的是空间就是家—— “把人类的思想、记忆和梦想结合起来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戴维·哈维,2003:273-274)。勒·克莱齐奥把沙漠蓝面人的家园意识纯粹还原为自然空间的建构叙事,从拉拉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角度展示了自然家园的真实存在。
(一)土地。沙漠这片土地里,给一般人的感觉是贫瘠荒凉的,但是沙漠部落的人们却对洼地、山川、土地充满感情。拉拉熟悉沙丘的每一种肉质植物,每一块洼地,以及沙丘中的蚂蚁、金龟子、蜈蚣、苍蝇、蜥蜴等小动物,沙漠的蓝面人及其后代生于大地,长于大地,向往大地,并以大地为最终的归宿。沙漠的孩子“是沙石、风暴、光明和黑夜里生长的男女,像梦一样出现在山丘的高处,仿佛来自没有云彩的天空,四肢经受了大自然苦难的磨练”(勒·克莱齐奥,2010:3)土地的形象是自然的形象,它包容了一切,无所谓好坏,人在土地上生存,与沙漠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而沙漠的岩洞,则像母亲的子宫一样保护着人类。拉拉和牧羊人阿尔塔尼恋爱时光,都雕刻在岩洞这一沙漠空间中。拉拉就如自然界的精灵一般,与阿尔塔尼没有世俗物质欲望的交易,纯粹是身体的交融,他们在岩洞一块光滑平整的大石头上融为一体,实现肉体与精神的结合,爱与灵魂的息息相通。
(二)风。沙漠环境中,风是一个强烈的意象。拉拉“只要吹到风,她就很高兴。”风给人自由的感觉,既有彪悍的一面,沙漠的风暴是令人恐惧的,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然而,轻悠温和的风也时常拂过拉拉的脸。拉拉各种内心体验被风以各种嗅觉、听觉的形式传递出来,从而带来了天地的气息。
(三)水。沙漠人喜欢水, “水,也是美的,”拉拉在雨天静听雨声,在深夜入眠,还可以去城里的浴室洗个热水澡。拉拉喜欢“还有像白雾一样笼罩着整个大厅的水蒸气,天花板上积了一层层水珠,透过窗户散发出去,光亮摇曳不止。”“这水多么纯净,多么美丽,这是直接从天上落到水池里的水,它是多么新鲜,肯定能治好那些需要水的病。”(勒·克莱齐奥,2010:240)除了雨水之外,拉拉还对大海有特殊的感情。小说故事发生在北非,面对地中海,有许多大海的景色描写,而拉拉经常唱的一首歌是《地中海》。
(四)火。拉拉爱火,大家都喜爱火,尤其是小孩、老人,每当有一堆火燃起,他们便盘着腿,围着火坐着,茫然的目光注视着跳跃的火光。火堆燃烧着,是老人给孩子们进行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时间了。火是光明的象征,给人以希望和热量。沙漠人不惧怕这种热量的传达,反而在皮肤的灼烧中感受到自然的力量。
以上四种空间自然元素显然为主人公拉拉的家园意识和身体记忆奠定了自然原始的基调,作家在叙事过程中也强化了身体各种感官对于自然元素的体验和反应,从而强调人物身体与自然界纯粹的亲近。作家所营造的不同于一般的家园意识,以家庭的舒适和建筑空间的宏伟,布置的精巧而引人入胜。相反,自然空间就是拉拉等沙漠人的家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沙漠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沙漠“被想象成一个集中的存在。它唤起我们的中心意识”(加斯东·巴什拉,2013:19)。沙漠广袤的空间给了沙漠人共生的自我认同的文化情感积淀。这个空间既是沙漠族群生活的环境,还因此催生形成了沙漠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勒·克莱齐奥通过拉拉的视角,表现了沙漠固有的古老部落的生活方式——自由,惬意,无拘无束的方式,既不是亚洲宗法制度价值观念的认同,而是一种真正的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大自然的方式;既不是被物质和欲望所制约的令人窒息的生活方式,而是充满了空灵和自由,自然与人和睦相处的生活方式。因此,沙漠空间成为了拉拉记忆的承载物,甚至带有宗教性质的“神圣空间”(龙迪勇,2014:36),与她在都市空间的生活具有不同的意义。
二、都市空间叙事:边缘化缝隙化的生存
《沙漠》第二部分是以漫游者拉拉的视角和体验来叙述法国城市马赛的街道、白圣人饭店、火车站、贫民窟等都市空间形象,展现了非洲黑人边缘化缝隙化的生存。沙漠的蓝面人后代离开了沙漠,置身于水泥、钢筋和混凝土的世界。这些泥土和沙缺失的场所,即人的本原缺失的场所。勒·克莱齐奥的空间叙事对于都市人类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严肃的批判。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曾提出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他认为对空间切割的过程忽略一个人的真实体验,列斐伏尔从方法论上给我们启示,要打破二元对立的空间模式,必须以第三空间的形式来穿越森严壁垒的界限 (列斐伏尔,1959)。因此,沙漠作为感知的空间,与都市构想的空间呈现相互对立的姿态,而处于都市边缘地带的第三空间便是拉拉生存之所在。作者通过拉拉的叙事视角,建构了独特的空间形象。
(一)街道。《沙漠》小说中最著名的街道是“巴尼街”。拉拉从非洲来到法国马赛,与姑姑阿玛重逢,他们所居住的是马赛贫民窟的巴尼街,“窄窄的小巷,剥落的旧墙,昏暗的屋子,潮湿寒冷的房间,房间里混沌的空气令人窒息”(勒·克莱齐奥,2010:256)。黑人们就是巴尼街的工厂不停地劳作,成为工业社会的永不停歇的螺丝钉。巴尼街穿梭往来的是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经常有各种暴力血腥事件发生。而面粉广场的普瓦街,则是红灯区,有大量的妓女出卖肉体。拉拉目之所及的街道,基本是底层人民所生活的贫民窟。
拉拉在街上结识了十四岁的小偷拉第茨,他心地善良,喜欢美丽的拉拉,用盗窃的钱给拉拉买吃的,温暖了在大城市底层挣扎的拉拉。但是拉第茨却在停车场盗窃过程中被警察追捕到大街上被车撞死。作者以拉拉的认同经验出发来建构的街道,显然是罪恶的场所,噩梦的空间。
(二)白圣人旅店。一所低端又鱼龙混杂的旅店,四层楼房,底层是殡仪馆,十分破旧,里面住着各色人种,充斥着暴力和色情。老板则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间里监视员工和顾客。拉拉在白圣人饭店担任清洁工,并住进了饭店顶层的小楼阁,每天接触到各种污秽的垃圾,还目睹了赛莱左拉先生晚景凄凉地死去,这个居住的环境与空间让拉拉内心恐惧又害怕。而反映拉拉处于都市的个性特征的私人空间——小房间则是“摆满了扫把、水桶和破烂东西,只有一盏电灯,一张桌子,一张帆布床。”在这极度压抑的居住空间中,拉拉感受不到都市生活的半点快乐。
(三)车站。拉拉喜欢在车站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喧闹声中她仿佛是一个孤独的灵魂。火车站附近有许多乞丐,妓女,流氓,他们在黑暗的夜色中过着非人的生活。拉拉的视野所触及的车站空间,是灰暗的边缘地带。
(四)咖啡馆。都市空间中属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地方,每次拉拉与拉第茨交流,都是在咖啡馆中进行,甚至几次晕倒在咖啡馆中,也有好心人送来热的三明治果腹。咖啡馆的包容性,沟通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
(五)摩天大楼和舞场。作者蓄意建构的是马赛底层空间的形象,而关于摩天大楼现代化的内涵毫无意外的缺失在拉拉的视野里面。巴黎大饭店的舞场是让人感到“恐惧和空虚”的地方,而不是现代生活的标志。
以上五种都市空间的叙事建构体现了马赛的“黑暗天空”、“黑烟弥漫”、“昏暗角落”,其叙事目的无不强化了拉拉居无定所,无法返乡的内心悲凉之感。“她多么想快快地离去,穿过城市的街道,一直走到没有房子,没有园子,甚至没有公路和河流,只有一条渐渐消失在远方的大沙漠的小道上。”(勒·克莱齐奥,2010:240)拉拉身体对都市空间的抗拒从而决定了她无法融入都市,成为漂泊者。有学者指出,“边缘化、缝隙化空间是指远离社会生活中心的区域,包括各种缝隙、角落、边缘等微不足道的空间形式。它不仅在现实空间中特定的位置,而且它总是对应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契合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童强,2010:93)拉拉成为都市的边缘人,生活在都市社会的“缝隙空间”。非洲来的黑人在巴黎,在马赛,在尼斯,都没有过上幸福的有尊严的日子。他们很多人去当小偷,沦落成为妓女,加入黑社会,处在社会的底层毫无保障地活着,成为都市“缝隙空间”的“囚犯”。
都市“缝隙空间”的生存叙事作者把集中笔墨在主人公拉拉身上。如果按照一般的叙事,拉拉要在新的环境中完成身份的转化,即以他者的形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体,她没有接受资本社会的筛选,沦为金钱的俘虏。她之所以能够坚持个人的身份不被异化,源于坚持了沙漠人的身份认同。“认同在这里仍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自我认同就是这种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它包括人的概念 (personhood)的认知组分。成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反思行动者,还必须具有有关个人 (如用到自我和他人时)的概念。虽然存在这种概念的一些因素对所有文化都是共同的,但对“人”的理解则肯定依文化的改编而改变。在转换的场域中运用“主我”以及每个已知文化的特质的能力,是个人性的反思性概念的最近被特定。”(安东尼·吉登斯,1998:59)事实上,她被摄影师发现她的美貌,成为风靡一时的海报明星。但是拉拉始终按照个人逻辑和价值观来生活,没有被都市的消费环境所异化,坚持“自我的反思”,反而觉得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拉拉没有实现都市他者的转换,反而作者一直强调拉拉的主体意识和对沙漠文化认同的心理。
沙漠的“土地”和“风”、“水”、“火”等空间元素所代表的自由和快乐,与都市的街道、旅馆、倒塌的楼房、窗口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不同的空间感受展现拉拉不同的自我认同体验。“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 (安东尼·吉登斯,1998:59)拉拉反思个人的存在,最终感到一种无限的空虚感和无根性——没有文化根基、家园意识和身份归属感,灵魂处于流亡的境地。以拉拉为代表的沙漠人缺乏社会和文化身份,这一切都日渐削弱了他们对都市空间的热情向往。拉拉憧憬着平等自由的的生活,希望和那些当地人没有距离感的生活,他们以“他者”的身份寻求全然的自我表现和文化认同,却愈发感到了自我身份的边缘化和处境低下,在现实社会的迷失使得他们义无反顾的要离开都市。
三、漂泊者的乌托邦之旅
《沙漠》结尾部分叙述拉拉从都市返回到了沙漠。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努尔在战斗结束之后依然期待明天的生活。而拉拉对牧羊人的思念,无法融入都市空间,成为消费社会的逃遁者。她身体的逃离和流浪成为寻找自我的唯一武器。勒·克莱齐奥在《沙漠》中预设拉拉离开的依据给予读者一种想象,即非洲黑人保持非洲部落原始文化的本真,远离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和消费社会的金钱法则。勒·克莱齐奥在拉拉身上也寄托了个人的理想,拉拉以近乎完美的形象来抵御资本主义的异化和符号化。如果说沙漠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传统,必须做出的选择,要么是武力的独立,要么是人性的异化,从他者成为进入异族文化的主体。努尔的经历恰恰代表沙漠蓝面人部落为了独立做出决绝的斗争和牺牲。他们捍卫的是他们的领土主权,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
拉拉最后放弃都市一切舒适的生活,回到故乡,在母亲生下她的那棵树下,以相同的方式,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加斯东·巴什拉曾《空间的诗学》指出了人类对于鸟巢诗意的想象。巢之于鸟,正如家之于婴儿,梦想喜欢栖息在高处,代表童年和纯真。栖息在两根树叉上的鸟巢具有女性意味,鸟巢像子宫,孕育着新的生命。《沙漠》结尾的无花果树“巨人铁壁一样有力的粗大”,护卫着漂泊者的母体。拉拉就在树底下生下了孩子,在大自然的保护下回到了沙漠人原初的真实的状态。这种传承既是诗意的想象,又是痛苦的现实,在自我认同和追求的过程获得终极的意义。
勒·克莱齐奥认为,不以文明的名义去掠夺和改变,尊重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沙漠中的蓝面人就是“想象中的共同体”(本迪尼克特·安德森,2005)。这是作家本人对自然空间的乌托邦的想象。福柯 (2006:53)认为:“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类似的总的关系的地方。这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空间。”小说的叙事总是在虚构中进行,我们无意讨论勒·克莱齐奥空间叙事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认为勒·克莱齐奥所建构的沙漠自然空间是“甜言蜜语”的乌托邦,其建立在都市和自然对立基础上的作家一厢情愿的自我想象。《沙漠》寓言般的漂泊者返乡之旅,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保持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平衡状态,这是作者为流浪者漂泊的乌托邦代言的理想。然而,如果我们带着现实的批判眼光去审视《沙漠》的自然情怀,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甜言蜜语”乌托邦。因为,拉拉即是返回沙漠,是否可以回到从前?是否可以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当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拉拉和她的孩子能否置之度外不受干扰?答案显然不能。在大树底下生下孩子的拉拉,有可能因为缺乏医疗条件像母亲一样难产而死,也有可能获得救赎。而现实生活中的非洲,有疾病和瘟疫,有种族之间的割裂和仇杀,每个地区都有其不同的矛盾和冲突,非洲的原住民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一样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商品和资本的流通依然存在。那种原始的生活,田园牧歌式的成长只能成为过去,不能昭示未来的道路。因此,面对现代性的冲击的问题,勒·克莱齐奥给出的解决方法只有返回自然,才能心灵安定的诗意栖居,而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文学成为了勒·克莱齐奥想象中的乌托邦,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蓝面人”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生存和发展,回去的也就是很少的一部分,流浪和漂泊是沙漠人无法停止的宿命,拉拉或是重复母亲的路径或是寻找自己的未来在小说的结尾有了虚构和想象的力量。
勒·克莱齐奥没有因为纠结于自然乌托邦的建构而放弃关于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进一步探索,他在后续的小说《寻金者》、《乌拉尼亚》等探讨的是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种探索显得更加成熟稳健,而创作手法也更加多样。但总体而言,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对两种不同的空间叙事建构无疑是与作家本人早年在非洲的经历有关,而对于非洲自然空间的叙事建构,有别于传统的作家对于黑非洲的印象,因而成为他的经典作品之一。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本迪尼克特·安德森.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戴维·哈维.2003.后现代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方,樊艳梅.2013.勒·克莱齐奥作品中自然空间的构建[J].外国文学研究(4):122-130.
加斯东·巴什拉.2013.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勒·克莱齐奥.2010.沙漠[M].许钧,钱林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龙迪勇.2014.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06.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6):52-57.
童强.2010.权力、资本与缝隙空间[M].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