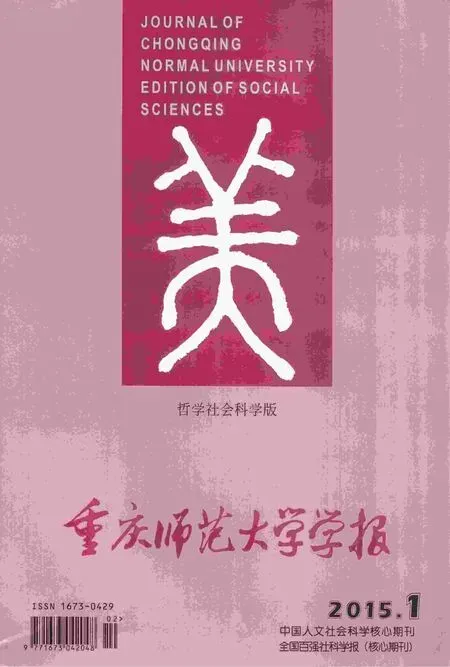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2015-03-20王敏
王 敏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误读”作为一种阅读现象,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是一种应避免的错误,其反面的正确阅读即是“正读”。既有“正/误”之分,就必然存在一定的阅读标准。如果以艾布拉姆斯“艺术批评的诸坐标”为参照系,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论主要是以“世界”和“作者”及其之间的关系为意义来源。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以“文本”为研究重心,读者系统文论则是把“读者”作为意义研究的中心。在文本意义研究问题上,真正实现颠覆性转变的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也是解构主义批评的奠基者,他提出“作者之死”的观念,消解作者意图的权威,倡导“可写的文本”,这可以看作是“误读”思想的萌发。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提出“一切阅读皆误读”,一方面否定了传统“正读”的存在及其权威性,另一方面视“误读”为一种绝对的存在,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全面展开。就耶鲁学派的学术历程来看,德里达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著名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被誉为解构主义的宣扬书,也是耶鲁学派文学批评的基本纲领,其发表标志着耶鲁学派展开文学解构活动的起点。在这篇演讲中,结构主义的中心全然消解,探讨文学的另一种方法取代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这就是“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德里达从此与美国思想界、与耶鲁学派其他理论家结缘。从1966年起,他便定期在美国几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与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一起组成了蜚声一时的“耶鲁学派”。耶鲁学派把德里达哲学思想运用到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之中,首先由德·曼和米勒分别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论,然后发展成为包括哈特曼和布鲁姆在内的强大文学评论队伍。
然而,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从诞生之初起,就由于其激进的阅读观念而不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以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也不断地与各种反对的声音形成争锋。这些论争围绕着解构主义“误读”之边界的问题展开,在讨论中把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推向深入,形成对这一理论的全方位审视。
一、解构主义批评的语言修辞论与意义观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种文学阐释结果都是无限阐释可能性中的一种,这是因为文学文本的阅读要牵涉到许多因素,正如解构主义的阐释者乔纳森·卡勒所总结的:“给定文本的复杂性,比喻的可逆转性,语境的延伸性,加上阅读之势在难免的选择和组织,每一种阅读都可以说是片面的。”[1]181文本内部的语言修辞、外部的语境及读者差异,这些客观存在的复杂因素,使得难以形成全面的、绝对正确的理解,每一种阅读方式都只能是单方面的、不完满的,每一时代的读者都可以证明前人的阅读是误读,却又被后来的阐释者发现残缺不全。因此,概而言之,“在一个较其倒置更为可信的形式中,理解是误解的一个特殊例子,误解之一特定的离格或确认。……在一个总体化的误解或误读中运行的阐释过程,既促生了所谓的误解,也促生了所谓的理解。”[1]157由于消解了“正读”的权威地位,“误读”不再被视为边缘化的存在,而一跃成为理解的一种合法形式。
伴随着对“误读”的重新认识,传统设定的以获得“正读”为目的的各类阐释标准被取消。首先是对作者意图论的消解。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口号,作者原意不再是作品的唯一意义,文学阅读和阐释活动成为一种独立于原作者的文学再生产活动。其次,文学意义也不仅仅是文本字面的客观意义。文学文本的性质,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一个文本可能会把它无力表述为一个命题的东西,某种与意义与表意的本质有关的东西,‘示’(show)于我们。对于德里达来说,一切语言都展示着这种超出准确意义的‘剩余’,一切语言都始终威胁着要跑过和逃离那个试图容限它的意义。”[2]131~132本有所言、有所不言,在言说的文字之外,更有许多难以言传的、不能用命题来陈述的意蕴被文本字面义所掩盖。因此,文本意义不能通过字面意义的归纳总结来完成,必须通过反复的阐释活动,挖掘文本内部各层面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因素来揭示更为复杂的潜藏意义。第三,文学意义也不是读者所能完全赋予的,读者所拥有的视野是有限的,不能阐释出文本内在的所有可能的内涵。解构批评家反对“自信”得到真理的批评家,任何阐释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都具有偶然性,所以都只不过是极有限的解读方式,在它之外还有许多种解读可能性,因而不能简单地将某一种结论作为中心和标准。
解构主义批评家的阅读实践否定统一标准的存在。希利斯·米勒在专著《小说与重复》中指出,艾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自从面世以来受到了各种角度的阐释,其中米勒较为认可其中的十五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视野下的性的戏剧;一个与门、窗的母题有关的神秘故事;一个关于强烈激情受挫的道德故事;一个关于性与死亡关系的故事;一个关于作者对她死去的姐姐怀有同性恋感情的故事;或者一出风暴与宁静对立冲突的戏剧……米勒本人则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作者宗教观点的戏剧性故事等等。[3]50这些阐释在批评方法上有社会历史的、精神分析的、原型批评的……多种方式,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十分明显,作者意图、文本语言、读者感受等阐释标准都发生了作用,但都只是多重阐释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所有阐释都只通过一定方式而强加给文本的一种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模式的存在。由此,米勒总结道:“最好的阅读是那些能够最充分显示文本的异质性的阅读,这种阅读是对由文本决定的、系统相关却又逻辑矛盾的意义形式的展现。”[3]51可见,在解构主义批评家那里,由于不存在统一性的标准,文学文本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准确意义”,具有多种潜在的意义生产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作者意图指涉的主观意义、作品“书页文字”的客观意义,也不只是读者阅读赋予的某一种体验意义,而是文本自身因语言修辞而存在的多重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生产出不同的意义,只能在误读性的接受活动中把握它们。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之所以推翻一切阐释标准,是因为文学阐释是在一定语境中发生的,而语境是不可饱和的,这就决定了意义的不可确定性。语境构成了文本阐释的意义场,是制约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语境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意义在语境中生成,被语境所限制和规范,另一方面语境本身是无限的,因而又赋予意义解读的无限可能性。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反对先验化和普遍化的意义阐释,认为文学解读是对某一境遇的反应,同时也会引发另一不同的反应,依此类推,不断延伸下去。这就正如米勒所说:“标准法语或标准英语中那个假定的、充分的语境是一种错觉。”[4]276不存在一个可靠的语境来对文本进行孤立、封闭的研究,文本意义总是在开放的语境中展开,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独特的风格,因而注定无法一劳永逸地解释清楚文本的意义。文本在再语境化的过程中由自身向他者转化,可以脱离原始语境而在其他语境中不断重复,从而实现意义的延伸。因此,对文本最佳的解读,就是在无标准的前提下展示出各种可能的意义。这些意义同时存在于文本之中,但在逻辑上彼此是不协调、不统一的。
二、“作者意图论”之争
“作者原意”是传统阅读理论重要的判断标准,却也正是解构主义批评家坚决否定、力图颠覆的标准。在他们看来,阅读的魅力和价值不仅不在于遵从作者意图,恰恰要用创造性的意义形式来颠覆作者意图。这正如哈特曼所说:“认真的阅读不就是一种复杂的辩护吗?这种辩护反对一个骗人的神祗——也就是反对我们称之为一部小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和有吸引力的实在的作者——创世者。”[5]61这一点构成了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与传统阅读观念之间的冲突,使得持传统观念的批评家担心由此带来文本意义的混乱。美国学者赫施便尖锐地指出:“对作为意义规定者的原来作者的消除,就是对使解释具有有效性的唯一有说服力的规范性原则的否定。”[6]14赫施是作者权威的坚定拥护者,在他看来,作者意图是意义的来源,也是阐释活动不可逾越的边界,对作者意图的消解会使得其他任何阐释失去说服力,这意味着阐释有效性的丧失。
文学语言不同于普通语言,它具有多义性特征,对这一点赫施是认可的。为了在多重意义中显现作者意图的地位,他把意义分为“含义”和“意义”两种:“一件本文具有着特定的含义,这特定的含义就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中,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而意义则是指涵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意义总是包含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的极点就是本文含义。”[6]16-17这里,“含义”是运用语言学方法所得到的意义,具有稳定性原则;“意义”则不是固定的,与具体的阐释语境有关,包含种种变化。由于外在语境的存在,一个文本可以有多个并行的阐释。然而赫施又指出,所有阐释都不应违背作者意图,否则“意义”一词就失去了价值。这也就是说,“含义”作为一种客观的、内在的意义,它能够传达作者本意,因而是意义阐释活动的基础;“意义”是读者对作者本意的领会,是主观的、外在的意义,必须在作者意图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显然,这种重“含义”而轻“意义”的阐释思想,是以作者意图来限定其他多重阐释,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必须作为对作者意图的揣度而存在。因而可以说,作者创作时的意图是文本的唯一意义标准。
赫施用“作者意图”来统辖所有语言的意义传达,认为不管是文学语言还是普通语言,都应当服从作者的原意,这也就把文学和其他语言形式混为一谈了。巧合的是,赫施和德里达都有把文学语言与其他书写语言一视同仁的倾向,但立足点却是根本相异的:德里达把所有书写都视为如文学语言般具有修辞性,因而是多义的;赫施却是把文学语言视为如普通语言般一定要讲究原意和确定性,因而是单义的。两种迥异的观念正反映出解构主义语言观和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差异。赫施坚持传统语言观,把作者原意与文本的“有效性”与“客观性”联系紧密。不可否认,赫施对客观性的重视,对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意义研究有纠偏作用,然而他对读者主体的忽视也有偏执一端的缺陷,取消了文学语言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因此,仅从作者意图的标准来讨论这个有效性与客观性的问题,是失之偏颇的。
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也曾撰写了论文《如何以文行事》,不无讥讽地批评德里达、布鲁姆以及读者反映批评家费什:“在我们这个阅读时代里,文学交际行为中的第一动因是作者。对一个不再是新手的人而言,看到近来的书和文章作者得意地宣称自己死亡,总让我觉得好笑。”[7]251他秉持“作者意图论”宣告:“不论批评家针对弥尔顿而创造的文本是多么有趣,都远远比不上弥尔顿写给他心目中那些读者的那个文本,尽管这些读者在数量上并不多。”[7]265关于传统文学批评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艾布拉姆斯的理解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即把解构主义批评视为全新的阐释范式,它与传统理论是根本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把它自身推入颠覆一切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中,因而失去了批评的价值。艾伯拉姆斯打了一个比方:单义性阅读是一棵高大的橡树,它扎根于坚实的泥土里,由于被解构批评这根长青藤心怀叵测地包围缠绕而受到了伤害。然而事实上,解构批评家存在与传统相关的保守倾向。米勒从“deconstruction”(解构)入手,指出:“任何一种解构同时又是建构性的、肯定性的。这个词中‘de’和‘con’的并置就说明了这一点。”[8]130~131解构批评中同时包含着否定和肯定、解构和建构两个方面的辩解。误读理论反对传统批评对确定性的追求,这并不意味着误读理论完全抛弃了传统批评,也并不把文本瓦解成支离破碎的片断,误读并不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伤害文本的意义,反而以更全面的方式来建构文本意义,以误读的方式来对既定意义作修正与补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的误读理论离不开传统阅读方式,这并不意味着解构批评是依附于传统批评的。艾布拉姆斯把与语法相关的阅读称为“基础阅读”(under-reading),认为这是意义阐释的第一层;把针对语言修辞的阅读方式称为“超阅读”(over-reading),视为阐释的第二层,并且它是建立在第一层阅读之上的更深入的阐释方式。这种分类方式表现出逻辑的力量,修辞语言就是附加于语法功能之上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立足于语法的阅读是必需的,而立足于修辞的阅读则是可有可无的。米勒反对这种划分方式,认为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不存在这类等级关系:“没有艾布拉姆斯所假定的那种普通的‘基础阅读’的东西……事实上从一开始,超阅读也就仅有一种形式,即对语法和转义的共同阅读。”[8]130~131也就是说,在对文学文本进行语法阅读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修辞阅读,这两种形式在阐释过程中不是相继而出,而是同时发生、并存共生的,当一种意义不存在时,另一种也就无法存在。文本各种阐释方式之间,不是等级递进的关系,不能说一种阅读是另一种阅读的基础,它们是并列的。文本具有多种复杂意义,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另一次阅读方式的踪迹,但这踪迹显示出的是对另一种阅读的消解而不是承继。误读理论不是层层深入,不追求终极意义,而是层层颠覆,体现出文本的非逻辑性,目的在于使文本中各种因素活跃起来。
三、“文本意图论”之争
意大利符号学教授昂贝多·艾柯从“文本意图”的角度对误读理论进行了批评。艾柯并不全然反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多义性的观念,他接受了文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阐释这种思想,肯定了读者在阐释文学文本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早在1962年,他就在被誉为“意大利新先锋派”的代表作《开放的艺术品》中提出,任何艺术作品,即使是已经完成、结构上无懈可击的作品,依然处于开放状态,具有开放式结构,提供了无限多个阐释的可能,读者可以不断地参与阐释,发掘文本新的、甚至作者未曾想到的内涵。然而,艾柯小说《玫瑰之名》发表后引起了关于“玫瑰”的阐释热潮,一时间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乃至匪夷所思的阐释一拥而上。面对这种意料不到的情况,艾柯提出了“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的问题。他于1990年在剑桥大学主持了一场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讲座,与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三人展开辩论,探讨有关意义的本质以及诠释之可能性与有限性的问题。艾柯所谓“过度诠释”是指过于主观、不顾文学文本内在含义的阐释活动。他指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不是没有边界,不设定界限的阅读只能干扰对于文本意义的解读,必须保持严格鉴定的尺度以防止阐释的失控。艾柯认为:“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说一个文本潜在地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9]25他明确指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德·曼、米勒的批评方法赋予了读者过多的阐释自由,由此带来“无限衍义”。艾柯强调说,阐释符号不能随心所欲,文本的解释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和标准。[9]42
为了抵制无限制的误读,艾柯提出“文本意图”的概念来作阐释的标准,认为读者阐释的应当是文本本身所隐含的意图。“文本意图”在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不受制于作者意图,也不会对读者意图的自由发挥造成阻碍。它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10]68然而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具备一定素养的“标准读者”,即按照文本的要求、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的读者。同时,艾柯觉察到让“文本意图”充当诠释的限定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历史的发展会影响这种操作原则,因此他又引入了“历史之维”这个概念,指出文本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相关联,历史语境的变化会导致诠释结果的不断追加。虽如此,艾柯又指出:不管在什么历史语境下,经典的诠释都要考虑文本的意图,远离了“文本意图”,也就逾越了合法诠释的边界。
艾柯一再声称:“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着力强调“文本的内在连贯性”与“无法控制的读者冲动”之间的区别,强调前者的权威。[8]130~131然而,艾柯理论有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因为任何理论家都没有资格确定“过度诠释”的标准,即使是在同一个时代也不会形成所有人都承认的标准。就“文本意图”来说,是必须依靠读者来发现的,但同时它又束缚、限定着读者的阅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陷入一种悖论。基于此,乔纳森·卡勒批评道:“艾柯被他对界限的过分关注误入了歧途。”[11]130他认为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任意性并不意味着意义是读者的自由创造,相反,它反映了语言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表明文学语言的运行机制是复杂的。并且,甚至可以说,对文学文本内在因素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即使是“过度阐释”,也比只是回答标准读者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更好,因为它有可能获得新颖的发现。对于艾柯提出的“历史之维”,卡勒也指出:“语境本身是无限的:永远存在着引进新的语境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惟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设立界限。”[11]130语境所蕴含的因素是变动不居的,不能预先为它限定边界,因而对经典作品的诠释存在着无限衍义的可能性。可见,“文本意图”说的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试图为共时的文学作品阅读与研究确定一个意义方向,从而排除那些在共时状态下对文本不合理的诠释,但它毕竟不足以囊括文学阐释活动的多重决定因素,因而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关于文学意义阐释标准问题,赫施、艾布拉姆斯及艾柯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批判,分别从传统作者和现代文本两个角度展开,为误读理论有效性的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然而,无论是作者还是文本的意图,都不是文本意义的唯一决定因素,不能为文学阐释提供标准化的意义模式,否则阐释活动又将走回封闭、单一的老路上去。实际上,由作者、文本、读者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产生了意义,这些因素都可以作为意义阐释的标尺,但不应将任何一种固定化为永恒的、权威的标准。这些争论,体现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传统阐释学、现代文本理论的差异,然而却很难说最终解决了阐释标准的问题,这却也正说明解构批评家主张“一切阅读皆误读”、反对阐释标准单一化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误读,反映出人类面对语言的矛盾处境:一方面,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交流的媒介,人类必须依靠语言来相互交流、建立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语言却并不可靠,它所呈现的未必就是本原世界,因为按照解构主义理论的思维原则,“真理”是被悬置的,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对“诗”的“思”需要无限进行下去,对已有定论需要进行不断的反省,从而使文学艺术更显生机与光彩。
[1]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Miller,J.Hillis.,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4]米勒.1984[C]//.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M].张德兴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6]赫施.解释的有效性[M].王才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7]艾布拉姆斯.如何以文行事[C]//.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周劲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8]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C]//.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艾柯.诠释与历史[C]//.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0]艾柯.过度诠释文本[C]//.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1]卡勒.为“过度诠释”一辩[C]//.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