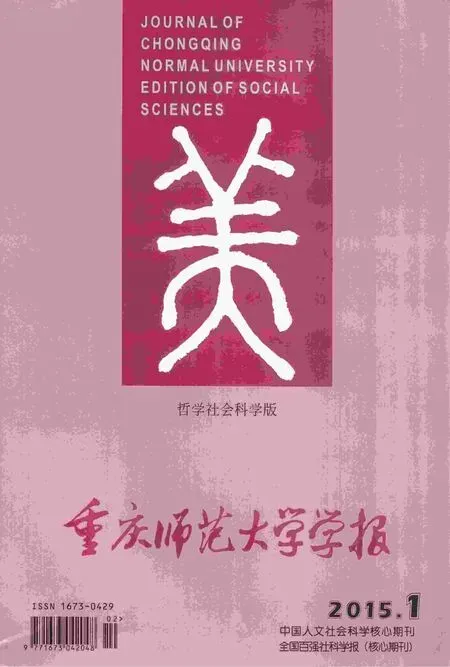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2015-03-20叶李
叶 李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叙述历史的态度与历史小说的尊严
今天,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强调“活在当下”,甚至试图将之泛化为现代社会普适性在世态度的人们,对历史演义和演绎历史的兴趣与叙事冲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从盗墓到考古,从专家坛上坛下、书里书外讲圣祖明君、贤臣高士到职业写手、业余作者掀起“天雷阵阵”的穿越之风。讲什么样的历史固然吸引大众的视线,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展开历史叙事时“我有我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较《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和《明朝那些事儿》的畅销现象,更值得玩味的是书名本身所隐喻的态度与方式。当对历史的发问与追索由“历史是什么”置换为“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对“是什么”的回答由“上下五千年”、“国史十六讲”、某某史论一变而为唐宋元明清的“那些事儿”,我们便不难明白,“历史”对于诸多身处当下价值多元杂糅的文化语境中充满叙述冲动的个体来说,既无需膜拜为旧历史主义里绝对的客观存在,也不用安放在新历史主义的讲坛上从诗学意义或文本建构的角度来审视。在那些饱含“求真”之欲的探讨里,历史的面目如此严肃、深沉又复杂难测——历史这个概念对于漫长历史进程里渺如恒河之沙的个体来说,仿佛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庞大固埃”,又仿佛幽深而神秘的黑洞,或者像是时光隧道里传来的旷远的回声。平凡的个体对于巨人的每一次接触都有可能是“盲人摸象”式的探寻,而非庖丁解牛式的全盘在握;黑洞充满巨大的吸引力,被深深吸引的个体却无法绝对靠近;那旷远的回声引人在时光隧道里发足飞奔、寻踪觅迹,然而却征途遥遥,难明所终。现在,对于星光灿烂的“历史的天空”,满怀敬畏的仰望不是唯一的姿态;洞穿岁月烟尘、拨开历史迷雾、寻找真相的决心与信念不是必需的准备;在阐释与建构中返照我们的来路,深掘历史之根,汲取精神与力量,重现光荣,遥望梦想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理由。抛却这些之后,历史就不再是意味深长的千年一叹,不再是神秘艰辛的文化苦旅,不用“借我一生”也能寻出“笛声何处”。历史没有那么难,就像“初恋那件小事儿”一样,它不过就是那些人的那些事儿——历史可以不过是些好玩的故事,可以是一次“少年的奇幻漂流”,可以是一场荡气回肠的“风花雪月的事”,可以是一个交织血腥与暴力的阴谋,可以是中国版福尔摩斯的悬案奇谭。
在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压缩历史的宏大话语之后,人们乐此不疲的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历史书写中的“流行Style”在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引无数粉丝竟折腰。流行自然可以成为一种写作追求,但在良性的叙事生态里,流行绝对不是唯一的价值所在,我们对作品、对叙事的期待远可比流行更多。当此之时,刘保昌先生通过崇文书局推出的《楚武王》恰恰回应了此种期待。作品疏离“流行前线”,暗淡了狗血八卦,远去了奇侠幻情,立志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于重走“寻常路”的叙事选择中显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以彰显历史意识的写作姿态,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捍卫当代历史小说的叙事品格与尊严。
在逐潮而动、闻风而写的书写者那里,历史是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只要这打扮足够受欢迎。刘保昌则在《楚武王》中做出了“不合时宜”的逆向写作选择:不是为历史这个小姑娘穿上最时尚的衣裳,而是“为楚人和楚王‘正名’”。对于作者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写作冲动所在——“拙作正是这种‘正名’冲动的产物”。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有时候体现我们本质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创作亦然。娴熟的手法、良好的语感、精巧的结构,简言之,熟练的技巧所代表的叙事的能力未必能够最终标示一部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和它的品质,文学作为蕴含着“梦想力量”与“希望原则”的“世界上曾经知道的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有时候在创作中选择怎样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去展开叙述、用怎样的艺术理想引领叙述,可能比技巧所表现出的叙事能力更能凸显写作的品质。《楚武王》正符合这样的判断——用富有勇气和包蕴“理想力量”的叙事选择体现了作品值得赞赏的品格与质地。
选择“困难”还是选择“容易”,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这个选择的勇气就在于对问题给出了舍易而求难的答案。毫无疑问,遵循当下流行的套路,卸载看似沉重的历史意识,悬置对历史的发问与追索,回避史料的爬梳与甄别,不过借古事的躯壳,完成“故事新编”——回到古代谈谈情、说说爱,讲讲宫廷秘闻、权谋要略,营造历史的梦境成全现代人的白日梦,撩拨现代人内心隐秘欲望的兴奋点,对于写作者来说既讨好又讨巧——投大众所好,又能把艰难的写作转化成便宜行事,因为“对于历史,更多的是想象”[1],只需靠想象历史的方法便能轻易地去填充历史叙述。可是,如果把实现为历史“正名”的写作冲动视作一部历史小说写作旅程的抵达之地,那么对作者来说,通向终点的道路上实则关隘重重。“历史诠释的本身就是艺术”[2],用历史小说为历史“正名”、为历史人物“正名”,从历史到文学同时对作者提出挑战。史料、史观、史识、史见、形象塑造、语言运用、叙事策略样样都需要作者通关。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如何恰当地择取剪裁,如何使史实的叙述与文学的虚构水乳交融、合情又合理,如何用文学之美照亮历史之真,用历史之真熔铸文学之美,这些既考验创作者的知识储备、艺术功力,也必然需要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力。字字看来皆不易,数年辛苦不寻常——“这部篇幅不算太长的《楚武王》,前前后后竟然写了两年四个月,其中的艰难,的确始料不及。几度驻笔,几番犹疑,最后知难而进,终于完稿。”[3]308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有勇气的选择不是源自追求“异乎众人”、刻意反弹琵琶的冲动与偏执,而是基于长期浸润于楚文化研究中而勃发的兴趣与热情。作者楚地楚人,在楚文化的熏染陶养下又系统地研习楚地历史、文化流脉,这使其对楚文化有着清醒的历史认知,又不乏精神血脉深处那一份文化认同。二者共同造就了作者面对历史的思索、质疑、发问——“在既有的历史文献、文学创作中,楚王都被丑角化、妖魔化,几无例外,其根源在于‘中原正统’史观。戴上‘中原正统’的有色眼镜,则楚人莫不沐猴而冠,楚王莫不小丑跳梁。其实只要稍作思考,我们就会心存疑惑,如此弱智的楚人楚王,怎会立国八百年?又怎会从方圆五十里的蕞尔小邦,发展壮大为方圆五千里的东周时代的煊赫大国?”[3]308~309发问是探寻的起点,作者由此希图正视历史而展开追索,以历史理性和文学的情感力量消除基于“偏见”的误解与误读,显示另一种理解历史、澄明历史的可能——楚地不是化外之境,楚文化并非怪力乱神,楚人也有豪杰英雄、人物风流,“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领先,再从中兴到衰败,从辉煌到落寞,其间蕴含着多少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吸取和借鉴?早就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早就应该有几部正面描写楚国兴毁成败的历史小说”[3]309。
如果说“傲慢与偏见”仿佛冷雪寒冰,而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对于历史更合理的理解与认知就似为冰雪所覆盖的那片静寂而冷硬的冻土的话,那么没有什么比“理智与情感”更适合充当融冰化雪、解冻驱寒、洞照历史幽深处的阳光。这次为历史正名的旅程正是一次充满理智与情感的探寻。对于一部哲理小说来说,用故事或一个个形象揭示世间的真理、人生的本质、万物的普遍规律,用虚构的艺术向世人吐露世界最幽深的奥秘,正显示了其“理性的深度”;而对于一部怀着严肃目的的历史小说来说,对“历史”有所揭示,不管是以还原或重塑的方式去实现,都不是“逐末”,而是不折不扣的“逐本”。历史理性的驱动往往潜隐在这种“逐本”式的追求背后并提示了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理智”的存在。显然,《楚武王》正是这样怀着严肃目的的历史小说——“为历史正名”无疑意味着作品要用文学的方式“寻找、发现并呈现历史的真相”。作者汲汲于此,所以虚化历史,把历史打造成白烟缭绕、迷雾茫茫的迷蒙化境,着力以情感激流的跌宕漫洄演绎豪情壮歌、心灵舞曲、意绪幽渺就并非其选择。同时,尽管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竞起,风云变幻,遥远神秘,充满冲突又蕴含丰富的可能,但作者也无意就此选材择料,拆解拼贴组合重装,搭建最瑰奇炫目的舞台,用最曲折离奇的情节、匪夷所思的场面、拍案叫奇的人物把历史讲述成摄人心魄的传奇。虽然,在楚国崛起的那片历史的天空之下,战争、杀伐、恩仇、血债、情爱、欲念、诱惑、漂泊、死亡,每一点经由文学的浪漫想象、艺术夸张成就通俗传奇的因素都不缺乏,然而在作者笔下,一切仍然在历史理性的范畴之内展开叙述。在这部作品里,演绎历史从来不是为了把历史变成最有趣的演义——很明显,呈现真相或者说“正名”的行为离不开某种依据历史材料基于理性的判断,而最大限度地传奇化历史中的人与事显然殊途异路。
《楚武王》这个书名已经明确地指示出,在作者那里,认识一段历史从书写一个人物开始。实际上,从选择叙述对象开始就显示了一个谙熟楚史、具有专业历史素养的写作者结合写作目的从历史材料出发的精心考量。楚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不少,论起文治武功,非楚武王独有,楚文王同样颇有建树;说起宫廷喋血,楚武王也绝非唯一,楚穆王照样不落人后;讲起奇闻轶事、人生跌宕,楚武王难称“力压群雄”,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更是赫赫有名。不过,既然作者不是在为最浪漫曲折的传奇挑选顶合适的男主人公,也不是在为抒怀纵情的言情历史大戏寻找最佳男主角,即使我们不能排除写作者的某种情感偏好,稍微了解一下史料,我们也能明白作者选择背后的理智所在——楚武王的出现代表了楚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历代楚君中楚武王熊通第一个正式称王,使楚国的发展从此后不用受北方周天子的限制,他首创的县制对古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4],他雄才大略,广开疆土,使楚国由弱转强[5]。还有什么选择会比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会比这样一个人物崛起的转折性的历史节点更适合体现楚王楚民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更适合展现楚国由弱而强的发展之路,从而廓清中原正统观的迷雾,为历史正名。
二、历史理性:想象的边界
写作诉求往往决定了作者观察历史、呈现历史和展开叙述的角度与方式。希图为历史正名的作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叙述中化身为一段历史的介入者,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潜入历史的罅隙中打捞碎屑般散落的细节,用对细节的夸张与放大、或者以对历史细节乐此不疲的日常生活化书写消解历史的宏大、解构历史的整全感;当然,他也不着意于由历史人物的心灵褶皱中撷取、凸显无意识与非理性的精神片段展现历史因果链条的脆弱与荒谬。他更乐于充当历史情境中一个特殊的在场者——洞悉—切“已然”并具有充分的判断,用全知全能的叙事姿态胸有成竹地带领读者展开探寻之旅。于是,叙述人像是一个做足了功课的导游,引领我们在深宏的历史景观中目视耳闻。他缓步徐行,按照历史发展的顺时性线索,方向明确,路线清晰,一路向我们绘声绘影地描述人事风物,也时时考虑到历史旧迹对寻访者的隔膜而指点精髓要义,补叙背景知识,说明因果来由,有时也不惮于抽身而出,直接给出诉诸理性的判断和评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阐释历史的冲动始终潜隐在故事的推进中,描写与评述、说明结合的方式成为小说重要的叙事选择。叙述者从不回避以直接的评论与说明传达历史认知,更进一步说,基于历史理性的评价与阐述正是其实现“正名”诉求的有效手段与方法。因此,读者在小说提供的这场楚地漫游里,一边欣赏云梦春会的浪漫与激情,看年轻的生命如春花般怒放,一边听叙述人引经据典将云梦泽的地理位置、云梦春会的来历与习俗娓娓道来;一边看熊通自刀光剑影、政治阴谋中突围而出,自立为新君,一边听叙述人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出发评价其意义:“从部落联盟体制中蜕化而来的早期楚国,在弱肉强食、列强环伺的格局中,求生存的愿望是第一位的。历史的理性更需要有一位精明能干、能征善战的英雄作为自己的国君,而熊通,正是这样一位青年英雄。这才是历史的选择!”[3]164当小说写熊通在位日久,武技精进,政治上更加成熟,同时亦对周边小国征伐不断,急速扩张,叙述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抛出史书对熊通“强暴好战,有僭号称王之志”的记载,直发议论“这当然是中原史学家们,秉持周朝正统的历史观,对南楚所下的不实之辞”[3]209,同时又给出理性的辩证分析:“但也透露出某种历史的‘真实’,因为楚人自古就有‘楚狂’的称谓,熊通是楚人的代表,也是典型的楚人,‘狂’亦是他的人格特征。楚先祖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曾经自立为王,不久自去王号——时当周厉王时代。”[3]209叙述人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隐匿在故事之后,仅仅把故事交给读者,他总是乐于亲自出面在事件、人物和读者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直接面对读者解说、评析,引领读者触摸历史、理解历史。于是,在情节推动、事件勾连的间隙里插入的评述时时令投入故事的读者反抽而出,令其得以站在历史舞台之外,立于视野更宏阔的高远处,向那台上上演着的人物风流、金戈铁马、情仇爱恨、劳作征伐以审视的姿态投去遥远的一瞥。显然,叙述人并不希望这趟历史之旅中的人们仅仅流连于历史片段中的风情,淹没在碎片式的细节里,而恰恰希望借由基于历史理性的把握为他们建构起一种历史的整全感,勾勒出完整的历史逻辑链条,展现历史发展中的合理与必然,使其在文学的叙述中获得具有可信度的历史认知。
除了小说中的评述与议论直接有效地传达“正名”式的历史阐释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对于历史的文学演绎和想象始终以对历史的合理的理解为支撑,或者说对于历史的合理的理解为小说的虚构与想象限定了边界、提供了框架。作品里对于历史的阐释始终交融于文学的叙述之中,尤其是那些对于楚武王的认知与理解最容易产生争议的部分。熊通掌国后,重兵征申、一举灭权国、两番伐随等一系列对外征伐是《楚武王》中颇为吃重的章节,然而作者不只为战争而写战争,以“暴力诗学”展现刀光剑影、死亡极境而寄望于借血腥、杀戮来增添历史故事的精彩,也无意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把楚武王一再发动的战争和燃起的战火描写成一个雄强的王者在本能与原欲驱动下挥发男性荷尔蒙的结果。作者当然了解通俗传奇中的卖点,也从不排斥和回避历史中的偶然,然而他更乐于坚守一个专业研究者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理性,揭示事件与事件间的因果,探寻动机。所以他在这些故事与场面的描述中往往提供富有阐释功能的细节。比如熊通发兵平斗缗之叛前,与臣下有这样一番交流。熊通“端起长案上的茶杯,一口喝尽”,“接着道:‘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启草莽。迄今已历一十五世,蕞尔小邦,列强环伺,其中艰险,自可想见。然而,楚国先祖不甘沉沦,斗氏、成氏、蒍氏,多家老世族联手经营,外抗强敌,内抚众生,西开濮庸,东伐扬越,整军经武,未敢稍有懈怠。楚国民众,众志成城,誓死抗争,硬是在弱肉强食之际,堪堪地生存下来。多少血泪,流成了江水,莫不是为了楚国的强大,为了楚国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值此乱世,灭国的滋味不好受啊!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汉阳姬姓、姜姓小国,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相继被列强消灭,殷鉴不远,楚国可想步其后尘?’”[3]203作者借熊通之口提示我们,这一系列的征伐,除了归因于楚武王强暴好战这一传统史书富有偏见的解释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合理理解,熊通固然雄心勃勃,壮心不已,然而连续的征伐背后更有客观历史条件的驱策——诸侯割据、众强环伺之时,主动扩张谋求发展乃生机所在、出路所在。熊通的选择绝非个人意气,背后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当然不会缺少人之情性和个体生命的温度,但是人又何尝不是历史中的人,人的选择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熊通的一番诛心之论,“大家听得心惊肉跳”。“沉默良久,众人一齐抬头,看着熊通:‘君上,下令征伐吧!’”[3]203还是细节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认知:楚武王绝非嗜血好战而屡屡出兵,而是基于对楚国实际处境的清晰判断制定发展战略;也不是以暴君之淫威胁迫臣下屈从盲目的战争,无论是对外扩张还是平叛,他恰恰是以清醒的认知获得了臣子的理解,形成统一意识;他绝不是在政治上盲动,处于孤立之境,而是赢得了充分的支持。倘若熊通好战且暴,为何连续征伐却未尽失人心、千夫所指、孤立无援?叙述者通过这样的细节岂非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指出:“以往我们常常把连接我们与‘过去’之间的‘历史叙述’给忽略了,仿佛我们可以直接穿透历史叙述与‘过去’发生关系,因而‘历史叙述’仿佛是一面透明无碍的玻璃,常常被忽略不计,而后现代历史学则帮助我们认识到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6]118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叙述”的地位与意义则更加凸显,它甚至天然地与虚构、特定艺术形式的呈现交融在一起,以文学方式展开的历史叙述怎样也不会成为透明无碍的玻璃,更像是重演事件和铺陈各种人生形式的荧幕,不过,《楚武王》中对于历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并非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来填补“观察资料的空白”,相反正是“正名”的诉求决定了作者如何展开想象和提供细节,并由此完美地传达出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判断。熊通灭权国之后,随即设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权县,这是其载入史册的重要政治创举。可是,熊通一举灭掉权国,是纯粹心血来潮?是一味好战逞强?作者同样在史籍记载之外,用合理的想象于历史框架的细部填入丰富的细节,通过对于细节的描写传达出不乏历史理性的认知。熊通率车兵伐申失败。兵败后的战场一片凄寂。唐河两岸的春雾映衬着熊通战场失利的暗淡心情。他手抚“楚公家秉戈”,自觉此役无功,自己难辞其咎。可是,在斗缗、熊率且比相继就此次失利提出迥然不同的对策后,一代雄主,迅速调整心态,冷静分析,采纳合理建议,当机立断,决定回军途中灭权国,显示出“伐弱强楚”不可动摇的决心。他“眉头紧锁,突然虎目圆睁,道:‘权国新君性情高傲,耽于声色,横征暴敛,民怨沸反。只要示之以弱,令其麻痹玩忽,乘其不备,伺机进攻,仍然不乏胜算。如能灭掉权国,可算躬行天罚’”。[3]196这段描写充分显示了熊通政治上的成熟,灭权并非单为施暴逞强,而是审时度势之后扭转战败颓势的战略。且如熊通所言,权国君王荒淫无德,民不聊生,对权开战,代天施罚,灭除一个无道的政权,难道没有合理性?精心设计的情节为“正名”的意图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支撑:对熊通不可简单以暴君论之,相反,他对楚国的崛起有清醒的谋划和战略性考量,战争包括灭权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而这一系列的征伐也不能全然归结为不义之战,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熊通善于为征伐提供道义上的合理名义,出师有因也出征有名。布克哈特曾说:“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7]258显然,深具历史研究素养的作者在小说中充分展示了基于历史理性的想象的结果,并由此构筑了一条探索历史之“真”的文学路径。
三、情感:理性的限度
“但是历史学家并不只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史次序排列的事件。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着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但是他在他的概念和语词里注入了他自己的内在情感,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意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7]237按照这样的判断,既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需要调动个人经验与灌注内在情感来对历史上的他人经验与事件作出判断、展开叙述,那么“有其确定的诗性本质,有其超离的美学追求”[8]的历史文学在打开时光隧道,引领读者返回历史深处寻幽探胜时,就更有理由用情感、激情、个人经验在文学性的叙述中绘出丰富的精神图景,铺展生动的生活画卷,用妙笔状写情感的温度、生命的韧度与心灵的幽深、宽广,令人驻足流连,纵情千古。《楚武王》中并不缺乏这样的迷人“风景”。尽管作者言明立意围绕楚国的兴衰成败撰写历史小说,乃是源于作为一个谙熟楚史、楚文化的专业研究者为历史“正名”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并不是受历史理性的绝对支配,在完全依凭历史文献、查考事实,严格还原历史的框框内左冲右突,呈现严谨却枯瘦的历史文本,而是与另一种发自肺腑、作为一个“有历史”的文学痴爱者再自然不过的抒发自我的冲动交融在一起,激扬滚涌而至“月涌大江流”的阔大、深厚——“《楚武王》中自然也有我的自叙成分,有我成长和行走的人生经验。”[3]309作者少时便倾心于文学的缪斯,进入大学专研历史,后治现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历史与文学在作者的学养、研究经历和生命经历中本就浑然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在历史小说中寻求历史理性与文学的诗性的完美结合,既成为写作者清醒的写作意识,又是其发乎自然的内在追求,因为,“在内心深处,一直葆有一片文学的蓝天”[3]310。
起笔之初,作者就确定不移地追求历史中的诗,希图挥洒诗性、浇注诗情。“听着细雨敲打窗棂,轻风吹拂铁马,急雪扑打灯笼,浪涛拍抚海岸,无眠的深宵,内心总会涌动急管繁弦……这应该是一本饱含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和正义的书。”[3]310于是,投入个人的生命经验去贴近历史人物,“倾力塑造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活生生的生命”[9],写出历史中的人的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就成为了作者的追求。内心总有波澜的作者不能不灌注情感于笔尖写楚武王的行动与激情、写他面对的问题与寻求答案的艰辛,融自我的成长经验与对理想的坚持于楚武王披荆斩棘、排除艰险、强国兴邦的奋斗历程中。从这样的生命经验去体认、去书写的楚武王从一出场就不是政治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阴谋家,抑或屈居王兄之下、心有不甘蓄谋篡权的野心家,而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怀与政治理想,走过青春走向成熟的一代雄才,一身英雄气。王兄蚡冒在位,熊通虽遭防范,然而心无怨怼,低调行事,主掌大风堂,力行职事;楚庸之战建奇功,营救斗伯比智计出众,却不居功,不自傲,而是勤练武术,精修兵法。他与斗伯比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不作趁危夺位之谋,而论立国决胜之策,“底定江汉,重整江山;组建车兵,强国富民,方可大出于天下。代有传奇,只是主角已换,时势固然造就英雄,但英雄也未尝不可以造时势……”,思楚之危势,谋国之未来,天地豪情,壮志满怀。理想与才略的化合产生出惊人的政治能量和超凡的政治智慧:前途莫测不妄动不贪权;为奸所害身处危境,仍以国为重,宁舍己而免内乱;形势逼人退无可退则当机立断,顺势而为,果断继位;列强环伺,善谋敢战,拓疆辟土,求生存谋发展。“历史的理性更需要有一位精明强干、能征善战的英雄作为自己的国君。”[3]164作者笔下的熊通正是具备了能力也怀有高远政治理想的英雄。作者更通过在一系列具体历史事件中展现的英雄的性格、行动与抉择去表现这个英雄的追求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向,他用自己的努力迎来命运的垂青,历史选择了他,而他凭借睿智、勇气与无与伦比的行动力造就时势,开创历史。同时,这个英雄的奋斗之路也正是由于熔铸了作者自身对理想的坚执而产生动人的力量。现在与历史的互动,今与古的交流,生命经验对生命经验的交融从另一层面上实现了对历史的“正名”——楚人自有英雄出。
孤星血泪、卓然独立是英雄,投效名主、忠义无双、共成大业也是英雄,作者并不打算集中全副笔墨刻画孤身一人、举柱擎天式的英雄人物,而立意裹挟着情感的浪花写一群肝胆相照,勇往直前,共赴大业的英才与雄杰,绘出英雄气长。远见卓识、志存高远的斗伯比,武艺惊人、心念故国、为国远谋的斗仲比,风华正茂而置生死于度外、血染疆场的斗廉,江山代有才人出,楚地自古多英雄。这群“天地男儿”百折而不悔,追随着楚武王熊通的追求、理想与他的政治抱负,只为楚国在周室衰微,群雄争霸的时代发奋图强,屹立一方。英雄不仅是一个名称,更是一种气质,甚至拼死护主的忠仆琴伯,轻视生死、杀奸抗暴、后来成为楚武王之妃的卢妫也都充满慨然之气,令人动容。
无情未必真英雄,有情如何不丈夫,何况楚地地理条件与气候条件优越,“没有物质上过于沉重的担忧、羁縻,楚人才能在精神上多奇思幻想,在情感上多浪漫绮思”[3]56。写楚地楚人、为楚之历史“正名”,只走笔政治斗争、战争风云,抛开楚人在精神情感上的文化特质,必然大为逊色。对楚文化有着深刻体察与认同,希望写出青春、爱恋的作者怎么会容忍这样的缺失,他恰恰以此为重要线索,写出一片风光旖旎、浑朴率真、瑰奇绚丽。在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勾连的空白处、在史实与史实对接的缝隙间,作者以大胆又合理的文学想象挥笔其间,渲染出浪漫的色彩与氛围。
这种浪漫就来自于作者用怀着青春激情的笔调,写出旖旎之爱、原欲之真、神巫之奇。陨候宫内,人如冠玉、青春洋溢的斗伯比与姬荷再见倾心,风情万种的少女、心旌动摇的少年陷入痴狂而迷醉的爱恋,身心相合,人生自是有情痴,只因为“于斗伯比而言,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东西,可以历经沧桑而不褪色,可以饱尝苦难而备感温馨,那就是少年时代得到的真情关爱,那就是少年时代的那个大眼睛小妹”[3]72~73。“鱼游在水里,花开在风里”[3]73,青春那么美,正在于爱得那么真。楚武王的公主容兰对少年英武的斗廉初见钟情,一往而深。斗廉战死殉国,容兰痛不欲生,后在斗祁的包容下平静地经历婚姻生活,逐渐领悟爱的真谛、体会平淡中的温情。青春不褪色,就在于恋得那么深。云梦春潮云梦会,青年男女眉目传情,追欢逐野,尽享情爱,没有后世礼法的约束,只有“顺应天时、和谐阴阳”的认可,作者纵笔而歌“年轻男女的快乐,像天空那样高远,像云梦泽那样深广”,[3]65写熊通与几位女性的爱欲缱绻。这种对于本能的快乐的追求,不是淫邪歪道,而是春秋时代的时俗,折射的乃是我们的祖先在华夏文明青春期的原欲之真。
神巫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独特之质。如何把神巫文化的呈现有机地融合到历史事件的叙述、历史人物的书写中,是对作者艺术功力的考验,但同时也最能见出作者的匠心。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显露了自己的巧思与运用技巧的能力。他放弃对神巫文化做单列式地展现或简单的背景化处理,而是将之编织进历史事件的过程、人物命运的起伏,个体情感的跌宕之中,使神巫文化与历史叙事有机相溶。楚武王宠婢小致寻巫求孕,反遭迷奸侮辱,与下女月容被逐宫外,月容情人观海(巫瑞之徒)及全家被杀。祸种就此埋下。月容流落宫外,苦修巫术,成为女巫灵仙。王子公子元作为熊通的庶出之子,面对继统之争,为全身避祸,受巫师指点,决意职事巫祝,既可出入庙堂,又可在巫风盛行的楚国凝聚民心,襄赞国事,于是跟随月容习巫,有了交集。此后,登堂入室的月容既协助巫尹公子元力行巫职,抚慰亡灵,又癫狂纵欲,更处心积虑为旧情人报仇,最终刺杀了一代英雄楚武王。作者巧妙运用神巫文化这条线索连通朝与野、宫廷内与外,民风民俗与政治斗争,串起王子间的权力分配,王权的继承与传续,牵起人的情与欲,甚至用它写就楚武王命运的结局,赋予作品以传奇的色彩。公子元的选择,显示了神巫文化在民间流行和因此具有的重要地位,小致受辱无疑又揭出神巫文化中的糟粕。神巫文化不仅牵系人心所向、民风民情,甚至楚武王对巫祝的态度也经历了由反对到宽容乃至依赖的变化。作者绝不直接评述优劣好坏,然而情节设计本身已经足够显示神巫文化具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还有它瑰奇的魅力。实际上,盛行于楚地的神巫文化,岂非本就与楚人的生命千丝万连,早就深潜在楚人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世界之内?
爱恋、理想、浪漫总是天然地与青春绾系在一起。小说中的楚武王熊通从一出场到晚年身亡,没有流露过一丝暮气,他的性格自始至终都是坚毅强韧,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充满豪情。这种富有青春进取之态的精神特质从不曾改变,即使年近八十,仍要带兵亲征,直至殒命征途,死于“在路上”。在作者的笔下,似乎难见青年、中年、老年熊通的差别,他的整个生命仿佛只奏响过一支曲子,那就是“青春之歌”。在“青春之歌”的旋律中,楚武王将强国兴邦的政治理想的火把一直燃烧到生命尽头。从斗伯比、斗仲比、若英、姬荷到斗廉、斗丹、容兰,青春的圆舞曲代代相传,青春的爱恋、奋斗总是与青春的身影相伴。事实上,在楚武王的带领下,在英才勇士的努力之下,不断崛起的楚国,不正是处在自己发展历史中的青春期吗?作者有什么理由不写出这崛起的王国青春的姿态和深藏的青春能量呢?作者以动情的笔调摹写的英雄之气、旖旎之爱、神巫之奇、浪漫之情共同造就了楚国崛起的历史阶段的青春之美。
情感使历史理性具有了温度,也为理性提供了限度,使历史不至与诗分道而行。这样为历史正名就不是简单的用文献资料的现代译文进行证明,而是个人与历史的问答,个体与历史的对话,个人生命与历史中曾有过的生命经验的互动与交流,这是需要文学去发现、开掘的另一种事实。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作者抛弃历史叙事中一味个人化的追求,而转为“化个人生命”进历史叙事,“用诗意情怀去感知历史,去再现历史”[10],为历史“正名”的实践里就既有了史料支撑,又兼具了情感的认同。历史在这里不再是工具化的存在,不再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宫廷版,不再是以古代斗争哲学打通现代处世技巧的生存谋略的文学版。历史小说也绝不是借助历史的夹缝和幽暗的角落上演暴力和血腥的狂欢,并不因为“历史”一词所具有的距离而带来的安全性,借由历史秀下限、以文字的方式描写“恶之花”。历史小说里,人物的追求仍然可以是理想和奋斗。借由历史叙事我们回望过去,认清来路,所希望的还可以是用期待的目光迎接未来——这是《楚武王》对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持守。作者以清醒又热诚的写作姿态对历史小说书写的“最炫流行风”给出了严正的启示——“理解历史文学,应该把它统一到追问生活意义和历史意识的叙事本体的高度上”[11],这一点是不应被今天的写作者抛弃和忘记的。
这部着意“正本清源”的历史小说借用一部流行电影的名字来说可谓“非常幸运”——作品的品质不仅根植于有价值的叙事选择,还因作者展开历史书写的能力而获得保障——能力与选择共同赋予作品以光彩。摆在我们面前的《楚武王》证明了作者有足够的能力不致使坚持“理想力量”的叙事选择沦为想象历史的方法,而是呈现为令人欣赏的文学现实。这样的现实是我们期待历史小说摆脱了历史叙事的流行模式与“机械复制”后,不断奉献于读者面前的。
[1]陶春军.解构历史:新历史小说与穿越小说[J].广西社会科学,2010,(5).
[2]林佩芬.两朝天子·后记[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3]刘保昌.楚武王[M].武汉:崇文书局,2012.
[4]周家洪.楚武王的创新及其作用[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5]刘纪兴,贾海燕.楚国著名历史人物[J].世纪行,2005,(21).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8]叶诚生.构筑历史与人生的诗境——现代历史小说的一种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1).
[9]金汉.逼近:“人本”与“文本”——世纪之交中国小说的深层变革[J].当代作家评论,2005,(2).
[10]周百义.诗化的历史小说王国—读赵玫的唐宫三部曲[J].小说评论,2001,(6).
[11]陈雪虎.理解历史文学:叙事塑形与历史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