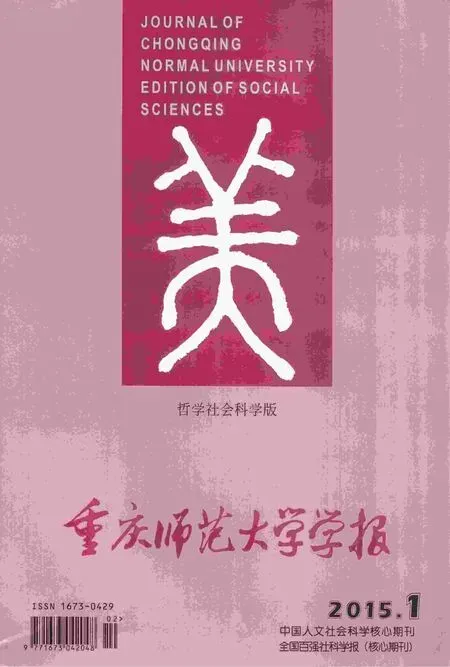人与城:刘庆邦“保姆系列”的城市书写
2015-03-20许心宏
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230030)
新世纪以来,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文学文本不可计数,内中切入的是对社会制度、城乡差异、生存地位、文化身份、家园意识等时代问题的社会反思。在文学的介入性、批判性书写中,文学与历史形成了同期共振效应。不同的是,近期的刘庆邦则专注于“保姆系列”的小说叙事,“保姆在北京之N”的副标即为此类小说的明证。聚焦在保姆寄寓化生存场所的空间诗学上,从性别意象上来说,农家出身的保姆建构了性别化群体症候的生存镜像;从文化空间上来说,它所切入的是城市家庭内部的私密空间;从叙事视角上来说,体现的是作家代言的内视角叙事特征。“保姆系列”的因人写城与城乡社会结构的在场,使保姆意象成为文化冲突的承载体,建构与表征的是城市意象的文化隐喻意义。
一、人与城:性别化、私密化城市空间构想
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式民工潮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而产生。裹挟在民工潮的生存迁徙中的农家女作为一个重要分支,她们在城市/农村、城里人/乡下人、异乡/故乡的求生空间与文化双栖的矛盾冲突中,其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交往方式出现了生存与身份的焦虑意识。在文化习得上,进城前的农家女在本乡本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原初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规范的认同感。然自从进城之际起,她们在异乡与故乡文化形态的差异性感知中,惶恐的则是故土文化的失依感。实际上,刘庆邦专题化的“保姆系列”文本,既难纳入城市文学流派中,亦难纳入乡土文学之中,相反则暗置于城乡冲突的结构化文化诗学体系中。在大时代的小人物叙事中,“保姆系列”文本中的农家女作为“卧底”与“尖兵”[1],建构的是城市外来者向度上的性别化城市意象。
保姆的职业劳作空间有其特殊性,因为她们寄寓于城市社会家庭内部。体现在文学叙事中,保姆视角切入的是世情化日常生活场景,它与华丽光鲜的城市光晕无关,相反却是“城市芯片”意义上的内探式写作。体现在小说叙事视角上,保姆作为“卧底”与“尖兵”,她们担负的是探秘者与发现者的角色,继而凿开了体窥城市面影的一个内在剖面。客观来说,城市本身就是待人阅读的文化文本,但源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叙事视角、文化身份的不同,文学表述的城市意象亦各有分殊。在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为人熟知的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茅盾《子夜》中的吴老太爷、高晓声《陈焕生上城》中的陈焕生、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等。实际上,文学长廊的乡下人进城在文学与历史的互证与阐发中,文学的“人与城”的叙事负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话题,内中的乡下人意象有其文化承载的历史意义,限于篇幅此处不论。当代文学史上,就“保姆系列”而言,若将其与邱华栋、卫慧、何顿等都市文学加以比较,则“保姆系列”的主人公不是小资、白领,而是学历层次偏低的社会底层群体。当然,将其与总体概念上的“农民工进城”小说文本相比,凸显的又是出生农家的性别化城市生存镜像。因而,嵌置于城市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上,雇主与保姆“主客之分”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内中寓意的则是性别化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问题。
聚焦在城市家庭内部,如果说“物以群分,人以类聚”,那么保姆与雇主构则成了最直接的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差异。如在《走进别墅》[2]《后来者》[3]《找不着北》[4]《金戒子》[5]等小说文本中,雇主与保姆人物意象并置,不过是时间化了的文化空间冲突,表征着主体性文化身份的差异化特征。身为女性,雇主也好保姆也罢,她们有着生理性别的同一性;然基于城乡二元户籍的不同,则有空间规训的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尊卑之别。因而,原本的雇佣关系却夹杂着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的高低贵贱之别。寄寓在城市屋檐下,保姆常是雇主话语刁难与身份审视的对象;而保姆眼中的雇主往往是尖刻、阴冷与自私的他者,继而对其加以嘲讽、贬压和丑化。在空间化权力话语对弈中,根深蒂固的乡土话语却被现代城市话语所排斥,继而处于权力话语的边缘。源于城里人与乡下人户籍制度的划分,保姆既怨怒又艳羡的是女雇主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当然,如此比较只是宏观层面上的,因为城里人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但就户籍划分与文化身份称谓而言,整体表征的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失衡与文化身份的不平等。
城市是客观的社会空间,本无空间性别的界定,但在空间与权力交叠的话语表述中,基于社会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结构的历史在场,使得性别化的生存场景愈加凸显了权力空间规训下的农民、女性、保姆的文化身份与社会角色意识,体现出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身份结构的内在统一性。在古代社会,保姆常被称为下人、奴仆、丫鬟,而当下社会则称其为家政保姆。不过,源于出身农家与农村户口的空间限定性,称谓的现代化却也无力改变文化身份的既定性。当然,除了《走进别墅》与《后来者》中相对高学历的保姆外,其他文本中的保姆学历较低且无技长,因而从事于庸常繁复的伺候人的底层劳作,内中又暗喻了教育失衡、农村社会发展迟滞的社会问题。因而,保姆进城之际即已背负社会惯性思维的传统、落后与贫穷的文化语义逻辑。基于此,即便与雇主朝夕相处却又近而不亲,根由在于文化身份与生存地位的空间化驯服。然就在保姆与城市的权力空间隐喻中,特别是在市场化劳动契约关系中,保姆视角的城市显示出空间意象的男权症候,继而“人不自贱,贱却自生”地难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中。这既表征着城市主体性的文化地位,又间隙出她们生存地位的弱势化特征。
二、叙事可靠性:代言化、探秘化叙事视角
且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亦不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就保姆系列发生于家庭空间的私密化“性叙事”而言,作者是何以得知的?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关涉到叙事“可靠性”问题。在此意义上,保姆生存状态的调查实录或许有着较为可信的意义,但也不能绝对化,因为任何文本的语言编码都暗含着权力话语的密置,可谓权力话语无处不在。在保姆系列中,文学想象的本身自有作者代言的特征,因而切肤切肉的生活原场景何以显现?原生态的农家女心态究竟如何?在此,有人认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总是一成不变地以与‘真人’对立为界定的;文学好像从来也没能把这位‘真人’传达给读者。”[6]57因而,就发生于城市家庭内部的“性”表述,难道是农家女口述给作者的吗?即便是,那么口述过程中她们是否回避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如果不是“访谈录”的口述,那么作者又是何从知晓的?其实,即便是口述史,谁又能明证口述者“口述”本身的真实性?显然,此乃文学的虚构使然。但是,就男性作家代言的家庭内部私密化叙事而言,作者的揭秘本身则潜隐着男权视角的窥视欲,特别是城籍男人与保姆的“性纠葛”叙事,如《习惯》[7]《钓鱼》[8]《找不着北》等小说文本中,作家代言的“性”叙事可谓游刃有余。问题是,这种“缺席化”的“在场”叙事,其情境真实性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兴许,如此疑问纯属多余,因为小说就是虚构。不过,小说文本通过保姆“性遭遇”的探秘式书写,旨在揭露出保姆生存境遇的私密性、阴暗性与尴尬性。
刘庆邦的中短篇小说多以情节取胜,这是大家所熟知的。然在接受美学角度上,保姆系列在情节诱人的设置下,矮化的却是读者的智商,难免不带有媚俗之嫌,因为“兴趣点”亦为“性趣点”。也许此举并非作者的本意所在,相反旨在寄意于性的文化能指意义,因为性既有自然性亦有其文化性。就后者而言,“性私密”叙事成为农家女文化身份与生存地位冲突的意义源点,内中既有城籍鳏夫性饥渴的为老不尊的性骚扰,亦有城里离异男人对保姆的猎色伎俩,还有默认丈夫“养二奶”的亚文化现象。然无论是性骚扰,还是猎色以及蓄养外室,保姆宿命式地成了被玩弄与被欺侮的对象。典型的如《找不着北》中的妻子对丈夫越轨行为的故作不知,如是心态既是对男权思想的屈服性认同,又是对女性意识的自我压抑。在现实情境中,妻子不过是暗借保姆的肉身稳控住丈夫的色欲。在性别意识上,她与保姆同属女性,然文化身份上前者是城里人,而后者是乡下人,因而,妻子眼中的保姆不过是丈夫的“玩物”,两者偷情与婚姻无关而与肉欲相连。小说文本既写出了妻子较之于农家女文化身份的优越感,又暗含着她对农家女生存地位的蔑视感。当然,妻子对丈夫的出轨可谓含恨在心,而对被丈夫玩弄的保姆,她又有复仇式的快感,这种心态既矛盾又统一。但是,就保姆的暗自庆幸与迎合雇主的心态来说,保姆又不过是作者怜悯大于批判的书写对象,因为保姆不过是城籍夫妻合谋下的“局外人”与“边缘人”。再就是《习惯》中病卧在床的鳏夫,女儿为其雇来的保姆就达十来个,然保姆受雇的时间都很短,因为其父虽卧病在床,但长期性压抑导致的心理病态,继而外化为对保姆的性骚扰。显然,外人无从知晓保姆的“被骚扰”,然小说经由保姆内视角的“看其所看”,旨在揭开城市家庭内部某种阴暗与病态。这种爆料性的揭丑化叙事,消解的是保姆视域的城市主流文化意象,最终促使保姆生存地位的低微内化为文化身份的暗伤。因而,保姆的进城史,既是文化身份的卑微史,亦为其心理私密的受伤史。
保姆作为打入城市内部的“尖兵”与“卧底”,作者本可承沿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入下去,但《走进别墅》与《谁都不认识》[9]却呈现出梦幻迷离的现代主义风格,因为两部小说的保姆仅流于职业的外衣,内隐其中的则为移花接木的作者探秘视角的在场。就前者而言,保姆与雇主儿子的“性娱”实为遮人耳目之策,继而密探城市上层社会权钱交易的内幕。但是,保姆的“献身精神”总觉得过于空幻,因为它缺少令人信服的坚实理由,且保姆的“卧底”显示出“为卧底而卧底”的主题先行性。当然,在创作心理学上,反证的则是作者在场性体验的有限性。因而,叙事技法的变换暗示的是作家边缘性想象的浅表与乏力。就后者来说,小说的开篇就布满了侦探与反侦探的悬疑色彩,因为女雇主希望雇来的保姆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因为她畏惧的是官商来往、钱权交易的“家事”走漏风声。反讽的是,保姆却恰恰是泄密者与偷盗者。保姆与其男友的报复行为,源于城里人对其文化身份的蔑视,如女雇主要保姆说话要说普通话,因为方言太土;其男友虽为小区的门卫,但却被城里人训斥为“看门狗”。经由隐含作者叙事声音的在场,保姆与其男友合伙偷盗的是不义之财,即便雇主报案也是投鼠忌器,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实际上,两篇小说的选题常见于新闻媒体的报端,而作者经由保姆视角的探秘与小说情节的构思而有了文学性。但是,在小说事件在证实与证伪的两可之间,文学的叙事有其“艺术真实”的光亮外衣,但“事件真实”的叙事可靠性也是其短板所在。
三、婚姻梯度化与情感暧昧化
婚姻乃人生大事,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在农家女进城的同时,业已潜隐着婚姻观念变化的可能性。不过,与城籍男性的婚姻结合见证的又是文化身份主体性与依附性的差异。《升级版》[10]中年轻貌美的保姆通过婚姻改变了农村户口。但实际上,农家出身的保姆还是半个城市人,因为若说她扎根在城里,只是她与城籍丈夫婚后却无子嗣,而“无子嗣”隐喻的是她成为城里人的未完成性。当然,就其嫁给城里丧偶的男性而言,可谓是攀上了高枝的“上嫁”。但是,如果说“少来夫妻老来伴”,那么两者的结合究竟谁是谁的“伴”呢?就“伴”的话语分析而言,保姆的“陪伴性”体现了城籍丈夫的主体性。因而,“陪伴”暗含的是其婚姻结合的替补性特征。虽然婚姻的结合引来了“周围人”的艳羡目光,即认为娶了保姆“值了”,而“周围人”不过是“城里人”泛指,因而看似“值了”的褒奖,寓意的是城里人对其婚姻本不抱多大期望,但因保姆宽厚为德的克己与隐忍,继而成了城里人认可的理想女性。按理说女人的伟大,母爱是其不可或缺的主要体现。然保姆主动提出舍弃生养倒不是说她没有生育能力,但究竟为什么呢?其实,保姆自弃生养之举,为丈夫化解了子女家产之分的潜忧。就丈夫而言,他不但抱得“少来伴”,又不担心父子不和,可谓是何乐而不为!从城乡户籍制度上来说,这种婚姻的结合体现的是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梯度特征,即保姆与城里人结婚并非不可,但农家保姆必须自知文化身份的“低人一等”,然后再由无悔的辛劳与宽容弥补文化身份的欠缺。惟其如此方能赢得城里人怜悯式的心理认同,而这种认同心理则源于保姆道德崇高的征服。其实,小说中的“周围人”看似为无关紧要的“看客”,实则是城里人自感文化身份优越的集体无意识体现。换言之,城市本无其扎根立足之地,因为跨越身份藩篱的“上嫁”终不过是“升级版保姆”。同样,《走投何处》中丧偶的农家母亲进城是为了照看孙女,其子虽经高考完成了“农转非”文化身份的转变,但儿子与城籍女子的婚姻却暗含着文化身份、社会地位的相斥性,因为小说中儿子形象的若有若无,表征的是其家庭地位的边缘化,其母因之亦愈加边缘化。时逢城乡家园双向无依的尴尬处境中,年迈的母亲嫁给了城籍的鳏夫,然这般“上嫁的替补”如出一辙地喻示着农家女性文化身份的低矮。
除去梯度化婚姻表征着文化身份壁垒的在场,在《钓鱼》《说换就换》《找不着北》等文本中,暧昧化的情感叙事亦寓意着如此的身份结构逻辑,只不过这种暧昧游曳在婚姻与情欲交叠的灰色地带。典型的如《说换就换》中的保姆受雇于丧偶的已退休的美学教授家里。虽说保姆的辛劳赢得了雇主的认可,但伪装的认可既有暧昧的情欲需求,又有朦胧的续弦之意。不过,教授之女还是歇斯底里地要辞去保姆,如是行为的怪异源于其女的创伤性记忆,个中原因作者虽未交代,但在其女“为尊者讳”的言辞躲闪中表明,其父早年就曾与保姆有着失范的暧昧行为。既是这样,其父本应自知女儿“说换就换”保姆的旧因所在,然作者对魏教授“不自明”的心理描写,看似抓住了读者的兴趣,然终有愚弄读者智商之嫌。就其女而言,她既是经历四次婚姻的失败者,亦是其父身心诉求的规训者。就其父而言,他虽披着美学教授的外衣,然与保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暧昧性交往,内中的“心怀鬼胎”却也不言自明。因而,小说在“父有其疾”与“女有其病”的隐疾化书写中,揭开了父女俩人格面具的画皮。但是,围绕保姆去留的父女暗战,保姆却成为殃及池鱼的无辜者。因为,保姆的“好”招致了教授之女“好的保姆都是妖精”的谩骂与诋毁。其实,教授之女与其说骂保姆,不如说暗贬其父老来寂寞的好色与狡黠。在小说结尾的突转中,其女为父雇佣一保姆,这使得其父的晚景更加压抑与寡味;与此同时,小说写已经离开教授家的保姆打电话给他,说有时间会继续给他“讲故事”。只是,保姆这般“以德报怨”与教授之女儿“说换就换”,如是冲突在寓意弱势的保姆在同情强势他者的同时,作者使用了“向内转”规避与化解现实矛盾的叙事策略,即坚固的身份冲突让位于农耕文化伦理的宽厚与慈悲。但是,这种退守式矛盾化解的避重就轻,既表明保姆生存地位的贫弱,又表明她在权力话语博弈中的孱弱无力。
四、空间寄寓化与心理隔膜化
源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城市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她们从熟稔的故土走进人地两生的城市。然而,城市社会对其“经济上接纳,地位上排斥”的处置方式,使其作为“外来者”的“边缘人”与“局外人”的身份意识愈加凸显,因而,文学的底层叙事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意识。城市本是开放的社会,但开放的社会并不是平等的社会。就保姆而言,城市宛似一块磁铁,她们对城市可谓是爱恨交加,城市总体上缺少诗意的光晕。退一步来说,20世纪中国小说镜像中的城市意象总体上亦是如此。但就进城的保姆而言,更加突出的是其性别化、底层化的生存境遇与文化身份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根植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语境,进城本身即已表明她们既是在寻求生存发展空间,亦是在感知与认识现代城市文明。风景不殊,时间流动,如果说“文变染乎世情”,那么与保姆叙事相比,可堪与其比较的则为“知青文学”。知青的城市—下乡—返城的空间行旅带生发了审美间距化的文化感知与乡愁建构。但是,作为文化身份相异的群体,后者在城市空间的仰视中,见证的则为城市空间表征的生存地位不平等的历史苦味。源于保姆劳作于城市家庭内部空间的特殊性,因而,正是城里人“家”的存在,反证的是农家女“他乡只是客”的身份迷失感、文化异己感与家园荒芜感等。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无论贫富贵贱,“家”表征的都是安全感与归属感的个体性空间,但越是走进城市家庭内部,她们越是自感外来者的文化身份,城市因之成了理想与压抑并错的“他者”空间。
实际上,除去“保姆系列”文本之外,作者在诸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到城里去》《家园何处》《兄妹》《到城里去》《东风嫁》等小说中业已写到农家女进城与返乡的时代主题。值得提及的,就是在《家园何处》《月子弯弯照九州》《兄妹》等小说篇什中,作者已发掘了农家女从“卖力”到“卖身”的生存转向问题,此项主题我们在《城市外来者:农家女身体书写与文化表征》中已有专门的阐述。[11]其实,相比于作者早期《毛信》中主人公视野的“城市”而言,“城市”不过是精神意念的“远方”空间意象。当然,《毛信》与铁凝的《哦,香雪》一样,她们怀揣“向外走”的“期待”与“等待”心理,乃为社会转型期乡下人文化心理的微观写照。但是,这种“向外走”有其共同的年龄症候,即它是乡下少女视角的城市遥想,因之城市有着朦胧的诗意。然从乡下少女到进城保姆,从空间意象的“遥远”到现实情境的“在场”,从“距离产生美感”的审美抒情到“现实场景”的历史批判,保姆视角的城市意象可谓是解构大于建构、批判多于认同。作者为了保证城市批判的空间有效性,选择了城市家庭内部场景作为文化冲突的切入口,内中性别化的探秘与揭秘的私密化书写,显示出了作者“以人写城”的社会批判意识。
[1]刘庆邦.进入城市内部[J].北京文学,2012,(5).
[2]刘庆邦.走进别墅[J].北京文学,2012,(5).
[3]刘庆邦.后来者[J].十月,2013,(5).
[4]刘庆邦.找不着北[J].上海文学,2012,(11).
[5]刘庆邦.金戒指[J].人民文学,2013,(3).
[6][挪威]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林建法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7]刘庆邦.习惯[J].作家,2013,(4).
[8]刘庆邦.钓鱼[J].作家,2012,(13).
[9]刘庆邦.谁都不认识[J],花城,2013,(4).
[10]刘庆邦.升级版[J].上海文学,2013,(7).
[11]许心宏.城市外来者:农家女身体书写与文化表征[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