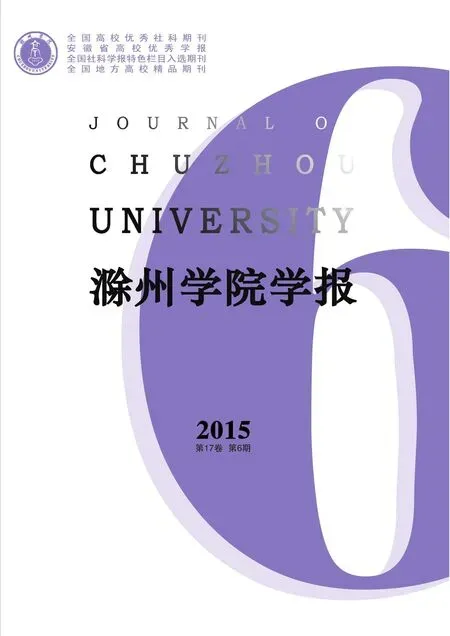以现代人文精神提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顶层设计”的思考
2015-03-20章会垠
章会垠
以现代人文精神提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顶层设计”的思考
章会垠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扰,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解决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困境的根本出路;而要建设好这一学科,就必须做好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顶层设计”。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顶层设计;现代人文精神
一、目前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高校一线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似乎都抱有某种不满情绪,他们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就如何解决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各种设想。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小力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1]一文中认为目前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课时压缩而引发的选择困难:是“应该强化文学史教学,还是增加作品的学习”?“课堂教学文学史论,有无必要”?不得已的选择是:“以作品选的学习代替目前的文学史论的教学,并尽可能地增加课时数。”孙先生的意思似乎是:都是课时压缩惹的祸;只要课时充裕,古代文学史论教学与古代文学作品阅读教学都能得到充足的课时保证,则古代文学教学便是一片艳阳天。
在笔者看来,课时的压缩只是目前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而非“问题”。“以作品选的学习代替目前的文学史论的教学”,不失为一条出路。但无论作品学习还是文学史学习,都存在“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这是两个远未解决的核心问题。
刘伟生在《历史真实还是心灵真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2]一文中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古代文学的教学成了‘职业的批评’”,“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显然失败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由于缺乏人文情怀、当代意识、学术规范和宽广视野,古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排除在现代学科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逃脱了文学传统应负的社会历史重任。……古代文学教学成了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很少做到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文学。”出路在于改造古代文学现有的学科架构,并据此改善古代文学教学。他认为:“要理顺历史传统与当代意识、社会本体与文学本体、宏观统摄与微观研究、学问文学与心灵文学的关系,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古代文学的教学也应以审美视野整合学术视野和文化视野。”
“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走出困境的正途。中国古代文学向来被认为是一门十分成熟的学科,或许正是这种过度自信遮蔽了这门学科历来所存在的真正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顶层设计”的缺位。这种“顶层设计”的缺失,表现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反思:
1.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价值指向这一根本问题还缺乏深入而明确的认知。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应确立自身的价值定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价值定位是什么?它与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的建设有无关联?如何发生关联?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把中国古代文学仅仅当作过往的陈迹,因而以冷漠的、知性的态度把它处理为一套“知识体系”,而漠视它与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存在生命关联的可能性。
2.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还缺乏一个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形相称、足以统摄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大文学”理念。以目前流行的反映论和审美论的文学理念来处理中国古代文学,难免会使其沦入一种扁平化的较低的层面。如何本着“文学即人学”的基本信念,探讨一种既能凸显文学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的个性特征,又能统摄各种相关人文学科、具有宏大视野、表现高远人文理想的大文学理念,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跃升至更高层面的关键。
3.基于上述两点原因,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性质,学界还缺乏准确的判断或定位。反映论的文学史观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社会史的记录;审美论的文学史观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美文的历史。这些观察的表面性与单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远未能切入文学史的核心,更是对中国文学史本质的遮蔽。
4.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全程缺乏整体性、有机性的观察与描述,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个别性的、线性的联系,而对中国文学史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有机关联,还缺乏宏观的考察。如此一来,中国文学史就成为一些偶发的文学现象的堆积,而无法对其成因作整体性的解释。
5.一种普遍存在的倨傲姿态也是困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因素。在诠释文学现象时常常出现的庸俗社会学论调以及在作品解读时通常使用的“时代背景+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认识意义”的模式,是这种倨傲姿态的典型表征。这种缺乏同情理解的倨傲姿态使人无法充分感受、体验作品的鲜活生命,因而也就无法产生心弦的共鸣和理性的洞见。它往往以分析性的冷漠态度,居高临下地君临于古诗哲之上,并以所谓“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其实乃是一偏之见)对古诗哲任意褒贬,因而往往降低或漠视古诗哲及其作品所固有的价值。
6.视点的单一与方法论的贫乏依然不容忽视。文学现象纷纭复杂,视点的多变与方法的正确使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方法创新乃是理念创新、学术创新的前提之一。目前学界部分学者秉持乾嘉学派的做法,在某些无关紧要且永远不可能搞清楚的细节问题上反复纠缠考证,使学术研究过于琐屑化,造成许多低层次的重复,而难以产生真正有创意的学术洞见。
二、学者们的意见
古代文学学界已开始注意到相关研究与教学存在的问题,并谋求某种改变。2008年9月首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根据舒红霞、隋丽丽撰写的《首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研讨会综述》[3]来看,本次会议成果有限,各种观点、建议依然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未能就上述问题有所阐发,未能对如何建设“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有效思考。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孙小力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一文中即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对此,笔者深表同意。然而,这种“人文素养”的内涵是什么?文章未能深究。
王前程《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兼谈高校古典文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4]一文即指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显著的实用价值,培养传统人文精神是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对青少年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宏博、最生动的活教材,高校应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古典文学的德育功能,使广大青年学生在学习古典文学的过程中获得传统道德精神的熏陶,从而真正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王前程看到古代文学所包含的传统人文精神,并强调古典文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值得赞赏;但笔者并不赞成“培养传统人文精神是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目标”这一断语。对传统人文价值,我们应该秉持理性审视的态度,因为传统人文价值中的许多方面,已不能满足建构现代心灵的需要。其实,我们在看到古代文学中的传统人文价值的同时,还应该别具慧眼,透过这种传统人文价值,去发现在其深处,还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现代人文价值——正是这种现代人文价值,才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拥有了超越时空的不朽魅力。葛剑雄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过:“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严格地讲,就是塑造一个‘人’字。要鼓励他去追求真理,有时也意味着,他要挑战一个现有的真理。”[5]何谓“现代人文价值”?葛剑雄对此进行了非常好的解答——那就是“普世价值”!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如果不能发掘、传播这种现代人文价值,恐难以参与国人现代心灵的建构,也就会丧失其活力。
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顶层设计”的思考
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解决目前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困境的根本出路;而要建设好这一学科,就必须做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顶层设计”。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可能还不成熟的思考,以期引起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一)确立“大文学”的理念
所谓“大文学”,就是立足于一种高远的人文理想,来努力突破目前那种或单从反映论角度,或单从审美论角度来看待文学的倾向,摈弃将文学与史学、哲学等学科置于同一平台而并列的传统做法,以“文学即人学”作为基本信念,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成因复杂、内涵深邃、影响深远的综合性精神现象,因而需要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地加以观察、体验和研究。为此,必须以史学的眼光、哲学的思维、文学的锐感,聚焦于人的内在存在形态,努力发掘在这种存在形态中所蕴藏的深层次的“人性-精神-文化-心理”内涵。这种“大文学”理念,实际上是要打破学科分野,综合运用多种相关的学科知识来探讨、描述人类的存在境况,尤其是人类的内在心灵存在状况——这正是文学所特有的对象领域。
(二)中华民族心灵史: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性质的重新定位
“文学即人学”,这是关于文学的经典定义,它揭示了文学的本质,是我们揭开文学奥秘的一把“万能钥匙”。
回归“人学”,基于上述“大文学”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因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全息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积淀、演变的全程,它饱含着我们先辈诗哲们在其特定历史情境中所产生的种种悲欢离合、心灵激荡、人生领悟、精神蜕变与人性光辉,其中蕴含着丰富深厚、超越时空、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价值,这种价值在独具民族特色的、精美的艺术形式中得以传达。
(三)当代国人的灵魂塑造: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价值的当下关切与现代审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指出:“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作文学的。”[6]任何文学,只有当它切入当下读者的生活与心灵,才能赢得读者的喜爱,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价值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作为汉民族的心灵史,其核心价值应在于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亦即当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的建构,能否做出贡献、做出何种贡献以及如何做出贡献。
随着左倾思想的逐步肃清与思想解放思潮的推进,当下应该无人会怀疑中国古代文学参与建构当代国人精神家园的资格;但对于“做出何种贡献以及如何做出贡献”,回答则莫衷一是。
《新民周刊》记者在与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对话时,对比了中国大学课堂与欧美名校课堂的差别:“英美这些名校的课堂还是思辨的。但是我们的多数老师有时还是单方面的传声筒,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些欧美的教授能把问题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截面。而我们的不少高校教师要么就是照本宣科,要么就是不着边际。”可见大学教育应该在“知识传授”“思辨能力”与“批判意识”三者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结构与平衡。由此,葛剑雄发现“什么样的社会,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而反过来说,什么样的教育,也会塑造什么样的社会。“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所以,“要鼓励他(学生)去追求真理”[5],从而塑造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创造一个崇尚真理的社会。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既是当下中国人的心灵关切,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现代审视,还应该秉持“拿来主义”的主体精神与“有容乃大”的若谷虚怀,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价值,乃至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价值,从而不断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传统。
(四)人文精神与艺术审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天职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当然是其本质属性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天职之一就是要准确鉴赏中国古人所特有的审美品质。然而,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停留于此;如果就此停留,不仅会错过古代文学更为精彩、更具现代价值之处,而且也会导致对古代文学的审美品质缺乏深刻领悟——美感背后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是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另一天职就是要阐明包含在文学作品中的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
(五)正、反、合、变:中国古代文学的有机整体观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顶层设计”还应该包含“中国古代文学的有机整体观”。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从未中断;事实上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因此,我们应该运用有机整体观来看待中国文学史,而不应将其割裂成互不相干的片段。在我看来,一部中国文学史,以逻辑语言来描述,乃表现为一个“正、反、合、变”的逻辑进程。
1.正题阶段——先秦两汉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可描述为中国文学史的正题阶段。这是因为:(1)以儒学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所倡导的理性精神,道德情感,现实关切与忧患意识,对历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强化,而日益显著。(2)与此相关联,儒家倡导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念,它对文学在道德伦理教化与政治干预方面的实践价值的强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价值取向起着一种影响深远的内在塑造作用。(3)由《诗经》确立的“风雅”传统(现实主义精神)制约着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审美特征。(4)“诗言志”观念的明确提出,使作家把努力培育并抒写其社会性、道德化的情感作为其使命,以礼为准则、以善为指归的情意抒写,使中国古代文学表现出一种醇厚深切的社会关切和现实情怀。(5)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受楚辞影响而产生的汉赋,因其与儒家文学观存在龃龉,而在整个汉代地位未定,这是儒家文学观主宰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表现。
总之,在正题阶段,文学还处于依附地位,对文学的艺术特质还缺乏清醒的认知。
2.反题阶段——魏晋南北朝文学
所谓“反题”,是对正题的反驳。论者普遍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代。首先,在反题阶段,文学摆脱了附庸地位,获得独立。曹丕《典论·论文》可视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宣言书。其次,对文学的艺术特征已有明确意识,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和抒情功能,陆机《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观点逐渐成为共识。第三,文学创作已表现出高度自觉意识,作家在题材领域、艺术形式、语言修辞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富于创造力的开拓与尝试。第四,文学理论在这一反题阶段取得巨大成就,《文心雕龙》与《诗品》是这一成就的突出代表。
导致这一“文的自觉”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的觉醒”思潮,而“文的自觉”则以其全部丰富感性表现“人的觉醒”的深刻主题和丰富内涵。这种“人—文觉醒”的内涵可具体表达为以下命题:我痛,故我在;我爱,故我在;我死,故我在;我畏,故我在;我乐,故我在;我思,故我在。
总之,此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都应置于“人—文觉醒”的大背景这下加以观察和解读。
3.合题阶段——唐宋文学
在“转益多师”的理念下,唐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唐代诗人面临前代巨大的文化遗产。是被遗产压倒,在遗产的阴影中裹足不前,还是化遗产为财富,创造新的辉煌,这是摆在唐代诗人面前的巨大课题。唐人的创新精神,就在于他们将中国文学在正题阶段所确立的现实人文关切的价值取向与在反题阶段所作的艺术探索,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加以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佛家禅宗义理神韵,做出了新的创造,使得中国诗歌文学精神获得深化与升华[7]。在这一过程中,唐代作家充分地表现出其作为创造主体的主体性精神。
词在李煜那里实现了由伶工词向士大夫词的转变,不仅使得新起的词文学接纳并弘扬诗歌文学的悠久传统,而且创造出“别是一家”的独特的美学风尚。唐诗和宋词一起将中国抒情文学推向极致。
4.变题阶段——元明清文学
一个逻辑进程进入合题阶段,往往意味着这个逻辑进程的终结;在这个即将终结的进程中,必然诞生一个新的逻辑命题,开始其新的“正-反-合”的逻辑进程。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学——抒情诗而言,以唐传奇为标志的中国叙事文学的确立和元明清时期戏剧与小说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巨变:一些全新的文学元素和文学样式兴起、发展,甚至取代了传统文学样式(诗歌)的主导地位,中国文学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变题阶段。
[1]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2007(6):43-46.
[2]刘伟生.历史真实还是心灵真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绥化师专学报,2000(3):93-95.
[3]舒红霞,隋丽丽.首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研讨会综述[J].大连大学学报,2009(1):94.
[4]王前程.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兼谈高校古典文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J].三峡大学学报,2007,29(6):41-45.
[5]季天琴.我们为什么没有牛校.[N].新民周刊,2010(47).28-32.
[6]宋石男.莫言与当代中国的魔幻现实[J].二十一世纪,2012.(6).93.
[7]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96.
I206.2-4;G642
A
1673-1794(2015)06-0115-04
章会垠,滁州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安徽 滁州239000)。
2015-05-11
book=119,ebook=460
责任编辑:李应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