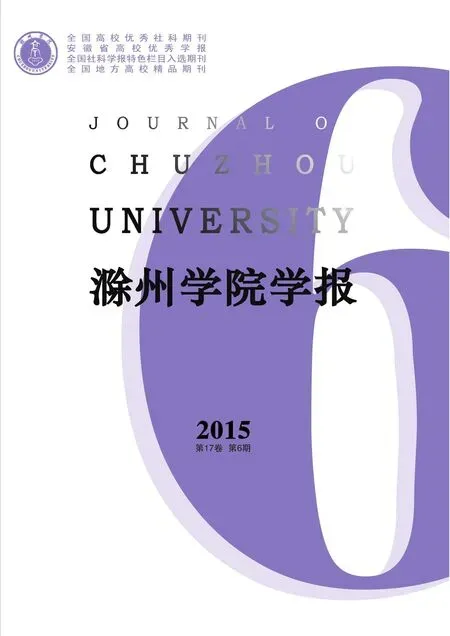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快乐王子》复译
2015-03-20郑雪霏
郑雪霏,胡 勤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快乐王子》复译
郑雪霏,胡 勤
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外国童话之一。这篇作品的翻译贯穿了从晚清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近100年时间,正值儿童文学翻译从边缘化向非边缘化过渡的探索时期,本文选取贯穿这一时期的三个译本,运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对三个译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该小说改写的变化过程和论证复译的必要性。
改写理论;《快乐王子》;复译
英国著名唯美主义作家、诗人、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一经问世即受到广泛好评。迄今为止,《快乐王子》已经发行了多种译本。目前,中国和西方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其中,运用接受美学、目的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居多,而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关注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对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三个经典中译本(即20世纪初周作人的译本、40年代巴金的译本以及21世纪李解人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探讨其改写过程,论证复译的必要性。
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
上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之后,对翻译的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80年代,文化已经被正式纳入翻译研究当中,成为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考核标准。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操纵和改写,标志着操纵论的正式形成。
该理论认为,翻译即是改写,在改写过程中,身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或调整,以使其与改写者所处的社会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也就是说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所服务的[1]。该理论包括三个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会影响翻译活动。诗学是关于诗歌创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诗学涉及的内容也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赞助人是文学系统的双重操控因素之一,对翻译的影响贯穿整个翻译的过程之中。
从这一理论看,《快乐王子》的不同译本是与当时的社会形态紧紧相联系的。周作人的译本产生在晚清,巴金的译作是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而当今的译作则是出现在社会主义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些不同的背景造就了译者不同的选择。
二、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看《快乐王子》的复译
(一)周作人对《快乐王子》的改写
190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东京出版,《小说集》分一、二两册,共收入英、法、美、俄、波兰等国文学作品16篇,其中有英国的一篇即周作人所译的《安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安乐王子》用文言文写成,打上了晚清时代的烙印。
1.晚清时期的意识形态、诗学及儿童文学发展情况
晚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救亡图存,其主要实现手段之一是“西学东渐”。中国的晚清是一个动乱的时期,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加重了民族危机,救国图存成为中华人民族,尤其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诉求。他们憎恨西方列强的同时也被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明的政治制度所影响,一方面向西方学习,进行各种改革,另一方面拿起手中的笔,创作各种形式的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现状,挽救民族危亡。
此时的文学主要以文言文文体书面语呈现,其主要功用是其教化功能,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一直最信奉的“文以载道”准则。作为当时主流文学体裁的小说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1902年11月,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
此时的儿童文学,相比晚清以前,地位有所提升,进入了萌芽阶段。西方列强的入侵迫使中国打开了国门,一方面使得外国先进思想传入中国,加速了外来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翻译,另一方面由此引发的“西学东渐”热潮使国人意识到儿童的重要性(儿童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比成人更具优势),因此改变了国人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不重视的态度。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救亡图存社会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政治功用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关注儿童文学本身的特点,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只是小说的附属品,依然处于次要地位。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翻译也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关注的不是儿童本身,而是如何把儿童教育成为能承担国家重任的人。
2.周作人的《快乐王子》译文
周作人对《快乐王子》的改写带有晚清的时代特征,这篇童话本来是写给儿童的,但周作人在改写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儿童文学的特征和对儿童读者的关心。
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的开篇就表示,他的翻译带着某些政治目的。在第二版的前言中,鲁迅写道:“我和周作人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意识到,文学有改变人们思想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功用,这就是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原因”[2]。《快乐王子》主要描述的就是黑暗的社会背景下贪婪的统治者和好心的王子之间的对比,周作人认为这个主题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斗志,从而团结起来反抗不平等的社会。
周作人把“Theatre”译为“梨园”,把“pomegranate”翻译成“榴华”都是为了创造诗化的效果。梨园原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后来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成为艺术组织和艺人的代名词。而花(华)则象征着美好的大自然。周作人还运用骈体来达到优雅的效果,对字词的选择也十分考究,他的译文只适合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鉴赏能力的人,老百姓似乎并不能很好的理解接受。
周作人译文中儿童化的缺失还表现在翻译策略的使用上,他主要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这在外来词的翻译中最能体现。
例1:HepassedovertheGhetto...
周译:复过葛多……
李译:他又飞过商业区……
例2:…andonagreatgranitehousesitesthe GodMemnon.
周译:大神曼浓(希腊神话、曙光之子、死于多罗之战者。又埃及尼罗川畔、有巨人象二、一为曼浓、每当日光照及、中发大声、如弹箜筱、希腊巴沙尼亚著书云)据华石之坐。
李译:掌管农事的神灵坐在花岗石宝座上面……
周作人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音译的方法,比李解人的翻译要晦涩很多。在文言文中没有“葛多”、“曼浓”这样的表达,所以周作人在后面作了注解,虽然做到了忠实原文,但会显得译文冗长呆板。“商业区”、“掌管农事的神灵”虽然没有最大程度的忠实原文,却以简单明了的语言迎合了儿童读者的喜好。周作人认为逐字翻译是最好的选择,逐句翻译是最坏的选择,宁可语句晦涩也不能改变原文的意义[3]。周作人对“忠实”的追求是由晚清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最大程度的照搬西方知识以达到政治目的。
受到深重的民族灾难的影响,周作人的译文不可避免的反映残酷的社会现实。
例3:AndnowthatIamdeadtheyhaveset meupheresohighthatIcanseealltheugliness andallthemiseryofmycity.
周译:逮死后,众置我高居是间,吾遂得见人世忧患。
巴译:我死了,他们就把我放在这儿,而且立得这么高,让我看得见我这个城市的一切丑恶和穷苦。
“Misery”涵义宽泛,可指由于疾病、死亡、恶劣的环境、不幸的遭遇以及贫穷等所导致的苦难,周作人在译《安乐王子》时头脑中时刻思索的却是民族的危亡,所以将“Misery”译为忧患。同时,“city”这个词的界限也被打破,城市的丑恶与不幸被置换为更大范围内的“人世忧患”。于是,安乐王子所目睹的不再是一座城市的不幸,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难,这无疑反映出译者对晚清中国社会现状的关注和忧虑。
(二)巴金对《快乐王子》的改写
巴金于1942年翻译了《快乐王子》,译本于1947年出版。他的翻译与五四运动中儿童文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巴金在翻译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儿童这一目标读者。但是,频繁的战乱也让他不得不关注残酷的社会现实。
1.20世纪40年代的意识形态、诗学及儿童文学发展情况
40年代的意识形态受到社会现实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两个因素为儿童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巴金翻译《快乐王子》的时候,中国还处于水生火热当中,人们已经开始觉醒,被动地接受新的文化。当巴金的译作出版时,我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不久却又陷入了内战当中,巴金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揭露统治者贪婪的嘴脸,促进人们去改革,去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国人的文学观,倡导反映社会人生、改造国民精神的文学观,语言上完全废除僵化的文言文体,用白话写作,白话成为官方和学校使用的书面语。
此时的儿童文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系。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开始重视儿童的地位,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约翰·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传入中国后,学者们开始了对儿童文学的探索。郭沫若认为儿童文学必须“基于儿童的感觉、想象力和创造力,采用儿童化的语言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4]。茅盾认为“儿童文学需要教会儿童什么是真正的生活”[5]。因此,反帝反封建的社会现实成了儿童文学的主题,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外国文学也优先被引进,这一时期翻译和改写的目的是让孩子面对真实的现实世界,并教育孩子如何成长。
2.巴金的《快乐王子》译文
五四运动之后,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巴金的翻译也显示出对儿童的关心。但是,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家又陷入内战之中,巴金的翻译也不得不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
出于对国家的命运的关心,巴金希望以“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为武器反抗侵略者,其曾说到:“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读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出自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同胞,不仅道出他们的遭遇,也控诉他们的敌人”[6]。韩艳芳曾评价过巴金的翻译,“对于巴金来说,儿童文学的翻译是改革旧社会的武器……巴金在翻译的过程中选择了王尔德的童话而不是戏剧,因为这些童话更能反映出当时人民的遭遇和统治者的贪婪”[7]。
然而,除去黑暗的社会现实,巴金也意识到儿童文学应有的特点,他认为王尔德的童话很唯美,充满丰富的想象[8]。在翻译后记中他写道:“……到了一九四六年正月,为了给上海朋友们办的《少年读物》月刊寄稿,我想起王尔德的童话来,决定在重庆继续那个中断已久的翻译工作”[8]。从这里可以看出,与周作人不同,巴金将《快乐王子》看作一篇童话而不是小说,他注意到童话的特征,如“丰富的想象”、“富于音乐性”等,所以他与周作人译文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原文中王子与燕子有大量的对话,所以翻译对话时,语气显得尤为重要,关系到人物性格的展现,巴金的译文很好的还原了燕子孩童般的语气,比如:
例4:“Idon’tthinkIlikeboys”answered theSwallow.“Lastsummer,whenIwasstaying ontheriver,thereweretworudeboys,themiller’ssons,whowerealwaysthrowingstonesat me.Theyneverhitme,ofcourse;weswallows flyfartoowellforthat,andbesides,Icomeof afamilyfamousforitsagility;butstill,it wasamarkofdisrespect.”
周译:燕曰、“吾殊不爱小儿。去岁夏日、尝游水次、遇二顽童、为磨工子、恒以石投我。顾未尝一中、燕皆善飞、石胡能及、矧吾家本以疾飞名世者。然儿之为此、则终不敬也。”
巴译:“我并不喜欢小孩,”燕子回答道,“我还记得上一个夏天,我停在河上的时候,有两个粗野的小孩,就是磨坊主人的儿子,他们常常丢石头打我。不消说他们是打不中的;我们燕子飞得极快,不会给他们打中,而且我还是出身于一个以敏捷出名的家庭,更不用害怕。不过这究竟是一种不客气的表示。”
以上这段话发生在燕子与王子第一次见面时,王子恳求燕子帮助一个可怜的男孩,王子的语气哀伤而诚恳,燕子的语气则像一个单纯又自满的小孩。周作人的翻译用文言文写成,文笔简练,语言客观冷静,不太能看出人物的感情。但巴金的译文更加体现出原作人物的情感,把of course、and besides、but still翻译为“不消说”、“更不用害怕”和“不过”,燕子得意洋洋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其次,反复是儿童文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根据表达需要,有意让一个句子或词语重复出现,符合儿童说话的习惯。
周译:燕随绕苇而飞、以翼击水、涟起作银色
巴译:他便在她的身边不停地飞来飞去,用他的翅子点水,做出许多银色的涟漪。
以上译文显示,周作人没有译出“round and round”的重复感,而巴金重复了“飞”的动作,既做到忠实原文,又保持了语言的流畅。
再者,王尔德的丰富想象致使童话中的外来词及文化负载词很多,如“passion-flowers”、“the Temple of Baalbec”等,为中国读者难以理解,巴金以儿童为目标读者,所以尽可能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来翻译。周作人把“the Temple of Baalbec”译为“贝克庙”,而巴金译为“巴伯克的太阳神庙”。巴尔贝克是埃及的一座古城,以太阳神庙而闻名。周作人只是给出音译,并没有做出解释,对于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大人和儿童来说都难以理解。而巴金的翻译不仅忠实了原文,而且做了解释,语言也很简洁。而对 “passion-flowers”这一热带植物的翻译,巴金也与周作人的翻译不同。该植物在巴西、秘鲁很常见,其花朵酷似莲花,英国人也种植这种花,女士们喜欢把这种花的图案秀在衣服上。对于这种花的翻译,周作人创造了一个新词“爱华”,将两个单词分开译为“爱”和“华(花)”,具有诗意,但只能为品味高雅的知识分子所理解。巴金译为“西番莲”,虽然没有周作人的翻译那么优雅,但生动形象,即使没有见过这种花的人也能大概想象出它的模样。
巴金一直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丰富的儿童想象之间徘徊,力求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认为王尔德的童话既写给儿童,也写给成人[8]。
(三)李解人对《快乐王子》的改写
李解人翻译的《快乐王子》于2007年出版,在当今的社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百花齐放,各国的文化文学都被国内的广大读者所接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儿童文学也上升成为文学的一个类别,受到了相应的重视。
1.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诗学及儿童文学发展情况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政治的开放,更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使文学作品实现了多样化。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大众为导向的流行文化,文学体裁和文化产品都努力迎合市场需要。所以,以大众为导向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功用也不再限于政治,而是朝着娱乐和艺术审美发展,种类也逐步增多,以适合不同人群。
[11]黄廓,姜飞.国际主流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2)
新时期儿童文学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新兴文学,由之前的以“社会现实”为主体转变为以“儿童”为主体,改变了之前的说教式儿童文学风格,开始真正关注儿童的内心和需要。为了吸引儿童读者,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以“益智”和“添趣”为导向,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语言的连贯性和逻辑性是关键;生动形象的描述是吸引孩子的基础;对话可以最大限度的展示人物性格[9]。总体而言,此时期的儿童文学语言要通俗、简介、连贯、生动,真正实现了“儿童本位”的原则。
2.李解人的《快乐王子》译文
李解人在开篇之语中便指出,此书面向青少年读者。译者也在译本中对用语之音、词与句进行微观调控,以满足青少年读者群体的需要。
第一,口语化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特征。儿童的理解和欣赏能力有限,晦涩的词句会阻碍其理解,所以李解人选择简单易懂的词语来翻译。比如对 “the roofs”中复数s的翻译,周作人并未译出,巴金译为“栉比的屋顶”,而李解人译为“一座座屋顶”。“栉比”出自成语“鳞次栉比”,意思是像鱼鳞和梳子齿那样有次序地排列着,多用来形容房屋或船只等排列得很密很整齐,很难被没有多少知识储备的儿童所理解。李解人考虑到了儿童的接受能力,用“一座座”既忠实原文又浅显易懂。
第二,儿童文学需要很强的逻辑连贯性来帮助孩子理解,生涩的句子结构会使儿童困惑,比如:
例6:“Itisaridiculousattachment,”twitteredtheotherSwallows;“shehasnomoney,andfartoomanyrelations.”
周译:他燕啁晰相语曰、“是良可笑、女绝无资、且亲属众也。”
巴译:“这样的恋爱太可笑了,”别的燕子喃喃地说,“她没有钱,而且亲戚太多。”
李译:“多么荒唐的恋爱呀!”别的燕子议论纷纷,“她并不富有,还有那么多的穷亲戚。”
周作人和巴金都把连词“and”译为具有递进和强调之意的“而且”。然而,“亲戚太多”跟“她没有钱”并没有直接联系,儿童容易产生困惑。李解人为了显出句子的逻辑关系,增加了“穷亲戚”这一含义,这样一来句意就很明确了,即她本身就不富有,一大堆穷亲戚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第三,李解人的译本短句简单句较多,句意明确,短小精悍,比如:
例7:Andhewrotealongletteraboutitto thelocalnewspaper.
巴译:他便写了一封讲这件事的长信送给本地报纸发表。
李译:为此,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文章,寄给了报社,并发表在报纸上。
汉语与英语不同,英语中介词可以指代动作,从而简化句子,但中文里没有这种用法。巴金的译文完全对应原文,因而使用了欧化的长句,“写”“讲”“送”这几个动词叠加在一起,听上去冗长费力。李解人则把长句分成短句,每个短句中都有一个动词,既形成一种韵律,又方便儿童理解和阅读。
第四,音乐化的语言符合儿童的喜好,能吸引孩子的注意,比如儿歌就是儿童文学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体裁形式之一,它词句音韵流畅,易于上口。不同于周作人和巴金的翻译,李解人注意到儿童文学语言的音乐性,主要通过押韵和拟声词来展现这一特征,比如:
例8:InthedaytimeIplayedwithmycompanionsinthegarden,andintheeveningIled thedanceintheGreatHall.
周译:昼游苑中、夕就广殿、歌舞相乐。
巴译:白天有人陪我在花园里玩,晚上我又在大厅里跳舞。
李译:白天,臣仆们陪伴着我,在绿草如茵的花园里嬉戏;晚上,我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领舞。
不难看出,李译中“茵”和“明”形成一种韵律,前后句子结构相同,形成并列对仗关系,使译文读起来娓娓动听,充满了旋律感。此外,李译还用“咕咕”形容鸽子的叫声、“吧嗒”形容水滴声,这些拟声词的使用既可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又创造了一种音乐效果,体现出儿童文学语言的音乐性特点。但是周译和巴译却未注意到这点。
三、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三个译本的不同之处。周作人由于受到晚清时期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和文以载道的诗学功能的影响导致其认为儿童文学作品的译文并不是为儿童服务的,而是为了学习西方文化以唤醒国民,不需考虑儿童文学的特征;巴金由于受到40年代社会现实和新文化运动,其译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儿童,努力使作品符合读者大众的品味,但当时中国仍处于战乱之中,他也希望通过作品揭露社会现实;李解人则受到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和艺术审美的文学功能的影响,其译本则完全实现了童话中“儿童本位”的原则,把儿童作为目标读者,语言简单生动。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快乐王子》重译本不断产生,其中所呈现的儿童文学意识不断增强,这些都不是译者主体操纵的偶然结果,而是意识形态和社会诗学因素作用下儿童文学地位不断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同年代、不同时期,非常有必要对同一文学作品进行复译,以便适应相关年代或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要求,才能真正为相关年代的读者所接受,进而使相关文学作品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
(致谢:笔者在成文过程中得到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吴小芳老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1]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2.
[2]鲁讯.鲁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1.
[3]周作人.随笔录二十四[J].新青年(5)卷3,1918.
[4]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J].上海民铎(第二卷),1921:5-13.
[5]茅盾.关于“儿童文学”[A].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108.
[6]叶圣陶.稻草人和其他童话[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34.
[7]郭著章(编).翻译名家研究[M].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72-273.
[8]奥斯卡·王尔德(著).巴金(译).快乐王子[M].上海:上海文化与生活出版社,1948:244-245.
[9]杨实诚.论儿童文学语言[J].中国文学研究(2).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7-22.
H315.9;I046
A
1673-1794(2015)06-0092-05
郑雪霏,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胡勤,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贵阳550025)。
2015-09-22
责任编辑: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