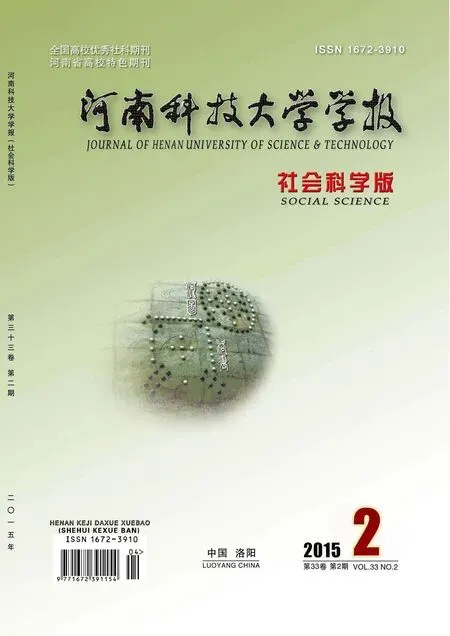试论影视改编的叙事策略——以《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的比较为例
2015-03-20许菊芳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郑州450000
许菊芳(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郑州450000)
试论影视改编的叙事策略——以《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的比较为例
许菊芳
(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郑州450000)
摘要:影视文学改编受制于文本的传播媒介、受众群体与接受心理等外在因素,而从文本的内在生成机制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其主题思想。影视改编,正是在围绕文本的内在与外在机制进行叙事策略的转换。这一普遍性的逻辑与创意规律在《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转换中有鲜明的体现。
关键词:《唐山大地震》;影视改编;叙事策略
在中外影视史上,以文学作品作为影视创作基础的案例屡见不鲜。如何借鉴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的改编,成为影视创作中的重要论题。影视文学的改编,既是对文学作品通俗化的传播,也是保证影视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重要支撑,还是对文学作品的二次加工与创造。新世纪以来,《唐山大地震》三个互文本的创意无疑是影视改编史上的一个成功实践——2007年,海外华裔女作家张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余震》; 2010年7月,冯小刚根据《余震》改编并导演电影版《唐山大地震》;2013年5月,由姚晓峰执导的38集电视连续剧《唐山大地震》由河北卫视首播。在三个文本中,影视文本基于原著,但又根据需要设置创意了其中的诸多内容。三者之间彼此借重、相互推扬且自成一体,成功地实现了适应传播媒介、受众群体与接受心理需要的影视创意。因此,对三个文本的叙事策略进行深入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传播媒介对影视改编的内在规定
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以语言文字作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前者则是用影像复制与再现生活。由于语言文字的多义性与丰富性,文学作品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可以展示人物复杂的心理,能够有相对自由的篇幅,这是文学的长处。影视作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视听转化的同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许多复杂的心理、细腻的感触、叙事的时空和人称视点如何恰当地转换为视听语言,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中传播媒介对文本起着内在的制约作用,文本媒介不同会直接导致作品篇幅的差异。文学作品可以有相对宽松的篇幅,短篇、中篇、长篇皆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进行合理构思和驾驭。但电影作为集中的视听表现,篇幅却不宜太长,一般时长在90至120分钟,少数影片时长或在150分钟左右。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集中生动地表达主题思想,这是对影片制作的严峻考验。电视剧却不同,它可以采用分集的形式连续播放,以适当扩展篇幅。这就决定了电视剧可以细腻地诠释人物的内心世界,甚或展示生活中琐碎而富有质感的细节。
因此我们看到,以唐山地震为主干情节的三个文本各自体现出相应的传媒特性。从人物设置和形象塑造来看,小说的人物设置较为分散,除了对核心人物小登①在小说、电视两个文本中,李元妮的女儿原名“万登”,电影中原名“方登”,但小名都为“小登”,在经历地震被收养后,人物自主改名“王小灯”。为保持全文的一致性,文章中提到该人物时统一使用“小登”。的精心刻画之外,其他人物的塑造则具有较大留白。电影中的角色创意和形象塑造却高度集中,比如对小登养父形象的转换,对生母李元妮形象的删减,对生父万师傅之死的处理,均是为了强化矛盾冲突,调节影片节奏,进一步凸显影片的主题。而电视剧则由于相对较长的篇幅,故而可以对每个人物展开充分的刻画,对人物逼仄的心理困境进行细致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电视剧中内心无比纠结的小登,坚韧好强而又慈爱的母亲李元妮,从地震的阴影中逐步摆脱出来、进而成长起来的小达,这些形象都显得更为立体传神,真实感人。
从结构上来看,小说的结构自由灵活,时空跨度很大。30年间的故事跨越唐山、天津、上海、美国等空间,不仅如此,故事时空也交叉展现:一方面是以小登为视点的倒叙式结构,一方面是唐山地震后小达和母亲李元妮生活的顺序式结构。4万字的小说包含了10余个场景,不同时空下的故事彼此交叉呈现,给人一种强烈的沧桑感,结局设置也给人一种似此而彼的模糊感。在基本承袭了小说的时空设置之外,影视剧的结构安排也各有特点。影片《唐山大地震》的结构高度集中,它虽然在时空上与小说有着同样的跨度,但是它集中展现的是23秒32年的震撼故事,是守护与回归的强大主题,给人一种叙事紧凑、结构集中的印象。同名电视剧则延续了所有电视剧的特点,结构拖沓,叙事时空多处穿插,更巧妙安排人物的多次相遇、彼此想念,又不断推开,不断逃离,最终人物才放下心理包袱,得到心理抚慰,完成大团圆结局。
对比三个互文本,从唐山地震后30多年历史且跨越海内外的这个故事来看,其时空跨度很大,故事构架宏伟,更适宜于用电视剧文本来展现。采用其他文本则未免存在诸多局限。如小说中,作为中篇小说表现如此厚重的主题未免拘束,无法深入全面展现人物的内心,难免陷入主题先行的窠臼;电影则受篇幅限制更只能集中展现故事的内核,突显其守护与回归的主题,其设置的重逢情节更显出机缘巧合的意味,难免因此遭遇各种质疑。从表现人性的深度、广度和生活的多变性来说,电视剧可谓优势独具。因此,它能够更具体、细致、全面地展现人物的成长转变历程。
二、受众心理对影视改编的潜在制约
不同的传播媒介面对的是差异化的受众群体,受众群体的心理预期和期待视野无疑对三类文本具有潜在的制约性。相对而言,小说的受众群体大都有私人化、小众化,甚或精英化的趋向。在当下的读图时代和数字化大潮中,小说的读者常常被影视媒体、网络所分流。因此,当前的小说读者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文学爱好者,此外便是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相关人员。而电影的受众群体一般来说多在14岁到45岁之间,是有一定经济水平的普通群众。他们显现出不受学识、职业等限制的多元化趋向。就其观影目的而言,有消遣娱乐、增长见识、缓解压力、释放情感等不同层面。电视剧剧情大多是关乎日常起居、人情世理的生活化描述,受众具有覆盖面广泛、群体基数大的特点,多是在一种家庭式的公共空间中进行观赏行为,而且大多抱着一种休闲、娱乐的心态,可能受到不同年龄、性别等的限制。
受众群体及其接受心理的差异,潜在地制约着创作者的思路和文本的传播与接受。在小说中,作为海外华裔作家的张翎用一种疏离的姿态透视地震之后人们的心灵创伤,这是对众口一声的认为地震后的孩子以后都会成为企业家的批判[1],是一种小众群体的传播。这种不肯相信大众呼声,追求思想自由的精神,承续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种观念,一般大众是难以理解的,唯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群体才能首肯。正因为如此,小说是在小众和精英化群体传播中展开的。电影则不同。这首先是影片制作的商业机制决定的。影片高投资的事实既要求导演以商业票房为中心,又要成功地进行电影文本的叙事编码,力求抚慰32年后汶川地震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因此,电影《唐山大地震》将受众定位在普通民众,不仅包括从1976年唐山地震中走出来的人们,也包括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的震区居民和遭受心理创伤的、富有道义感的国人。其中除了普通百姓对于地震灾害的集体情感外,更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如何建设家园、如何维护亲情纽带等的恒久话题。尤其后者,更是对中国老百姓集体无意识心理的一次强烈碰撞。它契合了当下影片受众的社会心理,故观影者无论老少无不为之一鞠同情感动之泪。
基于以上原因,电影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作了重大改编,如影片对母亲李元妮形象的改编。小说中母亲李元妮的最大特点是“招人恨”,其原因一是她地震前作为舞蹈演员的气质,她时时刻刻都注意修饰外在形象;二是她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震后,这种幸福美满被打破,但是她又显示出母亲的坚强和伟大。她是震后最早站起来的人,“将每一个日子过得如同一个盛典”[2]。这样的母亲形象是独具特色、别有一番魅力的。但在电影中,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编剧删去了李元妮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她个性中锋芒毕露的部分被遮蔽了,着意刻画她作为震后母亲和传统母亲代表的典范性:坚强、善良、无私。即便在儿子已经能够买房买车时,她依然固执地住在曾经的狭窄小平房内,以便等待丈夫和女儿的魂灵回家;她不愿改嫁,恪守从一而终的传统文化信条。删改之后,她不再是文学中的“另一个”人物形象,而是千千万万中国母亲中的一个,是朴实、勤劳、善良、无私、伟大之中国母亲的代表,具有了普遍性意义。
对于电视剧来说,它为照顾到不同类型和年龄阶段的受众心理预期,必须给剧中的每个人物足够的戏份,给每个人物安排合情合理的生活轨迹、真实再现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之下的心理状态。因此,母亲李元妮、小登、小达等每个人物都有了合理的心理发展逻辑,曲折但较为可信的人生成长历程,略带遗憾但却圆满的理想结局。尤其是对小达人生道路的展现更是详细生动。在小说和电影文本中,小达只是作为一个串联性的人物出现的,两种文本对其着墨都不多。但是在电视剧中,编剧给了小达与姐姐小登、母亲李元妮相当甚至更多的戏份,突出展现了其成长的曲折历程。电视剧甚至虚构了小达的妻子阿雅,同时对小登的丈夫杨阳、朋友向前等也给予适当篇幅,生动演绎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心灵困惑。
三、主题在影视改编中的导向性
从影视改编的内在机制来说,影视改编的前提是确定改编文本的主题思想。主题决定了故事的发展走向、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和结构安排。影视改编既然是一次艺术再创造的过程,那么在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文本的主题思想。在《唐山大地震》电影和电视剧的改编过程中,由于文本主题的差异,其人物设置、情节结构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极大的变化。
从故事内容来看,《唐山大地震》的三个文本都是围绕一个故事内核展开的。故事讲述的是在唐山大地震中,原本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中的父亲死去,双胞胎姐弟被压在同一块石板的两端,母亲面临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的艰难抉择,她最终选择了救弟弟而放弃了姐姐。此后姐姐意外生还,但从此这个家庭残存的三人都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三个文本都是围绕这种心理创伤以及如何疗救所展开的故事。
基本相同的故事,却有差异化的主题诠释。小说《余震》的主题重在“寻找”:即当孩子的心灵遭受了严重心理创伤后,他们是否还能够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种心灵的余震能否过去,如何重建精神的家园;电影则是围绕地震之后如何疗救心灵创伤的主题展开的,体现出“守护”的主题,这是对以母亲李元妮为主要代表的唐山地震后家园守护者的赞歌,是由小说的“疼痛”向影片“温暖”的改编[3];电视剧则以宏大的篇幅既展现了小说“寻找”的主题,也完成了电影疗救的目的,即以“守护”的方式来完成彼此心灵的救赎。正是从表现主题的导向性与决定性出发,影视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多处改编。
(一)人物创设的差异性
首先,三个文本的主要人物设置有较大差异。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方登,作者通过对她抑郁症治疗过程的描写,逐步揭示出她在唐山地震之后留下深重的心理创伤,这种心理创伤迫使她不断逃离,并固执地以独断的方式来制约丈夫和孩子的自由,从而更加重了她沉重的心理负疚感。电影中的主要人物则是母亲李元妮,通过描写母亲震后对亲人沉重的负疚心理和守护家园的坚韧意志展示影片“守护”的主题,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下的亲情作为疗救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以之作为影片叙事的内在动力。电视剧中的主要人物则扩展为母亲李元妮、双胞胎姐姐方登、弟弟方达三人,以平行交叉线索以及更宏大的篇幅展现了三人艰难的心灵疗救过程。
其次,影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也经过了一定的改编。这在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电影《唐山大地震》是一次较为温情、积极乐观的改编,将小说中表现现实残酷的批判锋芒置换为提供疗救措施的暖色调。并以此为主题导向,对其中的诸多人物都进行了创造性的设置。
一是养父形象的置换。小说中的父亲是一个形象佝偻的中年男性,是中学教师董桂兰的丈夫,是在妻子过世后无法忍受身心寂寞而将可怕的黑手伸向13岁孩子的罪恶养父。这样的人物,对于受过严重心灵创伤的小登而言,无异于伤口上撒盐,将她进一步推到了心理绝望的边缘。电影既要表现积极乐观的主题,这样的形象自然难以为受众接受。为此,影片对养父的形象进行了积极的改编,电影中的养父转换成一位高大、隐忍又爱女的军人形象,他对小登的照顾不亚于一个亲生父亲,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疗救孩子心灵的良药。他对小登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曾引起妻子董桂兰的嫉妒。其中为女儿出面教训其男友的场面,更突显了其形象的高大。这样的父亲,是震后遭受心灵重创的孩子坚实的保护伞,是呵护孩子心灵的一剂良药。
二是丈夫角色的变化。小说中小登的婚姻对象是自己大学的同学杨阳,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一起奋斗,直至出国定居。在电影中,小登的婚姻对象有了较大变化:她大学里的恋爱对象杨志当得知其怀孕后,不敢承担责任,因此两人的恋情以未婚先孕而告终;最终小登嫁给了大自己16岁的外国丈夫,找到一个父亲般的爱人,这将小登心灵深处的“恋父情结”进一步凸显出来。电影对丈夫形象和养父形象的改编出发点是一致的,是一种女性视角向男性视角的全面转换[4]。此外关于母亲形象的改编更是影片的一大亮点,这在前文已有提及,不再赘述。综合了小说和电影的长处,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人性更为复杂和多样性的特点。剧中除对母亲李元妮、姐姐方登性格、心理等的细致描摹外,最突出的是对弟弟方达的重塑,真实再现了一个弱者的成长历程。他由童年的弱小任人欺负,到少年的打架闹事,到中年的为家庭负责,抚养妻子的女儿,这是从一个为姐姐活、为母亲活到逐渐摆脱童年的痛苦记忆,心灵创伤得到疗救的人物形象的真实写照,是对小说和影片中小达形象的进一步充实。
(二)情节结构的策略性
情节结构是主题表现的叙事性展开,因此,从情节建构和结构处理方面介入,无疑将抓住三个文本差异性的关键所在。
结构的展开。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从方登三次自杀介入心理治疗入手,以医生和方登的谈话来逐步展开故事。在方登的梦境中,鲜明的形象是一扇扇窗户被打开,但最后总有一扇窗户锈迹斑斑,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以此揭示主人公隐喻式的无意识心灵创伤。小说以场景为基本叙事单元,将不同的时空彼此勾连,隐约展现人物生活状态,其间又存在方登主观视点和叙事客观视点的转换,颇有电影剧本的倾向。电影的结构是正叙式的,以地震23秒的场景和其后32年的寻找救赎作为结构模式,时空上以三线平行展开,同时展现不同人物的生活时空,最终在32年后以汶川地震为归结点,三条线索交汇。电视剧同样是正序,并以多线结构模式展开,同时叙述不同情境之下一家三口的生活状态。这与电影的结构模式基本相似,不同在于电视剧出于情节需要展开宏大时空,故而设置了三条线索之间的多次交叉重合。
结局的处理。三个文本的结局处理也有一定的差异。小说写的是方登在心理医生的干预之下逐渐放弃心理包袱,并借回国之机回到了故乡唐山,在母亲的楼下听到母亲念叨孙子、孙女的名字“纪登”、“念登”,她多年未留下的泪水在这一刻流出,多年的心结由此打开。至于此后相聚的情景,小说作了留白,形成了相对开放的结尾处理。电影的结局处理借用了巧合的技法,以汶川地震后的救援作为契机,设置姐弟俩在救援现场的相遇。同时,方登重新经历了地震的场景,并亲历一个四川母亲在地震中艰难抉择的痛苦,她受此触动放下了心灵包袱,回到了母亲的家,并痛哭以忏悔自己的过错,实现了圆满的大团圆结局。电视剧的结局处理更为圆满,它讲述了方登在遭遇自己家庭生活的种种不幸:精神抑郁、夫妻感情出现危机、孩子叛逆之后,她意识到了自己心理存在的问题,从而决定回到故乡,结果发现她的母亲由于长期的负疚心理患上了老年痴呆,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小登。在精神错乱的时候,她所做的事情便是搬动家具拯救孩子……这是一个更加现实乃至残酷的结局。电视剧与小说、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为每一个人物都安排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小登与丈夫、孩子的矛盾化解,一家三口回到国内团聚;小达与妻子阿雅经历情感的多次反复后,带着妻子与前夫的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细节的处理。细节运用关乎影视的质感,其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决定了影视作品的质量。在电影中,编导为父亲万师傅的死设置了一个理想的结局:父亲死在家中,是为救妻子和孩子牺牲了自己,这就将小说中一个普通的父亲形象塑造为一个充满牺牲精神的伟大父亲形象。电视剧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显得更为细致深刻。如对姐姐方登的心理刻画,电视剧较小说和电影做得更为圆融,将小登的形象刻画得更为丰满。比如方登一次次地在梦中见到自己的亲人,但在现实中,她又将他们一次次拒之门外。她渴望见到自己的亲人,以各种方式与亲人接近,但是当母亲、弟弟找上门来与她相认时,她却选择了逃避。这样的描写,真实再现了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立体。
当然,影视的文学改编,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之外,还受到时代审美趋向、商业机制、意识形态编码等多方面的影响与制约。改编是在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简单地以其中部分因素以偏概全,难免挂一漏万。如从制作动机来说,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是唐山市政府、华谊兄弟制片公司与冯小刚合力创作的结果,因此它承担着意识形态、商业价值等多重使命,其改编便将其中的个人化叙事转化成代表时代精神、民族意志等的叙事。其中虽不乏纪实内容,却降低了对于人物丰富心灵的挖掘程度。
总的来说,影视文学的改编,要考虑到影视的传播媒介特性、受众群体差异等影视形成的外在机制,更要掌握影视作为一门艺术的内在生成机制。在影视改编的叙事过程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影视与文学的差异,认识文本的主题之重要性,才能做到以文学为基础进行二次创造,而不是对原有的文学作品进行生搬硬套。
参考文献:
[1]张翎.浴火,却不是凤凰——《余震》创作谈[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2):70.
[2]张翎.余震[M].北京文学·中国小说月报,2007,(2):23.
[3]谷大勇.从《余震》的“疼痛”到《唐山大地震》的“温暖”——兼论冯小刚的改编策略[J].电影文学,2011,(11):41-42.
[4]朱庆颜.从小说《余震》到电影《唐山大地震》——从女性主义走向男性沙文主义[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1):24-27.
【艺文寻珠】
Narrative Strategies about Adaptation of Film and TV Works
XU Ju-fang
(Department of Film&Television Art,Zhongyuan College of Culture and Arts,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The adaptation from the literature into movie and TV works is subject to the text of external factors,such as the media,the audience and the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and so on.For the internal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text,the theme plays a decisive role.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s center o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mechanisms of the texts for conversion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which reflect the universal laws of logic and creativity in the text of“The Tangshan Earthquake”.
Key words:“The Tangshan Earthquake”; adaptation of film and TV works; narrative strategy
作者简介:许菊芳(1981—),女,湖北大冶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07-04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5)02-00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