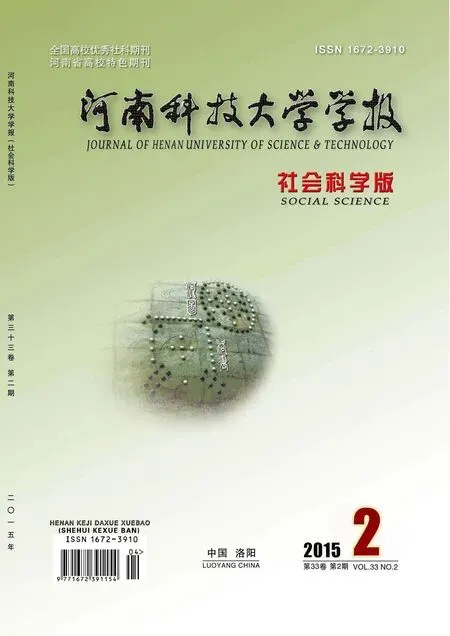孔子政法观念之再认识
2015-03-20陶佳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江苏常州213000
陶佳(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江苏常州213000)
孔子政法观念之再认识
陶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其法律思想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参照现代法学理论,形式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就是“刑”;实质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则是德礼、政刑的规范体系。孔子所理解的“法”基本被限制在“刑”的范围内,而“礼”则部分承担了“法”的“规范”职能,这也是“仁政”“德教”与“和谐”等孔子政法观念核心价值的立论基础。然而,当“法”不只是“刑”的时候,“仁政”“德教”与“和谐”等核心价值则需要被重新审视。
关键词:孔子;规范意识;法观念;道德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学派源头在孔子。事实上,无论是向孔子求经,还是向儒家回归,都表明当下的社会开始向传统低头,试图纠正过去那种全盘西化以及势必要与传统决裂的极端的倾向和认识。这种反思现象是好的,但形势未必可喜。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如何保持,本来就是一个问题,更不消说传统常常被误读。其中,对孔子政法观念的认识就存在偏差,这不仅导致了知识上的误读,而且影响到了今日的法治实践。
一、为什么需要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孔子政法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学术成绩。然而,很少有人对孔子政法思想中的“法”的本质问题予以正面回答。综观古代中国,虽然“法”的内涵始终是不甚明晰的,与“政”“刑”“法”“律”甚至是“令”“例”等等概念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究孔子之“法”的本质。并且,只有在明晰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政法观念的核心要义,从而准确界定孔子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事实上,探究孔子的“法”观念可以从孔子对待“法”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入手。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在学者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肯定者的观点认为,孔子肯定了德与礼的重要性,但也并不反对政与刑的功能意义。如有学者说:“孔子及其儒家在倡导德治、仁政的同时,并不完全反对刑罚,相反,充分肯定了刑罚的社会作用,认为刑罚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德礼与政刑正是孔子规范思想的两套体系,但是随之而来的某些判断就未必中肯了。部分学者陷入将“刑”等同于“法”的误区,往往以孔子并不彻底反对刑罚来证明其重视法律,甚至是以为孔子也是“法治”派。
否定者的观点认为,孔子之政是仁政、德政,而以仁、德为本的政治是与“法”无涉的。杨鸿烈先生早就说过:“这些都是孔子不重视法治的显明例证,尤其如《颜渊篇》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简直不承认法律的必要了。”[2]32当然,不可否认孔子的法律观念是相对淡薄的,但以“无讼”式的社会理想说明孔子完全漠视法律似乎就有些误读。事实上,这种理论的影响十分深远,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极为盛行。
这种观点对立的现象很有趣,更激发了人们探索孔子“法”观念之原貌的兴致。对同一个孔子,为什么认识会存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很明显,肯定者犯了一个基本的知识上的错误,即“刑”不能等同于“法”;否定者的知识缺陷则在于没有认识到“法”可以包括“刑”。不难发现,两派虽然观点有异,但所体现的思想局限性是相同的,即都没能准确界定好“法”的基本范围,并在这一前提下评价孔子。
那么,究竟该如何还原孔子之“法”的本来含义,还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一方面,我们必须回到孔子,从其一言一行中去发现他的规范意识及其政法观念。另一方面,我们亦要端正态度,孔子虽是先贤、圣哲,但终究是一个凡人,其思想必然具有时代性、局限性,切不可无原则地颠覆其思想本旨而为高扬法治服务。孰不知,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孔子的政法观念亦如此,只有探究其义理之真相才是正途,唯有如此才于古于今都有裨益。还原孔子之“法”观念的原貌,势必引出对孔子政法思想中的一些核心观念的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仁政、德治与和谐等概念无不与“法”有关。其实,探析孔子的政法观念,尤其是在判断孔子“法”观念本质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这样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因为孔子的“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子的仁政观、德治观以及和谐观。当然,本文不可能完成对重要概念的重新梳理和系统阐释,而且相关的研究已十分丰富。学术的任务主要在于创新,其途径之一就是正本清源,以明流变。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澄清孔子的政法观念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亦有意义。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法治实践的难题已基本上不再是法学知识的缺失,而主要是基于法治观念缺失而导致的法治实践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中国不仅没有“法治”的传统,而且至今缺少西方式的“法治”观念。在遭遇困境且痛定思痛之后,我们试图在政法观念领域进行一场革命,以缓解现代“法治”观念不足之急。结果之一就是,向古人借智慧、求经验,以期促进法律同社会实践的接轨。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在法治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仁政观、德治观尤其是和谐观成为政法实践领域积极倡导的观念。就借鉴传统的优秀法律文化而言,这无疑是必要的、可行的,毕竟现代无法与传统割裂。但问题是,如若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与实践的社会背景,就无法准确理解它的真正内涵,其合理的精华也就无法发挥于当代社会。更为严重的是,这可能会对我们的法治实践产生误导,损害现代性的法治观念。例如,就法治与和谐的关系而言,法治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良善,而良善的实现就可谓和谐。不过,在法治实践中,人们并不关注和谐的原始义,更不曾深究法治之于和谐的意义,相反,为了实现狭隘的暂时矛盾解决式的和谐而无视法律,以“无讼”为美,却不知良法之治是和谐的应有之义。因此,揭示孔子政法观念之原貌,有助于澄清基本概念,更有利于法治中国的实践。
二、孔子之“法”实为“刑”
正如上文所说,与“法”相关联的概念还有不少,“德”“礼”与“政”“刑”在孔子的思想中都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德”“政”与“法”的关系又过于抽象,尤其是“德”更涉及另一层次的问题,这里很难厘清其关系。就探究“法”观念而言,准确界定“礼”“刑”与“法”的关系无疑成为了关键点。本文无意从训诂学的视角去探析其词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实践结果,而旨在说明在孔子的规范意识中此三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及其地位如何。
一般而言,“法”主要是一套制度性的规范体系,而“刑”主要是违“法”后的补偿手段。换言之,“法”可以被看作是“刑”的上位概念。将“法”与“刑”贸然割裂,实则是为了说明孔子之“法”实为“刑”。这种界定似乎极易引起非议,但透过对孔子一言一行的分析,似乎也仅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研读孔子的思想文献我们发现,孔子及其弟子们很少谈论“法”,有关“刑”的论述却有不少。事实上,这与孔子对“法”的认识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认为作为“规范”意义的“法”从来都不是最主要的,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换言之,孔子基本上只在“刑”的范围内讨论“法”。从为数不多的涉及“法”观念的材料中,可以择选出以下几条作为例证。
其一,《论语·颜渊》载:“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从历史上看,“无讼”不仅代表了孔子的法律理想,更是两千余年传统社会对法律秩序的基本追求。“无讼”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和谐”,意味着现世社会对理想秩序的美好期盼,这对传统礼法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孔子追求“无讼”的原因何在?它和孔子对“法”的认识是否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以从“讼”的结果来看。古代社会虽刑民有别,但就责任承担方式而言却是刑法化的。也就是说,“讼”的结果是可能招致“刑”。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不仅有“刑”的部分,更有许多与“刑”无涉的内容。这一点,在孔子的思想中无疑是欠缺的,作为“规范”的“法”始终未能获得他的认可。
其二,《论语·子张》中记载了孔子弟子曾子的这么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大意是说,裁判案例如果发现事实真相,为此不能太过于欢喜,相反,却要为案件的发生而省思。这一思想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孔子的主张。与法家的“刻薄寡恩”大不相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始终是温情脉脉、以感化教育示人的。之所以要“哀矜而勿喜”,一方面是源于对道德理想的坚持与贯彻,这不失为一条重要的施政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案件审理的结果可能会引起“刑”,而孔子本人又是极具同情心的,这恰好说明了孔子所认为的“法”的残酷性。表现上看,这种推理似乎有一些牵强,但放在孔子政法观念的整体脉络中,就显得适当多了。同时,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在孔子那里也实在发现不了“规范”意义上的“法”的影子。
其三,孔子也曾直接言及“法度”二字,只是意蕴不同。春秋之际,法律的载体形式渐渐由神秘而走向公开。面对晋国铸刑鼎的法制变革景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孔子的这番话:“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这是有关孔子“反对成文法”的记载,虽言及“法度”却非为“法”的正当性证明。相反,体现出的是一种“礼”的情结以及对“贵”的肯定。
以上是从“法”的视角看孔子的政法观念,接下来,可以从“刑”的角度出发继续探索。
孔子虽不直言“法”,但他对“刑”的论说及其记载的相关故事有很多。也正是从这些论说与故事中,我们发现了孔子对待“刑”的基本态度。孔子很少单独讨论“刑”,而习惯于将它同“德”、“礼”相对照而论,这样既可以彰显后者,又能够否定前者。例如,《论语·子路》载:“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又如,《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从孔子论“刑”的言说中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组结论:一是孔子并不单纯地否定“刑”的实用价值,其存在合理性的前提是“礼”、“乐”之兴;二是孔子认为“刑”的价值位列是最低的,不是理想的存在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惩戒手段。其实,这组结论可以简化地理解为“刑”是“无讼”理想到来之前的工具性存在。
如果说有关孔子论“刑”的记载,或许还只是未经证实的推理,缺乏说服力,那么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公案则可谓一桩实例。《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为官七日就诛杀大臣,似乎有点操之过急,完全违背了“不教而杀”的为政宗旨。不过这也可以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参与现实政治的人必定要能当机立断,敢想敢为。孔子也不能例外。
三、孔子之“规范”在“礼”而不在“法”
一般而言,“规范”是指一套公认的能够引导、控制社会行为的标准体系。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规范”则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先秦时期的“规范”体系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有学者曾有这样的判断:“看来,我们不妨大胆断言:三代之‘礼’乃是广义的法,西周的‘礼治’其实就是奴隶制的‘法治’。”[3]也就是说,三代的“法”应取广义,“礼”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事实上,孔子所提倡的“礼”也可以算是一类广义的“法”,承担着制度规范的基本职能。
不同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法家将“法”看作是治世之良药,希望通过“法”的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法家不同,孔子欲借这套儒家式的理论促使“失范”的社会回归正轨。在对制度规范的认可上,儒家看重的是“礼”的价值而非“法”的功能。有学者总结说:“礼有上述实践的社会功能,足以维持儒家所期望的社会秩序,而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欲以礼为治世的工具。”[4]事实上,孔子之“礼”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许多本应单纯由法律作用的领域。甚至说,“礼”取代了“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礼记·曲礼》记载:“分争辨讼,非礼不决。”杨鸿烈先生曾分析说:“孔子所说的广义的‘礼’字,颇含有法律的性质……”[5]可见,孔子虽很少言“法”,实质上却颇有“法”的精神,不同的是这种精神由“礼”所承载。
孔子之“礼”所承担的“法”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法”有关,其与后来的“国家法”的功能类似,如规定了各个阶层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二是与“私法”有关,其所承载的价值则远远超出了“国家法”的范畴。如陈顾远先生认为:“往昔,一切准绳皆归于礼,礼有所失,始入于刑。礼应认为系广义的法,欲求民事方面之规范,舍礼难得其梗概。”[6]可见,就“私法”方面而言,“礼”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国家制定法,而孔子之时成文法才刚刚兴起,“礼”的地位一定更加重要。
梁治平先生称:“从时间顺序上看,我们今天称之为古代法的,在三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秦汉以后则主要是律。”[7]这种认识很有见地,不仅指出了不同时期所谓古代法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表明今人常常以实证法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客观地讲,实证法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探究孔子之“法”的实质,却也容易遮蔽对孔子另一套规范体系的认识。孔子的政法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源于三代而不能超越时代,尤其体现在把“刑”当作“法”上。孔子的时代有别于孟子、荀子之时,更有别于秦汉以降。他的思想比后来的儒者更加保守,没有如孟子一样喊出“徒善不足以为政”的声音,更不可能像荀子一样“隆礼重法”。孔子的一生都在为复归“周礼”而努力,奉行的是“克己复礼”准则。总而言之,孔子的“规范”意识是被“礼”所主导的,是以“刑”为后盾的。这一论断也是与孔子之“法”实为“刑”直接相关的。因为孔子理解的“法”基本就是“刑”,而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另一套规范以维持秩序,孔子的“礼”实际上就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只是,他的“礼”所承担的“规范”仍需要“刑”作为辅助性手段。
此外,孔子看重的不仅仅是“礼”所具有的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更在乎的是“礼”所承载的教化功能。如果说“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形式,那么“德”则是“礼”的内在精神。孔子以为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优于法律制裁的强制作用,故“德礼”优于“政刑”。“政刑”更接近于孔子所理解的“法”,这种“法”仅被认为是制裁性、惩戒性的法律,没有“礼”所具有的指引性、规范性的功能。
四、孔子政法观念核心价值的再审视
将孔子之“法”界定在“刑”的范围之内,无疑是对孔子法律思想的一大颠覆。这样的判断也许会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遗憾,但笔者仍愿作一尝试,并试图以此为视角解读孔子政法观念的核心价值。可以反向假设,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概念,那么孔子政法观念的某些核心价值就需要予以重新审视。
首先,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那么“仁政”的理想价值和制定意义将会有所降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其政法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仁政”。所谓“仁政”就是为政要以仁为本,主张德礼教化,反对滥刑乱杀。如《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如《论语·子路》篇载:“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反对刑杀,尤其是“不教而杀”之刑,但不能否定“刑”的工具价值。不过,他在潜意识中已然否定了作为“刑”的“法”的理想价值。概而言之,“仁政”是排斥“刑”的,但“仁政”离不开“刑”的衬托。换言之,“仁政”又与“刑”紧密相连。事实上,在孔子的观念中,只有“刑”才能更好地为“仁政”正名。也正因为有“刑”的冰冷与泛滥,才有“仁政”的温暖与施行可能。当然,这种思维模式不为孔子所独有,后来人一般也这么思考问题。
我们知道,“刑”只是“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远不是大部甚至全部。我们要问的是,“仁政”是否必然需要“刑”的衬托?如果“法”不只是“刑”,那么“仁政”的形象是否还会那么伟岸?这些问题必然人言人殊。事实上,“仁政”以去“刑”为目标,但没有“刑”也就无所谓“仁政”。“刑”只是“法”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种极端的补偿或制裁措施,以此为理想状态的“仁政”作论证,必然缺少信服力。也就是说,如果“法”不只是“刑”,那么“仁政”所具有的道德优势势必大大降低;如果“刑”不完全代表“法”,那么至少“法”就应当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也能如同“礼”一样成为一套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规范。
其次,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那么“德礼”也不会对“政刑”呈压倒之势。“礼”在孔子思想中是一套具有价值意义的规范,是“仁”“德”的制度化的实践与表达。“德”“礼”相较于“政”“刑”而言更有指导意义、教化意义。在孔子思想中,“德“”礼”优于“政”“刑”的另一层表达就是“人治”优于“法治”。先秦“儒法之争”的启示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处理“人”的灵活性与“法”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人治”中的“仁治”与“法治”中的“刑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从“儒法合流”的历史事实来看,无论儒家的“人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不够满足社会治理秩序的需要,唯有合流才有出路。当然,孔子并不是先知,他的预见是有限的,其政法观念仅代表了儒家一流。他认为“人治”具有天然的社会治理优势,具有至高的道德性,而“法治”则意味着威吓、制裁,故“人治”优于“法治”。孔子不理解“法治”所具有的“规范”意味,仅仅将其看作是制裁的手段,也就是自己所谓的“政刑”。
“德礼”之所以对“政刑”呈压倒之势,就在于孔子将前者看作是指导规范,而把后者作为制裁手段,同时将作为制裁手段的“刑”理解为“法”。事实上,规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有指引性的内容,也有制裁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法”不只是“刑”,而是一整套规范,那么“刑”就是规范体系中的一环,无所谓轻重,“德礼”也就不会对“政刑”呈压倒之势。当然,在孔子的思想中,“德礼”优于“政刑”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理想是泛道德化的,无论是作为弘扬社会风气的教育内容,还是作为制度实践的礼治秩序,都是以道德指导为核心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制度实践的“法”也应该是由道德引导的。因此,作为道德引导之表现的“德礼”势必处于“政刑”之上。
最后,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那么法律的终极目的将不再只是“无讼”式的“和谐”。简单地说,“无讼”式的理想就是希望纷争、诉讼不再发生,而且主要是指在社会风气好、民众素质普遍高的背景下实现的,也即不存在诉讼发生的社会土壤。一直以来学界对“无讼”都有一种误解,以为追求“无讼”就要“息讼”、“抑讼”以致“压讼”。其实不然,在孔子的观念中,“无讼”指代的是一种社会理想,而非现世的实践指导原则。但是,这种社会理想预设了这样一个结果,即作为“刑”的“法”存而不用,或废而不彰。换一种讲法,则是说在“无讼”的社会理想实现之前,“刑”将必然存在,无法废弃。可见,即使再不喜欢“刑”,也要将“刑”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常备手段,以备不时之需。
《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学者解释称:“‘礼’,即周礼。周礼是当时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虽不都是法,但包括了法。大凡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根本法,以及刑事、民事、行政、经济、军事、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都在其中。”[8]“礼”作为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自然包括了“法”,“礼”的使用以“和谐”为贵,“法”的实施同样如此。法律具有定纷止争的基本功能,而和谐自然是法律实施的效果之一。但是,孔子所理解的“法”基本上是与“刑”一致的,此时,“和谐”的内涵就有了变化。当“法”所指代的内容是“刑”的时候,“法”的“和谐”就是无“法”,就是“无讼”。反之,如果“法”不只是“刑”,那么“法”就可以像“礼”一样构成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和谐”的法律精义也将变得更有价值。
总之,“仁政”“德教”与“和谐”的假设基础之一便是孔子所理解的“法”只是“刑”。而当“法”不只是“刑”的时候,“仁政”“德教”与“和谐”等孔子政法观念的核心价值将失去一定的道德基础,进而促使其价值意蕴的相应降低。如今,我们特别强调传统法律文化的借鉴意义,但若无法认清孔子之“法”实为“刑”的基本前提,无疑会妨碍我们对于传统法律思想的认识,更会有损于今日之借鉴。
五、结语:德礼、政刑的规范体系
在谈论孔子政法观念的时候,不可以忽视孔子对作为“刑”的“法”的认识。从历史借鉴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看,恰当地理解孔子的“法”观念,进而准确把握传统法文化的几个核心命题,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和法治观念。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因为我们无法也不能忘掉传统,并且依旧试图从传统中寻找治世之道。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源头上认清传统资源的思想原貌,势必无法真正借鉴传统,甚至会给“法治中国”的建设带来阻碍。
从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看,孔子政法思想中的“法”只是“刑”。对此,有学者总结说:“从《论语》及其他有关史籍记录中考察,孔子思想中出现的都是‘刑’的概念,还没有后世‘法’的概念,或者说制度层面的思考;孔子只知道‘礼’制,没有制定其他法律制度的考虑,而只知使用刑罚工具。”[9]孔子否定“刑”的工具价值,但忽视了作为其上位概念的“法”的存在。孔子几乎不在法理的基础上讨论“法”的起源、“法”的性质与“法”的作用等一般性的问题。相反,我们所见的更多是有关“刑”的论说。儒家与法家的分野主要体现在这里。固然法家的“法治”亦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但是从法律制度的建制上看,法家肯定了作为制度的“法”的规范作用。总之,作为儒家最大代表的孔子,并没有为后来的儒者开创出一套规范的、制度设计层面的“法”的思想体系,相反,后世所谓的正统法律思想则是“儒法合流”的结果。
然而,我们又无法彻底否定孔子的法律思想。不可否认,从现有史料来看,孔子几乎不讨论诸如立法、司法与执法等法律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孔子为现实世界寻求价值基础、创立礼义制度的努力。孔子之“规范”在“礼”而不在“法”,这表明其所认同的社会制度主要是礼制主导的。《论语·为政》篇载:“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章明确提出了德、礼、政、刑的四维概念,也指出德礼与政刑是两组相对的概念。有学者对此阐释说:“这里提出了一种以德礼政刑为基本概念的规范二元论,提纲挈领地阐发了儒家治国的基本态度。”[10]所谓规范二元论是指用两套规范分别调整秩序和非秩序的一种秩序和规范文化的构思,并且认为德礼是优于政刑的规范。因此,探究孔子的政法观念不仅要在“法”的范畴下讨论,也要将德、礼与政的基本理论纳入研究范围。也许,这已经超出了实证法学的探索范围,但就社会治理而言,这种研究不仅是实证的,更是实用的。
综上所述,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特殊的,“礼”“乐”正在慢慢崩溃,而“法”的地位尚未凸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孔子所理解的“法”实际上是“刑”,与后世的“法”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但另一方面,孔子所倡导的规范二元论思想,指出德礼与政刑实则分属于两类规范模式。前者是为本,以正向的引导为主;后者是为末,以引导失效后的规诫为,二者共同构造成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因此,我们需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认识孔子的政法观念。形式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就是“刑”;实质的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则是德礼、政刑的规范体系。
参考文献:
[1]杨义芹.儒家德刑观论析[J].现代哲学,2010,(1): 51 -55.
[2]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2.
[3]马作武.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与法[J].现代法学,1997,(4):108-111.
[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3.
[5]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45.
[6]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30.
[7]梁治平.“法”辩[J].中国社会科学,1986,(4): 71 -88.
[8]艾永明.孔子法律目的说析论——兼议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J].江苏社会科学,2001,(3):114-119.
[9]杨师群.孔子政治思想批判[J].探索与争鸣,2008,(4):35-39.
[10]於兴中.《孔子家语》中的法律思想[J].中国法律评论,2014,(3):110-118.
【法坛论衡】
Re-exploration on Confucius’Idea of Politics and Law
TAO Jia
(Tianning District Peoples’Court,Changzhou 213000,China)
Abstract:The law thought of Confucius presents some conservativefeatures.With reference from modern theoryof law,its formal meaning of“law”indicates“penalty”,and its essential meaning of“law”turns out to be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ritual and government order.His idea of law is basically limited in the range of penalty,and rituality undertakes partial functions of law,which a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ore values such as benevolent government,virtue education,harmony,and so on.However,law is not only penalty.Accordingly,the core values of Confucius’idea of politics and law need to be reexamined.
Key words:Confucius; mormative consciousness; idea of law; sense of morality
作者简介:陶佳(1988—),男,江苏徐州人,硕士,主要从事法律思想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4-11-09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5)02-009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