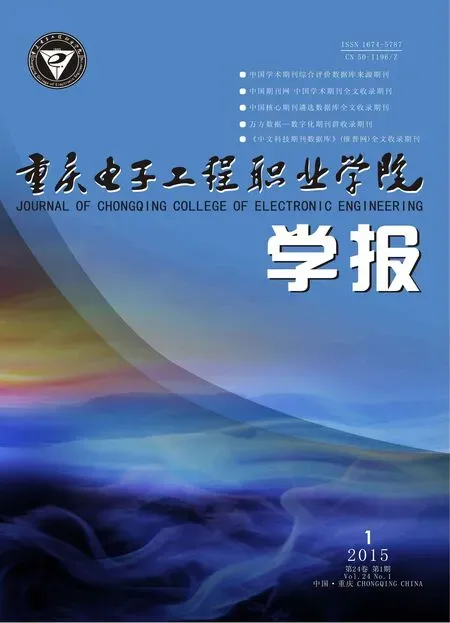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2015-03-19韩雅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韩雅(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韩雅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生命意识是个体生命对于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和感悟,体现在萧红的小说中,它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喜爱与赞美,对种种生命形态的细致描摹,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以及对荒凉人生命运的感叹。进一步来说,则是对自由美好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麻木自私人性的敏锐洞悉,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反思。正是通过对种种充满原生态意味的生命形态的描写,作品不仅实现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反思,更通过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达到了对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观照。
萧红小说;生命意识;生死观;女性命运;生命悲剧
萧红是东北沦陷时期一位极具创作才华的女性作家,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不息,其中以小说的成就最大,最具创作个性,原生态地展示了东北乡村的群体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充满浓厚的悲剧色彩。在这种刻意营造的悲凉氛围背后,是萧红对于“改造国民灵魂”的深切关注,是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不懈追问,是对生与死、灵与肉问题的深沉思索。她至死不渝地信仰和追寻的“温暖和爱”,就是对人类最美好的生存方式的追寻。
萧红曾说:“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作家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从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临终之作《小城三月》,从成名作《生死场》到代表作《呼兰河传》,生命意识一直是贯穿于萧红小说的深层主题。
1 生命的理想:生机勃勃的世界
费尔巴哈说:“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2]萧红的一生颠沛流离,辗转经年,饱尝艰辛,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屡屡求而不得。然而,萧红却把对自由命运的憧憬与追求都倾注在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之上。在萧红笔下,一切的生灵都是那么生机勃勃,灵动、自由、令人神往,这是萧红自由的生命理想的象征。在这个充满生机的自然世界里,作者以一个女童的视角感受着自然的生机与活力。这种一生都未脱去的“孩子气”使萧红获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别样眼光。以儿童的视角观察世界,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以自己的直观的、感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最大限度地去除了世俗的功利观念,更直接地发现和展示事物的本来面目。生命的平常与原始,本真与鲜活,就在这自在自然的天地间得以尽现。
在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构筑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然世界,即“我”家的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中,一切仿佛都是活的:金的蜻蜓,绿的蚂蚱,胖圆圆的蜂子以及飞来飞去的各色蝴蝶,样样都有,热闹非凡,“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花鸟藤蔓都有了灵魂和意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花开了,就像画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在这里,不仅这些原本有生命的动植物如人一般拥有自主意识,就连那些角落里的人造物也同样拥有生命,拍一拍大树会发响,叫一叫站在对面的土墙也会答应,甚至还能孕育出新的生命,“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着,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的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比方缸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在这个生机勃勃自由自在的后花园中,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没有阶级或权利的倾轧,所以当“我”或祖父一挨骂的时候,“我”就拉着祖父到后园去,“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正是在这生机肆意的自然的感召下,《后花园》中的一直在黑洞洞的磨坊里彻夜打梆子的冯二成子,发现并悄悄地爱上了邻居家的笑起来像一朵大葵花似的姑娘;《小城三月》中的翠姨也是在三月春天的蛊惑下恋爱了,要求上学读书,开始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新生活。在萧红的笔下,生机勃勃的自然万物挣脱了僵死的社会制度,重新回归到自由和平等的原始状态,与生命的本真最为接近,寄予了作者对于被束缚和被压制的生存状态的反思。生机肆意的自然景物,是萧红对自由平等的生存状态的向往与追求,是她理想生命图景的映现。
2 生命的困顿:浑浑噩噩的生死场
在萧红短暂而漂泊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穷困、饥饿、囚禁甚至几次直面残酷的战争,她对于当时人们愚昧麻木的生存方式有着最直观和最真切的感受。在萧红的小说中,自然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本应该是更有自主意志,更富于生机,然而萧红笔下的众人却走向了自然的反面,人的外表和内心,甚至于行为动作都已如动物一般。“这动物性的人众有头脑而没有思想,有欲望没有希望或绝望,有疼痛没有悲伤,有记忆而没有回忆,有家庭而没有亲情,有形体而无灵魂。”[3]。萧红通过人物互喻的方式对人们浑浑噩噩的生死状况细致描写,刻画了苦难中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丧失,更表达了她对生存困顿的迷茫和追问。
鲁迅曾说萧红的成名之作 《生死场》“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亡的挣扎”[4]。在《生死场》中,作者写出了当时东北乡村一群蒙昧的乡人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他们“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5]乡村中的人,是动物一般的外表:麻面婆“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她抱着茅草到厨房做饭,就如同“母熊带着草类进洞”。她的丈夫二里半“面孔和马脸一样长”,喝水时“水在喉咙里有声,像是马在喝”,他唤羊的声音“像是一条牛”。老王婆的脸纹发绿,眼睛发青,像“猫头鹰”。这些描述并不是为了说明人的形体的丑恶,而是为了指涉人类以动物的方式支配着生命。成业与金枝在一起,并不是为了什么爱情,而仅仅是出于动物性的本能。人的生育如同动物繁殖一样盲目而随意,只是随季节变化而来的本能,只是一种机械的、毫无情感的肉体程序:“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隔着一堵墙,屋内的女人与窗外墙根下的猪一同生产。“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他们体验不到情感,只有物质和欲望来满足他们,他们生存的意义仿佛只剩下如何填饱肚子,由此带来的是对于物质和欲望的赤裸裸的追求,并直接导致对生命的漠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王婆三岁的女儿意外摔死了,可她一点也不后悔,一滴眼泪都没有淌下,因为麦子获得了丰收;金枝误摘了青柿子,“母亲就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平儿偷穿了父亲的靴子,母亲就“好像山间的野兽要猎食小兽一般凶暴”。在萧红笔下,一再强调的是农民生命价值的无意义和正常人性的扭曲与丧失,他们只是一味地屈从,为反抗地主加租而组织“镰刀会”最终解散,日本人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固有的生存状态,可是对于“爱国军”,他们仍然“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他们只是没有饭吃!”他们的“生”,是挣扎在天灾、饥荒、传染病以及专制、战争等人祸之下的浑浑噩噩的“生”,他们的“死”同样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死”。五姑姑的姐姐难产而死,刚出生一个月的小金枝被摔死,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被折磨致死,甚至于传染病肆虐之时大批村民的死亡,他们的死亡悄无声息,并不能给活着的人带来什么改变。《呼兰河传》中人们的生死虽不像《生死场》中所描写得那样惨烈,却同样是蒙昧无知、麻木恣睢的:大泥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却从来不愿意填上,因为它是人们生活中仅有的乐趣;造纸的纸房里饿死个私生子,但因为是个初生的小孩,就算不了什么了;卖豆芽的王寡妇的独子淹死了,她虽时常疯子似地哭闹,但哭完了仍然卖菜,仍是平平静静地活着。他们对于他人的生命同样是看客一般的漠视:儿子踩死了一个小鸡仔,母亲就打了他三天三夜;小团圆媳妇因为长得高,就被邻居说闲话,她的婆婆就整天打她,为“规矩出一个好人来”,甚至最后在群策群力之下被活活烫死;王大姐做姑娘时,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可未经明媒正娶就与门不当户不对的冯磨倌结合后,却是“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最终在人们的流言之下悄无声息地死去;有二伯和老厨子去参加葬礼,回来只顾着说“酒菜真不错”,对于葬礼的经过却一字不提。他们活着,活着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吃饭穿衣,而死则是“人死了就完了”。在他们眼中,“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限制了人们的视野,阶级制度又给人们套上了枷锁,人们从未获得人格的尊严与独立,也无从展示他们自主的生存意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只是动物一般的存在。
3 生命的悲悯:身不由己的女性命运
女性是生命的创造者和承继者,没有女性就没有人类。然而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女性只是男性社会的附庸,始终处于被压迫、被歧视、被制约的状态,其自身的人格和生命的价值意义从未被承认过。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萧红曾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我是个女人。”[6]作为旧时代女性的直接受害者,萧红早年为反对包办婚姻而逃出家门,漂泊一生,对于女性在男性社会压制之下的悲哀命运,萧红有着切身的体会,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浸透着萧红对于女性命运的特殊关注与思考。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体验映射作品中的人物,自觉地为中国最广大下层女性代言,用尖锐逼真、悲悯深刻的笔触,谱写了一曲曲女性向命运抗争的悲歌。
萧红曾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7]在萧红的眼中,女性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当她一出生的时候,就套上了来自男性社会的重重枷锁,就连名字都带有被奴役的烙印,如黄良子只是在丈夫黄良的名字后面加个“子”而已,有些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名字,如麻面婆、小团圆媳妇等,不过是一些代号。父权、夫权等封建制度迫使女性处于生活的最底层,总是处于被压制和被奴役的地位,更没有作为独立的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不论一个男人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他总有统治和压迫女人的权利。如《生死场》中的二里半尽管窝窝囊囊,低眉顺眼,但是他对妻子仍然行使着主子的权利,对她又打又骂。成业对金枝没有情感上的爱,有的只是出于原始本能的宣泄;婚后的金枝整天为家务忙碌,换来的仍然是咒骂,当生活更加窘困时,成业只会拿妻儿撒气,要把金枝卖掉还债,最后竟残忍地把出生才一个月的女儿摔死。《生死场》里的麻面婆、金枝、月英、五姑姑的姐姐等每天需要应付的主要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来自男人的奴役与伤害,就连庙中的女神像,也不能逃脱被男性压迫的命运。《呼兰河传》中,娘娘庙中的娘娘像塑得十分温顺,老爷庙中的男人却塑得十分凶猛,人们总是先到老爷庙去打过钟磕过头,而后才到娘娘庙去,以至“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女性的尊严被任意践踏,生命被任意摧残,她们都是奴隶的奴隶。除了来自男性的压迫之外,女性在精神上、心灵上更是受到代表男性意识的封建传统道德的毒害,成为传统习俗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是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温柔顺从的典范,却依然不能逃脱被抛弃的命运;五姑姑的姐姐难产时,收生婆的一句“压柴,压柴,不能发财。”就让家中的婆婆把席下的柴草又都卷起来,她只能像一条鱼似的趴在土炕上,传统陋习使女性神圣的生育也成了一种刑罚。金枝的母亲在平时像老虎一般打骂着自己的女儿,但当她听说金枝有了身孕时,却像一个温柔的母亲了。然而她并非是出于母亲对女儿的关心,而只是出于礼教对她的嘲讽压力,并没有真正为金枝的未来和幸福考虑。
在萧红的小说中,女性不仅承受着男权社会与传统意识的双重压迫,更为可怕的是,女性意识不到这种不公,反而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她们木然地看着自己的同性在痛苦中死去,甚至没有最起码的悲哀和同情,麻木到没有反抗,没有怨言,甚至她们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金枝母亲愿意把痰吐到女儿脸上,当金枝无意识地损坏了农作物的时候,她就会像老虎一样扑向自己的女儿。而当金枝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遭到了强暴和蹂躏时,不仅旁边那些女人“对于这件事并不表示新奇和注意”,就连金枝的母亲在看到了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愤与屈辱的钞票时,也沉浸在金钱的幻想中,忘记了自己曾经叮嘱的“不许和男人打交道”,忘记了对女儿抚慰和怜惜,反而还催促女儿尽早回城。在这里,“母亲”不再是伟大的慈爱的形象,而是一个无情而冷酷的身份代号,女性就这样无知无觉地陷于同性的迫害中。《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本是一个健康、活泼的纯真少女,来到婆家后,因为不符合传统意识中合格媳妇的标准,众人就都对她百般挑剔,于是婆婆就整天打她,为的却是 “规矩出一个好人来”,“不打是不中用的”。就在这样“善意”的帮助下,小团圆媳妇悲惨地死去了,成为封建意识的牺牲品。无论是金枝的母亲还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她们没有一个是罪大恶极的人,她们并没有害人或害己的意思,然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平庸的恶”,成为封建传统意识的帮凶,不断地迫害别人,并被人迫害。萧红不仅关注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更深入到对病态社会制度与封建意识的揭露与批判中,由此揭示出女性在重重桎梏之下可悲的命运和扭曲的灵魂。
4 生命的悲哀:荒凉悲惨的生命色调
对人类生死问题的关注是萧红小说的基本主题,其小说虽涉及阶级斗争、农民劳作、地域风俗、男女爱情等诸多题材,然而其深层的主题都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在萧红笔下,人类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短暂,挣扎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脚下,许多生命无声无息地消逝。母亲因难产而死,女工被工头毒打而死,患病的月英被折磨而死,健康活泼的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致死,温婉沉静的翠姨抑郁而终,这些年轻而美丽的生命都在生活的摧残下消亡了,更有不计其数的生命终结在饥荒瘟疫和战争冲突之中。生命的脆弱易逝固然是悲剧,然而顽强活下来的人却并不意味着他们逃脱了这种悲剧,反而陷入一种更加悲哀的宿命轮回之中,跳不出悲剧命运的怪圈。《后花园》中的磨倌冯二成子,整天只知道拉磨,生命仿佛静止了一般混沌沉滞。邻居姑娘唤起了他生命的活力,也让他开始了痛苦的思索,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不曾有过的心理和思绪:“他越往回走,他就越觉得空虚。路上他遇上一些推手车的,挑担的,他都用了奇怪的眼光看了他们一下:你们是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只知道为你们的老婆孩子当一辈子牛马,你们都白活了,你们自己还不知道。你们要吃的吃不到嘴,要穿的穿不上身,你们为了什么活着,活得那么起劲!”冯二成子仿佛被点破似的从睡梦中苏醒,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悲剧,然而他却无力改变自己毫无目标的人生,更毫无自主意识。他只能宿命地退回到磨房,沉滞的生命如同一岁一枯荣的后花园一般毫无改变,他就像拉磨的驴一样,转不出命运的磨道。《小城三月》也是一个命运的悲剧,小说中的翠姨,因为是寡妇的女儿,就只能嫁给同样是寡妇的人家的儿子,她认定自己的一生命运早已注定,反复感叹“我的命,不会好的”,内心非常痛苦,任凭生命一天天枯萎下去,直至死亡。她坟头淡青的草,不同于鲁迅在《药》中烈士的坟头上平添的花环,它并不象征着新生的希望,而只是又一个春天的来临,又一个悲剧的开始。《红玻璃的故事》是萧红的遗构,在这个故事里,王大妈在女儿家看到外孙女玩一只红玻璃花筒,她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女儿小的时候,都玩过这样一只红玻璃花筒,她开始对命运有所领悟。“现在小达儿是第三代了,又玩儿着这红玻璃花筒。王大妈觉得她还是逃不出这可怕的命运安排的道理吗?——出嫁,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留下她来过这孤独的一生?谁知道什么时候,丈夫挖到金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作老婆的能不守空房?”一只小小的红玻璃花筒,揭示了生命的荒诞与悲哀以及命运的不可抗拒。
面对这种无力改变和逃不出的悲剧命运,萧红的感受是悲哀且荒凉的。荒凉和悲哀在萧红小说中带有作家极强烈的自身体验,也可以说是萧红作品的基本色调。《呼兰河传》中反复出现“荒凉”一词,“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生死场》则是在整部作品中显现出生存环境的荒凉色彩。萧红小说中许多关于景物的叙述都表现出生命的荒凉和幻灭。如《呼兰河传》中的放河灯,开始的时候放河灯的人成千上万,繁华热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河灯流向下游,场面已渐趋冷落,等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一种繁华过后的凄凉,从那明明灭灭的河灯中油然而生。又如“每到秋天,在高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寥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篙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繁华和冷落是生命的两个侧面,繁华是短暂的,当一切繁华过后,留下的则是长久的幻灭。在《呼兰河传》中,作者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止一次地代替叙述者,发出哲学意义的终极拷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这种对人生困境的追问,真切地表现出萧红对生命悲剧的深刻体验。
文学创作的历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8]萧红把创作的目光锁定在人类精神最深层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力上,透过凄凉的世事、悲惨的人生,看到了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双重桎梏下,人类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的混沌生死以及愚昧麻木、残忍扭曲的人性尤其是作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描写,对其在多重压制下人性异化的揭露,增强了作品的悲剧力度。她把自己的不幸融入笔下的人物的不幸中,把自己对于人的生命意识倾注在笔下人物的生存状况的描写中,体现了她对麻木国民性的揭露与批判和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浓浓的悲剧氛围中对理想生存方式的探寻与向往。萧红以她独特的叙述方式,使她看似个别的人生悲剧描写获得了哲学上的普遍意义,也使人们仅凭她对社会一角的描述,窥见整个人类的荒凉与悲哀。
[1]萧红谈话录(二)[A].萧红全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富育光.萨满文化析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9(7).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C].王观泉.怀念萧红[C].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5]胡风.《生死场》读后记[A].王观泉.怀念萧红[C].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6]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7]林贤治.漂泊者萧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徐雷虹.论司汤达的心理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责任编辑闫桂萍
I206.6
A
1674-5787(2015)01-0072-05
10.13887/j.cnki.jccee.2015(1).21
2014-11-20
本文系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2014年提升计划“萧红小说视觉性研究”(项目编号:2014yks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韩雅(1990—),女,安徽泗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