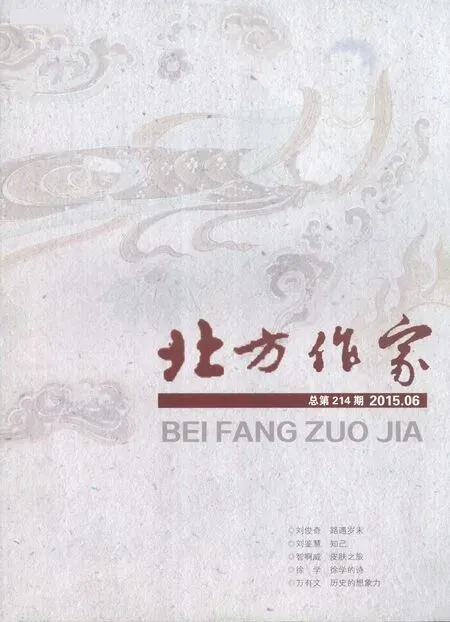浮 萍
2015-11-14湖南汉寿徐凤敏
湖南汉寿 徐凤敏
金枝又站在这块池塘边发呆了。
她用自己的左手轻轻地抚摸自己的右肩头,就像有人抱住自己的肩头一样,有些温暖,心里也感觉踏实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孤独的时候,她都会用这样的动作来减缓心中的苦闷和压力。这大概是刚结婚那阵子养成的嗜好,如今快二十年过去了,仍难以割舍。
金枝原本和朋友合伙开了家夜市店。现在她不得已辞掉了这份工作。无事可做的她,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散心,所以来池塘边傻傻发呆的时候就更多了。
金枝喜欢这块池塘。她没读过多少书,不知道用那些美好的诗句来形容这池塘。她觉得这池塘亲切,与老家门前的池塘很相似。一样的绿草铺在池塘的边缘,池水一样的清澈,无风的时候能照见金枝白白胖胖的脸。“金枝,你的脸真白,海南这地方的太阳怎么就晒不黑你呢?”每次阿南捧着金枝的脸都会说类似的赞美的话。阿南语气里的自豪和幸福,把金枝的心滋润得甜蜜而温暖。
金枝注视着池塘里浮着的一片树叶。池塘边有一棵榕树,很年轻,新叶儿是淡淡的绿,兴许是昨晚的风太大,池塘边落了几片树叶,有一片掉进了池塘。叶片儿很轻,静静地浮在水面上。“就这点不一样,老家的池塘里总是漂着些浮萍,无风的时候也飘来荡去的,让人看不清自己的影子。”小时候,金枝总喜欢在池塘边梳头。母亲很勤劳,总是在金枝还没起床的时候把屋里、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金枝不忍心把头发梳落在干净的地面上。
“母亲,你在天堂过得好吗?”
金枝用力深吸了一口气,想以此驱除盘踞在心中的那些烦乱。“回家看看吧。”这一念头在脑海中突然闪过,可是,她又急忙打消了。已经两年没回过家了。18岁的儿子在北京打工,工资不高,平时没有休假,春节又赶上春运,票涨票少,干脆也不回家,打打电话就拜年了。唔,丈夫在家。可是,两年前,丈夫到海南来看她,她没让丈夫住在自己的小出租屋里。她在宾馆给丈夫开了房间,住了三个晚上,可是,金枝说夜市生意忙,愣是一个晚上也没陪丈夫睡觉,丈夫能不生气么?丈夫不能说金枝什么闲话,因为家里的收入基本是是金枝支撑着的。一个女人每年交给丈夫8万块钱呢。8万块,对于农村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呢。金枝在外八年,给家里挣了几十万,修起了两层楼的小洋房,多少男人羡慕金枝的丈夫啊。
“走就走吧,有种的别再用我的钱。”金枝白天到宾馆找丈夫时,发现丈夫的行李不见了。
丈夫不声不响地坐火车回湖南了。天晓得他是怎么找到火车站买上火车票的。海南到湖南的火车坐票特少,更不用说卧票了。丈夫在火车上站了18个小时,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粒粮,没说一句话。金枝事后听丈夫的朋友说起这些时,心里疼了好多天。
“我不能回家。”
虽然很想家,但无论如何,金枝不想让丈夫知道自己的近况。因为,见到丈夫,金枝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老家在湖南的北方,坐飞机的话也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现在是淡季,飞机票3折,金枝是出得起这笔钱的。可是,金枝还是感觉家是那么遥远。
那件事发生已经一个月了。
金枝小学毕业后不爱读书,就在家里帮着母亲做农活。那时候,父亲还在世,只是身体不太好,不能干重体力活。金枝长到17岁的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整天只能躺在床上。因为贫穷,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坏,两个读书的弟弟也开始逃学,金枝成了母亲的出气筒。所以,那天,有个媒人带了一个男人(后来成了金枝的公公)来到金枝家。那男人围着金枝前前后后仔细端详着,那眼神就像牛贩子见到满意的牛一样。金枝的命运就在那天改变了。牛贩子和病床上的父亲讲了一会儿价(金枝在屋外看着两个男人说话时的表情猜测的),很快就敲定了金枝出嫁的日期。
金枝是害怕出嫁的。离出嫁的日期越近,她跑到池塘边的时候就越多。母亲担心她会做傻事,不准她去。其实,金枝只是害怕,并不是不愿意。因为,她的未婚夫来过好几次了,金枝对他的感觉也还好,并不讨厌。有时候,趁母亲不在屋,未婚夫把金枝抱进屋,两人在床上亲热一番。被未婚夫压在身上的金枝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那是混合了烟草味的男人味道。于是,金枝内心深处就有了一种冲动。终于,在金枝并不懂得爱情的时候,她嫁给了大自己7岁的丈夫。
婚后的日子很无聊。做饭、洗衣、带孩子,丈夫在家做铝合金门窗。吃饭的钱虽然也有,但从出嫁到儿子5岁,金枝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公公死后,家里盖新房子的承诺也随之去了地狱。丈夫日夜敲打铝合金,存折上仍然没有上过4位数。眼看孩子要读书要花钱了,金枝心里急呀。那年春节,表姐来看婆婆。表姐穿得很时尚,手腕上的金链子亮晃晃的,金枝看得头晕。
“金枝,愿意跟姐去海南么?”表姐似乎看透了金枝的心事,主动提出了带金枝外出打工的话。
金枝心里千万个愿意。“谁不盼着钱多一点呢。”那时候,金枝想外出的出发点是考虑多挣点钱,毕竟儿子要上学了,要给他存一笔钱将来上大学呀。金枝跟丈夫软磨硬泡了好几天,婆婆也承诺帮助带儿子,丈夫终于同意了放金枝走。不过,丈夫有个条件,金枝必须跟村里其他的堂客们在一块儿打工,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金枝来海南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她和村里的堂客们在一个镇上做事。金枝在发廊当过洗头妹到餐馆端过盘子刷过碗,可是,她不懂海南话,没干几天就被辞退了。老板要听得懂海南话的,这样不至于走掉大部分顾客。就在金枝时而就业里面失业的时候,一起出门的堂客们陆续都有了人,是那种不算大款,但也可以供她们吃喝,还可以给点零花钱的男人。金枝看到那些比自己年纪大而且黑得像牛屎的堂客都可以不做事轻轻松松的花钱,心里就不情愿起来。
“我就不相信我会比她们差。”
金枝本是个聪明的姑娘,只是脑袋没有开窍。一旦有了榜样,金枝的心里就有了计划。她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皮肤白净,体态丰满,精瘦而皮肤黝黑的海南人大多喜欢丰满的女人;没什么文化,不会给男人制造麻烦;湖南人,有丈夫,这一点得严格隐瞒。因为,海南男人不喜欢说普通话的外来妹,那种婚外情容易暴露。金枝权衡了利弊,开始学习海南话,并且托人办了一张广东的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了3岁。这样,新的金枝就出现了:20岁,广东籍,结过婚,丈夫病逝,儿子刚满一岁由婆婆看护,为养活儿子和婆婆而出门打工。
新金枝出现三个月的时候,阿南也出现了。阿南是在朋友请吃饭的时候认识在餐馆干活的金枝的。金枝白净的婴儿肥脸蛋,丰满的体态,浅浅的笑,令阿南失眠了一个夜晚。第二天,阿南通过餐馆老板了解了金枝的身世,怜香惜玉的情愫如五月疯长的野草,爬满了蠢蠢欲动的心田。为什么用蠢蠢欲动这个词呢?因为,阿南是小镇上的国土站的出纳,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有实权,吃喝玩乐都可以开发票的,而且,在土地如金的海南,只要沾上国土这两个字就能闻到浓深的金钱香味。不过,阿南是谨慎的。他也很想有一个情妇,省得朋友聚会时自己孤单一人。但,阿南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妻子在镇教育行政部门当会计,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都很聪明,大学快毕业了。阿南可不想因为情妇的事而闹得家庭不和。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对象——不求年轻漂亮,但求善解人意。他摸清了金枝的底细后,认为金枝是一个合适的情妇人选。
“金枝,做我的情妇你会不会后悔?”阿南在餐馆的包间里单独请金枝吃饭。
“只要你对我好,我不会让你为难的。”看着比自己大15岁的阿南,金枝的心如玻璃一样透明。
“你有什么要求?比如每个月给多少钱?”阿南问。
“我不提要求,只要我对你好,我相信你不会亏待我的。”
金枝真没提任何要求,倒是阿南提出了要求。他为金枝重新租了一个房子,希望那里是他和她两个人的爱巢。
自从跟了阿南后,金枝再也没有到任何店铺打过工了。凡是阿南认为可以带金枝出现的场合,金枝都会跟随。阿南为金枝买了黄金首饰和新衣服。阿南经常会收到一些红包。他从来不看红包里有多少钱,总是直接将它们给了金枝。金枝存折上的数字很快就突破了5位数,高的时候达到了6位数。
金枝从不开口向阿南要钱。她只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她把情妇看成一项工作。比如,阿南住在出租屋不回家的时候,金枝会认认真真地履行妻子的所有职责,家务活从不要阿南沾手;阿南宴请朋友时,金枝会根据需要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时是同事,在时是情人,有时是朋友,那时候,金枝的海南话说得很地道了,没有人当她是大陆人。金枝的酒量之大是阿南没有料到的。金枝常常会在阿南被灌酒时反败为胜,以至于后来每当单位里有业务上的酒宴,阿南的领导都会说:“阿南,把你那朋友金枝带过去,让湖州来的那般人喝好喝醉。”
村里来的堂客们经过短暂的被包养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又成了孤家寡人,而且因为打工挣的钱太少活又重,终于回到了起点去,只有金枝一个人留了下来。那时候,阿南开始整夜地留宿在金枝的床上,因为,妻子办了内退手续,到广州去和儿子女儿住在一起,只有春节的时候才回来。
“宝贝儿,你真是我的宝贝儿。“在床上,阿南总是抚摸着金枝白皙的肌肤,并喜欢把头藏在金枝深深的乳沟间。
金枝全身心的付出,终于得到了阿南的认可和信任,有时候,金枝根本就忘记了“情妇“的身份,以为阿南就是自己的丈夫。她虽然每年都回家两次,这是和阿南约定好的。春节要回家给婆婆拜年,暑假要回去安排儿子读书的事。头几年,金枝每次回家按约定可以住15天左右,随着信任度地增加,金枝可以作主回家住多少天了。可是,金枝越来越不爱在家多住了。虽然家里的小洋房早已完工,明晃晃的瓷砖建筑矗立在四周都是稻田的高坡上像一尊具有纪念意义的雕像,高高在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在阳光下炫耀着富裕。可金枝不愿意多住一天。
“你不能轻点吗?“
家里的夜晚总是那样冷清,不,是冷漠。爱的亲密接触成了金枝最痛苦的梦魇。金枝和丈夫是分开睡觉的。这不是金枝提出的要求,是丈夫多年养成了习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在电视播放中睡觉,醒来后又继续看电视直到天亮。金枝喊丈夫上床睡觉,丈夫说习惯了睡在沙发上。金枝也不勉强便独自睡了。金枝睡到半夜被吓醒了。丈夫扑在了金枝的身上。金枝摸了摸短裤仍在。原来丈夫懒得动手脱金枝的短裤,从短裤的裤腿里硬往里闯,弄得金枝痛苦不堪。
丈夫完事后很快又回到沙发上去了,留下金枝躺在床上暗自落泪。这时候她恍然想起了“妓女”这个词。丈夫全然不顾她的疼痛,一声不吭地,像憋足了劲的撞钟和尚。“丈夫会是在报复吗?”她自然想起了阿南。阿南从来不这样粗鲁地做爱。阿南的手很温暖也很温柔,他在抚慰金枝的身体的时候,金枝就觉得自己化成了水。她希望自己真的变成水,让阿南喝个够。
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儿子大学没考上去了上海打工,金枝就越发不爱回家了。为了奖励金枝,阿南投了5万块钱与人合伙开了个夜市,让金枝负责打理一切。金枝的生活更充实了,觉得找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对工作对阿南都有了强烈的自豪感。
可是,那天傍晚,金枝刚刚把夜市的铺面打开,将桌子依序放在街道边上,一伙染黄头发的小青年闯了进来。
“这里是金枝的夜店?”为首的小青年问金枝。
“是的。你们要吃点什么?”金枝和蔼地问道。
“我们什么也不吃,只是告诉你,滚回湖南去。”小青年恶狠狠地说:“不然,我就砸了你这铺子。”
“凭什么砸我铺子?”金枝在海南呆了多年,说得流利的海南话。
“装什么海南人。你是广东人吗?你除了骗阿南还能骗得了谁?滚回老家去吧。”
“金枝,先回避一下吧?”金枝的合伙人叫阿珠,劝金枝道。
街面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金枝的脸涨得通红。她艰难地回到出租屋,坐在床上,深呼吸好几次,可是无论如何都控制不住颤抖的双手,最后还是把一只水杯打碎了。水杯上印着阿南的头像,做过处理的,轮廓很像,不知情的人是认不出来的。阿南的头像碎了。金枝环视着屋内,除了碎片,再也找不出一件有明显的阿南标志的物件了。金枝拿出手机找阿南。
“对不起,你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对于这段从二十三岁时就开始的恋情,金枝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并不对将来做出任何承诺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见到阿南的第一天起,金枝就觉得他是可以的信赖的好人。尽管丈夫粗鲁,两人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金枝也从来没想过离婚,更没有想过要和阿南结婚。她本来早就要回湖南了的,家里房子也修起来了,儿子结婚的钱也差不多了,可是,她就是舍不得阿南,舍不得和阿南在一起的那些记忆。
“是谁干的?”这一疑问一直萦绕在金枝的脑海中,以至于夜不能寐。她开始怀疑和自己接触过的阿南的那些朋友们。她不再去夜市了。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晚上就去池塘边呆想。她每天满脑子都是:“是阿南的妻子发现了我和她丈夫的事吗?是阿南知道了我的假身份的事吗?除了年龄和家庭住址是假的,我对阿南的一切都是真的,阿南从此不再理睬我了吗?“
金枝常常想着想着就会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她突然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虚伪。一想到那么多年的感情,就因为妻子的干涉或者知道了一些真相便逃得无影无踪,连手机也关机,金枝觉得心存的对阿南的自豪感突然间就灰飞烟灭了。
“即使是他再来找,我也一定不理他了。“金枝决定换掉手机卡,不再跟阿南联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闹失踪,金枝都仍然往好处想阿南的难处:或许阿南的手机被他妻子没收了。金枝不想再给阿南添乱了。
金枝刚刚删除阿南的号码,手机突然就响了。她吓了一大跳。她看到屏幕上出现了“爸爸”两个字。是丈夫打来的。说来好笑,为了防止阿南发现自己的秘密,她把丈夫的手机号码编辑成“爸爸”,丈夫打电话时,遇到阿南在身边,金枝就会对阿南说是爸爸来的电话,然后金枝就用家乡话跟丈夫说话。阿南傻乎乎地听,听不懂,傻乎乎地享受金枝与爸爸通话时的亲情。那时候,看到阿南傻乎乎的表情,金枝还有点内疚。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
金枝接通电话。
“你在哪里?过来接我一下。我在长途车站。”丈夫说。
“你怎么突然来了?”金枝坐了出租车赶到车站,把丈夫接到自己的出租屋,一边倒水,一边问道。
“最近家里没活儿干,突然想你了,就来了。“丈夫脸上的表情木木的,语气也更平时没什么两样,可金枝听起来居然很感动。她忍住了,没让眼泪落下来。
“你这屋子布置得很温馨啊。”金枝似乎闻到了酸酸的味道,是从丈夫的声音里泛出来的。金枝有些内疚。自己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快20年,这是丈夫第一次进来。
看到金枝脸上的窘迫相,丈夫没忍心继续住下说。他转过身子,打量了金枝几眼,问道:“你瘦了,是不是很累?”
“没有的事。我减肥了。”
“谁让你减肥的?女人胖才好看。”丈夫说话的声音比平时许多:“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妈生病了,想见你。”
丈夫说的妈是婆婆。金枝的母亲已经去世了。金枝与婆婆的关系很好,一听婆婆病了,心里自然着急,连忙问:“送医院了没?什么病?”
“医生也没看出是什么病。妈说是相思病,她想你了。”
丈夫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每次回家,金枝都要和婆婆在一个床头睡一晚,婆媳俩拉一拉家常。婆婆生了四个儿子,总说儿子不亲热,还是女儿好。婆婆喜欢金枝,总说金枝是家里最辛苦最孝顺的。金枝也很体谅婆婆,逢年过节都给婆婆买礼物。金枝奇怪丈夫的说的话,不过,心里却感觉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如果一直在这个出租屋里满脑子都想那件事儿,太痛苦了。
“回家就回家吧。”
一提起故乡,金枝心情就很沉重。十多年了,自己连家乡的街道都不熟悉了,和自己一起出来打工的堂客们也衰老得没有了共同语言,不仅如此,对于自己在异乡的生活,她们像新闻主播一样准时、热情、详细。可是,再呆在海南也是很无趣的呀。
金枝回到久违的家中,婆婆没有大病,只是比两年前更爱唠叨了。婆婆依然给金枝做最好吃的菜,但菜的口味比以前重了。房子虽然瓷砖仍然明亮,但明显有了岁月风雨留下的痕迹。
金枝的房间还一直保留着两年前的老样子。她努力不去想夜晚那床上曾经发生的痛苦的事情。她一边在窗前眺望着外面的景色,一边心不在焉地想着婆婆的变化。她的房间在二楼,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田野和池塘。田野里刚刚收割完庄稼,村民们把那些散落在田间的稻草子挪成垛,用火将它们烧成灰烬做为肥田的肥料。青烟在无风的空中燃成一条线,越往上去越细,最后与天色融为了一体。因为距离比较远,金枝看不清暮色中的池塘。水中的鱼儿还是照样推着浮萍转悠吗?
夜色暗了下来,金枝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快九点了。金枝还不适应家里的生活节奏。在海南,这时候忙得正欢呢,那些宵夜的人正在陆续进入街市上的各种排档。老家的生活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早上六点钟田里就有人在干活了,晚上一到九点,村子里各家各户的灯光就开始少了。金枝有点不知所措。她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怎么过。
丈夫依然在客厅的沙发上躺着。也许是累了,丈夫的鼾声均匀在响起来。金枝想走过去看会儿电视,可那念头刚一出现,立刻觉得胃隐隐地不舒服起来。她赶紧跑到卫生间洗漱起来。
金枝十点整就上床休息了,但没有睡着。黑暗中,她警惕地倾听着客厅沙发上的动静。鼾声响着,她的心里就踏实,鼾声停了,她的心跳就加快。她心里惴惴不安的是,如果丈夫突然进屋来做爱,她是顺从还是将他推开。
金枝翻来覆去睡不着。算了,不睡了。她想起床喝点热茶。因为在黑暗里静静地呆着,更容易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披了一件厚点的外衣,来到了一楼的厨房。出乎意料的是厨房里居然亮着灯。婆婆正坐在灶前烧火。金枝看见了婆婆被灶火映红的衰老的脸,心里不由得一酸。
“妈,你在做什么?”
“哦,我想烧点水,兵崽晚饭后杀了一只鸡,我想把鸡收拾干净。”
“明天做吧,明天我来做。”
“反正闲着也是没事。你回来一趟不容易,多休息休息。”婆婆站起身,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看看水是否烧开了。锅盖很大,将婆婆瘦小的身子几乎全部遮住,腾腾热气瞬间吞没了婆婆的身影。
金枝坐在婆婆烧火的位置上,拿起柴火往灶孔里塞。婆婆说:“不用放柴火了,再捂一下水就开了。”说完,婆婆将锅盖重新盖上。
在等水开锅的时间里,金枝的望着灶孔里剩余的柴火慢慢变成灰烬,婆婆望着金的脸,看那火光在金枝的脸上忽明忽暗。
“金枝,兵崽是不是对你不好?”婆婆忽然问道。
金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是,啊,没有。“
“金枝,你别怕,兵崽对你不好你只管告诉我,我来管他。“婆婆说:”我四个儿子中兵崽最孝顺,我的话他不敢不听的。“
“没有,妈。“金枝感激婆婆。虽然丈夫行事粗鲁,但刚结婚那几年还是比较体贴的。那时候,金枝的妈妈还在,经常生病,弟弟不肯读书,妈妈就叫人把金枝叫回家去,一是要钱治病,二是要她管教弟弟。金枝很烦,脾气变得急躁起来。兵崽总是用双手抱着她的肩头,轻轻地安慰着:”别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金枝不由自主地双手抱住肩头,抬起头,望着婆婆的眼睛说:“妈,没有,兵崽对我很好。”
“那兵崽为什么睡在沙发上的?”
“妈,兵崽心疼我,怕我累了,让我好好睡一觉。”金枝心情有些复杂。自己外出这么多年,丈夫也许有了其他的女人了吧?记得上次丈夫在海南不辞而别后,金枝在电话里对丈夫说过:“我一个人在外打工,没有手艺,没有劳力,若没人罩住,一个外乡女子开餐馆能开下去么?你若是心里不舒服,就找个女人吧。”
“妈,就你喜欢多想。”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厨房。他穿着曾经被金枝扔掉过的旧睡衣,手脚麻利地把杀死的鸡放进水桶里,拿大木勺将刚刚开锅的水舀起来淋到鸡身上,然后用钳子夹着鸡在开水里打个滚,让鸡毛湿透后将鸡放进大木盆里,快速地拔掉散着腾腾热气的鸡毛。
“金枝,别打工了,回家来吧,还是家里好。家里人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婆婆牵着金枝的手,两个人回到客厅。
“妈,你们是不是听到什么话了?”望着疼爱自己的婆婆,不可名状的后悔感一股脑地涌了上来,金枝不由得垂下了头。
“别人说什么我不听,但我知道打工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我不希望你受一点点委屈。兵崽也不想你受委屈。你为这家里付出得太多了。”婆婆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金枝的肩头。婆婆的手暖暖的、轻轻的。金枝的泪水不断地从眼里涌了出来。一个人在海南漂泊,生活的寂寞,永远得不到回报的恋情,伤害别人家庭的悔恨,以及这一个多月体味到的痛苦和悲伤都在瞬间释放出来。金枝啜泣着。
“金枝,别多想了,早点睡吧。”婆婆站起身,手在金枝的肩头拍拍,慢慢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金枝回到房间,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了。当年自己打工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家人和自己都生活得好一点,然而,现实生活是残酷的,你不得不时时修正原定的生轨迹。金枝的生活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迹,她不得不经受因自己的选择而滋生的屈辱和痛苦,不过,婆婆的一番话,多少给了她安慰。
“金枝,还没睡?”丈夫处理完厨房的事,看到金枝房间的灯光仍然亮着,走到门口问:“你想吃哪种味道的?红烧的还是清炖的?“
“随便。“丈夫做菜的手艺是村里公认的。金枝想,丈夫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当厨师呢?
“哦。那你早点睡吧。“丈夫停在门口说。
“你还睡沙发吗?“金枝突然很想闻闻丈夫的烟草味道了。
“唔,你太累了,明天吧。“丈夫的脚向房间挪了一小步,很快又退了出去。他替金枝关上门。金枝听着他的脚步,慢慢地走向客厅。
金枝疲惫地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她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婆婆和丈夫已经把早饭都做好了。
清炖鸡汤的香味飘荡着。金枝还没到厨房就已经闻到了。青菜是从屋后的菜园子里摘下来的,甜脆可口。一碗油炒的米糊辣椒,蓬松酥软。金枝的胃口一下子好了起来,仿佛饥饿了好多年。
“金枝,好吃吧?“婆婆眯着眼,笑盈盈地问。
“嗯,真好吃,好久没吃到这样的饭菜了。“金枝一边吃,一边答应着。在海南,金枝几乎没有吃过早餐。夜市店收摊一般都在凌晨三四点。阿南上班时总是轻轻地起床,然后在十点左右(如果不出差开会的话)将早餐买好送到房间。
金枝又想起了海南,忽然有些不安。她开始在考虑婆婆的建议,结束打工生活。可是,自己一直过着的撒谎的生活,还有那些不同的生活作息方式,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男人,这些都能统统忘掉、重新再来吗?
“金枝,我把那块池塘承租下来了,你抽空去看看养点什么比较合适。“吃过早饭,丈夫推着摩托车出门。今天,他要去县里谈生意。
“兵崽,带金枝去县里逛逛,池塘的事你们两个人回来再商量。“
金枝倚在门口,听见婆婆跟丈夫说话。金枝好几年没去过县城了。上一回去县城是陪儿子缴学费,已经四年了。那时一家三口坐一辆摩托车,儿子坐在中间,一路上跟金枝聊不停。现在,儿子在上海打工,除了在电话里短暂的聊天之外,一家三口天各一方,已经没有家庭的氛围了。
“去吗?“丈夫跨在摩托车上问金枝。
“去吧,去吧。你等她一下。“婆婆催金枝上楼去换件衣服。
金枝不想辜负婆婆的心意,心里也想去县城看看。县城变化很大,金枝想,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可能认不得路了。
“兵伢儿,带媳妇儿去逛街?莫把牙乐到车轮子底下去了哦。“从村头经过时,一群人正在树荫下闲聊。
“兵伢儿,你媳妇儿越来越漂亮了,要看紧点哦。“
“谁说这种无聊的话?“金枝不认识说那话的男人,问道。
“开玩笑的话,不用往心里去。农村人嘛,粗一点,心都不坏。“丈夫的话里似乎有话,但语气很平和,金枝也恼怒不起来了。
丈夫的车速很快,金枝有点害怕地用手扯着丈夫的腰边的衣服。她又嗅到了那久违了的熟悉的味道。
“不怕吧?坐稳了,抓紧点。“丈夫转过头叮嘱了一句。他的脸被头盔罩住了,金枝无法听清他说的话。前方在修路,车子颠簸得厉害。金枝把丈夫的衣服抓得紧紧的。也许是被金枝扯得不舒服了,丈夫松开掌车的手,抓住金枝的手,把它放在了胸前的位置。
进城之前要经过一条长长的乡镇公路,据说这条笔直的公路是中央的一个大领导直接拨款下来修的。公路两旁边的柳树已经长到能遮荫了。金枝对路边的沟渠突然有了兴趣。原来,沟渠里栽了莲的,虽然现在已经不见了荷花和莲蓬,但荷叶儿还青青的,有的如鹤立鸡群般独立于水面,有的则匍匐着随水波荡漾。“那是荷叶还是浮萍?“看着渐渐远去的、浮在水面上的小小的叶片儿,金枝问自己。荷叶儿终是有根的,若是浮萍就不同了,它不知道该去那里找自己的根,却又总想找到,所以才随流水不停地漂泊。漂泊是自由的,可并不代表永久的快乐,无根的寂寞和孤独的冰冷,始终令它无法停住脚步。金枝忽然觉得自己一直过着浮萍般的生活。她骤然感到一阵凉意,身子自然贴在了丈夫的背上。
金枝靠紧丈夫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突然向旁边急转了一下。金枝吓坏了,赶紧离开丈夫的背脊。丈夫停下车,掀开头盔,问道:“怎么啦?“
“是荷叶还是浮萍?“
“你说什么?哦,是荷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