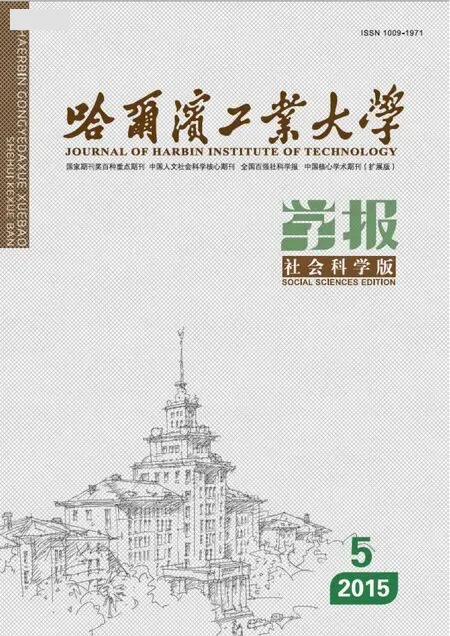灵魂里的山水———论冯至散文集《山水》
2015-03-17陈邑华
陈 邑 华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350108;2.闽江学院 中文系,福州350121)
引 言
冯至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作家、学者,以诗著称,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冯至的诗歌领域,对其散文集《山水》很少涉及。《山水》出版于1943年,大部分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冯至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这时期,冯至在昆明市郊的山野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外界是战争、通货膨胀、喧嚣,而山野素朴宁静,倾心于里尔克的冯至,这时候阅读、研究歌德、杜甫,对自然、对生命有了深切的领会与感悟。《山水》富于“宇宙精神”的自然观,贯穿着“正当的死生”的主旋律,清朗深婉的行文,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魅力:宁静素朴的自然,光风霁月的哲思。这在中国现代散文中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一、富于“宇宙精神”的自然观
冯至的散文集《山水》,虽题名为山水,却于一般的山水游记大相径庭,重心不是描摹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抒写大自然的瑰丽雄奇,也不是探寻历史遗迹,思考文化变迁,而是倾心于自然中领悟人生哲理,寻求精神的启悟。
冯至对自然山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边含有无限的永恒的美。”[1]435冯至欣赏的是素朴、本真的自然,他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致,如原野、树、草、鸟的成长、姿态中体会到无限的美、永恒的美。而对于人们热衷的富于历史文化气息的自然景观,不仅没有兴趣,而且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如对于闻名遐迩的杭州西湖,冯至最为不能忍受的就是人为地将历史的糟粕堆在西湖的周围,使得原先纯粹的西湖山水变得支离嘈杂。杭州的西湖,三面环山,湖光山色,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游览、歌咏的游览胜地。白居易、苏轼、杨万里等著名诗人都留下了歌咏西湖的诗篇。民国时期,西湖景点和文物古迹不断得以修建,数次翻修岳王庙、岳坟,修建了灵隐寺的大悲阁、黄龙洞、钱王祠,构筑园林。当时的政府将孤山的御花园辟为公园,左侧则辟为浙江忠烈祠,并在西泠桥近旁建了徐锡麟、秋瑾等烈士陵墓。钟敬文正是有感于西湖的历史、文化,喜爱吟咏西湖的诗文,因着诗文的诱惑,于大雪天游览西湖,写下了富于浓郁诗情的游记名篇《西湖的雪景》。冯至并非不懂历史、不了解文化,之所以不能忍耐西湖被堆积的历史糟粕弄得支离破碎,是由于此时的冯至,内启外发,中西文化的熏染及赴德求学、回国的经历、昆明时期的生活,已形成他自己的自然观。
冯至在《〈山水〉后记》中提出,不应把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应该还给山水本来的面目。他极为欣赏中国宋元以来山水画家对自然的态度。山水画在中国由来久远,早在六朝,就出现了谈论山水的画论。当然,当时的山水主要是作为人事环境的背景,还谈不上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山水画。到了宋代,山水画达到高峰。这时的山水画注重客观、全景整体性地描绘自然,既要真实,又要具有很大的概括性,追求一种人与自然愉悦相亲、“可游、可居”牧歌式的审美境界。这显然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从中晚唐到北宋,禅宗在中国日益流行,出现了许多宗派,可谓是独领风骚。正如李泽厚所说:“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2]北宋的山水画吸取禅宗、道家哲学与自然亲近的准泛神论思想,追求“无我之境”的审美境界,通过纯客观地描绘自然山水,虽然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但仍然清晰地传达出画家对牧歌式自然山水的欣赏与向往。冯至理解、欣赏宋元以来的山水画家对自然的态度,这种“无我之境”的追求,已然贯通天地之精神。
冯至的自然观还深受里尔克以及歌德的影响。1925年,冯至的族叔冯文潜从留学的德国回乡省亲,向冯至介绍了自己喜欢的一些德国近代诗人,其中就有20世纪最杰出的德语象征派诗人里尔克。翌年秋,冯至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极为惊喜,赞赏其绚烂的色彩、铿锵的音调,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散文诗,有如神助。1930年10月冯至到德国留学,就开始大量阅读里尔克的作品。冯至翻译并高度赞赏里尔克的《论“山水”》。在《论“山水”》中,里尔克探讨了山水画的类型,区分出了三种不同的自然山水观。第一种山水观,是作为背景的古希腊人的山水观念。在古希腊人看来,曾经走过的路,曾经去过的海港,曾经消磨过岁月的剧场和舞场以及佳节朝神的游行、热闹欢乐的良宵,都是山水。这里的山水,只是背景,只是作为为人而存在的背景。第二种山水观,是为人所赞美,高于人之上的中世纪的山水观念。“人这样无意地感到了温暖、幸福和那从牧野、溪涧、花坡、以及从果实满枝、并排的树木中放射出来的光彩,他如果画那些圣母像,他就用这些宝物像是给她们披上一件氅衣,像是给她们戴上一顶冠冕,把‘山水’像旗帜似的展开来赞美她们。”[3]87同时“山水成为人的情感的寄托、人的欢悦、素朴与虔诚的比喻。”第三种山水观,倡扬人与山水的相互融合、转化,也就是里尔克所欣赏的山水观念。“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3]91冯至汲取里尔克对山水的理解,自然万物相互平等和谐相处,而又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众生一体,山水是一个人内在的产物,它根源于人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自我的内心化而呈现出来。
歌德的“蜕变论”亦给冯至很深的影响。蜕变论源于歌德对于生命生成、地球形成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研究。冯至在《论歌德》中清晰地表述了歌德的蜕变理论,歌德认为不同种类的植物都是由一个“原型”(即原始植物)演化而来的,一个时段一个时段地转变、提高。歌德也将这一理论运用于阐释动物、矿物,乃至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发展。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在生长着、蜕变着。蜕变可以说是一切生命必然经历的过程,是一切生命永恒的主题。生命中的每一次蜕变,都使得生命重新获得新生。在战争时期,冯至读歌德的作品,对其“蜕变论”有着更为深切的领悟,无论读长篇巨著还是短小诗句,往往感同身受,经常有抛弃旧我迎来新我的迫切需求[4]。
在20世纪40年代混乱狂嚣的抗战时期,昆明的一隅素朴、安静的自然山水成为了冯至的精神寓所,也促使了冯至自然观的进一步形成。冯至在《〈山水〉·后记》中就谈到他的自然观的形成,得益于寄居昆明的七年生活。昆明附近素朴、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1]436。冯至汲取中国禅宗、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一体”的思想,融合里尔克的山水理念以及歌德的蜕变论,形成自己独到的富于“宇宙精神”的自然观,即众生一体、万有同源,一切均在关联变化中向前向上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不同于中国传统自然观,淡化个性,追求天人合一,或追求“出世”,将自然作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这一自然观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充满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冯至的自然观超越了游者对自然山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游赏、表现的境界,也超越了游者“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寄情山水的境界,进入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抵达本体的境界。这一自然观亦是一种宇宙观,贯彻着一种“宇宙精神”,传承道德的存在载体,领悟生命的智慧之源。
正是有着这一独特的自然观,域外风物、国内山水、自然景观、人生际遇,能够引起心灵感应和共鸣的审美对象,这些“灵魂里的山川”,都是山水,都成为了《山水》中表现的对象。当然,冯至关注的不是外在的形貌,而是热衷于在山水中探寻人生哲学、生存哲理,寻求贯通天地精神的大道。
二、主旋律:正当的死生
冯至的《山水》关注“灵魂里的山川”,流淌着光风霁月的情怀,贯穿着富于宇宙精神的主旋律:正当的死生,正应和了康德所说的“心中的道德律”和“头上的星空”,即关于生长、关于死亡的思考,充溢着担当、坚忍、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以及睿智坦荡的生死观。
冯至于昆明的生活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质匮乏,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这时的冯至虽然物质生活贫乏,精神却是健康愉悦的。冯至散步于山林、原野,领略自然风光。田埂上的小草,山坡上的树木,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给予冯至诸多的启示,使得冯至从中领悟到了什么是生长,什么是忍耐。昆明的山水给予了冯至丰富的精神滋养。这时期,冯至阅读歌德、杜甫、里尔克等人的著作,皆感到无比的亲切。这亲切感的产生,犹如友人的相处,因性情的相投,因相互的欣赏。冯至在《工作而等待》中就说:“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1]356现实生活的艰辛,冯至更深切地领会到杜甫诗歌的伟大。杜甫在战乱时期,坚持创作,坚持“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抒写现实图景,二十年的时间,这饥饿的身躯竟绘制出一个时代的苦难。冯至感佩杜甫诗歌的艺术魅力,更感佩杜甫的生活态度、执着的精神。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冯至就指出,在当前如此艰难的时代,敷衍蒙混、超然洒脱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执著的精神才是目前迫切需要的。冯至阅读、研究里尔克、歌德、杜甫等诗人及其作品,对成长对人生对生命有了更多的理解与思考。
《山水》中所记述的景、人、物,都平常、平凡。如自然景色,有德国柏林郊外的爱西卡卜、瑞士东南的罗迦诺乡村、河北大沽口外的荒岛、江西的赣江、昆明郊区的林场、昆明滇池的西山、广西的平乐,大多为无名的地方,即使是著名的风景区,冯至也没有去描写迷人的风光。他所倾心的风景是宁静平和、带有原初意味的朴素的山和水。在这安宁静谧背景下活动的人物,除了《两句诗》中提及的贾岛、《C君的来访》中的C君(冯至的中学同学陈展云),其他都是无名氏,甚至连姓也没有。《赤塔以西》的牧师,《蒙古的歌》的歌者,《怀爱西卡卜》的房东太太,《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的雕刻家、少女,攻读博士学位的P君,《罗迦诺的乡村》的邮递员和他的妹妹,《在赣江上》的船夫、领船者,《一棵老树》中放牛的老人,《人的高歌》的石匠、建灯塔的船夫,《山村的墓碣》的无名死者,都没有具体的姓名,这并非作者的疏忽,显然是有意为之。这些平常景、平凡人,看似不起眼,却孕育着令人崇敬的人格力量,蕴含着深邃的生存哲学。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叙写的鼠曲草,在欧洲难以采撷到的名贵的小草,在这里,却一年两季开遍了山坡。冯至喜欢这鼠曲草,赞赏其蓬勃的生命力、积极的生命形态。暮春、初秋一年两季,在这偏远的山坡,触目所及的都是这鼠曲草,蓬蓬勃勃,却又默默无闻。这些掺杂在乱草中的白色花朵,谦虚、纯洁、坚强,“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1]314。一个小生命,却庄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冯至钦佩这样的生命姿态,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还有高高耸立的植物界最高的加利树,这来自异乡移植不久的树,已然使命在身,努力地生长着。冯至感觉到,这加利树每一瞬间都在成长,把自身、周围乃至整座山都带着生长起来。这劲头,这态势,望久了,觉得如同面对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有股神奇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追随它。不管身处何处,加利树义无反顾、努力地向上生长,努力地实现自我,这种执着、坚韧的精神深深地鼓舞着冯至。
《人的高歌》中石匠凭着一己之力,不顾寒暑,不管风天或雨天,十多年如一日,在峭壁上凿出了一条石路。一位在海上遇风暴被救的船夫,决心在荒岛上建筑起指示航程的灯塔,到处请求布施,毅然决然用火点燃缠在手指上的油布的方法到处化缘筹建灯塔,最后又甘当守塔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石匠、船夫身上,有着一种担当的责任感、使命感,更有着一股坚不可摧的坚忍的精神力量,执着、忍耐。冯至感佩这种担当、坚忍的精神,从石匠、船夫身上,领悟到何为生长。
这时期的冯至走过创作初期的浪漫主义阶段,进入中年沉思的成熟阶段。对于生死的思考,成为冯至创作的主旋律。正如这时段写的小说《伍子胥》,伍子胥的形象由原先浪漫的形象,变为一个在艰险的现实中被磨练着的人。《伍子胥》与十六年前所想象的全然不同了,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了现代人,尤其是近代中国人的痛苦。当朋友问冯至,是否还要继续写吴市以后的伍子胥,冯至回答:“不想继续写下去了;如果写,我就想越过三十八年,写伍子胥的死。”[1]443冯至打开《吴越春秋》,向朋友诵读一段伍子胥与被离关于死亡的对话。读完,冯至重复着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冯至想越过三十八年,直接写伍子胥的死。这样的表白,实则表达了冯至这时期探讨的创作主题:正当的死生,如何生存,如何面对死亡。已创作的《伍子胥》一出场就是伍子胥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的决断,以及艰险的逃难经历,面临一系列生死的考验,贯穿的主题正是责任与担当,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这是冯至钦佩、倡导的人格力量。如何对待死亡,往往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对死亡的思考,亦是冯至《山水》的主旋律。
《一棵老树》叙写了一位林场放牛的老人,每天从早到晚只做一件事,放牧水牛。老人似乎感受不到时间的变化、气候的转变,一年四季,无论早晚,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衣裳。老人终年生活在这山林,且只限于四周的山坡,掺杂在鸡、犬、马、牛中间,仿佛“生”在这里了。老人、水牛与林场是如此的和谐,老人与林场的一切融为一体。可是,当牛死了,无牛可放时,老人竟随牛而去。《一棵老树》展现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且昭示着冯至的生死观。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必须自觉去承担去完成自己的死生。老人老了,虽不能像三四十岁的壮年,背起斧头,做披荆斩棘的工作,但依然担当着放牛的责任。当牛死了,无牛可放时,他无所依凭,于是随着承担的消失而消逝。老人已经承担了自己应当担当的责任。老人的死,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正当的死生。《人的高歌》中的石匠、船夫亦是这般,当完成了使命,便坦然的地走向死亡。《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中的少女亦从容地选择了死亡。她的微笑至死未改变,生与死在此成为和谐的统一。天使的微笑在死亡中得到了永生。死亡,在他们看来,如瓜熟蒂落,自然而然,悄然而去,似乎是回家。
《山村的墓碣》写了冯至在德国和瑞士交界的山村,看到的墓碣,上边刻着:“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1]325读到这样的诗句,冯至“非常感动”。这随意轻松的诗句,蕴含着睿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生与死仿佛毗邻而居。在人生旅程中,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农人们对待死亡,潇洒而轻松。“我生于波登湖畔,我死于肚子痛。”“我是一个乡村教员,鞭打了一辈子学童。”[1]326这些饶有风趣的墓碣,这种对死亡达观坦荡的态度正是冯至所欣赏的。生时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担当,坚韧地生长,死时,从容坦荡。生而不俗,死而不惧。“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1]108“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辉煌完成,从而主张人应以雍容乐观的态度对待死亡,以饱满的热情倾注于现在的努力,以领受生命这最完美的时刻。”[5]
这便是冯至倡导的生死之道。这一生死之道,无疑吸收融合了丰富的中外思想资源,有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念;道家的“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的思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观点,即人带着对死亡的先行理解珍惜生命,活出自己的价值;里尔克的死亡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向死而在”的存在论等。冯至倡扬的生死之道:正当的死生,洋溢着坦荡乐观积极自主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富于主体意识的价值论,亦是贯通天地精神的宇宙观。
三、沉思的诗
冯至的《山水》探寻“正当的死生”,充满人生智慧与哲学思考,行文行云流水,澄明清朗,沉着深婉,韵味悠长,宛如一首沉思的诗。每读一遍,似乎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李广田评价其散文是散文中的精品,明净、含蓄,于平凡中见出崇高,于朴素中见出华美[6]。
“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草从杂草中露出头来。”[1]314夕阳、村女、羊、山、树、鼠曲草,简约、流畅的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宁静优美的乡村牧羊图。“这时我正从城里来,我看见这幅图像,觉得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1]314自然 而 贴 切 的 联 想、比 喻,形 象 生 动 的表达,给人诗意的美感与意犹未尽的韵味。“山坡上,树林间,老人无言,水牛也没有声音,蹒蹒跚跚,是一幅忧郁的画图。因为他们同样有一个忘却的久远在过去,同样拖着一个迟钝在这灵巧的时代。”[1]308山坡、树林、老人、水牛,意境古朴、悠远,地老天荒般,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时间与历史。以具象表现抽象,以图画展现存在,语言凝练、诗意,韵味悠长。
这般清朗深婉的文调,与其创作理念息息相关。冯至认同并且于创作中自觉运用里尔克倡导的原人式的观察以及“经验”。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希望青年诗人:“你要像一个原人似的练习去说你所见、所体验、所爱、以及所遗失的事物。”[3]7这种原人视角类似雕塑家的视角,注重观看,注重客观观察,从而发现事物的本质特点。这显然受罗丹的影响。里尔克曾在罗丹那里学习,他在《罗丹论》中着重论述了罗丹如何辛勤地永不停息地工作,如何观看事物。艺术家在模制一件物品时,上下左右、方方面面都要看到,无所隐瞒,无所忽略[7]。现实生活中,世俗的观念,因袭的做法常常遮蔽了事物的真相、本质。艺术创作中这种全方位的观察,就是要求艺术家要摆脱因袭的习俗,认真观察事物,从而发现事物本质性的特点。里尔克还强调“经验”。通常人们认为诗主要来自情感,里尔克则认为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里尔克所强调的经验摒弃诗人激情的喷涌,倡扬的是知性之思,强调的是一种融入,从外部返回生命本身,是外在世界心灵化的过程,从而获得生命的内在韵律,获得一种带有灵性的生命体验和超越性的形而上思考。可见,里尔克所强调的“经验”是一种冷静的体验,是具有本体论层面的生命存在。诗人(作家)必须学会让自己的心灵沉潜下来,才能跨越自我与外物的界限,从生命存在的深处与身外的事物融为一体,从而把握事物的本体,体悟真实的存在。
冯至深谙并践行里尔克这一艺术理念。《山水》的写作可以说就是这艺术理念的产物。正如冯至在《山水》后记中所表述的,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不管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长的也许几年,短的则是几点钟,可一旦离开它们,它们便如一粒种子似的种在心间。冯至把体验形象地比喻为一粒种子,在身体内沉埋、发芽、开花、结果。这种将自我溶浸其中,感受、体味生命,感情与理性交融的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具有一种穿透的能力。真正的体验是无法忘却的,正如“尼采说:‘在涵养深的人那里,一切经历物是长久延续着的。’他所指的就是:一切经历物不是很快被忘却的,对它的吸收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且它的真正存在以及意义就恰恰在这个过程中”[8]。
《山水》清朗深婉,诗情与哲思水乳交融,了无痕迹。正如冯至的《两句诗》,在清寂的山林里,冯至夹着书,散步,读到贾岛的名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细细咀嚼,意味无穷,觉得这两句诗道尽了独行人在宁静的自然里无限的境界。一样清寂的环境,一样的独行人,冯至无疑已融入这般清净安宁的境界,体验到何为“明心见性”,体验到“自然和人最深的接融”,当自己把身体靠在树干上,感受到人与树已分不开,从自身血液的循环自然体验到树是如何从地下汲取养分,输送给枝干、叶子,甚至好像也传输到自己的血液中。冯至靠着树干,“数息树边身”,这种全身心的融入,体验精微、具体;这种融入,跨越时空,与天地精灵交流,与古今圣贤对话,流淌着丰盈的诗情与生命的智慧。
《山水》中,村庄、小溪、道路、牧羊女、老人、曲鼠草、加利树等这些平凡平常的微观意象,以及森林、草原、荒原等宏观意象,不仅有具体的感性形象,并且充满丰富的精神内涵。冯至笔下的意象,或具体鲜活,或构成图画,或形成背景,成了沟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宇宙的载体,承载着意味无穷的存在、绵绵不尽的哲思。冯至不对意象的外形进行工笔式的精雕细琢,而是抓住最能表现其精神风貌的特征,融入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常以比喻加以形象化的描述。如加利树,没有描述树的形状、叶子的大小、突显的是生长的姿态及其带来的感受,“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1]315,将内在感受具象化、形象化,使得我们似乎也看到、感受到加利树的风姿,义无反顾、努力向上生长、生长。如《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对这位无名少女,没有服饰、五官、形体的具体描写,笔墨的重心在于少女的微笑。这天使般超凡的微笑,如鹅毛一般的轻,所包含的似乎又比整个世界还重,人人似乎都可以从这微笑中懂得一点事物,冯至着力描摹的是自己体验到的微笑。这难以形容的无形的微笑,在冯至的笔下,竟如同雕塑般凝定,充满意味。这天使的微笑,超乎悲喜,轻盈、超然,似乎包容一切,蕴含着无穷的韵味,把读者带入了感受与沉思的精神漫游中。
这些意象的选择与表现,正是冯至以原人视角,注重经验式体察与把握世界的体现,从而以具象表现抽象,以图画展现存在,冯至又善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捕捉意象而又超越意象进入富于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的境界。《罗加诺的乡村》写的是瑞士东南特精省南端的一个背山临水的乡村,一切松缓随意,人们生活自在、轻松、惬意。人与境谐,这里的生物亲切可爱,仿佛久别重逢的老友。午间蝉声无边无际,夜晚窗外时有悉悉索索的声响,蝎子在墙缝里出没,成群的壁虎在壁上、草间爬来爬去。大自然的生物自由自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亦是生活自在、轻松、惬意。邮局的少女、老邮夫、送面包的少年等,不慌不忙,从容随意,而又信守承诺。在这儿住不上几天,冯至自己也不知不觉融入这里松缓的节奏与氛围,脱去皮鞋,换上布鞋,抛开领带,换上衬衫,也不用带时表了。这里的人们、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按照自己的习惯本真地生活着。这里,人、事、景如此和谐,浑然一体,这是一个清净、坦诚的世界。静默的青山,变幻的云,转个圈消失了的汽船,一切又归于宁静。水、船、山、云,静与动,瞬间与永恒,时间与空间,胸怀宇宙,思接千古。这一境界已然是东方的禅境,动中极静,静中极动,空灵、悠远。“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禅’的心灵状态”,从而“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9]。
结 语
冯至是个诗人、学者,语言富于诗与思的美感。“因为他们同样有一个忘却的久远在过去,同样拖着一个迟钝在这灵巧的时代。”[1]308“全身都是零乱。”[1]310“他们的血里还有那样的呼声吗,向着旷野,向着森林,向着远方的自由?”[1]329“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1]312“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1]314灵活巧妙地调用词性,陌生化的语言组合,充满诗意的情怀,充满思想的张力,饶有情趣,且寓意丰富。《山水》中还常常出现一组组相反相对的词语,如小与大、不变与变化、轻与重、喜与悲、迟钝与灵巧、生与死、平凡与伟大、小生命与大宇宙、瞬间与永恒等,两两相对,看似对立与冲突,实则对立统一,融通于生命的气象中,在对立统一中领悟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感悟正当死生的澄明与旷达。
朱自清曾在20世纪40年代将冯至的《十四行集》称为“中年的诗”。中年脱去了年青的豪情与放纵,也没有老年的沉闷与滞缓,中年意味着成熟,沉稳,克制自我,体验世界,思考人生。冯至的《山水》澄明清朗、沉着深婉,字里行间传达着一种雍容宁静、明澈朗悟的智慧,宛如一首沉思的诗,所达到的正是一种“中年”的境界,如林语堂《秋天的况味》中所说,“如文人已拍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10]季羡林先生从中西比较中高度评价冯至的散文,他认为冯至的散文具有中国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富于神韵,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飘逸、简明、生动,而且诗意盎然,读之如食橄榄,余味无穷,三日口香”[11]。季羡林先生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冯至《山水》讲述的是“灵魂里的山川”,观照“心中的道德律”,仰望“头上的星空”,在现代游记中风格独具。
[1]冯至.冯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73.
[3][奥地利]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M].冯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冯至.论歌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4-5.
[5]解志熙.生的执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55.
[6]李广田.谈散文[G]//俞元桂,等,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149.
[7]里尔克.罗丹论[M].梁宗岱,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56.
[8][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95.
[9]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89.
[10]林语堂.秋天的况味.20世纪中国散文[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247.
[11]季羡林.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先生[G]//冯姚平,编.冯至与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99-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