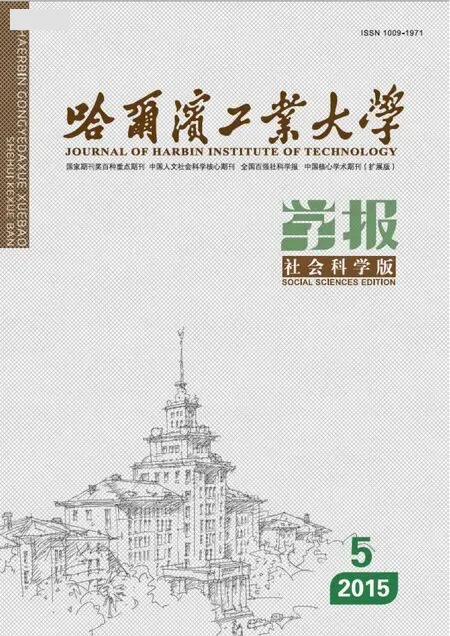鲁迅视野中的基督世界
2015-03-17吴霞伍珺
吴霞,伍珺
(九江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文学与文化研究·
鲁迅视野中的基督世界
吴霞,伍珺
(九江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摘要: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对宗教文化的关注和探讨,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罕见的。这种深度和广度,或许并非体现在他对某一宗教探究的深刻性与系统性方面,但却体现在他对整个宗教文化本质性内涵的突破性体验上。鲁迅对基督教更多地是关注其对人的道德净化和艺术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将宗教观念与“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鲁迅在文本中重新解读基督教:撒旦是反传统的异端力量,耶稣成为为民众谋福利反遭迫害的“精神界之战士”,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复仇。鲁迅以自己对人生的体认阐释宗教,其视野中的基督世界是“别一番世界”。
关键词:鲁迅;基督教;撒旦;耶稣
收稿日期:2015-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的基督徒文学研究”(14BZW145)
作者简介:吴霞(1975-),女,安徽枞阳人,讲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伍珺(1973-),女,江西九江人,讲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志码: A
文章编号:编号: 1009-1971(2015)05-0104-05
Abstract:Connecting the religious idea with the thoughts of enlightenment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and “fostering personality”,Luxun expressed the Christianity afresh in his text. Satan was considered as the heterodox strength against tradition and Jesus was described as a spiritual soldier striving for the people's welfare and revenged in a special way.Then taking his life attitude into religious understanding,Luxun's vision of the Christianity is unique
一、“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前提与基础
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近几年已经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鲁迅曾经对宗教的起源、宗教的本质以及其社会作用都做过深邃的论述,因此学者们不仅用心理学、传记学的方法考察鲁迅与宗教的深厚渊源,而且也通过现存的资料和文本来分析鲁迅对各种宗教的观照和取舍及所受中外宗教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一言以蔽之,就是两个极具辩论色彩的悖论性判断:“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1]30
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对宗教文化的关注和探讨,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罕见的。这种深度和广度,或许并非体现在他对某一宗教探究的深刻性与系统性方面,但却体现在作家对整个宗教文化本质性内涵的突破性体验上。鲁迅不是按照抽象而先验的宗教文化理论来阐释宗教,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体认去阐释宗教[2]232。这是鲁迅对宗教文化本质精义独特的理解,也是从宗教学意义上理解鲁迅精神特质的前提和基础。
以此前提和基础,鲁迅对基督教更多地是关注其对人的道德净化和艺术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他在《破恶声论》一文中指出:“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希伯来民族所具有的宗教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超越精神,鲁迅肯定了这种“向上”精神。在他看来,信仰对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宗教对人的思想裨益就在于他的坚定信仰上。而中国却充斥太多“精神窒塞,惟夫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的“浇季士夫”[1]28,他们是毫无节操与信仰的。真正有信仰的人应该“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摄也。”[1]25这样的要求有如圣经《诗篇》中的追问:“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正,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诽谤人,也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重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了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3]鲁迅的感叹,更多是寄托,“顾浊流茫洋,并健者亦以沦没,朊朊华土,凄如荒原,黄神啸吟,种性放失,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已”[1]26。以自己对人生的体认来阐释宗教,鲁迅是把自己的宗教观念与“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总体目标联系在一起了。如此,鲁迅视野中的基督世界是“别一番世界”。
将宗教观念与“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启蒙思想相联系,首先表现在《摩罗诗力说》中对摩罗诗人的呼唤上。“摩罗”,“欧人谓之撒旦”[4]66,专事抵挡上帝而与上帝为敌,在《圣经》中是魔鬼之名,是罪恶与黑暗的象征。鲁迅却赞扬他是人类精神的引导者,“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惠之及人世者,撒旦其首矣”[4]73。同时,鲁迅从“权力”的角度解读上帝与撒旦的关系:“神,一权力也;撒旦,亦一权力也,惟撒旦之力,即生于神,神力若亡,不为之代;上则以力抗天庭,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弛,莫甚于此。”[4]78这里的权力并不在独占权力的人和无权而顺从的人之间制造差异,撒旦也是拥有权力的。这就有点接近福柯的权力理论了。福柯以为权力不应该看作某个个人对他人,或者说某一群人或一个阶级对他人稳定的同质的支配现象。权力可以看成是在循环的过程中具有的一种链状结构。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不仅个人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态之中[5]。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同时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上帝是,撒旦是,“众生”也是(他们不是“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作赏玩,做慰安吗?”[6]366)。不过这里,撒旦的权力是从上帝那里产生的,他是个叛逆者,如果上帝的力量消失了,撒旦也不会取而代之,而且他之所以要压制“众生”,正是为了反抗的缘故,因为如果大家一起反抗,就不需要再压制他们了。这里只是“如果”啊,因为事实恰恰不是这样,撒旦(反抗暴力的叛逆者)和众生(被压制的暴君的臣民)之间有深深的距离。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具有撒旦精神的摩罗诗人,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从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4]99。可另一面却因“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4]66,甚至会存在“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4]100的悲惨命运。
欧洲有摩罗诗人这样反传统的“精神界之战士”,这是他们的福分,虽然众生会剿杀自己的战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的笔触直指“众生”。但偌大的中国,连这样的福分也没有,“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4]100鲁迅大声地疾呼着。为什么?鲁迅痛苦地思考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7]这三个问题伴随了鲁迅的一生,也贯穿了他自始至终的文本创作。
应该说,有了撒旦这个魔鬼所开启的“新声”,再看鲁迅日后文本中对基督教的解读,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因着“立人”的思想,撒旦成了鲁迅基督世界里反传统的异端力量,但只到此为止。鲁迅更多的笔墨给了圣经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耶稣。
二、《药》——耶稣受难情节的中国版本
耶稣是整部圣经的中心人物,他带着神的使命来传播爱的福音并拯救人类,但却被以“犹太人的王”的罪名钉杀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对信徒而言,耶稣是神人关系的唯一凭借和所有内容,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凭借他才能到天父那里。因而,耶酥是整部圣经的中心人物,他带着神的使命来传播爱的福音并拯救人类,但却被以“犹太人的王”的耶稣汇集了基督教义里爱、怜悯、宽恕和救赎等内涵,耶稣本人就是基督教的纲领。
鲁迅显然并不关注耶稣其人的历史身份或者死而复活真实与否。作为一个非教徒,他也不可能以基督教的价值眼光来认同耶稣的神性和救赎意义。本着启蒙的目的,他关注的是耶稣受难这一事件的悲剧性——有如孔子、释迦牟尼等“大人物”“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8]的悲愤,也有前所列举摩罗诗人“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的悲惨。“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看。”[9]89但是如何“看”呢?鲁迅有他的独到之处,“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9]89。因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6]366言外之意,耶稣的死,暴君的臣民应负更大的责任。
要知道,这沉痛的控诉就发生在《药》的创作前后。鲁迅虽说“中国不要提了罢”,但抱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0]419。于是,《药》里一个隐含的耶稣形象——“猛士”、“前驱”夏瑜诞生了。革命者夏瑜之死和《马太福音》里耶稣之死有大致相似的情节,都有被出卖——受折磨——被残杀——探坟——显灵等五个情节序列,可以说这是耶稣受难情节的中国版本。
耶稣被自己的门徒犹大所卖,得血银三十两;夏瑜被自己的伯父夏三爷所卖,得血银二十五两。
耶稣被捕后遭受狱卒的百般凌辱,被钉杀后,狱卒拈阉分了他的衣服;夏瑜入狱后被狱卒红眼睛阿义打了耳光,被杀后,衣服也被其独吞。
耶稣被钉十字架,夏瑜被处死丁字路口。
耶稣死后,信徒玛丽亚(女性)去探坟;夏瑜死后,夏四奶奶在清明节上坟。
耶稣第三日复活;夏瑜死后没有复活,但坟上的花圈给了夏四奶奶大声哀悼的理由,乌鸦骤发的厉声也打破了坟地“死一般静”。
此外,在很多场景与细节上,鲁迅也引用并借鉴了《圣经》,有研究者已做过具体详细的比较。但作为一个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并致力于创新的作家,并且是以自己对人生的体认去阐释宗教,鲁迅有他成功的吸收与消化。
倘若不是非常熟悉圣经并阅读《马太福音》,普通读者单凭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这一事件是无法了解鲁迅真正的创作意图。即使是辩出了文本中的两条情节线:华小栓病死的情节线和夏瑜为革命牺牲的情节线,读者仍然可能对问题一无所知。因为“夏瑜的革命是在民族时空中发生的事件,华小栓病死是在家庭时空中发生的事件。在这两个时空结构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它们既没有同一性也没有直接的对立性”[2]681。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药》的创作背景,回到鲁迅“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目标中去。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6]366
由此,鲁迅在构思这篇小说时,要“有他人的苦”,就要有“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者;要有“血”,就要有“渴血”者,缺一不可。因而,华小栓就不仅仅是一个“病人”,而同时是一个“被拯救者”。有“被拯救者”,就有“拯救者”,革命者夏瑜就是“拯救者”。“拯救者”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拯救民族,“血”就是他的生命。华小栓吃了夏瑜的“血”(“渴血”),也就是说“被拯救者”吃了“拯救者”的生命。没有了“拯救者”,“被拯救者”当然就得不到“拯救”,于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在不同时空结构中同归于尽。
毫无疑问,革命者夏瑜之死已经被赋予耶稣受难的意味,鲁迅也借此中国化的情节(有材料证明秋瑾是夏瑜的原型)解读了受难的悲剧性:施爱者反被受爱者所害,“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而这主题几乎成了鲁迅作品中最动人的情节模式,将自己对宗教的认识与“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总体目标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一斑。故而这种阐释和基督教义中耶稣受难的救赎意义及神性价值有很大区别。这里笔者要指出两重误读——两个断没有的可能,体现了鲁迅对国民缺乏诚与爱的“衷悲”和“疾视”[4]80。
首先,《马太福音》表现耶稣被杀的被动的同时,也表现了耶稣的主动认同,一是经书上写着人子必定要死,二是神已预言了他的复活,因此,耶稣面对审判的被动与忍耐是因为怀抱投向上帝的期盼和信心。耶稣在没有确定父的意志的时候也祈祷,也害怕死亡,然而他认识到父的意志后,他就趋向前去献身给死亡。如果说耶稣的命运也有悲剧的话,那就是神性的悲剧,隐含有绝对和希望(此绝对和希望都来源于人和上帝的关系)。如果上帝向人显灵,人也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人便超越了悲剧,耶稣就从悲剧走向了悲剧的超越。鲁迅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对人和事物的终极性、完美性都持怀疑的目光。因此,《药》中根本没有一个绝对者存在,夏瑜的死完全是被动的,他的悲剧也是现实的,断没有超越的可能。
其次是对“拯救”的理解。在基督教里,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义。恩就是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代受死亡,流血以赎信者的。信,就是信主耶稣。神有爱,主有恩,若没有人的信也不能得救。而且,拯救的实质在于,这个已经度过的生被拯救,而不是将人赎出这个生。拯救意味着:上帝解救已经度过的生,受过限制的尘世生命分有上帝的生命,终将结束的生命时间分有上帝的永恒,负有罪过的人类生存分有上帝的荣耀[11]。我们必须注意,基督教里的拯救是属于信徒的,是针对已经度过的生,而不是生命无限的延长,更不是灵魂不灭。在《药》中,华小栓吃了夏瑜的“血”,显然是为了延长生命,“血”是一剂偏方;夏瑜不惜流血是为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血”是他改造国民性的手段;刽子手康大叔卖血是为了赚钱,“血”是营生。他们各自为各自,此信非彼信。在基督教里,蒙恩的罪人只要信主耶稣,就有得救的希望。但是在《药》中,“血”的价值都没有达成一致,又如何言“信”呢?鲁迅愤然指出,只要人们不停止“渴血的欲望”,就断没有拯救(希望)的可能。
三、《野草》——由救人走向复仇的耶稣
诚然,鲁迅对耶稣受难感受最深的不是他的宽恕、怜悯,而是施爱者反被受爱者所害的悲剧意义。在《药》里,他已经宣泄了自己的悲愤,到了《野草》中的《复仇》一二、《颓败线的颤动》,他已将这种控诉渲染到极致,以至于施爱者们不仅仅只是忍受牺牲了,而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始复仇了。
1919年到1924年,短短几年内,鲁迅的生活及周围发生了很多变故。《新青年》团体涣散,兄弟失和,大病,尤其是和二弟周作人的失和给鲁迅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害。人人都说《野草》是鲁迅隐秘的内心世界一次最充分的展示,他自己也说他的人生哲学都体现在《野草》中了。的确,《野草》中有高度的紧张和不安,有深刻的孤独和悲哀,有强烈的愤怒和仇恨,还有难言的牺牲和背弃(施爱者反被受爱者所害)。1907年《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怒斥陷拜伦于不幸的奴隶,“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4]80。当鲁迅立誓“我以我血荐轩辕”,挺身为“精神界之战士”时,他面临的却是比拜伦更恶劣的环境。这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2];这是一群“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的奴隶[13]163,这是一群只等着牺牲者沥血之后“散胙”的奴隶。如果说1919年前后,鲁迅是“哀其不幸”,抱“希望是在于将来”“破破中国的寂寞”,或呐喊或彷徨的话,到1924年,鲁迅在“怒其不争”中已盼着“野草的死亡和朽腐,火速到来”了[14]173。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3]164。鲁迅没有掩饰他的心情,他在《〈野草〉 英文译本序》中就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14]173写这封信的时间距《复仇》写作时间已有十年,此时的鲁迅似乎摆脱了当年的心境,因而能理智地回忆、评价旧作,称其为“愤激之谈”。不难想象,他一度曾被《复仇》之中那种特殊的“愤激”心态深深包围与缠绕。这种愤激心态是《复仇》其一所表现的主题,更是《复仇》其二、《颓败线的颤动》所表现的主题,即不再一味地牺牲,而是以牺牲来实现对愚昧的奴隶的复仇。
《复仇》其二直接取材于圣经,文中多处引用圣经原文,但鲁迅剪除了耶稣身上神子的属性(是神于人就无关痛痒),改造了耶稣之死的救赎旨向,主要表现耶稣作为人子的现实困境和复仇心理。耶稣与他们(庸俗的群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他们打他的头,吐他唾沫,戏弄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情节几乎都是圣经的承袭,但在被迫害的悲剧气氛渲染上,《复仇》其二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要表现的是人子耶稣,是由救人转而复仇的耶稣。
“看那,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呵,这使他痛得舒服。”[14]174
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文字啊!是什么力量让耶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甚至超越自身的痛苦令人胆寒地“玩味”对方所加给自己的行为?是仇恨!他不用没药调和的酒来麻醉自己的神志,他要清醒地目视,他要他们不安。钉子把掌心穿透了,反使他觉得痛得柔和;钉碎了骨头反使他痛得舒服,“大痛楚透到心髓”,他却“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这怎不让“暴君的臣民”心惊胆颤、气急败坏呢?他们无法称心如意,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从耶稣口中听到“阿呀”的呻吟,永远也不能从被虐者身上得到“娱乐”和“慰安”,他们得到的反是耶稣不屑一顾的目光和似笑非笑的面孔。这就是鲁迅式的复仇:仅仅是牺牲,并不能构成复仇,只有在牺牲者的牺牲是刽子手的劫难之源的时候,牺牲才能成为复仇。
在基督教义中,耶稣是上帝之言的宣告者,他不仅以言语传言,而且以行为证明关怀人的上帝之国临近。他的所作所为流露出对他人的关切,尤其是那些失去生存权力的弱者。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但耶稣之死并没有以门徒逃走告终,而是演变成对耶稣的信仰,信仰本身对此做了解释:上帝在死去的耶稣身上显示了自己的荣耀,十字架成就了基督的舍身、慈爱和救人。这本只是一个宗教故事,宣告了耶稣基督的爱,一切建立在一个神圣的绝对价值基础上。但于鲁迅,这个坚决的无神论者、彻底的怀疑主义者,爱是不切实际,宽恕是怯懦和软弱,复仇反倒是“不足为奇的”[15]223, 耶稣已经走出了圣经世界,成长为向庸众宣战的“孤独的个人”、为民众谋福利反遭迫害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灵魂的最深处是救世思想,他“走异路,逃异地”[10]415,弃医从文,为的都是立国立人。带着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他寻找“精神界之战士”,以唤起“国人之新生”。他忧国忧民,他又深深绝望,因为在未庄、茶馆、阿Q、耶稣的周围是一批麻木冷酷的灵魂。他不是教徒,他也无意于终极的设定和追问,他所置身于其中的精神传统也从来没有为他提供过对爱心、祷告寄予无限信赖的信念。他执着的是“现在”,是“地上的人们”[16],是“于天上可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到无所有”[14]202。鲁迅深知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诚和爱,他也于冷眼中觉醒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他却依然选择了恶,“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15]223,让爱的使者——耶稣基督也走上复仇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刘勇.鲁迅精神特质的宗教学阐释[M]//冯光廉,等.多维视野中的鲁迅.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3]《圣经》新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7:824.
[4]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04.
[6]鲁迅.暴君的臣民[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许寿裳.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8]鲁迅.无花的蔷薇[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6.
[9]鲁迅.寸铁[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德]E·云格尔. 死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108.
[12]鲁迅.灯下漫笔[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3
[1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3.
[14]鲁迅. 野草题辞[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鲁迅.杂忆[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鲁迅.杂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
The Christianity in Luxun's Vision
WU Xia,WU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Jiujiang University,Jiujiang 332005,China)
Key words: Luxun; Christianity; Satan; Jesus
[责任编辑:郑红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