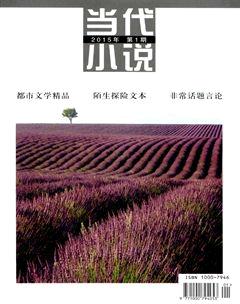美玉
2015-03-13张红欣
张红欣
时间耽误在一本相册上。
是一本浅棕色皮面压纹相册,一半软皮,一半压细致的蜥蜴纹,左下角一枝凌空伸出的藤蔓,缠缠绕绕,霸道地横亘了半个封面。最初,宋美玉并没有过多关注它,她下意识地翻开它,只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比如,一沓钞票。
没有钞票。相册扉页上,一对新人执手相看,身后是蔚蓝的大海,白色的浪花泡沫一样堆在脚底,新娘长长的婚纱随风飘舞,一直拖到海里,染成和海水一样的碧蓝色。扉页右上角,是一行扁而稀疏的小字:
我们的故事,从现在开始……
显然这不是一个年轻的故事,照片上的新娘都老了,一张脸敷脂抹粉,还算光洁,下颌处却松弛拖沓,因为笑得努力,看起来像有两个下巴。更不要说垮掉的胸部,臃肿的腰身,和裹在白色蕾丝长袖里的粗壮的小臂——岁月是把杀猪刀,这女人的青春显然被凌迟了。宋美玉的目光移到新郎身上。那是个长得不错的男人,浓眉,方脸,青茬胡须,腮帮骨略微外扩,牵出嘴角一丝笑意,有点儿刚柔并济的味道。相册扉页厚而沉重,裱着金边,摸上去妥帖踏实。宋美玉拿手指轻轻滑过新郎的脸庞。
她被他脸上的胡须扎得哆嗦了一下。
相册搁在床头。这是一个单身女人的房间,宋美玉刚刚翻过衣柜。满满一面墙的整体衣柜里,琳琅满目,全是女人衣服,羊绒、皮草、棉麻、雪纺、真丝,大衣、短衫、长裙、吊带、披肩,几十条风格不一的裤子。衣柜最下面有两个抽屉,一个专门放胸罩,一个放女人的内衣内裤、袜子、丝巾之类。只有最靠边的柜门里,挂着一件男式衬衣,浅灰色的雅戈尔。
宋美玉对着那件衬衣看了一会儿。
除了压在内衣下的两张发票,衣柜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当然,发票也不值钱,但发票上的内容值钱——那是一只五万块的翡翠玉镯,和一条白金项链,付款方是手写的三个字:廖美玉,应该是这间房子的主人。这个也叫美玉的女人,戴着一只价值不菲的玉镯,既有品位,又有意境,宋美玉想,真的是名至实归了。
宋美玉也有过一个玉镯,据说是缅玉,送她镯子的男人说,玉石通灵,心地善良的人佩玉,会让它越来越滋润,反之,会越来越污浊,玉饰送给有情人,代表着眼前这个人的可遇不可求,就像你。男人咬着宋美玉的耳垂,低声说:你就是我的美玉。宋美玉是被最后这句话感动的,那天,她破天荒让男人留了下来。他们做了三次,在出租屋窄小逼仄的格子间里,宋美玉被男人压在身下,像模像样地呻吟了一夜。
窗外霓虹闪烁,变幻不定的灯光打在墙角一株滴水观音上,让那肥大的植物有了梦幻感,宋美玉捧着相册,觉得自己也在做梦。这是一栋临街的小高层,宋美玉在东南角的1103室,开锁只用了两分钟。房间不大,两室一厅的格局,装修精致,石膏吊顶,硅藻泥墙漆,原色的竹木地板。按前几日踩点得出的结论,这个时间段,或者说这个日子,房主是不在的,宋美玉有足够的时间把房间翻上一遍,当然她也这么做了,动作很迅速,很老练,很——专业,对,是专业。这显然是个有钱人家,但宋美玉一无所获,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这不,她收获了这本相册。
空气里有香薰的味道,脚底下铺着厚厚的长绒地毯,踩上去无声无息。这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房间。宋美玉重新跌坐在床头,松软的席梦思床垫弹跳几下,照样是无声无息——温柔乡就是这样子吧?温厚,笃定,柔软,舒服,让人忍不住意乱情迷。宋美玉怀抱相册,目光涣散,有那么几分钟,她觉得自己像一台散了架的机器,直到听见外面的开门声。
是女人的声音:咦,门怎么没锁?
宋美玉激灵一下,一跃而起,四下望望,找不到藏身处,又本能地一个反身,重新扑到床上。感谢温柔乡,让她这一连串动作,没发出一点儿声音。
女人没有换鞋,高跟鞋笃笃地敲着竹木地板,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往书房那边去了。宋美玉保持着鸵鸟姿势,一动不动。锁撬得很专业,她甚至没有破坏锁芯。客厅和书房也不凌乱,因为觉得时间充足,一切翻过的物品都归了原位。现在,没法解释的只有她这个人。按照电影里的情节,她应该藏到柜子里,或者窗帘后面,或者直接跳窗出去,但那是电影,电影需要高潮,她不需要,她需要缓冲——被发现了怎么办?电影里可以拔刀相向,她不可以,她需要后路,哪怕这条路,看起来那么险狭。宋美玉匍匐在床上,脑子里轰轰隆隆,盘旋着一万架飞机:那个美玉,她怎么突然回来了呢?
脚步声朝卧室这边走过来,宋美玉压住咚咚狂跳的胸口,她已经做好了迎接一声尖叫的准备,心脏紧绷着,身体却软下来,呼吸也变得粗重。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昏睡的人。
没有尖叫。脚步声明显在门口那儿迟疑了几秒,随后来到床边,一双手轻轻推了推宋美玉:“哎,醒醒,你是谁,怎么在这儿?”
宋美玉翻了个身,发出一声梦呓。刚才,因为扑得太猛,她的胸口被相册厚而坚硬的棱角硌了一下,紧张的缘故,竟然不知道疼,现在翻过身来,才觉得离开胸口的相册像一把钝刀,正缓缓从身上抽离。宋美玉闭着眼,轻轻哼了一声。
一双温热的手搭在宋美玉额上,随后,女人抬起另外一只手,贴了贴自己的额头,确定宋美玉没事后,才加重了手上的力气,使劲推了她几下:
“醒醒。你醒醒。”
不能不醒了。宋美玉睁开眼,茫然地看看面前的女人,又把头往旁边一歪,要睡。女人赶紧扳过她来:哎,你不能睡,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女人手上用着劲儿,宋美玉被她连拉带拽地弄起来,摇晃两下,才坐直身子。装傻比装睡难多了,坐起来的宋美玉延续着刚才的状态,木桩一样戳在那儿,睡眼惺忪,似醒非醒。
接下来,宋美玉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喝酒了?”女人问,“看看,醉成这样——连门都走错了吧。”
是喝酒了。每次行动之前,宋美玉都会喝上一小杯衡水老白干,她的酒量不大,二两一杯的老白干足够壮胆。喝了酒的宋美玉思维敏捷,行动利落,一张脸却藏不住心事,两颊绯红,口唇青紫,连鼻孔都往外喷着酒气。她是过敏体质,二两老白干就能让她兴奋半天。现在,壮胆的酒成了最好的掩护,宋美玉将错就错,醉得越发如痴如呆:
“你……是谁?”
“这话该我问你。”女人说。她脸上并没有宋美玉想象中惊慌的样子,“——咦,我想起来了,你是三单元的吧?以前见你在楼下遛过狗,你们家的小泰迪很可爱。”
宋美玉一副混沌模样,脑子里,一万架飞机轰隆隆落了地。眼前这个美玉,她一点儿也不比自己轻松,她要打破僵局,要稳住对方,最难过的,她还要找一块合适的垫脚石,替对方解围——她做得太满,都有缓兵之计的节奏了。宋美玉怀抱相册,两眼虚飘飘地盯着女人:“三单元?三单元在哪儿……我不在三单元。”
“三单元是西边那个门。”女人说,“你不在三单元在几单元?”
“六单元。”宋美玉咧嘴一笑。
“瞎说,这栋楼就没有六单元。”
女人脱下外套,转身挂进衣柜,又弯腰抹下脚上的高跟鞋,踢在一边。她穿着一件珠花手绣羊绒衫,胸前有镂空的白纱,一朵朵绣工繁复的花儿堆在薄纱上,衬着点缀其间的水晶亮片,看起来又高贵又典雅。女人两手抱胸,立在那看了宋美玉一会儿,足足有一分钟时间,然后,她光着脚走到梳妆台边,从一个玻璃壶里倒了杯水:
“给,先喝点水。”
宋美玉没接纸杯,她不信任地盯着女人,往后躲了躲。女人把纸杯放在床头,伸手去拿宋美玉怀里的相册,被宋美玉激烈地拨开:“别动,这是我的!”
“你的?”
“我的……唔,我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吗?”宋美玉打开相册,指着扉页上的两个人,给女人看,“瞧,这是我老公,他很帅是不是?”
女人本能地往后一闪。她被宋美玉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仿佛对方递过来的不是相册,而是一把刀。宋美玉咯咯笑了,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表演天赋。
宋美玉重新坐好,继续往下翻着相册。次页,一对新人立在礁石上,背景仍然是蔚蓝的大海,女主角背靠新郎,粉面半扬,两臂做出一个展翅欲飞的动作,新郎则垂着眼,一只手绕过女人腋下,搭在腰上,另一只手轻轻揽着女人肩膀,他的嘴巴凑在女人鬓边,像是沉醉,又像耳语。相页右上角,是一首小诗:永远到底是什么呢/是夜色里闪着荧光的浪/还是那暖暖的海风/是我们脚下湿润的沙岸/还是你迎着风的/羞怯微笑的面容……
“对,我离过婚,孩子他爸嘛,跟人跑了。”宋美玉说,“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征婚——征婚你知道吧。他可真抢手。当然我也不赖,大伙儿都说我们俩是那个……郎才女貌,对,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呵呵。”
“你喝多了。”女人盯着宋美玉,“你住哪儿?我叫人送你回去。”
“住哪儿……我住哪儿呢?”
女人握着手机,离宋美玉一米多远的样子,静静看着她。宋美玉摸过床头的纸杯,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光,递给女人。女人转身又去倒了一杯。她仍然光着脚,但比刚才镇定多了。水杯递给宋美玉,她就势坐在了床尾。
“平常不怎么喝酒吧?”女人说,“跟我一样,沾酒就醉。”
宋美玉没接女人的话,她低下头,继续翻着相册。第三页,照例是海边,新郎一身白西服,倚在一架白色的钢琴旁边,深情地凝望着新娘,他们身后,无垠的大海蓝得像一块碧玉,海天一色处,照例是几句诗:可不可以不走/让时光就此停留/可不可以,化作野生的藤蔓/紧紧守住这无垠的沙岸/紧紧守住/这无星无月的夜啊/这温柔婉转的一切……
宋美玉抬起头,冲女人扬扬眉毛,轻轻笑了。
“北戴河,他的家乡。”宋美玉得意地指着相册,“他最喜欢海了,沙滩,礁石,帆船,海鸥,他说他是海的儿子……对,他就是用这首诗追到我的,在那个网站上,人人都那么现实,张嘴闭嘴都是工作、孩子、车子、房子,他不是,他给我发了一首诗……”
“那是海南,三亚。”女人说,“不是北戴河。”
宋美玉翻开第四页,进入眼帘的,是一片蓝天白云,海边,一棵高大的椰子树下,一对新人执手相依,目光望向遥远的天边。宋美玉拿食指挖着树干,一点一点,像要把它抠下来:
“你是说椰子树吗——那是假的……嗯,道具,道具懂吗?”
宋美玉抬头瞟了一眼女人,后者正两手抱膝,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的左腕上,一只温润的玉镯在灯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晕。
“我们去不起海南,是的,太贵了。”宋美玉停下手里的动作,抱歉地冲女人一笑,仿佛没去海南是她的错,“但是,如果有爱,哪里的海不是海呢,你说对不对?”
床尾的女人动了动嘴唇,什么都没说。
“你是不是想说,爱情怎么能掺假?”宋美玉喃喃地说,“刚开始,我也这么想——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不掺假的呢?”
宋美玉怕冷似的往后缩了缩,她的身下是一床大红提花蚕丝凉被,手边是同样花色的一对抱枕,抱枕旁边,是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水貂绒空调毯——这间不大的卧室,处处透着稳稳当当的奢华。宋美玉想起自己租住的格子间,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号称“棚户区”的一片城中村里,房东拿石膏板隔出一个一个鸟笼一样的房间,专门租给进城务工的农民。石膏板做的墙壁空洞单薄,每天晚上,宋美玉搂着女儿妞妞,拿被子紧紧蒙住耳朵,才能抵挡隔壁传来的延绵不绝的鼾声。她在那里已经住了五年。
“他看起来像个有钱人,对不对?”宋美玉说,“其实不是,他没钱——这个年代,谁还靠写诗赚钱呢,糊口都不够……哦,忘了告诉你,他是个诗人,自费做着个诗歌网站,对外的头衔么,是网站CEO……很吓人吧?呵呵,我经常拿这个头衔取笑他,因为这个CEO,手底下没有一个员工,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连电费都交不起了……”
床尾的美玉愣了一下,宋美玉看见,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住了。
“第一次见面,我给他交了五百块钱的电费。”宋美玉往后靠了靠身子,仿佛陷入了长长的回忆,“……那时候正好是春天,春天是发情的季节你知道吗?交完电费回来,我们去了一个小公园,河边的公园,梨花开得正好,我们坐在树下的长椅上,梨花落了满肩,我就是那么被他打动的。”
宋美玉伸出一根指头,摸了摸相册上的男人,蓝天碧水中,那男人笑得又优雅又从容。
“那时候我想,人活在这个世上,总得有一些真东西吧……我还年轻,他也不老,我们在一起,可以像年轻人那样,从头开始——你相信吗,那几分钟,我真是这么想的。”宋美玉垂下头。酒精的作用正在慢慢消退,她的脸已经没那么热了,她因此调整了语速。
床尾的美玉点点头,示意她继续。
“可是,就几分钟而已。”宋美玉抬头,脸上带着一抹惭愧,“这么说,你会笑我吗?”
“为什么?”
“……因为,后来我就开始犹豫。对,他的确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男人。”宋美玉眯起眼,目光虚虚地落到女人身上,“他只适合谈情。你知道吗,和诗人谈情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他会带你游山玩水,吹风淋雨,逛庙会,淘地摊,各种玩,他还会拿着一架破相机,连续半个月跟拍一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总之,他能用最小的成本,带给你最大的浪漫。经常,我们手拉手淘遍一条街,只为找一张新上映的影碟,然后,两个人捧着一袋爆米花,或者一只烤红薯,缩在被窝里,舒舒服服地看完。”
“一边看,一边听他骂导演,批编剧,把演员从头到脚议论个遍,是吗?”
床尾的美玉突然插了句嘴,她的眼睛在幽暗光线里一闪一闪地发亮,像猫。宋美玉停下来,等着她把话说完,她却又像猫一样警觉地一凛,戛然而止了。
嗯,没错。男人总喜欢在女人面前高谈阔论。短暂的停顿后,宋美玉意味深长地笑了:“抛开世俗的一面,他其实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多情,落拓,又散漫,不被现实压迫的时候,他身上,还有中年人少见的天真……嗯,我这是,在哪儿呢?”
酒精的作用已经消失殆尽。装不下去了。宋美玉揉着太阳穴,从床上坐直身体,又抹了一把脸。出门前为什么没多喝点儿呢,她想,比如两杯,两杯的话,就可以保证她的脸再红上半个小时。现在,红热褪尽的脸像一张风干的白纸,又薄又脆,手指碰上去,居然有窸窸窣窣的响声,仿佛一个不小心,这张脸就有被弄扯的危险。
宋美玉缓缓吐出一口长气。
“你在我家。你喝多了。”女人再次晃了晃手机,“我打电话给你家人?”
“不要!”
这一声简直像从胸腔里直接喷出来的,有歇斯底里的味道。宋美玉差点去捂自己的嘴,但她很快调整了语气:“麻烦你,再给我一杯水好吗?”
女人坐在床尾,慢悠悠地看宋美玉喝水。她这次喝得很节制,一小口,又一小口。空气仿佛在两个人之间凝滞了,世界上只剩下喝水这件事,直到客厅里传来“咔哒”一声,随即,是一段高山流水的音乐,一只鸟儿“布谷、布谷”地叫了起来,一声主叫,伴一声回音。
宋美玉默默在心里数了十下。
“十点了。”女人看了看手机,“你喝这么多,家人不担心吗?”
“家人?我没有家人。”宋美玉摇摇头,她顺利地让自己转入了半醉半醒的状态,“曾经,我把他当成了家人,后来才发现,他不是……对……他是路人。”
街上的霓虹渐次灭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盏,像深海里鬼魅的眼。宋美玉瞅了瞅窗外,黑夜像一张严严实实的网,吞噬了一切。十点了,妞妞一定还没睡,那个敏感的孩子,一定蜷缩在床角,安静地等妈妈回来。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她都该走了,眼前这个美玉,已经心知肚明地给她铺好台阶——但,为什么她就是不想走呢?
“我是个天生没有安全感的人。”宋美玉把白色的纸杯举到眼前,慢慢转着,“很多时候,我都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儿,赤条条来去,可是,我又不能像孤儿那样,无牵无挂——你累了是吗,你不愿意听一个酒鬼的唠叨,是吗?”
“没有。你说。”
床尾的美玉摇摇头,她的拇指一直压在手机屏幕上。
“比如,小时候,我总担心我们家的房子会垮掉。”宋美玉说,“那是一个有着四十年历史的老宅子,山墙开裂,地基凹陷,墙皮长满青苔,我从三岁起就揣着这种恐惧,直到五岁,才有机会表达出来,那天,我妈说她眼皮跳,右眼皮,她说,这是要有什么灾星呢,我忍了又忍,终于说,不会是我们家房子要塌了吧?”
床尾的美玉笑了。
“那时候正是冬天,北风吹得像狼嚎。我妈转过头,诧异地看我一眼,抬手就扇了我一个嘴巴——她可真不是一个好妈妈。”
宋美玉停顿了一会儿。
她有多久没给她妈打电话了?十天,或者更久。那个名义上的母亲,只有月末或者月初才会叨扰她一下,浮皮潦草地问过妞妞的病情,便开始她的话题——张家阿姨在吃花粉,李家婆婆推荐了大力丸,王家奶奶新近得了一盒黑蚂蚁胶囊,治好了三十年的老寒腿——她是那么热衷养生,最初只是热爱,后来变成了病态的依赖,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居然是妞妞一天重过一天的病情,是的,连那么小的孩子都可能随时死掉,她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老命呢?最后,她会把所有话题浓缩成一个主题,那就是:她需要钱。
是的,她需要很多很多钱。这么多年,她像趴在宋美玉身上的一只水蛭。窗外最后一盏霓虹也灭掉了,宋美玉屈起双膝,她有点儿冷。
“上小学后,学校里没有水井,同学们都拿空酒瓶从家里带水。”宋美玉说,“女孩子们往水里放上糖精,再对上几滴醋,泡上樱桃,或者一牙苹果,或者一瓣橘子,水就变得酸酸甜甜,又好看又好喝。下课后,她们把瓶盖拧松,瓶子斜到嘴边,吸吸溜溜地喝水——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动作,让我羡慕了好几年。”
床尾的美玉微微挑起半个眉毛,表示不解。
“因为,我们家没有酒瓶,最普通的都没有。”宋美玉微笑着,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一直拿输液瓶带水,瓶子是我爸跟队上的赤脚医生讨来的,矮矮胖胖,顶头一个橡皮塞,拔出来嘭的一声,能吓人一跳。小学五年,我一直把那个输液瓶藏在课桌里,每次渴得不行了,才把头钻到桌斗里,偷偷喝上一口……”
还有药盒做的文具盒,秫秸做的铅笔,马粪纸订的练习本,破洞的尼龙袜,断带的凉鞋,不合身的衣服,月经期永远不够用的卫生纸,因为没有一件乳罩而不得不含胸驼背的整个青春期……宋美玉轻轻咬一下唇,把涌到舌尖的话又咽了回去——眼前这个女人,雍容华贵,腕上一只手镯就能顶她两年工资,她理解得了吗?
“初中毕业后,我考了个师范学校。”宋美玉说,“对,我成绩很好——自卑嘛,就总想着一鸣惊人。其实也挺惊人,那个破破烂烂的乡中,从没出过那么好的学生。我完全可以挑个最好的学校,但是最后,我还是读了个师范,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为钱。那时候的师范生,享受国家补助,每月二十三块钱。就是这笔钱,直接切断了我妈的目光,然后,她利用她的家长身份,简单决定了我的人生。”
床尾的美玉安静地听着。
“我很早就结婚了。因为冷。”宋美玉看着女人,加快了语速,“结婚最直接的目的,是想找个人,抱团取暖。可是你看,没有温暖,哪儿都没有,爱情很快被柴米油盐淹死了。婚后不久,他跟我妈的矛盾就直线升级——也难怪,一条不屈不挠的水蛭,遇见了一块铁板,怎么能和平共处呢,我们很快离了婚,然后,那个人就不见了……”
布谷鸟又出来叫了一声,十点半了,宋美玉望望窗外,漆黑的夜色像一团凝固的墨,正一点一点渗进屋里。她得走了。妞妞在干吗?她肯定猜不出妈妈深夜不归的原因。去年,她在街上捡了个钱包,还是妈妈带着她,亲自送到了派出所,钱包里,整整齐齐的五千块钱,正好是她一个月的透析费用,但是妈妈跟她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要是知道妈妈悄悄走上了另一条道,那个七岁的孩子,会怎么想?
一阵突然的心痛蓦地席卷过来,宋美玉闭了一下眼。
“你知道离婚女人的市场有多萧条吗?”宋美玉自嘲地笑了一下,“离婚后,我相亲过的,有小贩、保安、屠户、厨子、传销公司的讲师、送水公司的苦力、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一个刚死了老婆的出租车司机,嫌我带着孩子,而一个大我二十岁的退休教授,嫌我胸脯不够丰满……直到遇见他,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故意自欺欺人地忽略了很多东西,比如他的工作、收入、地位,再比如,他的多情、滥情和薄情……喂,你在听吗?”
“嗯,在。”
床尾的美玉坐成了一尊雕像,她原本绾着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散开了,长长的发卷倾泻下来,覆住眉梢和眼角,这使她看起来像躲在头发后面。
相册已经翻到了最后,两张经典的天涯海角的图片,取角的原因,新娘洁白的婚纱覆盖了半个沙滩,新郎依旧西装笔挺,目光专注地看着宋美玉,嘴角带一抹轻笑。
当然还有诗,在相页的某一角,宋美玉拿眼扫了一下,像扫过一粒沙。
“或许,用薄情来形容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并不合适。”宋美玉摊开两手,久坐的姿势让她感觉有点儿累,“你说,人到中年,还要不要相信爱情呢,很久以来,我一直耻于跟人讨论这个问题,我像一个提前步入老龄的妇人,偶有心动,也只是一刹那而已。当然,他也是。所以,确定关系以后,我们仍然各自心照不宣地结识新人,因为彼此都清楚,婚姻,光有爱情是不够的——太不够了。”
床尾的美玉专注地研究着床头的美玉。宋美玉的视线无处可落,只好再次望向窗外。窗外的城市已经睡着了,偶有车辆驶过,刷的一声,像深海里的潮。
“他住在租来的地下室里,每天三分之二时间都泡在网上,昼伏夜出,三餐不继。”宋美玉说,“但是,他一点儿都不掩藏这种落魄,相反,有时候,他还会夸大它。你知道,女人是擅长幻想的动物,喜欢逆向思维,她们会由此推算他辉煌的前半生,会想,只有看尽繁华的人,才能在落魄时保持这种坦然,尤其是,这种落魄还挂钩着诗歌,挂钩着艺术,其实她们不知道,落魄才是他行走江湖的武器……”
床尾的女人沉默着,像得了失语症。
宋美玉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没错,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宋美玉说,“而且,我经常被这种逆向思维弄得心情激荡,于是心疼,我给他洗衣,做饭,给他晾晒地下室发霉的被褥,给他购置全套的炊具,之前,他都是用蜂窝煤炉做饭的,铝锅,铁勺,塑料案板,从饭店顺回来的快餐饭盒。我跟他说,这样不健康。我还省下三个月的早点,给他买了一件雅戈尔衬衫,让他穿着它,去参加诗人们的各种聚会,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女诗人们的崇拜——当然,还有暧昧。他可真喜欢那件衬衣,连和别的女人幽会,上床,都舍不得换一件……”
宋美玉偏过头,墙边,栗色的整体衣柜像一个巨大的魔方,在灯下散发着乌油油的光泽。
“当然,我也没闲着。”宋美玉把一只肘架在另一只手臂上,她是真的累了,“我仍然不断地跟各种男人相亲,不放过每个可能改变现状的机会。很奇怪,做这些的时候,我从来没感觉对不起他。他应该有所察觉,但也不问。我们不约而同地随波逐流,像不约而同地遵循某种潜规则一样,心甘情愿。所以,我从来不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怨妇,离婚的男人是块宝,离婚的女人,是根草,这个世界上,男女从来就没平等过,我只是没他的行情好而已……”
床尾的美玉终于动了一下,她换了个姿势,把长长的头发拢到脑后,拿腕上的皮筋捆好。然后,宋美玉看见,苏醒过来的美玉按亮了手机,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划了几下,像看时间,因为同时,她说了一句此地无银的话:
快十一点了。
宋美玉无声地笑了。她的声音忽然变得非常热切,有了某种兴奋:
“其实我知道,跟我谈婚论嫁的同时,他还在跟另外一个女人交往,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女人,前夫被小三撬了去,留下一笔不菲的财产,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摇摆在我们之间,确切地说,是摇摆在年轻和富有之间,举棋不定。他陆续换了手机、电脑,添了心仪很久的索尼单反,最近好像又有了个IPAD,而在此之前,为了给读大学的闺女凑学费,他连仅有的一部半智能手机都卖掉了。我正琢磨着给他买个新手机时,他有了一部苹果……所以你看,我的前半生输给了二十三块钱,后半生,输给了苹果、索尼、IPAD。”
“这也是潜规则。”床尾的美玉终于开了口,她没有宋美玉想象中的失落,“人走高,水走低,这是一个充满潜规则的社会。你不懂吗?”
是,我们就是太懂了。宋美玉埋下头,重新一页一页翻着相册。这次她翻得很快。
“因为太懂,才会被各种规则绑架,不敢反抗。”宋美玉说,“有一段时间,他频繁找我,我们见缝插针,抓紧一切时间上床,做爱,像要把后半辈子的激情提前用完。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每次都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还觉得不够,他就把我箍在怀里,一寸一寸亲下去,从发梢到脚跟——他的胡子好硬。”
宋美玉拿手指摸着相册上的男人,麻酥酥的感觉顺着指尖升上来,带着某种蛊惑。
“经常,我被他刮得发青的下巴弄得满身通红,我知道他舍不得我,就像舍不得他自己的青春。我就躲在他怀里,不出声。我特别怕自己一不小心,做了怨妇,那是最不美的结果——你说,我们的人生,为什么都这么狼狈呢?”
布谷鸟出来,叫了十一下。床尾的美玉往门口瞅了瞅。
“你走吧。”她把手机扔到床上,像扔了个包袱,“我老公要来了,刚才,我给他发了个短信。”她指指宋美玉手中的相册,“——我猜,你不想见到他,对吗?”
“我也有过一只这样的手镯,他送的。”宋美玉没理会女人的话,她盯着女人抬起的手腕,缓缓地说,“我猜,他是用那个女人的钱买的。他说,玉石通灵,心地善良的人佩玉,会让它越来越滋润,反之,会越来越污浊。玉饰送给有情人,代表着眼前这个人的可遇不可求……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叫美玉,他说,我是他生命里惟一的美玉……”
床尾的美玉摆摆手:你走吧。她看起来像经历了一场长途跋涉,整个人都有些委顿:“你走吧……不要说了,走吧你。”
“可是,那只手镯戴在我身上,才两个月,就变得污浊不堪。”宋美玉把相册放回床头,不紧不慢地下床,她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女人的脸,“——你知道吗,我怕极了,我把手镯偷偷摘下来,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我不敢让他知道,我不是美玉,我只是一块瓦砾。”
宋美玉冲女人笑了笑,然后起身,整理好靠歪的被褥,又把枕头拍拍松。
她打算走了。
女人也从床边站起来,她看起来更老了,眼角的鱼尾纹都塌了下去,里边有厚厚的脂粉。“我们都是瓦砾。”她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时代,不在了——你快走吧!”
宋美玉愣住了,她惊讶地望着那个美玉,喉头一紧,忽然升起一种想抱抱她的冲动。她想给她讲讲妞妞,那个患了尿毒症的孩子;讲讲她的母亲,一生飞扬跋扈,因为怕死,晚年忽然变得卑微恭顺;讲讲她人间蒸发的前夫,至今音信全无;她还想讲讲那只手镯,其实是个地摊货,她走投无路时拿去典当,被店伙计嘲讽地扔过来二十块钱……可是没时间了,那个美玉看起来疲惫不堪,她嘶哑着嗓音,几乎要过来推她:
“你走吧,快走啊你!”
宋美玉踉跄着走出那个房间,一边走一边回头看。身后,那个美玉虚弱地靠在门框上,起先还冲她摆摆手,后来便一动不动,像根年深日久的木桩。宋美玉拐过走廊,电梯正好打开,一个男人跨出来,几乎和宋美玉撞个满怀。等男人惊讶地转过身,宋美玉已经像一个影子闪进了电梯,随后,她伸出一只手,挡住即将合拢的两扇门,冲男人粲然一笑:
她说:“你今天,没刮胡子吗?”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