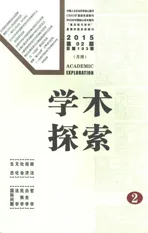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思辨
2015-02-26张晓君
张晓君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思辨
张晓君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精神内涵之一,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有必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公民的内涵,正视和处理好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与坚持党的领导主导性,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共生性,与公民主体意识觉醒和公民参与机制的关系。
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公民”是现代主权国家的主体,以法治方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是现代主权国家的责任。“在现代国家,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P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将全面保障公民权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由此可见,《决定》强调“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明确以构建五大体系为之铺路织网。诚如沈宗灵先生所言,“法律或法律秩序的任务或作用,并不是创造利益,而只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2](P291)以法治方式系统保障公民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的根本主旨之一。①事实上,西方很多著名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参见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M].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4;蒂博、萨维尼.论统一民法对于德意志的必要性:蒂堡与萨维尼论战文选[M].朱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85。这次举世瞩目的会议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程的新纪元。
在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应该在理论上回应诸如“何谓法治化”“谁来法治化”“如何法治化”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厘清“公民”“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保障主体”“法治化”②从法理上来看,“法治化”仍然需要在逻辑上细化,必须要达到一些最低的制度性要求,否则就不能确认制度手段与价值目标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关系,也就是说,“必要性原则”是判断“法治化”的最低制度化标准。不仅强调“法治”价值制度化的“多”与“少”的问题,更重要的和首要的是涉及“法治”价值的“有”与“无”的问题,是“法治”价值是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参见莫纪宏.法治与小康社会[J].中国法学,2013,(1):33.事实上,当前的法治评估标准正呈现出多元性、嵌入性、区域化、广义化等特征。参阅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2,(4):140-160。等内涵。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理清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中“主体范畴”“主导地位”“主体意识”和“包容思维”等处于“元叙事地位”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其间又存在何种关系?为此,除推进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法治体系建设外,在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过程中,尤其需要认真处理好以下四组关系。
一、“公民”概念的内涵厘定是法治建设的起点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提速,公民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但与此同时,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如校车事件、暴力拆迁,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浙江“叔侄强奸冤案”等冤假错案和“躲猫猫”“坠楼死”、太原讨薪女工命案等事件的发生,严重侵害了公民合法权益,损害了国家执法和司法公信力,破坏了公平正义,激化了社会矛盾。屡有发生的冤假错案、侵害公民权利行为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和错综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正确辨识公民及其正当权益的内涵。例如,思想观念中的遗留“有罪推定”和处理敌人(罪犯)“罪有应得”的态度,此种意识和思维或多或少地导致了少部分执法和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行为。殊不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公权力面前,每个公民自身权利都可能是被非法侵害的对象。若不坚守和推进法治建设,公民权利必将得不到进一步保障。由此可见,现阶段,公民意识尚未在全社会普遍形成和确立,权利意识尤其是违法公民权利保护意识尚不强烈。这是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社会环境障碍,因而应该在全社会公众观念中厘清其与违法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非两个不同的权利类型。
厘清“公民”内涵,可以从政治、文化、法律等不同语境和场域出发,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人和法律对公民一词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理解,其内涵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如世界公民。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谓:“公民”之本质犹如“城邦”①在古希腊,与不设防的乡村相对应,城邦属于城市范畴,是指设防的居民点。直至约公元前八世纪,城邦才被赋予政治意义,即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古希腊文中,公民是指有资格参与庆典、进入神坛和享用公餐的人,后来指享有从事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等权利的人。故而,从词源看,公民是指属于城邦、国家的人。,常常引发争辩,至今仍未形成公认定义。但无论古今中西,公民一词内涵虽然历经发展、内涵各有侧重,但均未剔除“犯罪之人”或者“有犯罪嫌疑的人”。从法律角度识别现代“公民”概念的话,一般是指取得一国国籍并依据该国宪法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进言之,公民不是法律虚拟的任何人,而是实实在在的所有生命体,其从事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也必须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对公民(包括所谓“罪犯”)权利保障的法治化更应该做到全面系统。②参见韩大元.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J].中国法学,2009,(6):17-19;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58。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即任何公民享有宪法法律规定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其规定的义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即使是违法公民,其也应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一般而言,公民可分为守法公民和违法公民。前者是指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捍卫法律尊严的公民;后者是指违反宪法法律的公民。公民不同于人民,前者是与国家国籍相关联,与非该国公民相对应,后者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与“敌人”相对应。公民是具有从事管理国家、社会等能力并且享有从事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权利的人。其包含的对象比人民更广泛,亦即公民中既包括人民也包括“敌人(罪犯)”。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国体,人民享有全部公民权利并履行公民义务;敌人(罪犯)则不能享有从事国家和社会管理等公民权利。从公民本质属性来看,公民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体现为公民是基于自然生物规律存在的生命体;其社会属性体现出公民以一国社会成员的身份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参与社会活动。公民的本质属性体现了保护其权利的必然性和绝对性。
因此,“公民”概念内涵反映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具而言之,无论是守法公民或是违法公民,无论是人民或是敌人(罪犯),只要是中国公民,其正当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障,包括敌人(罪犯)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当然,公民权利③公民权益主要是指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宪法规定的权益,包括平等权、自由权、社会经济权、文化教育权、监督权、宗教信仰自由、获得国家赔偿权和特定主体权利等等。也不同于人权,人权内涵更加广泛,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权益,而不论是否具有中国国籍或者是否属于人民,尤其是诸如刑讯逼供、违法强制拆迁等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从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对权利的保障等制度层面、从对相关立法者和执法者观念和意识层面加以解决。
只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权利才能获得尊重和保障,依法享有自由权利,才能真心拥护和捍卫宪法法律,法治中国才能形成,而不至成为理想主义者的词汇和执政者的美好承诺。[3](P2~4)总而言之,公民权利必须在法治环境下才能得到有效保障,而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起点就是一视同仁地尊重与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
二、法治建设中坚持党领导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的核心价值,也是“法治中国”的本质要求①诚如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所言:自由的人们讨论他们的政府,并非基于政府的“恩准”,而是基于他们的“权利”。参见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侯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8。,必然要落实在具体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而不应是抽象化的学术范畴。法治不仅追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外在的价值目标,而且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目标,既包括静态的法律规范和抽象的法律理论,也包括动态的社会实践和系统运作的社会体系。
诚如富勒所言,法治就是致力于规则治理的事业。然而,现代法治的建构从来都是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治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法治,是一个具体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并非任意无原则、无边界的法治愿景。正基于此,法治进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必要内核。诚如中国革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才能取得胜利一样,中国法治建设也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成功。那种抛开一切只谈法治的观点和做法,如果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或是法治理想主义者,就是刻意散播西方法治模式、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阴谋者。事实上,世界上任何法治形式包括欧美法治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开政治、政党而自发自在地形成。
其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内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法治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法治建设的总路线。②参见张文显.中国法治建设将呈现新局面[EB/OL].[2015-01-13].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9/c_1113021365.htm。在“法治建设”这一宏大的叙事体系中,如何才能使法治具有中国特色,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紧密结合,而不照搬西方模式和被西方化,最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法治体系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当然,对于少数党员干部的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权力腐败行为[4](P86),一方面既要建立健全反腐败的规则体系并运用法治的手段加以规制惩处,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对待这些腐败行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个别问题,不能任意夸大甚至以偏概全。
最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保证。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精神来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推进依法执政。当代最为著名的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非常重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且强调守法,尤其是掌权者的守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5]公民权利保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而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和根本保证,是由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历史决定的,是由中国国体和政体决定的,更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依法治国首先必然是依宪治国。毋庸置疑,这也是世界上任何拥有宪法的国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更进一步,“权利理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或暗示应该或者必须给予个人以高于社会的优先权”,也“并不要求给予个人绝对的自由,或者要求允许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需要而牺牲他们所属的社会”。[5](P16)
因此,在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等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建构的各领域。
三、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与法治中国的共生性
法治的发展与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与建设重心。[6](P145)回顾“依法治国”理念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工程和长期的实践过程,“依法治国”理念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到1997年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再到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一次写进宪法等,直到党的十八大和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大体系,更重要的是首次明确提出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建设,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纳入法治中国建设重中之重。如此高度重视法治并专门研究法治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全会史上绝无仅有,反映出党把法治作为主要任务,强调法律是政治生活的准绳,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逾越,以恢复社会公众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制度的尊重和拥护。诚如施特劳斯所言,“国家的职能并非创造或促进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而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7](P185)我国政府也致力于履行如上职责。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在沐浴法治改革春风、收获法治改革新成果的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系统化过程。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长期性是由构建法治体系与提升公民意识的长期性所决定的。现代法治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既包含形式理性化的法律规范,也包括实质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一方面,需要不断地从技术层面、非人格层面建立完善规则程序体系,不断地从形式理性化层面将人工具化,即是将社会编制成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倡导提升实质理性化的理论思维,以消除形式理性规则程序运作中可能发生的有罪者从法网中漏过、无罪者却遭惩处的现象。同时,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作用下,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也需要长期的普法宣传与反复实践。如上,公民权利保障法制化的进程本身就是十分漫长的,需要数代人的共同努力,纵然有几百年法治历史的欧美国家也经历了长期的法治建设过程。
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建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其必将遇到诸多阻力和困难,甚至可能出现侵害公民权益的情况。其原因在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具有物质的同一性和量上的对应关系”,两者在“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统一。[8](P15~18)例如,立法工作中可能存在部门利益、争权诿责、权责脱节等现象,执法和司法中可能存在不公开透明、不严格规范、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现象,部分社会成员中可能存在不信法、不尊法、不守法和不用法等现象。因此,正确认识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可能存在的难题具有深远意义。法治和国家治理要实现的秩序是“包容性秩序”。[1](P6)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充分意识到,“如果想要被公平对待,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9](P52)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学家们,都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包容的目光,去审视和评判在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既要鼓励立法执法司法者不断推进法治改革,又要容许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和不足,允许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可能会因改革发展而付出一定的成本与代价。
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与公民参与机制的构建
要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应当建立和完善“五大体系”,推进两大“三个一体化建设”,系统编织法治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方式在于肯定公民的主体地位并积极发挥其主体能动性。公民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必须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允许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不断增强公民自觉学法、尊法、守法和用法的意识,并充分认识到法律既是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自身正当权利的有效保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有赖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参与机制的构建。
其一,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是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扎实根基。法治是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事业,它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强烈的主人翁独立意识与自觉意识,表达的是社会公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0](P7)黑格尔曾指出,“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11](P314)由此可见,在保障公民权利过程中,应当教育引导公民自觉信任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宣传法律和监督法律实施,使公民真正崇尚法治和自觉捍卫法治,从而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形成法治社会环境,使保障公民权利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自觉行动。从法治教育层面,应当重视加强公民法治宣传教育,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普法机制和普法队伍建设,开展公民普法教育等法治文化活动,完善网络信息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建立公民守法信用记录信息体系,全面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健全公民守法诚信褒奖与违法失信惩戒机制,强化规则意识和公序良俗。
其二,完善公民参与的法治体系是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前提要件。要制定良法应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根本理念,努力做到每一部法律、每一个条款都能反映出公民的共同意愿、维护公民的共同利益,并且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同和遵守。基于此,在所有法律制定过程中,应当坚持贯彻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体现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富勒也曾指出,具备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应涵纳八个要素: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循性、稳定性、同一性。①参见富勒.法律之德[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莫纪宏.法治应当传递的是时代正能量[N].检察日报,2013年1月25日第6版。同时,保障公民权利法治化,应当健全法律起草、论证、协调和审议机制,建立健全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和公民沟通联络协商机制,广泛发动公民有序地参与立法机制,充分发挥公民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法律法规的公信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效性。
其三,公民参与的法治实践是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核心要素。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源自于公民的信仰和拥护。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生命在于实现法治,而且主要是在于公民主体自身的法治实践。公民权益要依靠法律才能得以保障,法律权威要依靠公民才能得以维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12](P99)一方面,任何公民都应当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并履行义务(或职责),应当自觉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尊严和权威,自觉参与法律监督,重点规范和约束公权力,努力营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社会,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权利和义务相一致。[13](P10)诚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所言,自由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坚持强化公民内心的法治平等思维,是法治中国的内在尺度,是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在公民权利保障过程中,应当努力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建立完善公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公民规范,充分发挥诸如“民间法”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公民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的机制,积极发挥公民组织在公民权利保障中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和权益维护等作用。
[1]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北京:中国法学,2014,(4).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杨春福.制度、法律与公民权利之保障[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2).
[4]张文显.权利与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6]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14,(1).
[7]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童之伟.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J].中国法学,1995,(6).
[9]Steven Greenhut.A buse of power:How the Government Misuses Eminent Domain[J].Seven Locks Press,2004.
[10]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2).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3]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Reflection on Civil Rights Protection by the Rule of Law
ZHANG Xiao-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1120,China)
The legalization of civil rights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irit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s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c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under the rule of law.During the legal construction,it is vital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correctly the connotation of citizenship,and face and hand 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rights protection by law and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itssymbiosiswith 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aswell as its re lation with the awakening of citizen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citizenship;rights protection;rule of law
D621 5
:A
1006-723X(2015)02-0001-05
〔责任编辑:左安嵩〕
张晓君,男,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