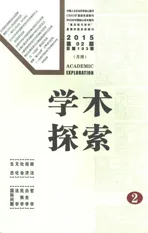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小产权房
2015-02-26罗熙
罗 熙
(广东警官学院 法律系,广东 广州 510000)
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小产权房
罗 熙
(广东警官学院 法律系,广东 广州 510000)
小产权房现象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立法的“暧昧”、政策的限制、执法的放任,小产权房如星星之火般燎原发展。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考虑立法对策时,不能仅从“就法论法”的角度细化立法、完善法律实施机制,法律毕竟是基于人性而构建的制度,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深入剖析小产权房产生的内在动因、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和司法实务的进一步考察可知,“失范”的小产权房应借助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动力转变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的规范内容。
小产权房;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制度变迁是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与变革无不是制度变迁演绎的成果。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当现存的制度结构中出现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那些期望获得该利润的行动主体就会成为推动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现存的制度安排就存在着创新的压力。[1]制度不均衡下的获利机会将推动制度变迁,新的制度会逐渐取代旧的制度。
小产权房,又称农村小产权房或乡产权房,根据《土地管理法》小产权房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流通,而不能向外转让。实践中,国家正式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并不对小产权房发放正式房屋产权证,因而有不少人认为小产权房就是没有产权的房屋,这实际上是对小产权房的一种误解。①根据《物权法》第30条规定,因合法建造等事实行为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这就意味着无须办理登记就可直接发生设立物权的效力。所以小产权房不需要登记就可直接发生设立物权的效力。参考自:《农村小产权房的物权变动——以法院裁判引起的物权变动为视角》,《法律适用》2009年第5期。从本质上来看,小产权房的物权设立并不必然违法,立法及国家政策只是对其物权变动(通常所称的“流转”)进行了立法限制。
作为法律禁止向城市居民任意流转的小产权房,何以从20世纪90年代“星星之火”式的个别流转发展到“遍地开花”式的大规模流转的局面?其中不乏立法的“暧昧”、执法的放任、各种利益的博弈等因素。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是“潜在利润”的存在逐渐突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各利益主体重新分化组合并改变以前的制度偏好,试图进行制度的再安排或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中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灰色激励”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策导向”,合力产生了小产权房流转这一看似违法却又符合市场逻辑的“失范自治行为”。小产权房的现状从客观上反映了打破城乡二元化体制、完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物权平等保护的制度变迁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讨论的小产权房并非所有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而仅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②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条,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被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部分,所以这里所指的小产权房只能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房屋。在农村农用地上建设房屋,将被作为违法建筑而拆除,没有讨论是否值得流转的价值。参考自:《农村小产权房的物权变动——以法院裁判引起的物权变动为视角》,《法律适用》2009年第5期。小产权房的流转禁止也并非仅是房的问题,同时也包含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问题。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小产权房
(一)渐进式改革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要求法律体系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产权和契约以及独立的司法。[1]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一度被西方经济学家批评为改革目标不明确、改革步骤混乱。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渐进式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年均9.83%的GDP增长率,被西方经济学理论视为在法律制度不完善、弱产权法律保护、契约实施不力、政府干预盛行情况下出现的“中国奇迹”。[2]
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的政策文件在很多时候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开始时是以党和政府文件形式推动的,这些政策内在地界定了国家、集体和劳动者在土地生产经营方面的产权关系,实际上起着法律的作用,使农村生产经营焕发出巨大生机。[1]这种以政策破冰、立法垫后,以点到面、从地方“零售式立法”到中央“批发式立法”的方式,一方面为改革节约了国家立法成本,另一方面充分保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前提,也为经济活动者提供了大量的激励机制。不仅包括合法激励,也孕育了灰色激励。行政权力默许的法律灰色地带增加了新政策成功的概率。行政默许、国家法律的特殊“时滞”所导致的灰色地带,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3]
从逻辑上看,正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法律特性之间的悖论导致了这种“灰色激励”存在的必要。赵万一教授认为“微观经济的内在要求在于排斥强制性限定的倾向”。事实上,经济的自由发展与法律的稳定性一直是立法最难以协调的矛盾体。微观经济日夕万变,旧有的法律规范很快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新型经济形态又亟待新的法律规范来确认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与经济秩序。经济对于法律的稳定特性如电子的正负两极,即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市场经济越发达就对法律提出了越高的前瞻性与包容性的要求。所以,新型经济形态在各地以“星星之火”发展,对法律的突破不到一定程度,都先静观其变,这是中国改革急速转型中常有的“灰色激励”现象。大量的“灰色激励”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创造了极为丰饶的土壤。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都是渐进式改革中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典范。
在这种渐进式改革下,国家在立法层面(包括《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禁止小产权房向城市居民流转;小产权房非法流转发展初期,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也没有予以严厉监管和打击的意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与少数开发商有着流转小产权房的利益驱动力,某些乡、镇地方政府也加入了小产权房非法流转的利益链条。在立法的“暧昧”、执法的放任、利益的驱使下,小产权房在全国迅速掀起一股城市居民购买的热浪。
(二)小产权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达出来的。”[1]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产生的小产权房向城市流转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渐进式改革下,由正式制度外的“潜在利润”灰色激励下的必然产物。双轨制土地制度之下,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低价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再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高价出让给商品房开发商,获得极大的土地增值。土地财政从根本上缓解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在地方财政的比例日益下降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土地储备中心建立之后,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趋势就更为严重,实际上成为土地财政的主要受益人。作为集体土地的真正所有权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无法在正式制度下找到处分集体土地使用权而充分实现土地增值的有效渠道。政府、开发商、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在土地利益链条中的地位极度失衡,原有制度逐渐演绎出利益非均衡的动向。
“当行动团体认识到现行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潜在收益,而主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他们就会竭力改变现行的制度安排,处心积虑实现潜在的收入,从而推动制度变迁。”[1]小产权房向城市居民流转的趋势从“星星之火”到“遍地开花”,客观上反映了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乡镇政府与部分开发商打破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绕开这一“中间商”的社会利益诉求。
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原本不值钱的宅基地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稍加盖造就可以卖个好价钱,这种轻而易举的获利远远高于早出晚归的种地收益,突破现有制度均衡而追逐“潜在利润”的行为尝试便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强大驱动力。对于城市购房者而言,小产权房由于建立在集体自由的土地上,不存在土地出让金和众多环节税费,销售成本低,相比城市商品房,一般要比市区同类商品房价值低30%~40%,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5]小产权房的主要购买群体是中低收入阶层,在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在社会保障房制度远远不能满足日常的住房需求,小产权房成为进城打工、中低收入者等普通公众在住房经济利益上的一种自我救济手段。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数据显示:1995—2010年间全国小产权房竣工建筑面积累计达到7 6亿平方米,其中“十一五”时期小产权房竣工规模达到2 83亿平方米。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2007年以前,全国小产权房的面积累计高达66亿平方米。另据国土资源部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天津、成都、西安、武汉、南京、济南、郑州、广州、深圳等地,均已建起大量的小产权房。以北京为例,据非官方机构不完全统计,北京目前小产权房数量约占整个房地产市场的20%,涉及近30万户家庭。①《北京处理小产权房不会“一刀切”》,《经济参考报》2012年10月。小产权房通过带房入城、旧城改造、合村并镇、新农村建设、城镇居民的依法建造、村集体直接开发、合作开发、各种形式的信托持有等多种途径和形式,[6]达到现存全国实有村镇房屋建筑面积330亿平方米的20%以上。[7]2008年10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小产权房绝对不允许再建,但对于已经在农村购买了小产权房的消费者,政府要保护其合法权益。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以及政策上的松动下,铤而走险非法购买小产权房的群体愈发庞大。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下演进的小产权房
(一)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法律制度
国家是享有立法权的合法主体,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由国家或政府来推动立法或者制度变迁。政府主导经济立法和法律制度的供给方式也有其独特的优势:短短三十年改革进程中,通过“加快”“加强”立法,客观上实现了中国人急于摆脱旧的计划经济和法律制度束缚,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与法治的愿望。很多学者认为,小产权房的本质问题是土地法律制度问题,具体来讲是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法律制度问题。但政府主导之下的农村集体土地往往承担了其所不能承受之重。孟勤国教授指出,“农村土地不仅要养活中国人,为几亿农民提供就业和生存的最低保障,其承载的社会价值十分沉重”②中国现有耕地18 3亿亩、粮食生产总量5亿吨左右、人均拥有粮食380公斤/年,略高于世界人均最低生存需要。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处于基本满足中国人口需要的状况,没有太多的余粮。参考自:姚惠源 世界粮食生产与加工的基本格局和新世纪的发展趋势[J].粮食与饲料工业,2001(5)。。
从经济学角度看,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使得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以市场作为基础性配置手段,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单一经济价值上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也应该将经济绩效作为检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放开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不应让农村土地承载太多负担。但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土地双轨制,使得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虽然在《物权法》上取得平等保护地位,在政治上却很难做到一视同仁,现实中更是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下,粮食政策、粮食安全是国家的立国之本,政府主导的土地法律制度不得不保守地对待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新形式,继续维持农村土地的经济价值让位于社会价值的利益格局。在以政策为先驱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法律时刻不忘“为政治保驾护航”,当其基本价值理念与政治战略相违背时,法律体系内部出现了无法周延的逻辑矛盾:一方面,《宪法》规定平等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与个人财产;另一方面,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不置可否。一方面,《物权法》强调平等保护原则;另一方面却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裹足不前,仅作指引性规定,将问题抛给《土地管理法》。一方面,《土地管理法》并未明确禁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另一方面却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后经政策解读为总体上禁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
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在小产权房并未作为一个立法概念在法律上出现之际,进而许多学者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是禁止小产权房流转的真正原因,小产权房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
(二)土地政策与小产权房政策分道扬镳
从法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如果国家强制性供给的法律不是源于现实的生活需要,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那么,就不能简单地把不知法归咎于人民的无知,而是应反思国家主导经济立法的方式本身。[8]国家或政府控制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在于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及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其政策逻辑在于:现有的育种技术不能短时间内提高粮食产量,而其他技术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下,18亿红线耕地意味着生存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农民宅基地的转让,也会导致大批卖房农民无家可归,从而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造成社会动乱。[9]一切经济价值追求都毫无疑问地要为生存权和社会稳定让位。
这种逻辑演绎的理由看似非常充分,却以简单的理性思维替代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国家对农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进行严格控制是无可厚非的,这的确关系到泱泱大国的粮食问题。但从中国的数据统计①据报道,虽然法律仍然认为违法,但实际上,珠江三角洲集体所有的土地占所有建设用地的50%。参考自江平.《物权法》的核心还有三个难题[EB/OL].焦点房地产网,http://house.focus.cn/showarticle/2453/540170.html.2007-03-22.中可以看到,每年新增的大产权房并非空中楼阁,其所占据的土地主要来源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与转化,也涉及侵占耕地问题。都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都是农地的数量减少,为什么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就必须将其卖给国家或者政府?为什么地方政府就可以在这种大义凛然、冠冕堂皇的逻辑中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
美国实证主义法学家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国家对于农村土地交易市场的限制,让农村土地流转呈现自发性、隐形性。小产权房的各方参与人——农村经济组织、农民与城市购房者,对于市场规律和交易规则的把握要远比立法机关灵敏,对于交易规则的效率也有更高要求,因此如果国家立法不符合市场逻辑,他们基于经济理性,会主动向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规律靠近。“小产权房”从最初萌发于市场经济极度发达的一线城市的郊区②“小产权房”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及部分城中村,如北京主要集中在通州、顺义、密云、怀柔、房山等郊区;西安集中在东郊沪浦河、长安区、北郊方新村、未央湖、白家口、鱼化寨、三桥等城乡及城中村区域附近;南京的“小产权房”以栖霞区和雨花台区最为集中;武汉集中在黄破区、汉南区、蔡甸区及武昌的洪山村、徐东村、南湖、汉阳的建岗、汉口的后湖等地;天津集中在东丽区、西青区等地;广州主要集中在白云区同和、天河区杨箕和海珠区康乐村、下渡村等地:济南集中在段店、大饮马、二环南路、小清河等城郊结合部以及历城区等地。城市具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潜力,城市周边的小产权房既能享受城市便捷的各类基础设施,也能享受到集体土地所具有的优势,促成了“小产权房”的发展。张云华:《“小产权房”的成因及其治理》,《调研天地》2011年第7期。迅速发展到市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的许多二线城市,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激发了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需求。这在客观上要求以法的形式来规范土地产权的内容、界限和形式,调节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并约束其行为。[10]
国家在农村土地政策与小产权房的政策上却花开两朵,逐渐分化为截然不同的两条轨迹。一是土地政策方面,《土地管理法》第63条对因破产、兼并而使乡村企业用房占用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流通留下了余地。200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和2003年3月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我国拉开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序幕。2005年,广东省专门出台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允许集体土地在不经过征收程序在市场上自由流转。不仅政策、立法上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还在全国各地设立试点。二是小产权房方面,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严令禁止建设“小产权房”。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第2条规定,“农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强调,“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2007年6月18日,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发布《关于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风险提示》,提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此类房屋,将无法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且明确表示“城市居民不要购买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素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11](P96)2008年初,国务院再次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准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2008年7月15日,国土资源部要求尽快落实农村宅基地确权发证工作,同时明确指出,不得为小产权房办理任何形式的产权证明。2010年3月2日的《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要求,农村的土地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开发。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中的“宅基地不能流转,通过出让、转让、出租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开发和住宅建设”等限制性规定,实质上也是不允许小产权房向城市居民流转。
在保护生存权和社会稳定的考量下,政府逐渐认识到在保卫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可以逐步放开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试点、出台地方性法规。同时,却在2012年、2013年出台了严令清理整治全国小产权房的最新政策。在房与地政策上的分道扬镳,不能不让人质疑政府主导下的对小产权房流转的限制是否真的来源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是否真的来源于保护全国人的粮食供给和农民社会保障的需要。
三、地方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下的小产权房之正当性
小产权房向城市居民流转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来看,是渐进式改革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与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逻辑具有一致性。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应当遵循自生自发而非理性设计和强制干预的逻辑演进。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慎重对待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更需要慎重对待干预市场的强制力。密尔说:“在文明世界中,强力(power)能够正当化地适用于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任何成员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对他人造成损害。”[12]当保护生存权和社会稳定的考量,已不能成为限制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正当化强力,其何以能成为阻断小产权房流转的正当化强力?而能够阻挡小产权房流转的正当化强力又究竟是什么呢?
宏观政策层面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早已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就要求打破城乡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13]对于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弊端,学界亦早已达成共识。禁止小产权房在城乡之间流转,是人为在城乡之间建立壁垒,不利于消除城乡二元化体制结构,显然违背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小产权房,但是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通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这次改革将建立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平等交易的新土地制度。若集体建设用地能够在市场上公开流转,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小产权房将来必然能够在市场上流通,只是国家设置的相应条件的多少而已。
从物权平等保护的角度来看,小产权房的建造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依据《物权法》第30条规定,可直接取得合法物权。虽然立法及政策导向是禁止小产权房在城乡之间流转,现实生活中却早有依据法院判决而实现小产权房在城乡之间流转的案例。政策导向之下的法律体系逻辑矛盾不能阻却市场经济这一天生的“公平派”“平等派”在城乡之间的穿梭,更无法阻却“等价交换”这一价值规律在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之间的践行。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理应由国家来承担,地方财政的压力理应通过深化税制改革来解决。“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不仅是政治生活的写照,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化大分工在法律领域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上,还是宏观政策与物权基本理念上都没有禁止小产权房向城市居民流转的必然理由。揭开纷繁复杂的层层面纱,我们发现“真正支撑政府限制小产权房流转的理由是县级以上政府在现行二元化土地利用机制下,通过垄断土地供应所产生的巨额利益。这种巨额利益以牺牲农民自主权益和城市居民饱受政府与房产商的双重挤压下的高房价之苦为代价”。[14]在地方政府大行举债、入不敷出的巨大财政压力下,土地财政的不合理社会各界都“心知肚明”,但在分税制体制下,大家也清楚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无奈之举。
但任何法律的设立都需拷问其正当性,任何强力的施加都需拷问其必要性。土地市场难道仅是政府、开发商的原始积累和财富源泉?从权利的正当性来看,国有土地代表的是亿万人民社会生存和财富创造的基础,农村土地代表的是农民的集合体社会生活和财富发展的基础。在现有的土地征收体制下,从农村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征收过程,基本不考虑农民的意志。在现有的土地交易制度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对外流转的主要渠道——即销售小产权房,也不考虑农民的意志。当政府基于为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考量而禁止小产权房的流转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自身却成为这一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许多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用于赢利性的房地产开发,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这源于基本利益冲突角色之下的立法难道不带有一点偏颇之色彩?
伟大的法学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法官,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代表者。何以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的意志能够被其他人所设想或代表?简单的小产权房违法,不能回答这一禁止性政策或立法的正当性。当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路径偏离时,秉着私法自治的精神,还原一个真实世界的本来需求,可能是最好的答案。这也是法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推崇的,符合正当性的规则是自我演进的“内生规则”。
正如在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简单的理论演绎不能替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事实上,国家在禁止小产权流转的政策导向下,曾在2007年掀起一场小产权房拆除之风,但其结果是“未去旧病,还添新愁”。[15](P132~150)这不得不让人反思,禁止小产权房流转的立法与政策本身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律,是否能够引领制度的创新需求。渐进式改革道路下的小产权房制度变迁,不能仅局限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还应当遵循“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各自的角色,在行动者群体间的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制度的演进本来就是一个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动态循环过程,“潜在利润”的存在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推动着现有制度向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禁止小产权房流转的立法或政策早已无法维持均衡的利益格局,小产权房的流转现象才会在各地蓬勃发展,我们必须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对待这种现象,反思、检讨、修正现行的经济立法。只有以这样的心态,才能在不断的试错中满足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需求。
[1]孙同鹏.经济立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周林彬,黄健梅.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改革的实践[J].学习与探索,2010,(3).
[3]周林彬,孙琳玲.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一种制度变迁的视角[J].政法学刊,2010,(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刘涛.论小产权房与我国土地的利益分配[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
[6]两部委正酝酿规范性文件.小产权房将引来最后审判[Z].第一财经日报,2009,(6).
[7]陈耀东,吴彬.“小产权”房及其买卖的法律困境与解决[J].法学论坛,2010,(1).
[8]孟勤国,黄莹.中国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三个前置性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
[9]胡光志,朱三英.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的思考——以“小产权”房为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09,(3).
[10]陈耀东,吴彬.“小产权”房及其买卖的法律困境与解决[J].法学论坛,2010,(1).
[11]密尔.论自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2]张伟.关于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法律制度探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3]鲁晓明.论小产权房流转——原罪的形成与应然法的选择[J].法学杂志,2010,(5).
[14]王玉臻.小产权房法律问题探析[D].吉林:延边大学.
[15]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Restricted Property Right Housing under the View of Changing System s
LUO Xi
(Law Department,Guangdong Police College,Guangzhou,510000,Guangdong,China)
The issue of restricted property houses has been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They have been expan ding rapidly in face of ambiguous legislation,policy restrictions and slacken law enforcement,.In this respect,circl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should go beyond the attitude of law for its own sake in discussing legislativemeasures,such as to further refine re lated legislation and to perfect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as law is a kind of human nature-based system construction.This paper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interests demands involved in housing with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hanges,and then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ed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Finally,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unaway restricted property right housing should be regulated by the top-down mandatory forces rather than the bottom-up induced ones.
restricted property right housing;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change;mandatory change
DF521
:A
:1006-723X(2015)02-0047-06
〔责任编辑:黎 玫〕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4CZZ009)
罗 熙,女,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讲师,主要从事民商法、经济法、经济犯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