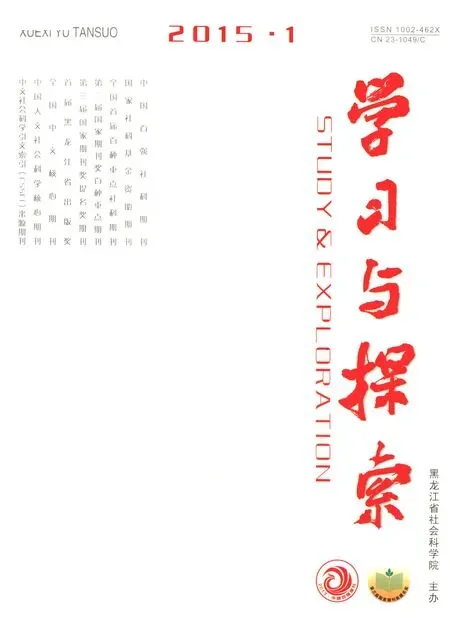论演示类叙述的“真实”与虚构
2015-02-25胡一伟
胡 一 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论演示类叙述的“真实”与虚构
胡 一 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虚构与纪实,是人类叙述活动乃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两个范畴。演示类叙述作为与人性最相契合的叙述方式,其现在在场性、受述者参与等特点容易致使人们搁置或漠视叙述框架,甚至将一切还原成经验事实。通过考察演示类叙述的展示、即兴与不可预测、受述者参与、非特有媒介等体裁特征,可以将虚构变为“真实”的种种可能揭示出来。
演示类叙述;纪实;虚构;叙述框架;符号媒介
虚构与纪实,是人类叙述活动乃至思维方式最基本的两个范畴。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将叙述基本类型划分为纪实型体裁与虚构型体裁这有益于辨清各种叙述体裁与“经验真实”的本体地位的关联[1]2。 无疑,人性是两者相关联的核心:“经验真实”与人(的认知)有关,叙述表现为“卷入人物的事件”,人必然是叙述的中心。而用身体、实物等作符号媒介的演示类叙述,与人类的诞生同时开始,都体现了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会用身体、言语、实物演示故事。进言之,演示类叙述所用媒介构成的品质以及人卷入周遭世界的程度,将演示类叙述是与人性最相契合的叙述方式这一关系揭示了出来。
对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的区分,关键在于文本如何让读者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体裁。可以说,文本对读者的作用贯穿于读者的整个体验过程。而“区隔框架”[1]74这一理论的提出,把这种感知连续带分成了几个本体地位很不相同的独立域界:再现外与再现内,虚构外与虚构内[1]80, 从而巧妙地将纪实叙述与虚构叙述区分了开来。当然这种区隔不是绝对的,文化的规约性以及个人的认知方式等因素都会对纪实叙述与虚构叙述的区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譬如情感的过度投入,会使人们搁置或漠视叙述框架,将一切还原成经验事实。而作为与人性最相契合的叙述方式,演示类叙述的现在在场性、受述者参与等特点不仅丰富了人们投入情感的途径,还能增强人们的情感投入程度。考察演示类叙述卷入情感、甚至让人过度投入情感的体裁特征,有助于将虚构变为“真实”的种种可能揭示出来。
一、从“卷入”到“浸没”
叙述表现为“卷入人物的事件”,它必须有人物参与的变化。在演示类叙述中,对非特有媒介的运用,必然要“卷入人物”,因为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展示与受述者参与则为“卷入人物”的情况打开了另一条路径。即兴与不可预测性能够将“人物参与的变化”这一点鲜明地展现出来。然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人物,形成有人物参与的变化之时,还易于“卷入”人们的情感因素,或达至“浸没”状态。譬如,演示类叙述要求受述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叙述过程中来,这能够调动受述者的情感,甚至有时受述者的情感因素会反向作用于叙述者人格。而不可预测与即兴则将叙述者人格和受述者人格中的不同情感功效凸显了出来。换言之,从情感“卷入”到“浸没”的过程中,能体现出叙述者与接收者两者情感投入程度渐增(变)的一个趋势。一旦情感投入程度滑向“浸没”这一端时,人们往往会搁置或擦除掉框架,将一切还原成“真实”。诚然,任何叙述都会卷入情感,但不同的叙述体裁卷入情感的方式和程度不一。从文本形式上看,文本中的空白、断点等会召唤人们对其进行填补,或者产生二次叙述化,同时也提供了投入情感之机。较之于其他叙述类型,演示类的现在在场性、受述者参与等特点丰富了填补空白、二次叙述化的诸种可能。下面将从演示类体裁的四个基本特征——展示、即兴与不可预测、受述者参与、非特有媒介出发,来看其召唤情感投入的方式。
1.展示。展示意味着文本的空间朝向是面对观众,把故事“直接”演示给观众看。因为演示的意义必须由观众此时此地在场实现[1]41。 这种同时在场性能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不同关系——表演角色转换或形成共同体等情况呈现出来,因此,展示所要求的同时在场性可以作为在场者情感“卷入”达至“浸没”的一个途径。由于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受展示空间,即展示的框架以及这个框架为观者提供的展示维度的影响,故而,这里主要从演示叙述需要的展示空间来立论。
空间的利用与安排会影响演员通过这一空间的动作及观众的观赏和参与方式。而双轴上的选择行为易使得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譬如:重新安排或改造演出空间、让观众和演员能够随意活动,表演者和观众角色转换的可能性将达到最大。以法朗克·卡斯托尔夫(Frank Castorf)导演的《记录列车机车号》为例。演出是在舞台上进行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后台为观众搭建了一个脚手架。观众若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必须横越舞台。先到观众席的人可观察到后来的观众如何踉踉跄跄穿过舞台,甚至把一些台上装牢的建筑用灯扯断的举动。也就是说,早在进入剧场时,观众就各自在扮演角色了:后进场的观众,在早已安顿就座的观众的面前,担当了表演者的角色。为了能成为观众,他们先必须成为表演者,但在舞台的后台上,他们曾经也被人当作过观众。 该例中的演出场地未曾变形,“舞台”依旧是演员“经典的”行为场地。因此,整个演出空间的走动易使观众占据演出中心区的位置,并“加入到故事中去”[2]162, 此为展示空间扩大的一例。
2.即兴与不可预测。展示体现出演示类叙述的现在在场性,要求演员和观众身体的共同存在。此时,不同身份的人“相遇”,就极有可能产生即兴和不可预测的情况。因为“演出”是由一个与自身有关的及在不断变化的反应链所控制和表现出来的[2]53。 即便是同一场戏或者提前策划好演出进程,所演出的每个文本也必然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多与人们当下的心理状态以及所卷入的情感程度有关。若观者被演出吸引,其沉醉投入的样子会鼓舞并激发表演者,表演者可能因此自说自话地杜撰些插科打诨和其他的即兴发挥。当然,表演者也可以因为演到某一段受到剧场环境、氛围的影响,突然进行“心迷神醉”的即兴创作等。
由于即兴与不可预测的情况多与人们认知心理状态有关——情感会导致行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偶然的即兴或干预行为审视情感从“卷入”达至“浸没”的渐变过程。以南斯拉夫女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因斯布鲁克的克林青格尔美术馆表演的作品《托马斯的嘴唇》为例具体说明。该表演以完全脱去其衣服这一行为开启接下来的种种自我伤残表演:用手粉碎喝空的瓶子和杯子,剃须刀片在自己肚皮上划五角星,抓住鞭子自笞背部,躺在冰上用热辐射器发出的热量致使伤口流血等。之后,几个观众因为不能再忍受目睹这一切痛苦了,便奔向冰块,抓住女艺术家,把她从十字架上搬开移走,于是该表演就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结束。其间,“自虐”的行为能够持续上演,超过30分钟而不被打断,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了两类不同的观众,一类是受自身“道义”的影响无法忍受血腥自残行为的观众,另一类是“无动于衷”的观者。这里的“无动于衷”有两层含义,也体现出了观者的两种态度:其一,他们知道这只是一场作伪表演,不会“全心全意”进入虚构世界之中,因此不管表演如何血腥残忍他们仍会继续观看而“无动于衷”。其二,由于整个表演在祭祀仪式与艺术之间摇摆,对基督教或死刑仪式有着虔诚信仰的观众,会将其作为一个体验与享受的过程。当此类“自虐”行为被当成苦刑仪式、即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时,他们便不会制止“自虐”的举动,甚至有可能跨入二度区隔中共同体验。此处的“无动于衷”便是一种情感浸没的表现,具有这种情感体验的观者无疑会忽视叙述框架,将虚构世界还原成经验真实。
3.受述者参与。在论及演示类叙述的展示空间时,虽然空间布局与展示的维度能够让观者“卷入”到演出文本中,但观者并不一定都会投入真情实感并沉浸于故事里、或愿意扮演其中角色,更多的是由于空间因素或剧本指令要求他们参与其中。而论及即兴与不可预测情况时,表演者和观众相互接触的不同方式则是从侧面反映出或者反过来影响人们情感的投入程度的。换言之,展示为受述者的参与创造了条件,即兴与不可预测情况在影响人们情感投入的程度方面增加了动因。但从受述者的参与方式和卷入程度的角度来看,它们与观者所卷入的情感呈最直接的关联,即情感与行为的双向作用,这固然与为情感投入创造的条件和增强投入程度的动因有所区别。譬如,当观众情不自禁地加入演员的表演行列与演员一起演出时,他们的情感已然被激发了出来。对于那些事后丝毫未察觉自身参与行为的观众,其迷醉程度可见一斑。此类情形的产生如同乔治·福克斯(Georg Fuchs)对新表演艺术希望的一样,它们能使演员和观众进入那种“少有的陶醉状态”。“这种状态,当我们感到自己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统一地在行动的群体时,便会向我们袭来。这时,肯定立即有一种战栗猛烈振荡我们全身,只要我们满怀激情地感觉到与其他人、不计其数的其他人是一个巨大的统一体,是一个群体之时。”[2]73由此可知,类似沉浸、陶醉的状态会让受述者情不自禁地参与到表演当中,即进入二度区隔内的虚构世界。由于区隔内文本横向真实,对于在二度区隔内的受述者而言,我们看来的虚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却是一种经验真实。此外,虚构与“真实”的转换,以自我扮演、自我演示之时的表现最甚。
4.非特有媒介。作为演示叙述的文本符号载体,非特有媒介与人们日常所用之物没有什么不同。正因如此,它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也是最能引发人们的各种情感的。特别是这种媒介的“非特有性”集中表现在演示媒介的身体性上。也即是说,所有的演示类叙述,都是以身体为中心展开的:言语、歌声、吼喊等,是身体的功能;乐器、武器、器具等,是身体的延伸;乐音或其他声音,是用器具产生的人声替代;化妆、衣着等,是身体的配备;道具、场面、光影等,是为展示身体功能而添加的设置。 进而言之,由身体带来的脉动感、节奏感——表现在声音乐音等等方面,最能拨动心弦。
为此,我们就会理解为何直逼身体的声响,会引起心理的和情绪上的反应,譬如寒战袭来,听者起鸡皮疙瘩、脉搏加快、呼吸变得短而局促、转瞬变得伤感或者亢奋,渴望、回忆等等情绪开始在观众心里翻腾起。这是观众的情感“卷入”。甚至,身体功能的节奏性传递能够产生心醉神迷的状况,如同G·福克斯所说“空间中人群的节奏性动作能够使其他人进入同样的或近似的节奏振动,并从而使之处于同样的或近似的心迷神醉状态”[2]84。这在祭祀仪式中有最为典型的表现(例如在咒语、仪式音乐的运用上)。总之,由演员节奏性的动作和节奏性的话语(歌声)中释放出的情感与能量会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循环作用,它能使观众对演出的进程发生影响——能作用于观众,并触发观者行为,抑或使人卷入并沉浸于二度区隔之中,达到“浸没”效果,将虚构转换为“真实”。
纵观上述四个特征,可见与其他叙述体裁相比,演示类体裁更易让情感“卷入”“浸没”的关键在于观众与表演者同时在场:所演述的故事直接发生在(观众)眼前,故事发生在此时此地并为观众所看见。观众在一次演出中所看见和听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永远是现场的。而这种同时在场会营造出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氛围,演员在舞台上富有激情的动作,观众看了之后会受激情主宰的动作所传染,从而使观众同样为这种激情所支配。这种传染通过看见演员在场的(当下的)身体传染到观众在场的身体。这种“感染”只能通过演员的在场和时间的当下性,这就是说只能通过演员和观众的“身体的同在现场”才有可能。 不管是对于早期教会人员(认为观看演出对观众的心灵来说是潜藏的危险)或医生等人来说都是如此,演出在观众身上能产生强烈的情感作用,对于现代人而言演出的作用亦是如此。因为“我们渴望我们生活的‘当下’的意义,我们处身在当下,我们要把这‘当下’当作可感觉的‘当下’来经历”。故而不难理解,在场的观众们缘何投入情感,沉醉于虚构世界的行为。而此时,叙述框架被搁置或擦除,“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变模糊了。
二、从“寻常”到“特用”
此处的“特用”不仅包括以身体为演示性媒介之“特用”,还包括演出空间等方面的“特用”情况。叙述框架作为演示叙述中最关键的一环,它不仅能把身体和物件这些日常物品转换成演示媒介,还能将演出空间被“特用”的情况呈现出来[3]。也就是说,观“寻常”与“特用”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叙述框架的“隐”与“现”。一旦框架未能被人们识别,一切便还原成经验真实。由此,这里将从以身体为中心的演示媒介以及环绕身体的空间来论叙述框架的隐现辨析真实与虚构的问题。
1.身体性的特用。所有的演示类叙述都以身体为中心展开,这些具有身体性的演示媒介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无根本差别。演示叙述中的细节真实(与日常生活无异的物)所带来的真实感,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让人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但是身体和物件这些日常物品在进入叙述框架后,其用法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尽管身体还是这个身体,但在演出时做出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经常做。因此,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用法反观隐藏的叙述框架。
从身体自身的功能来看,演示框架中的言语、歌声、吼声等功能与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不同。譬如舞台上重复的慢动作或者类似“上吊”“杀戮”等举动不会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无故上演,却时常通过叙述框架呈现出来。而反观舞台上这些频繁发生、显而易见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将叙述框架凸显出来。即使有时演员会走下舞台来到观众当中,与观众接触,他们的犯框之举也会将原有的叙述框架标显出来。例如,在《69年的狄俄尼索斯》中曾有过一个场面:穿着十分暴露的女演员走到观众当中,蹲下来,把身子躺在观众的旁边并开始抚摸他们,并延伸触摸的部位。虽然演员将其行为延伸到了舞台之外,但展示维度会随着演员行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而其抚摸的动作与日常生活中抚摸的含义自然也有所不同,正如台上“咬”的动作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咬”一样。
从以身体为中心展开的媒介功能来看,灯光、场面、道具、衣着等演示性媒介与日常经验所用之物无异,但它们在演示性叙述中的作用却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譬如在演示类中,会利用光影对身体的投射制造特殊效果——从舞台空间投射到屏幕可以是平面抽象的线条、也可以呈现3D立体的动态效果,而在日常生活中则不会经常这样使用。在行为艺术或杂技魔术表演时,人类可与动物一起演示。虽然动物依旧是动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不常见到,也更不会与其共处。在身体的配备上,我们不会在平日的生活中使用面具或装扮成特殊人物(女扮男装等等)。一旦这些日常经验之物显示出其“特用”的效果,叙述框架就会被标示出来。有时这些演示媒介往往还可以作为叙述框架,譬如光影转暗、幕布升起等,从而将身体和其他物件转换为演示媒介。倘若无法区分出日常物品“特用”的功效,人们就会因忽视叙述框架而分不清“真实”与虚构。
需要注意的是,对“特用”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社会文化规约会使得“特用”的方式不同或者造成对“特用”理解的方式不一。譬如某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本就具有文化象征意义,不同文化属性的人会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当它变成一种演示媒介后,其意义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就是说,受社会文化程式的影响,不同地域文化的人对媒介的使用方式有其差异,所产生的理解各异。如《托马斯的嘴唇》一例,不同的观众对十字架、五角星等符号的理解就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社会文化程式的差异还会使得人们对叙述框架产生不同的认知。
2.空间性的特用。前文论述展示时,从展示空间的形式与卷入情感的角度对空间的“特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即空间的安排与运用会为观者情感的投入及沉浸创造客观条件,这里则将从空间的“特用”情况与叙述框架的关系来看“真实”与虚构问题。
为营造出一种逼真的效果,人们试图用日常公共的生活空间来模糊实在世界与虚构世界的界限,以掩盖叙述框架,这是空间被“特用”的一种方式。以康奈斯通小组剧团在圣泰·莫妮卡大型散步区购物中心演出贝克特/皮兰德娄的《脚/嘴》为例。演出小组预先给观众装上了耳机,随后被领到购物中心的最高层。同时,演员也在整个购物中心活动。由于观众并不知道谁是演员及演员从哪个方向过来,他们会把每个行人当作演员。即使观众后来知道谁是演出小组成员及谁是偶然经过的行人时,行人们依旧完全被当作特别类型演员来看待,甚至不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个别观众身上。在这样硕大的日常空间中,几乎无法澄清这里谁是演员或谁是观众。在购物中心漫步的人,可能会变成演员,或者变成观众。无疑,该例对日常空间的“特用”模糊了日常经验世界与虚构世界的界限。
概言之,演示类叙述之“真实”与虚构,离不开对其体裁特征的审视。较之于其他叙述类型,演示类叙述的特征更容易煽动人们的情感,让人浸没其中,进而将虚构转换成经验真实。而演示媒介及展示空间之“寻常”与“特用”的情况又会作用于人们对叙述框架的辨识,进而影响人们对“真实”与虚构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演示性体裁容易让人过度投入情感,将一切还原为经验事实,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以纪实为底线的基础之上的。即无论何种区隔内的叙述文本,其底线的“纪实”品格都为这种认知接收心理效果提供了基础[1]86。
[1]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2] 李希特 费.行为表演美学——关于演出的理论[M].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塔拉斯蒂 埃.表演艺术符号学:一个建议[J].符号与传媒,2012,(5).
[责任编辑:修 磊]
2014-1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胡一伟(1988—),女,博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和符号学研究。
I0
A
1002-462X(2015)01-01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