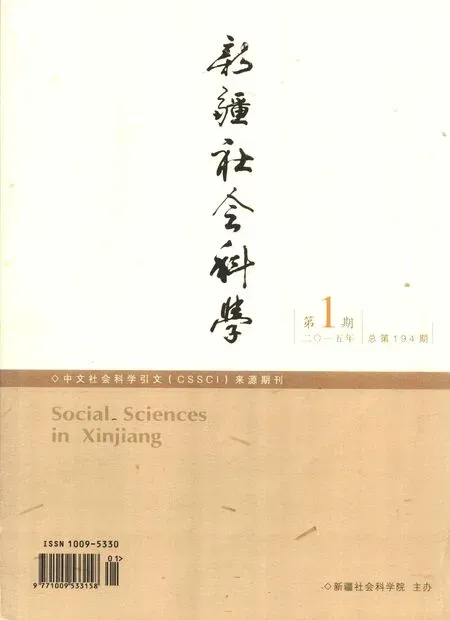论荀子德性修养三境界:学·诚·独*
2015-02-25陈光连
陈光连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的主张,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德性修养问题作理论上的阐述。学、诚、独,体现了道德积靡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修养境界,与荀子“长迁而不返其初”的知性性格和思维理路一脉相承。
一学:德性修养的实然路径
荀子德性修养论与他的性恶论相联系,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德性的形成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即使是尧舜也不是天生的圣人,也是通过修养而成的。“尧、禹者,非生而具备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荣辱》)人之荣辱在于修与不修,他说:“君法仪,禁不为,莫不说教名不移。休之者荣,离之者辱,孰它师。”(《荀子·非相》)荀子指出,所谓修,并不是“案污而修之之谓也”,而是“去之而易之之修。”(《荀子·不苟》)认为“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处穷而荣,独后而乐”,靠的是道德修养。(《荀子·儒效》)
为此,进行道德修养,荀子首重为学。没有学习,就不懂得为人的规矩,不能明辨是非善恶。所谓君子,应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天生的气质再好,倘若没有学习,在德性修养上也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因此荀子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荀子 《劝学》第一句就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学的过程是由少而多的逐渐积累、完善自我的德性修养的过程。学对于人的重要意义,就好像木线对木材的纠正,磨石对刀剑的磨砺一样,最终是要使人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君子正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切己省察,不断磨炼,从而智识日明而避免了错误。孔子也尝论为学的重要,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学,作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与人的在世生存具有相始终的关系。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克服自身超越自然之性以达到圣人君子的崇高境界。孔子 《论语》以 《学而》为第一章,荀子也是以 《劝学》为首篇,使学与伪有了内在的联系。“这个学实质上已不限于修身,而是与整个人类生存的特征——善于利用外物、制造事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了联系。”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学而结合着善“假于物”,则其固然不限于单纯精神修养的范围,而通向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的道德实践,意味着道德价值永远是一种有待进一步实现的东西,以及作为静态的已然结果的现状与有待实现的未来相比的某种缺憾性,“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者也”。(《荀子·劝学》)这种假于物的缺憾表现于现实内在的本然之性以及秉受于天的内在生命的非道德性质,而应然的德性则归结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对社会秩序规范的认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之中。相反,孟子之学则归结为人的先验道德潜能,“是内向地在自我精神中挖掘寻找本有的生命意义。如果说,这种学也是某种意义上实践的话,则这种实践在本质上,只能是个体在精神心理领域,对曾经是真实地发生的外在群体性物质实践活动的复演。”②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305页。
在荀子之前,孔子曾教导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的时代,礼是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总称,伦理道德规范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强调对于伦理道德标准的学习,是符合修身的一般规律,因为认识和了解道德标准是道德行为的第一个前提。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说:“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也,必颠蹶陷溺”。(《荀子·礼论》)礼作为道德修养的标准,体现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悖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成宁。”(《荀子·修身》)在荀子看来,人的修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血气、志意、思虑,即性情、意志和思想;二是饮食、衣服、居处、动静,即衣食住行;三是容貌、态度、进退、趋行,即接人待物的仪容举止。这三个方面遵循礼就会畅通,不遵循礼就会悖乱;遵循礼就和谐有度,不遵循礼就遇到坎坷,发生疾病;遵循礼就会文雅端庄,不遵循礼就会倨傲乖僻,庸俗粗野。而这三个方面又可以归纳为内在的道德心性和外在的仪容举止两个方面,也就是荀子 《儒效》所云:“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此,荀子特别强调德性修养要表里如一,内外兼顾。
荀子还认为学习要“思索以通之”。就德性修养而言,在学礼诵经的同时,还要时时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礼义的要求,在自己道德修养的精神性反思或活动中进行道德评价。在荀子看来,倘若只是学习,而没有自身品质行为实际的反省,就会惘然而无所得,不会有自身品德的真正提高。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对于荀子而言,人的行为是内心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后天修为创造而获得的道德成就在内心的体征,孟子思想则不同,认为人性有获自于天的德与善,注重内心的觉悟,讲知“至明觉体悟初即是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而荀子则把内心的自省与行为的过错结合起来,反映了动机与效果、志与功、知与行的统一。荀子曰:“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葘然,必以自恶也。”(《荀子·劝学》)在此,荀子预示“德—得合一的真谛是以德获得,正义谋利,所以首先需要一种道德的真诚,真诚的基本内核是以道德为目的,而不是工具。道德的忠诚则是对道德的固执,择善固执,在任何条件下,都执着于道德,‘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①樊浩:《道德形而上学的精神哲学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其择善固执处于坚守不变,始终如一的德操的持养中,在生与死、义与利的冲突中化解道德与功利的矛盾,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
进行德性修养,只有自我道德的反省是不够的,还要把所学的伦理规范应用于道德实践。在道德修养上,孔子特别强调以行为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又说:“古之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的弟子子夏也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矣。”(《论语·学而》)进行道德修养不能仅停留在意识或思想的层面上,必须坚持与道德行为实践相结合。孔子提出以行为本的道德修养方法,坚持的是扎扎实实的道德修养功夫,并在荀子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挥。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杨倞注:行之,则通明于事也。②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2页。和孔子、孟子思想相比较,荀子哲学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言知,特别重视外在的辨合、符验。这是荀子知性思想的现实主义品格在生活中的折射。
荀子针对孟子性善论的虚妄和妄想,从其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以人性出于自然,道德出于人伪,自然之性不能提供任何道德的内容,人的德性之知最后必于行上见,由行来验证回答,否则,“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按照孟子的观点,假如内心出发点是对的,即使出现不良后果,也是属于无心之过,仍属于道德的行为。但在荀子看来,虽然某种结果并不能证明人们心怀恶意,但是这种行为显然是违背人的初衷,因此,如果能够掌握必要的知识,选择正确的方法,实行恰当的行为而证明心意之善,行为之德,则“知明而行无过”。(《荀子·劝学》)所以荀子曰:“道虽迩,不行不至。”(《荀子·修身》)因此,在荀子看来,要涵养德性,培养人格,就要把所学知识牢记于心,积累德知,认识礼义,而且在礼的范围内进行思考,坚守礼的规范,将其内化成内心的理性自觉,以一种坚定的意志对自己的本性在实践中加以改造,从而化恶为善,形成理想人格。
二诚:德性修养的涵养工夫
荀子德性论归根结底都要落脚于个体诚的修养,诚就是一个贯穿德性修养的重要范畴。从修养的角度来审视诚时,实际上就表现为一个诚之的过程,其中诚所内涵的高度道德自觉精神得到了充分地体现。③笔者此处仅就荀子“诚”的修养工夫论进行诠释。关于“诚”在荀子思想中的位置,“诚”和 《荀子》中的理想人格关系,“诚”和自我实现可能的关联,请学者参见邓小虎先生的 《荀子思想中的“诚”:回顾和梳理》,2014年6月 《荀子研究的回顾与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荀子 《不苟》篇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荀子养心之要,在于致其诚心以守仁、行义,果能如此,则可以行、神而能化,明理而能变,达至与天合德的实功。要理解荀子以诚修德的理论意义,首先要对诚这一概念内涵作一分析,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诚指的是“自慊”。“此所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④朱熹:《四书集注·大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08页。。第二,诚就是指专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一者,诚也。第三,诚即真实。但这个真实不是实然意义上的真,而是在价值实现前提下对性的真实拥有。诚的字面意义是“实”。这实可以分解为两层涵义:一曰真实拥有。王船山 《尚书引义·洪范三》:“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有弗然,尽其所可致,而莫之能御也”;又其 《读四库大全说卷二·中庸》说:“为发之中,诚也,实有之而不妄也。时中之中,形也,诚则形,而实者随所著以为体也。实则所谓中者一尔。诚则形,而形以形其诚也。”二曰真实无妄。朱熹 《中庸章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船山和朱熹的解释,很好地揭示荀子诚的本质内涵。
但荀子不同于孟子“思诚自反”的思维路向,而以知性外求于行为来证明诚是德性的心灵根基及人的内在品质。荀子曰:“善之为道者……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他所说的“形”就是表现于外,而诚表现于外就是道德行为,这里,他既指出了不事道德行为是由于不诚,也指出了道德行为对于证明人诚的重要性。在荀子的思想中,德性是指人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不是先天而是获得性的,是通过人们后天的教化、学习而积渐形成,因此,以德性为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并将诚作为人所固有的、潜在的德性的理论为荀子所摈弃,而是把诚与外在的礼相结合,以诚所蕴含的礼善为行之本并体现于外在的色、言之中。如此,荀子所言诚不仅是主体内在的精神素质,而且诚与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诚为百行之源,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据:“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惟所居以类至。操之则存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也;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荀子·不苟》)由诚作为人“择善固执”的道德意志而言“所居以其类至”。所居,当系为存在或存有之意,如孟子所谓“居仁由义”,而操则存,舍则失以及下文单就操而说的轻、独行、济、化,则谓以诚为道德力量感化他人、促进他人德性形成的积极作用。诚如《中庸》所言:“诚者所以行德,君子以诚行知、仁、勇。”(《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另一方面,诚不离行,诚的德性需要外在的道德行为来确证、体认。德性是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它是通过人的长期稳定的道德行为而表现出来,而只有当践行某种道德行为成为人的一种习惯,并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守道德原则时,才可以说它具备了相应的道德品质,形成相应的德性。
荀子所谓的“诚心”“天德”是因为在泛道德的意识下,求一一譬解现实事态而衍生的比附之辞,并没有孟子 《中庸》“反身而诚”的内在而超越的道德本体之意,而是把诚作为心所认识的对象,依赖心的认知功能使诚由潜在的存在转化为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由于荀子的天是没有意识并完全是自发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当从人的角度理解诚时,它非但不是心的本体,而且是心所认识的对象,心通过对诚的认知和把握而把诚置于意识的控制之下,使之成为主体意识的存在,渗透到主体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之中,体现了主体对礼仪道德法则的高度的自觉认同,道德意识和礼仪规范的有机统一,并以自身实现诚为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虽然“心以征知”①在此,东方朔教授在 《荀子思想论集》谓“心以征知”其实即是说心能知,能辨识、验证,至于如何能知,荀子即谓“待天官当簿其类”,如是,即心之理智的作用亦便成为认知的根本条件。之心具有主宰的功能,但心并不是主宰者,心外所具之礼才是真正的主宰,心以礼为准则并使礼的规范通过后天的道德践履而注入心中,礼的自我迁化、自我识道、自我认同的过程,也是诚的涵养而积的境界。荀子 《解蔽》云:“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把通过虚静的修养功夫所达到的心灵境界称之为“大清明”,当然,大清明并不是指拥有天下万物的无所不知的能力,而是排除蔽的自由的德性心灵的境界。
可以说,荀子养心致诚与王夫之是一致的。德性修养目标的距离有远近,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最终能否达到目标与距离的远近和能力的大小无关,关键在于人是否一心一意,坚持不懈。荀子反复强调专心致志的道理,告诫人们:蚯蚓虽没有锋利的爪牙,强健的筋骨,却可以食泥土,饮泉水,因为它用心专一;螃蟹虽有两只锋利的钳足,却要寄生于别人的巢穴,是因为它用心急躁;眼睛不能同时看两个东西而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而清楚,只有专心才能一致,宁静才能致远,意志坚定、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刻苦修为,才能成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此即荀子所谓:“为仁之为守”“独行而不舍”。(《荀子·不苟》)促进德性生成,践履道德行为,维持和巩固固有的德性,则为人们形成稳定的道德情操提供内在的心理保障。荀子养心致诚既重视行为的积靡,也重视心志的守一,其意也概如此。
因此,对于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关系,荀子主张“诚于内而形于外”,即外在的仪容举止以内在的心性为基础,内在的道德心性以外在的仪容举止为表现。在此,荀子以礼为度而把内在的德性显发形成于外在的实践中,以心治性而实现心与身、性与礼、德性与德行的统一。可见,荀子论诚尽管与内圣一线的“反身而诚”“自明诚谓之性”大为不同,其诚明显着眼于礼义实践的外在事功,但“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表明,荀子亦在主体精神、道德人格的培育上主张“诚”,因此与内圣相通。荀子要求“诚心守仁”“诚心行义”,尽管并不意味着他的“知性心”已成孟子的“道德心”,却也将心的认知能力与诚的道德要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所谓的“养心”“致诚”便可视为培育道德知性——认识、把握道德观念、法则、秩序的客观知性能力与态度。
三独:德性修养的精微境界
慎独是传统儒家提倡的一种德性自我修养方法,也可以指经过道德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道德境界,更是通向诚的一条重要途径。慎独为儒家学者所普遍推崇,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得到发展,尤其为宋明理学家所看重,不少学者对其探颐索隐、阐出发微,由慎独之学凸现心性之学的精微和圆熟,而至刘宗周获得新的诠释,成为一个逻辑紧密的工夫之学。何谓慎独?许慎 《说文解字》曰:“慎,谨也。独,犬相得而好斗也。”段玉裁注:“谨也,慎也。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引申假借之为专壹之称。”许慎以“慎独”为“谨慎独处”之意,即哪怕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谨小慎微,不做违背道德的事情。东汉郑玄所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①《礼记·中庸第三十一》,《十三经注疏》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5页。,亦是此意。孔颖达对慎独的注疏与郑玄的注解不相违背。“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十三经注疏·礼记》)作为君子之人,于不睹不闻之处,能循性而行,合于常道,睹闻之处便自然不会有所违越。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于微”即是使罪过愆失不见迹于幽隐之处,不显露于细微之所。可见,慎独能使人挺立道德人格,进入极高的道德境界。历代注家对慎独的疏解基本上忠于 《大学》《中庸》原意。即自己的独居、独处时的言论和行为,始终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尤其在个体在面对自我时也要达到心灵的专一和虚境,戒慎恐惧、谨慎不苟、自我审视、自我满足而诚不自欺;此外,是扩展自己的内心体验,无论在众人之间,抑或是个人独处,都要力图格物致知,力求个人有独到体会而卓然挺立人格。可以说,慎独是儒家所强调的“正心”“诚意”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个人在道德修养中摆脱了礼的外在形式的约束,内心所达到专一的精神状态。
荀子最早提出“慎其独”的命题,并把它与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荀子·不苟》言: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而致其诚者也。君子之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也,不诚则不能化万民。
荀子认为“不诚则不独”,说明他是从内在的诚来理解“慎独”,慎独是由诚所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一个人的修养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诚,君子有至德,所以为人们所理解、亲近和恭敬,这就是因为他能“慎其独”的缘故。然而,只有做到诚才能“慎其独”,才能显示其至高的品德,支配万物,教化百姓。在荀子看来,天地虽然神圣,博大无比,如果不诚,就不能感化万物;圣人虽然智慧无比,如果不诚,就不能教化万民;父子虽有骨肉之情,如果不诚,关系就会疏远;君主虽然位尊权重,如果不能诚心修养德行,不能严以律己,就会失去民心,其权势就会变得卑微。天地与万物、圣人与万民、父与子、君主与臣民的社会人伦,无论哪一部分,都不能忽视道德修养,做到诚不自欺,也不欺人,尤其其中的主导方面更是如此,否则,社会将伦理失序、道德沦丧、矛盾激化。
荀子的道德修养其中重要的是将诚与家庭、国家甚至天地自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便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内圣外王”的德治总纲,体现了荀子“诚于中而形于外”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致性。关于诚的重要性,《大学》中也有明确说明:“所谓诚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见善。人之视之,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由 《大学》而反观荀子之诚,则知道德修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而不是用来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诚实是要求我们为修德而修德,只有真心实意地修养道德才能遏制歹念的萌发,达到慎独的境地。否则,充其量不过是伪君子,即使伪装得再好,小人本色无不见于隐微之处,“芷兰生于森林,非以无人而不芳”。(《荀子·宥坐》)
其次,独的形善于外并不仅是变化气质,还表明了诚心著明德化天下的观念,这正体现了儒家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因而,荀子所谓的独则形,既是无所依傍的独特自由人格的表征,亦是道德人格所臻之化境。“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杨倞注云:“持至诚也而得之则易举也,《诗》曰:德輶如毛。”轻,意谓易行义。也就是说,人深造自得于道,而达于“不思而得,不免而中”之境,这便是一种自然自由的行为,或是一种无所依傍的独行。此“独形”之形便可超越形表,而直接感通人心,所谓至诚能化,其道理也是如此。《中庸》引 《诗·大雅·烝民》“德輶如毛”句,杨倞注亦引“德輶如毛”来解释慎独之义,比喻圣人至诚慎独而化民于无迹之意,准确地揭示了诚、独、形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①此处关于诚与独的关系,李景林先生认为,“诚”实有诸己而真实无妄,“慎独”则是诚之实有诸己的内在性之表现。盖人之一念发动处 (犹今语所谓动机),人虽未知未见,而自己独已真切知之。必于此心之所发的隐微处敬慎其所行,方为“至诚”。参见李景林 《教化的哲学》第226~227页。
慎独这种时刻对自身言行、意虑进行反省的修养功夫,有利于人们诚的精神的形成和持守。由于人的欲望倾向于恶行,而使人心受蒙蔽陷于不诚的境地,因而需慎独时时处处对自身的意念以及独处的行为进行自我反思、自我约束、自我警醒,人若时刻做去恶为善的慎独功夫,则日自化性而至于诚明之境。故荀子云:“君子至德……夫此顺命,君子慎其独也。”
由此可见,荀子致微而至圣人的自由心灵境界是与孟子戒慎恐惧的隐微迥然有别,甚至是截然相反,而更接近于道家文献 《文子》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子》慎独思想贵在顺性适欲。《文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能,不再是通过自身的勤勉修身来加以完善,而以利人之性为立足点,一切以顺性适欲为要。如 《上义篇》所言:“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齐辑之乎辔衔,正度之乎胸中,内得于中心,外合乎马志,故能取道致远,气力有余,进退不曲,莫不如意,诚得其术也。”《文子》顺性适欲与荀子重视人之情欲而导之以情是相通的;其二,《文子》慎独思想的要旨是积道积德,利人成和。心知目有所不睹,耳有所不闻,不是戒惧而是明白四达,不是向内探求诸己,以内心的执著追求完善自己,而是向外溯求诸人,假众人之所长,贤愚并用,因资立功,假人成德,与荀子积靡成德、反对自忍、自强、自思,知性外求于礼而善假于物,因势法术而实现圣人之治的理念基本一致。“浊明外景,清明内景”乃是微的具体描述。“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以下,是说在微的境界中,知行而为一时应发生的从容中道的效果。“道心”是达到微的功夫,而微是道心的效验。他在 《非相》篇中说:“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即是知道而以道权衡的意思。所以荀子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是要人知道而以心顺道,才能保证心知性能力的正确性;他并不以为心本身就是道,而称为“道心”。荀子以心为虚一而静,以精微为德性理想境界,这与后来的禅宗有相似之点。禅宗谓“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指月录·卷六·牛头融篇》)认为心性修养不能仅仅从抽象的层面来谈,将其具体的落到实处便是时刻保证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违背当时的普遍道德观念,这种专一不苟特别体现在独处无人的情况下无数次的控制自己的行为,禅宗谓之“精进”。禅宗的道是道德原理、道德理想的体现,是存于心中具足佛性的心之虚无,而荀子认为心之本身容易“危”“倾”而需可观的礼道来作权衡,才能保持心之大清明的本性,而此本性只是进一步知道行道的“几”“微”境界,但其本心并不是道,道之微是沉浸于知性客观化于礼法规范之中,并作积习渐靡的道德修养而识道体道的自我认同。可见,禅宗的虚静、精微是道之本体与心相融内在超越的德性境界,而荀子所谓的虚静则是礼道治性所达致的精微之几,前者更侧重于心性的涵养,后者则倾向于知性的外求。因此,荀子知微的过程应是这样:求道→心虚一而静→心知道→微。心求道,是心求得一个礼义标准,有了礼义标准,才能虚一而静,心能虚一而静,才能知道,则心与道一,而可达到微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