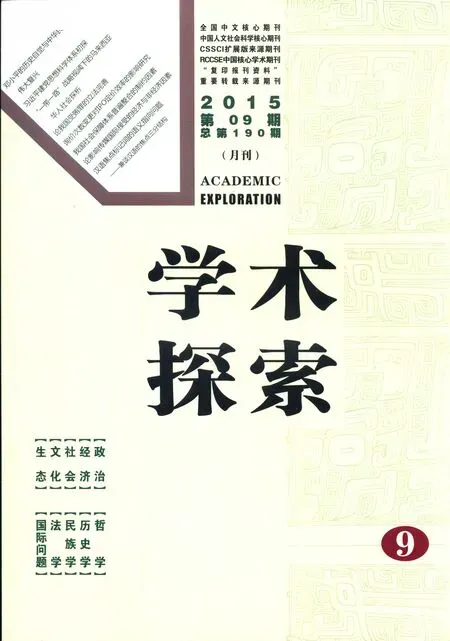我国慈善私益募捐的法律规制
2015-02-25王众
王 众
(昆明理工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我国慈善私益募捐的法律规制
王 众
(昆明理工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因救助对象的特定性,慈善私益募捐被冠以“私”字,但实属公益范畴。由于法律规范缺失,我国慈善私益募捐存在募集主体及程序失范、募捐财产管理混乱、募捐剩余财产权归属不明等问题,常常陷入信任危机。只有将慈善私益募捐纳入慈善事业法统一调整的范畴,并建立慈善公益组织介入慈善私益募捐的机制,才能有效解决慈善私益募捐面临的困境。
慈善私益募捐;公益;募捐财产;募集人;慈善公益组织
近年来,我国因贫穷、疾病、灾难等原因引起的,以特定个人或团体、组织为捐助对象的慈善私益募捐俯拾皆是。1999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将以私益为目的的捐赠排除在外。当前,我国慈善私益募捐不断重复着“遇到困难→发起募捐→爱心救助→真相怀疑→善款争议……”的发展过程。希波克拉底誓言:“寻善而无害”是慈善最为基本的原则,意为做善事而不伤害预期目标。该原则同时也包含着对于实际结果的一种警告:“好的愿望并不总是意味着好的结果”,[1](P142)这一谶言无疑是我国慈善私益募捐乱象的写照。本文力图分析慈善私益募捐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相应的法律对策。
一、慈善私益募捐与公益募捐的界分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须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2](P486)但我国目前尚无慈善私益募捐的法律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募捐”的定义是“募集捐款或物品。”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05页。慈善事业始终无法抛开筹集捐赠财产、让捐赠财产保值增值、使捐赠财产有效运作三个方面。筹集捐赠财产即是募捐,显然,慈善募捐是慈善救助得以行进的基础,也是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只是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募捐法,只有通过捐赠法对募捐行为进行规范。
因救助对象范围的不同,慈善募捐被分为慈善公益募捐和慈善私益募捐两种类型。公益也称为公益利益,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公益的最大特别之处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具体包括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3](P182~187)私益是与公益的对称,指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但公益与私益二者并非绝对割裂的关系。表面上的公益形式具有整体性,但最终落实为私益。私益亦可升格为公益。私益升格为公益有三种情况:其一,因享有私益主体的多数性和不确定性而升格为公益;其二,因私益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突出意义而升格为公益;其三,基于民主原则将私益通过政治或是立法的途径升格为公益。[4]
慈善公益募捐是指募集人为实现某种社会公益事业的目的,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劝募,募集财产的活动。慈善私益募捐是与慈善公益募捐相对称的概念,是指由募集人发起的,为救助特定对象进行的劝募活动。二者有如下不同:第一,受益对象不同。慈善公益募捐的受益对象是不确定的,受益人数众多。慈善私益募捐的受益对象具有特定性,局限于封闭的、有限的人群,不具有普遍性。第二,募捐目的不同。慈善公益募捐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事业或是因公共目的而进行的募捐,其目的只需符合公益性质,无需具体明确。慈善私益的目的是具体明确的。譬如救助某一烧伤儿童、患病老人等等。第三,对募集人的要求不同。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第10条第2款、第3款进一步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和非营利事业单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由此,我国慈善公益募捐的募集人必须是慈善团体或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其他组织或是个人不具备慈善公益募捐的募集主体资格。由于法律并未对慈善私益募捐的募集人主体资格进行规范,实践中,慈善私益募捐募集人任意性较大,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募捐活动。第四,募捐的程序不同。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2条、13条、14条、15条对慈善公益募捐的程序进行了规范,具有规模化、组织化的特点。慈善私益募捐因无法可依,募捐程序任意性较大,可以随时随地发起。
当然,慈善私益募捐并非静止不前,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遵循“劝募→捐赠→救助”的运行规律,学界一般所指的“慈善私益募捐”是包括三个运行环节在内的宽泛概念。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受赠人的身份为标准,来划分捐赠行为是否属于公益或是非公益的性质,并不符合慈善自身的逻辑。虽然,从微观视角看,慈善私益募捐因救助对象的特定性而被冠以“私”字,但就宏观视角而言,捐赠人或是募集人都是“出于提供帮助的意图将金钱或者其他方式的援助简单地和无条件地转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5](P5)希冀实现对没有法定扶助义务的人给予帮助的目的,涉及社会公德愿景的实现,事关公共利益,因此,慈善私益募捐实属公益。
二、我国慈善私益募捐的现实困境
(一)相关法律规范缺失
目前,在全国性的立法层面,涉及慈善事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有全国人大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办法》、《关于救灾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办法》。此外,还有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制定的相关规章和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法规和规章。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现有的慈善法律体系,[6]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所有规范性法律文件无一涉及慈善私益募捐行为的调整。
在地方立法层面,2011年5月正式实施的《湖南省募捐条例》是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结合湖南实际情况,专门针对募捐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尚未制定关于募捐活动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具有填补我国当前募捐领域立法空白的作用,但《湖南省募捐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募捐人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以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为了帮助特定对象,面向本单位或者本社区等特定人群开展的募捐活动和民间互助性的捐赠活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不适用本条例。”明确将慈善私益募捐排除在外。江苏省于2010年5月施行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将慈善募捐的主体限定于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并明确规定“为帮助特定对象在本单位或者本社区等特定范围内开展的互助性募捐活动,不需要经过行政许可。”同样,将慈善私益募捐排除于法规的调整范围之外。
换言之,就目前状况,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抑或是地方性法律规范,均没有对慈善私益募捐进行规范,更无谓禁止性规范。就社会生活的变动性而言,立法终究无法穷尽行为人自由创意的空间,事实行为的广泛性也绝对不是法律行为的边界所能揽括。
(二)募集主体及程序失范
当下,几乎任何组织或是个人均可成为慈善私益募捐的募集人。募集人身份属于自发取得,无需向任何机构申请或是备案,作为自然人的募集人也不需要提供道德品质方面的证明。因受益人与募集人是否为同一人,可将慈善私益募捐分为募集人募捐模式和受益人募捐模式两种。募集人募捐模式,是由募集人发起社会劝募,为受益人进行捐助,捐赠人通过募集人将捐赠财产交付给受益人的慈善私益募捐模式。该模式由募集人、捐赠人、受益人三方当事人构成,募集人身份可能是与受益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也可能是受益人的近亲属或是其法定代理人。受益人募捐模式,是由受益人本人直接发起的劝募,捐赠人直接将捐赠财产交付给受益人的慈善私益募捐模式,此时的受益人即是捐赠合同的受赠人。学界所讨论的一般是募集人募捐模式。
由于没有法律的规范,慈善私益募捐从“发起→终结”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的程式限制,随性而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为求助信息的迅捷传播提供了便利。发起慈善私益募捐活动的方式呈现多样化,有借助传统媒体,譬如电视、广播、报纸发起的募捐,也有借助新兴媒介,譬如网络、微博、微信等发起的募捐。但是,这些求助的信息没有经过任何核实的程序。受助账户开设随意,缺乏监管。募集人在接受捐赠时也不需要向捐赠人出具有效凭证,客观上,无法保障捐赠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行使。
(三)募捐财产管理混乱
“每一个捐赠者都希望他的钱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没有谁希望那些来之不易的财富被白白浪费掉。”[7](P2~6)但事与愿违的是,我国慈善私益募捐中,对募捐财产的管理处于无序而混乱的状态。
究竟谁有权利来管理慈善私益募捐财产原本是爱心私益救助的中心环节,但由于既没有法律的确定性指引,也无禁止性规范。客观上缺乏捐赠财产管理人的选任机制,慈善私益募捐的“募集人”往往理所当然的成为捐赠财产的“管理人”,实际上拥有对捐赠财产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当然,也会有一些募集人主动将募集到的捐赠财产交与其他相关机构或是个人管理的情况,此时管理人的身份出现“让渡”。
目前,因募集人身份的不同,主要存在两种慈善私益募捐财产的管理模式:第一种模式,由相关机构负责管理。在“杨尔特诉陕西省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案”中,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既是慈善私益募捐的募集人,也是募捐财产的管理人。①资料来源《杨尔特诉礼泉县教育局、礼泉县教育工会给付募捐款纠纷案》,发布于http://china.findlaw.cn/info/case/jdal/3455. html,访问日期2014-05-18.其后的广西“余其山诉横县地税局募捐剩余钱款纠纷案”中,横县地税局同样兼具募集人和管理人的角色。第二种模式,由自然人负责管理。此模式的募集人大多为自然人。有时会由受益人的近亲属、法定代理人代管或是受益人本人直接管理募捐财产。“王海林事件”中,王海林既是慈善私益募捐的募集人,也是募捐财产的管理人。
慈善私益捐赠者的意愿是向那些身处绝境者伸出援手,通过资源的简单再分配获取小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客观上,慈善私益募捐中的受益人本人,由于年龄、认知能力、身体状况等各种因素,并不具备管理捐赠财产的能力。相较而言,由无利害关系的相关机构负责管理捐赠财产的模式更科学、合理,也更能保障捐赠财产的用途符合慈善捐赠的目的。问题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慈善私益募捐财产管理人的选任进行规范,由受益人的近亲属或是法定代理人代为管理的情况较为普遍。不难想象,没有有效监督,仅靠个人道德品质保障的管理是一个难以确定预知的因素。那就是想“怎样管、就怎么管”,顶多受到舆论的指责。现实中,募集到的捐赠财产不按发起时的意图和捐赠目的使用,或据为己有或挪作他用,无法保证捐赠人的爱心得到实现的案例时有发生。[8]
(四)募捐剩余财产权归属不明
由于求助需求与捐赠数额的供需之间不可能完全平衡,募捐剩余财产权的归属往往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将原本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耗殆尽。从1997年全国首例追索慈善募捐款案——“杨尔特诉陕西省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案”伊始,因捐赠剩余财产权归属不明产生的争议屡见不鲜。司法实践中,法院解决慈善私益募捐剩余财产归属权的主要依据是《合同法》对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但一般赠与合同与慈善私益募捐有着明显的区别,仅凭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无法解决慈善私益募捐中并非单一的法律关系,因此,不同法院基于对法理和事实不同的理解,对相同或相类似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裁判。
综上,对慈善私益募捐行为结果的反馈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可疑的,有时,慈善活动的结果可能令人困惑,表现不如预期成为慈善私益募捐的自然状态。虽然,慈善私益募捐属于一种“小众”的慈善方式,但上述令人失望的情况加剧了社会信任危机,影响了慈善事业整体的社会公信力,也对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伤害。
三、解决问题的法律对策
“为了拥有自由,必须限制自由”,对自由合理的限制就如硬币的两面随影相伴而共存于一体。[9](P195)一方面,慈善私益募捐需要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的推动,另一方面,慈善私益募捐属于社会公众扶危济困的善意表达,只不过受益人特定而已,如若没有任何限制,势必会造成慈善私益募捐行为的无序,影响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正因如此,美国在将慈善募捐视为受言论自由保护的“表达行为”的同时,对慈善募捐的内容进行限制,[10]我国也应不例外。解决我国慈善私益募捐问题的对策设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慈善私益募捐纳入慈善事业法统一调整的范畴
慈善私益募捐具有道德性,并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涉及社会公共道德。西汉刘向在《新术.道术》中云“恻隐怜人谓之慈”。《论语.述而》认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到南北朝时期,“慈”、“善”二字字义逐渐合一,包含博爱为慈、乐举为善两层含义。[11](P1~3)慈善私益募捐是社会公众以捐赠财产、志愿服务等无偿形式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自愿行为。表面上看,慈善私益募捐针对的仅是对个体的捐赠,但仍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来完成对个体的帮助,实质上仍属社会公益的范畴。
显然,当前,仅靠对个体道德的约束来实现对慈善私益募捐行为的调整,已无法适应我国慈善私益募捐发展的需求。将慈善私益募捐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成为学界公认的共识。分歧在于究竟是采用单独的立法模式,抑或是在相关单行法中对慈善私益募捐进行补充规定的立法模式。由于我国统一的《慈善事业法》尚处于草案征求意见稿制定阶段,笔者认为,可将对慈善私益募捐的调整纳入统一的慈善事业法,而无需采用单独的立法模式,理由如下:第一,节约立法成本;第二,有助于促进我国慈善事业法的整体构建。
(二)确立募集人的信义义务
信义义务的英文为“fiduciary duty”,也称为信赖义务。《布莱克法律辞典》对信义义务所下的定义是:“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后,为他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义务。信义义务标准是法律上最高的义务标准。”信义义务的受信人只能为了受益人或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权利,不得使自己的利益与受益人或委托人的利益冲突。
慈善私益募捐的募集人是慈善私益募捐的发起人,也是捐赠财产实际上的管理人,在捐赠人和受益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捐赠人通过募集人将捐赠财产交付给受益人,因此,确立募集人的信义义务是受益人得到救助的保障,也是慈善私益募捐行进的关键。慈善私益募捐募集人的信义义务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注意义务(duty of care)。慈善私益募捐募集人的注意义务,是指募集人在行为时所承担的采取积极措施避免其行为损害他人利益的义务。大陆法系中的注意义务与善良管理人义务常被混用。在民法上,民事主体在行为时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判断标准采用的是“善良家父”或“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标准。如果募集人在行为的时候采取了大多数与其身份、地位相同或者类似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则募集人在行为时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第二,忠诚义务(duty of loyalty),慈善私益募捐募集人的忠诚义务是指募集人应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处理慈善私益募捐事务的唯一目的,而不能在处理事务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他人图利,不得将自己置于与受益人利益相冲突的位置。[12](P130~135)
(三)建立慈善公益组织介入慈善私益募捐的机制
从时间维度来看,任何个人和机构,任何时候均可发起的慈善私益募捐固然有其及时性、便利性,但无序而过于随意的募捐始终潜伏着隐患,也会为“诈捐”者提供可乘之机。1986年美国“全美检察官协会”制定的《模范慈善募捐法》首要限制的对象就是“诈骗”。美国最高法院在Schneider案和Cantwell案中认为“以慈善和宗教之名的诈骗活动无疑应当被宣布违法”,并在Schaumberg三部曲中反复重申了禁止以慈善募捐为名实施诈骗。[10]2008年我国汶川地震期间,就有不法分子非法侵入部分红十字会官方网站,通过篡改网站的抗震救灾募捐专用账号,实施诈骗。
“有效慈善”是慈善募捐希冀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公益募捐或是私益募捐概不例外。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目前,由个人发起的慈善私益募捐,无需提供诚信证明,捐赠账户为个人账户,没有任何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侵吞、滥用善款事件频发。而由非慈善公益机构发起的私益募捐,往往在事后卷入“剩余财产归属”的纠纷中,如文中所提“杨尔特案”、“余其山案”便是如此。
前述诸多问题的根源实则是“如何募捐?”笔者认为,不妨考虑以公益组织作为慈善私益募捐中介机构的方式进行慈善私益募捐,即由求助人申请,慈善公益组织在确认求助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迅速为某特定受益人进行专门募捐,并设定特定账户,所得捐赠财产用于救助特定受益人的方式。理由如下:第一,慈善公益组织拥有相对完备的管理机制。尽管我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因制度瑕疵而饱受诟病,但和个人或是其它机构相比,无论是账户管理、人员专业化、财产安全性等方面均更有优势。第二,以私益募捐促进公益事业。私益募捐慈善的本质决定了慈善公益组织难以置身事外。结合实际,积极开辟慈善公益组织的中介职能,将会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目前,已有通过慈善公益组织作为中介的私益募捐案例,取得了较为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设立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社会公众的监督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失灵的不足。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包括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外部监督包括公众监督、舆论监督、政党监督等。[13](P139)相比政府行为谋定而后动的特点,民间性的慈善私益募捐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决定了其监督方式采用社会公众监督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要真正让社会公众对慈善私益募捐的监督落到实处,必须要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打通监督的“渠道”。第一,设立慈善私益募捐的社会公示制度。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2条规定“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香港《慈善筹款活动最佳安排参考指引》规定,所有由慈善机构举办或代表该机构举办的筹款活动,须公开慈善机构的名称和筹集善款的目的,慈善机构宜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就个别筹款项目编制财务报表,以供公众查阅。[14](P236)慈善私益募捐不妨参考公益募捐的社会公示制度,将捐赠财产的管理置于“玻璃口袋”。第二,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捐赠人的捐赠是慈善私益募捐得以实现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对捐赠人知情权的保障被忽视,可考虑给予捐赠人开具捐款凭条,出具证明文件,接受捐赠人对捐赠财产使用和管理的查询和监督,确保其知情权的行使,实现由捐赠人进行监督的目的。
[1][美]罗伯特.L.佩顿,迈克尔.P.穆迪.慈善的意义与使命[M].郭烁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台]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丁保同.民事公益之基本类型与程序路径[J].法律科学,2014,(2).
[5][美]彼得.弗朗金.策略性施予的本质:捐赠者与募捐者实用指南[M].谭宏凯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6]于丽杰.当代我国慈善事业法律问题研究[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7][美]托马斯.蒂尔尼,约尔.弗莱什曼.从梦想到影响:一流慈善的艺术[M].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8]孙琦琳.浅析我国慈善私益募捐[J].知识经济,2010,(11).
[9][英]爱德蒙.柏克.美洲三书[M].缪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吕鑫.慈善募捐的自由与限制[J].浙江学刊,2011,(4).
[11]莫文秀,邹平,宋立英.中华慈善事业思想、实践与演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2]王众.信托受益人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3]衣保中,邱桂杰等.可持续区域开发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4]徐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China's Private Charitable Donation
WANG Zhong
(Law School,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500,Yunnan,China)
For the specific assistance object,private charitable donation has been dubbed the name of“private”.In fact,itbelongs to the domain of public welfare.Due to lack of legalnorms,there are problems ofanomaly in the raising subjectand procedures,confusion of collection propertymanagement and ambiguity of ownership of surplus collection property in the present private charitable donation of our country,which is apt to fall into crisis of confidence.To deal with the dilemma effectively,we should incorportate private charitable donation in the adjusting domain of Charity Law,an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tervening private charitable donation.
private charitable donation;public welfare;donation property;charity-raiser;public charity organization
922.181
:A
:1006-723X(2015)09-0051-05
〔责任编辑:黎 玫〕
昆明理工大学人才引进项目(KKSY201324088)
王 众,女(白族),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