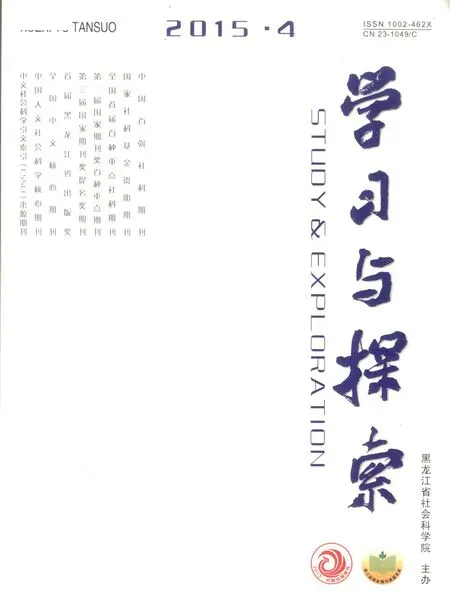促进当代文艺理论分歧的解决
——兼与王先霈商榷
2015-02-25熊元义
熊 元 义
(1.上海交通大学 美学、艺术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2.文艺报社 理论部,北京 100125)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促进当代文艺理论分歧的解决
——兼与王先霈商榷
熊 元 义1,2
(1.上海交通大学 美学、艺术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2.文艺报社 理论部,北京 100125)
众所周知,文艺争鸣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很难开展。不少文艺理论家在狭隘利益的束缚下不敢正视并积极参与文艺争鸣,而是回避积极的文艺争鸣、各说各话。不少偶发的文艺争鸣大多在没有解决文艺理论分歧前就不了了之了。有些文艺争鸣甚至还引起了外在力量的干预。这对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与王元骧、王先霈等老一代的文艺理论家商榷,我们踌躇再三。我们并非喜好论战,而是在梳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时发现王元骧与王先霈在文艺理论发展上是对立的。无论在把握文艺理论的发展上,还是在把握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上,他们都存在较大的分歧。如果这种文艺理论分歧不解决,就将严重影响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了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我们没有搁置王元骧与王先霈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分歧,而是努力在更高层次上解决这种文艺理论分歧。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有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观与粗鄙存在观文艺批评观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当代文艺批评观,而王元骧与王先霈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对立不过是这两种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观分歧在文艺理论上的发展和延伸。因此,王元骧与王先霈即使没有直接的思想交锋,也有间接的思想交锋。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绕开这种文艺理论分歧。也就是说,即使在王元骧与王先霈之间没有出现直接的思想碰撞,在其他文艺理论家身上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这种思想冲突。王先霈在回应我们的批评时认为我们把他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能回避的文艺理论论战”的一方并尖锐地批评他“回避文艺理论分歧”的“鸵鸟心态”,感到很委屈。王先霈认为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身处在这场文艺理论“论战”中,甚至不清楚这场文艺理论“论战”的存在,因而很难参与到他并未意识到的这场文艺理论“论战”中去[1]。首先,这种反批评是戴错了帽子的。我们并没有批评王先霈存在“回避文艺理论分歧”的“鸵鸟心态”,只是在梳理王元骧与王先霈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分歧时批评了王先霈文艺理论的缺陷,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就是对这种文艺理论分歧的科学解决。其次,虽然王先霈认为他并不清楚他与王元骧在文艺理论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却不能否认这种分歧的存在。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不少文艺理论家并不是不清楚一些文艺理论分歧的存在,只是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往往间接回应对方,而不是挑明分歧、主动进行论战。王先霈是否直接或间接回应了他与王元骧在文艺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与王元骧在某些观点上存在根本分歧。是搁置这种分歧还是努力解决,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能否长足而有序发展的关键。科学存在观文艺批评观是我们解决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观与粗鄙存在观文艺批评观的分歧的结果。我们梳理和总结王元骧与王先霈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分歧并促进当代文艺理论界解决这种文艺理论的分歧,就是为了推动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在理论上进一步地完善和丰富科学存在观文艺批评观。
王先霈在回应中还认为,文艺理论的分歧会“影响团结”“阻碍深化”“迷失方向”,难有同感;对我们期望的“重大文艺理论分歧彻底解决”不抱乐观态度,并且不以之为一定要追求的目标。认为文艺理论总是在分歧、讨论、争论中发展,越是“重大文艺理论分歧”,越难有“彻底”的解决;“彻底解决”了,没有了分歧,文艺理论不仅不能深化,反而必定会走向停滞。王先霈的这种反批评与我们倡导的又是相反的。我们明确地认为:“如果这些文艺理论分歧得不到彻底解决,就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的团结,并严重阻碍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深化。可是,有些文艺批评家却有意回避甚至掩盖这些文艺理论的分歧,各说各的话,各弹各的调。这种鸵鸟心态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失效乏力甚至迷失方向的重要主观原因。”[2]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认为文艺理论的分歧“影响团结”“阻碍深化”“迷失方向”,而是认为对文艺理论分歧的搁置和不能科学解决“影响团结”“阻碍深化”“迷失方向”。我们之所以要推动当代文艺批评界解决当代文艺的理论分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深深地感到中国当代文艺界不重视甚至轻视文艺理论。近些年来,当代文艺批评之所以没有出现飞跃发展,不是因为在数量上增加不快,而是因为在理论上不彻底有时甚至糊涂。当代文艺批评界的不少分歧虽然既有对一些文艺作品认识的差异,也有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追求不同,但从根本上说都是理论贫困的产物。当然,我们在推动当代文艺理论界解决当代文艺理论分歧上绝没有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王先霈没有特别分歧。不同的是,我们侧重强调了当代文艺理论界不从根本上解决当代文艺理论分歧的严重后果。
我们在概括王元骧与王先霈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根本分歧时认为王先霈过于强调文艺理论对文艺现象的适应和调整,而王元骧在抵制拍马屁的文艺理论的同时则强调文艺理论对文艺现象的批判和引导。“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上,文艺理论家王元骧与王先霈虽然没有直接交锋,但却有间接交锋。他们这种文艺理论的冲突就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虚无存在观与粗鄙存在观的对立在文艺理论上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能回避的文艺理论论战。”[2]我们和王先霈都认为文艺批评应从文艺现象出发,只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强调了文艺批评不能被文艺现象牵着鼻子走。而王先霈却在没有分歧的地方反复申辩:“文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就下判断,就做出结论,怎么能服人呢?”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的第一要务是把握文学现象的事实。“事实没有弄得清楚准确,却气势磅礴地褒贬,不容分辩地抑扬,即使文采焕然,又有多少价值,又怎么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多年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和大众文学接受的实际存在距离的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变;对于具体文本细腻敏锐的感受力,还强调得不够,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薄弱之处。”王先霈严厉批评的恶劣现象在不少文艺批评家身上的确时有发生。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赶场文艺批评家甚至宣称没有来得及看文艺作品或看完文艺作品,却敢口若悬河地对文艺作品指指点点。结果是当代文艺批评界中不少文艺批评无半句实话、真话和切中肯綮的话,而空话、套话和隔靴搔痒的话则连篇累牍。对这种浮夸不实的文艺批评现象,我们也是深恶痛绝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王先霈没有任何分歧,也不会臆造王元骧与王先霈在这一点上的分歧。与王先霈一样,王元骧明确地强调了文学批评应坚定不移地从文学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这一点,认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判的时候,文学批评“包含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这样双重的性质。而在认识与评价两者之间,认识是基础、是前提”。文学批评家的一切正确的评价,总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认真阅读和深入阐释而得出的结论。文学批评首先是一项科学活动,必须排除个人的主观好恶和偏见,坚定不移地从文学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3]。我们和王先霈的主要分歧在于我们还强调了不同时代的民族、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这是王先霈等不少文艺理论家所无意或有意忽略的。
首先,我们坚决反对文艺理论只是跟着文艺创作后面跑。文艺创作是不断创新的,文艺理论如果只是跟着文艺创作后面跑,就无法甄别有意义的艺术创新与无意义的艺术创作,就将既不能评判文艺创作,也不能引领文艺创作。有的文艺批评家认为文艺批评家应该有更开阔的胸襟,看到文艺作品的差异,看到作家、艺术家的千差万别,认为如果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多元化,多样化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这些文艺批评家完全被文艺现象牵着鼻子走,不管作家写什么,他们都照单全收,甚至盲目肯定相互矛盾的文艺作品。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洛夫在倡导对话文艺批评时指出:“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4]175在这个基础上,托多洛夫批评了教条论批评家、“印象主义”批评家和历史批评家,认为他们都只是让人听到一种声音即他们自己的声音,而历史批评家又只让人听到作家本人的声音,根本看不到批评家自己的影子。这都是片面的。而“对话批评不是谈论作品而是面对作品谈,或者说,与作品一起谈,它拒绝排除两个对立声音中的任何一个”[4]175-176。既然文艺批评不仅有作家、艺术家的声音,还有文艺批评家的声音,那么,文艺批评以及文艺理论就不能只是跟着文艺创作后面跑,不能“颂赞”满天飞。
其次,文艺理论不能只面对文艺现象,还要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统治阶级中间的分工时不但深刻地指出思想家包括文艺理论家在这种分工中的社会角色,而且深刻地指出这些思想家包括文艺理论家在这种分工中的社会责任。他们指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5]也就是说,思想家包括文艺理论家是从事精神劳动的,不仅积极编造自己的幻想和思想,而且还积极编造自己所属阶级或集团的幻想和思想。因此,这些参与编造他们所属阶级或集团的幻想和思想的文艺理论家不但要明白他们的社会角色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不是高人一等的,而且不能忘记他们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认为这是使统治阶级的思想独立化。他们深入地批判了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独立化的严重后果,认为这是社会虚假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根源。文艺理论家不仅参与编造所属阶级或集团的幻想和思想,而且还推动作家、艺术家编造和表现所属阶级或集团的幻想和思想。而文艺理论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审美理想就不全是文艺创作的概括和总结,还包含了不同时代的民族、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恩格斯在总结19世纪法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经验时提出了文艺应表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审美理想,这不仅总结了一切进步文艺的成功经验,而且承载了恩格斯对未来文艺的期许。1888年,恩格斯在批评英国女作家哈克纳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时指出,这部中篇小说只是表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即不积极地反抗、消极地屈从于命运,而没有表现工人阶级生活的积极面,即“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6]。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文学提出的这一审美理想显然不是既有工人阶级文学的总结和概括,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工人阶级文学的殷切期望。比恩格斯稍早,1847年,俄国伟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信》中要求俄国进步文学保留有生命和进步的新锐力量:“在这个社会中,一种新锐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决到外部来,但是,它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所压迫,它找不到出路,结果就导致苦闷、忧郁、冷漠。只有单单在文学中,尽管有鞑靼式的审查,还保留有生命和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文学上是这样容易获得成功的缘故。诗人的头衔,文学作家的称号在我们这里早就使肩章上的金银线和五光十色的制服黯然失色。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任何一种所谓自由倾向,甚至即使是才能贫乏的人的,都特别受到大家普遍关注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不管是真诚地还是不真诚地,卖身投靠正教、专制制度、国粹的伟大的才能,他们的声名立刻就会下降的缘故。”[7]在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种新锐的力量还处在萌芽状态之中。别林斯基是在批判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粹》时提出文艺要表现这种新锐的力量的。这无疑是当时俄国进步文学还没有完全实现的审美理想。直至1860年,在俄国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批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作品《大雷雨》时,俄国进步文学才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审美理想。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8]358。杜勃罗留波夫之所以高度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是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的价值并不是只在于力量的程度:我们引为重要的是,他在生活底普遍(要求)还是隐藏着、表现得很少而且很微弱的时候,就发现了它们的本质”[8]374-375。尤其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大雷雨》有一种使人神清气爽、令人鼓舞的东西,不但暴露了专制统治的动摇和日暮穷途,而且揭示出了一种新的生命,即卡德琳娜的反抗。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度肯定当时俄国进步文学所表现的新锐的力量,不过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那些压迫这种新锐的力量的顽固势力搏斗的延续。因此,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对文艺作品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不仅在文艺作品中汲取诗情,而且还从人类历史发展中汲取力量,即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如果仅仅局限在文艺作品里面,就不可能透彻地把握文艺作品并挖掘出文艺作品那些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而王先霈却以不是每个文艺理论家都敢于承当“深入地认识和科学地解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这种重大的社会责任为由推卸了文艺理论家本应集中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
王先霈在反思过去的文艺理论时认为原有的文学理论的立脚点太窄小了,而“理论能够到达的深度,与它据以出发的实际材料是单一还是丰富、片面还是全面关系极大”。在这个基础上,王先霈提出了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扩展范围,认为:“文学理论关注文学实践,需要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我以为,文艺理论研究依据于实际,既需要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还要着重于当前的文学实际;既要关注文人创作,即所谓雅文学,也要关注民间的、大众的文学,即所谓俗文学;既要着重于本土的文学,也必须参照域外的文学;既要关心文学创作的实际,也要了解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实际,了解不同人群的文学接受的复杂情况。”王先霈认为文艺理论关注文艺实践,需要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不能只看到、只关心、只承认一种形式,而应探寻对象的“各种形式”,关注不同形式之间的联系和转换。这是我们并不反对的。在文艺理论创造上,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文艺理论家甚至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而不被腐朽所同化。因此,文艺理论家不要先验地区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精华和糟粕,而应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作为文艺理论创新的养料,并在文艺理论创造中吐故纳新、推陈出新。而文艺接受与文艺创造则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有利于欣赏能力的养成的,即鉴赏力不是观赏一般的文艺作品而是要观赏最好的文艺作品才能够养成的,并且应以优秀的文艺作品为主。因此,我们和王先霈的分歧焦点不在文艺理论立足点的宽窄上,而在文艺理论对不同的文艺现象有无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上。
王先霈在强调每个文艺批评家心里要装着文艺世界的整体时,提出文艺批评家要意识到、要承认文艺世界这个整体存在,文艺理论的立足点应将浅俗、低俗乃至恶俗的文艺作品包括在内,即文艺史不能成为单纯的优秀文艺的历史。而王元骧则认为并非所有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是文艺的,文艺理论的立足点应是真正的文艺。显然,这是尖锐对立的。而心里装着文艺世界的全部、整体的王先霈不可能不看到他和王元骧的这种文艺理论分歧的存在,不能不至少间接地回应,除非王先霈根本不屑于关注王元骧的这种文艺本体论。这种假设对力求心里装着文艺世界的全部、整体的王先霈来说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王先霈认为他并未意识到他和王元骧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分歧,因而很难回应,也是不成立的。我们指出王元骧与王先霈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分歧,不是为了挑起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为了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正视并更好更快地解决这种文艺理论的分歧,迈上更高的发展阶段。
的确,文艺现象是丰富多彩的,并在时时变化中,文艺理论家不能不全面关注。然而,这种“文艺现象既有富有生命力的,也有即将灭亡的,既有健康的,也有畸形的,文艺批评家对文艺现象不可能不分好坏、真伪地都照单全收”。而“王先霈强调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承认文学世界的整体存在,虽然看到了文艺世界的联系,但却没有看到文艺世界的差别。王先霈所说的文学世界的全部、整体既有好的和真的文艺现象,也有坏的和不真的文艺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文学世界是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在这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文学世界里,文艺批评家如果承认文学世界这个整体的存在,即存在即合理,而不是激浊扬清,就不但放弃了真正的文艺批评,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中。”[2]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文艺批评家尖锐地批评了作家王朔的小说创作。作家王蒙、王朔在抵制和反击这些文艺批评时认为,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作家都像鲁迅一样“不见得太好”。而王先霈认为每个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要意识到、要承认文学世界这个整体的存在,不能仅仅研究成功的文学作品。可见,王先霈和王蒙等作家在文艺观上是步调一致的。而我们从王蒙文艺思想的转变中不难看出我们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王蒙在2013年终于从强调多样化的文艺转变为追求蕴含独到、高端的思想智慧的经典创造,“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从害怕中国当代作家都像鲁迅到为中国当代文艺界很难出现像鲁迅、茅盾这样的好作家而忧心忡忡,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坛除了要有给人挠痒、逗人笑的东西之外,更要有能提高整个社会精神品位和文化素质的文艺作品,认为这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所在[9]。作家王蒙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转变了,文艺理论家王先霈能否这样与时俱进?令人遗憾的是,王先霈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指责我们的批评不实。王先霈认为,他和其他文艺理论家都没有说过文艺理论研究要对文艺现象“不分好坏真伪地照单全收”。似乎我们的批评是不实的。无独有偶,文艺理论家陈众仪的类似批评更尖锐、更到位。陈众仪在辛辣嘲讽今天说这个好、明天又说那个好的文艺批评家时认为,卫慧、棉棉这批女作家“横空出世”时,文艺批评界有许多人追捧她们,还由此制造了一系列概念,诸如美女写作、私小说等等,在实际上起到了推手的作用,把文艺引向了一个可疑的甚至错误的方向。但当遇到外力干涉时,这些文艺批评家又转而不理睬这些作家了,甚或跟着臭骂一通。因此,陈众仪提出文艺批评家应“关注文艺现象,却并不被现象牵着鼻子走,不能把‘存在即合理’带入文艺批评、为现象当吹鼓手”。他坚决反对“有人一旦看好一个作家,不管对方写什么,都照单全收”,认为“这便丧失了文艺批评家的基本立场。文艺批评家如果只是跟着现象走,最后就会被层出不穷的现象所淹没”[10]。可见,我们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虚立靶标。王先霈认为我们不该把“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与“坏的文学”连接上,暗示我们将“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与“坏的文学”等同起来了。王先霈的这种反批评正好暴露了王先霈与我们的分歧。我们既不可能将“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等同于“好的文学”,也不可能将“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等同于“坏的文学”。我们之所以批评王元骧,就是因为他将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作品完全排斥在文艺以外了。我们只是认为这些“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中存在“坏的文学”,应该严格甄别出来,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重视研究这些“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是可以的,但却不可放弃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王先霈热情肯定文艺新生事物,对那些善于从被冷落的文艺新生事物中提炼、抽象出文艺理论的李贽、巴赫金、本雅明等文艺理论家非常推崇。这都是我们赞同的。的确,不少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在文艺史上虽然曾经遭遇一些文艺批评的质疑、否定和曲解,但最终确立这些文艺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却不是这些质疑、否定和曲解的文艺批评,主要是那些肯定阐释和深度开掘的文艺批评。我们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概括出了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生存的痛苦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21世纪初期提出中国当代青年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向,2013年又推动中国当代优秀作家艺术家的艺术调整。王先霈相当不满文艺理论仅仅研究成功的文艺作品,认为浅俗、低俗的文艺作品乃至恶俗的文艺作品都可以也应该作为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对象。这是极有见地的。但是,王先霈却忽视一些尖锐批评文艺新生事物的文艺批评的价值即这些文艺批评是文艺批评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没有看到有些文艺新生事物不仅是在肯定中发展和壮大的,而且还是在质疑中改进和完善的。这就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了。
在梳理和总结一些文艺理论论战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不少文艺理论家在文艺争鸣中既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已有的文艺理论成果,也不弄清各种文艺理论分歧的焦点,而是自说自话。这对于那些热衷引进和袭用域外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家是难免的。然而,这种文艺理论发展现状却既不适应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即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也很不利于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在文艺论战中,无论是王先霈还是王元骧,都是在没有完全弄清论战双方的分歧焦点时就自说自话。过去,在我们和王元骧围绕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展开的论战中,我们不是反对文艺的审美超越,而是不敢苟同王元骧仅仅从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层面上界定文艺的审美超越。而王元骧则反复申辩文艺存在审美超越和人类社会需要审美超越,而这都不是我们所反对的。因此,不少文艺理论论战往往不在同一层面上展开,而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出现了文艺理论论战的三岔路口现象。而我们和王先霈的文艺理论论战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在把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时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在积极汲取人类有益艺术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而王先霈则提出,中国当代文化界对异质文化既不要见异思从、见异思迁,也用不着见异思堵,见异思斥。我们和王先霈在对待异质文化上本来没有分歧,但王先霈却认为我们将“异己文化”“异质文化”一概作为排斥对象。这就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论战了。我们所说的异质文化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这种现象恰恰是在不同文化的广泛交流中产生的。如果我们完全排斥“异己文化”“异质文化”并将其堵在外面,就无异质文化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这些麻烦了。而任何民族文化在与不同文化广泛交流时都存在被异质文化同化的可能,这种现象在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并不鲜见,我们对民族文化发展提出这种警惕是很有必要的。难道这还要遭到“维护意识形态”的揶揄?文艺理论的发展不是无序,而是有序的。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之所以出现混乱无序的发展状态,是因为不少文艺理论家不能科学总结和深刻把握文艺理论发展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尊重文艺理论的创新和推进文艺理论的发展。在这种浑水摸鱼的无序发展状态中,文艺理论论战既可以弄清文艺理论界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分歧焦点,也可以凸显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发展上的独特贡献。这是我们不得不参与文艺理论论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1] 王先霈.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的品格[J].江汉论坛,2014,(2).
[2] 李明军,熊元义.理论分歧的搁置与文艺批评的迷失[J].江汉论坛,2014,(2).
[3] 王元骧.文学原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4.
[4]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3.
[7] 别林斯基选集:第6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71.
[8]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9] 王蒙.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J].读书,2013,(10).
[10] 陈众仪.重构当代文艺理论[N].文艺报,2013-02-18.
2015-01-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论”(14AA001)
熊元义(1964—),男,编审,文学博士,从事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