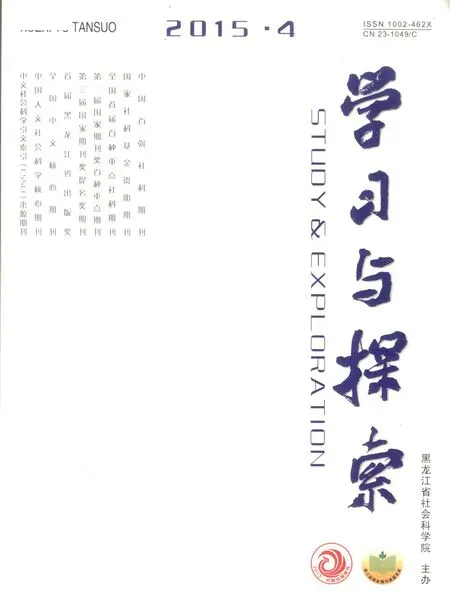患者生存机会丧失的侵权法救济及其界限
2015-02-25刘洋
刘 洋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杭州 310008)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患者生存机会丧失的侵权法救济及其界限
刘 洋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杭州 310008)
当患者因自身疾病恶化及医方不作为的过失行为相结合而丧失生存机会时,该生存机会代表的延命利益应受到保护,应将其纳入生命健康权的名下予以救济。此种侵权责任的成立应具备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失及致害行为,其中损害事实指生存机会本身;事实因果关系应采用替代法判断,并可产生全有全无的法律效果;过失的认定应结合医疗水平论而展开,在划定赔偿范围的阶段,赔偿的对象是患者所受的财产、非财产上损害,应采用比例因果关系规则、并依医方过失在损害后果发生中的参与度确定具体数额。侵权法对生存机会的救济应当保持谨慎,须经此上述三重机制的过滤,以确保医患双方的利益平衡。
生存机会丧失;侵权责任法;医疗纠纷
为应对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医疗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专设第七章,就医疗侵权法律关系中的基本问题做出统一化规定。《侵权责任法》乃是以医疗活动中的常见状况及典型纠纷作为预期的调整对象和所设规则的理想适用模型的,但在复杂的医疗实践中,各种非典型的例外状况则层出不穷。对此,前述既有规则可否畅通无阻地适用,则难免存有疑虑,适例之一即体现为患者生存机会丧失的案型。详言之,若病人就医前即已罹患致命性疾病、且根据医学统计资料该疾病的存活率(即生存机会或治愈率)低于50%,而其就医之后医方存有延误治疗、诊断偏差或其他不作为疏失并最终导致患者死亡结果时,侵权责任法应否为患者提供救济并向医方课以侵权责任?*在此须对如下问题予以说明:其一,患者罹患某种疾病后的存活率,是根据医学临床实践的统计资料而得出、并由医疗专家做出判断的,本文将此作为讨论展开的基础;其二,本文不拟讨论患者生存机会高于50%的情形,因为此种情况本可直接依据传统的侵权责任理论予以规制,且患者在提出优势证据以谋求救济的问题上并无严重障碍,而在患者生存机会低于50%时则否,此时患者无法满足传统侵权责任理论框架所要求的优势证据标准,故有必要探求新的救济途径和调整模式;其三,本文将患者生存机会降低至零(即死亡)的场合作为讨论原型,但“生存机会丧失理论”的适用范围亦可扩展至患者存活率降低特定比例而非完全消灭的情境。就此案型,其中存有疑问并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其一,此种有限的“生存机会”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的权益客体?其二,如若予以侵权法救济,则在判断责任成立与否的层面,其中的损害后果、事实因果关系与过错又当如何认定?其三,在认定责任成立后,医方的赔偿范围又当如何确定?
同时,也须注意到,中国正处于医疗体制改革及整体社会转型阶段,医患关系紧张,这就要求在医疗法律问题处理上必须兼顾医患双方的利益诉求,把确保两者的地位平衡作为根本基点,而非将法律的天平一味向患者倾斜。是故,本文将以中国司法实践中对此案型的处理为基础,从平衡保护的视角出发,期盼能一方面为患者疏通救济管道,也兼顾医方地位的保障,防止责任的泛滥,明确侵权法为生存机会提供保护的边界所在,促成法律的妥当适用及社会整体效果的达成。
一、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保护客体的证立与克制
在生存机会丧失的案型中,欲为受害人提供侵权法上的救济,则必须就生存机会作为侵权法保护客体的法律地位进行证立和阐明。如此,方能为患者的救济提供足够的正当性基础;否则,就是对侵权责任制度的滥用及民事主体行为自由的肆意剥夺。显然,生存机会并非《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列举的18项具体民事权利之一。然而,生存机会的丧失意味着患者原本可享有的、在医方实施有效救治情形下即能维持自己生命延续与生命安全为内容的生命权遭受侵害[1]。准此以察,生存机会似乎又可被纳入生命权的内容要素之中,从而归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利序列。此外,亦有可能将“生存机会”纳入该条款中“利益”的外延覆盖之下,进而运用侵权法予以保护和救济。但是,医方亦可抗辩:患者本身已罹患致命性疾病,即便施救也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免于死亡的最终后果,亦即患者死亡后果的根源仍在于自身疾病,而医方的不作为只是未能舒缓病情,或者未能推迟此一结果的到来和发生而已。故此,若单从后果发生的必然性与难以避免性上观察,又似乎患者并无任何可受侵权法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当无获得侵权法救济的道理。
可见,生存机会在侵权法上的地位与定性问题面临多重解释的模糊与困境。在此背景下,如欲要求医方为患者生存机会的丧失承担侵权责任,就更须慎重和考虑医方的正当抗辩,并提供充分理据。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外司法实务中对此问题的应对策略。
就中国司法实践而言,笔者以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公布的案件为样本,分别以“生存机会”和“存活机会”作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共搜集到关于生存机会丧失的案例7起:(1)朱某某等诉A医院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2)徐民一(民)初字第6222号民事判决书。(2)梁某某等诉柳州市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2)鱼民初(一)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3)廖某某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参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1)虹民一(民)初字第5121号民事判决书。(4)牛某等诉上海长海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1)杨民一(民)初字第6823号民事判决书。(5)彭泳钧等诉溆浦县康复医院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参见湖南省溆浦县人民法院(2009)溆民一初字第997号民事判决书。(6)吴树曦等诉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参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1)思民初字第5166号民事判决书。(7)李某某等与富蕴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乌中少民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以上7起案例均来源于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其中在案例(1)、(6)、(7)的判决中,法院均明确将患者的生存机会纳入生命健康权的名目之下加以保护;尽管患者的死亡后果主要源于自身疾病,但仍要求医方就其过失所致的患者生存机会丧失比例或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就患者死亡的全部损害后果负责。案例(5)的判决虽仅指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未明确指出患者被侵害的到底是何种具体权益,但却引用了《民法通则》第119条作为裁判依据,而该条恰是关于侵害生命健康权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故法院的裁判逻辑亦是将生存机会作为生命健康权之内容要素的一部分而予以保护。与此相似,在其他三起案例中,生存机会虽尚未被剥离并作为独立的保护客体,法院也是认可了生存机会作为保护对象及其保护价值,只不过将其暂收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外衣之下而已。比如,案例(2)援引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案例(4)援引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6条、案例(3)援引的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而且,在上述案例(2)、(3)、(4)、(6)、(7)中均明确给予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这与法院将生存机会作为生命健康权之内容要素展开裁判和予以保护的思维逻辑也是一致的。此外,除案例(1)因法院否认医方过失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而仅判决予以“补偿”外,在其余案例中,赔偿项目与计算方式均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相应规则加以逐项认定的。这表明,法院确实承认生存机会作为保护对象的地位与价值,但还没到将其独立于现有的权利体系并单独保护的程度,而是仍置于人格权名目之下做出裁判,并根据生存机会被剥夺的比例和程度决定赔偿数额。
综上可见,存活机会系患者对未来继续生命的期待。它意味着患者在死亡时点上原本具有生存的高度盖然性,且在其后亦可期待自己生命可得续存相当之长度与期限,而医方的不当行为却使其本可于该时点存在和享有的“延命利益”被剥夺。对于患者此种客观存在、现实可享的利益,自然应当予以肯认并定性为受侵权法保护的对象。但要指出的是,“生存机会”之用语并非中国《侵权责任法》中正式使用的规范性概念,亦未在现行立法中得到正名,而毋宁只是学者进行理论探讨时用以描述生命权之内容要素而使用的分析工具。不惟如此,在解读这一概念时,还必须时刻注意医方职业环境的维护及正当诉求的保障,防止医方责任的畸重及民事权利体系的泛化。
所以,就此案型中保护客体的确定而言,生存机会中承载的延命利益固然应予保护,但救济患者并不意味着打压医方。相反,应当注重当事人的地位平衡及规范体系的联动效应,在不突破现行民事权利体系的格局下,借助于理论和实践均已相当完善成熟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概念名称与操作逻辑,实现对生存机会的实质性保护。如此,则可兼收如下效果。其一,生命权属于《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列举和予以保护的权益客体,可消除“生存机会”是否属侵权法保护对象、能否获得侵权法救济的疑问,这也就很好地疏通了救济患者的通道。这既符合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中“以受害人为中心、权利救济为本位”的根本价值取向[2],也可顺应人格权保护强化及其内容要素不断扩展的国际性发展趋势[3]。其二,使生存机会这一新生概念必须接受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既有术语的检验,其救济亦须经由《侵权责任法》的规范体系和既定框架而展开,这就能有效防止其在具体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随意性及模糊性,从而防止权利概念的空洞化或者对医方的不当苛责,并维持现行民事规范体系与医方执业环境的稳定。经此界定之后,患者所丧失的生存机会即可被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和第54条应予救济的“损害”,并以《侵权责任法》第54条作为请求权基础提出诉求,主张相应的损害赔偿。
二、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的责任成立与边界划定
尽管生存机会应受侵权法的保护,但只有当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加害行为这四要件完全齐备之时[4],方可判定医疗侵权责任的成立。否则,就应当将之过滤出去而不得向医方苛加莫须有的责任,以求确保医疗关系中两造地位的平衡。故下文将围绕此案型中责任成立与否的问题,分别就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三个要件予以分析,*鉴于医疗损害责任中的加害行为要件较为容易判定,故本文不做详细探讨。以期澄清患者寻求救济时应负的举证责任,划定医疗损害责任的边界所在,确保责任认定上的妥切性。
(一)责任成立阶层的损害要件及其限定
损害事实乃是侵权赔偿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正所谓无损害即无赔偿[5]175-176。但在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决定医疗损害责任成立与否的损害要件指什么?是患者丧失的“生存机会”本身、伴随“生存机会”丧失而生的死亡后果,还是接续死亡后果而生的财产及非财产上的损失?
该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侵权法上损害概念及其内部构造的澄清为基础。为此,应将“损害”拆解为“侵害损害”和“结果损害”两个层次。前者乃是从被侵害客体(权利或利益)的角度观察,侧重事实属性,并指代与侵害(如身体损害)密切结合、不可分的损害(如受伤本身)之现象[6],从而在侵权责任制度的规范结构中被用作判定责任成立与否的要件;后者乃是从权利或利益被侵害后所生的效果角度观察,侧重价值取舍,并指向前一层次的权利侵害给受害人造成的财产上、非财产上之后续衍生性损害结果,从而应在侵权责任制度的规范结构中被用作划定赔偿范围大小的要件[7]。这种拆解观察的分析进路,亦在中国台湾地区[5]、日本[6]、德国[8]、美国[9]侵权法的体制中得到充分的支持。而在中国,也有学者基于对侵权责任传统构成要件的反思,提出对《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文义进行重构,把该款规定的“权益侵害”作为一般侵权责任成立层次的独立构成要件、结果损害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附加构成要件,并在责任成立之后的下一个阶段(即划定赔偿范围的阶段)对其展开认定[10]。这对侵权责任要件的框架结构无疑是一次纯化,而且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依此逻辑,在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判定医方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阶段,应以患者被剥夺的生存机会本身作为其中的损害要件;至于最终的死亡后果,其根源则仍然在于患者自身疾病的恶化,并不是医方诊疗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亦非可经由侵权责任谋求救济。否则,如果将患者死亡的最终结果完全归因于医方,显然是不当地过分加重了医方的负担,并错误地掩盖了疾患本身在死亡结局的出现中所发挥的作用力因素。同时,一如前文在论证应受侵权责任制度保护的权益客体时所示,在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实质的保护对象乃是由生存机会所表征的“延命利益”及“生命续存期间”,故不能将患者死亡的整个结果完全苛责于医方,否则必将导致最终在界定赔偿范围时过度赔偿。至于其后出现的财产上、非财产上损失,则性属由第一次的“侵害损害”波及影响从而引发的“二次损害”,对此,应当置于下一阶段在算定赔偿范围的过程中根据合理的价值考量及机会减损的比例予以确定,而非用作判定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要件。
(二)责任成立阶层的因果关系及过滤作用
在判断责任成立的阶段,事实因果关系乃是重要的筛选机制。但在中国实务中,前述6起案例的判决书在认定责任成立时并未将因果关系问题作为说理的重点加以充分展开,且其中逻辑理路也都基本一致。除了案例(5)的判决书明确指出医方的医疗过失与患者丧失生存机会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之外,其余案例中,法院均是在认定存在医疗过失或者医方违背其作为专业人员而应尽的善管注意义务之后,便径直肯定医方的过失不当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进而责令被告承担相应比例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论证显然有避重就轻的痕迹,从而难以令人信服。分析该案型特点可知,其实属不作为侵权类型,此种场合下事实因果关系的检验应当借助替代法(substitution method)为之,而非排除法(elimination method)[11]。亦即不应当从“是否加害行为导致了损害的发生”(排除法)的角度观察,而是应当从“如果被告达到了应有的注意程度、实施了其应当实施的作为行为,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替代法)的角度来理解。若被告实施了其应当实施的作为行为,损害后果不会发生或者可以减轻,则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认为存在因果关系[12]。
但也应指出,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性在于,疾患本身构成了因果关系链条上的介入因素,从而导致患者极易因为无法证成医方不作为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败诉。这也体现了事实因果关系在责任成立问题上的过滤作用及其对医方的保护效果。然而,若原告能够证明被告负有特定的保护义务,且该保护义务的本旨正是在于保障处于其保护下的对象免受介入因素的损害,或者制止处于其控制下的介入因素侵害他人,那么,所谓的介入因素(比如受害人自身因素、第三人行为等)就不会阻断被告的消极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3]。而此种积极保护义务的来源,可以是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之延伸,甚或社会一般生活常识等。因此,在医疗服务合同中,医疗机构负有运用医疗技术、遵循医疗常规为患者诊断和治疗且须善尽必要的注意,尽心尽力为患者排忧解难之主给付义务[14]。而该义务的本旨正是排除疾患等介入因素对于患者身体健康的侵袭与损害,因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会因为疾患因素的介入而中断。
(三)责任成立阶层的过错要件及限责功能
医疗损害责任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的规范体系内属于过错侵权类型,所以责任的成立还必须以过错的存在为前提[5]11-13。而在判定医方是否违反义务并据此认定过错时,其具体操作又必须结合医疗水平展开,并相应地接受医疗水平的合理限制[15]。这对于维护医方执业利益、限制侵权责任的过分扩张,并在医患双方之间合理分配风险至关重要。比较法上,医疗水平在美国经历了相对化的地域标准向绝对化的全国统一标准的发展历程,而日本的医疗水平论则恰恰相反,经历了绝对化到相对化的发展过程。两者之间所以形成此种差异,实则与其各自不同的医疗体制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在解读中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的“医疗水平”时,无疑亦须结合中国特殊的医疗体制予以展开方属合理。
对此,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已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考核和培训制度,继续教育制度以及全国统一的临床诊断和治疗规范,但医疗技术的普及存在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地域也是影响新的治疗方法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可将医生所处的医疗环境甚至地域作为判断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的衡量因素之一。这在对乡村医生与普通医生采取不同考核办法的做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验证。具体而言,对诊疗规范中已有明确要求的诊疗行为以及一些属于基本性操作的诊疗行为,并不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别;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病情的诊治,或者实施于特定场合的医疗行为,则可以在判定过错时纳入对地区等因素的考量[16]。依此逻辑,在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若医方行为符合当时医疗水平的,便不存在过失,当然不应予以责难。司法实务在处理此类案例中也均是根据当时的医疗水平展开医疗过失存在与否的认定,再在完成该基础性步骤之后进入其他环节或其他要件的证成的。比如前述案例(1),医方处理措施虽有些微不妥,但在患者死亡方面并无过失,法院进而以此为由否认了因果关系的存在。由此,以医疗水平为标准评判医方是否存在过失,再认定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否,也是侵权法救济生存机会的重要界碑,并能够很好地限定医方责任的界域边缘,防止滥诉风险。
三、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的赔偿范围及限度
在判定责任成立的阶段,只是在客观事实的层面弄清已存在的损害现象到底源自何处、因何而生。但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后,还必须借助于“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工具,并更多地顾及利益衡量、价值判断等诸多因素的动态影响[17]来划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患方遭受的损害结果纷繁多样,其中究竟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与医方的不作为疏失之间存有所谓的“法律上因果关系”?
就此问题,考察前文统计的中国司法判例,除去案例(1)中因医方没有过失无须负责外,其余的5个案例裁判说理的进路均是:依托医学鉴定对医疗过失参与程度的确认,判决被告承担比例赔偿责任。可见,司法实务均是考虑到:医方侵害的对象仅是患者的生存机会和存活概率,而患者生命的丧失则根本上是源于自身疾患,亦即患者因生命丧失而生的全部损失中并非全部源于医方行为,而只有确实因生存机会或存活概率被剥夺而产生的那部分才源自医方行为,才应作为损害赔偿责任救济与填补的对象。也就是说,只应根据医方过失在损害后果发生中的参与度或者原因力大小,责令其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
考察比较法,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中亦以医疗过失导致患者所失生存机会的比例乘以全部损害数额,再最终确定被告的赔偿范围[17]。
而在欧陆法的语境中,适用“全有全无规则”造成的“显失公平”的法律效果正遭到日益严厉的批评。Stark提出的质问便极具代表性:“在一个处在25%和75%之间的盖然性情况下,如果简单绝对地认定,加害人不承担任何赔偿义务或者承担全部赔偿义务,难道不存在任何问题吗?如果人们做出其明知无法知晓但却似乎知晓的决定,难道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不都是带来了不公平吗?”[18]3在此背景下,“机会丧失理论”应时而生,主张以机会丧失的几率计算赔偿数额,以求避免传统“全有全无原则”适用时仅因几率确定上的细微差别而导致结果完全相异的极端处理方法。至少从目前来看,该种方法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策略[18]683。
美国司法实务在面对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法律上因果关系”困境时,其处理策略经历了从“全有全无规则(all-or-nothing rule)”到“实质因素说(Substantial Factor Test)/实质可能性说(Substantial Possibility Test)”,再到“比例因果关系规则”的演变过程。对此演变轨迹,Makdisi教授指出,在此类因果关系不甚明确的案型中,赔偿效果确定上的“全有全无”路径必然与侵权法所欲追求的矫正正义相悖反,从而有害于侵权法阻吓被告不法行为之目的的实现[19]1063。进一步说,对于满足优势证据规则从而被肯定了因果关系、但事实上因果关系并不存在的案件,被告却要对本非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责,即承担过度赔偿责任;反之,对于不满足优势证据规则从而被否定因果关系、但事实上存在因果关系的案件,被告却逃脱了法律的责难和本应填补的损害,即形成威慑不足的局面,这自然是对侵权法预设宗旨的偏离[20]1073。但适用比例因果关系规则却不会引发诸此问题,它要求被告仅应对自己行为实际减损的法益价值负责,受害人自身疾患这一预设前提(preexisting condition)既然属于最终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理当对其造成的法益价值的减损(the reduced value of the interest)承担相应比例的份额责任[9]。这种理论在McMullen v. Ohio 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案中得以践行。*725 N. E. 2d 1117, Cite as: 88 Ohio St. 3d 332, 725 N. E. 2d 1117. McMullen v. Ohio 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 335.Ohio州最高法院指出:McMullen的生还机会虽受法律保护,但被告的赔偿范围则应根据其过失导致生存机会丧失的比例(即以最终损害的数额乘以机会丧失的比例)加以确定,而不应要求医方对患者遭受的全部损害结果一概负担赔偿责任。
综上可知,在为生存机会丧失案型求解的过程中,比例因果关系规则已成为各国或地区侵权法理论与实务的共同选择。而且实践证明,到目前为止,它也确实成为划定生存机会丧失案型中赔偿范围的最佳选择与妥当路径。因为它在保护患者生命、健康、身体等人格利益的同时,又能不失理性地顾及医方行动自由之保障,实则具有赔偿范围之控制阀的作用,从而在最终效果上能够确保“罚责相当”、防止偏倚或者失当,并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找到了利益的平衡点。
结 语
医疗活动中本已存有医疗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这就使得生存机会丧失的案型中极易出现请求权竞合的现象。对此,尽管根据《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受害人可以在契约上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之间择一主张,但需指出,从法律规范妥当适用角度而言,契约上请求权则应当处于优先检索的顺位[8],而不应撇开契约法律关系已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通道却径直跳跃到对于侵权请求权的检索适用。更何况随着现代社会中契约关系项下的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等合同义务群已成体系并日益丰富[20],债务不履行责任本身就能比侵权责任引致更加宽泛的法律效果,这就更意味着契约责任本身即已为患者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救济[15]。
另外,即便是允许当事人依据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提出主张,也尤须牢记如下戒律:侵权法既是一部有关责任的法律,也是一部有关无责任的法律,在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民事权益与维护人们的行为自由是同等重要的[21]。又加之,在中国侵权责任法律制度明显存在不断扩张趋势的背景下,就更有必要对于适用侵权法救济所谓生存机会丧失的案型保持克制,以理性的态度廓清侵权法与合同法之间的界线和分野所在[22]。否则,难免造成民法内部体系混乱、结构失衡的严重后果。为此,针对生存机会丧失的案型,必须经过前文详述的三重检验之后,方可以侵权责任机制向患者提供救济。否则,就只能将损害后果视为不具可救济性的意外风险而谨守“风险自负”的理念,并不得要求医方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以求维持医患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衡。而且,在这三重的责任过滤机制中,尽管所谓的“生存机会丧失理论”经由重新界定保护对象及损害概念(即将“生存机会”本身认定为保护对象及受损的法益)在一定程度上已优化了患者的境遇,但就判定责任成立阶层的事实因果关系与过失要件、划定赔偿范围阶层的比例因果关系规则来说,均要求患者一方承担充分举证的责任及举证不能的风险;同时,在规范适用上亦须接受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现行民事权利体系之原有保护路径的检验。这些无疑都能很好地发挥对侵权责任的限制功能,防止责任泛滥的风险,并可为医方创造有序而优良的执业环境,从而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以兼顾。
[1]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03.
[2]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以救济法为中心的思考[J].中国法学,2008,(4).
[3] 王泽鉴.人格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02-305.
[4] 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的具体判断[J].法律适用,2012,(4).
[5] 王泽鉴.侵权行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5-176.
[6] 周江洪.日本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述评[C]//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203-210.
[7] 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208-210.
[8] 梅迪库斯 迪.请求权基础[M].陈卫佐,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67-172.
[9] KING J.Causation, Valuation, and Chance in Personal Injury Torts Involving Preexist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Consequences[J].Yale L. J.,1981,90(55).
[10] 龙俊.权益侵害之要件化[J].法学研究,2010,(4).
[1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5.
[12]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3.
[13] 巴尔 克.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61.
[14] 韩世远.医疗服务合同的不完全履行及其救济[J].法学研究,2005,(6).
[15] 周江洪.服务合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71-480.
[16] 周江洪.侵权法背景下的医疗水平论[J].浙江社会科学,2010,(2).
[17] 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J].法学研究,2003,(3).
[18] 库齐奥 海.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J].朱岩,译.法学家,2009,(3).
[19] MAKDISI J.Proportional Liability: A Comprehensive Rule to Apportion Tort Damages Based on Probability[J].N. C. L. Rev.,1989,(67).
[20] 王泽鉴.债之关系的结构分析[C]//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2-110.
[2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J].中国法学,2009,(4).
[22]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功能定位、利益平衡与制度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
[责任编辑:朱 磊]
2015-01-10;
2015-03-10
刘洋(1991—),男,博士研究生,从事侵权法研究。
D923
A
1002-462X(2015)04-007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