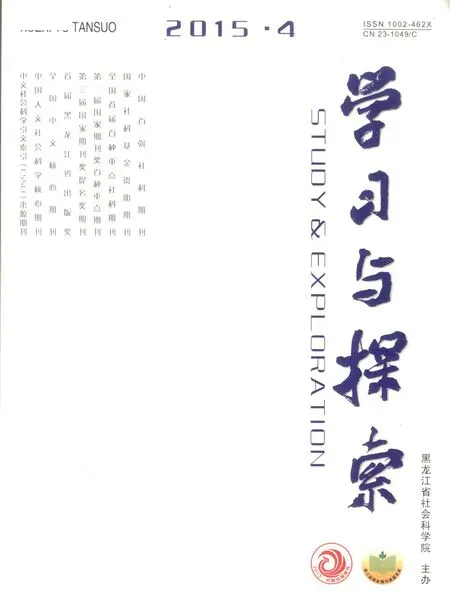新兴权利的证成及其基础
——以“安宁死亡权”为个例的分析
2015-02-25刘小平
刘 小 平
(吉林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长春 130012)
新兴权利的证成及其基础
——以“安宁死亡权”为个例的分析
刘 小 平
(吉林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长春 130012)
在新兴权利研究中,什么样的要求可以成为权利?这首先涉及具体权利的证成,即通过分析一项要求所提供的理由是否是内在理由来证成具体权利。其次,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内在理由的性质,即思考何为内在理由。何为内在理由取决于对权利是什么的认识,这与权利理论的论辩和建构息息相关。目前,中国的权利研究不仅需要在分析实证的层面上展开具体权利的证成,更需要一种权利理论为权利研究提供一个自己的理论基础。
新兴(新型)权利;内在理由;外在理由;安宁死亡权
一、导言:新兴权利标准缺失
新兴权利研究已经成为目前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方面,新兴权利研究试图回应新的时代背景下层出不穷的权利问题。不仅既有的权利体系已经无法涵盖日益增强的权利呼声和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而且在人的权利问题之外,动物“权利”乃至植物“权利”等自然体的权利也被广泛关注和加以讨论[1]。另一方面,新兴权利研究也是在理论上推进权利本位论的一种尝试。20世纪90年代以来,权利本位论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的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新兴权利研究试图从理论层面上的权利研究转向具体化、制度化的权利研究,从而推动权利本位论向纵深发展。
作为在具体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推进权利研究的重要理论尝试,新兴权利研究引发了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对权利问题的普遍关注,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的反思和批判。在理论层面上,有学者开始对已经成为中国“唯一正统学说”的权利学派及其权利话语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其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2]。还有不少学者引用美国学者格伦顿对美国权利话语的批判,认为权利话语会导致责任话语的缺失[3]。在实践层面上,新兴权利研究更是引发了“权利泛化”的担忧。人们担心,在权利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权利名目和名称被人们以当年“放卫星”的速度和规模制造出来,例如“亲吻权”“悼念权”“同居权”“容貌权”“养狗权”“视觉心理卫生权”“招聘权”“聊天权”“拥抱权”“抚摸权”“初夜权”“良好心情权”“相思权”以及被一些人关注和探讨的“乞讨权”等等[4]。
在笔者看来,对于新兴权利研究来说,实践层面上“权利泛化”的批判更应引起其足够的重视。因为对“权利泛化”现象的担忧指向了新兴权利研究必须直面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新兴权利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说,面对社会层出不穷的权利呼声和要求,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新兴权利?哪些主张和要求可以被认为是新兴权利,而另外一些要求和主张却不能被认为是新兴权利?新兴权利的研究之所以引起“权利泛化”的担忧,实质上涉及的就是权利的标准问题。一旦新兴权利的标准得以确定,“权利泛化”的担忧自然就会淡化乃至消失。
实际上,在姚建宗教授的《新兴权利研究》一书中,一定程度上已经注意到新兴权利的标准问题。书中姚建宗教授区分了权利之“新”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上,以时间和空间为标准来确定新兴权利之“新”;在实质标准上,则从纯粹的“新兴”权利、主体指向的“新兴”权利、客体指向的“新兴”权利和境遇性“新兴”权利四个方面确定新兴权利之“新”[5]8-13。然而,从这些论述中也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所谓的形式标准还是实质标准,集中关注的都是权利之“新”的标准,而更为核心的问题即为何可以称之为新兴“权利”的标准问题却基本上没有涉及;其次,对标准问题忽略的原因是姚建宗教授把新兴权利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描述性的问题。比如,在他所认定的实质性标准当中,他对纯粹的“新兴”权利、主体指向的“新兴”权利、客体指向的“新兴”权利和境遇性“新兴”权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以至于这些何以称得上是“权利”这一规范性的问题却被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而被忽略了。
因此,目前既有的新兴权利研究基本上是在描述性层面上展开的,对于何以称得上是新兴“权利”这一规范性问题,亦即借以区分“权利”与“非权利”的标准问题却付之阙如。正是由于确定新兴权利标准的缺失,目前对新兴权利的研究有导致“权利泛化”的担忧。新兴权利研究如果缺失对何种要求可以成为“权利”这一前提性问题的探讨,那么即使权利的字眼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其悖论性后果必然是权利的论证性力量和正当性却会愈来愈弱,甚至消失。因为在什么都可以成为权利的情形下,权利本身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么,什么是新兴权利的标准?新兴权利研究怎样才能实现“权利”与“非权利”的界分,从而确立其规范性内涵?在笔者看来,这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一方面,这是一个具体权利证成的工作;另一方面,这还涉及更为基础的工作,即权利理论层面的论辩和建构。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引入Alon Harel关于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区分[6],从而论述新兴权利研究如何在既有的实证权利体系下展开具体权利的证成。第三部分则借由对何为内在理由的进一步讨论而进入到新兴权利证成的更为基础的层面,即权利理论的论辩与建构影响甚或决定了我们对何谓权利的理解。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将以“安宁死亡权”的证成及相关争论为个例,以阐明新兴权利研究之不同层面的问题。最后,本文指出目前中国的权利研究不仅需要在分析层面上展开具体权利的证成,更需要一种权利理论为中国权利研究提供一个自己的理论基础。
二、具体权利的证成及其内在理由:以安宁死亡权为例
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增强的权利呼声和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新兴权利研究必须提供一个在作为权利的要求和不作为权利的要求之间进行区分的标准,即根据何种标准有些主张和要求可以被划归为权利,而其他可能同样具有一定价值的主张和要求却并不能被划归为权利。与对权利标准的探究相关,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提问方式:一种是哲学家们经常提出的问题,即是什么使得一项要求X成为一项权利;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提问方式是,是什么使得一项要求X成为一项更为基本的权利Y的一个实例[6]?显然,前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对权利之性质和基础的认识而后一个问题则相对不那么具有根本性,它是在存在一项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如何把一项具体要求划归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证成对它的保护,这涉及的是具体权利的证成问题。
就新兴权利研究而言,更为经常性涉及的是具体权利证成的问题。首先,在一个权利时代,我们对于何谓权利这一问题有了一定的前提性理解,在进行新兴权利研究时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对权利的性质问题做过于深入的探讨。其次,当前已经存在着一些公认的经典权利,并且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也有着权利法案和基本权利的规定。因此,新兴权利研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探讨权利的基础问题,而是进行具体权利的证成,也就是如何把一个具体的要求划归为一种权利。
(一)具体权利证成: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
为什么一项要求可能被划归为一种权利,而另一项要求只能被视为在提出一项重要且有价值的要求而不能归为基于权利的要求?在Alon Harel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证成这一要求所提供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具体权利的证成上,把一项要求界定为一项权利取决于构成这一要求之基础的理由[6]。
Alon Harel 由此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由:一种是内在于一项权利的理由,即那种由于它们而使得特定的要求被划归为权利的理由。另一种是外在于一项权利的理由,即那些影响一项要求应受保护的力量或重要性,但是对于把它划归为一项权利的一个实例却并非必要的理由[6]。
内在理由和外在理由的区分对于具体权利的证成是具有根本性作用的。一项要求只有其所提供的理由是内在理由,才能被划归为一项权利;如果所提供的是外在理由,则尽管这一要求可能是有价值并且值得加以保护的,但却并不是作为一项权利来加以保护的。因此,具体权利的证成依赖于所提供的理由是什么。只有内在理由,才能证成具体权利。
为了说明内在理由和外在理由之区分以及其在具体权利证成中的重要性,Alon Harel以美国围绕言论自由的相关争论作为例证[6]。有关争论很大程度集中在特定形式的言论上,例如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商业演讲等是否可以受到言论自由权的保护。反对意见认为这些形式的言论不能作为言论自由权加以保护。因为证成保护这些形式的言论的理由,比如通过诉诸促进经济繁荣来证成对商业言论的保护只不过是一些外在理由。这种证成有可能支持对商业言论予以非常严格的保护,但它并不足以提供一个将商业言论作为言论自由权的一个实例予以保护的内在理由。相反,支持的一方,比如保护色情作品的支持者经常基于对观念市场的作用来证成对色情作品的保护。“观念市场”不仅是一个证成保护言论的理由,还是证成把言论作为一项权利予以保护的理由。双方的论证都基于同样的预设,即在证成不受制于审查制度之要求的两类理由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第一类理由(内在理由)包括诸如自主或观念市场这样的理由。内在理由不仅证立要求不受制于审查制度,它们还能证成把要求作为一项权利的划分。第二类理由(外在理由)包括诸如规制色情作品的财政费用这样的理由,尽管可能会证成一项要求不受制于审查制度,但却并不是那些由于它们而使得要求被划归为一项权利的理由。只有内在理由与一项特定的权利相关联。
Alon Harel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在于,在实践推理中,内在理由发挥着与外在理由不一样的作用。内在理由是以一种统一的、超语境的、类似规则的方式运行的,而外在理由是以一种变化的、语境化的、排他主义的方式运作的。换句话说,决策者赋予内在理由独立于情境的统一的力度,而不是情境化地检验它们的力度。另一方面,外在理由的力度经常是在对特定情境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视情境而定的[6]。
(二)安宁死亡如何构成一项权利:内在理由
对于新兴权利研究来说,Alon Harel关于权利及其内在理由的观点为新兴权利的辨别和实质性证成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理论上的证明方式。通过诉诸具体权利的证成这一理论过程,即如果一项要求提供的是内在理由的话,就可以称得上是一项新兴权利;反之,如果其提供的只是外在理由的话,那么尽管这一要求可能有价值且值得保护,但却不能作为一项新兴权利加以保护。因此,面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要求和主张,可以诉诸一个富有操作性的清晰的论证过程来确定它们究竟是否是一项新兴权利。本文将以关于安乐死的论辩为例来说明安乐死的呼声和要求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被试图论证成为一项(新兴)权利,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才有可能被归为一项(新兴)权利。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的,原意是指舒适或者无痛苦的死亡。自安乐死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息过。因为尽管对于作为生物体的人类来说死亡是一种自然宿命,但是当死亡成为一个选项的时候,其正当与否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哲学、道德乃至法律上的难题。关于安乐死之正当性的种种讨论,其初始目的就是要把安乐死除罪化和合法化。因为安乐死涉及生命的放弃和终结,而生命权被公认为是最为根本的权利。一个思路就是为安乐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得尽管安乐死与对生命权的保护不相符合,但是由于对生命权的保护被这一更为重要的理由所超越,因而是一种正当的侵犯(infringement)。*Judith Thomson区分了(可允许的)权利侵犯(infringing)和(不可允许的)权利违犯(violating),前者是基于正当的理由而对权利的侵犯(infringe),而后者是一种不当的违犯(violate)。参见Judith Thomson, The Realm of Righ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对Judith Thomson理论的阐述可参见F. M. Kamm,Rights,in Coleman and Shapiro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78.确实存在着一些可能证成安乐死的理由,比如减轻病人痛苦、为了病人自己的利益,以及并不损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等。但是,要想找到一些能够凌驾于生命权之上的更重要的理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与生命权这一根本的权利相比,这些理由全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另一个思路就是将安乐死的要求本身就归结为一项权利,作为一项权利的安乐死,证成其存在的理由不仅与生命权不相违背,而且还可能是内在一致的。什么是安乐死成为一项权利的理由?显然,减轻病人痛苦、为了病人自己的利益,以及并不损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等各种考量不仅在安乐死问题上不足以使之正当化,而且对于安乐死作为一项权利的证成来说,也只是一些外在理由。把安乐死界定为一项权利,需要一个内在理由。在对安乐死的权利证成中,支持安乐死作为一项权利的内在理由在于它反映了作为根基的康德的自主性原则: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能在未得到个人同意的前提下,为他人的目的而牺牲和利用他们。在康德那里,“如果一个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的意志不为外界因素所决定,而且这个行动者能够仅依据理性而应用法则于自身,那么他就是自主的(autonomous)”[7]63。
显然,如果有人认为具有行为能力的病人可以在医生的协助下安排自己的死亡,那么他就是在诉诸自主原则[8]181。在个人自主这一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下,选择死亡作为一个权利可以在道德上加以证成。既然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主原则基础上的,自主的个体在其生命的尽头完全可以期待人们尊重他/她的个人意愿和需求,只要这种个人意愿和需求没有伤害他人。相反,如果不顾病人的个人意愿或者认为病人对死亡的选择不能代表他/她的最佳利益,则是对个人自主和尊严的侵犯,在道德上得不到支持。因此,在自主原则下,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权利和自由去支配自己的最终命运。例如有权拒绝医疗,这一权利也应包括自由选择死亡及走向死亡的方法,甚至在必要时按其意愿请求他人帮助自杀。
基于自主这一内在理由,安乐死作为一项权利在道德上得以证成。事实上,安乐死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权利的层面,而且已变成一种制度层面的法律权利,在现实权利体系中享有一席之地。目前,在法学层面,人们推动安乐死或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所诉诸的基本法理就是“死亡的权利”(the right to die)[9]。比如,在美国宪法的语境下,1990年最高法院最早在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一案中指出,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为人们提供了拒绝通过医疗手段维持生命的宪法上的权利[10]。尽管在1997年最高法院在Washington V. Glucksberg*Washington V. Glucksberg, 521 U. S. 702, 735 (1997).和Vacco V. Quill*Vacco V. Quill, 521 U. S. 793, 807-809 (1997).案件中认为,无论是正当程序条款还是平等保护条款都不禁止各州把协助自杀的行为视为犯罪,但到了2006年,在Gonzales V. Oregon案中,最高法院又裁定布什政府制止俄勒冈州尊严死法案的行为是无效的,俄勒冈州的尊严死法案授权医生给那些忍受不治之症折磨的成年人提供致命的毒药。Gonzales V. Oregon同样援引了“死亡的权利”这一通常的法理,认为正当程序条款创造了一种实质性的宪法权利。由此,最高法院裁定,医疗行为包括医生协助自杀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这在事实上为各州承认“医生协助自杀”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后,华盛顿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佛蒙特州相继承认安乐死合法化。
三、新兴权利证成的基础:何种意义上的内在理由
如前所述,在新兴权利的具体证成中,内在理由是关键。如果一项要求提供的是内在理由,那么就可以划归为一项权利;反之,则该新兴“权利”不能成立。然而,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理由是内在理由(而另一个是外在理由)?根据什么来确定内在理由?或者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区分也总是确定的吗?内在理由总是固定不变的吗?到目前为止,新兴权利的具体证成过程只是告诉我们需要一个内在理由就可以证成一项具体权利,但内在理由之实质是什么、怎样才构成内在理由,或者什么决定了一个理由是内在理由,这些问题涉及新兴权利证成的深层基础,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究。接下来,笔者将以安乐死为例,来进一步探究内在理由。
(一)质疑“死亡的权利”:自主的迷思(myth)
在目前的论证中,基于自主这一内在理由,从而安乐死被成功地归为一项权利。这一“死亡的权利”类似于霍费尔德意义上的“特权”(自由权)[11]33。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由此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自主做出“生”还是“死”的决定。基于自主,安乐死不仅与生命权不相违背,而且可能是内在一致的。但是,对于运用自主作为理由来证成“死亡的权利”也存在诸多质疑。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个人自主的悖论。个人自主确实意味着个人有权支配特定的财产,有权选择自己的行为,甚至有着诺奇克所说的“身体所有权”。但是为人们所公认的是,个人自主从来就不包括有权奴役自己。换言之,有权自由并不意味有权不自由。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悖论,就是是否可以在自主的名义下实质性地损害自主呢?显然,以自主的名义把自己卖身为奴,在直觉上是有悖于自主原则的。“死亡的权利”同样是这样一种悖论性的存在。一方面,以自主的名义似乎可以推知,人可以根据自主的意愿选择生或死;但另一方面,自主又是以生命的存在为载体的,如果要维护自主,就必须保护生命。当自主所面对的选项是生命本身的时候,人还有没有自主性呢?“死亡的权利”是在践踏还是在维护自主的原则呢?举轻以明重,既然卖身为奴违背自主原则,那么放弃生命是否也与自主不相符合呢?举重以明轻,既然可以自主决定放弃生命,那是否也可以自主决定放弃自由呢?至少以自主作为支撑性理由来论证“死亡的权利”就是一件值得质疑的事情了。
第二,安乐死真的是理性的吗?在康德那里,一个人只有是理性的、有自身独立的个人意志,才称得上是自主的个体,理性是自主的前提。因此,安乐死一个重大的限制条件是必须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才能够实施安乐死,这是为了确保自主原则。 然而,安乐死真的是有理性的自杀吗?
研究表明,自杀与可医治的精神疾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尽管大多数精神病人不是死于自杀,但在欧洲和美国,有90%的自杀死亡者可以见到不同形式精神障碍的证据[12]。所以,当一个人选择自杀时,在很大程度上他并不是一种理性自主的选择,而是由于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对于那些罹患绝症,不仅要忍受病痛折磨而且还要面对离别、无助感、失去自控能力、对死亡的恐惧和悲伤的病人来说,大多数都会经历精神上的痛苦。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癌症患者的心理疾病问题[13]。有文献指出,部分癌症患者并非由于癌症侵袭而死,而是由于心理压力、不愿接受治疗而死,甚至由于绝望而自杀[14]183-185。在这种心理下要求安乐死,能说他们是理性的吗?理性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仅仅基于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自愿选择这一点就说他的选择是理性的,这显然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证伪。
另外,很多人选择安乐死是因为难以忍受疾病所带来的疼痛和生命质量严重缺失。然而,随着医学发展,通过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可以有效地解除大多数患绝症病人的痛楚,打消他们由疼痛而引起的恐惧和绝望。事实上,调查显示,姑息治疗的结果使俄勒冈州的一些病人改变了他们要求协助自杀的主意[15]。对姑息治疗的医生的调研显示,大多数参与调查者不支持安乐死和协助自杀[16]。基于此,安乐死也很难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第三,自主与社会的关系。诉诸个人自主论证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密尔式的原则:“这是我自己的事,与人无干”,或者说不伤害他人。但就是在这一点上,论证也很难站得住脚。首先,安乐死并不是真的“与人无干”。事实上,对于久治不愈无行动能力的病人来说,安乐死往往需要他人从旁协助,或者是由医生拔掉卫生设备,或者是提供致命的毒药,甚或其他更加积极的协助。既然如此,就很难说是真正纯属于个人自主的事情,而是涉及他人或公众的事情。其次,一旦从自主原则出发把死亡视为个人的权利,可能会得到损害自主的社会效果。很多人的担心可能是有道理的,即一旦安乐死合法化了,将会有很多还想活下去的人被迫选择结束生命。比如有些患绝症的人,可能会因为无形的压力或者愧疚而选择安乐死,以减轻其家庭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还有那些贫困而无法支付医疗护理费用的人,或者某些少数群体会面临“歧视安乐死”的危机,被巧妙地强迫“自愿”选择安乐死。最后,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会产生“滑坡”效应。也就是说,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其使用可能将延伸至其他类型的病人,比如患老年痴呆症或大脑退化或那些生来就有严重残障的唐氏综合症的婴儿。总之,个人自主本身都从来不是绝对的,一旦与他人的自主产生冲突,或者与公众或社会的目标及价值不一致,这种权利是否能够成立就需要加以审视和仔细权衡了。
(二)何为内在理由:权利人中心论VS共同善进路
上述质疑直指安乐死作为权利据以成立的核心——自主,并以此否定安乐死作为一项权利。然而,从质疑的角度来看,这三种质疑是不一样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和第二种质疑实质上可以归为一类,因为这两方面的质疑都指向安乐死是否真的是自主的。比如,第一种质疑指出自主走向极端可能会背离自主,如放弃自由、放弃生命等极端情形;第二种质疑则通过摧毁安乐死的理性基础来表明安乐死不是真正的自主。这两方面的质疑都否定了安乐死与自主的关联,由此,安乐死不能再以自主为理由来实现权利的证成。第三种质疑的角度与前两种不同,自成一类。它并不否定安乐死与自主存在关联,但是即使安乐死是自主的,也不能证成为权利。至少自主不能单独证成为权利,除非个人自主能够与他人的自主甚或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相一致。
这两类质疑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前一类质疑实际上并不否定自主可以作为与权利相关联的内在理由,只不过由于安乐死不是真的自主,所以不能利用自主来论证。而后一类质疑则是对自主本身是不是内在理由提出质疑,涉及何为内在理由的问题。在具体权利的证成中,内在理由充当了关键性的角色,一项要求如果提供的是内在理由,则可划归为权利。但是,什么样的理由才算得上是内在理由?这涉及对内在理由性质的思考,需要我们对内在理由做更加实质性的探究,这也在深层上构成了新兴权利证成的基础。
在前述对安乐死的讨论中,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两种对内在理由的不同理解:一种主张个人自主可以构成内在理由;另一种则认为不光个人自主,还得考虑他人的自主乃至于社会的层面。正是由于这种基本观点上的差异,导致对安乐死是不是一种权利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两种观点可以对应两种不同的权利理论:一种是以权利人为中心的权利理论(rightholder-centred theories of rights),*当前主流的政治和法律哲学在批判和反思功利主义的背景下,发展出了一种主张个人权利的首位性权利理论,用德沃金的话来说,就是“权利作为王牌”,以保护个人免于不受限制地对集体目标的追求。参见Ronald N. Dworkin,Rights as trumps,In Jeremy Waldron (ed.),Theories of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153.该理论认为保持权利的唯一正当理由源于权利人;另一种是拉兹的共同善进路(common goods approach)的权利理论[17]。拉兹认为,权利是根据它们有助于公共善(public goods)而得到证成的,这些公共善有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不单单只是权利人本身。这两种权利理论对于内在理由/外在理由的区分以其各自在具体权利证成中的作用并无不同,但是对于何为内在理由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按照权利人中心论的理解,自主完全构成安乐死这一要求的内在理由,从而能够从自主这一内在理由出发证成“死亡的权利”。但按照拉兹的共同善进路,诸个体意义上的利益(interests of individuals)及自主乃至于共同善才是最为关键的,如果个人的自主损害到其他人的自主乃至于共同善,那么没法从这一单纯的个人自主出发以证成“死亡的权利”。
因此,何为内在理由这一问题触及了新兴权利证成更为基础和实质性的层面。对于什么构成内在理由或者说内在理由的性质这一问题的探究,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具体权利的证成问题了,而是一个更加深层的对内在理由、权利的道德基础的探寻和建构的问题了。就像上述权利人中心论和拉兹的共同善进路两种理论的差别那样,不同的权利理论基于不同的基础有着不同的对内在理由的解说。
四、结语:需要一种权利理论(a theory of rights)
对于新兴权利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规范性问题是一种要求如何可以称得上是“权利”。这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进行具体权利的证成,通过分析一项要求所提供的理由是否是内在理由来证成具体权利。其次,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内在理由的性质,思考何为内在理由。这是更为前提性的工作。在本质上,权利是一种理论建构的产物,何为内在理由取决于对权利是什么的认识,这又与权利理论的论辩和建构息息相关。
目前,中国权利本位论自提出以来,有关研究方兴未艾。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是权利的观念研究。比如从义务本位模式到权利本位模式,权利代表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其二是权利的概念分析。权利本位论的重要贡献就是对权利展开语义分析,把权利建构成法学的基石范畴,并围绕权利义务为中心建构了法学的范畴体系。而随着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兴盛,对权利的实证分析和论证有望进一步发扬光大。就此而言,新兴权利研究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具体权利的证成工作。实际上,目前法学界尤其是部门法学对具体权利及其制度的关注和论证已经表明了具体权利的论证层面上的不断推进,只是在分析的工具、方法和论证层面上还需要进一步精细化而已。然而,在目前中国权利研究当中,唯有一个重要且更为基础的层面被忽略掉了,这就是权利理论的建构层面。在后权利本位论时代,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权利理论。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发生在中国的各种权利问题,为权利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具体到新兴权利研究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权利理论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思考和解决新兴权利的标准问题,从而引导我们探究内在理由的性质等根本性问题。
[1] 张文显,姚建宗.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5).
[2] 桑本谦.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J].山东社会科学,2008,(8).
[3] 宁立标.美国“权利病”的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读《权利话语》一书[J].学术界,2008,(5).
[4] 钱大军,尹奎杰,朱振.权利应当如何证明:权利证明的方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1).
[5] 姚建宗.新兴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 HAREL A.What Demands Are Righ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Rights and Reasons[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7,(1).
[7] BUNNIN,YU J.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8] DWORKIN R.Life’s dominion: an argument about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individual freedom [M]. New York: Knopf, 1993.
[9] RUBIN.Assisted Suicide, Morality, and Law: Why Prohibiting Assisted Suicide Violates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J]. Vanderbilt Law Review, 2010, 63 (3).
[10] SEIDMAN L.Confusion at the Border: Cruzan, “The Right to Die”,and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J]. SUP. CT. REV, 1991, (47).
[11] 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M].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12] 李占江.积极关注:精神疾病与自杀[J].心理与健康, 2006, (10).
[13] 袁宝兰.960例癌症病人精神行为状态分析[J].河南肿瘤学杂志,1999, (1).
[14] 张天泽,徐光炜.肿瘤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15] GANZINI L,NELSON H,SCHMIDT T,KRAEMER D,DELORIT M,LEE M,Physicians Experiences with the Oregon Death with Dignity Act[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0,(8).
[16] BROECKAERT.The Attitude of Flemish Palliative Care Physicians to Euthanasia and Assisted Suicide[J]. Ethical Perspectives, 2009,(16).
[17] RAZ C.On Liberal Rights and Common Goods[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5, 15(1).
[责任编辑:朱 磊]
D90
A
1002-462X(2015)04-006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