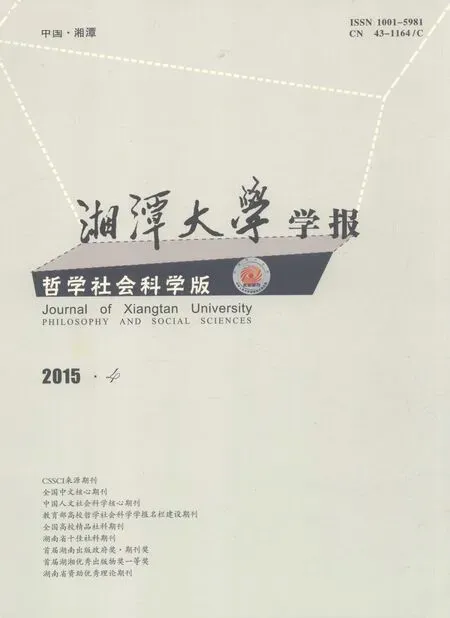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文学情感*
2015-02-22李志雄
李志雄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湘潭411105)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文学情感*
李志雄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湘潭411105)
摘要:在马克思成熟的宗教观中,宗教批判是一种常用的反思性武器,其特色是与马克思的文学情感活动相辅相成。对教会及其机构的腐败与反动的痛恨是与对人民及劳动在历史上的创造并以文学抒情般的爱戴而互衬统一的。对宗教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掩盖性的批判是与以审美情感方式对劳动者的赞美而对立统一的。对宗教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着力纠正是与以文学激情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来确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互助统一的。由此,从爱恨情感到审美情感再到文学激情,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文学情感是密切相联的。
关键词:马克思;宗教批判;文学情感
在对马克思的宗教观研究当中,我们确实没有关注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常是与其文学情感融合在一起的,以文学的爱恨情感来痛斥教会等组织的黑暗;以文学的审美情感来贬斥宗教意识形态的虚假,以文学的激情来冲破宗教历史唯心主义的藩篱,由此构成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内涵,具体论述如下。
一
马克思所生活的欧洲,基督教在帮助贫苦民众、关爱弱势群体、解救社会灾难乃至普及教育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基督教的历史,欧洲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然则,基督教作为宗教与其宗教组织并不是一回事,教会等机构的社会职责并一定是代表最需要帮助的民众的,信徒的具体实践与基督教的教义并不是永远统一的。由此,教会及其机构常存在着腐败甚至是反动的情况,这在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和法制腐败的国家尤为严重。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德国就是如此,德国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便染上了基督教病症,这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尖锐批判的:“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宗教改革之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仆。革命之前,德国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土容克和庸人的忠顺奴仆。……德国可以比作染上了基督教病症而且日渐衰弱的偶像崇拜者。”[1]10-11可见,当时德国的教会实际上已经成了官方的思想统治的武器,成了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宗教改革之前德国受制于罗马天主教的神权统治,改革之后路德新教蜕变为削减人民革命行动的精神鸦片,农民战争因遭遇神学而失败,如此等等,马克思对德国的宗教势力和教会组织等充满了无比的痛恨,对它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新奇的是,马克思以文学抒情的方式,甚至以艺术表演的方式来进行宗教批判。他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所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1]9-10这样鲜活的语言在一般人的政论文中是少见的,马克思的政论语言简直就是文学语言,“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四个排比,气势连贯,层层推进,情感起伏,抒情气氛浓烈。而那个冒用法国人口吻的一句话,就是滑稽的喜剧台词,令人忍俊不禁。人们可能想象不到,一位哲学家竟用这样俏皮的话来讽刺和挖苦,简直是一位文学家的手法了。即使是《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旷世名篇,开篇就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教皇,但其批判的语境竟是优美的文学意境,充满了艺术的审美趣味。“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1]271以幽灵来象征共产主义,以幽灵的游荡来象征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对幽灵的神圣围剿来象征教皇等旧欧洲的反动势力对革命运动的扼杀,他们把自己扮演成神圣的角色,而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污蔑为妖魔。马克思用这样的文学抒情来启动政论檄文实则是用文学想象来催发文笔,以文学意象来渲染批判的力度。所以,“幽灵”的确切理解是“被污蔑为妖魔的革命精神”,而不能想象为欧洲文学中常被描绘为“妖魔”的邪恶力量。
以形象而生动的语言来批判教会的反动本质和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这也是马克思运用文学情感来进行宗教批判的常有方式。在《反宗教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一文中,他详细记录了1855年6月25日爆发于伦敦海德公园的示威游行,事因是为了抵制《啤酒法案》和《禁止星期天贸易法案》,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英勇不屈,反映了英国教会的腐朽邪恶,马克思写到:“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说过,伏尔泰,给我们;弥撒和十一税,给人民。十九世纪的英国贵族说过,信奉上帝的话,由我们来说;执行上帝意志的事,由人民去做。基督教的古圣先贤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羞辱了自己的肉体,而当今有教养的圣者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羞辱(mortifies)民众的肉体。”[2]114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的话,尽管只是转引,但可看出他们共同的信教本质:口是心非、沽名钓誉、奸诈狡猾、奴役人民。转引、对照和比较,尽管不仅为文学的修辞而用,但加上鲜活的用词,描述得形象而生动,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具有刻骨铭心的效果。马克思接着描述下层民众的反抗行动和革命精神,他的用词达到了一种文学细致描述的极致,文学家恐怕都难以超越他的文学词汇量。“咕哝声、发嘘声、呼哨声、嘶叫声、咆哮声、怒吼声、低哑声、尖叫声、呻吟声、咔嗒声、呼啸声、咬牙切齿声,所有刺耳嘈杂的声音(cacophony)汇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恶魔般的音乐会!这是一种足以使人发狂、使顽石点头(move a stone)的音乐。真正古英国式的幽默和压抑已久的狂怒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爆发了。唯一可听清楚的喊声是:‘到教堂去!’有一位女士为使气氛缓和一下,从马车里递出一本精装的祈祷书。千百个人的声音像霹雳(thundering)一样回答:‘叫你们的马去读吧!’”[2]117马克思的文学才华从他所描述的12个关于人的叫喊声显露出来,这些词的细微区别,没有细致的观察,没有对劳苦群众的深切同情,没有对他们的由衷爱戴,应该是写不出来的。而且,马克思很擅长以幽默的口吻和戏谑性的对话来调侃或讽刺教会及其组织的虚伪和腐败等恶行,他所转述的民众的机智回答,“叫你们的马去读吧!”,让人捧腹,戏剧性的台词,堪称文学讽刺的典范。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一方面是对教会或宗教组织的反动和腐朽等的无情痛斥,另一面是对劳动人民或下层民众的勇敢和正直等的尽情讴歌,它们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宗教批判中隐含了道德赞美,是文学情感的审美方式,不是干巴巴的理论阐述。
二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第二个维度是对宗教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掩盖性的批判,这是一个提升,即由第一维度的对宗教的物质实体的批判上升到对其精神意识的批判。在他与恩格斯所合写的《神圣家族》中,他们以玛丽这位深受磨难的妓女为例,说明她被宗教感化、悔悟自己的“罪孽”、皈依上帝、进入修道院并在当修道院院长时死的光辉历程,实质上见证了她是基督教虚假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应于玛丽的个性,结果她死了。基督教的信仰只能在想像中给她慰藉,或者说,她的基督教慰藉正是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即她的死。鲁道夫就这样把玛丽花变成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成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3]224-225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生动地说明玛丽被欺骗的实质,他们归纳出玛丽形象的“罪女-修女-死尸”的三阶段,足以道出像鲁道夫之类的教徒,尽管他还是玛丽的亲生父亲,但也最终还是将自己的女儿欺骗至死。这样的欺骗看起来很温和也很文明,但终究是欺骗,它最终是对家庭关系和亲情等人伦法则的无情践踏,与冷酷的资本家以金钱至上而践踏了家庭成员或亲友生命没有区别,而教徒在资本主义风气中所形成的伪善本质,根本上是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275“神圣光环”与“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是生动而美丽的文学比喻,马克思对教徒伪善以及对宗教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都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宗教批判,不但借助于文学意象,而且创造出文学审美意象。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并不是永远中立的,总是有一定的社会倾向性,在阶级社会就有阶级属性,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并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98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顺应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就自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宗教的意识仿佛是来自“神”、“上帝”等超人间力量的意识,其实这些超人间力量的意识是虚幻的,实际上是来自人间,是对人间意识的折射性或间接性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4]162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阐释,任何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都具有阶级性,它反映一定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统治阶级总是力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阐释为被统治阶级的乃至整个社会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此来加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此意识形态就带有虚假性和掩盖性。宗教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反映阶级利益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归根结底在于它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要让人懂得这样的道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结合生动的文学形式来阐释这样深奥的理论问题,使读者能轻易地理解。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法国天主教如何成了以波拿巴为代表的金融贵族和工业巨头对人民精神奴役的工具。“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苍天是刚才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了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1]683马克思在这里对第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天主教会的讽刺是空前的,对小块土地的耕种者农民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当苍天这样的自然力对农业有利而农业丰收时,教士们不会干涉农民;当苍天不利而农业歉收时,一旦农民将抱怨推向苍天,教士们便开始干涉农民,马克思形容他们是“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一比喻太形象了,它把教士充当波拿巴政权奴役人民群众的走狗的丑恶嘴脸揭示出来,胜过千言万语。因而一个反动的波拿巴政权,连同它反动的教士阶层,他们是多么冠冕堂皇,实则是男盗女娼;他们是多么仁义道德,实则是虚情假意;马克思撕破他们的脸皮,让劳苦民众看到他们的真相。“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1]685从文学修辞来说这既是一个排比又是一个反语,气势联贯,情感强烈,讽刺入骨,批判有力,体现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文学特色,以强烈的审美情感来批判宗教的虚假意识形态。
马克思也喜欢用生动的文学审美来对人民群众反宗教的虚假意识形态进行赞美,他常以哲学来启迪人民群众的觉悟。当他还是青年黑格尔派时,所撰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以论战形式抵制了《科隆日报》政治编辑海尔梅斯关于禁止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的反动立场,维护了哲学干预现实生活和探讨宗教问题的权利。如他所论,“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过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和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5]219-220此处的“借代”修辞手法是何其醒目,他用“教士长袍”来借代禁欲主义,用“报纸的轻便服装”来借代《科隆日报》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动性禁止;他所用的比喻是何其的生动,说明哲学家不是像蘑菇一样轻易冒出来,而是时代斗争和人民支持的产物;他的三个‘最’的排比,展现了他激昂的文学情感所触发的宗教批判意识,因而,说马克思是高明的文学能手和睿智的宗教批评家一点都不为过。
马克思还很善于将揭露反动教士的丑恶嘴脸与赞美人民群众的觉醒意识结合起来,形成其宗教批判的双重力度,使这样的力度浸染在文学审美之中。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他针对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海·瓦盖纳的反动宣传,批判了普鲁士政府通过宣传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的险恶用心。“请注意,在国教顾问梳得溜光的头顶上开始露出狐狸耳朵来了。‘议会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原则的问题。’这条博爱的毒蛇多么圣洁啊!”[6]213溜光的头顶暗示国教顾问被普鲁士政府喂养得很肥,使他充当人民的代表,其狐狸的本性还是露了出来,他内心是毒蛇一般,但其外表是博爱的教士。而人民群众要识破他们的伎俩,无产阶级要觉醒。“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顺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6]218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批判与对无产阶级的赞美是同步进行的,两者的思想性格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对基督教的清醒批判中,无产阶级不但获得了食物的面包,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精神的面包。这样的审美境界,为马克思所构建,这样的宗教批判,为马克思所坚守。
三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第三个维度是对宗教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着力纠正与以文学激情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来确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互助统一。马克思是哲学家,他对宗教批判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哲学的批判。“……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1]1-2这里包含了马克思对宗教本质认识的三个层面:一是宗教与人的关系,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二是宗教与世界的关系,宗教是对世界特别是苦难尘世的曲折反映,看起来很神圣光荣,但并不能彻底解决苦难。三是宗教与真理的关系,宗教从根本上阻碍着人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认为宗教决定了世界、人、真理等一切客观存在,实质上是客观存在决定了宗教。对此,要将这样深奥的宗教哲学问题让民众懂得,马克思并没有采用枯燥烦琐的理论论证,而是采用形象生动的文学方式来进行宗教批判。马克思把宗教比喻成人民的鸦片,说明它能一时镇痛而不能永久解痛;还把它比喻成虚构的花朵,说明它没有实在的内涵;再把它比喻成虚幻的太阳,说明它曾竭力支持的“地心说”是何等的荒谬。如此,他所进行的宗教批判,是在构建了丰富文学形象的基础上,以文学审美的情趣来展示的,即:戒除鸦片、撕碎假花、驳倒地心说其目的是要矫正其历史唯心主义哲学观,让人们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
人们并不会马上就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由于宗教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长期影响和文化浸染,对人自己的本质还可能弄不清,误解人的本质就如同宗教所宣扬的“博爱”、“公正”或“信奉”等。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也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的,而是从具体而丰富的文学创作活动来开始的,文学创作激情是他体验什么是人的本质的实效渠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洞察到了人的感性并进而由此所形成的情感等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最终成就人的本质力量。“……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7]126显然,人的感性并最终发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厚重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人的感情是社会历史的,人的本质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生产活动中铸就并予以确证,这对人的情感构成肯定,使人产生愉悦,于是有激情的体验。“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因而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情感、激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7]169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人受动的特性,这是人成为感性的人的前提,如此人才有感受的功能和水平,才能被感动并提升为激情这种最强烈的情感,而激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人把自己视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这是动物所不具有的能力,人强烈追求自己的本质力量,这个本质,并不是人作为感性的人的特性,动物也是感性的;也不是爱、恨等情感的构成,任何一个阶层或社会的人都会有这类情感,这些都不构成为人的本质特性。
到底什么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质特性呢?这就要联系他对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此批判能深化对基督教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基督教的“宗教创造了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的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但仅以一切旧的唯物主义(如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去批判是不够的,而必须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去批判才彻底,因为它涉及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情感”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60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人的本质,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所谓神或是上帝的产物。他一方面彻底批判了宗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又具体回答了什么是体现人的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个具体性就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血缘关系到情感关系、从家庭关系到社区关系、从政治关系到经济关系等一切纷繁复杂的关系,最根本的是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存在性关系。宗教是属于上层建筑中的一员,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不仅是批判它本身,而是深入到它的根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去批判,因而其宗教的批判是最深刻的。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批判到其发展的内在机制中去了,而这样的内在机制又要结合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能一概而论。同样是基督教,马克思的批判是结合其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状况来进行的,他对资本主义时期的基督教和对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基督教批判分析不同而结论不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得出如此精彩的结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有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8]142新教、自然神教之所以是最适合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宗教形式,因为它满足了无所不在的商品交易和彻头彻尾的私有制的需要,甚至把人也可抽象化为可任意商品交易的符号,而这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行不通的,其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支持这样的交易关系。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基督教,它将人的本质抽干,干缩为路德所宣称的“因信称义”,实质上是迎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世界观;或是之后韦伯所洞见的“劳动天职”——“忠实的劳动最能使上帝愉悦,哪怕工资低廉且生活中没有其他谋生机会。……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获得恩宠确定性的最佳手段,归根结底往往也是惟一的手段。……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了现代工人的特征,一如对获利的相应态度成为了商人的特征。”[9]272劳动使上帝愉悦而不使劳动者本人愉悦、劳动是主动的行为却要获得恩宠的被动性批准、工人被驯化去创造使用价值和商人放纵去谋取交换价值,这些都被基督教的宗教世界观所容纳并被其宗教意识形态合理化和合法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扼杀,是对人的本质观的颠覆,是资本主义宗教病根。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从批判对象来说主要是基督教;从批判内涵来说主要是资本主义宗教的腐朽性、欺骗性和反动性等。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特色是具有强烈的文学情感,文学情感成为了他宗教批判的力量。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三个维度是层层深入的,从批判教会和宗教组织到批判宗教意识形态、再到批判宗教世界观,其批判的理论话语越来越抽象,但其批判的话语却是一如既往的生动、形象和鲜活。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修辞手法等,灌注其中是形象突出、想象丰富和审美绚丽的文学情感,马克思是非凡而高明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Karl Marx.Anti-Church Movement―Demonstration in Hyde Park In K.Marx and F.Engels On Religion[M].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5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万莲姣
Marx’s Religious Criticism and His Literary Emotion
LI Zhi-xiong*(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In Marx’s well-considered viewpoint of religion,religious criticism is a frequently-used introspective weapon whose characteristic is supplementary to his literary emotional activity.His hatred to church and its institution for their corruption and reaction both sets off and unifies with his love to the people and their work in historical creation by means of literary lyricism.His criticism to religious ideology for its falsehood and concealment both opposites and unifies his praise to laborers by means of aesthetic emotion.His strenuous rectification to historical idealism of religion both mutually aids and unifies with his affi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means of literary passion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human essential power.Thus,from love-hate emotion to aesthetic emotion then to literary passion,Marx’s religious criticism and his literary emotion are closely associated.
Keywords:Marx; religious criticism; literary emotion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马克思与基督教关系的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10YJA751039)及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马克思的文学情感与批判意识研究”(项目编号: 13JD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志雄(1966-),男,湖南湘潭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和宗教理论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01-30
中图分类号:I0-02; 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5) 04-01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