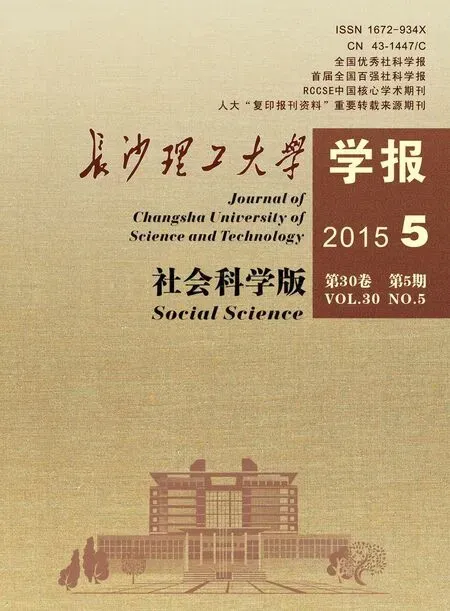狄金森笔下的上帝与不能感到的崇高
2015-02-22向玲玲
向玲玲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对外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狄金森笔下的上帝与不能感到的崇高
向玲玲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对外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狄金森创作了大量宗教主题诗歌却终生没有入教。从崇高与恐惧的关系出发,解读发现:狄金森“知道”上帝是崇高的,但对其无法克服的恐惧使她停留在习得的知识而无法实现从恐惧感向崇高感的转化;无法“感觉”到上帝之崇高的诗人,只能以世俗化或“人化”策略消解这种恐惧;对上帝的恐惧本质上是对自己有可能违抗上帝意志的恐惧。狄金森在形成崇高感的心理要素——“惊惧”、危险或痛苦、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后,在耶稣令人惊惧的受难事件和仁慈的替罪行为中实现了从恐惧感向崇高感的转化。
狄金森;上帝;耶稣;崇高;恐惧
一、存在着的上帝是崇高的
生活在浓郁的宗教环境,经历过数次宗教复兴的热浪,却终究没有把自己“交出去”的艾米莉·狄金森,并非没有郑重考虑过皈依的问题。这位以孤绝于世、特立独行著称的女诗人,也曾加入过小的祈祷圈,并在幼年时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救赎:“我从未感到过如此完美的宁静和幸福,在那段短暂的时期里,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救世主。”“我独自和崇高的上帝亲密交谈。”[1](P167)用“崇高”形容上帝,无疑是最正确的语法。何况,她深知宗教的慰藉和信仰的甜蜜:“服从的人幸福无比”(J1)①、“那必定就是太阳!……/一位身着灰衣的牧师——/轻轻拉起黄昏的栅栏——把善男信女们领去——”[2](J318)但是,一生创作了大量宗教主题的诗歌,却没能说服自己走出关键一步的诗人,不仅是宗教复兴运动中的冥顽分子,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罗杰·伦丁(Roger Lundin)在《狄金森与信仰的艺术》中考察了狄金森不入教的三个原因:不愿以任何公开忏悔的形式向众人做内心告白,而这种站出来分享喜悦的方式正是加入教会所必须的;未能从个人生活与体验中找到“圣恩”的果实,如“得救者”们通常宣称的蒙恩前后人生的巨大变化;自青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强烈的自我观念[3](P53)。阿尔弗雷德·哈贝格(Alfred Habegger)则将其在火热的宗教复兴运动中的纠结与矜持归结为“为捍卫人格独立而进行的顽强抵抗”[1](P163-164)。
这些分析,无疑都是建立在对诗人的人生轨迹与惊鸿一瞥的心路历程的深入理解与同情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浪漫时代的孩子,诗人的自我意识已充分觉醒,不愿因公共空间的压力而将复杂的内心世界以简单提纯的方式献给他人裁判,因为任何简化都必然变形;而同时作为一位忠实于内心体验和感受的诗人,她也不能接受自己不诚实或麻木敷衍,正如诗人曾在一首诗中批评的一样:“高声宣布/无关痛痒。”(J662)也就是说,即使免去组织化、制度化的公开忏悔的要求,她也不一定能说服自己皈依,因为她的确并不能“感觉”到圣恩在自己身上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终生没有皈依的诗人,却依然保留了向“三位一体”的神祈祷、寻求慰籍的习惯,虽然她的祈祷可能并不像教徒那样仪式化或有规律:“救世主!我无处去诉说——/所以就来烦扰你。”(J217)“于是——我就这样——祈祷——/伟大的圣灵——请赐予我/一个天国”(J476)“至少——耶稣啊——被遗留——/被遗留在空中——求告——”(J502)最有趣的是这首:“当然——我祈祷过——/上帝可曾介意?”(J376)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诗人在扮鬼脸,为自己作为“教外人士”而享用教徒权益的非授权行为而感到有些尴尬,自我解嘲。
也就是说,诗人并非完全不信上帝的存在。大多数时候,她置疑的并不是神的存在本身,而是神的存在方式。虽然偶尔“在更加冷静的时刻”,她也会说出“压根儿不可能存在摩西”这样近乎无神论的说法,但紧接着又为了老摩西所受的“委曲”(“让他看见——迦南——/而没有进去——”)义愤填膺地向上帝抗议,认为他不该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如同男孩——对付更小的男孩——”(J597)一般纠缠摩西,命他看着迦南福地,却不许他进去,因为这是比处死他更大的伤害。
这里,上帝是一个喜欢斗气、折磨人的“男孩”。再来看看上帝的其他画像:
我有一位默不作声的国王——(J103)
上帝是一位远方的——高贵恋人——/如他所说,通过他的儿子——求婚——/诚然,这是一种代理求婚——(J357)
天父领着特选的孩童/与爱远远分离,/常常穿越荆棘的国度/却不大经过温柔的草地。//经常是由龙爪/而不是朋友的手/把那命定的小孩/引向故土。(J1021)
沉默、遥远、高贵。大多时候不在场,连求婚都由人代理。而当他在场时,伴随而来的则是更大的考验。试想,“命定的小孩”由西方观念里通常作为恐怖大自然象征的怪兽、或如《圣经·启示录》第12章、20章所称的“古蛇”、撒旦的化身——“龙”的爪子相牵着回到“故土”乐园,将是一幅怎样的情景。
当然,从1 789首诗里选取几首出来,证明自己的任何观点都是有可能的。但至此为止,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了:第一,大多数时候,上帝是存在的,这是诗人创作大量宗教主题诗歌的前提;第二,诗人“知道”上帝是崇高的。而在这两个肯定的前提和一个否定的结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二、对上帝的恐惧即是对自己可能违背上帝意志的恐惧
在尚未彻底弃绝教会活动的青年时期,狄金森曾在一封信中对朋友说,一位来访的牧师“宣讲了死亡和审判,以及那些行为不端的人,意思是奥斯丁和我,会落得什么下场——不知怎的,这篇布道吓到我了。”“万劫不复这个话题不知怎的[让来访的牧师]很开心。在我听来它如此严肃。”[3](P69)圣经里关于不信上帝而受惩罚的故事很多,前文提到的摩西只能“观看”迦南而不得入内就是其中一项,而终极的惩罚还是在“地狱之火”、即“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接受“第二次的死”(或称“永不复活的死”)。《启示录》第21章第8节中所列举的将被投入“火湖”的名单中,“胆怯的、不信的”与其他如“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等一起赫然在列,怎能不叫人惊骇。
恐惧与信仰之间不无关系。世界各大宗教都有各种禁忌,譬如基督教忌讳的“偶像崇拜”、伊斯兰教徒在饮食、服饰各方面的禁忌、佛教徒的“五戒十善”等。宗教场所的肃穆、噤声,信徒们以跪拜、嗑头或嗑长头、诚惶诚恐的表情和声音对待神和神的象征,唯恐自己有冒犯冲撞的地方。另一方面,正如《福音书》中反复宣讲的“不要怕,只要信”,世间有万般的凶险困厄,但只要信了就能得依靠,只要把自己全部托付给主,就可以不再忧惧。至少对于内心来说,信了就能得安宁。
由此可见,恐惧既是信仰的形成条件,又是可以依赖信仰而克服的。正如康德在《审美判断力批判》中所分析的:“有德之人恐惧上帝,却并不由于上帝而恐惧,因为他把对抗上帝及其命令的意愿设想为他决不耽忱的情况。”[4]
但狄金森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因为怕,不能信。”差池似乎就出在这一个“怕”字:“恐惧——是上帝的引论——/因此——被奉为神圣——”(J797)“我的价值是我全部的怀疑——/他的功绩——是我所有的恐惧——”(J751)她“知道”上帝是神圣的,她知晓神的丰功伟绩,却置疑他是由于令人恐惧(而非其他,如狄诗中常用来形容耶稣的“仁慈”“怜爱”“巨大的牺牲与痛苦”等美好或深刻的品质)而被奉为神圣,因此连他的功绩都是令人恐惧的。
如果诚实的诗人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违背上帝的意愿,那么她就依然暴露在愤怒的上帝面前,即使已经通过某种仪式性的情感表达而被纳入教会的仪式场景之内,也并没有真正来到“安全地带”,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因为她的内心还在蠢动,还在作为独立的人格活动着:“‘父啊,愿你的意愿实现’/因为我的意愿走别的路线,/而它好像是背叛!”(J103)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脱“罪”的诗人有像力士参孙一样被挖眼睛或别的忧虑。但对于这些罪与罚的想象,狄金森是这样说的:“在被人挖掉眼睛之前/我喜欢看个清楚——”(J327)“所以会有——两个身体——/捆住一个——另一个就飞走——”(J384)“我依靠恐惧生活……//仿佛那是灵魂上的——马刺——”(J770)“明知故犯”的诗人似乎已不打算摆脱这种恐惧,且从这种恐惧中找到了前进(如果不是上升)的动力。看起来,诗人“灵魂上的马刺”不止这一颗,才会激励她保持着清醒的痛与激情,眷恋着尘世、描绘着永生,创作不辍。
也就是说,这种对上帝的无法克服的恐惧本质上是对自己的恐惧,是对自己有可能违抗上帝意志的恐惧,无论这种违抗来自理性的逻辑还是情感的冲动。如前文提到的第597首为了老摩西所受的“委曲”而向上帝打抱不平。深知自己已告别纯真年代的诗人,无法再像从前一样:“孩子的信仰新鲜——/完整——像他的原理——/宽阔——像照在/刚睁开的眼睛上的朝阳——/从未有过一点怀疑”(J637),以绝对的“信”和“服从”脱罪,从而真正摆脱恐惧。
三、不能“感觉”到上帝的崇高
关于恐惧与崇高的关系,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早在《诗评之基》(Grounds of Criticism in Poetry)(1704)中就提出,除了恐惧没有别的激情“能够赋予诗作以伟大的精神”[5]。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1757)中提出“崇高”形成的心理要素:“惊惧”、危险或痛苦、一定的距离。即首先在一种“惊惧”的状态下达到全神贯注,包括不再注意到除了占据心神的那个对象的其他芜杂事物,也不能“分心”对那个对象进行理性的分析;同时,这种危险或痛苦不能太近,否则就不能予人任何愉悦,而只是纯粹的恐惧[6]。
康德(Kant)则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直接提出了“安全地带”一说,认为只有当人们处于既可见恐怖,又不受恐怖威胁的安全地带,才能在“凝视静观的情调和完全自由的判断”的状态下使心灵的力量被“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从而使恐惧感转化为崇高感[4]。
很明显,狄金森并不在这个安全地带。恐惧常在的诗人如何能够“凝视静观”上帝的崇高与伟大,而不是心生畏惧、闪避、侥幸、幻想、绝望、抗争、蛮勇、或诸如此类的“杂念”?如果说从恐惧通往崇高之间有一座桥梁,这些“杂念”就像飞鸟衔来的野藤杂木的种籽,此处不该有,却已然已经有了,且在理性、情感等自我意识的浇灌下自由生长,直到长成阻断交通的天然路障,横亘在习得的知识与个人的感受体验之间,使狄金森“明知”上帝的崇高,却不能真实感受到他的崇高。
虽然从小浸淫于其中的宗教环境使狄金森大部分时间并未从根本上置疑上帝的存在本身,但却对他的存在方式颇有微词,同时也对自己极可能违背他不太公正、不太仁慈的命令和意志的自省而无法心生全信与依赖,由此产生的不可摆脱的恐惧最终阻断了诗人从人皆有之的对上帝的恐惧之心到达真诚宁静地感念上帝的崇高的释然之途。那么,对于无法摆脱的恐惧,诗人将如何处置?且先看看这一组:
天上的爸爸!/请关注一只老鼠/它在受猫的糟蹋!(J61)
“你若不为我祝福/我决不放你走”——生客!(J59)
我要发起一声“诉讼”——/我要维护法律——/天帝!选好你的律师——/我把“肖”保留!(J116)
或者叩击天堂——天堂——无人答理/那我就要骚扰上帝/直到他放你进去!(J226)
篱墙那边——/我能爬过——我知道只要小试一场——/浆果香甜!//不过——要是我把围裙弄脏——/上帝一定会痛斥责骂!/哎呀,——我猜假如他是个男孩——/要是他能——他也会——爬!(J251)
信是凡间的一种欢乐——/众神却无法得到——(J1639)
只有上帝——能察觉悲伤——/只有上帝——/耶和华们——决不多嘴多舌——(J626)
儿语(“爸爸”而不是“父”)、撒娇或耍赖、世俗的正义武器(法律)、骚扰、抬扛、诡辩、甚至使用复数指称至高无上的唯一神,虽然其中可能有“三位一体”教派理论的影响,但直呼“耶和华们”,却依然不免让人目瞪口呆。如果说修辞是一种武器,诗人在这里无疑将它用到了极致,似乎如此就可以彻底消解因没有全信而造成的恐惧:将神性降低、拉平到人性可与之对话、将心比心的地步,否则就要向他(上帝)索要无差别的同情和绝对意义上的公正。这种世俗化或“人化”策略似乎使狄金森的宗教主题诗歌离神性越来越远。
四、转向耶稣
狄金森的研究者们注意到她对圣子与对圣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并将其创作的大量狄式耶稣故事称作19世纪美国版新《圣经》[7]。在她的笔下,耶稣是位“绅士”(J1487)、“温柔的先驱”(J698)、“彬彬有礼的受难者”(J388)、头戴荆冠的“最高贵的”王或勇士(J1735)。他的仁慈与友爱对心怀恐惧的诗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在狄金森的耶稣故事里,没有像上帝题材诗歌里那样的杂音,而是更纯然的崇敬、倾诉和靠近。如前文所提到的向圣子祷告倾诉的需要,又如:
基督将会解释各个苦恼/在那座亮丽的苍穹教室。//……而我——对他的痛苦感到惊奇——/便会忘记那一点苦痛/尽管它此刻把我烤炙——把我烤炙!(J193)
一种仁慈如此普通——/我们几乎不再惊骇——/使最渺小的——/和最遥远的能够——崇拜——(J694)
没错,她的确使用了“教室”(schoolroom)一词,不知是否指涉的是诗人曾就读的霍山女子学院压迫性的宗教氛围。蒲隆先生此处所译“亮丽”的原文“fair”,也可理解为“公平的”“合理的”等。此外,这几个关键词或许更为重要:惊奇、痛苦、不再惊骇。“惊奇”于耶稣受难的惨烈程度(也许还有受难者的“甘愿”本身),备受某种煎熬的诗人暂时忘却了自己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那一点苦痛”(the drop of Anguish),虽然它正在现实地“把我烤炙——把我烤炙!”
这里,“惊惧”、危险或痛苦、一定的距离,三者皆已具备。我们可以从狄金森宗教主题诗歌中盘亘不去的“骷髅地”“十字架”等意象中感受到这一事件对于诗人心灵的冲击——“惊奇”到全神贯注,个人的苦痛暂时得到缓释。但另一方面,引起这种“惊惧”的事件并非源于惩罚,而是出于拯救、或以身殉难者的仁慈,所以诗人才能心定神宁地“凝神静观”,并在仰望的姿势使心灵得到升华。也就是说,由于对自己终有可能违背上帝意旨的恐惧无法感受到神的崇高性的诗人,在以世俗化或“人化”策略极力消解愤怒的上帝引起的恐惧之情同时,却在令人“惊惧”的耶稣受难事件、救世主出于拯救而非惩罚的仁慈的替罪行为带来的安全感,即“不再惊骇”的心理状态中感受到了神性的崇高,实现了从恐惧感向崇高感的转化。
[注释]
①括号内为狄金森诗歌编号。诗歌译文均来自蒲隆译《狄金森全集》(2014),编号为译者主要参考的约翰逊(Thomas H.Johnson)版诗歌编号,简写为J1。下文凡引用狄金森诗歌均同此例。
[1][美]阿尔弗雷德·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M].王柏华,曾轶峰,胡秋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美]艾米莉·狄金森.狄金森全集[M].蒲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
[3]Lundin Roger.Emily Dickinson and the Art of Belief [M].Grand Parids,Michigan/Cambridge U.K.: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8.
[4][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8.
[5]林新华.崇高的文化阐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25.
[6][英]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M].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36,50.
[7]刘守兰.狄金森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291.
The God and the Inexperienced Loftiness in the Works of Dickinson
XIANG Ling-l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2,China)
Dickinson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religion-themed poems,but she never joined in any religion.In term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oftiness and fear,we have found that Dickinson realized the loftiness of God but she couldn't overcome her fear which kept her in acquired knowledge and prevented her from shifting fear to loftiness.For the inexperienced-loftiness poets,the only way to remove this kind of fear is secularization or humanization.In substance, the fear to the God is a kind of fear to disobey the will of the God.Dickinson transferred from the sense of fear to the sense of loftiness in the frightening suffered cases happened to Jesus and in the humane substitutive criminals after forming lofty psychological elements:fright,danger or pain,certain safety distance.
Dickinson;the God;Jesus;loftiness;fear
I106.2
A
1672-934X(2015)05-0110-05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5.018
2015-08-25
向玲玲(1974-),女,湖南怀化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