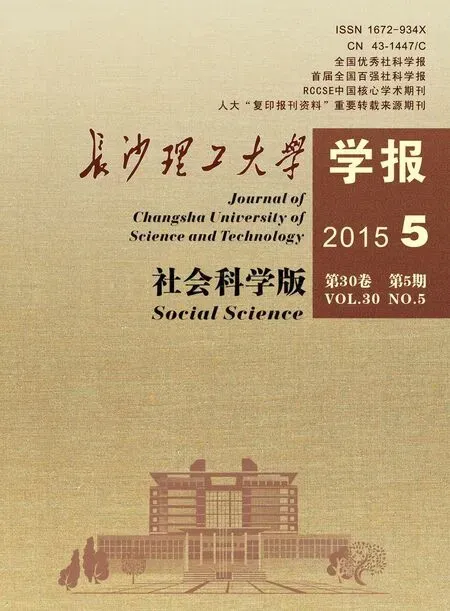在四月里如何谈论衰老
——西川《一个人老了》细读
2015-02-22李玫
李 玫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6)
在四月里如何谈论衰老
——西川《一个人老了》细读
李 玫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6)
《一个人老了》写于1991年4月,彼时作者的生理年龄与诗中感悟分别处于跨度相距较远的不同生命时段,由此在形成诗歌内在张力的同时,也使阅读必须面对在“四月”与“衰老”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问题由此被提出。对这种反差的成因分析是从文本的抒情节奏、抒情肌理以及价值立场与生命观等方面的异质特征切入,解读其在诗歌渊源上与博尔赫斯、聂鲁达等世界诗人之间的互文关系,进而追溯至作者西川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对阅读经验的习惯性倚重。
西川;衰老主题;知识分子写作
诗的写作时间是在四月。一个人为什么会在四月里突然想到谈论衰老?这个季节应该是草长莺飞春风拂柳的——除非他真的感觉到了老之将至。但1991年这一年作者西川28岁。28岁的西川何以会突然意识到衰老的存在,在无限春光里,一个28岁男性的世界不应该是长空浩荡大地无限地伸向远方吗?
两年零两个月之后的某一天,西川写下了他的另一首带着具体年龄刻度的诗《写在三十岁》。这在彰显诗人对时间的敏感之外是否暗示这个年龄段对其个人来说别有意味?从生命的刻度看,相对于与衰老之间的巨大跨度来说,此年龄显然应该是离青春期更近,但个体生命的感悟往往与刻板的生理时段切分并不同步。具体到这首诗中,在写作时间、生命状态和诗要表达的情绪三者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反差。这意味着,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春天里写一首谈论衰老和秋天的诗,这种反差使我们对诗歌本身产生隐隐的期待,这应该是一首有张力的诗,在生命的个性化感悟与生理时段的群体性刻板切分之间,在诗性与科学、生理与心理之间的张力。它不是一首老人谈老的诗,不是在秋天谈论秋天,不是在经验层面进行实时触摸和现场直播,它是超越的。因为超越而产生诗,如同一次挣脱地球引力而努力朝向相反方向的飞行,耳边有呼呼的风声。
诗歌乃至文学中从来不缺少对衰老的谈论,这是个体生命面对时间之流时对自我的体认,也是人类在浩渺的时空中遥相呼应的形而上的探索。老是什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和长者本位文化中,“老”一度是与经验和智慧之间呈现对应的,但在此后现代性进程的迅疾节奏中,衰老却因来不及更新而意味着缓慢与力不从心,意味着衰朽和被取而代之。而共和国文学长久以来的美学范式则是一路倾斜着驶向“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式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革命豪迈的激情范式,它和心甘情愿的牺牲相对接,用集体永存的慷慨宏大遮蔽个体消失的焦虑与虚无。它们和“螺丝钉”“铺路石”“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一起,共同组建了个体生命被悬置的集体美学。
那么,属于个体生命衰老的美学将走向哪里,成为西川的十字路口:轻车熟路意味着光滑顺畅疾驰而去荡起一阵尘土然后再四散着落去,无声无息;倘若寻找一条新路,则可能在一路披荆斩棘的推进中体验新的困境。西川没有选择,确切的说是诗没有选择,它时时需要新的打磨和擦亮。
一
诗作从中心/边缘、速度、高度、清醒度等方面来呈现一个衰老的个体面对世界时的感慨。
当世界被划分为中心/边缘时,“老”是随着身体的衰落逐渐被推向世界的边缘。衰老慢慢浮现:“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如此自然,如同烟的上升,如同水的下降。在万有引力的自然规律里,轻的自会上升,重的必要下沉,阴晴圆缺,生老病死。但这是一个黑暗渐渐走近的过程,头发变白,牙齿脱落,肉身渐次干枯。老了的生命像一则旧时代的逸闻,已然不能再吸引起读者的目光;或者戏曲中的配角,在时间的隧道里,从世界的中心渐渐后退,退到舞台的边缘,静待生命的大幕在某一天落下,灯光暗沉。首尾都是“一个人老了”,是循环,也像是一个封闭的结构,没有突围的出路。
如果换以速度作为比对的参数,以世界的正常运转速度为基本参照,则“老”是被世界的节奏所落下的,跟不上世界的节拍。仅从生理特征看,肉身在走向衰老的过程中呼吸和脉搏都是日渐缓慢的,老是慢一拍的节奏。如果“老”是季节,那个季节当是在秋天,时间在年度的三次轮换中渐趋收束,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秋收和冬藏都是收束的。秋露是凉的,这一季的节气中先是白露,后是寒露,露是秋天的水。北雁南飞,“落伍的”“熄灭的”“未完成的”都是在时间的节奏中慢一拍的,机器不再转动,是停滞的,青年恋人走远,远去背影留下的依然是被时间遗弃了的生命,飞鸟转移了视线,没有人会在停滞不前的物体面前一直停留。在西川的诗中,很多隐喻都是大有深意的,比如“鸟”:“鸟是我们理性的边界,是宇宙秩序的支点。……神秘的生物,形而上的种子。”[1]但在表层意旨的梳理途中,暂且不作深究也无妨。
倘是从生命高度的俯仰关系定位人与世界,“老”是站在时间累积的河床之上,俯视世界之川,于边缘处,在被落下之后。“所有掉进这河里的东西,不论是落叶、虫尸还是鸟羽,都会化成石头,累积成河床。”[2]生命在无数次的涨落累积里获得一个新的高度。时间累积也有它的收获,比如终于积攒了足够多的经验判断善恶,但是,随着衰老的降临,人生的轨迹也近乎完成,生命不会再有大的转机,需要判断和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机会和时间一样,如同指缝间的沙子滑落,而生命之门在次第关闭。夕阳西下,牛羊下山,关门闭户,等待一个结束和安息的夜降临。
换之以局内/局外的清醒度切分,则“老”是因为远和慢而得以清醒的旁观。时间把一个人从世界中隔离开来:个体生命在衰老时,整个世界仍在继续,如同一架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有人在造屋、绣花、下赌,各行其事,“生命的大风吹出世界的精神”,只有老年人能看出这其中正在遭受摧毁的时时刻刻,此处的“老”有着俯视的智慧和省察。
如同秋收之后是“冬藏”,衰老的尽头是与死亡衔接。一个人老了,徘徊在记忆的时光隧道里,随时要被淹没。无数的声音涌来,如同肉身终将挤进小木盒。游戏结束了,收拾好的尘世的一生:藏好成功、藏好失败,藏好写满爱情和痛苦的张张纸条,藏在房梁和树洞中……爱如流水,恨似浮云,一切都将归于大地。老了的生命不再有收获,也不再要摆脱。如同一棵在秋天里走向枯黄的植物,不会再有花开果熟,亦不会再有冲突和对抗,一切走向和解,走向生命的最初。老就是重新返回生命的最初,像动物那样,然后留下骸骨的坚硬。
二
诗中对于“老”的伤感和失落是淡而远的,表层文字中并不见沉重,这或者跟整首诗的抒情节奏直接相关。全诗是在三重不同的维度之间穿梭,以此生成它的悠远淡然的抒情节奏。
一重是自然现象:烟上升,水下降,秋天的大幕落下,露水变凉,雁南飞,大风吹起,落叶飘扬。在这一重维度中,所用意象都是淡远清凉的,是秋的萧素,像宋朝的山水画。
在西川的诗中,“秋天”一直是淡远安详的,他的另一首题为《秋天》的诗中,“大地上的秋天,成熟的秋天/丝毫也不残暴,更多的是温暖”,“甚至悲伤也是美丽的,当泪水/流下面庞,当风把一片/孤独的树叶热情地吹响”。在对西川诗世界的延伸阅读中,我们读懂了当他把“变老”和“秋天”对应时,诗的情绪何以呈现出如水般的淡远而清凉的质地。在另一首题为《黑暗》的诗中,也同样写到“但你举火照见的只能是黑暗无边/留下你自己,耳听滴水的声音/露水来到窗前”,“水”和“露水”一直在西川的“秋天”中反复出来。
当然,在浩渺的诗世界里,这样的意象并不带来原创性的陌生质地,它们在古典文学中曾不止一次的和我们对视过。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譬如朝露”“朝露待日晞”,在露与清晨对接的思维惯性中,原本是应该产生清新的质感的,但当其以“易干”的物理属性与时光的转瞬即逝相对应,则焦灼之感顿生。而在西川这里,露与暮色相伴,并与温度对接,夜凉如水,由此产生温度走低的审美质感;与之相应,在古典诗词里,“水”和“衰老”相组接时,是取其“流逝”之意,即在水流的速度和去而不返这一层面上使它和生命的衰老相叠合,“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奠定了这样的抒情思维图式。而在本诗中,水被使用,则是取其“重”,与烟的“轻”相对应,通过烟上升水下沉来对应自然衰老的不可抗拒。对自然之律的认可,代替了无能为力的恐慌。因而,尽管在意象的使用上,本诗与古典诗歌有重合和近似之处,但因为使用的角度和组接的层面的不同,新的意涵得以生成。
另一重维度是与身体相关的元素:目光、谈吐、头发、牙齿、骨头。在身体维度中,肉身的衰老呈现为“变少”,是生命在做减法。在纵贯全诗的身体维度中,衰老对应身体的变化:先是身心分离,“一个青年活在他的身体中,他说话是灵魂附体”;之后,“身体”开始置身于“昔日的大街”,并随时被落叶遮盖;最后,“整个身躯挤进一只小木盒”,游戏结束,仅存“骨头足够坚硬”。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以身体变化写衰老是其常见的抒情图式,其中尤其以“发白”和“齿稀”为普遍。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陆游《诉衷情》)等。“在白居易诗中,最常用的表现衰老主题的语言是‘华发’、‘霜毛’、‘白须’、‘雪鬓’”,以及“‘昏眼’、‘衰齿’、‘落发’”[3]等。西川的诗中承继了这一点,但在身体的生理性变老之外,写出肉身衰落之后与心灵的不同步,由此产生张力使衰老变得丰富和具有层次感
第三重维度是动作:看、说话、抓住、徘徊或停步。动作是个体生命和世界发生关联时的姿态,从“看”中所见的世界实则是对自身处境的省察。雁被从集体中拆散,从群体中析出意味着它不再是和天空和雁群一起在“南飞”中指称季节与时令。其中对“落伍”的强调,旨在突出在线性时间中的落后,是与衰老相对应的;而在古典诗歌中“雁”的离群并不与衰老相关,“孤雁”往往强调精神上的孤独感,不具有内在的时间元素。
跟“看”的视觉性相对,“说话”是语言表达,“抓住”是手部动作,而“徘徊”与“停步”则是通过足部动作实现对肉身的移动和控制。如果说第二重维度的身体还以肉身的静态展示为主,第三重维度则关注肉身的行动力与机能,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可能性。
倘是维度的单一,容易使情绪密集、深重和急促,但本诗有上述三重维度作为基本构架,诗的每一节,都是在三重维度间穿梭切换,抒情的力度和对身体的感知不断地被自然风物隔开,如同“看”“说话”和“徘徊”的动作不断地被天地之间的种种细节吸引,在影绰飘忽中且走且停,因而显出节奏悠然情绪疏淡。
三
在对抒情节奏的清点时,事实上已经开始接近对抒情肌理生成的追问。
从抒情肌理生成的影响渊源看,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点: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诗歌和汉译英诗。创作主体的个性化整合,以及由此生成的三种元素配比差异,是不同诗歌个性特征的生成机制。在抒情肌理的生成问题上,本诗首先是在对古典诗歌的接近与疏离中生成新的质感。西川自己说过,“请让我取得古典文学的精髓,并附之以现代精神。请让我面对宗教,使诗与自然一起运转从而取得生命。请让我复活一种回声,它充满着自如的透明。”[4]前述分析可以看出,西川诗歌中有大量曾出入于古典诗词的意象或隐喻,但在本诗的使用中却有了与既有传统不同的新的质地和光泽,在对核心主题“老”的呈现亦是如此。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呈现机制中,使这一话题与1990年代那场著名的诗歌争论产生对接。
在当代诗歌史上,西川的名字是和“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紧密相联的。“‘知识分子写作’乃特定称谓,它专指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臧棣、孙文波、张曙光、陈东东、肖开愚、翟永明、钟鸣、王寅、西渡、孟浪、柏桦、吕德安、张枣、桑克等人的诗歌写作”,“最早提出知识分子写作概念的是西川”[5]。在坚守思想批判的精神立场的同时,“知识分子写作采用与西方亲和互文的写作话语”,其中“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另一个是善用隐喻,行为怪诞的庞德”[6]。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论争中,不论是赞美还是否定,都是不约而同的指认西川和聂鲁达、博尔赫斯以及庞德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本诗而言,亦可发现抒情肌理的生成中有明显的异质渊源特征。
首先是隐喻的使用。《一个人老了》中有明显的博尔赫斯式的隐喻风格。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通常“以感叹死亡、病痛、美人迟暮、时光易逝为主的衰老主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主题之一”,而在衰老主题的意象选择中,集中体现在以“‘水’的流动性、不可挽回性与时间的同类性质相合”,或“以‘暮’、‘晚’、‘春’、‘秋’为核心的时间更替系列”,以此传达对生命不可避免走向衰老的叹息[7]。
如果说,中国古典诗歌中,“老”是通过物象的时间性予以确认的话,在西川《一个人老了》中,则更多是通过空间关系展示生命在时间中的渐次远离,其间有着明显的博尔赫斯式的异域质地。博尔赫斯乐于通过“迷宫”等隐喻探讨生命和时间的关系,而“迷宫”的物理属性恰恰是空间的,是空间的“交叉”与纷乱。与“迷宫”的隐喻相对应,西川的诗歌中用“街道”和“门”呈现个体和世界的关系,这在博尔赫斯的诗可以找到渊源与互文:《界线》中“有一条邻近的街道,是我双脚的禁地,/有一面镜子,最后一次望见我,/有一扇门,我已经在世界的尽头把它关闭”,在对个体与世界与时间关系的定位中,“街道”和“门”成为重要的物象。这种物象大量的出现在其诗歌中:“我的脚步遇到一条不认识的街道”(《陌生的街》),“时间残忍的手将要撕碎/荆棘般刺满我胸膛的街道”(《离别》),“还有那荒凉而又快乐的街巷”(《离别》),“时间中虚假的门,你的街道朝向更轻柔的往昔”(《蒙得维的亚》),“拥有庭院之光的街道”(《蒙得维的亚》),“我来自一座城市,一个区,一条街”(《DULCIA LINQUIMUS ARVA》),“今天曾经有过的财富是街道,锋利的日落,惊愕的傍晚。”(《维拉·奥图萨尔的落日》),“这是我所居住的一片街区:巴勒莫”(《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秘的建立》),“这些在西风里深入的街道/必定有一条(不知道哪一条)/今天我是最后一次走过”(《边界》),“这条街,你每天把它凝望。”(《致一位不再年轻的人》),“在南边一个街角/一把匕首在等待着他”(《阿尔伯诺兹的米隆加》),“有一条邻近的街道,是我双脚的禁地”(《界限》),“夜里一阵迷路的疾风/侵入沉默的街道”(《拂晓》)。
作为“一个只熟知街道、集市和城郊的城里人”[8],博尔赫斯诗中大量使用“街道”的意象,甚至街道成为感知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场域,“不要让任何人敢于写下‘郊区’一词,如果他没有长久地沿着街区的硬石地面漫步”;“多年来,我一直坚信我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富有传奇色彩,夕阳灿烂的街区长大的。”[9]对于空间场域中“街道”常与城市的关联,西川同样是有着自觉的体认和运用的,“城市的兴起是这样的:起初是贸易,……随后窝棚多了起来,有了街道、地窖、广场……”[10](P148)
与上述“街道”的隐喻相对应,博尔赫斯的诗歌中亦常以“门”呈现个体生命与时间和世界的关系:“有一扇门,我已经在世界尽头把它关闭”(《界限》),“某一扇门你已经永远关上”(《边界》),“宇宙是记忆的一面多彩的镜子,/一切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它艰巨的过道无穷无尽,/你走过后一扇扇门相继关上”(《Evemess》)等。这一隐喻习惯在西川诗歌中亦有回响,他多次写到的“门”,在隐喻意义上与之同质。如果说“一些门关闭了,另一些门尚未打开”(《写在三十岁》)对应的是生命与世界的阶段性关系——一些结束了而另一些可能开始,本诗中“门在闭合”则对应着与走向尽头的生命相对应的终极结束。
上述诸多中国诗歌传统中少见的隐喻方式使本诗在抒情肌理中呈现新的质感。
其次,在思维图式上,本诗亦与汉译诗的思维运转轨迹有相近之处。“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自高校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写诗之余都能做一点翻译。这种经历和境遇折射到创作中就有形无形地会利用翻译的便利,让外国诗歌中的一些语汇、语体驻扎进自己的诗里。”[5]比如在《一个人老了》和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11]之间,可以较为清晰地指认出艺术思维方面的互文性,其中开头部分的语言组接方式尤其相似:
(1)“在……之间”的短语结构。聂鲁达用了“在街道和大气层之间”“在春天和麦穗之间”,西川则是用了“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
(2)“像……”“仿佛……”等比喻的支撑功能。聂鲁达使用“好像一张未捕物的网”“像在一只掉落在地上的手套里面”“仿佛一钩弯长的月亮”,西川则用“像烟上升,像水下降”“像旧时代的一段逸闻”“像戏曲中的一个配角”。
在句式相似的基础上,以相近的思维图式进行组接,由此形成两首诗的基本相似的抒情纹理。所谓思维图式相近,是指诗意感受和诗意呈现的方式的相近。具体在这两首诗之间,体现为:将具体的意象置于能够产生张力的两种物象之间,但并不对物象本身予以描摹,而是直接用比喻呈现,在喻体中注入表意的因素,以此完成对诗意呈现的基本支撑。
从空旷到空旷,好像一张未捕物的网,
我行走在街道和大气层之间,
秋天降临,树叶宛如坚挺的硬币,
来到此地而后又别离。
在春天和麦穗中间,
像在一只掉落在地上的手套里面,
那最深情的爱给予我们的,
仿佛一钩弯长的月亮。
——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节选
一个人老了,在目光和谈吐之间,
在黄瓜和茶叶之间,
像烟上升,像水下降。黑暗迫近。
在黑暗之间,白了头发,脱了牙齿。
像旧时代的一段逸闻,
像戏曲中的一个配角。一个人老了。
秋天的大幕沉重的落下!
露水是凉的。音乐一意孤行。
他看到落伍的大雁、熄灭的火、
庸才、静止的机器、未完成的画像,
当青年恋人们走远,一个人老了,
飞鸟转移了视线。
——西川《一个人老了》,节选
“80年代以来,大量出现的汉语译诗,成为诸多诗人的模仿对象。诗语的欧化成为20世纪末汉诗诗语变化的主要倾向”[12],《一个人老了》中诗语的欧化特征和“译诗”风格,可以指认出清晰的影响路径,以及抒情肌理的生成机制。
四
此外,本诗在价值体认与生命观方面,亦有明显的异质元素。
在对诗歌史上“知识分子写作”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倡导者,西川的很多诗并不强调自我经验或者中国经验,更多来自于阅读产生的精神体验,这种经验有时来自本土与古典,但显然已走出更远。比如《厄运·E00一八三》[10](P116):
……
子曰:“六十而耳顺。”
而他彻底失聪在他耳顺的年头:一个闹哄哄的世界只剩下奇怪的表情。他长时间呆望窗外,好象有人将不远万里来将他造访,来喝他的茶,来和他一起呆望窗外。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发霉的房间里,他七十岁的心灵爱上了写诗。最后一颗牙齿提醒他疼痛的感觉。最后两滴泪水流进他的嘴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死时七十有三,而他活到了死不了的年龄。他铺纸,研墨,蘸好毛笔。但他每一次企图赞美生活时都白费力气。
此诗的主体框架看似源自《论语》,但其对生命的解读显然异于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此处节选的是在年龄上和“老”对应的部分,在儒家价值理念中,个体生命随着年龄增加而使智慧和自由也渐次获得,从“耳顺”到“从心所欲不逾距”,个体生命与世界的关系是随着时间的沉淀而趋于和解的。
但在这首《厄运》中,相对应的心理状态却是个体生命在面对时间时的悲凉与徒劳,是“长时间呆望窗外”和“每一次企图赞美生活时都白费力气”的怅惘。这一文本直观的体现了基于阅读的精神体验如何生长出新的诗歌体验。
相比较而言,《一个人老了》中的生命体验,更易于在西方诗歌中找到互文,如博尔赫斯的诗。关于“一个人老了”,博尔赫斯写过一系列的诗,对“老”作整体和诗性的展示,如《某人》《坎登,1892》《致一位不再年轻的人》等[13](P145,139,120)多首:
你已经望得见那可悲的背景
和各得其所的一切事物;
交给达埃多的剑和灰烬,
交给贝利萨留的钱币。
为什么你要在六韵步诗朦胧的
青铜里没完没了地搜寻战争
既然大地的六只脚,喷涌的血
和敞开的坟墓就在这里
这里深不可测的镜子等着你
它将梦见又忘却你的
余年和痛苦的反影。
那最后的已将你包围。这间屋子
是你度过迟缓又短暂的夜的地方
这条街。你每天把它凝望
——《致一位不再年轻的人》
其中“望得见那可悲的背景/和各得其所的一切事物”,写出了世事在时间沉淀中渐次清晰可见,与《一个人老了》中的烟上升水下沉一样,是世界图景在老年人眼中的呈现,是“有了足够的经验判断善恶”和“唯有老年人能看出这其中的摧毁”的清醒。在生命的征途中,看得见终点,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的清晰。“敞开的坟墓”“深不可测的镜子”“屋子”都和西川诗中老年人面对的未来世界图景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必然、不可知和吞噬性等质地。
咖啡和报纸的香味。
星期天以及它的厌烦。今天早晨
和隐约的纸页上登载的
徒劳的讽喻诗,那是一位
快乐的同事的作品。老人
衰弱而苍白,在他清贫而又
整洁的居所里。百无聊赖,
他望着疲惫的镜子里的脸。
已经毫无惊讶,他想到这张脸
就是他自己。无心的手触摸
粗糙的下巴,荒废的嘴。
去日已近。他的噪音宣布:
我即将离世,但我的诗谱写了
生命及其光辉。我曾是华尔特惠特曼。
——《坎登,1892》
“咖啡和报纸”与“黄瓜和茶叶”似乎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图景的中西版的互文和呼应,“去日已近”与“机会在减少”“一系列游戏的结束”都是在生命的标尺中看出“老”所在的刻度,叠放好一生的成败悲欢,是这一刻度应有的从容。而“快乐的同事”与老人的“衰弱而苍白”形成对照,正如《一个人老了》中将“老”与年青人的对比。“疲惫的脸”“粗糙的下巴”“荒废的嘴”都是写身体的陈旧和破败,尤其是“荒废的嘴”写出“老”之后生命与世界联结的某些机能的衰退,比如“表达”。
另一首《某人》,亦是把焦点稳稳的聚在“被时间耗尽”的“老了”的人:
一个被时间耗尽的人,
一个甚至连死亡也不期待的人
(死亡的证据属于统计学
没有谁不是冒着成为
第一个不死者的危险),
一个人,他已经使得感激
日子的朴素的施舍:
睡梦,习惯,水的滋味,
一种不受怀疑的词源学,
一首拉丁或萨克森诗歌,
对一个女人的记忆,她弃他而去
已经三十年了,
他回想她时已没有痛苦,
一个人,他不会不知道现在
就是未来和遗忘
一个人,他曾经背叛
也曾受到背叛
他在过街时会突然感到
一种神秘的快乐
不是来自希望的一方
而是来自一种古老的天真,
来自他自己的根或是一个溃败的神。
他不需细看就知道这一点,
因为有比老虎更加可怕的理智
将证明他的职责
是当一个不幸者,
但他谦卑地接受了
这种快乐,这一道闪光。
也许在死亡之中,当尘土
归于尘土,我们永远是
这无法解释的根,
这根上将永远生长起
无论它沉静还是凶暴,
我们孤独的天堂或地狱。
——《某人》
这三首诗涉及到与“老”相关的不同元素,而这些元素,与西川《一个人老了》对“老”的解读形成互文关系。其中“被时间耗尽”“连死亡也不期待”“感激日子的朴素的施舍”以及“回想她时已没有痛苦”等,都是生命与时间在不同层面关系的呈现,是在时间淘洗中泛出特定光泽,是“藏起成功,藏起失败”之后的从容与珍惜。
有意思的是,博尔赫斯的上述诗作是被收录在出版于1969年的诗集《另一个,同一个》中[13](P51),是晚年重新写诗时的作品,彼时,生于1899年的诗人已近七十岁。即便给写作和出版之间留有足够的时间差,写作这些诗作时,博尔赫斯也已真正进入到老年阶段,这应该是基于生命体验本身的写作。
而“知识分子写作”中,对阅读的信赖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个体生命的直接体验,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回答本文开头的提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何以在春天里谈论衰老:对于西川而言,衰老和生命的诞生与死亡一样,可能是个哲学命题,是人生话题,是文学命题,但却不一定是个体生命的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写作”通过对纯粹的形而上的问题的思索,使其避开或者忽略了个体生命体验的缺失。
[1]西川.远景和近景·鸟[A]//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44.
[2][巴西]保罗·柯艾略.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M].许耀云,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7
[3]王红丽.白居易诗中衰老主题的文化阐释[J].青海社会科学,2000(4):69-72.
[4]西川.艺术自释[J].诗歌报,1986(10).
[5]罗振亚.“知识分子写作”:智性的思想批判[J].天津社会科学,2004(1):90-96.
[6]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7(12):58-65.
[7]王红丽.白居易诗中衰老主题的文化阐释[J].青海社会科学,2000(4):69-72.
[8]罗佐欧.博尔赫斯诗歌中的隐喻艺术[J].柳州师专学报,2013(12):19-23.
[9]Peter Witonski.Borges of Pampas[J].National New York,Vol,XXV,No.9,1973(2):274.
[10]西川.远景和近景·城市[A]//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11][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聂鲁达集[M].蔡其矫,林一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29.
[12]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59.
[13][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诗选[M].陈东飚,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On Becoming Old in April:Intensive Reading on"One Become Old"by Xi Chuan
LI M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6,China)
"One Become Old"was written in April,1991,when the author's psychological age and his inspiration to the poem are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living periods with enormous span,which has formed internal stretching force in the poem,thus bringing its readers to the fierce contrast,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discussion is presented her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ve reasons begin with th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eatures of lyric rhythm and texture of the text, value standpoint,life view,and so on.This discussion interprets origi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oems by Xi Chuan and some world-famous poets such as Jorge Luis Borges,Pablo Neruda,furtherly tracing the habitual reliance of "intellectual writing"represented by Xi Chuan on reading experiences for their works.
Xi Chuan;theme of becoming old;intellectual writing
I207.25
A
1672-934X(2015)05-0095-08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5.016
2015-08-29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C-c/2011/01/12)阶段性成果
李 玫(1976—),女,江苏连云港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新时期文学、生态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