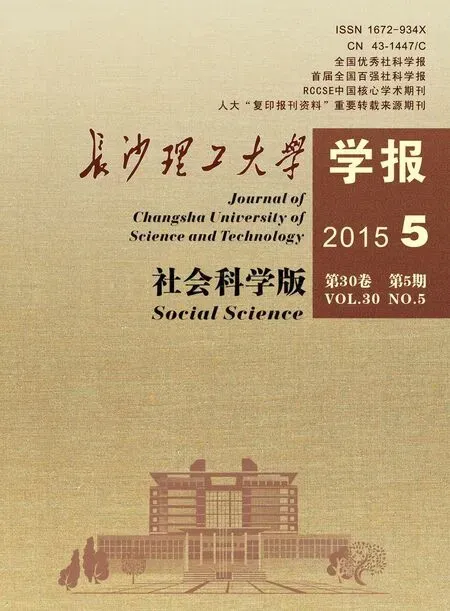自我与时代的心史
——重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兼及艾青的诗歌意义
2015-02-22贺仲明
贺仲明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100632)
自我与时代的心史
——重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兼及艾青的诗歌意义
贺仲明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100632)
“文革”后的诗歌史,艾青的地位呈现明显下滑趋势。这主要关联其诗歌特点与时代风尚的不一致:艾青诗歌强烈的时代和群体色彩及以抒情为中心的艺术风格,与当前诗歌界流行的个人性和知性特点存在较大冲突。但其实,艾青诗歌不是空洞群体思想的回声,而是将自我心灵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其时代声音中贯注着诗人真实的感情和感受。而且,抒情诗歌与知性诗歌各有所长,并不适合简单地臧否与取舍。艾青的名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典型体现出艾青诗歌的特色,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自我;时代
长期以来,在文学史界存在着所谓的“大我”与“小我”之争,也就是文学究竟应该属于个人书写还是时代书写。诗歌界的表现最为典型。如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近三十年间,是积极揄扬“大我”对“小我”横加挞伐的时代,徐志摩、李金发、冯至等以表现个人感情为主的诗人都被贬到边缘,郭沫若、贺敬之这样与时代关系密切的诗人则受到大力推崇,《凤凰涅槃》《雷锋之歌》等几乎成为诗歌的代名词。但是,8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诗歌几乎成了“个人”和“自我”的代名词,曾经被推至诗坛峰顶的郭沫若、贺敬之等时代性诗人遭受普遍的质疑和批评,完全远离诗坛中心。
然而,这种略显简单化的变换也许不应该是诗歌(文学)评价的正常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是片面的张扬时代和集体,还是极力地回归自我和个人,都存在极端化的缺陷。究竟以自我还是以时代为中心,只能是诗人(作家)的个人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完全可能呈现各自的特色,达到相应的高度。事实上,更普遍的情况是将个人与时代特征予以结合。特别是那些受到广泛好评的优秀作品,大都熔铸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因素。这些作品中既有真实的自我,又不局限于个人,它们能够在个人基础上透射出更广泛的关怀,呈现出更宽广的视野。
艾青的著名诗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是如此。这首广为人们传诵的诗歌,真切地传达了个人对民族、国家的深厚感情,又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土地的艰辛、苦难和奋争,可以说,诗歌所抒发的,既是自我的诚挚心灵,也是时代的沉重心史。这首诗歌虽然不被时下许多诗歌评论家所重视,但正如其中的名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一直为人所传诵,作品的价值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和认定。
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创作于1937年12月28日,正是中国抗战局势急剧恶化的时候。当时艾青刚落脚于湖北武汉,一个寒冷而带着雪意的冬夜,寒冷萧瑟的天气,家园沦丧和困顿生活的悲愤,凝成了喷涌的诗情,也造就了文学史上的这首名作。诗歌发表在1938年1月出版的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1939年1月收录在诗集《北方》中[1](P45)。
诗歌以“我”想象中的视角,细致地展现了一个中国北方冬天的雪夜,那些被日寇侵凌下的百姓生活场景。有“那从林间出现的/赶着马车的/你中国的农夫”,有“沿着雪夜的河流,/一盏小油灯在徐缓地移行,/那破烂的乌篷船里/映着灯光,垂着头/坐着的……”“蓬发垢面的少妇”,有“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异邦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尽管年龄、身份有别,但他们或漂泊无依,或颠沛流离,都遭受着侵略者的杀戮和凌辱,都处在生存的艰难和苦痛当中。正如评论家所说:“诗人对古国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穷人的形象,是使人禁不住感到伤痛的。”[2]诗歌中的这些百姓,既是真实的个体,也象征和代表着更广大的中国老百姓,代表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除了人的生存,诗歌还展现了更广阔的自然世界。在战争的阴影下,大自然也同样是阴暗而沉重的。除了“阴暗的天”,还有同样冷酷而无情的“风”,“像一个太悲哀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以及更辽远而抽象的生活画面:“透过雪夜的草原/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拥挤在/社会的绝望的污巷里,/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双臂”。这些画面,与前面描述的那些人物形象一道,共同构成了北方雪夜的整体图景,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沉重现实。这一切就如同诗歌的中心意象“雪夜”,既寒冷又沉重,静寂无声,却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让人苦闷、忧郁又无奈。诗歌中反复吟唱的主题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这一主题。
这样寒冷的冬夜,这样艰辛的百姓生活,诗歌的基调自然忧郁而沉重,它蕴含着诗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也体现了诗人的独特敏感。诗人深刻地洞悉到了战争中的苦难和沉重,认识到“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更传达出时代性的恐惧和迷茫,包含着对民族和未来的深深忧虑。这正如诗人对创作缘由的自我表白:“于是我在战争中看见了阴影,看见了危机。……我以悲哀浸融在那些冰凉的碎片一起,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3]
然而,尽管如此,诗歌却并不给人以绝望感。它忧郁沉重,但更促人思考和关注现实的艰难处境,以唤起更坚毅的勇气。而且,诗歌还蕴含着内在的向前的力量,让人产生对未来光明和希望的期待。这源于诗歌背后强烈的爱的情感基础。诗歌在描述雪夜中那些孤独无助的漂泊者和奔劳者的时候,不是置身事外,而是完全把自己当作其中的一员,把自己所经历的苦难进行坦诚地展示,表示出与他们同命运共患难的态度。“告诉你/我也是农人的后裔”“而我/也并不比你们快乐啊/——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的憔悴呀”。诗歌的结尾,诗人更将自己的写作与时代的苦难直接关联,进一步传达对时代的深切关怀:“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所以,人们在诗歌中,除了读到时代的苦痛,还可以感受诗人的温暖和关爱——这正显示了诗歌的独特价值。要求诗人像战士一样去冲锋陷阵是不现实的,要求诗歌一味做“子弹”和“投枪”也是得不偿失的短时功利。诗歌的意义正在于在苦难中表达温情,在痛苦中传达希望,以爱和希望的方式激励人们走出困境、走向希望。所以,虽然它不如稍后创作的《北方》那样在对历史英雄的歌吟中表达信心和希望,更不如更晚的《向太阳》《黎明的通知》一样以太阳、黎明等明丽的意象来传达对胜利的期盼,但是,这种将自己融入社会大众的感情更为具体切实,也更有感染力——对于这首诗歌所传达的感情和希望色彩,诗人显然感受很深,也颇为自信的。正如此,当诗人写完这首诗的时候,天气也很巧,真的下起雪来了,于是,他骄傲地对同行的友人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1](P46-56)
艾青是一个深爱祖国的人。他说:“如果一个诗人还有着与平常人相同的心的话(更不必说他的心是应该比平常人更善感触的),如果他的血还温热,他的呼吸还不曾断绝,他还有憎与爱,羞耻与尊严,他生活在中国,是应该被这与民族命运相连结的事件所激动的。”[4](P42)他的早期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真切地传达了诗人对乡人的深厚感情,对身份卑微的保姆,对与自己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保姆的子女们,诗人都充满着真诚的关切,抒发了对故乡土地、人民的真挚感情。抗战时期的艾青,颠沛流离,耳闻目睹了许多家破人亡的惨痛事情,以及惨不忍睹的人寰悲剧,强烈地感受着时代的压抑和压力,更强化了对故土、百姓的关切深情。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创作前的几天,当他听到家乡杭州被沦陷时,陷入极度悲愤的境地,以散文形式表达自己热爱家乡和悲痛的心情:“今天,我想念着杭州,我想念着,眼前就浮起了它(少时)的凄凉,我是极度的悲痛着,但我却不再流泪了。”[5]而在距离诗歌创作过去了四十多年后的1983年,艾青在回答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还说:“我对土地、家乡、穷苦人,总是充满同情。我写得《我爱这土地》,我把自己比作一只鸟,即使我死了,羽毛也要腐烂在故土上面。诗的最后,我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前一句也许有些夸张;这后一句,的确是发自灵魂的真音。”[1](P54)
正是这种真实而强烈的个人感情,使诗歌的时代抒写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特别的真切,诗歌中的“我”也同时具有了真实的艾青个体和时代抒情者的双重身份。从深层次上看,诗歌在思想情感上所具有的忧郁沉重和激人奋进的效果,正是来源于个人与集体、自我与时代和谐共振的关系。真实的自我感情,赋予了诗歌以强烈的关爱,而对时代的内在关切,又是真实自我情感的源泉。所以,诗歌既充盈着真实深切的自我情感,又传达出了时代的现实和精神状况,兼具真情的感染力和时代感召力。
正因为如此,著名诗人牛汉这样评价这首诗:“他的诗是艺术生命形态的生成和创造。语言不是简单的情绪的外化,而是与内在生命不可分割的,它整体地形成了诗的有声有色有形的搏动着的生命体。”[6](P133)确实,诗人的喉咙不能只为一己的哀乐而歌唱,如果这样,他的诗歌也就不能拥有更广泛的意义,不能被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读者只有在他的诗歌里读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或者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匮乏,才可能对之产生兴趣,被其所吸引。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既要是真实的自我——只有真实的诗人才能具有真情,才能感动人——同时又要是超越性的时代——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广泛的读者在诗歌中发现自己的生活,感受到自己的时代。所谓的“诗史”,都是如此!
二
艾青的诗歌艺术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新诗的集大成者,它融合了前人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也凝聚了“自由诗”和“格律诗”的某些因素。但也有批评家认为艾青的诗歌过于“散文化”,忽略了诗歌的音乐性特征。这一点,就像很多人评价倡导“自由诗”的郭沫若一样,认为他们对新诗发展方向有不好的引导。在这些人看来,诗歌离不开歌的韵味和音乐美的特征,如果失去了这些,就难以称得上是诗歌。
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形式,特别是对于自由与格律,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截然的定论。就上面从音乐性角度对新诗和诗人的批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笔者以为,诗歌确实不应该离开音乐性,但是音乐性内涵不应僵化固定,而是发展变化的,在变化中体现出新的音乐美。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诗歌的韵律上也给我们以启发。它虽然是散文的形式,但却绝对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化。它有一种贯穿性的情感,这种情感主导了作品的语言和节奏,也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韵律,而这内在的韵律正是我们许多自由诗所匮乏的。就像牛汉先生对艾青诗歌韵律的评价:“读艾青的诗(不仅指《北方》),我们仍能自然地读出它内在的有撼动感的深沉的节奏。艾青的自由诗,其实是有着高度的控制的诗,它的自由,并非散漫,它必须有真情,有艺术的个性,有诗人创造的只属于这首诗的情韵……”[6](P145)诗歌的音乐性既表现为外在的押韵回环,更应体现为内在意核、节律的贯通。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种音乐美,不只是技术上的原因,它更是思想和情感上的结果。也就是说,艾青诗歌散文化的形式特征和内在的节奏韵律美,在根本上来自于诗人对自我与时代关系的巧妙处理。
从时代角度考虑,为了再现时代的纷繁和复杂,以现代汉语的形式,是不可能采用那么机械的形式的,只有散文体的形式才能更充分地展示时代的状貌。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采用了异于古典意蕴却又非常典型的诗歌意象,它们完全来自于生活。如赶车的农夫,孤苦的少妇和老人……都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又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描画了“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的“中国的苦痛与灾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具体景象——也是诗人感受到的真实现实,也可以透过其背后去洞察更深远的大的背景。
但是,艾青的诗歌又不是一味地让时代来主宰作品,诗歌中始终有内在的主体感情为主导,统率着整个诗歌,因此,诗歌能够拥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整首诗歌的情感是完全的整体,对诗歌的朗诵,必须有贯穿性的情感,才能准确传达出诗人的情感和思绪。所以,在诗歌音乐性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说是为中国新诗提供的一个突出个案典范。关于新诗的形式,自由与格律争论各执一词永无休止。我想,大部分人能够形成共识的是,新诗确实不能完全“自由”,但也不可能真正以僵化的格律来规范它。闻一多“新格律诗”的实验失败,已经意味着表面格律化道路的终结。艾青的诗歌貌似无格律,实则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并且与内容融合在一起,既不生硬勉强,而且富有变化。他这种音乐美的效果其实并不逊色于各种新格律诗。比如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等,算是新诗史上比较有名的格律化诗歌,它们也确实显示了格律化的特色:或一韵到底,或每段用韵,都体现了对旋律化和节奏化的追求,也都因其音乐性特质而流传久远。艾青对诗歌音乐美的理解和实践方式与闻一多等人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都具有生动灵活的艺术效果。而且相比之下,艾青诗歌的韵律可以根据诗歌内容、情绪的需要进行自动的调整,更为自然多样,方法也更灵活,富有变化。这不是说艾青的诗歌形式就一定可以作为新诗典范和方向,但是,它的成功至少能够为新诗形式探索提供很好的启迪。
三
在今天的文学背景下,谈论艾青的诗,似乎有些逆时代潮流的意思。当前诗歌界流行的,是奥登、艾略特以及其他的欧美现代诗人,即使偶尔谈到中国新诗,主流也是穆旦、冯至、李金发,最多还有一个戴望舒。曾经在文学史上很辉煌的郭沫若、徐志摩,已经早被弃之若履了。艾青的遭遇也基本相似,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与一些朦胧诗人闹翻之后,主流诗歌群就基本上将艾青作为落伍者的代表,最近三十年间,艾青在诗坛的地位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这其中有因为政治或文学观念所导致的情绪化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诗歌观念方面的变化。其一是前面谈到的个人与时代关系。近年来个人写作成为潮流,艾青、郭沫若等诗歌中较强的时代气息不符合这一潮流,自然难以被人青睐。其二是对诗歌主旨由抒情到哲理的偏重。在传统诗歌观念里,抒情是诗歌最重要的要素,但近年来,在西方现代诗歌观念影响下,人们对诗歌主旨的侧重有很大变化,抒情受到贬斥,思想成为诗歌的首要要素。传统的浪漫主义诗人基本上退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以哲思见长的诗人,知性诗歌成为最受推崇的类型。中国现代诗歌方面,穆旦、冯至、卞之琳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曾经辉煌的郭沫若、艾青等。
从诗歌观念看,随时尚的发展而有所变动是很正常的事,或者说这是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必需过程,只有经过时间和风尚的反复淘洗,才能留下真正的珍宝。但是,完全以时尚作为文学的评判标准,也难以沉淀真正的经典,它们更需要客观全面的辨析。
其一,需要对个人感情与时代感情有所区分。诗歌当然要以个人真情实感为基础,只有情感真挚,才能具有感人的力量。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一己情感,不能将之升华与拓展,诗歌的境界、格局始终会受到局限。只有将个人情感与更广泛的社会关怀结合起来,才可能达到更高的文学境界,实现更高的价值意义。一个诗人在创作中需要思考:诗歌究竟是为什么而写作?也许存在着一些为自己写作或为未来写作的诗人,他们也会在一定的潮流中被认可、被追捧,但是任何在诗歌史、文学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诗人,都必须首先在自己的时代深深地刻下印迹,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这样他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历史的空间。能够与时代如此之紧密地联系,铸就了艾青诗歌的内在魅力,也是抗战时期文学的宝贵遗产。
笔者以为,只有将个人和时代和谐统一、将个人情感予以时代性和人类性升华的诗歌,才是最有价值的诗歌。艾青说过:“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4](P45)显然,他是以之作为他诗歌创作的追求目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正是从“小我”的真诚和深切出发,却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创痛,表达了难以排遣的民族苦难和生存苦闷,以及对未来、对自由难以遏制的渴求,它是将自我与时代融合和升华的杰出作品。
其二,诗歌中的思想和情感的地位问题也应该更全面地分析。的确,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界,存在着抒情泛滥、虚假的情况,而思想的厚度也会增加诗歌的深度意义。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诗歌,情感的力量从来都不应该缺失。事实上,真诚、坦率、质朴的感情,特别是蕴含了更广泛内涵的感情,也是有感染力、穿透力的。建立在真实生活感受基础上的抒情诗歌自有其魅力。诗歌针对的主要还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往往与具体的人、生活密切联系。所以,我们不宜将抒情或思想作为诗歌发展中相互割裂的两种方向,而是应该以更宽容和丰富的态度对待它们,促进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
特别是就中国诗歌传统来说,保持自己的抒情个性,使其往深远处发展,也许更有意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充分体现了抒情的真诚和质朴。它没有丝毫的炫耀和玄虚,而是将自己与农民等同,心灵相连,感情朴素而真切。在诗集《北方》的序言中,艾青写道:“我是酷爱朴素的,这种爱好,使我的情感毫无遮蔽,而我又对自己这种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很久了,我就在这样的境况中写着诗。”[7]
为了更好地比较诗歌的个人与时代、知性诗歌与抒情诗歌的特色和意义,我们可以选择抗战时期著名诗人冯至的著名作品《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来与《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比较。冯至的诗歌重视哲理性和个人性,他的诗集《十四行诗》近年来广受推崇,《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是其中流传最广泛的一首。全诗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慧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它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冯至的这首诗歌确实意蕴深沉,它致力于对抽象的生命和哲学意义问题的深邃思索,富有思想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而且,其诗风内敛,感情深藏在意象和思想的背后。不过,就与时代的关系看,这首诗歌体现得不是很明确,诗歌几乎完全融化在个人的思想世界里,与时代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也难以在诗歌中感受到当时的战争背景和时代氛围。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风格与之完全不一样,其沉重深切,浓烈的时代气息和个人感情传达,体现的是另一种诗歌趣味和艺术追求,它更容易为人理解、接受,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性的感染力。两首诗歌属于知性诗歌与抒情诗歌的不同典型,其思想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诗人都关注时代,但可以期待所有诗歌都真诚,都有比自我更深远的关怀。同样,我们可以喜欢艾略特、穆旦、冯至那种充满知性和理性光辉的诗歌,但也不会忘记普希金、聂鲁达和艾青这样优秀的抒情诗人。诗歌的殿堂本来就应该是丰富的、多元的,而不应该是单一的、狭隘的。特别是从抗战的特殊时代背景上看,我们更应该看到艾青诗歌方向的意义,在民族危难的时期,沉湎于个人世界显然是对于自我责任的逃避,关注时代也正是关注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深重的民族危难中走来,也必将更长久地融化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文学中。无论在任何时代,这样的作品都不会失去其经典意义,也不会丧失其深广的感染力。
[1]叶锦.艾青年谱长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五)[J].新文学史料,1985 (2):27-35.
[3]艾青.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A]//海涛,金汉,编.艾青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167.
[4]艾青.诗与时代[A]//艾青.诗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42,45.
[5]艾青.忆杭州[A]//艾青.艾青全集(5)[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6.
[6]牛汉,郭宝臣.艾青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7]艾青.北方·序[A]//海涛,金汉,编.艾青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82.
Mind History of Ego and Era:Rereading"Snow Falling onto Chinese Land"and Ai Qing's Poetic Meaning
HE Zhong-m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100632,China)
As a poet,Ai Qing's prestige obviously glided down in the poetic history after Cultural Revolution,which resulted from the inconformity between his poetry and the prevailing vogue:Ai Qing's arts style in the poetry with strong era and group color as well as lyrics as the center largely conflicted with the current poetic individualism and intellectuality at that moment.As a matter of fact,Ai Qing's poems were not the ego of the hollow group,but the fusion between ego soul and era spirit.And the era of sound concentrated on poet's real feeling and motion.What's more,both lyric poetry and intellectual ones had their own advantages,which was not proper to comment and to take or reject.Ai Qing's masterpiece"Snow Falling onto Chinese Land"typically performed his writing features in poetry, and its historic status was non-ignorable.
Ai Qing;"Snow Falling onto Chinese Land";ego;era
I207.25
A
1672-934X(2015)05-0089-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5.015
2015-08-27
贺仲明(1966—),男,湖南衡东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